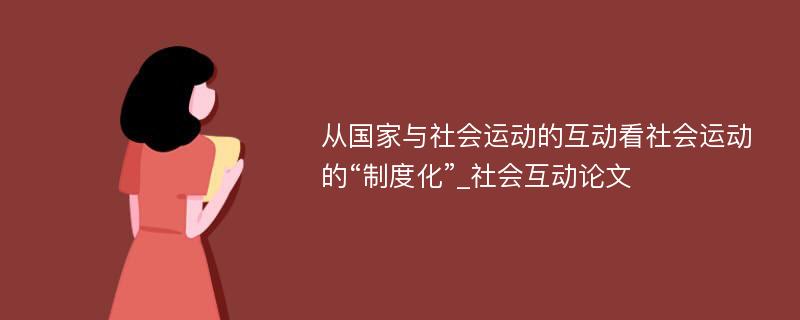
从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看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互动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运动”是群众自发表示各种抗议或诉求的集体性行动。它们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产生各种影响。因此,社会运动始终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由来已久,尤其是上个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较为密集地爆发了新社会运动之后,这一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社会运动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或部分制度化日益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西方学者的目光也因此日益集中在“制度化”这一趋势上。
一、社会运动“制度化”的两个层面:运动自身的变化与国家政治系统的开放性
一般意义的“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的模式转化的过程,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表示个人、组织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程度以及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制度化”强调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组织或制度自身从非正式到正式、从不健全到健全的发展过程;其次是组织或群体的行为、生活方式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过程。
具体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解释。
马克·G.朱格尼(Marco G.Giugni)和佛罗伦萨·帕西(Florence Passy)将社会运动制度化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社会运动通过与国家或政党的协商,允许社会运动传播信息、发表意见以及进行政策提议;其次,社会运动通过整合而被赋予某些执行政策的责任;最后,社会运动通过代表授权来进行决策和实施。②据此,我们可以将社会运动归纳为协商—传播阶段、整合—执行阶段以及代表—决策阶段。
大卫·S.迈耶(David S.Meyer)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的“运动社会”(Social movement society),主要也是基于欧美国家大部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现状。在他们看来,制度化是指创造一种可重复的、根本上可以自我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相关的行动者都可以诉诸已有的、熟悉的常规。社会运动制度化包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常规化(routinization)——挑战者和当权者都有共同的“剧本”(script)可遵守,能够辨识熟知的行动模式以及潜在的危险变化;包容及边缘化——愿意遵守常规的挑战者可以获得在主流机构进行政治交换的渠道,反之则不然;吸纳(cooptation)——挑战者将通过不破坏常规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其诉求及策略。③
也有研究者将社会运动向政党或压力集团的转变称为制度化,比如安东尼·奥伯肖尔(Anthony Oberschall)就认为,对于社会运动而言,成功意味着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组织、公众意见以及政府将社会运动视为部分支持者的合法代言人,并更好地承担实现运动目标的重任。“制度化”意味着社会运动自身失去了作为运动的特征,转变为压力集团,被吸收进入政党或者与能够代表运动支持者利益的公共机构结成联盟。④这一定义强调社会运动较之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地位,获得了体制内的、常规化的利益代表及实现途径。
同样,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也认为,“制度化”意味着社会运动组织(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MO)向政党和利益集团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主要包括SMO资源来源的稳定、内部组织的发展、目标的现代化、行动剧目(action repertoire)的常规化以及SMO被吸纳进入现有的利益调节机制中。⑤但是,也有学者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与社会运动向政党和利益集团转化严格区分,将后者定义为“转化”。⑥
上述几种关于社会运动“制度化”的不同定义都蕴含着同一逻辑主线——国家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社会运动自身在行动方式、组织结构等方面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社会运动行动剧目的常规化。⑦有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关键指标是集体行动方式的转变”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社会运动:1768—2004》一书中考察了社会运动在西方的发展史,其中涉及社会运动剧目的演变。18世纪60年代以前,在特定的节假日、葬礼、教区聚会上举行集会或者有组织的工匠和民兵在自己的节日里举行游行等方式就已经存在,但是这些方式并没有被模式化,也缺乏可迁移性。后来,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议会改革、公民政治权利的扩大,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逐渐稳定下来。到19世纪时,社会运动的剧目形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与旧有的直接行动多数与暴力相伴随相比,此时的社会运动大多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进入20世纪之后,政府当局对公民的游行、示威、公开集会等权利持更为开明的态度,相关政策、法律也更加灵活和更富弹性,运动参与者与当局的关系也发生了明显改变。
约翰·D.麦卡锡(John D.McCarthy)和克拉克·麦克菲尔(Clark McPhail)对比了1968年和1996年美国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警方和抗议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上个世纪的后30年里……公民抗议已经成为政治过程的常规组成部分,它所传达的信息被视为选举、请愿、游说等试图影响政府政策和实践的合法补充;同时,抗议者和警方反复使用的行动剧目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已经制度化、常规化,变得可以预测……”⑨当时,华盛顿特区几乎所有的抗议都采用集会、游行、罢工、守夜以及资料分发的形式,后三种方式(构成了抗议示威的大多数)主要由很小的团体使用,这些方式很少会涉及抗议公民的不服从或者警方与抗议者之间任何形式的暴力对抗。总体而言,西方国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剧目已经常规化,这也就意味着其可预测性的增强。极端、暴力的行动方式虽未完全消失,但已经大为减少。
其次是社会运动组织和结构的变化。麦卡锡和麦克菲尔在对美国社会运动的考察中指出,社会运动制度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运动组织自身的变化,即它们像当局一样倾向于抗议事件的可预测性和有序性。例如,社会运动组织日益职业化,越来越多地雇用全职的经理人而不是依赖志愿者领袖;同时,更多的社会运动组织愿意成为国家正式注册的非营利组织,这样它们就可以使用美国的国家邮件系统,降低联络成本;另外,注册也可以保证那些给予运动团体财政支持的人获得税收利益。
关于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是否一定采用正式组织的形式,西德尼·塔罗认为,对于社会运动而言,最有效的组织形式不是全部采用正规的组织形式,而是“部分立足于自发的、根植于一定的背景中的地方团体,这些团体一般通过联系结构连接在一起,并由正式组织来协调”⑩,即兼有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身份,其中前者发挥着协调作用。
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在对法国、德国以及美国的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从理论上区分社会运动、政党以及利益集团是比较容易的,但现实中往往很难将三者区分开来。鲁赫特认为运动组织有三种基本模式:草根模式、利益集团模式和政党取向模式。这三种模式在社会运动内部都会有所体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相比较而言,法国的社会运动倾向于政党取向模式,美国的社会运动则较为明显地体现为利益集团模式,而德国则是较为均衡地体现了三种模式。(11)
第二,国家政治系统逐渐开放。
这实际上涉及社会运动同制度化政治的关系,学术界对此看法不一。在蒂利的分析范式中,社会运动被严格限定为体制外的“挑战者”角色,他强调社会运动是一种体制外的、非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它与政党政治、竞争性选举等有着明确的界线。
但是杰克·A.戈德斯通(Jack A.Goldstone)等人则认为,社会运动除了反映民众对政府和政策的态度、充当发泄不满的途径、确立政治议题等作用外,还与常规的政治参与方式紧密交织在一起,推动国家政策甚至机构的变更,因此不应该将社会运动排除在制度化的政治手段之外,社会运动是对其他政治参与形式的补充,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他们进而提出了“跨越制度化政治与非制度化政治”。(12)其实,对西方民主国家而言,大多数的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或部分制度化了。制度化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总量增加了,但是破坏力和冲击力却下降了(13),社会运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规范政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即便是蒂利也认为,抗争、政治权力以及制度、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存在于独裁政体和动荡的转型政体之下,同样存在于“稳定的民主制国家中那些看上去更为常规的政治生活中”(14)。
二、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双重动因:国家的塑造、吸纳与社会运动的战略选择
关于制度化的动因,学者往往都会提及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寡头统治铁律”。米歇尔斯认为,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最终都必将走向寡头统治的结构。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成员的增多,正式建制的扩展和分化,组织领袖更需要通过对知识、信息以及组织内部沟通渠道的特权来垄断对整个组织的控制,与此相对,普通成员对于参与决策过程越来越没有兴趣,对组织的直接影响力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在米歇尔斯看来,寡头统治是任何现代组织都无法摆脱的“宿命”。(15)寡头铁律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却是研究政党、官僚政治、代议制民主以及社会运动等问题的学者都会提及的论断。
以工人运动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运动,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有着较为严密的等级结构,米歇尔斯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及社会民主党的考察,总结出了寡头统治的铁律。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被纳入现有体制的:第一,工会组织成为常规政治领域内利益调节的制度安排,利用开放的制度化渠道伸张诉求;第二,工人运动的行动剧目日益制度化,比如,在有些国家,罢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合法的行动方式;第三,工人运动经历了被纳入政党的过程,进而使得运动在政党结构内部得以维持并对政策发挥持久的影响。(16)
20世纪60、7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似乎打破了上述铁律。新社会运动标榜新的抗争形式,主张反官僚化、反等级制,强调个人主义,倡导个性解放,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甚至没有统一的领导者和纲领。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挑战了常规的制度化政治。(17)但是,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学者发现新社会运动也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逐渐被现有体制所吸纳,其最初要求建立未来新社会的主张也日渐转化为在现有体制下的完善与修复。于是,有学者认为,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再次应验了,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步骤:一是社会运动组织内部的集权结构的组织化形成;二是通过组织结合进国家政治体系中。
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他们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置于抗议周期和浪潮之中。塔罗在对19世纪40年代末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组织及其与无政府主义对抗的研究中发现,欧洲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存在制度化趋势与破坏趋势二者的对立。后续的发展和研究也说明,这种对立在后来也依然存在,而且会不断重现和再生。20世纪60年代的运动就验证了这一点,当时的民权运动大多已经制度化了。塔罗在研究中发现,制度化往往始于抗议周期的高潮,但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规模破坏性的活动方式并未消失。主张寡头铁律的学者认为,正规的组织是必需且不可避免的;而主张抗议周期的学者则认为,社会运动的正规组织呈现出周期性的起伏跌宕,反映了运动潮流和情绪的变化。(18)抗议周期理论还认为,制度化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不是最终宿命,而是暂时的,会随着抗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克里西等学者在考察西欧的新社会运动时,也将制度化置于抗议浪潮中加以考察。他们认为,在抗议浪潮中,制度化是趋势之一,但其他的新社会运动则不一定遵循此趋势。克里西等人,认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同激进化趋势一样,是抗议浪潮内部相互作用的产物,至于二者谁占上风,取决于政治精英同抗议兴起的关系的变化。除了精英的战略之外,有些国家为新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提供了有力的结构性因素,比如瑞士。(19)显然,在抗议周期中解释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更能反映出制度化的动态过程,以及推动制度化的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既有政治系统提供的结构性机会吸纳或稀释了社会不满。比如大卫·S.迈耶在研究美国的社会运动时说:“美国的开国之父所设计的政治制度通过‘补选’新的组织的利益阻止了激进主义的产生。这鼓励了社会运动的产生,同时也限制了其潜力。”(20)迈耶以冻结核武器运动为例,分析了美国政治制度应对社会运动的方式。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反映了麦迪逊式的通过分裂政治权力来处理不同政见的战略,这样的结构为一些挑战者提供了相对容易的制度化渠道以及常规政治参与的舞台,以此来分裂、吸纳、消散社会运动。迈耶将这种分裂和消散划分为边缘化、去政治化及制度化,并分析了冻结核武器运动是如何被分化、部分被制度化,并导致运动最后沉寂的。(21)这实际上就是克里西所谓的社会运动体制化的结构性因素,这种结构性因素体现了国家政治系统吸纳社会运动的能力。无论是寡头铁律式的解释还是周期式的解释,都认为制度化是社会运动按照某种预定的路径发展的必然结果或必经阶段。
然而,社会运动不是完全被动地制度化的,即制度化另一方面的动力源自社会运动本身的战略选择,它们会主动作出调整以便进入体制内。除了对现有体制和当权者提出挑战之外,社会运动也会主动选择与国家合作。尤其在复杂的现代社会,政策的执行、公共问题的解决等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寻求同国家合作的活动对于被定义为抗争性政治的社会运动来说,成为日益重要的补充形式。女权运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它们一直在寻找制度化的渠道,从而可以从体制内影响国家。女权运动的组织同当局合作,共同寻找解决不公平或性别歧视问题的出路。新社会运动在寻求与国家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或部分实现了制度化。社会运动本质上的抗争性决定了它同国家的合作带有冲突性,这种“冲突性的合作”体现了社会运动在制度化过程中,一方面想要寻求和借助制度化的渠道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尽量保持同国家的距离,从而可以保持自身的特点。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看,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有些运动更容易同国家建立合作关系:首先,运动所提出的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这些议题不会对当局产生直接的、根本性的挑战,从而使得当局比较容易接受;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性较强的议题,比如环境保护等,会令当局需要运动组织的专业意见。这样的运动比较容易同国家形成合作关系。其次,具有官僚化、职业化、高度结构化等特点的运动组织更倾向于寻求制度化的渠道,因为这同其内部组织的特点比较吻合。最后,温和的运动较激进的运动更容易为国家所接受。(22)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社会运动同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因此,如果社会运动试图寻求制度化的渠道来发挥影响,往往会按照有利于制度化的要求进行组织和动员。
社会运动为了更直接地影响国家决策,或者为了更充分地利用资源及机遇,以抗衡对抗性运动和其他竞争性运动,也会寻求同政党建立战略联盟。例如,在美国历史上,通常农民、反共产主义者以及宗教右翼组织等发起的社会运动同共和党联系紧密,而民主党则倾向于吸收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等发起的社会运动。(23)同政党建立密切关系是社会运动实现制度化的重要渠道之一。
制度化不是社会运动被动接受的宿命,而是国家和社会运动互动的结果。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会制度化,即使是某一种社会运动也不一定会实现全部的制度化,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实现了制度化。所以,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是有筛选性的,影响这种筛选性的因素来自国家和社会运动两个方面。
三、“制度化”对社会运动和国家的双重影响:关于社会运动后果的争议与对国家能力的考量
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制度化对社会运动来说是有害的,因为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意味着运动自身丧失了作为社会运动的基本特征和形式,从最初自愿、松散的组织形式逐渐发展为职业化、官僚化的组织;它们对常规政治的挑战及对现有社会的替代性方案也不复存在了。制度化不仅使运动的行动和目标更为温和,还有可能使运动由于转向常规政治而日渐退出抗议舞台,从而逐渐褪去激进的色彩,对现有秩序的扰乱与破坏性也逐渐减弱。在制度化的过程中,社会运动有不断被边缘化的趋势,制度化往往意味着社会运动的衰落。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化对社会运动而言并非坏事。因为制度化并不等同于运动被现有体制收编,也不必然导致运动的边缘化、去激进化以及动员的减弱(demobilization)。专业组织的介入并不只意味着将运动纳入体制内,还可以动员更多的人。而且即便是制度化了的社会运动,也可以在与当局合作和保持运动自身特征之间保持平衡。它们通常懂得在常规与非常规的集体行为方式之间摇摆,甚至可以二者兼有。(24)社会运动进入常规政治舞台,可以利用体制内政治提供的机会结构施加自己的影响。制度化为社会运动以一种更常规、更稳定的形式在决策、执行等环节中发挥影响提供了渠道。总之,不应该简单地将社会运动的制度化等同于被现有体制收编或运动失败。
从对女权运动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关于制度化对社会运动影响的分析存在分歧。爱波斯坦·芭芭拉(Epstein Barbara)在对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研究中指出,美国女权运动在制度化的同时也被边缘化了,尤其在第二次浪潮中,尽管出现了大量的活动团体、正式组织来争取和维护工作女性及有色女性的权利,但是基层的草根活动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公众对女权主义的感知主要受由行政人员主导(staffrun)的组织的影响,而这些组织大多关注的是中上阶层支持者的利益。这些变化确实有助于女权主义意识在大众中的传播与扩散,但同时也使得女权主义从一项声势浩大的运动逐渐沦为一种观念。(25)琼·艾克(Joan Acker)和赫斯特·爱因斯坦(Hester Einstein)则认为,女权主义的衰退是由于财富和权力的极化,以及右翼势力的增强,这些因素使得女权主义的反对势力增强。从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发展来看,制度化对于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推动女权主义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制度化并不像爱波斯坦·芭芭拉所认为的那样导致了女权运动的沉寂。(26)
制度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实质上涉及衡量社会运动成败与结果的标准问题。如何界定社会运动的成败及结果,直接决定了如何看待制度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威廉姆·A.甘姆森(William A.Gamson)曾经从两方面对社会运动的成功进行界定:一是接受,主要是指在多大程度上,挑战群体被其目标所接受,成为一系列合法利益的有效代表,这关系到挑战群体作为一个组织的命运;二是新的优势,主要指挑战群体的支持者能否在运动中及运动过后获得新的优势,比如其目标的实现。之后,甘姆森又将其细化为:全面反应(full response)——同时获得接受和新的优势;吸纳——被接受,但没有获得新的优势;先占(preemption)——获得新的优势,但没有被接受;崩溃——既没有被接受也没有获得新的优势。(27)
后来,学术界在对甘姆森的定义进行借鉴和修正的基础上,开始从社会运动对政治过程和结果所产生的因果影响入手考察其成败和结果。从宏观的结构层面看,运动主要的潜在影响包括对民主权利与实践的扩展、新政党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从相对中观的层面看,运动会促使相关政策发生变化,从而为该运动的支持者提供持续的获益、增强集体认同等。(28)这样将决策过程进行分解,有助于更清晰地考察社会运动的政治影响;同样,基于这种对社会运动结果的考量标准,制度化也就很难被认为是社会运动衰落甚至失败的标志。因为,制度化正是研究社会运动是如何影响乃至进入决策体系,成为合法的利益代表以及决策者的。因此,衡量社会运动结果的标准不同,对制度化给社会运动带来的影响的看法也就不同,而这归根到底又源自对社会运动的不同理解。如果像蒂利那样严格地将社会运动限制在体制外,那么制度化无疑意味着运动的衰落;而如果像戈德斯通等学者一样,打破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政治之间的界线,把社会运动视为民主制有效运行的要素之一,制度化则是社会运动继续发挥影响的方式之一。实际上,在西方国家,社会运动未必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与常规政治参与方式泾渭分明。
另一方面,社会运动能被制度化反映了制度自身的弹性以及面临挑战时的稳定性。出现社会运动的社会是否稳定,关键在于它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在现实中,国家、社会运动与民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时至今日,社会运动成为“趋于集中发生在民主制度下的东西”,而且“强能力的民主政权”造就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社会运动(29),而将社会运动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国家和政府的能力。
在《集体暴力的政治》、《欧洲的民主与抗争(1650—2000)》以及同塔罗合著的《抗争政治》等著作中,蒂利都论及了政治制度的两个方面——政府能力以及民主明显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暴力性质和强度。他根据这两个维度将国家分为: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低能力的非民主国家、高能力的民主国家以及低能力的民主国家,进而考察不同性质的政体对集体行动暴力程度的影响。
克里西等人通过国家分化结构、体制结构、主导战略以及联盟结构四个因素的设定来分析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四国不同类型运动的动员情况及行动技能的影响。其中,国家分化结构指的是四国传统的社会分裂,例如阶级分裂、中心—边缘分裂、宗教分裂以及城市—农村分裂。作者认为,“突出的传统分裂对于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是有相当的限制性的”(30),同法国相比,传统分裂不那么突出的德国、荷兰和瑞士的新社会运动的动员有更多空间。
体制结构和主导战略是作者引入的政治机会结构中的因素。前者是指有形的体制结构,比如国家中央集权的程度以及国家权力分离的程度。作者将国家的结构系统分为三种:议会舞台、行政舞台以及直接民主舞台,以此来分析四个国家通道的开放性以及社会运动行动能力的强弱。主导战略是指事关挑战者的无形的程序或支配性的战略,分为包容和排他。将行动能力的强弱和战略的包容与排他相结合,就可以将考察的国家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例如软弱的包容、强力的排他或者居中状态等。软弱的、包容的国家产生了一种动员水平高但行动技能非常温和的社会运动;强力的、包容的国家,总体动员水平较低,但是非常规的甚至暴力的形式相对较多。
联盟结构是指各国中左派力量和政府中有无左派。比如新左派与老左派的力量构成、左派是在政府之中还是政府之外等,都会影响新社会运动的动员。
上述影响社会运动动员的因素可以延展至对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研究中。由此,可以归纳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运动制度化能力的三个层面:性质层面——政体的性质直接影响了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和方式;结构层面——基本的体制结构、社会的分化结构以及联盟结构等直接决定了社会运动制度化实现渠道的开放性;关系层面——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运动组织同当局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了社会运动得以制度化的社会土壤。这三个层面主要是就国家而言的,从社会运动角度而言,社会运动制度化的实现不只是国家体制结构对运动的规制与约束,同时也是运动自身的战略选择和需要,社会运动自身的诉求主题、组织结构都会影响其被制度化的可能性和程度。因此,社会运动制度化是运动组织的微观层面和国家体制结构的宏观层面结合的结果,是国家的约束和社会运动的战略选择互动的产物。
对于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理解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制度化是社会运动发展的趋势之一,但不是唯一趋势。不是所有的社会运动都会被“制度化”,也不是某一种社会运动会被完全制度化。如果想要建立一种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理想模型,那么通常会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会获取某种进入主流政治和文化的渠道,但是却会限制其诉求的范围;第二部分则基本上放弃进入主流政治机构发挥影响的前景,转向更基础的工作,致力于培养清晰的观念和认同,这是一种潜在的影响;第三部分则会放弃或者不再重视运动的主题,而是转向关注其他问题,个人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31)这三部分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第二,制度化并不意味着社会运动完全丧失了其反叛的特点,而是更多地反映了社会运动同制度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正如塔罗所说,社会运动同制度化政治之间的交汇在欧美国家表现得都很明显。社会运动未必像其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截然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但也不会完全被引诱进制度化政治之内,而是处在“门口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the gate),在政体的边界运行,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其战略与动力中包含了含糊与矛盾。(32)
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运动制度化的经验事实及研究成果,有助于正确看待各种社会运动或群体事件的出现,并制定正确的政策予以规避或加以引导。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都会面临各种问题和矛盾,在转型期如何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维护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美发达国家以其发展时间及程度上的领先,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教训。
注释:
①《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
②Marco G.Giugni and Florence Passy,"Contentious Polities in Complex Societies:New Social Movements betwee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in Marco G.Giugni,Doug McAdam,and Charles Tilly,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8,pp.81-107.
③David S.Meyer and Sidney Tarrow,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21.
④Anthony Oberschall,Social Movements:Ideologies,Interests and Identities,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3,p.31.
⑤Hanspeter Krisie,"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a Political Context",in Doug McAdam,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Political Opportunities,Mobilizing Structures,and Cultural Framing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52-184.
⑥何明修:《社会运动制度化:以台湾环境运动为例(1993—1999)》,中研院社会所“组织、认同与运动者:台湾社会运动研究”小型研讨会论文,2001年6月21日。该文不属于国外研究现状,但是此处有所涉及,所以稍有提及。
⑦社会运动的“常备剧目”,诸如为特定目标组成的专项协会和联盟、公开会议、依法游行、集会、示威、情愿等政治行为方式的随机组合。见[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4页。
⑧Patricia L.Hipsher,"Democratic Transition as Protest Cycles: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Democratizing Latin America",in David S.Meyer and Sidney Tarrow,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p.153-172.
⑨John D.McCarthy and Clark McPhail:"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e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S.Meyer and Sidney Tarrow(eds.),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Contentious Polities for a New Centu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p.83-110.
⑩[瑞士]汉斯彼得·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4页。
(11)Dieter Rucht,"The Impact of National Contexts on Social Movement Structures:A Cross-Movement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in Doug McAdam,John D.McCarthy and Mayer N.Zald,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Political Opportunities,Mobilizing Structures,and Cultural Framing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5-204.
(12)参见[美]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
(13)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4)[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
(15)参见[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Marco G.Giugni,"Social Movements and Change:Incorporation,Transformation,and Democratization",in Marco G.Giugni,Doug,McAdam and Charles Tilly,From Contetion to Democrac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s,INC.,1998,pp.XI-XXVI.
(17)Offe Claus,"New Social Movements: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Social Research,Vol.52,1985,pp.815-868.
(18)[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73页。
(19)[瑞士]汉斯彼得·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4页。
(20)See David S.Meyer,The Politics of Protest: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30.
(21)See David S.Meyer,"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the End of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Sociological Forum,Vol.8,No.2,1993,pp.157-179.
(22)Marco G.Giugni and Florence Passy,"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mplex Societies:New Social Movements betwee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in Marco G.Giugni,Doug McAdam,and Charles Tilly,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1998,pp.81-107.
(23)See Mildred A.Schwartz,"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Movements and US Political Parties",Party Politics,Vol.16,No.5,2010,pp.587-607.
(24)David S.Meyer and Sidney Tarrow,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Contentious Politics for a New Centu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23.
(25)Barbara Epstein,"What Happened to the Women's Movement?",Monthly Review,May 2001,Vol.53,No.1,pp.1-13.
(26)Barbara Epstein,"Response to Acker and Einstein",Monthly Review,Oct 2001,Vol.53,No.5,pp.53-55; Joan Acker and Hester Einstein,"What Happened to the Women's Movement-An Exchange",Monthly Review,Oct 2001,Vol.53,No.5,pp.46-49.
(27)William A.Gamson,"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Change",in Marco G.Giugni,Doug,McAdam and Charles Tilly,From Contetion to Democrac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s,INC.,1998,pp.57-77.
(28)Edwin Amenta,Neal Caren,ect.,"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10,pp.287-307.
(29)[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3、71页。
(30)[瑞士]汉斯彼得·克里西等:《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32—166页。
(31)See David S.Meyer,The Politics of Protest: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30.
(32)Sidney Tarrow,Strangers at the Gates-Movements and State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