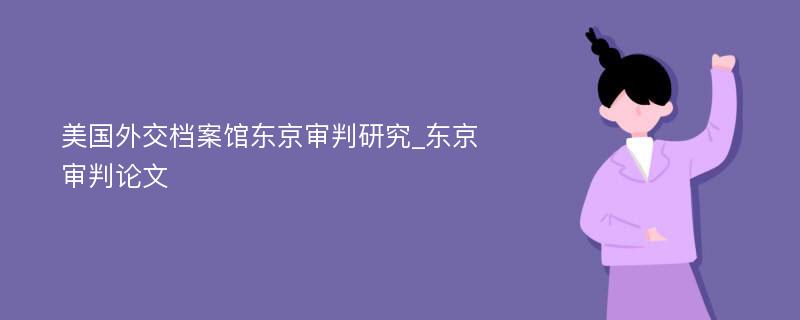
美国外交档案中有关东京审判的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京论文,中有论文,美国论文,外交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5)20-0012-11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为落实反法西斯盟国有关处置日本的政策主张提供了前提条件,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惩罚日本战犯,也是盟国有关处置日本政策发展的逻辑必然,《波茨坦公告》明确宣布:“应该对所有战争罪犯实施严厉法律制裁。”①通过审判战犯这种法律手段来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则进一步明确了人们对于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后果的预期,这对于维护战后和平、构建亚太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东京审判都是国内外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进行错误的历史观教育,以及日本右倾化日趋严重,加上日本某些人企图对东京审判进行翻案,因此,有关东京审判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这些有关东京审判的学术成果、研究视觉也非常多样化,或者法学的,或者历史的,或者国际关系的。考虑到东京审判时美国独占日本的特定背景,因此,对东京审判中美国因素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很重要。我们批判美国言行前后不一、违反国际法、违背肩负的国际责任,但是美国对现实纷争所应负有的国际法律责任和义务究竟如何形成的?这种历史形成的美国应负的国际法律责任到底是什么?体现在哪些文件中?如果我们用美国人自己的材料分析是不是说服力更强?是不是更能加强我们主张的公信度?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发掘更多有利于支撑我们主张的证据材料?美国相关的档案资料和外交文件已经公布,但国内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的成果还没出现。鉴于学术界研究现状,本文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外交档案文件,对东京审判中有关国际法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论述,以求教于学界。 一、确定溯及既往日本战争犯罪的时间 法不溯及既往是一个基本的法治原则,毋庸讳言,“二战”后对战犯的法律制裁打破了这一法律原则,如同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曾如此评述法律中的“溯及既往”:“法律很少有纯粹的溯及既往,而不纯粹的溯及既往的法律是人们可以容忍的。”②如果现在还有人利用所谓“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来争论、怀疑甚至否定“二战”后对战犯的审判,那只能说这些人是别有用心了。阿库斯特也曾就此述评道: 即使《纽伦堡法庭规约》的某些规定确实是溯及既往的立法,国际法上也没有反对溯及既往的立法的一般规则。的确,溯及既往的立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不公平,但是,谁要是以为正义竟然要求在纽伦堡的人应该无罪释放,那么,这个人的正义观念实在太古怪了。不管怎么说,在将来的案件中,再也不可能抱怨立法的溯及既往了,因为,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已为未来树立了先例,而且《法庭规约》所规定的原则和法庭的判决后来都经联合国大会和国际法委员会批准了。③ 日本战争犯罪起算时间直接关系到之后东京审判中所适用法律的溯及既往多长时间,是之后拟定战犯名单并实施抓捕的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工作,也是讨论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二战”结束前,盟国在准备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已经被提起,1944年11月28日,在重庆召开了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远东与太平洋分委员会(Far Eastern and Pacific Sub-commission)的组建会议,王庞惠被选为分委员会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由荷兰和澳大利亚提出了以在中国开始的那场战争为时间起算点问题,这一问题并被提交至在伦敦的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④美国非常重视重庆分委员会的工作,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Hurley)提议艾奇逊(George Atcheson,时任驻华使馆参赞)出任分委员会的候补代表(alternative representative),在赫尔利不能出席会议时代表其出席。赫尔利认为,虽然重庆的分委员会仍然处在组建中,还没有涉及特别重大的问题,但美国必须维持其有常任代表出席的地位。⑤ 1945年1月5日,在重庆分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在中国开始的哪场战争作为时间起点的问题再次被提出。伦敦的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还没有最终确定,但赫斯特(Cecil Hurst,伦敦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英方主席)在给王庞惠私人信件中建议对此问题作“初步讨论”,当时只有战争罪行中国委员会(crimes Chinese Commission)已经考虑将1937年作为起算时间。澳大利亚人认为,绝对不能让那些自1937年7月之后对在中国发生的极端残忍、无法用言语表述的暴行负责的日本战争罪犯逃脱法律制裁,虽然在中国的战争是一种“没有宣战”的。这种暴行不仅针对中国人,更波及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认为除非将1937年7月8日作为战争开始的时间,否则分委员会的作用将被极大削弱。我们应该支持中国人的在这方面的观点,并作为一种一般政策(general policy)。⑥ 1月16日,代理国务卿格鲁(Grew)致电赫尔利,表示美国的立场是远东战争起始自1937年7月7日,美国将会推动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尽快做出决定。⑦2月5日举行的重庆分委员会会议决定向联合国家战争罪行委员会作出建议:重庆分委员会将中日战争的开始时间固定在一个确切的时间点是没有必要的,应该充分考虑每个事件的性质。澳大利亚代表宣称其政府认为分委员会没有权力将战争犯罪时间延伸到1941年12月之前。鉴于中国的反对和伦敦委员会的程序,伦敦委员会决定将1937年7月7日作为战争开始的时间是不明智的,显然美国人又支持了伦敦委员会的这一立场。⑧鉴于澳大利亚代表发表声明称其政府不反对分委员会处置1941年12月之前的日本战争罪行,伦敦委员会在2月7日的会议上决定建议重庆分委员会不要将其工作局限于某个时间点之后的战争犯罪,应该根据案件的性质进行工作。⑨ 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SWNCC)太平洋与远东分委员会(SWNCC's Subcommittee for the Pacific and Far East)1945年9月12日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10月2日得到协调委员会的批准。其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甄别、逮捕和审判战争罪犯嫌疑人的草案”明确规定: 追究战争犯罪没有必要被限制在某一个特定时间之后,以使有关责任方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一般情况下,案件的追溯时间应该自1931年9月18日奉天事件,或者在此前的一段时间。考虑到战争犯罪案件发生的集中程度,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算起似乎更为妥当(The preponderance of cases may be expected to relate to the years since the Lukouchiao incident of July 7,1937)。⑩ 二、战犯名单 战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者进行法律追究,这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共识。反法西斯盟国受到日本侵略的程度是不相同的,所以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也会出现差异。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名单的确定,实际上也是盟国之间互相协调统一的过程。作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两支主要力量——中国和美国,在日本战犯甄别的问题上配合协调对于东京审判的最后成功非常关键。 (一)中国提交的日本战犯名单 在日本还没正式投降,遭受日本侵略巨大苦难的中国在制订日本战犯名单方面就已经行动起来,重庆分委员会于1945年7月27日提出了一份大约包含100名日本军人的战犯名单,这是分委员会提供的第一份日本战犯名单。而且,中国国家办公室(Chinese National Office)已经组建并有效运作,战犯的甄别工作被期待将加速进行。(11)重庆分委员会在8月3日再次罗列了另外的30名日本军人作为战犯。(12)赫尔利就此评价道,在中国国家办公室6月成立之前,重庆分委员会的工作是缓慢的,但自从国办有效运作以来,分委员会迅速提交了一份战犯名单,7月27日拟订了第一份战犯名单,至今已经形成了342名的战犯名单。9月7日,在重庆分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罗列了82名具有显赫地位的日本主要战犯,包括这些臭名昭著的人如山下奉文(Yamashita)、本间雅晴(Homma)、土肥原(Doihara)、寺内正毅(Terauchi)、松井石根(Matsui)和本庄繁(Honjo)。犯罪事实和证据材料已经国办提交给了分委员会。(13)这是首次在战犯名单中列出具体的战犯姓名,显然是以举例方式列出,而不是完整战犯姓名的列举。 1945年10月20日,中国向美国驻华使馆递交一份经蒋介石批准认可的包含土肥原(Doihara,Kenji)、板垣征四郎(Itagaki,Seishiro)、东条英机[Tojo,Aiki(Hideki)]、影佐祯昭(Kagesa,Sadaaki)等12人的日本主要战犯名单。中国询问美国政府对这份日本主要战犯名单是否有异议,如果没有,中国政府将请麦克阿瑟逮捕拘留这些日本主要战犯。(14)1946年2月11日,中国外交部再次向美国驻中国使馆转交一份包含有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广田弘毅、松冈洋右、东乡茂德、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21名战犯名单,这是中国递交给美国的第二批日本主要战犯名单。中国还强调除了谷正之(Masayuki Tani)已经向中国投降,小矶国昭(Kuniaki Koiso)被报道已经自杀(美国档案中注:其人并没有自杀)外,其他罪犯大部分已经被逮捕,中国外交部将此名单递交司令部以调查每个案件,抓捕那些还没有被逮捕的罪犯,依法对他们进行处理。(15) (二)美国的日本战犯名单 如果说中国在甄别遴选日本战犯问题上动作迅捷的话,那是因为中国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但美国在提名日本战犯名单上也是毫不延迟,个中原因当然有美国也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国之一的因素,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战后独占日本,试想如果不通过法律途径审判这些战犯,宣告这些人的罪行,宣布这些也是使日本自身处于深重灾难的罪人,那么,美国独占日本的合法性从何而来?当然美国战后独占日本,也必然担负重要职责,其中之一就是提名日本战犯名单。表现在美国外交文件中,美国人提交了多批次的战犯名单。 1945年8月16日,参谋长马歇尔(Marshall)向麦克阿瑟(MacArthur)发出指示,其中讲到战争罪犯名单正在准备中,会尽快提交。战犯的甄别和逮捕暂时执行盟国在德国战败后的做法。(16)8月23日,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给驻英大使怀南特(Winant)发电,其中说主要日本战犯名单正在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准备中,将发给麦克阿瑟。这份名单仅限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即1945年8月8日签订的《伦敦协定》第6条所表述的A级战犯。(17)1945年9月14日,美国国家战争罪行办公室发给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的战犯名单包括了45名日本主要战犯嫌疑人,并且特别说明这份名单不是完全的而是可以增减的。(18)9月14日,发往东京的日本战犯名单,实际上包括两份,一份是日本战犯总名单,一份是日本主要战犯的特别名单。这些名单已经陆军部、海军部和国务院批准认可。(19)虽然这份战犯名单上的具体姓名没有在外交档案中公布,但美国在准备日本战犯名单方面是毫不迟疑的。而且随着美国全面占领日本的完成,战犯名单的甄别遴选工作已经转至驻日盟军司令部。 1945年10月5日,盟军最高司令的政治顾问艾奇逊(Atcheson)在给国务卿的电报中,提及由麦克阿瑟司令部提供的两份日本战犯名单,一份上面注有时间9月28日,另一份上则是有10月2日的调整名单(这份名单包含有不同国籍的56名战犯名单),两份战犯名单的具体姓名在档案中都没有公布。1945年10月11日,艾奇逊在致国务卿的电函中又附录了另外15人的战犯名单。(20) 如果说这几批美国拟订的日本战犯名单在美国外交档案中都没有列举出具体姓名的话,那么1945年11月12日艾奇逊提交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就包含有13人的战犯名单并附有个人简介,这是美国国家战争罪行办公室在国务院的帮助下拟定的。(21)11月15日,艾奇逊再次转交麦克阿瑟第二份含有22名日本主要战犯嫌疑人的名单,并附有简介。艾奇逊认为,这些都是日本的显赫人物,美国已经掌握了可用的证据,这些人应该被立即逮捕。(22) 持续的战犯甄别抓捕工作给日本政府内外的政治人物带来不小压力,增加了日本政治气氛的紧张,也不利于战后日本社会的稳定,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显然不利于美国稳固其对日本的占领。所以早在1945年12月11日艾奇逊就向麦克阿瑟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建议说,可以口头告知日本首相或者其他日本政府适当官员,但不做具体承诺,就驻日美军当局来说,以反和平罪指控主要战犯嫌疑人的工作大体上已经完成。(23) 三、抓捕战犯 抓捕战犯是东京审判前所必需的准备工作,但日本战犯的抓捕是在两个前提下进行的,一是美国独占日本,二是根据《波茨坦公告》,所有日本武装力量及其民事机构必须撤出北纬30度以南地区,即撤回其本土。所以,如果说战犯的甄别遴选除美国之外其他盟国还可以积极提名的话,那么,抓捕日本战犯、至少是大部分战犯只能由美国完成了。美国独占日本是以反法西斯盟国的名义进行的,因为只有如此,美国的这种独占日本的行为才能获得足够的合法性,但美国在享有这种权利的同时,为盟国抓捕战犯则是其肩负的重要义务之一。 (一)美国有关战犯抓捕的考量 应该说,抓捕战犯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看似一种法律执行行动,但实施抓捕时必须充分考虑时机的把握、局势的预判和后果的评估等因素。 日本战犯的抓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谁是战犯,必须要有个确切的“战犯”定义。1945年11月6日艾奇逊向麦克阿瑟提交一份备忘录,其中就谈到美国当局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中言词宽泛,概括而不具体,以致他无法确定谁是美国政府或是盟国政府想要起诉的。以致美国驻日当局抱怨道,如果我们以不明确的“战犯”的名义去抓捕或监禁了一些人,结果发现我们没有事实材料对抗他们,最后是不经审判而加以释放。如此的举动会为将来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它违背了现有的法律和国际法规则。除了一些概括性的指示外,麦克阿瑟没有任何行动的基础,而这些指示却不能为整个抓捕工作提供充分的指南。(24)虽然如此抱怨,但美国人对于直接侵害过美国利益的那些战犯嫌疑人,则是没有这些顾忌的,如抓捕木户幸一(Marquis Kido),美国认为作为天皇玉玺的管理者在推选东条为首相时所处的立场,以及在珍珠港事件后其仍任职于政府,这些已经足以使其承担发动对美国、英国、荷兰战争的责任。(25) 美国认为抓捕战犯的行动应该很快进行,其原因美国人是如此分析的:第一,美国占领日本和日本的非武装化已经完成,建议可以考虑对战争罪犯嫌疑人实施抓捕。日本人民直到当时还没有严重不利于占领当局的反应,民众已经接受了被认为会对其造成很大心理冲击的事件,如天皇屈服从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前首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的被捕;天皇最近造访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要求言论自由包括讨论天皇等。第二,日本民众已经表现出寻求改革和变化的动向了,他们此时不再抱有幻想,民众对那些误导他们并给国家带来灾难的那些人进行了广泛的公开的批评,日本人民期待美国当局逮捕更多的嫌疑人,大多数民众不反对这种逮捕。但这种态度不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由于民众经济上苦难的加重,特别是快要到来的冬春季节,一部分对抗不可避免地转向美国占领当局,因此,从日本民众的角度对大部分日本战犯嫌疑人实施抓捕越快进行越好。第三,美国人已经觉察到,日本政府内外的许多温和的政治领导人处于犹豫状态中,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列为战犯嫌疑人。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如果逮捕时间拖延过久,被列为嫌疑的人会重新进入政治领域,等到他们走向公职或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础,那时再进行逮捕,我们必然会遭受批评。(26)抓捕战犯行动越早完成,那些担心自身是否与战犯相牵连的高官要人会越快地平稳下来,这有利于他们对战后日本的改革做出贡献。 美国制定了具体的抓捕策略,认为抓捕战犯方面慎重行动也是必要的,制定一个抓捕被列为战犯的高官的具体方案是可取的,在短时间内完成抓捕工作,在抓捕行动之间留有充足时间以观察民众反应,视情况再决定加快还是推迟这一行动。东久迩稔彦(Higashi Kuni)是天皇之下最高级别的官员,他的逮捕也为其他日本高官的逮捕铺平了道路。(27)另外,美国一般不直接进行抓捕战犯的行动,而是指令并监督日本政府行动,这样既避免了与日本人的正面冲撞,也为自己的抓捕行动留下回旋余地。如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逮捕11月13日提交给他的13名战犯嫌疑人,除板垣征四郎(Itagaki)和山田乙三(Yamada),据认为他们不在日本国内。(28) 对日本一些位居要职的战犯嫌疑人的抓捕,美国给予了充分的政治评估。虽然还有争论说逮捕近卫文麿(Hidemaro Konoye)会对现政府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媒体上对他和其过去政策的广泛批评已经表明这种影响不会是负面的。他的身份问题以及他与天皇的紧密联系,以致他的逮捕是否会引起天皇的战争罪责的问题,正如日本媒体所表明的那样,政治责任在于天皇的顾问们,而不在天皇,因为天皇仅仅是在按照顾问们的建议行事。如果像近卫这种政治经历的人可以逃避战犯嫌疑人的正式审查,而且还在继续参加政府性质的重要活动,是完全不合适的。(29) 美国抓捕战犯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那些挑起对美战争的日本高官,即使没有参与,哪怕仅仅当时在政府中任职,也必须绳之以法,严厉惩罚。除了后文提到的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东条英机时期内阁的所有成员外,艾奇逊作为驻日美军司令部重要成员曾经向国务卿辩解,因为驻日当局由于没有逮捕已经建议应当逮捕的东条英机内阁的6名成员,八田嘉明(Hatta Yoshiaki)、汤沢三千男(Yuzawa Michio)、石渡庄太郎(Ishiwata Sotaro)、野村直邦(Nomura Naokuni)、重光葵(Shigemitsu Mamoru)和山崎达之辅(Yamazaki Tatsunosuke)而遭到批评,但实际情况是,要起诉整个东条内阁成员,除了野村直邦(Nomura Naokuni)外,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对他们的逮捕和起诉。(30) (二)逮捕战犯 1945年9月11日,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以东条为首的包括珍珠港事件时整个内阁成员的39名战犯嫌疑人,包括本间雅晴(Masaharu Homma)、黑田重德(Shigenori Kuroda)、铃木启久(Colonel Suzuki)、桥本欣五郞(Colonel Kingoro Hashimoto)。10月15日,逮捕包括沢田研二(Kenji Sawada)等3人,(31)因为他们与处决上海附近杜立特飞行中队(James H.Doolittle,詹姆斯·杜立特陆军准将,以他为首的飞行中队曾于1942年4月18日轰炸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本土)3名飞行员有关。10月22日,逮捕铃木内阁的内政大臣安倍源基(Genki Abe)。盟军驻日司令部法律部发言人于10月22日宣称,太平洋地区要被审判的战犯嫌疑人总数达到4000人。11月17日,日本政府被命令逮捕并移交包括荒木贞夫(Sadao Araki)、本庄繁(Shigeru Honjo)等11名主要战犯嫌疑人。(32)这些人被认为对1931年、1937年、1941年侵略事件负主要责任,他们和之前已被捕的以及将来被抓捕的那些人将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33) 作为驻日司令麦克阿瑟的政治顾问艾奇逊在向国务卿汇报战犯抓捕情况时这样说道: 1945年11月13日向司令官建议逮捕13名战争罪犯嫌疑人,11月16日再次建议司令官逮捕22名嫌疑人,11月27日再转给司令官二份主要战犯嫌疑人名单,并分别有嫌疑人简介,其中一份名单包括二人,这二人分别是藤原(Fujiwara)和中岛(Nakajima),建议现在立即进行抓捕,第二份名单只含一个人,即米内光政(Yonai),其应该因为反和平罪而受到审判,因为1937年他是海军部长,而正是在那时中国被攻击,日本的海军飞机轰炸了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因为违反战争法和战时习惯法特别是海牙公约第1条而应该受到起诉,建议在将来合适的时间再进行逮捕。我们的前三份名单包括了美国战争罪行办公室所列举的所有嫌疑人,这些人还没有被逮捕,所有不利于他们的证据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然而我们得知,被战犯办公室列为战犯嫌疑人的伏见宫博王子(Prince Fushimi Hiroyasu),报道称其去世了,但仍然活着,虽然病了。关于阿部信行(Abe Nobuyuki),我们被告知其已经被逮捕,但实际上是逍遥法外。根据可靠消息,木村兵太郎(Kimura Heitaro)、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和寺内寿一(Terauchi Hisaichi)在缅甸或马来西亚的英国人手中,山田乙三(Otozo Yamada)在满洲(Manchuria,中国东北)俄国人手中,建川美次(Tatekawa Yoshitsuga)、阿南惟几(Anami Korechika)、末次信正(Suetsugu Nobumasa)和杉山元(Sugiyama Gen)已死亡。土肥原贤二(Doihara Kenji)已于9月23日在日本被捕,武藤阿基拉(Muto Akira)已被控制在菲律宾,多哥茂德(Togo Shigenori)被软禁在东京。(34) 虽都没有公布名单,但美国外交档案记载,驻日美军当局分别在1945年12月1日、11日拘捕了两批日本战犯嫌疑人,计57人;同年12月3日、15日又分别指示日本政府逮捕8名和69名战犯嫌疑人并移送巢鸭监狱(Sugamo Prison),这些人都被指控对联合国家的国民实施了残暴和攻击行为。(35) 驻日美军当局还于1946年1月17日指令日本政府逮捕并移交110名战犯嫌疑人,包括7个将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将军中的5个人,即和知鹰二(Wachi Rakaji)、矶谷廉介(Isogai Rensuke)、酒井隆(Sakai Takashi)、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和谷寿夫(Tani Hisao),包括在1945年10月由驻中国大使馆转交给美国政府的中国外交部所列的12名日本主要战犯嫌疑人名单中。中国的12名战犯名单,其中9人已经由美国驻日部队逮捕或命令逮捕,本庄繁(Honjo Shigeru)在1945年11月在被命令逮捕后自杀,板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和喜多诚一(Kita Seiichi)分别被英国人控制在新加坡和被俄国人控制在满洲(中国东北)。(36) 四、天皇的处置 如果说确定日本战争犯罪的起算时间、甄别遴选战犯以及实施抓捕,其中虽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总体上应该还是法律属性的事情。而天皇的处置则更多的是政治利益的盘算,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法律与政治的冲突,但最终还是独占日本的美国在政治上的权衡决定了天皇的处置。 作为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害的中国人民在处置天皇的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也迫使美国尽快明确其立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The People's Political Council)于1945年7月17日通过一份决议,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这样评论道,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当地媒体中出现一种舆论,支持拥护将天皇作为战犯的立场,所以在重庆分委员会中将天皇列为战犯的问题可能会被提出,美国驻中国使馆需要了解国务院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以为美国代表采纳。(37)8月4日,驻华大使赫尔利再次询问国务卿在天皇问题上美国的立场。(38) 如果说中国的立场是深受其害者作出的,那么美国非政治人物如何看待日本天皇的呢?哈克沃斯(Green H.Hackworth,法律顾问)认为,如果国务院采取回避或者没有清晰的政策思路将会遭受广泛批评,国务院应该现在或者稍后就做出决定,他承认关于天皇的处置问题上需要考虑一些政治因素,但是他认为在实施正义问题上不应该受到权宜之计的影响。 同一个问题,作为代理国务卿的格鲁则是另一番分析,也充分体现了美国政治人物思维上的实用主义习惯与特质。格鲁表示: (自己)倾向于如果日本拒绝遵守波茨坦公告,拒绝无条件投降,迫使我们使用武力进入日本本土并因而造成了美国包括盟国在内人员的伤亡,这种情况下天皇应该被列为战犯,以实现完全正义。将天皇列为战犯并不意味着他会被判有罪,这将取决于证据,取决于天皇是否参与了谋划实施了战争残暴行为,还是仅仅是一个傀儡而无法控制或者影响那些军方领导人。在这一特殊问题上,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忽略一些政治因素的考量。我们应该利用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利用他们来说服天皇发出圣谕,命令日本军人为了他们国家的未来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而不是顽强抗争到最后一刻。没有天皇的批评认可,日本在海外的军队是不会遵循其政府命令的。如果我们将天皇列为战犯,在日本国内将会产生使任何可能迈向无条件投降与和平的努力行动前功尽弃,结果可能是加强了日本人的团结而抗争到底,所以国务院的立场非常重要,以致影响到数以万计的美国人的生命。 格鲁还不忘提醒说: 虽然我没有和史汀生(Henry L.Stimson,Secretary of War,美国时任陆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 V.Forrestal,Secretary of the Navy,美国时任海军部长)交流过这一问题,但从我所知的情况看,他们可能与我是相同或相似的观点。我建议去电赫尔利,告知远东与太平洋分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在是否将天皇列为战犯的问题上,美国不要主动提出这一问题。(39) 如果说格鲁的立场是“以拖待变”的话,那么在美国独占日本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情况下,不管是国务院还是美国军方都不会在如此关键的时间节点就这一重要问题明确态度或表达立场。国务卿贝尔纳斯于8月8日致电赫尔利,表示重庆分委员会提出将天皇列为战犯的建议很遗憾,期待赫尔利能够想尽各种办法阻止这种企图,万一这一问题被提出,请电告国务院以便作出指示。(40)1945年9月12日,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远东事务分会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要求驻日美军最高司令在收到处置天皇的特别指示之前不能采取将日本天皇列为战犯的任何行动。(41)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的立场越来越清晰。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在给参谋长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电函中如此分析道: 将天皇的确切活动和过去日本帝国的政治决定在不同程度上联系起来的具体确凿的证据还没有被发现,我已获得明确信息,直到战争结束天皇与国家事务之间的联系主要是臣属性的以及是对他的顾问的意见的自动反应。天皇任何企图阻挠由处于支配地位的军事集团所控制和代表的社会舆论的行为都将使他处于一种危险境地。如果天皇受审,占领日本的计划必须作很大调整,而且在具体行动之前必要的准备工作必须完成。天皇的被诉毫无疑问会在日本民众中引发巨大的震动。天皇是日本联合的象征,实际上所有日本人都尊崇天皇作为国家的社会领袖,而且相信波茨坦公告是维持他日本天皇地位的。日本民众会将盟国的行动看作是对他们历史的背叛,由此引发的仇恨敌意和对抗不满会毫无疑问地持续到可预见的将来,由此开始的循环报复的仇恨可能持续几个世纪而不能结束。(42) 既然美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那么美国必须要有一些将天皇排除于战犯之列的事实材料以作佐证,1946年2月16日驻日美军当局政治顾问办公室的一份电函则显得恰逢其时。其中迫水久常(Hisatsune Sakomizu,曾任日本内阁书记官长)讲述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天皇本人是反对战争的,但是受限于官方行动而没有阻止战争,因为理论上天皇是不能单独做出决定的,而是应该接受大臣的建议,这些大臣则应该对采取的行为负责。迫水久常讲道,1941年12月4日或5日,天皇通过面部表情(facial expression)表示同意战争不是保护日本利益的唯一方式。在宣战的帝国法令中,天皇自己加入了一段话,揭示了与美国、英国的战争并没有得到天皇本人的支持。在签订德意日三国协议时,天皇告知近卫文磨这个条约可能给日本带来重大不幸。并且迫水久常将会继续提供能够开脱天皇战争责任的证据材料。(43) 五、美国审判战犯政策 必须将日本战争罪犯嫌疑人绳之以法,这是反法西斯盟国包括美国的共同意志、决心和政策。但在美国独占日本的情况下,为审判日本战犯而建立的司法机构与美国驻日当局之间的关系怎样处理?审判机构的规模如何控制?其他盟国选派的司法人员地位怎么安排?这是美国审判战犯政策需要考虑并要予以解决的。实际上美国的远东审判政策首先是从协调统一自身立场开始的。 (一)驻日美军当局主导战犯审判工作 在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特别分会9月6日的会议上,关于审判战犯应遵循的政策已经被提出来了。国务院赞同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建议向盟军最高司令发出指令,以建立一个针对主要战犯的准备案件的检查起诉机构,以及一个由美国和其他盟国军官或文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主要战争罪犯。这样,有利于消除之前在欧洲建立并运作这种起诉机构和军事法庭时遇到的拖延和困难。这种程序也有利于建立盟军最高司令处理各种事务的权威。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国可能会感觉到在处理这些国际重大问题的时候,对盟军最高司令的指令应该得到他所代表的所有主要盟国的认同。而且审判战犯的法庭如果能够直接在国际性的权力机构下运作将更有利。这样的法庭在建立先例和争取日本人民方面会赢得尊重,也利于分担美国的责任。 鉴于此,在协调委员会特别分会的国务院代表应采取如下立场: 除非在我们主要盟国态度立场清晰的情况下,有关国际检查起诉机构和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事务的指令不得向最高司令官作出;应该采取在最高司令官之下设立联合起诉机构的政策以起诉战争罪犯,另一方面审判战犯的法庭应通过主要盟国之间的协议建立,并在他们的权威之下运作;这样的立场应通知给英国、中国、苏联和其他盟国,以得到他们对这些政策的同意;一旦得到盟国的批准,应该立即向最高司令官发出指示,以组建起诉机构,并采取必要步骤建立审判庭。(44) 显然,国务院的代表已经意识到在美国已经单独占领日本的前提下,驻日美军当局的地位不可动摇,日本战犯的审判必须有利于加强其地位,提高其权威,但同时又将驻日美军当局置于盟国之间协调的权威之下,显然有点“不合时宜”。所以副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代表国务院对此进行了答复,认为最重要的是拥有一支统一的起诉职员,他们依据一套单一的关于案件准备和报告的指示运作,因此其认为麦克阿瑟应该建立这种职员队伍,向他们发出指示,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邀请其他有关盟国参与。最重要的是法庭的程序和原则,包括战争罪行定义,必须和起诉德国战犯相协调。由麦克阿瑟建立一个法庭,有关战争罪行的鉴定、适用规则和程序都依照在德国的先例,并且宣告这已成事实,再邀请有关的主要盟国任命法官。德国的实践已经表明,与其他国家(中国没有参与欧洲有关问题的协商谈判,他也无法了解来自中国方面可能的麻烦)就战争罪行的鉴定、审判规则和程序达成协议不会很顺利或者是一个很耗时的过程,尽管麦克阿瑟如果采取了上述步骤可能更耗时。艾奇逊倾向于让麦克阿瑟承揽整个工作,特别是因为这样可以维持其权威。(45) 9月7日,助理陆军部长麦克洛伊(McCloy)致电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表示他理解在远东战犯问题上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之间产生了分歧,陆军部、海军部方面认为麦克阿瑟应该被赋予权力:(1)建立远东军事法庭来审判所有远东战争罪犯,包括主要和次要战犯;(2)制定颁布程序规则和适用于所建立法庭的大量可行的法律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必须与适用于欧洲的相关程序和规则相协调;(3)根据参与方的提名任命法庭成员。 陆军部和海军部都认为,依据有关国家政府的提名进行任命审判法庭成员的权力应属于麦克阿瑟,而不是将任命权交由有关国家政府。而国务院似乎倾向于法庭成员直接由各自国家任命。希望国务院和陆军部、海军部的立场统一起来,这样有利于避免许多在德国遇到的拖延和麻烦。 作为盟军最高司令有权任命特别国际军事法庭成员,有权颁布或批准法庭的程序规则。盟军最高司令有责任执行国际军事法庭或裁判庭作出的判决,也有权力批准、减少或者改变法庭或裁判庭作出的判决,却不能增加判决的严重性。最高司令官可以授权参与占领日本的任何一个盟国的军事长官来组建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没有被国际军事法庭或裁判庭处置的战争罪犯。(46)这个政策立场于1945年10月2日被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批准,10月18日国务卿将包含这些内容的美国有关远东战犯的逮捕审判政策发给了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47) (二)法庭的组建 美国认为在组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过程中,仔细借鉴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规模应该控制在最小,建议法庭只能由接受日本投降的四个国家(美国、中国、苏联和英国)的法官组成。根据美国逮捕惩罚日本战犯政策,美军驻日最高司令有权任命来自两个及以上联合国家的军官和文官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以审判日本战犯。美国国务院将邀请中国、苏联、英国每个国家指派军事法庭的5个合适成员(如果国务院需要,还可要求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菲律宾、新西兰每个国家指派3个合适成员),指派(不管是军官还是文官)工作必须尽早进行,以便最高司令从这些指派人选中选出合适成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国务院在请这些国家指派人员时,为了管理和实际的需要,选派的军官和文官能够使用英文,以尽量减少在欧洲遇到过的语言上的困难。军事法庭应该有文官代表,所以联合国家政府指派代表时军官和文官应予一同考虑。(48) 1945年11月21日,国务卿致电中国大使魏道明,询问提名法官以建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选问题,同样的信息在同一时间发给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苏联和英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49)这是美国第一次将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规模和联合国家需要指派的法官人数通知有关国家。 但在11月27日,远东事务处主任文森特(Vincent)与中国大使魏道明谈话时,提及指派法官以组成法庭审判日本A级战犯问题,文森特作了不同于之前要求的表示,他说盟国政府仅仅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候补法官而不是一组法官,对于达到我们的目标就已足够。文森特解释道,美国开始要求盟国政府指派一组法官的请求,其意图是建立不同的法庭以审判A级、B级、C级战犯,但是现在我们紧迫地要审判A级战犯,所以指派一名法官及其候补即可达到我们的目的。(50) 不仅如此,原来设计由接受日本投降的4个国家指派法官和检察官,后来扩大至日本投降协议的签字国。1946年1月8日,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苏联使馆代办凯南(Kennan),其中表示,1946年2月初盟军驻日最高司令将在东京组建国际军事法庭以审判那些被指控为反和平罪的日本主要战犯,也正在任命由日本投降协议签字国所提名的法官和副检察官。国务院已经发出电函要求盟国提名人选,目前中国和新西兰已经进行了提名,英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和加拿大已经表示他们期待参与审判,并很快进行提名工作。(51)艾奇逊在1946年1月18日所发的电函中再次明确了有权提名法官和检察官的国家范围: 日本投降协议的9个签字国已经被请求提名法官和副检察官,以由盟国驻日最高司令任命组成法庭和国际检查起诉部门,中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完成了提名,英国已经提名了副助理检察官,法国、荷兰和苏联已经表示他们会很快作出提名。印度和菲律宾不会被要求提名法官,但考虑到发生在它们各自国家的战争罪行和残暴行为。它们应该被邀请提名助理检察官。(52) 1946年1月4日,印度提出其有权提名1名法官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在1月23日代表美国答复称,希望印度和菲律宾政府各提名1名助理检察官,以由盟军驻日最高司令任命组成国际检查起诉机构。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英国和新西兰检察官的提名已经收到,并转交给了最高司令。国务院已经通知法国、荷兰和苏联,希望它们能在不久的将来完成提名工作。(53)印度对国务院1月23日对于印度要求选派法官到国际法庭的答复是不满意的,虽然印度政府还没有新的指示,但任命助理检察官可能被阻止。(54)1946年3月1日,国务院近东与非洲事务处建议美国在远东委员会的代表积极投票支持印度任命1名法官参与军事法庭,得到国务卿的批准,并通告了陆军部。4月29日,国务院被告知印度政府已经提名巴尔(Radha Binod Pal)为法庭法官。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Delfin Jaranilla)也被任命为远东军事法庭法官。(55) 法律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稳定的预期,在规范人类行为的基础上而形成一种平稳的秩序,所以人们应当服从法律规则。但当现有的法律规范不能有效地规制人类行为,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正义,则有必要也必须突破原先的法律思维模式。战后对战犯的审判应该说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原有的不管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的法律框架和原则,这种突破显然源自于对之前残酷的战争事实的反思,结果是人类法律思想发展的大跨越。事实也有效证明了,战犯审判活动推动了现当代国际法理念的提升、规则的创新和结构体系的完善。 通过前文我们看到,美国于战后初期不管是在战犯的甄别逮捕还是组建审判法庭,都表明了美国与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一样,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认识是清楚的,处置战犯的立场是明确的,这些认识和立场通过东京审判法律化了。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的战争的侵略性质在法律上的确认,而且是在突破人类原有的法律原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成果,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这样的认识、坚持这样的立场。 从美国的角度看,东京审判是美国战后独占日本合法性的基础。试想那些战犯如果没有受到正义审判,那么他们统治日本这个国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将继续维持,而恰恰是他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不仅祸害了邻国,也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遭到自己人民的唾弃,才致使他们陷于非正义、不合法的地位。这种不义和非法正是美国当局在日本地位合法性的源泉,也是维持战后日本社会秩序的正义基础。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中国、美国、英国等为代表的反法西斯盟国通过审判日本战犯,对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统一了认识,明确了立场,宣告了日本侵略所造成的非正常、不合理和无正义的亚太秩序的非法,这正是战后亚太秩序建立的法理基础。 [收稿日期]2014-08-22 注释: ①PROCLAMATION BY THE HEADS OF GOVERNMENTS,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UNITED KINGDOM,FRUS,the Conference of Berlin(the Potsdam Conference),FRUS,1945,the Potsdam Conference,Volume II.p.1476. ②[美]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著:《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 ③[英]M.阿库斯特著:《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朱奇武、余叔通、周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17~318页。 ④The Chargé in China(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December 9,1944.FRUS,1944,Volume I,p.1399. ⑤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January 6,1945-9 a.m..FRUS,1945,Volume VI.p.898. ⑥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January 6,1945-2 p.m..FRUS,1945,Volume VI.pp.898~899. ⑦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Washington,January 16,1945-4 p.m..FRUS,1945,Volume VI.p.899. ⑧⑨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London,February 6,1945-2 p.m..FRUS,1945,Volume VI.p.900. ⑩Report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Subcommittee For East,Washington,September 12,1945.FRUS,1945,Volume VI.p.933. (11)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July 28,1945-11 a.m..FRUS,1945,Volume VI.p.901. (12)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August 4,1945-9 a.m..FRUS,1945,Volume VI.p.902. (13)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September 9,1945-8 a.m..FRUS,1945,Volume VI.pp.923~924. (14)这12人战犯名单具体如下:Honjo,Shigeru; Doihara,Kenji; Tani,Hisao; Hashimoto,Kingoro; Itagaki,Seishiro; Hata,Rokujin(Shunroku); Tojo,Aiki(Hideki); Wachi,Takaji; Kagesa,Sadaaki; Sakai,Takashi; Isogaya(Isogai),Rensuke; Kita,Seiichi.The Chargé in China(Robert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October 20,1945-5 p.m..FRUS,1945,Volume VI.p.948. (15)这21人战犯名单如下:General Jiro Minami、General Sadao Araki、Baron Kichiro Hiramnna、General Nobuyuki Abe、Admiral Mitsumasa Yonai、General) Kuniaki Koiso; Admiral Shigetaro Shimada; Koki Hirota; Yosuke Matsuoka,; Shigenori Togo; General Yoshijiro Umezu; General Iwane Matsui; Marshal Juichi Terauchi; Lieutenant General Kadoya Mudakuchi; Masayuki Tani; General Otozo Yamada; Hachiro Arita; Kazui Aoki; Admiral Nobumasa Suetsugu; General Juzo Nishio;(General Masazo) Kawanabe.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Smy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February 14,1946-2 p.m..FRUS,1946,Volume III.p.410. (16)The Chief of Staff(Marshall)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Army Forces,Pacific(McArthur),at Manila,WASHINGTON,16 August,1945.FRUS,1945,Volume VI.p.909. (1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Washington,August 23,1945-1 p.m..FRUS,1945,Volume VI.p.910. (18)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Hodgson),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5.FRUS,1945,Volume VI.pp.937~938. (1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Washington,October 15,1945-3 p.m..FRUS,1945,Volume VI.p.944. (20)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October 5,1945.FRUS,1945,Volume VI.p.940. (21)这13人战犯名单是:Sadao Araki; Honjo Shigeru; Itagaki Seishiro; Kanokogi Kazunobu; Kuniaki Koiso; Fusanosuke Kuhara; Kuzuu Yoshihisa; Matsuoka Yosuke; Matsni Iwane; Mazaki Jinzaburo; Minami Jiro; Shiratori Toshio; Yamada Otozo.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13,1945.FRUS,1945,Volume VI.pp.961~966. (22)这22人战犯名单是:Aikawa Yoshisuke; Amau Eiji; Ando Kisaburo; Aoki Kazuo; Goto Fumio; Hata Shunroku; Hiranuma Kiichiro; Hirota Koki; Honda Kumataro; Hoshino Naoki; Konoye Fumimaro; Nishio Toshizo; Oshima Hiroshi; Shioten Nabutaka; Shoriki Matsutaro; Suma Yakichiro; Tada Hayao; Takahashi Sankichi; Tani Masayuki; Toyoda Soemu;Umezu Yoshijiro; Ushiroku Atsushi.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16,1945.FRUS,1945,Volume VI.pp.967~970. (23)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December 18,1945.FRUS,1945,Volume VI.p.985. (24)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13,1945.FRUS,1945,Volume VI.pp.961~966. (25)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19,1945.FRUS,1945,Volume VI.p.973. (26)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6,1945.FRUS,1945,Volume VI.pp.952~953. (27)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October 5,1945.FRUS,1945,Volume VI.pp.941~942. (28)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19,1945.FRUS,1945,Volume VI.p.972. (29)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17,1945.FRUS,1945,Volume VI.pp.971~072. (30)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December 19,1945.FRUS,1945,Volume VI.pp.985~986. (31)这三名战犯分别是:Kenji Sawada; Major Hata; Lt.Wamitsu. (32)这11名战犯分别是:Sadao Araki; Shigeru Honjo; Kazunobu Kanokogi; Kuinaki Koiso; Fusanosuke Kuhara; Yoshihisa Kuzuu; Yosuke Matasuoka; Iwane Matsui; Jinzaburo Mazaki; Jiro Minami; Toshio Shiratori. (33)Report by Mr.Robert A.Fearey,of the Office of the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FRUS,1945,Volume VI.p.974. (34)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November 30,1945.FRUS,1945,Volume VI.pp.976~978. (35)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December 20,1945.FRUS,1945,Volume VI.p.986. (36)The Ac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January 22,1946.FRUS,1946,Volume VIII.p.393. (37)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July 28,1945-11 a.m.FRUS,1945,Volume VI.pp.901~902. (38)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ungKing,August 4,1945-9 a.m.FRUS,1945,Volume VI.p.902. (39)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Gre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August 7,1945.FRUS,1945,Volume VI.pp.905~906. (40)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Hurley),washington,August 8,1945.FRUS,1945,Volume VI.p.907. (41)Report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Subcommittee For East,Washington,September 12,1945,FRUS,1945,Volume VI.p.936. (42)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 to the Chief of Staff,United States Army(Eisenhower),Tokyo,25 January 1946-1:45 p.m..FRUS,1946,Volume III.pp.395~397. (43)Mr.Max W.Bishop,of the office of the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Tokyo,February 16,1946.FRUS,1946,Volume III.pp.412~415. (44)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Ballantine),Washington,September 6,1945.FRUS,1945,Volume VI.pp.919~921. (45)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Ache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Ballantine),Washington,September 6,1945.FRUS,1945,Volume VI.p.921. (46)Report by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Subcommittee For East,washington,September 12,1945,FRUS,1945,Volume VI.pp.926~936. (47)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Wei),Washington,October 18,1945,FRUS,1945,Volume VI.p.947. (48)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Chairman of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Matthews) to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3 October,1945.FRUS,1945,Volume VI.pp.938~939. (49)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inese Ambassador(Wei),Washington,November 21,1945.Volume VI.p.975. (50)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Vincent)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Acheson),Washington,November 27,1945.FRUS,1945,Volume VI.pp.975~976. (51)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é in the Soviet Union(Kennan),Washington,January 8,1946-4 p.m..FRUS,1946,Volume III.p.386. (52)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 General at Manila(Steintorf),Washington,January 18,1946-1 p.m..FRUS,1946,Volume III.p.390. (53)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Indian Agent General(Bajpai),Washington,January 23,1946.FRUS,1946,Volume III.pp.393~394. (5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Mr.Albert H.Garretson,Assistant to the Legal Adviser(Hackworth),Washington,February 4,1946.FRUS,1946,Volume III.pp.399~400. (55)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Near Eastern and African Affairs(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March 1,1946.FRUS,1946,Volume III.pp.418~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