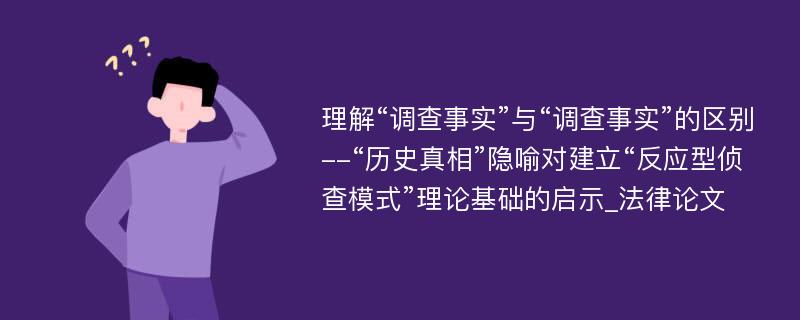
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之甄别——“历史真相”隐喻对确立“回应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址论文,事实论文,启示论文,真相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是世界上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正如英国学者皮尔逊所言:“分类事实和依据事实推理的艰苦而无情的小路,是弄清真理的唯一道路。”法国学者斯特劳斯甚至认为:“任何一种分类都比混乱优越,即使在感官属性上的分类也是通向理性秩序的第一步。”但是,如果只是单纯分类和简单解释,当然不会自动生成一个自圆其说、顺理成章的理论体系,我国理论界关于回应型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的分类解释及其理论建构正处于这样一个尚待完善的阶段。
以往相关研究至少需要廓清如下三方面问题:一是解决因分类标准不明导致内涵表述不够清晰的问题。笔者认为,区分两种侦查模式的根本标准是行为目标:回应型侦查以特定犯罪案件为目标,具有明确的破案目的;而主动型侦查则包含概括性的侦查破案的目的,就实践而言其目标较为复杂,主要是获取违法犯罪情报、打击某类正在进行或将要进行的犯罪活动、阵地查控危险人员和物品、整治治安乱点和复杂地区等,其核心目标通常是不特定的可能案件(涵括主侦案件带破、协破的类案、窝案和串案)、可能犯罪者、可能侵害对象、可能活动时段、可能活动(如销赃或藏匿)场所等。可能性是一种预防性,对可能性的预判显示主动型侦查具有施动性、计划性和绩效评价的自在性等特征。二是对两种侦查模式的理论基址解释不够,影响了侦查学理论本体性的重构。长期以来,侦查权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属性争议日久却莫衷一是,阻碍了我国侦查学理论的本体性塑造与结构。同时,体制上多警种对刑事案件的混合管辖现实,使司法警察与行政警察这两个在理论上区别明显的概念一旦与实际警察活动相连接和比照,便显示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不相适应。理论本体性是理论分化、独立,特别是其自洽、自足的品性,源于权力属性和体制现实的理论建构不是侦查学理论本体性重构的唯一路径。侦查学理论塑造还需从侦查活动的分类及其理论基址确立中获取奠基的柱石,至少是理论扩张的知识范式。由是,应对回应型侦查和主动型侦查的分类及其理论基址分别或一并加以深入论证。三是理论界以往对回应型侦查模式与主动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简析主要集中在法学、公安学等范式,理论发展还需要从侦查活动的特性出发,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由于主动型侦查活动对象分别指向已然犯罪的历史事件、正在犯罪的即时事件、未然犯罪的可能事件,因而其间“主动”和“客动”的关系错综纠缠,认知其理论基址要比回应型侦查模式复杂。相形之下,回应型侦查模式指向具有唯一性,它直指已然犯罪的历史事件,甚至是时过境迁的陈年旧案。从历史哲学范式分析,某种意义上,回应型侦查是一种侦查主体通过不断地搜证而对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一系列认识与证明活动,发现证据以证明案件的“历史真相”是其恒定目标,“历史真相”之“真”是所有侦查活动均倚重的特质。
总结上述思考,笔者想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真相”之于回应型侦查,不仅是一种司法过程和一种理论路径,它还是一种价值理想,它表征了“侦查事实”的向度、宽度、精度和容度。在回应型侦查“发案——立案——查案——破案”的推进程式中,由证据建构的侦查事实的“真”是后续诉、审机构建构法律事实的基础,侦查事实正确是法律事实正确的前提,没有侦查事实的客观性就谈不上法律事实的客观性。如果据证而出的侦查事实虚假,起诉和审判中的法律事实就根本构不成“事实”,所以说证据不足或虚假致使侦查事实虚假是形成错案的原因之一。即便如此,一些研究可能囿于关注的重心和视角,研究者在讨论“事实”与“证据”问题时概念混淆的情况较为严重,突出表现在认识与证明不分。①
不论是“侦查事实说”还是“法律事实说”,在讨论从“发现真相”到“还原真相”的过程时,往往笔锋一转,由证明问题直接铺陈到认识问题,似乎两者是同一概念,可以混同使用。尽管认识事实可通过证据分析,认定事实亦可通过证据证明,然而认识侦查事实(历史真相)与依据各种证据对其展开证明毕竟是两种并不相同的实践活动。侦查认识是一个自明、自足的内闭型过程,而侦查证明还隐含着一个他明、后验的开放型理解体系,显然认识活动不能简单地等同或涵摄证明活动。这一差异启示我们:在侦查学主体性的重构过程中,历史哲学范式固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一种必要条件,是理论秩序化管理活动中的“迷宫引线”,也是我们理解回应型侦查模式理论基址的基本参照物,乃至侦查理论和证据理论创新的立足点之一。②据上而论,在确立回应型侦查模式的理论基址时,应对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这一对既具有相合点、又具有不合点的组合问题加以区别。两者的不合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象:侦查事实的未知和已知
所谓“认识”,是主体“知道”的主观映像,《辞海》中将认识解释为“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科学意义上的认识“不仅倚赖感官知觉并有赖于理智的溶解之作用”。“证明”作为一个通用的概念其涵义是“论证”。《辞海》中将证明解释为“根据已知真实的判断来确定某一判断真实性的思维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综合运用,可区分为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演绎证明和归纳证明等。当证明作为诉讼中使用的概念时,则其既具有“认识”的意义,也具有“论证”的意涵。比较上述两个概念可以发现,需要认识的往往是未知的侦查事实,认识的核心功能是探究、发现新情况,而对新情况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客观、是否合乎实际往往需要证明来检验,因而证明的对象多是已知的侦查事实,基本属于旧情况范畴。尽管证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认识活动,但证明绝不仅仅是认识,不能将其简单地看做是认识活动。侦查认识与侦查证明存在对象上的新与旧、未知和已知的差别,其原因在于:
(一)侦查认识具有自我独立的扩张与前进惯性,每一个主体都具有推进认识并形成符合认识法则要求的历史事实解释之需要
在个案侦查过程中,不论是认识还是证明,都可由特定的侦查主体针对不同的对象独立完成,进而形成了关于历史真相的自我认识。雅各布分析了历史真相在单一个体中的形成过程:“历史学家不是炼金术士,不能将黑的事实和白的语言描述掺和而发明出历史实在;历史学家也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观察者,不会自称能制造出灰色的叙事,确实无误地与既有的事实相符。历史学家只是按过去留下来的记录重构一个拼凑的过去。”对该侦查主体而言,需要认识的对象往往是未知的历史真相及其碎片;就需要证明的对象而言,其对象必然是已知的历史真相或其碎片。因为只有把握了前历史真相及其碎片(局部侦查事实),才能拼接、补缀下一步(后侦查事实)乃至整体侦查事实,使侦查事实符合一种“历史解释”的形式和实质意涵,即符合经验法则、矛盾法则、发展法则和时空法则。正如加登纳所言,历史事实的解释框架需要“填补”,填补必然会增加事实表述和判断的精确性。③
(二)侦查认识推进所获得的历史事实与证据的质和量直接相关,新证据意味着新情况和新发现,侦查证明活动则通过检验既有证据的质和量而完成
与侦查活动的回溯性思维相近,历史同样要研究过去的事实,历史研究的初始单位是事件,事件是由在现实生活感知记忆并实录了的事态变化或发生过程的记注者所定义,历史记注是关于社会事实的实时记录。虽然往事已逝,但对查史者而言,记注传递了查证的意义和结果。为确保事件的真,需要人们在本体论的视角视原始记注的事件及其碎片和事件的意义为同一,并尽可能多地收集史料,因为很难存在也很难发现那些记注整体历史的质料,更不存在观察到所有事件的“上帝之眼”,此即傅斯年所论“史学即史料学”。为此他一再强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之于史料与侦查之于证据具有同向度的认识路线,都通过现存的材料去认识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要使侦查事实从未知到已知,所知之事由少到多,需要侦查证明在其间穿针引线,核验证据的质和量,以使所知之理由浅入深、由粗而精。证据的质和量是认识和证明赖以进行的前提,特别是证据的量,即证据的充分性问题,它是侦查认识区分侦查证明的标准之一。当在整个侦查活动展开之初,证据越不充分,认识与证明的区分越明显,没有证据无以认识“历史真相”,没有充分的证据更无以证明“历史真相”。
(三)为克服历史解释的局限性,侦查主体会引入多种排疑解惑的技术手段来增加确定性,使侦查事实完成从查明到证明的跃迁
犯罪活动必然引起生物、物理和化学变化,会遗存各种形态的痕迹、物证,各种变化以及各种痕迹、物证之间客观上存在关联性,这种关联是犯罪活动的反映。侦查人员为弥补认识能力的不足,常常借助技术手段再现变化、痕迹和物证,进而反推和结构犯罪活动的过程。笔者看来,侦查取证活动与历史实证研究中的博物考古、田野调查和文献训诂等调查活动本质上并无二致,在一些特定公案的调查中两者在执业理念、专业手段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相似性,如曹操墓地考古和光绪死因调查。④人们在描述侦查和历史研究的专业化进程时均把其置于现代学科的语境范式中阐释,如两个学科都强化物理、化学、生物等硬科学手段适用在解释疑难问题时的攻坚作用;在获致历史事实的同时,社会学、心理学等人文软科学又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事实的描述细节中,以形成一个情节圆润饱满的人们能够理解的“历史真相”。硬科学手段和软科学手段都充当了认识的工具,它们延伸了主体的认知力臂,同时也完成了对历史事件从查明到证明的科学演绎。
(四)侦查主体探求未知,形成和发展新的侦查事实乃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改良的无止境过程,证明活动在其中的作用有时并不突出
历史哲学启示我们,对于整个侦查活动而言,认识犯罪的全部过程,并获得完整的证明是认识侦查事实的理想状态,但侦查事实形成不是一个现今见之于过去的“镜像论”,再现一个包含每个行为细节、全部主动和客动关系的事件过程有时既无必要,更不可能,有时甚至会出现错误。在一起入室强奸杀人案中,中心现场死者所在的东屋地上有一盆盛着少量液体的菜盆,经查验后发现是尿液。死者不太可能用菜盆这一重要炊具来接尿,最大的可能就是嫌疑人所留。嫌疑人为什么在现场留下自己的尿液,侦查员对此曾有过多种误解。这起案件破获后,讯问嫌疑人后才得知他在菜盆里接尿是自己饮用,原因是嫌疑人经过与被害人搏斗并制服被害人、强奸被害人、杀死被害人等一系列过程后,累得满头大汗,渴急之下拿来炕桌上的菜盆接尿自饮。这个案例说明,对未知事实的认识往往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除疑祛魅、除旧布新的过程,正确的侦查事实往往是不断改良、修正的结果。
二、规则:侦查事实的发现模式与证明模式
作为“知道”的认识,其过程是从无知到有知,这同样与历史发现相似。因此其所适用的规则是发现模式,而侦查证明活动所适用的则是证明模式。发现模式和证明模式完全不同。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强调观察的发现价值:只是因为我们有局限的感官和理智的特征,孤立的事实才存在。思想本能地和自行地进一步编撰观察,并就事实的部分、结局和条件完善事实。任何迄今还未通过观察弄清的事物,都能够变成在思想中完成的对象,变成推测、假定或假设的对象。假设的基本功能是,它导致新的观察和实验,不断地观察和实验确认、反驳或修正了我们的猜测,从而扩大经验。汤因比指出主体能动性所具有的“发现”意义:历史事实不是绝对的混乱或偶然,但也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它是经过打磨的燧石,人的活动对其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没有人的活动,它们也就不会有人们看到的样子,因为在我们说出它们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的过滤了。本雅明用“捕获”指代“发现”: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过去的真实图景就像是过眼烟云,它唯有在能被人认识到的瞬间闪现出来而又一去不复返的意象出现时才能被捕获。在此揭示发现模式与证明模式之全部涵义当然不易,但为进一步澄清侦查中历史真相的认识与证明的差异,讨论其中一二则是必要的。
(一)侦查中对历史真相的发现与证明所需要的是两种不同的主体智见
发现较证明所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创造性的活动,它往往与侦查人员的直觉、灵感、顿悟等非逻辑思维形态相联系;而侦查证明则可以大体上全部仰仗逻辑——归纳和演绎而完成。尽管发现(认识)过程常伴随着证明活动,但证明之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在发现和进一步发现过程中的作用却十分有限。以至于克莱因说:“逻辑并非发现真理的可靠工具,用别的方法得不到的真理,逻辑也一样不能推导出来。”马赫在考察逻辑学发展史后也认为,“中世纪的逻辑在探究方面几乎完全是无结果的。它也许包含着较少的事实材料,而较多地关注它力图榨尽被认为是真命题的一切东西,这种方法所揭示的大都是相当令人不满的纸上的食物”。毫无疑问,犯罪“历史真相”的始作俑者,即“案件是谁怎么干的”这一问题始终是侦查事实的核心,但从寻找、找到以及查清、证明全部真相显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某抢劫案件中,一名出租车司机被杀死,犯罪嫌疑人抢劫得手后驾驶该名被害人的出租车逃离现场。侦查员排查后发现案前半小时被害人的手机接过一个电话,但该号码是嫌疑人用后即扔的犯罪专用的非实名制电话,此后再无任何通话记录。一名侦查员从号码想到销售此号的地点和场所,他借由销售商连号售卖的特征,而将这一可疑号码的最后五位加减5(如电话号码是139×15415,可调取139×15410-139×15419等9个号码),分别联系持这些卡号的人员,询问他们手机卡的销售地和销售点,侦查员赶往售卡地,并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再如,在一宗深夜一点发生的多人结伙故意伤害多人的案件中,三名被害人都不认识追砍他们的这些人员,也搞不清这些人为什么要追砍他们。一名侦查员面对这种临时起意、犯罪原因不明显的案件突然想到,嫌疑人纠结起来需要一段时间,其中必然有一名主使者,而深夜时分案发地附近通话很少,因此可通过查询附近基站的“一点对多点”形态的通话记录入手查找嫌疑人。全案正是通过这种思路找到线索,最终抓获了嫌疑人。上述案例说明,发现模式在侦查工作中是极为重要的,常常起到“取一点而撼全局”的效果,侦查员在特定情境中涌现出的个案侦查智慧常常成为马赫所言的“探究的小径”。上述案例还启示人们,尽管发现模式与证明模式在侦查中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但并不能借此形而上地得出孰轻孰重的必然结论,发现在侦查中往往具有先致性,而证明则常常表现出一种后验性,多起到检验已知认识成果的作用。
(二)逻辑的结构性、自洽性和严密性尽管是所有证明推理活动必备的特征,但对发现而言,往往成为应予摆脱的束缚
在案件侦查中,证明活动所要求的逻辑推理往往因为亦步亦趋、循规蹈矩而效率低下,其作用因而被主体自觉不自觉地限缩。嫌疑人不可能按照侦查员的认识“逻辑”去实施犯罪,犯罪所留下的痕迹、物证和信息也并非一定符合“逻辑”,许多突发性、偶发性的刑事案件更是难以找到案件发生的“逻辑”。就整个侦查活动而言,侦查员发现(认识)历史真相,证实和证伪案件事实的情节不可能表现为逻辑的形式系统的特征,因为客观事实时过境迁、千变万化,往往导致证明所赖以推进的形式逻辑难以预见。考夫曼指出:“法律发现实质上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复杂结构,这种结构包括创造性的、辩证的、或许还有动议性的因素,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创造性的发现模式与保守性的证明模式常常发生冲突,这在侦查初始阶段表现得更为显著,在认识(侦查)开始及其过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知之甚少到逐渐加深的过程,为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有时甚至需要极力摆脱逻辑的束缚。如侦查员在对某一强奸杀人案的侦查中,发现附近某人具有性违法犯罪的前科,且具备相应的作案条件(如作案工具),此时虽无证据说明案发时该人就在犯罪现场,甚至还有证据表明该人可能不在现场,但侦查员仍可能将其列为本案的嫌疑人。这是因为,在发现并建构“历史真相”的张力驱使下,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发现模式”,但却不一定符合“证明模式”。
(三)鉴于“仅仅这些形式的知识(指逻辑,笔者注)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它至多可以有助于核验思想路线,而无助于发现新思想”,因此实践中侦查证明活动多不必然构成那种严格的形式逻辑,即证明也往往需要依靠简化式的逻辑形式或者潜隐暗含式的逻辑构造,甚至是逻辑之外的手段来达至
实践中人们常常把起到一种说明、一种消除疑虑、确定可信度的活动都视为证明,之所以产生这种简要式的证明,并不是因为证明的内容,而是证明的形式,即实际生活中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来代替晦涩艰深的证明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把起到确立可信度作用的活动都视为一种证明,对这种证明形式的评价正如霍姆斯所解读的:“在形式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常常是不清楚和无意识的,但它却是整个过程的根基和叶脉所在。你们可以给任何结论披上逻辑的外衣。”通俗易懂的形式相当于维特根斯坦所言的“只是一种不支撑任何东西的墙檐物”,而晦涩艰深的证明形式则是“一种建筑学结构上的需要”。证明形式之严格程度与证明标准高低直接相关,而标准的选取取决于主体解决特定问题的需求程度和紧迫性强度。因此,世俗意义上一般问题的证明形式与侦查活动的证明形式、历史调查活动的证明形式必然存在着差异之处。
三、范围:侦查事实的已知与已证
从活动结果上来看,认识与证明侦查事实的范围往往并不一致,认识了的情况未必是被证明了的情况;认识了的情况未必是正确的,可能只是假象掩盖下的所谓“真相”,尚待证明来论证。从时间上来看,认识和证明往往是不同步的,两种行为进行常具有一定的“时差”和“序差”。⑤从案件的认知范围上来看,从侦查事实的已知到侦查事实的已证显然存在一定的距离。这是因为,由于主体想象力的作用和主体能够收集到的有限证据,认识的范围往往要大于主体能够证明的范围。一方面,认知历史事件往往囿于证据的有限性、主体认知需求、证据表征信息的消损和主体理解力的差异。陷于现在时空里的人们渴求对过去时空中的某一事实做出有意义而准确的陈述,但吊诡之处在于,证据是生活在过去的人或者生活在现在的人在过去留下来的过去事实,证物是留存在现在的时空里,就存在而言,过去是存在于现在,所以证据本身时常会变成争斗的焦点。另一方面,证明侦查事实经常面临历史事件的证据存量与增量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证据增量的信息描述方向与证据存量不相一致的问题。
既然认识到的历史事件的情节未必是已经证明了的,认识到的也未必是能够证明的,那就似乎揭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能认为证明活动包含着比认识更多的东西,那也可以至少理解为证明过程系一个并不与认识重合的过程,尽管两种活动进行中“混群”现象是思维的常态。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和证明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及困难,当然也会不尽相同。认识到这一点是极富深意的,正因为这一点,人们可以认识到,在侦查事实的诸构成体系中,人们对有的问题和情节的认识并不困难,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可能相当简单易懂,甚至昭然若揭,但对其的证明却可能极其复杂,有时甚至欠缺必要性而常常遭到放弃。如“老马识途”原理在侦查中的应用。一个地方发生一起盗窃铁路物资的案件,由于犯罪嫌疑人盗窃得手后被人及时发现,他惊慌之下来不及将东西运走就逃跑了,现场留下了嫌疑人的马车。有侦查员根据“老马识途”的说法,认为马从哪里来的马会有印象,因此把马解开,让马自己回家,然后跟踪这匹马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又如一起抢劫杀人案中,被害人的工作是每天下午5时赶着毛驴车往返与甲地和乙地之间运草。一天乙地收草点的工作人员发现被害人死在毛驴车上,头部被打烂了,根据尸体僵硬程度,他已经死了5个小时了。从甲地到乙地途径2县共6个乡镇,被害人到底在这一区间什么路段什么位置被害(第一现场)的,一名侦查员想到,被害人赶毛驴车运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毛驴能在被害人死后自行赶到乙地的收草点,所以毛驴走老路已成习惯,应该它对甲地到乙地的路线形成了条件反射。因此侦查员赶着这个毛驴车重新回到甲地,也是下午5时出发赶往乙地,让毛驴在无人驱赶的情况下任其自行,侦查员记录了毛驴赶到每一个地方的时间。实验显示,毛驴可以在无人驱使的情况下能够自己从甲地走到乙地。根据被害人5小时前死亡的信息和毛驴的行驶速度,初步判定事主被害的大致时间,进而找到了第一现场。这两个例子说明,认识往往基于主体先在的知识(认识)体系(包含生活经验、阅历等等),⑥而证明常涉及更复杂的知识和证明工具,有些情况下不需要证明所有与案件相关的问题,只需达到认知和解决问题的程度(两起案件中,证明老马为什么识途和毛驴为什么走老路可能就是一个几无必要且苦难重重的问题)。因此,证明在侦查中常常充当了辅助性的论证认识结果正确与否的工具,且这种论证只能在已知情节和已有证据的基础上展开,辅助性还是主导性取决于特定证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案件中的重要程度。
甄别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并不意味着认识与证明活动是截然分离的。由于侦查工作的性质和需求使认识活动经常处于历史真相的中心位置,但在证明能力的运用上却很被动,这一情况似乎隐含在以往一些错案的侦查工作中,问题之存在要求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侦查中的认识体系和证明体系之间的关系。一些侦查员在面临认识僵局时,出于口供本位效能的迷思,以各种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后再围绕口供表述的情况收集“证据”,进而构建一个所谓的证据链。这种办案思路的一个突出危害在于,实际工作中容易“先定后侦”,只重视DNA、指纹等客观性高的物证,对其他物证利用重视得不够,以至于技术部门如果在办案中拿不出有价值的物证结论,就主要依靠侦查部门单打独斗;或者在侦查部门找到“犯罪嫌疑人”后,由技术部门介入补充其入罪的“物证”。上述表述和评价是否客观、准确另当别论,但是侦查工作中有必要正确理解和处理认识体系和证明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致力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打通这两个体系。随着科学技术对侦查工作的不断渗入,认识体系不难从科学证明的空间中找到其切实的支点和触点。虽然科学证明并非万能,因为任何研究都不可能中立,即使科学也不例外。⑦但是如果除了科学证明以外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方法来检验和论证认识的结果,我们就只有相信科学,并始终保持着科学证明的姿态。迄今也唯有提供客观性模式的科学才可能拨开假象,获得真相,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证明活动。
从科学证明的发展来看,证明工具也是运用人们已经发现(认识)、掌握了的科学技术手段。以DNA技术为例,这项迄今最重要的手段引入侦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人体DNA技术发展到生物DNA的过程,显示出科学证明的强大威力。在物证中心主义和信息化侦查的时代,DNA技术手段在疑难案件侦查中已经成为获得破案线索、突破侦查僵局、划定侦查范围、确定侦查方向的“触发装置”。1984年,英国累斯特大学遗传学部教授埃利斯·杰夫瑞斯和助手维基·威尔逊在人类基因里首次发现“小卫星”的微小结构,总结数据后两人于1985年在《自然》上发表了关于“DNA指纹图的检验方法”课题的著名论文,并首次在一起移民案件中将DNA技术应用于亲子鉴定。人类DNA技术随即成为侦查破案的利器。1986年英国列斯特郡那波诺夫村一起强奸杀人案中,警方运用DNA技术成功串并另一起两年前的奸杀少女案,并抓获系列案件真凶考林·皮特克弗科。人类DNA技术的成熟和检测方法的创新推动了人类及其它生物物种DNA技术的深入发展,一系列基因工程学科的奠基与突破为动物、植物和微生物DNA技术引入侦查领域提供了可能及其现实进路。1992年美国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马克·伯根杀害丹尼斯·约翰逊一案中,警方在嫌疑人伯根的皮卡车后箱中发现两颗帕洛佛迪树的豆荚。DNA测试后发现,每棵帕洛佛迪树都具有其独特的DNA分型,而豆荚的DNA与尸体边上的一棵被刮蹭过的帕洛佛迪树的DNA具有同一关系,证明了伯根的皮卡车到过案发现场,从而获取了他涉嫌杀人的关键证据之一。这是美国首次将植物DNA鉴定技术应用于侦查破案的经典案例。人类DNA和生物DNA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成功实践,标志着生物物证鉴定技术在分子层面上实现了从侦查认识到侦查证明的跨越,目前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DNA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
四、结构框架:侦查事实的无限与有穷
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发明了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模式、过程、因果互动系统等,这乃是理解社会行动的一个有力的知识工具。正如帕森斯所言,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人类行为总是发生在制度和文化的结构——强有力、无所不在、隐而不现的结构——范围之内。社会行动结构不能决定人的行为,却会在每一时刻限制人可能做出的抉择,即使结构本身发生变迁,其约束力依然存在。在查证过程中,由于对象的非至上性和认识能力的至上性,侦查思维呈现一个对历史真相认识的无限和证明的有穷的对立结构。认识在理论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但证明相形之下却是社会行动结构规定下的一个有限过程,它是一种只能在有限步骤、程式和工具完成中才有意义的活动。
认识与证明活动的这种差异帮助人们分别讨论两种活动的特点并使讨论具有意义,从而避免陷入将两者混淆而出现的困境。对象的非至上性使得认识的对象具有无限性,世间一切事物都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甚至于认识本身也可能成为认识的对象,而这些之所以成为认识对象,主因在于主体的怀疑主义。“怀疑主义既是一种求知方式,也是一种哲学立场。自古希腊时代起,对于宣称的真理表示某种怀疑就一直是追求真理时所不可或缺的态度。”但对侦查证明活动而言,证明必须在不能再予以怀疑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证明活动的基本理路是“据实以明真伪”,证明必须以无可置疑的“实”为起点,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证明不能陷入循环论证的无限倒退之中,人们不能连续地对“证据的证据的证据”怀疑下去,否则证明活动连开始都不可能。
上述分析显示,对“侦查事实”认识的无限结构与对其证明的有穷结构在本质上都源于主体把握客观世界的能力,对于历史事件——往事的理解和考察更因主体站位与立场、知识与水平的差异而发生认识和证明上的变化。“历史学家无法完全了解冲撞一个事件的所有变数。人类参加了一个密密麻麻的互动系统网络,其中有的系统调节他的身体功能,有的支撑好奇心和情感反应。必须考虑到全部的系统反应,才能够对事件做出完整的解释”。而这种系统反应常常沦为对一种理想状态的愿景式表述。侦查活动对于历史事实的探究并不因嫌疑人之多少、案情复杂程度之高低而能确立一个“无限”与“有限”的边界。
在某老夫妻二人被抢劫杀害案中,现场有犯罪嫌疑人制造的大量垃圾,垃圾的数量和种类显示其在案后很可能在老夫妻家中住了一晚,嫌疑人吃水果、喝易拉罐、名酒和药酒,还随地大小便。为认识犯罪过程、找到嫌疑人,侦查员仔细勘查了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如对药酒的检验认为“人不宜喝这种药酒”,这种药酒是老人生前钓鱼用的,嫌疑人喝这种药酒说明对老人的情况不了解,从而基本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嫌疑人用斧头砍保险柜,说明这个人外行,没有关于保险柜的常识;在保险柜的劈痕里发现人血,说明嫌疑人是先砍人,再砍保险柜;现场被喝过的“五粮液”瓶下有血迹,这一物证的叠加变化说明嫌疑人是先杀人(而遗留血迹),再从酒柜里取酒饮用。
又如一起母子被杀案,被害母亲是穿毛裤开门,说明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更大,但双方熟悉到什么程度却是一个必须深入分析的问题。按照费孝通旨在描述传统中国人之间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理论,人的交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分层结构,每一个自我会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或层级采取相应的行动,以维系所谓的“私人道德”。这起案件中各方面证据显示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地位要比被害人家庭的社会地位低,并且嫌疑人是不受欢迎的。其主要依据有三点:一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一般家里来客人要请到客厅上座就坐,而从现场上犯罪嫌疑人喝水的杯子和烟头的位置来看,嫌疑人一直坐在一进门的沙发上;二是茶几上放了好烟,嫌疑人却没有抽(女死者没有让他抽的可能性更大),他抽的是自己带来的价格便宜的劣质香烟;三是从喝水的杯子看,有茶叶的杯子被喝得很干,茶叶都贴在了杯壁上,即使这样女死者也没有给他续水。
再如一起改革开放之初冬天发生的路边抢劫杀人案件中,根据尸僵程度和现场其他情况推测,案件发生在夜间1点左右。经过走访被害人家属得知被害人身上的10元钱、2斤油条和1个破皮包被抢,但其手腕上戴的手表却没有被抢。侦查员勘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是“打杠子”,就是先把人打死再抢劫,这说明是一人作案,如果有两三个人就不必要把人杀掉,可以在不杀的情况下达到抢劫的目的。没有抢手表,说明嫌疑人的年龄是比较大的。当地农村很少有人有手表,年龄大的人基本没有手表的概念,他在犯罪时心情是保持一定张力的,他不知道被害人有手表,也因此不会去找手表。还有气温非常冷,嫌疑人不太可能在路边伺机作案,他是遇见被害人后临时起意作案的。
对上述历史事件的情节反推有时表现为“有形实验”,但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实验”。这些情节反推都是基于现场有限的痕迹、物证而对嫌疑人现场活动的刻画,有限决定了它只能是局部事实。现场勘查活动类似电影中“蒙太奇”的片段手法,全景式的、整建制的、巨细无遗的推现犯罪全过程尽管是侦查员认识“历史真相”的极致状态,但实际工作中却并不可能。侦查工作关心犯罪过程,其重心在于如何找到嫌疑人,并在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事实和情节上予以严格证明。因此,认识“侦查事实”与证明“侦查事实”之无限与有穷的差异既源于侦查主体把握客观世界的能力,还在于法律实践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客观要求。
基于如上分析可以确立一个结论,认识“侦查事实”之无限结构框架,其可能基点在于相信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和完整程度,不能有时也不必要把“完全确知过去”搞成僵硬的概念,完整性是有所保留的完整性;证明“侦查事实”之有穷结构框架其可能起点在于相信历史事件认识的结论正确性(至少是具有建设性的认识)和适法关键性。因此关于“历史真相”描述的侦查事实的价值与意义必然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问题,即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地制宜的主体选择问题,这似乎揭示出:侦查员对案件事实证明的有穷结构的形成还与每一名侦查员对试图解释、论证历史事实的价值和意义的不同判断结果直接相关。
注释:
①认识与证明不分与我国法律中关于事实与证据的复杂关系界定有一定关系。《刑事诉讼法》将侦查终结的标准规定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在这里事实与证据是一种并列关系;但对于证据的概念(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则将证据也规定为一种事实,事实与证据间令人困惑的关系引发了诸多误读。与形象的证据概念比较,事实是一个抽象而涵义不确定且不可通约的原子概念,充当认识对象和证明对象的事实和证据常常又是主体认识活动和证明活动得以推进乃至完成的要素和根据。
②[英]亨利·庞加莱在论证理论秩序化时指出:“科学是由事实逐步建立的,正如房子是由石头渐渐垒砌的一样;但是一堆事实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转引[美]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③“历史事实展现了大量相互关联的因素,对我们希望解释的事件来说,很难确定哪些是有关的,哪些是无关的。处理的事件越复杂,他们在时空中的扩展越宽广,对历史学家判断的要求就越高。”[英]帕特里克·加登纳.历史解释的性质.江怡译.文津出版社.1900.
④一代枭雄曹操的墓地到底位于何处以及光绪皇帝为何在慈禧死前一天突然死亡,长期以来是争议颇大的历史悬疑。考古人员对河南曹操墓地的确证和河北光绪墓地的调查都穷尽了各种专业手段。如1982年清西陵管理处、中科院生化所等多家单位对光绪陵墓展开的联合调查工作运用了生物化学、毒物学、土壤学、法医学、痕迹检验学、地质学等学科手段。这次调查基本确证了光绪皇帝系被砒霜毒死的死因,但迄今为止,现有证据仍无法确定到底是谁指使毒死了光绪皇帝,留下了慈禧说、袁世凯说和李莲英说等多种可能。
⑤“一个持续体是由现实事态组成的一个完全集合,它的所有的成员相互都是共时的。其中相邻的成员都是紧挨在一起的,而且它包含了一个持续体过去和将来的成员,肯定也包含该持续体的一个或更多的成员”。[英]A.N.怀特海.过程与实在(卷二).周邦宪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⑥侦查经验是侦查人员在工作、生活、学习过程中的各种知识的积累,其重要作用在于以往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形成了侦查人员有效应对侦查实践的前提意识、参照情景、结论性描述等等。见郝宏奎、马丁主编.侦查中的隐性知识——专家观点与经典案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⑦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科学类型的区别来看,自然科学成立的前提在于人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可以做到彼此互不影响;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由于我们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论怎样保持中立,都会对观察结果产生影响,而观察结果出现后,对象也会受它的影响。以股市为例,当专家提出利好信息时,许多人会跟进投入,反而使其崩盘,导致预测失败。所以,物理学可以预言未来的变化,而社会科学却不能预言未来,否则就会落入“科学主义”的窠臼。然而,纵使自然科学可以中立,但科学研究中也存在大量影响中立的因素。以冲击波实验和多普勒效应研究闻名于世(马赫数以其命名)的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指明了物理学研究不能中立的一个根源:“虽然用感觉——这是心理要素——建立每一个物理经验时没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们却无法预见借助目前在物理学中使用的要素描述任何心理经验的可能性。”[奥]恩斯特·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洪佩郁译.商务印书馆.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