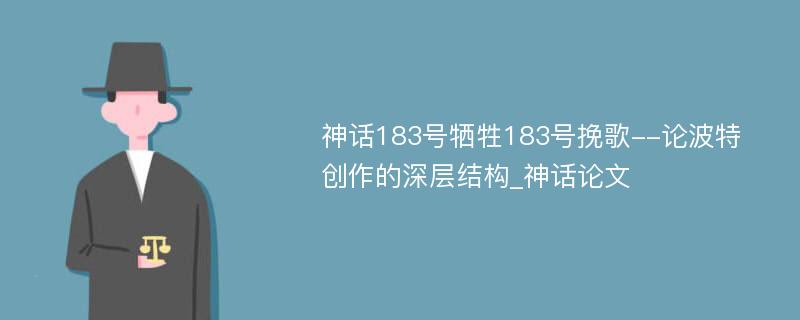
神话#183;献祭#183;挽歌——试论波特创作的深层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特论文,挽歌论文,试论论文,神话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是美国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我国学界大多从写作技巧层面对其作品进行研究,较少涉及主题,而主题研究则偏重女性主义解读。诚然,波特是一位热衷文体艺术的女性作家,为了追求文体上的“尽善尽美”,她花了近30年构思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愚人船》。但如果认为波特作品除技巧外别无他物,或仅表现出女性主义思想,则是一种误解。波特本人对“文体家”的标签不胜其烦,对性别主义的赞同也只是一种艺术立场而已。①相比之下,国外学界更多探讨波特作品的文化内涵,关注作家如何反思话语体系对个体存在及身份构建的影响。例如,盖里·休巴认为,一战摧毁了原有的意义体系,导致“单调的、做梦般”的话语流行,使得波特笔下的角色处于精神荒原之中。②安德烈亚·弗兰克维茨以性别为研究视角,认为波特作品呈现了“有关性别角色和身份形成的文化意识形态”。③贾尼斯·斯托特则探讨了左倾思潮对波特政治立场的影响。④他们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波特作品各个维度的意义,但解释的范围却常常局限于数篇故事,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波特的创作思想。
本文借助人类学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分析来探讨波特的整体创作思想,认为她的短篇小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呈现出“神话—献祭—挽歌”这一深层结构。这些作品描写了社会人的处境:他们的生活完全受到社会话语所创造的诸多神话的控制。神话的受众(subject)会刻意规范自己的行为,异类则被迫充当“牺牲”(sacrifice)的角色,遭到肉体或精神上的摧残。波特作品对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引发的群体暴政进行了反思,对弱势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并有意识地创造了一个个对抗群体思维、弘扬个人感受的挽歌手形象。这些主题各自被一系列仪式化的场景所呈现,并最终组合构成波特作品的深层结构。
一、神话
本文所指的神话是具有特定秩序的意义系统,即意识形态。每种意识形态都拥有一个神圣化了的中心理念,整个话语系统都衍生自这个中心理念,并为受众规定了身份、位置和价值。大众一旦接受了某种意识形态,就会形成共同的集体心理,并使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易受支配。究其原因,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总管行为的控制机制——计划、处方、规则、指令”,而人“极度依赖…这种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⑤社会神话与个体身份构建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波特的短篇创作中得到了深刻体现。根据受众的范围,波特描绘的神话可以分为公共神话、家庭神话和个人神话三类。公共神话指调节整个社会的政治话语,在波特创作中主要表现为战争和革命宣传;家庭神话指南方“值得尊敬之家庭”的概念,主要涉及家庭成员关系;个人神话则构建个人身份,规训个人行为,以淑女神话为主。
公共神话作为全民众共同参与建构的话语系统,除了依赖国家机器推行外,更多地倚靠民众主动建构。古斯塔夫·勒庞指出,国家的威力建立在群体的想象力之上。真正能够引发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社会事实,而是事物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因此当权者经常借助于各种鲜明形象来达到宣传目的。勒庞进一步归纳出了公共神话影响群体头脑的三种手段: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⑥断言法将某种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以煽动性的口号和信条加以概括,使之迅速成为流行的真理,把运动的领导人推上神坛;与此同时,各种宣传途径又会重复口号和信条,使之成为统一民众的精神工具。口号的重复和传染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精神共同体,并将其带入营造的狂热气氛中,致使全民形成了趋同的权威主义人格,运动也因此演变成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演,仪式“使行为神圣化”,“使人们形成的有关存在秩序的一般概念相遇与互相加强”。⑦换言之,仪式是参与者和神圣理念的盟约,参与者通过表达忠诚以相互强化精神同质性并获取奖赏。
波特在创作盛期先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墨西哥革命,因此对公共神话的运转机制深有体会,并在故事中对这三种宣传手段及其作用均有所刻画。⑧在《绽放的紫荆》中,墨西哥的革命组织就靠“机器是圣物,是工人的救赎”的口号聚集大量的工人为其卖命。尽管革命领导人布拉齐奥尼是个耽于肉欲、玩弄权术的自恋狂,却能使他的追随者“沐浴在他脸上的光辉中,并从中得到温暖”。⑨《庄园》将社会运动对口号和信条的依赖进行了高度概括: “革命的记忆轮流坐庄,许多事情的名称也随之改变,几乎每一次都以增加全人类福祉的面貌出现。”(135)《灰色骑士灰色马》所描绘的一战情形则充分证明了仪式化的社会运动对个体行为的塑造和制约。在小说中,一战被极大地美化了,其目的在于“为了彼此证明、并向世界证明我们信仰民主。”除了在战场献出性命的士兵外,其他人也参与了这场仪式:大家都以自鸣得意的爱国声调说话,称呼自己从来不用单数的“我”,而都用复数的“我们”;青年妇女们自发举行茶会筹钱为伤员买慰问品,家庭主妇们则兴高采烈地准备食物,“供奉在国家的祭坛上。”与此相对,个人的命运是无关紧要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独自的身份。大家都被强迫买“为了自由”国债券,不买的个人会面对国家机器和公众舆论的双重惩罚,遭致“个人灾难、愤怒的指责和骇人的重罚”(278-293)。米兰达甚至不敢公开谈论自己对战争的厌烦,即便日常聊天时碰到同样讨厌战争的人,说话也特别小心谨慎。这说明在公共神话的控制下,私人空间荡然无存。战争不仅是官方和公共语言的主导内容,也主导了私人之间的交谈。这一切体现了意识形态迫使个人行为与其符码和系统相一致。⑩
波特反对神话和压制的自由主义立场并不只体现在对公共政治的关注之中,也体现在对家庭神话和个人神话的批判上。尽管缺乏公共神话的激烈程度和国家机器的推行,家庭神话和个人神话仍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其强迫机制通过道德舆论得以实施。在波特笔下,这两类神话对受众的控制力量不亚于公共神话。
波特作品中的家庭神话以美国南方家庭为描写对象。美国南方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基于单家单户为形式的农业经济的庄园生活。这样的生活造成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家庭的意义在南方比美国其他任何地区都突出。此外,南方人强烈的荣誉感和身份意识也被带进了他们的家庭观,最终导致了“值得尊敬的南方家庭”神话的流行。在这个神话中,忘我的奉献和无言的忍耐是核心概念。波特小说主要从经济和婚姻两个角度反映了此理念对受众的控制机制。从经济角度讲,“值得尊敬的南方家庭”要维持它值得尊敬的表象,不能承认贫穷,更不能接受社会的慈善施舍。故事《他》中的韦伯一家就是典型例子。他们生活非常艰难,却非常在乎邻居的看法。韦伯夫人虽然牢骚满腹,但在有邻居在场的情况下绝不抱怨。故事形容韦伯一家感受所用最多的词是“羞愧”,表达了他们对家庭神话的内化和因自己未能符合规范而产生的心理焦虑。为了待客,他们在家境极端困难时杀了准备卖钱的猪崽做菜。虽然这样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但当自己所表现出的热情好客得到外人的承认后,韦伯夫人感觉到了“温暖和幸福”(53)。与经济问题相比,婚姻是家庭神话中更隐蔽而又更具个体控制性的意识形态。男性被期待要如骑士一般呵护自己的爱人,对女性而言,持家这个不断重复的日常行为也是一种仪式,是她们向婚姻神话表示顺从的方式。《斯人已去》中的加百利始终让自己生活在对亡妻的回忆之中,其行为的理想性和重复性已经与仪式无异。这种行为使他获得了他人的认可和颂扬,却使他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也伤害了现任妻子。完全内化了婚姻神话的女性,如《玛利亚·康赛普西翁》中的同名女主人公,则会对没有女人伺候的男性充满“居高临下的同情”。婚姻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来源,一旦失去婚姻便会感觉“空虚”和“死亡”(6-7)。
个人神话为个体设立行为规范,往往具有特定的受众。波特的女性身份和经历使她在创作中侧重于思考南方淑女这一神话。她自小在南方长大,后来又成为“新女性”中的一员,深知性别身份构建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理想化的淑女形象是南方文化的核心之一。此神话对受众行为的控制意图较之其他神话更加明显,其控制机制自女性幼年时起便已发挥威力。它按照“娴雅、圣洁、沉默、顺从”的标准,通过奖惩交替机制去规训女孩的行为。在《处女维勒塔》中,小女孩维勒塔身边的所有成人“对她没有任何期待,她只需要跟着西塔修女走,做一个乖女孩。”维勒塔一旦跨越了禁区,就会受到母亲的话语责备和父亲的体罚威胁,美其名曰是对她的“道德天性进行修复”(23-25)。《斯人已去》中的小女孩们视淑女形象为理想和模范,有谁满足要求就非常得意,其他人则充满了妒忌和羡慕。和公共神话一样,淑女神话也通过重复法来强化自身的接受。它的重复法不仅指共时性的行为重复,也指同一区域中的历史传承。在《斯人已去》中,有关艾米姑妈的一切记忆都成了神圣历史而为后人所铭记和重现。小女孩们尤其受到历史的影响:她们“感觉自己已经活得很久了。她们过的不止是自己的年纪,而且还有回忆。她们感到自己的生活在出生之前早已开始,在周围成人的生活中,周围超过40岁却总坚持自己也年轻过的老年人的生活中”。(174)意识形态的历史传承使得小女孩们“并不理解一些知识,只是重复听到的东西”(184)。缺乏理解的重复和遵从也已具备了仪式的色彩,正是在这些仪式化的行为中受众接纳了神话并形成了统一的精神共同体。
二、献祭
波特故事中的死亡和暴力意象一直吸引着评论界。M·K.福尔纳塔若—尼尔从“话语权力”角度进行解读,指出波特创作中总有某个失语的弱势人物,其身份依赖他人来构建;而享有话语权的人物在书写自己的同时也书写他人,通过语言的力量篡改甚至扭曲了他人形象以传递自己理想化的身份观和现实观。(11)他的观点不无商榷之处。首先,权力不对等的人群中存在死亡或暴力实属正常,关键在于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其次,细读波特文本可以发现,话语系统中身份依赖他人构建的不仅限于“弱势人物”,也有受人崇敬的英雄伟人,“享有话语权的人物”并不常是当权者,更多情况下是普通人。这与通常意义上的话语权定义完全背离。本文认为,波特创作中死亡和暴力意象的根源在于神话的“替罪羊”机制:意识形态的运转和维持不止于宣传和煽动,还在于献祭。
献祭指为了维持神话而剥夺游离于其意义系统之外的人或物的存在权。神话是一个封闭的、有中心的权力系统。为了维持整个意义系统的稳定,一切不满足神话标准的个体(不合“法”的事物)会被强制驱逐或边缘化。勒内·吉拉尔认为,一切神话都是迫害文本。每一个神话中都存在集体迫害的事实,并通过迫害仪式表现出来。在社会出现危机时,必须挑出一个“替罪羊”进行献祭以维持意识形态的稳定和再生产。迫害者不一定是当权者,精神共同体的任何成员都可能实施迫害行为,“因为他们梦想在团体里清洗腐蚀团体的不纯分子,清洗破坏团体的变节分子”。(12)下面将从目的、替罪羊的选择和仪式性三方面来分析波特创作中的献祭主题。
在意识形态的运转过程中,选择替罪羊进行献祭的目的在于消除社会危机,清除不符合话语体系的异端。波特故事中的死亡和暴力的文化意义正在于此,其所选择的对象大多对特定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献祭主题在波特涉及家庭神话和婚姻神话的故事里体现得最为明显。《他》从经济角度表达了献祭主题。作为贫困南方家庭的弱智儿,“他”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压力和社交上的尴尬,显然是南方家庭神话中的不纯分子。韦伯一家也自然将“他”当成了替罪羊,让他缺衣少穿,危险的活儿都让他干,最后还把“他”送到公立的疗养所,彻底完成了净化团体的献祭行为。吴冰教授指出了故事悲剧的经济根源,认为《他》体现了“贫穷对人性的摧残。”(13)就其文化批判意图来说,《他》则表现了家庭神话对不合法存在的清除,使集体的焦虑在受害者身上得到了暂时的释放。《巫术》则表达了婚姻神话中的献祭。波特本人不幸的婚姻经历使她对婚姻献祭的感受尤深,故事中的妓女尼内特是她本人的写照,也喻指所有已婚女性。(14)故事中,尼内特不堪忍受妓院的虐待而出走,结果遭到一系列的报复,最终在“巫术”的力量下又回到了妓院。此故事实质上表达了婚姻神话对女性的控制和驯服,“巫术”则象征意识形态那不可抗拒的惩戒力量。
献祭的对象,即替罪羊,常常是那些异于常人的个体,要么具有外在的文化特征,要么具有生理上的病态特征。宗教和文化的特殊,或生病、精神错乱、遗传畸形、车祸伤残,甚而习惯与他人不一致等都可能成为受难者标记。(15)波特作品里与死亡和暴力意象相对应的那些“怪人”就是替罪羊。《他》中的替罪羊“他”是一个弱智儿;《午酒》中的希尔顿是懂得很少英语的外族人,平常与他人不太接触,只摆弄自己的口琴;《斯人已去》中的伊娃姑妈因为长相丑陋,不符合淑女神话的要求而被孤立。他们都因为自身的异质特征成为献祭的牺牲,被暴力剥夺了话语权并从团体中(象征性地)清洗了。(16)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替罪羊的异质性是神话系统着力清除的对象,但有时候它恰恰来自意识形态本身。比如在淑女神话中,女孩被要求保持圣洁。对性的惧怕导致她们尽量保持孩童的身材,为此厌食以达到体重下降、控制月经的目的。这种情况经常导致“萎黄病”(chlorosis)的发生,而身体的疾患又会变成淑女神话清除的对象。(17)这是一个两难的、无以反抗的境地,表现了意识形态对其献祭对象所拥有的绝对霸权。
不过,波特故事里的替罪羊并非总如福尔纳塔若—尼尔所言的弱势人物。《灰色骑土灰色马》中朝气蓬勃的亚当被称作“羔羊”,是战争神话的牺牲。《斯人已去》中行为叛逆的艾米姑妈婚后不久即去世,充当了淑女神话的牺牲。他们这类的替罪羊并非可怜可悲的弱者,相反却形象光鲜,甚至成为公众膜拜和铭记的对象。这种奇怪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神话中存在“替罪羊的神圣化”机制。吉拉尔指出,“神话高速运转的结果是受害者的神圣化,致使我们看不见、甚至消除掉迫害的失真。”(18)也就是说,替罪羊机制不仅仅只有群体迫害这一次转化过程,还有圣化替罪羊的二次转化过程。这第二次的转化完全倒转了迫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使实际上处于被动地位的受害者变成了团体里的支配因素。波特笔下那些作为文化符号的角色,如亚当和艾米,都属于替罪羊机制第二次转化的产物。即便那些完全处于弱势的受害者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个圣化过程,如《他》中的弱智儿主人公。“他”在故事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始终都以英文中大写的“他”相代。这一方面暗示了他身份的丧失,另一方面也点出了其身份的不同一般:《圣经》中对上帝的称呼也是如此。可以看出,故事为“他”选择这样的命名其实颇具深意,概括了替罪羊机制中迫害和圣化两个步骤的转化过程,将牺牲者刻画成了耶稣式的祭品。
献祭是一个仪式表演,经常通过公共仪式来加强整个精神共同体的凝聚性。《绽放的紫荆》中为“革命烈士”们举行的祭礼是在广场上举行的盛大集会,与天主教徒赞美圣母的集会同时举行,在互为映衬中突出了彼此的仪式性。(19)波特笔下的献祭一般也通过仪式表现出来:对社会团体中不纯分子的清洗常常与某个牺牲动物的行为对照发生,且地点基本上是公共场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波特故事中充斥着动物意象。《他》中的杀猪崽一幕预示了韦伯夫人将舍弃“他”,正如她牺牲猪崽去维持家庭神话一样。“他”在故事中完全失语,甚至木板砸了头、受凶猛的家畜惊吓时都没有丝毫声响,只有在两个场合发出过声音:一次是看到韦伯夫人宰杀用来待客的小猪崽的鲜血,他“被震击般地抽了一口气”(52);另一次是被送出家门,他流泪时“啜泣,发出吞咽的声响”(58)。这两次都是向家庭神话的献祭仪式,故事安排“他”唯独在这时出声,深意不言而喻。《斯人已去》中的加百利在亡妻艾米死后多年仍然刻意维持着自己骑士爱人的形象,带着艾米的马驹参加赛马。过度劳累的马驹鼻血直流,膝盖不停地发抖。《坟》中米兰达通过一只被射杀的怀孕母兔和死于分娩的妈妈了解到家庭神话中每位女性都必须经历血的仪式和祭礼。
从献祭的角度理解,波特的一些经典故事会呈现出新的意义。《玛利亚·康赛普西翁》便是一例。墨西哥姑娘玛利亚·康赛普西翁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幸福的妻子,却发现丈夫胡安与同村姑娘玛利亚·罗莎偷情。后来他们私奔,在此期间康赛普西翁的孩子夭折。一段时间后,胡安带着即将临盆的罗莎返回村庄。悲愤的康赛普西翁杀了罗莎,收养了她的孩子。同村的妇女群体共同保护康赛普西翁,使她免受法律惩罚。故事展现了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炮制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神话以及这个神话对女性行为的塑造。在这个神话中,作为神圣婚姻入侵者的罗莎是必须要被清除的对象。她以娼妓的形象介入到他人的婚姻中,她的名字(Rosa)和玫瑰有关,暗示着风情、性感和激情之爱。对女性行为规范的违反是她的受难者标记。她的死亡也呼应着一次动物宰杀:康赛普西翁在故事中一共有两次杀生行为,即杀鸡为丈夫的老板做饭和刺杀罗莎。在故事中以复数出现的整个群体普遍接受了婚姻神话,同意选择罗莎进行献祭。故事的结尾是一个经典的“圣母抱子”情景:康赛普西翁抱着罗莎的孩子,获得了“奇怪的、醒着的幸福感”(21)。此外,从表面看,以怀孕女人出现、名字也是“怀孕”之意的康赛普西翁(Concepción)显然是一个“好”女人形象。但她与罗莎其实并非完全对立,而有内在同质性:她们的名字相同(Maria),取自基督教神话中的圣母,而且罗莎最后也怀上了胡安的孩子。她们共同代表了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双重形象。因此,家庭神话的献祭其实是整个女性群体。康赛普西翁所谋杀的是自己的另一面,最终的“和谐”结尾也不过是替罪羊的神圣化。
三、挽歌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特定结构的世界中,某种社会价值被赋予客观性的外表而成为神圣律令,决定了公共生活的本质和模式。献祭则通过仪式化的暴力加强了这种价值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但自称“总怀着一颗流浪出走的心”(20)的波特反对生活中的任何特定结构和强制性规范,在创作中表现出一种“拒绝的艺术”。(21)这就是其作品深层结构的第三部分:挽歌。挽歌主题通过一些特立独行的“挽歌手”形象表现出来。他们脱离了精神共同体,表现出对话语体系的怀疑与拒绝,最终通过个人的“反仪式”行为表达对献祭牺牲品的同情与体恤。
对神话的怀疑在波特作品中并不罕见。波特作品“并不涉及一个终极价值体系”,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具有可信度。(22)《斯人已去》中伊娃对有关淑女的官方叙事的声讨,《碎镜》中罗瑟琳对持家仪式的中断,《烈士》中女模特对革命艺术家的抛弃,《目击者》中黑奴吉比利对白色天堂的拒绝等等都宣告了各个范围神话的去功能化。神话对受众的控制是感性层面的,强调无条件的接受和服从,而怀疑者们通过理性抵制了意识形态的宣传。从波特对宗教话语的批判可见一斑:“我们就像在地窖里摸黑前行,能够指引我们的只有微弱的理性之光,但那边走来了一个神学者将这唯一的光亮给吹灭了。”(23)《遭弃的韦瑟罗尔奶奶》在主旨和细节上都呼应着这番话。韦瑟罗尔奶奶一生以宗教的要求规范自我,却在弥留之际没有看到上帝的救赎,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吹灭了床头的烛光。(24)这被称为波特“最可怕的故事”,因为它对天主教信仰提出质疑,冲破了宗教话语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桎梏。(25)
然而,波特笔下真正的“挽歌手”比这些怀疑者们要更进一步。除了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外,挽歌手并未放弃感性的认同:他们与献祭的牺牲感同身受,表现出强烈的悲悯意识。《绽放的紫荆》中的劳拉除了在墨西哥革命的狂热中独善其身外,还对运动的牺牲品尤金尼奥表现出理解、内疚和不安。在尤金尼奥被布拉齐奥尼“清除”后,身为布拉齐奥尼秘书的劳拉感觉自己也是帮凶,对神话和献祭的洞察和感受更进了一层。故事结尾她所做的吞食尤金尼奥血肉的噩梦体现了她对社会运动之实质的认识。表面上类似于牧歌田园诗的《假日》实际上揭露了乡村家庭神话的暴力,着意表现了挽歌主题。为了维持家庭的体面,幼时因病致残的大女儿竟被全家人漠视、整日关在厨房里干活。而叙述者“我”借助敏锐细腻的感受力体会到她对生活的强烈渴望。震撼中,“我”“想要发出一声她那种如狗吠般的绝望叫声,却又咽下,成为永远的魅影”(434)。这咽下去的叫声便是献给神话牺牲品的一曲挽歌。
波特作品中的“挽歌手”一般都是一位知识女性,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角色是米兰达。这个知识女性形象多次出现,其经历与波特本人极为相似。波特称“米兰达”为“我的另用名”。她很小就非常迷恋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她的“米兰达”不是取自莎翁《暴风雨》中女主角名字的拉丁义(“奇怪且迷人的”),而是西班牙语“注视的人”。(26)可见,波特笔下的米兰达避开了女性的刻板形象(女巫或妓女),通过注视形成了自己认知世界的独特方式。她看穿了社会话语建构的神话,痛感于献祭的血腥,通过自己的吟咏为那些牺牲守灵。在《灰色骑士灰色马》中,米兰达的“挽歌手”形象得到了最鲜明的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政客们炮制的关于民主、理想和爱国的神话,迫使包括米兰达和她的爱人亚当在内的年轻人奔赴战场。米兰达在故事中的身份很有象征意义:她的职业是戏剧评论记者,负责观看并评论舞台上所上演的一切。在以一战为背景的社会戏剧中,她也扮演着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对她来说,战争话语就是“瘟疫”(299)。她和亚当经常在一起唱一首名为《灰色骑士灰色马》的民歌,大意是死神带走了一家人,只剩下女歌手在吟唱哀悼。后来亚当死去,剩下米兰达一人追思无限,呼应了民歌中描绘的情景。乔治·奇塔姆认为,米兰达的一生……都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求索,她力图在对固有体系暴政的逃避和对固有体系未能解释的死亡的惧怕这两种心态之间取得平衡。(27)这低估了米兰达在波特创作中的意义,从《灰色骑士灰色马》可以看出,她不仅仅是怀疑者,也承担了为献祭的牺牲举行挽歌仪式这一任务。
在神话和献祭中,“仪式表演本身就引导人们接受权威”。(28)亦即仪式的本质是公共性的,意在强化公共话语的控制力。对于波特作品中的挽歌手来说,他们也通过带有浓重仪式色彩的行为来表达自我感受。不过,他们的“仪式”意在对抗公共话语,强调个人感受。就仪式的严格定义来说,这其实是“反仪式”。正是通过这些反仪式,挽歌手们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
仪式与话语息息相关。反仪式也致力于建立一种反抗性话语和适合个体经历的私人话语。这在波特创作中的表现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策略性的沉默”(29)。这类挽歌手没有明显的言说行为,而在行为和思想上表现出反仪式的特征,以年纪尚幼的米兰达和《绽放的紫荆》中的劳拉为主要代表。米兰达幼时就对大人们崇拜的事情很疑惑,因为与她自己的所见所感不一样。但大人当然不会允许小女孩“胡说”,她因此通过一些看似幼稚的反仪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无花果树》中,她埋葬了一只小鸡,听到它在土里哭着向她呼救。对动物的同情隐喻了对神话牺牲品的同情,她在《斯人已去》里的顿悟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让他们去互相讲他们的故事吧……至少我知道我所经受的真相。”(220-21)劳拉是社会运动领导人布拉齐奥尼的女秘书,人人都疯狂崇拜他,但劳拉却拒绝他的求欢,坚守自己“臭名昭著”的贞洁。她还违背运动组织的规定,偷偷到教堂去做祷告,从宗教而非革命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放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来考察,这些看似私人选择的小事就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思维角度的变化体现了劳拉拒绝神话、同情牺牲的立场——所以那些牺牲在她梦中才会以提供血肉供他人吞吃的耶稣基督形象出现。与表现反仪式第一层次的静默无声不同,第二层次展现出在公共话语内部进行言说的能力,亦即用新的语言来对抗权威话语系统的控制,属于“边界书写”。(30)这在波特故事中通常借“在镜子前面言说”这一行为意象得以体现。《碎镜》集中呈现了这一主题。罗瑟琳整天在家里照料年长自己30岁的丈夫,情爱和性爱的双重缺失使她的生活了无生趣。但受制于规训女性的各种社会话语,她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在卧室里放一面碎裂的镜子,整天以向别人述说自己虚构的梦境为乐。碎裂的镜子象征着对社会话语控制下的现实世界的拒绝,而个人言说则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想象世界。
波特的经典名篇《灰色骑士灰色马》所体现的社会思想在其创作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糅合了两种反仪式话语并体现了它们之间的渐变过程。起初米兰达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采取策略性的沉默:她与其他人一起为战争大唱赞歌,但会“满面羞惭地笑”(294);后来在昏迷中,她感觉自己“聋了、瞎了、哑了,再也感觉不到身体的各部分,完全抛弃了所有人世的目的”,“只剩下一个闪耀的、自足的存在,不依赖任何外在事物、不接受任何诱惑和鼓惑”(310)。她的感受明显具有死亡和重生的意味,暗示着脱离了旧意识形态的控制而获得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在沉默之外,她重复最多的反仪式动作是“思念亚当”,故事中有大段的意识流描写。除了体现波特写作技巧的革新外,意识流实质体现了第一层次的反仪式。与此相辅相成,米兰达的新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在战争的喧嚣中,她和亚当经常进行私密的交谈,彼此“有了新的语言”(296)。他们就如所唱的民歌中所预示的歌者,负责对战争神话的牺牲进行哀悼。在故事结尾,刚从死亡线上回转的米兰达在镜子前给死去的爱人写信。毫无疑问,经历了死亡和重生的米兰达在镜子前所写的内容必然是边界书写,是一首献给神话牺牲品的挽歌。
四、结语
美国的20世纪早期是标新立异、拒绝权威的反偶像崇拜时代,先前引导人们生活的诸多规范都受到了重新审视和批判。许多现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反思意识。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波特通过短篇故事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美国大百科全书对她的评价是:“用如此少的作品赢得如此高的赞誉,少有人在。”(31)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从生活中获得意义,波特的大手笔也来自对社会文化运转机制的深刻理解。她认识到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控制力量,揭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暴力方式,并对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表示同情。这种社会认识在她的创作中转化为撼动人心的“神话—献祭—挽歌”这一深层结构。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莱斯利·菲德勒的评价才显得恰如其分:南方女性作家都是“女性的福克纳”,在这个群体里,只有波特最接近这位父辈文风的“奇异张力和男性力量”。(32)
注释:
①芭芭拉·汤姆森《凯瑟琳·安·波特访谈录》,杨向荣译,载《青年文学》2007年第9期,第126-27页。
②Gary M Ciuba,"One Singer Left to Mourn:Death and Discourse in Porter's 'Pale Horse,Pale Rider'," in South Atlantic Review 61.1 (1996) 55-76.p.58.
③Andrea K Frankwitz,"Katherine Anne Porter's Miranda Stories:A Commentary on the Cultural Ideologies of Gender Identity," in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57.3 (2004) 473-88.p.473.
④Janis P Stout," 'Something of a Reputation as a Radical':Katherine Anne Porter's Shifting Politics," in South Central Review 10.1 (1993) 49-66.
⑤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⑥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⑦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138页。
⑧波特在墨西哥积极参与了当地的社会运动。1921年,墨西哥领导人下令将一批外国激进主义分子驱逐出境,波特名列其中。她由于支票账户被冻结而举步维艰,甚至到了趁朋友不在家偷吃食物的地步。非人道的待遇激起了她对革命专制的极大反感。而她与左倾的美国作家协会的友好关系也因为憎恶其帮派作风于30年代末破裂。
⑨由笔者译自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San Diego:HBJ,1979),第91-92页。以下的同源文本引用将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
⑩Sarah Youngblood,"Structure and Imagery in Katherine Anne Porter's 'Pale Horse,Pale Rider' ," in Critical Essays on Katherine Anne Porter,ed.Darlene Harbour Unrue (NY:G.K.Hall,1997) 195.
(11)M.K Fornataro-Neil,"Constructed Narratives and Writing Identity in the Fiction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 in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4.3 (1998)349-361.
(12)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第19页。尽管吉拉尔探讨的是平常意义上的神话,即口口相传的故事,但他从社会学的视角入手解读社会运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其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类同。
(13)吴冰《凯瑟琳·安·波特和她精湛的小说艺术》,载《外国文学》1996年第4期,第36页。
(14)Darlene Harbour Unrue,"Katherine Anne Porter's ' Magic':Levels of Meaning in a Neglected Masterpiece," in Southern Quarterly 42.3 (2004) 55-63.p.58.波特的首次婚姻非常不幸,丈夫滥施暴力,给她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她的四次婚姻(一说五次)和无数的恋爱都以失败告终。
(15)勒内·吉拉尔《替罪羊》,第21-23页。
(16)在故事中,说话能力往往是权力的象征。如《他》中的韦伯夫人总是喋喋不休地发布命令,向邻居解释,而“他”在全文中没有说过一句话;《午酒》中的希尔顿则沉默寡言到令人奇怪的地步,从来不为自己争取什么;《斯人已去》的伊娃姑妈早早为家庭所弃,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但在投身女权运动后变得善于论辩。这些描写体现了话语系统的霸权。
(17)Lorraine DiCicco,"The Disease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s Greensick Girls in 'Old Mortality '," in Southern Literary Journal 33.2 (2001) 80-98.
(18)勒内·吉拉尔《替罪羊》,第62页。
(19)广场是透明的公共场所,与人群保持着持续的、无阻隔的互动关系,尤其适合公共仪式举行。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
(20)芭芭拉·汤姆森《凯瑟琳·安·波特访谈录》,第121页。
(21)William L Nance,Katherine Anne Porter and the Art of Rejection (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4)6-8.
(22)Leon Gotffried,"Death's Other Kingdom:Dantesque and Theological Symbolism in Flowering Judas," in PMLA 84.1(1969)112-24.p.112.
(23)Joan Givner,Katherine Anne Porter:A Life (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1 ) 258.
(24)波特是天主教徒,因而故事中对韦瑟罗尔奶奶弥留仪式的刻画也遵从了天主教规定。天主教会规定,在教徒弥留之际,须为其举行临终涂油礼(extreme unction)。在该仪式中,弥留者床旁必须有点亮的蜡烛,神甫必须在场,为弥留者举行忏悔、抹油等一系列仪式,帮助弥留者向此世告别、踏上去天堂之路。
(25)Darlene Harbour Rurue,Understanding Katherine Anne Porter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88) 75.
(26)Elaine Showalter,Sister's Choice: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Oxford:Clarendon,1991 ) 36.
(27)George Cheatham,"Death and Repetition in Porter's Miranda Stori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61.4 (1989) 610 -624.
(28)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阐释》,第144页。
(29)短语借用自Janis P Stout,Strategies of Reticence:Silence and Meaning in the Works of Jane Austin,Willa Cather,Katherine Anne Porter,and Joan Didion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90) 185.
(30)短语借用自Stout,"Katherine Anne Porter's 'The Old Order':Writing in the Borderlands," in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34.4 (1997) 493-505,493-494; Catherine Himmel Wright,"Crossing Over:Katherine Anne Porter's 'Pale Horse,Pale Rider' as Urban Western," in Mississippi Quarterly 58.3-4 (2005)719-736.
(31)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Vol.22 (Danbury:Grolier Incorporated,1986) 424.
(32)Leslie Fiedler,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New York:Anchor Books,1992) 475-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