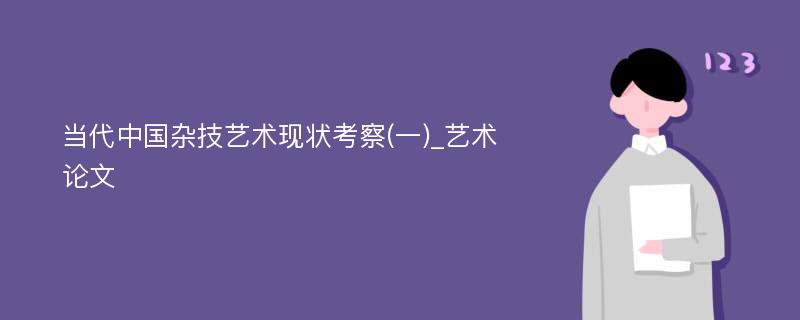
当代中国杂技艺术现状扫描(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技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现状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节目标题,是一个在我们日常的文化消费与艺术鉴赏中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舞台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必须环节。大到一台晚会,一出戏,小到一个舞蹈,一个小品,都有着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标题,以便把这个节目与其它的同类或异类作品相区别开来。
就一般而言,一个节目的标题,体现的是创作者对这个节目或内容、或主题、或立意、或形式的高度概括,在它的深层,涵藏着的是创作者的艺术观念与艺术追求。换言之也就是说,节目标题是创作者艺术观念与艺术追求的一种浓缩了的理性表达。
对消费与鉴赏而言,节目标题则具有指南的意义。
在我们的舞台艺术中,如音乐、舞蹈、戏剧……节目标题一般都是以独有的个性化形式出现而忌讳类型化。当一个标题被使用后,一般不会再有第二个相同的标题出现,在一些领域,只要标题知识产权所有者进入法律程序,标题还可受到法律的保护。节目标题的个性化现象是艺术个性本质的一种反映,也是艺术发展的一种必然。
但这个在舞台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带规律性的现象,却有个例外,那就是我们的传统杂技。
《辞海》关于杂技定义的文字表述为:
“杂技——表演艺术的一种,包括蹬技、手技、顶技、踩技、口技、车技、武术、爬杆、走索以及各种民间杂耍等,通常也把戏法、魔术、马戏、驯兽包括在内。”
“杂”为多种多样,“技”为技巧、技艺。当把“杂”与“技”合成为一个词用以界定一种艺术门类时,“杂技”便具有了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在本意的层面上,是对多种多样技的集合的总称,是对“杂技”这种艺术门类构成成分的表达;在艺术分类的层面上,标明“杂技”是区别于舞剧、歌剧、话剧、京剧……等艺术门类而独成一家的艺术样式。即是说,在现象层面,它概括了事物的性质,在艺术层面,它标示出了杂技的基本的美学特征。
杂技的技,就一般而言,都源于生活,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其相对应的形态。虽然杂技的技与生活中的技在形式上相同或相近,但它们之间在意义上却有着重要的不同。当技在人们的生活中作为生活的一种手段被运用时,技是以它的原本意义——实用的功利意义而存在;而在杂技范畴里,技的被掌握和使用,则超越了实用的功利层面上升为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技的表演成为观众欣赏的对象。
当技从实用的功利转换为非功利的审美时,也就成了艺术的一种——杂技艺术。在这里,“艺术”是指技巧表演的非功利审美属性,而“技”则是杂技这种艺术门类的本质属性及其基本特征。
传统杂技的演出,就是各种各样的技的表演:蹬技、手技、顶技、踩技、口技、车技……因此,在传统杂技节目标题中(本文所指的杂技节目不含魔术、滑稽、训兽类),由于其艺术构成的特殊性,节目标题的特征是类型化,表达的是技巧的类型。在传统杂技的演出海报或节目单上,除了表演单位的名称不同外,然后就是各种相同的技巧类型节目的排列:如车技、顶技、皮条、钻圈、柔术、转碟、顶碗……传统的杂技节目标题,明白无误地标示了该节目的内容及形式,同时,它也是杂技自我的一种本质界定——对某种技的表演。
在这种类型杂技节目的表演形式中,作为潜在的、引导着节目走向的艺术观念所关注、所追求的焦点,是对技的表现与展示。
由于历史的原因,传统杂技的这种标题形式不是来自某个特定的创作者,而是一种民间的约定俗成,它是杂技这种表演形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
传统杂技这种沿袭了久远历史的节目标题形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开明,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原来的一统天下开始发生裂变,新的节目标题形式:主副标题并用和单独主题的节目标题形式开始出现并迅速扩展开来。
经过二十余年来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创造,今天,杂技节目标题形式已经从过去类型化的天下一统发展为现今四分天下的多元格局。标题杂技节目、主题杂技晚会、杂技剧等节目标题形式的出现,是杂技在变革创新中完成了从技向艺转换的历史性跨越的浓缩反映。以杂技节目标题的发展变化为切入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杂技及其艺术观念发展变化的历史脉络和丰硕成果。
四分天下之一——类型杂技节目
类型杂技节目,是指以技巧作为节目标题的杂技节目,如顶碗、钻圈、皮条、爬杆、车技、手技、柔术、跳板、蹬技……这种节目标题所指的不是某一个特定的节目,而是对某种类型节目的泛指。
中国的杂技,从诞生以来一直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基本上都是类型杂技节目,即便到今天,类型杂技节目也是一般杂技团的日常演出的主体形式。
由于杂技这种艺术样式无语言、无故事、无个性人物的艺术特点,因此,杂技形式的意义就特别突出。
所谓杂技的形式,即是杂技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技的完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杂技的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
由于杂技在内容与形式的合一,杂技的形式便是具有了确定意义的符号性质,在技的完成过程中所展示的造型以及平衡、对称、倾斜、线条、力量……等形式美,便以其意义的直接性诉诸观众的审美观照之中。因此,杂技不需要借助其他辅助手段便可以得到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知识背景、不同信仰的观众的认同与感知。
杂技的形式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内容的意义,但并不是说形式就简单地等于内容,杂技通过对技的完成过程所揭示出来的人类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方式及对人自身巨大潜力的张扬中所蕴含的相对独立的深刻性,是杂技美学品格和审美价值得以展开的基点。
就一般而言,杂技的表演是以技巧的难为其基本特征的。难度越高,其价值就越大。人们观看杂技表演,审美评价的焦点,一般都集中在技巧的难度上。但是,难,作为一种形容词,在它所表示的是人对某种事物认识和把握的程度,难,并不就等于是美。在杂技的表演中,高难技巧之所以成为杂技审美价值的核心,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是因为其中经过了蕴含在形式中的意义——内容——作为转换环节而使形式具有了自己独有的审美价值。
在杂技的表演中,从表演对象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物的驾驭——如车技、晃板、转碟……另一类则主要是对人自身的身体的驾驭——如柔术、顶技……
在对物的驾驭类节目中,主要体现的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刻度。
比如稳定与平衡。
经验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在平面与平面为接触面或在多支撑点的物体上,才能构成人与物的稳定与平衡,这是常识,也是规律,是对规律认识把握后形成的常识。但在杂技《小管晃板》和《大球高车踢碗》之类节目中,人们看到的则是一种与日常生活中所认识的规律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现象:杂技演员在球面与球面为接触面的物体上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和平衡。《小管晃板》让人们看到,在三节或四节以不同球面方向相叠加在一起的小管上,各节管子在压力的作用下虽然不停地向不同的方向滑动,但演员依旧可以在多节滑动的管上作各种动作和技巧表演;大球与独轮车都是稳定性极弱的球面物体,而杂技演员不仅在大球上骑独轮高车,而且还要在独轮高车上用脚将碗准确地踢到头上。这类节目所展示的人类对平衡与稳定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并没有停留在我们在平常生活中认知的水平上,通过《小管晃板》和《大球高车踢碗》之类节目的表演向人们揭示,即便在多个球面相加的物体上,人依旧可以在上面保持平衡和稳定。无疑,杂技演员在球面与球面为接触面物体上所保持的这种平衡和稳定,标志着人类对稳定与平衡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的深化,通过杂技的表演,把这种对稳定与平衡规律认识和把握的深化用艺术的形式诉诸观众,使观众在审美之中感知到人类自身对客观世界规律认识与把握的深刻进步。
在以人自身的身体为驾驭对象的这类杂技节目中,表现的是对人类自身极限能力的挑战,对人自身巨大潜力的张扬。
如各种倒立技巧所展示的支撑力和控制力,各类有底座节目底座演员所具有的承受力,空翻技巧的弹跳力和人体在空中旋转时的控制力,柔术类节目所展现的人体的柔软度……等。可以说,一个杂技节目的表演,就是对人的巨大潜力的一次张扬,创造一个新的杂技节目,就是一次对人自身极限能力的成功挑战。
“如《顶碗》,早在汉代‘百戏’中即已出现,河南南阳出土的画像砖中,已有‘顶碗单手倒立’的生动形象。本世纪五十年代后,它得到了飞速发展:夏菊花首先在全面继承古老头顶技巧的基础上,大胆设想了倒立脚夹碗这一新颖技巧,从而为这一传统形式带来了重大突破;战士杂技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脚碗造型,郝美英指导下的顶碗与滚杯结合,为顶碗开辟了新园地,发展了双手各捧一摞碗在仅有1.5平米的圆桌上连翻空心跟斗的新技巧:高文珍将头顶与脚蹬有机结合,创造了‘磨碗’这一崭新动作;六十年代,上海的邱涌泉、王莹莹进一步丰富了碗的头顶动作;杭州的王一敏、刘红俊创造了两人在双层双飞燕上倒立又起倒立的双层双飞燕顶叠顶的高难绝技;七十年代河北省万献惠、万献存姊妹的双顶碗轰动了杂技界,她们以‘头上单手顶脚夹碗’等一系列高难新技巧,把顶碗单手顶的动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上海的蒋正平、王月云又表演了‘顶碗单手顶脚面夹碗打滚’和‘举顶下腰’等一系列地面难而美的新动作;八十年代,广州市杂技团的饶祥生、蔡淑慈、戴文霞的三人顶碗,以‘头顶双人双层夹脖顶过高梯’的新颖绝技,轰动了世界杂坛……”
从以上所引的唐莹在《杂技:超常的艺术》—书中对顶碗发展过程的描述来看,我们可以说,一次《顶碗》的发展创新,就是一次对人的潜力张扬的新胜利,一次顶碗技巧的新创造,就将出现一位向人的极限能力挑战的英雄,在这个意义上,一部“顶碗”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英雄史。
在杂技的表演中,一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办不到或不可能想象的事,在杂技演员那里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杂技表演所体现的对人的巨大潜在能力的张扬,使观众在审美欣赏中产生的是对人自身的崇拜,观众在观看杂技时被激发出来的是振奋,是力量,是勇敢,是无畏,是对人自身生命力的英雄体验。
观看杂技,不会使人产生怜悯,产生悲痛,产生忧愁,而是使人产生自豪,产生崇高,产生对人巨大潜力的崇拜。观众在观看杂技时看到的,不只是节目的外在形式,同时还通过这外在形式看到人自身生命力的英雄再现,越是高难技巧,越是能展示技所蕴含的英雄品格。
不论是从杂技技巧的完成过程来看,从杂技的审美价值看,还是从观众的审美感受看,杂技的技所蕴含和表现的都是人自身的英雄行为,它所激发的都是英雄意识,因此,杂技演员在展示技巧的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征服性的英雄行为,便构成了杂技美的基本内涵。而所谓的难,也因技在完成过程中所展示的英雄意义而转换为崇高的美感。因此,从杂技的本质上说,杂技是一种充满着英雄意义的艺术。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的角度来审视类型杂技节目时,类型杂技节目不论从内容、从形式、从美学、还是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类型杂技节目作为一种节目类型其内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类节目虽然在标题形式上仍然保持着类型的特点,但不论在艺术观念、艺术表现、美学追求、客观效果等方面,都已经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这里把他们分别界定为: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和新创作的类型杂技节目。
关于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
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主要是指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以前流传下来的节目类型及其表演形式。这类节目是传统杂技基本的表演形式,同时也体现着传统杂技基本的标题形式。
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在表演上的美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特征一:无角色的表演
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表演者虽然也对自己进行化妆造型,但这种化妆造型在一般意义上并不改变表演者的自然人身份,在技的完成过程中,表演者都直接以自然人的身份进行技的表演,在表演者和技的完成过程之间并没有一般表演艺术门类都具有的美学特征——以“我”(演员)——扮演“非我”(角色)。
在舞台表演艺术中,用角色这特定的艺术形象取代演员的自我存在,是表演艺术极其重要的美学特征。因为表演艺术的本质就是以角色的非我代替演员的自我,用演员的自我去扮演艺术中的非我。在表演艺术范畴内,演员只要一进入表演状态,他的自我的自然形象就必需被艺术的非我遮掩起来,观众欣赏到的是演员创造的人物、角色,也即是非我的艺术形象。从艺术美学的角度看,不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论,是布来希特的间离效果论,还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的表现论,不论是舞蹈,还是戏剧,只要进入舞台表演艺术的殿堂,都将接受这一艺术美学法则的制约。
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传统类型杂技节目的表演,则是演员的自我在直接进行技巧的表演,而不是演员对角色的表演。在这种类型杂技节目的表演形式中,作为潜在的、引导着节目走向的艺术观念所关注、所追求的,是技,是对技的展现过程。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在传统类型杂技节目的艺术观念里可以说还没有树立“演员对角色的表演”这样一种美学概念。
特征二:纯技巧的表演
在传统类型杂技节目中,由于不存在对角色的表演,情节、情感、情绪、意境等文化内涵便因为没有依附的支撑点而难以进入到节目当中,因此,传统类型杂技节目便只是一种纯技巧的表演。技的完成过程既是节目的外在形式,也是节目的内容所在。典型的传统类型杂技节目的表演,当下,在中国第一个以杂技为主题建立的主题公园——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江湖城中有真实的再现。在那种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中,除了对技的展示外,节目一般不再拥有其他的第二种意义。
特征三:处于空白状态的演出空间
由于表演者身份的直接性和表演节目的纯技巧性,传统类型杂技节目的演出环境(舞台)所提供的便只是一个能够展现技巧的空间,在表演过程中,这个空间没有特定的典型意义和个别的规定性,就意义这个层面来看,这个空间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特征四:缺乏艺术个性与情感表达的音乐伴奏
由于前面三个因素的存在,在传统类型杂技节目中,音乐(包括锣、鼓一类的打击乐)的主要任务便只停留在烘托气氛、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层面,因此,就一般而言,这个层面的音乐基本上不具备独有的艺术个性和对情感与意义进行表达的追求与能力。
在这种传统类型杂技节目的演出中,一台晚会,就是多种技巧表演的集合。
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由于缺乏文化的个别性,因此,尽管各个杂技表演团体之间在同一种类型技巧的表演上存在着难易、高低之分,但由于技的相似性,难免给观众留下一种“千团一面”的相似感。
关于新创作的类型杂技节目
新创作的类型杂技节目主要是指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创作的以类型节目标题为标题的杂技节目。
之所把类型杂技节目再细分为“传统的”和“新创作”的两种类型,是因为本文在对杂技节目进行分类时,不是以节目自身所拥有的艺术品格和节目所具有的美学意义进行节目分类,而是以节目的标题作为分类的标准,因此,相当部分新创作的类型杂技节目虽然被归类为类型杂技节目,但这些节目不论是在创意构思上,还是在艺术体现上,其所具有的美学价值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与传统的类型杂技节目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如果我们站在美学的层面细究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具有质的意义。
比如:
内蒙古杂技团在2004年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狮奖、2007年先后获第二十三届意大利“金色马戏节”金奖、第二十八届法国明日世界杂技节银奖的《五人踢碗》,是五个演员在高达2米的独轮车上表演踢碗的节目。
就技巧而言,由于独轮高车本身的局限,高车踢碗可供发挥创造的空间并不是那么大。但由于节目的创作者以其智慧的眼光把这种技巧融进了草原文化之中,《五人踢碗》除了让观众对技巧的高难与精彩深深的惊叹与折服外,同时还以其独特悠久的蒙古族文化传递出浓浓的大草原风情。
在高亢、悠扬的马头琴旋律与蒙古长调的歌声中,一群身着蒙古族长袍的女孩,在一种带有仪式意义的、以具有蒙古族文化特征的盅碗舞为基本动作元素的律动中,凸现着她们双手捧着的银碗的意义,五位身穿经过艺术加工的蒙古族服饰的姑娘骑着独轮车进来了,银碗,从身着蒙古族长袍的女孩手中,庄严的、仪式般的递到了独轮车姑娘的手中——作为“道具”的碗,在一种完美的形式中完成了演员之间的相互传递——一个精美的细节,体现了创作者艺术手法的严谨——仪式在这种交接中得到了合理的、完美的延续——银碗,由此从地面放飞到天空——在长调的旋律中,随着滚动的车轮不停地在空中飞舞着——继个人踢四个碗、踢五个碗后,是集体的丁字踢、交叉踢、链式后踢等技巧,在之后,是创新的前后二对踢转身接;四人四角定位踢,中间一人旋转接;一人中间前后踢,四人转圈接;四人踢,一人连接二十八个碗等高难动作。
节目的最后,姑娘们双手捧着洁白的哈达,围着高举的银碗、银壶组成的造型,既象征着仪式的完成,也象征着仪式的隆重与高贵。踢碗这种技巧,因与蒙古族特有的文化元素的融合而获得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沈阳杂技团在2004年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狮奖的《转动地圈》,大幕拉开,一个小伙子矫健的越过了耸立在场地中央的地圈,就在这时,另一个小伙子挡住了他的去路,由此,引出了两帮互不服气的愣小伙子,他们一个个额头上系着发带,发式及颜色各不相同,再配以敞胸的坎肩,人物造型所张显的时代气息中凸显着他们之间个性的差异,这两帮青春负气的邻家男孩,为了显示自己比对方更强、更高、更有力,他们以地圈为比试的手段,五个不同方向转动着的地圈,就是他们争强斗胜的坐标,夏正琦的“四圈叉跳”、“五圈720度后空翻”;佟天舒的“五圈提入”、梁恒的“四圈折体跳”……这些高难度的技巧在这里成了角色之间力量比赛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动作形式的编排上,以既时尚又充满着青春活力的街舞为连接,节目以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造型和亲切简洁的情节结构,向人们演绎着今天发生在身边街头的生活片段。
山东省杂技团在2004年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狮奖的《蹬人》。节目虽然命名为《蹬人》,但节目的创作者却为《蹬人》这个节目设计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环境:一群男孩在一起玩耍,在这群男孩中,有一个不论从年龄、还是从个头看都是最小的一个的小不点男孩,他最小,但却是最强大的。节目开始时,小不点不紧不慢的溜达着,一个大男孩想上来欺负他时,他毫不费力的将他撂倒在地……节目中,他在这帮大哥哥们的前面趾高气扬,这些大哥哥们想教训这个小弟弟一下,但他一回头,大哥哥们便都害怕地蹲在他身后,就在这种玩耍的情节中,小不点引领着大哥哥们,把“6组单脚蹬站”,“双板单人前扑两周对传”,“6节站肩”……等难度极高的技巧揉进了情节之中,节目结束时,这帮大哥哥们终于轻而易举地把小不点撂倒在地上,然后一起开心的坏笑着跑掉,出人意外的结局使节目《蹬人》在一种可知可感的情节与人物关系中传递出一种幽默诙谐的审美意境。
在表演形式上,节目的创作者打破了传统的蹬人躺在固定的道具座子上蹬的形式,而改用演员为底座,这样,底座演员可以躺在任何一个空间完成技巧,又不影响翻腾跳跃的进行,在传、抛接人时还可自由的调换空间。在技巧上,打破了过去蹬技只是用脚来完成技巧的传统,发展了底座演员用手来接尖子演员的脚、用脚来接尖子演员的屁股……等这样一系列的手脚并用的技巧。
尽管离第六届杂技比赛已经很久了,但舞台上那个头裹花布巾的小不点与大块头诙谐较量的情节及其艺术形象却总是挥之不去……
前进杂技团在2004年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狮奖的《绸吊顶技》,节目的特点是在突出技巧的难度时,特别地注意节目艺术造型美,当四位表演者在“倒立平卧脚勾顶杯”中连成一排、接成十字随着飘舞的红绸在空中飞旋时,顿时令人产生一种类似观看飞行表演时飞机拖着彩色烟雾在蓝天飞翔时的壮观与美丽,那种技巧与造型相结合而产生的美,成了这个节目给我的第一印象。
战士杂技团在2000年第五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狮奖的《现代男女软功》,节目创作者的立意是表现生命的本体意识,因此,节目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动作的设计上,凸显着的是现代舞的内涵与韵味。
节目标题为《现代男女软功》,如果我们就技巧的角度,就“功”而言,这个节目确实拥有“卷腿过门元宝肘上单手顶”、“高元宝脚上拉顶”、“元宝腿上曲体单手顶”、“头顶旋转”……等许多的高难软功技巧,但如果我们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可以说节目中又没有一处是在“表演软功”,因为不论是从节目的创意、编排还是整体艺术效果来看,软功和舞的思维方式已彻底交融为同一的肢体语言,充满着韵律的动作设计与行云流水般的肢体语言,在诉说着一个美丽而又朦胧的故事,它似乎无所具象所指,但却又似在清晰地诉说着什么。也许,在没有文字提示的前提下,一般的观众未必都能从这个精美的表演中领悟到节目创作者的立意是在表现细胞的分裂、进而表现生命的顽强这样一种寓意,但也一定不会把这个节目看成只是一种“软功”的表演,在观看的过程中,观者一定能感受到蕴含在这个充满现代意识符号的肢体语言中某种难以言传的、朦胧而又深刻的文化内涵:也许,它可以是抽象的阳刚与阴柔的相济与互补,或许是具象的生命状态“上善若水”般的至柔至坚,也许可以是现实中浓情蜜意中的依偎眷念,或许是伊甸园里那诱人的圣洁原罪……
天津杂技团在1995年第四届全国杂技比赛中获金奖、1996年,在法国第十九届“明日”暨第十届“未来”世界马戏杂技节中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的《单手倒立》,尽管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但节目给人留下的印象却依旧难忘。就技巧而言,张婷表演的《单手倒立》可供创作者发挥想象空间的余地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就是在这个非常有限的空间中,《单手倒立》的创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赋予节目鲜明的现代印象派意识的多义与模糊,把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艺术形象留在了观者的脑海里:那以亮片编织图案的紧身服及缀有亮片头花构成的艺术造型,配以在优美的钢琴旋律中手臂与身体的抒缓摆动,那不就是荡漾在蓝色波涛中令人浮想联翩的美人鱼?!一次次的起顶、拉腰、汉水……是那样的轻柔,是那样的舒缓,众多的“力”在这充满梦幻般的意境中褪去了原本的阳刚,在粼粼波光中化为了飘柔的美,刚与柔的交融把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推到了一种极致。一次单手倒立造型,不就像一次足尖旋转?一次顶上横叉,不就是一次倒踢紫金冠?“单手倒立”的全过程,不就是一次美人鱼充满着魅力的生命展示?!
《单手倒立》从头到尾确确实实都是张婷在表演“单手倒立”,只是“单手倒立”被有别于传统杂技观念的新的艺术思维赋予了一种新的潜质,所以《单手倒立》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不是单手倒立这种技巧,而是单手倒立技巧所表述的那个充满了想象的童话般的意境:也许,她并不是那么具象的美人鱼,而是一种更为空灵的意境,像王曦之笔下的狂草,似贝多芬键盘上的音符……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爱好、不同的知识积累,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情感和不同的美来。
这类新创作的类型杂技节目,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其中一些节目的标题并不能完全表达该节目的内涵和意义,也不能完全准确的体现该节目的美学价值,或者说,这些节目的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已经超过了标题所拥有的意义。因为在这类节目中,不论是创作者的主观动机,还是节目所产生的客观效果,都已经不只是对一种技巧的表演,除了技巧以外,还有可知可感的或文化内涵、或情节、或意义,或意境,而这些节目中的文化内涵、情节、意义和意境,常常会成为观众审美意识关注的焦点,成为观众在观看节目后思考与回味的关节处。之所以这类具有可知可感的文化内涵、情节、意义和意境的节目被创作者冠为类型标题并作为一种现象一直存在,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我个人以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用技巧类型为节目标题可以表示创作者对杂技本体意识的坚守。因为在杂技界,一直存在着如何看待、解释、理解、运用杂技“本体”的论争与探讨,以类型节目名称作为新创作的节目标题,大概可以作为创作者对杂技“本体”的认同与理解的一种表达方式。
另一种可能是:对艺术实践与理论提升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的不确定与犹豫。即是说,存在着创作者还没有找到能更准确的表达创作者艺术理念的理论切入点和具体的表达形式,因此便采取“退一步”的策略,回到以类型为节目标题,虽然不尽如人意,但稳妥且不易发生争议。
前面所举的几个节目,有的突出角色,有的突出情节,有的突出意境……这些节目所拥有的技巧,不论是主观追求还是客观效果,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表达创作者艺术观念的载体而不是节目所要表达和追求的唯一,因此,便产生了节目标题不能充分涵盖节目内容和意义的客观效果。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种客观效果则是创作者所具有的现代艺术观念的流露和表达。
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在今天新创作的类型杂技节目中,创作者那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艺术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新创作的杂技类型节目。实践在证明,在今天杂技节目创作者的艺术观念中,对技巧的理解与运用,已经不像过去传统观念中的那样单一了,即便是类型杂技节目,除了对技巧难度的追求外,立意的确立、角色的塑造、情感的表达、情节的展开、环境的设置、动作的意义、文化的内涵、形式的美感……都已是节目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然关注的重要环节,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艺术观念经过二十余年来的实践积累,已经成为了创作者的自觉意识,正是借助于这种自觉的艺术观念的成熟,今天的杂技类型节目才焕发出那让人眼前一亮却又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