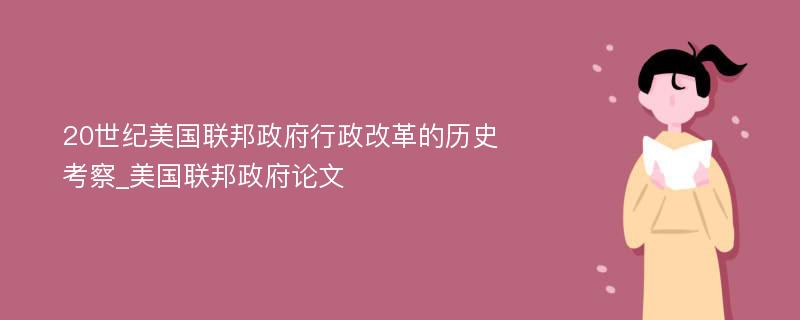
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政府论文,美国论文,行政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6-0050-11
20世纪的美国历史,是一部充满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历史。精简机构、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和整治官僚主义作风,是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应对问题的侧重点有别,政府在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所追求的目标上也有所差异。目前,从整体上研究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问题,学界现有的成果还不多见,所能见到的往往是零星的、分散的研究,并且这些成果大多从行政管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和研究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而缺少从历史学特别是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来考察这一问题。因此,以一个世纪作为宏大的历史画面,来探讨和研究这些改革在内容上的差异和目标上的转变,不仅有助于从微观上把握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管理本身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而且有助于从宏观上了解美国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演进与发展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一
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肇始于新旧世纪之交。20世纪初期,伴随企业科学化管理运动的方兴未艾,不仅科学管理意识和理念逐渐为美国社会所接受,而且由科学化管理运动所催生的“效率”一词更是家喻户晓,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美国政府管理中,“效率政府”已经取代19世纪的“绅士政府”、“大众政府”或“道德政府”,而成为“好政府”的代名词。因此,“效率政府”便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伴随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科学管理企业已经提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一时期西方企业科学化管理运动中,美国一马当先。因为当时“美国工商业的实践,不仅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正在发生着变化,而且企业越来越需要使用新的科学管理技术减少投入而增加产出”。[1](p.69)这一时期美国企业科学化管理运动是以“泰勒制度”(Taylorism)[2](preface)的创立作为主要标志的。20世纪初,由美国工程师泰勒提出了一套以提高工作效率为主要动机的企业管理新办法。这一套办法包括从企业中挑选出身体最强壮、动作最灵巧的工人,强迫他们极度紧张地工作,用秒或几分之一秒的时间为单位,记录下完成每一作业的时间,然后根据这些测定的时间结合全体工人的劳动情况,规定操作规程和时间定额,再根据这一“工作规范”,来决定每一个工人的工资和奖金。此后泰勒的名字便与“科学管理”和“工作效率”连在一起。“泰勒制度”为企业组织和管理生产提出了科学的管理原则和方法。“泰勒制度”创立以后,首先给美国的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伴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一制度也在美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不仅加速了工商企业的科学化管理运动,而且也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促进了公共机构科学化管理运动的展开。因此,“‘泰勒制度’同时对企业和政府管理如何进行产生了社会性和技术性的双重影响”。[1](p.69)
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公共机构管理,二者在本质上差别并不很大。因为它们都强调“管理效率”和“管理秩序”。在20世纪初美国科学化管理运动中,企业和政府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甚至管理内容上也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一,二者都处在一个完全相同的社会,并献身社会发展与进步;其二,二者共同建立在合理化哲学信念的基础上;其三,二者都相信科学和科学方法,并力图把科学管理方法应用到现实社会中的人事管理上;其四,二者都宣称信奉新的“上帝”——“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在美国公共管理机构中所进行的科学化管理运动,不仅是整个社会科学化管理的一个分支,而且也是企业科学化管理的一种延伸。因此,“‘泰勒制度’一问世,美国‘进步主义党人’立即将之奉为至宝加以信奉”。[3](p.84)因为科学化管理理念与“进步主义党人”改革家所倡导的政府应该是以“最好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观点是基本吻合的。“进步主义党人”认为,“19世纪末文官制度的建立,包括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只是联邦政府改革的第一步,而政府改革的第二步,应该是政府行政官员的职业化与科学化管理。”他们还主张,“政府应该根据其功能由职业官僚掌管。职业化和政府规模的合理化,是保证效率和消除浪费以及权力重叠的最好办法。”他们特别强调,政府的科学化管理,“不仅对州和地方政府层面是必要的,而且对联邦政府层面更是必需的”。[1](p.71)
在企业科学化管理运动和“进步主义党人”改革思想的启迪和推动下,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政府积极投身到社会科学化管理运动中。科学管理政府和行政效率,一时间成为政府管理中最时髦的话题。因此,这一时期中,从老罗斯福到胡佛,几乎每届联邦政府都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建立科学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提到政府工作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政府工作包括政治和行政两个部分。政治是法律的制定,行政是法律的执行。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为了防止政治在具体细节上影响行政,保证政府的连续和稳定,“必须把分别承担这两种功能的机构在法律上分开”。[4](p.15)但在美国政治实践中,甚至到1883年文官制度建立的时候,政府也并没有在理论上界定清楚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行政还远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和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它的功能和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1883年文官制度的建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联邦政府缺少稳定和连续的问题,但远没有解决由于政治与行政划分不清而带来的政府管理混乱及其效率问题。直到20世纪初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这些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
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首先在理论上承认和肯定了威尔逊总统早在19世纪末期所提出的“行政科学”的概念。如上文所谈到的,与企业管理有所不同的是,政府管理不仅涉及行政管理本身,而且还涉及政府中行政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政府不首先在理论上界定清楚这一概念,在实践中可能就无法实现有效的科学管理。早在1885年和1887年,当时还没有出任总统的威尔逊,在他的《行政随笔》[5](p.49)和《行政研究》[6](p.380)两篇文章中,已经在理论上阐发和界定了“行政科学”的概念。他指出:“行政是一种事务领域,因此,行政应该从政治的混乱与纷争中摆脱出来。”[6](p.370)威尔逊提出这一理论,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公共管理科学,以减少政治对行政的干扰,进而提高行政效率。但遗憾的是,威尔逊的理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20世纪初期,伴随政府科学化管理运动的展开,一些政府改革家,其中包括这一时期的几位总统,才接受了这一理论,并试图从理论中找到解决政府效率问题的办法。
在理论上接受了“行政科学”这一概念以后,美国联邦政府在实践中便致力于通过扩大“功绩制”的适用范围,来建立一个强大和独立的行政体制,进而适应政府科学化管理和进一步解决行政效率问题。
老罗斯福总统一上任,便把行政改革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扩大“功绩制”官员即职业官僚的范围上。1883年,文官制度建立之初,纳入“功绩制”管理系统的官员仅占联邦政府雇员比例的10%左右。但在老罗斯福的努力下,在他的任内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60%。[7](pp.202-203)与此同时,老罗斯福政府还积极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行政体制,目的是为了“寻求建立一个‘好政府’。”[8](p.19)在科学化管理的时代背景下,“好政府”就意味着“效率政府”。
塔夫脱政府的联邦政府行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扩大“功绩制”官员范围的努力。经过塔夫脱政府的行政改革,“功绩制”官员的比例又达到了占联邦政府雇员70%的程度;[9](p.193)与此同时,“对政府工作效率的要求”[3](p.90)也是塔夫脱政府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塔夫脱总统对行政效率的偏爱,实际上反映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和科学化管理的时代精神。
威尔逊总统“不仅是‘行政科学’的最早提出者,而且也是在实践中积极主张进行政府行政改革的倡导者。”[10](p.26)他在限制政治性官员职位的数量和对国会议员施压通过其行政改革方案等做法,其终极目标恰恰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因此,威尔逊政府时期,无论在扩大“功绩制”范围,还是在官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科学化管理。
20世纪初期的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在胡佛政府的进一步努力下达到了高潮。胡佛本人不仅是行政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也是后来的行政改革机构——“胡佛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到胡佛政府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无论在“功绩制”官员的范围上,还是在建立行政体制上,都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首先,职业官僚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功绩制”官员的比例几乎达到了占联邦政府雇员80%的程度。[7](pp.289-296)这一高比例数字,不仅是1883年文官制度建立以后第一次出现的,而且为实现行政的独立与有效的运行奠定了基础。其次,推动由政府行政机构特别是总统领导下的一个集中与协调的国家行政体制的建立与发展。1923年,美国联邦政府历史上第一个文官分类法律——《1923年职位分类法》获得了国会的通过。这一法律不仅确立了联邦政府文官统一的报酬制度,而且由于对职业文官的科学分类与管理,进一步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11](pp.50-51)更为重要的是,胡佛政府从根本上接受了“效率”作为以最低的投入并获得最高的产出——最大的社会效益——这一现代管理观念,从而基本上实现了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效率政府”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效率政府”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期美国联邦行政改革解决了政府存在的所有问题。从静态角度来说,政治与行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行政官员的“政治中立”问题,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关于文官“政治中立”问题的争论,可以看作是这一问题的继续。从动态角度来说,伴随政府的发展变化,不仅旧有的和已经解决的如“效率”问题重又出现,而且一些新的问题也开始困扰政府。
二
20世纪中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伴随着大战的结束和冷战时期的到来,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分歧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有效地保障官员忠于国家和政府,几乎是这个时期每届政府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因此,“忠诚政府”便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而追求目标从“效率政府”转向“忠诚政府”,又成为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初期的冷战,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职能和规模。从政府职能上来看,由于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联邦政府对外交、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干预不断加强。从政府规模上来看,由于战争对雇员的需求,从1941年到1942年,联邦政府职业官僚人数几乎扩大了两倍,即从140多万人发展到近270万人。[7](p.370)到了1945年,甚至达到380多万人。[3](p.113)因此,这一时期联邦政府除了要应对和解决以往存在的行政效率问题以外,还必须有效与科学地管理如此庞大的职业官僚队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和一些东方国家的发展壮大,使联邦政府对职业官僚在政治上的“忠诚”问题更是关注有加。
当然,强调政府官员忠于国家和政府,并不是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的首创。实际上,早在18世纪末合众国建立之初,政府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政府并没有法律性的规定。20世纪30年代,在国会众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众议员提出了联邦政府文官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的重要性以后,政府才真正开始重视职业官僚的“忠诚”问题。到40年代,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并进一步发现职业官僚中不忠于国家和泄露政府机密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是,政府对这一问题进一步引起重视。[12](p.20)到了50年代,由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麦卡锡在冷战背景下发表了“麦卡锡主义”的演讲以后,[13](preface)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因此,从小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这一时期的许多总统都把职业官僚的“忠诚”问题当作政府行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法律或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加以规定和确认。
与20世纪初期的老罗斯福、威尔逊和胡佛总统一样,小罗斯福也是一位对联邦政府行政改革贡献比较大的总统。但与前者的行政改革注重效率问题有所不同的是,小罗斯福政府的行政改革更多的是关注职业官僚对国家和政府的“忠诚”问题。1939年,在小罗斯福总统的催促下,国会通过了《哈奇法》(The Hatch Act of 1939)。这一法律规定:禁止联邦政府职业官僚成为任何政治党派的党员,或者禁止联邦职业官僚成为任何旨在威胁或推翻宪政形式政府的政治组织的成员。[14](pp.118-119)1943年,小罗斯福总统又签发了《第930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9300)。命令进一步要求政府控制联邦职业官僚任何颠覆政府的活动。[15]
杜鲁门不仅是小罗斯福总统职位的接任者,而且是其行政改革政策的承袭者。1947年,伴随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来临,杜鲁门总统签发了《第9835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9835)。命令决定建立政府职业官僚忠于国家项目计划。[16]此外,1950年,杜鲁门总统又督促国会通过《颠覆活动控制法》(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Act)。杜鲁门政府在官员政治忠诚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是把小罗斯福“忠诚政府”的目标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1953年,艾森豪威尔一进入白宫,就签发了《第1045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450)。这一行政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1947年杜鲁门总统签发的《第9835号行政命令》,使行政改革在追求“忠诚政府”方面的要求更具体和更详细。[17]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官员在政治忠诚方面的改革及其对改革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政策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对政府管理目标的要求。
此后,尽管上述有关职业官僚忠于国家与政府的法律和行政命令曾几经后来的国会法律和总统行政命令的补充与修正,但联邦政府对职业官僚在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方面的政策的控制却一直没有放松过。上述国会法律和总统行政命令所强调的“忠诚政府”,主要包括对职业官僚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两个方面的要求。
从理论上讲,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忠于国家是指政府官员对现存政府表示忠诚,而不能威胁国家的安全,更不能试图推翻现政府。通常说来,忠于国家的规定比较宽泛,而严守政府机密的规定相对具体。《第10450号行政命令》规定:如果出现联邦政府官员因为“强制、影响或压力等形式导致反政府叛乱,这位官员将立即被解职。”[17]一位有同性恋行为或者保持同性恋秘密的官员,也被认为是对政府有欺诈行为。经常酗酒和吸毒成瘾的官员,也被认为是可能泄露国家机密的一个途径。因此,《第10450号行政命令》和此后相关的法律都进一步强调:禁止任何政府官员犯罪、不光彩、不忠诚、不道德的和声名狼藉的行为,同时也禁止官员养成酗酒、吸毒和不正当的性行为的习惯。[17]此外,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在程序上也有所不同。忠于国家的要求是适用于所有的联邦政府职业官僚,而严守机密的要求只适用于那些工作在政府较为重要的或者敏感度比较高岗位上的官员。他们包括那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职位和那些处在决策层的高级文官。[18](p.416)忠于国家项目程序,通常要求政府官员在任职以前对国家口头宣誓,或者以文字形式签署忠于国家的誓言。但政府对于职业官僚忠于国家项目和官员本人背景的调查,通常是比较一般性的。例如,由联邦调查局例行调查后备案,并把一些调查表送到被调查官员以前的雇主手里,进而询问他们在对国家忠诚方面的表现和可信度。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被调查官员在这一方面有不良的表现,一般情况下调查书都能够获得通过。但与忠于国家项目不同,对政府官员严守政府机密项目方面的调查,不仅广泛而且深入。调查不仅包括与被调查官员本人的会面,而且还包括与他们以前的雇主、朋友、老师甚至是邻居的多层面会晤。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官员获得录用,那么政府不仅会定期对其进行个人性的面谈,而且官员每次被晋升或者被委派到新的岗位之前,政府都必须进行新的和全面的调查。[19](p.204)联邦政府文官管理机构(1978年文官制度改革前的文官委员会和1978年以后的联邦人事管理总署)为了对一位政府官员就严守国家机密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就要耗资675美元。[20](p.55)由此可见,政府对官员在政治上“忠诚”问题的重视程度。
尽管联邦政府对职业官僚在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方面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有些时候这两方面的要求又很难截然分开。例如,有些官员被撤职,通常不仅仅是由于上述一个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两个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其中包括:(1)他们对国家和政府不忠诚;(2)他们可能在一些方面有欺骗政府的行为。比较常见的例子有,官员没有能够及时通报他们在完成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后销毁一些保密材料,或者私自保留一些信息等。[19](p.204)特别是后一种行为往往被政府视为严重触犯了政府保密法。
从实践上看,联邦政府在官员忠于国家和严守政府机密这两方面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美国民主制的原则,侵犯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并对宪法提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挑战。因为要求职业官僚“忠于”国家和政府与“保障”他们的宪法权利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特别是伴随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对“忠诚政府”目标的追求,这一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由于政府工作的特殊性,“职业官僚实际上从接受政府任命的那一天,他们就不得不同意放弃宪法赋予他们的某些个人权利。”[21](pp.290-291)宪法赋予的个人权利的放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职业官僚开始在人格上出现了缺失。由于职业官僚在人格上的缺失,就会使其自觉不自觉地发展成为某些政客的附庸。因此,当他们不得不在“国家机密”与“腐败现象”等含糊概念面前谨慎区别什么是“证据确凿”,什么是“感情用事”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自身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实际上不仅意味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掩盖,而且意味着经常性的政治振荡。从这个意义来说,20世纪中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在解决政治忠诚问题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治腐败问题。因此,治理政府腐败,又成为下一阶段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主要任务。
三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的衰退与下降,特别是由于以“水门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丑闻的出现,使联邦政府陷入了全面危机。为了重振美国的国威与重建美国人的自信,特别是为了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如同19世纪末把治理政治腐败作为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样,这个时期联邦政府又突出强调官员的职业道德问题。因此,“道德政府”便成为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由于“政府官员每天的工作都代表国家及国家的形象”,[21](p.290)所以美国自建国之日起,无论是普通公众、政治家还是法官,都对政府官员在职业道德上寄予很高的希望。但是,1883年文官制度建立以前,联邦政府并没有建立一种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官员选任体制。无论是华盛顿总统所提出的政府官员应该是“有道德的和有能力”的治国理念,还是杰克逊总统所要求的官员对政党“忠诚”,都没有能够真正在道德上约束官员的行为。特别是在“政党分赃制”盛行的政治环境下,当政治家把官职作为“肥缺”分发给许多官员的时候,道德要求更显得苍白无力,政治腐败充斥政府。1883年文官制度的建立,政府腐败现象虽有所好转,但政府对官员在职业道德上的要求并没有提升到法律法规的层面。甚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政府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还仍然停留在理论说教和行政奖惩上,而缺乏系统的政策和法规。例如,当时政府只是比较宽泛地要求:政府官员不能利用公职以权谋私、不能接受个人或企业的馈赠和直接或者间接卷入股票投机行业等。[22](pp.339-34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水门事件”为代表的政府丑闻的不断发生,促使联邦政府把规范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考虑,并着手出台政府政策和法规。
1972年6月17日,尼克松总统竞选班子潜入华盛顿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进行偷拍文件与刺探民主党竞选情报等一系列特务活动的被抓获,在联邦政府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并进一步加剧了两党斗争。“水门事件”以及此后尼克松总统利用“行政特权”而隐瞒事实真相所进行的一系列阻碍司法调查的行为,最终葬送了尼克松总统的政治生涯。在尼克松辞职前数月,副总统阿格纽也因贪污渎职而离职。所以尼克松政府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缓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及为拯救美国日益衰落的大国地位所付出的努力,也随着“水门事件”的发生而逐渐被美国人民忘却了。相反,“水门丑闻”和尼克松总统“神秘人物”的特征,却深深地印在美国民众的记忆中。“水门事件”不仅仅牵连尼克松政府的政治官员,也有许多高级职业官僚也涉嫌涉这一政治事件。此外,在“水门事件”调查中,国会调查委员会又发现,尼克松竞选班子还曾经获得一大笔由利益集团非法捐赠的现金。[23](p.205)“水门事件”不仅暴露出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的腐败与黑暗,而且也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府的危机。因此,正像美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家弗莱德里克·毛舍所说的:“水门事件”使“美国公众又一次重新燃起关注联邦政府官员道德问题的火焰。”[24](p.105)
1977年,卡特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竞选总统和走进白宫的。卡特来到华盛顿时,恰好是“水门事件”后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达到最高点”、而对“总统的支持率下降到最低点”[3](p.149)的时期。卡特正是为了迎合当时美国民众的心理,并以自己“没有受过政治污染”[25](p.93)为资本,进而对华盛顿的“官僚迷宫”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从而拉开20世纪后期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大幕。因此,卡特是美国总统竞选史上第一位把改革政府官吏制度放在高层政治议事日程的总统。甚至直到卸任前,卡特总统还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绝对有必要控制官僚的迷宫,并彻底改进联邦政府的人事管理。”[26](pp.281-296)
卡特政府除了强调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和节约开支以外,还着重把官员的职业道德问题放在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特别是把此前政府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具体化。1958年,联邦政府曾出台了一个《政府雇员道德法规》(Code of Ethics of Government Services of 1958)。这一法规不仅重申了政府此前限制官员卷入的许多活动,而且进一步从法律上对这些限制性活动加以规定。[27](pp.659-666)例如,法规在第七条中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经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之相关的业务。[28]1958年《政府雇员道德法规》的通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对官员的道德监管由理论说教向法制化方向的转变,使政府在官员道德建设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正是以1958年《政府雇员道德法规》为基础,卡特政府进一步推进“道德政府”改革目标的实现。1978年,卡特总统督促国会通过了又一个道德法——《政府道德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27](pp.659-666)1978年《政府道德法》,除了要求政府官员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荣誉法典以外,为了防止官员贪污腐败或者涉嫌“政治丑闻”,首先特别规定官员必须向政府定期提供个人收入和财产说明。[21](p.290)实际上此前政府也要求官员向政府汇报个人收入情况,但由于没有从法律进行明确规定,致使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将他们的收入和财产情况及时或者如实地向政府申报。结果是,“联邦统计局所得到的关于政府官员财产申报情况,既不真实也不令人满意。”[29](p.8)有鉴于此,在1978年《政府道德法》中,政府特殊强调“财产情况申报适用于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主要部门所有的高级文官”。[19](p.189)与此同时,1978年《政府道德法》还对官员与企业的往来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由于政府的许多机构和部门都与企业存在一定的业务关系和往来,所以在交往过程中诱使政府官员离职到企业甚至贪污腐败的几率也比较高。在1978年《政府道德法》通过以前,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与企业的业务交往中所得到的好处远远高于其在政府供职的收入,于是一些官员便会离开政府到企业中去任职。而接下来这些人又会利用他们先前在政府的关系而作为企业的代理人与政府继续打交道。针对这种现象,1978年《政府道德法》又规定:政府官员离开政府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或者永远不得以企业代理人的身份与先前供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21](p.302)因此,要求官员定期向政府申报财产情况,非常有利于政府及时掌握官员的个人收入情况变化,以便防患其贪污腐败于未然。1978年《政府道德法》还规定:一旦官员退休或者离职,禁止其再对政府的决策施加任何影响。[21](p.302)此外,鉴于许多高级职业官僚参与“水门事件”,1978年《政府道德法》又进一步限制职业官僚过多涉足政治及政治活动。卡特政府改革以后,伴随“伊朗门事件”以及其他职业官僚滥用权力现象的不断出现,里根和老布什政府又通过发布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把“道德政府”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在里根政府强调“职业官僚必须清正廉洁和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法”[30]的基础上,老布什政府甚至还提出“对职业官僚的道德进行‘净化’工程”。[31](pp.1056-1057)
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在追求“道德政府”目标上的行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官僚主义的迷宫并恢复了政府的信誉。特别是1958年《政府雇员道德法规》和1978年《政府道德法》两个具有代表性法律法规的出台,使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被置于法律的限制之下,进一步抑制了政府的腐败和官员的堕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雇员职业的特殊性,对其道德行为在法律上进行强制,在实践中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从联邦政府和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上分析,实施职业道德法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其一,现代联邦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与政府功能的日益复杂,为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带来了许多的不便。例如,现在政府任何一项工程都耗资上百万和上亿美金,并涉及许许多多的大企业和大公司,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学者保罗·艾坡伯所提出的:“控制300多万政府官员每天的道德行为简直是不可能的,甚至即使是小规模的文官队伍,也很难保证他们在道德上的纯洁性”[32](pp.58-59)的论断,也不无道理。其二,随着政府职能的增大,职业官僚参与政治和政治决策,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难以控制的。只要官僚卷入政治,就很难保证他们在道德上的纯净。
其次,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上分析,实施职业道德法也有一定的困难。美国不仅是多元文化和多元利益的社会,而且也是价值观念变化比较快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如何保证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准则与社会观念相适应并为社会价值观念所接受,恐怕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李所说的:“今天被接受的准则,明天可能就被拒绝了,或者相反。”[19](p.194)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和其他腐败案接连发生以后,美国公众较之以前更关注政府官员防止“政治腐败”方面的道德修养和对职业道德法的遵守。而80-90年代以后,特别是克林顿总统“白宫实习生丑闻”的出现,公众又把关注焦点转移到政府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上。
再次,从职业道德法本身的特点来分析,真正实施这种法律也不是很容易的。与官员职业特殊性一样,职业道德法本身具有与其他法律不同的特点。从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上说,道德法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象征性”和“政治性”。也就是说,“通过道德法告诉公众,政府是重视和关注官员的职业道德的。”[21](p.303)此外,由于政府机构和部门如此之多,许多政府决策往往是在不同的环境下做出的,因此,“单一的和带有一般性的职业道德法可能很难在政府所有的机构和部门中得到认真执行”[33](pp.59-66)。
最后,从心理学和行政管理学的角度上分析,过分在法律上强制政府官员的道德行为,也未必很有效。因此,美国学者佩里·穆尔所阐述的:“美国联邦政府职业道德法,过分强调消极的因素,例如,规定官员不应该做什么,相反,应该从积极的因素方面引导他们应该做什么。如果这样,也许更能够唤醒和刺激人性中‘善良’的一面”[21](p.303)的理论,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
四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首先,经过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洗礼,到90年代,科技发展正进入一个饱和点。伴随科技发展高峰的过去,科技能否突破它在进一步发展中所遇到的障碍并再创辉煌,是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其次,经过战后经济的空前繁荣,到90年代,经济发展正进入一个低迷时期。伴随世纪末的来临,特别是伴随科技高峰的突破,如何摆脱经济滞胀和使经济重获繁荣,也是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应对的重要问题。最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伴随以官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为特征的官僚政治的产生和官僚主义的泛滥,到90年代,美国政府管理又开始进入一个全面调整时期。因此,“重塑政府”便成为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
在199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克林顿击败了在当时威信并不十分低下的时任总统布什。其原因不在于布什对美国经济的衰退表现出束手无策,而在于克林顿抛出了能够广泛吸引公众注意力的竞选纲领。与传统北部民主党人所追求的“自由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是,作为南部民主党人的代表,克林顿的思想中渗透着“商业主义”和“贸易主义”的思想意识。他在竞选中所提出的“自由贸易、重塑政府、缩减10万个联邦文官的职位、为中产阶级减税和支持死刑判决”[3](pp.198-199)等一系列竞选纲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克林顿新思想和新观念的集中体现,是其从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世纪末的“重塑政府”改革。
首先,“重塑政府”改革,在理论上承袭了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改革思想,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政府管理意识的新理念。
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伟大的社会”所带来的庞大财政开支,一些保守派和“新自由派”都开始批评官僚政治和政府腐败现象。他们批评政府低效率、文牍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但与保守派试图用取消联邦政府的许多计划和方案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不同的是,“新自由派”却是“用改革政府的办法来使职业官僚在国内生活中重新发挥它的积极和有效的作用。”[34](p.72)由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和“水门事件”的发生,使这些改革思想曾一度沉寂下去。而到了20世纪末期,伴随克林顿总统入主白宫和“重塑政府”改革帷幕的拉开,“新自由派”的改革思想又得以重新抬头。所以在克林顿—戈尔竞选纲领——《把人民放在首位》(Put People First)[3](p.205)中,人们很容易发现“新自由派”改革思想的痕迹。
如同20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科学化管理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泰勒主义”的启示一样,这个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重塑政府”改革,也是受私人企业的“再铸企业”运动的影响。199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有关企业管理的书籍——《再铸企业》(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提出了“减少公司的官僚等级管理而增加民主管理”[3](p.206)的观点,而且预见许多公司将在“再铸企业”的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从管理学角度来说,“再铸”就意味着通过对雇员进行培训,使其可以适应各种各样的工作任务。通过这种新方法,一方面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浪费,进而鼓励技术革新和节省企业在生产过程转变中的开支”;另一方面还可以“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并使一个雇员能够同时完成许多复杂的工作任务”[3](p.206)。正像美国学者戴维·舒尔茨等人所评价的那样:“‘再铸’实际上是‘现代’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理念,因此,与泰勒主义一样,‘再铸’从根本上说是20世纪末期美国企业自上而下的一次变革。”[3](pp.206-207)
1992年美国新闻工作者戴维·奥斯本和前城市经理与顾问泰得·盖博勒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政府管理的书籍——《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在这本书中,作者鉴于“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由‘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具有等级特点的文官制度和官僚结构,已经不仅不适应现代的美国政府管理,而且也不具有合理性”[35](p.332)的新的时代背景下,而提出了“重塑政府”的管理新理论。这一新理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为了应对来自新世纪的挑战,政府管理应该应用市场管理和组织机制。作者提出,“目前,竞争和自由市场,不仅给世界带来了迅速的变革,而且也给管理提供了高效率。然而,传统的政府管理还仍然停留在解决许多共性的问题和保证社会的正义和公平等问题上,因此,为了适应未来世纪的需要和使政府的管理更有效率,必须引进市场竞争机制。”[35](pp.333-334)第二,为了扭转官僚独霸政府的局面,政府管理必须改变传统的组织形式。作者指出,“政府不必要总是由政府官僚机构提供服务,相反,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替代的形式以满足各种管理的需要。例如,可以采取订立合同承包政府机构的形式、或者授权担保人管理政府,进而保证公民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服务机构的形式、或者通过奖励特许形式把政府机构让渡或出售给某些个人、或者通过鼓励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竞争的形式、或者鼓励政府机构和部门之间竞争的形式等。上述这些形式的合理与有效之处,就如同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竞争学生一样。”[35](p.332)第三,为了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管理必须改变政府的文化和组织结构。作者进一步提出,“如果政府能够不仅采取上述引进市场机制和改变政府组织形式的做法,而且能够改变它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我们将会看到政府效率的新形式的出现。这些需要改变的政府文化和组织结构包括:通过取消许多法规或者通过简化和取消大量的日常文书的办法来减少‘文牍主义’。特别是通过改革人事体制和职业文官制度,防止官僚主义泛滥和官僚阻挠政府革新。上述官僚政治和文官人事制度,不仅使政府解雇官员非常困难,而且妨碍了政府及时‘购置’雇员和‘购置’它所需要的雇员。”[35](p.333)第四,为了整顿官僚主义作风,“重塑政府”理论又提出了诸如削减中级管理机构和总部、改变组织结构——减少管理中的等级关系,而增加不同专业团队的结合形式,增加宏观财政预算,而减少微观财政预算和减少官僚对预算的支配权,使用信息技术测试雇员的工作业绩,使用物质手段奖励和惩罚雇员,改变组织文化,从而增强革新意识和反对墨守成规等。[35](p.334)
在上述改革思想的影响和启迪下,克林顿通过“重塑政府”的改革形式,在美国政府管理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管理文化观念。这种新的文化观念,一方面强调管理权力的分散,减少联邦人事管理总署对政府各部门人事管理的干预程度;另一方面强调政府预算多元化管理。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企业的管理方法,使政府管理既节省开支又更具效率。
其次,“重塑政府”改革,在实践上把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推向了高峰。
1993年,克林顿总统一走马上任,便通过其副总统戈尔所领导的“国家绩效评估”(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s)计划和“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改革的形式,在联邦政府层面掀起了一场全面行政改革的实践。1993年,戈尔副总统在白宫的玫瑰花园向克林顿总统提交“国家绩效评估”计划,拉开了克林顿政府行政改革的序幕。在改革计划中,戈尔提出了四百多个与“重塑政府”理论平行的改革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改变联邦政府管理中的个人和组织形式、改变预算和技术的应用;增加订立合同承包政府形式的使用、采用商业的客户服务标准等。[3](p.209)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同年,国会又通过了《政府工作业绩及效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根据这一新法律,政府要求各机构和部门重新制订工作计划和雇员业绩测试标准。新法律特别突出强调工作计划的战略性和测试标准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由于“重塑政府”改革是对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一个全面调整,所以,改革能否最终顺利完成,不仅有赖于新的管理法律与法规的及时出台,而且有赖于管理文化观念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戈尔副总统走访了驻扎在全国各地的许多联邦工作基地,进一步提高联邦雇员对“国家绩效评估”和“重塑政府”改革的认识。戈尔甚至“使用起重车倾倒上百万和上千万磅由联邦人事管理总署所颁发的脱离实际的管理法律与法规,使联邦人事管理总署无权再强迫政府各个部门遵守它所制订的政策与法规”[36]。正是由于克林顿“重塑政府”改革计划周密,宣传到位,从而得到了许多政府部门的支持。1994年,根据联邦政府调查显示,多数在华盛顿供职的联邦政府高级政治官员和职业官僚都一致认为:“‘国家绩效评估’和‘重塑政府’改革无疑将会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3](p.209)1995年以后,即使在克林顿政府面对众多不利因素的条件下,“重塑政府”改革仍在进行中。根据1996年国家绩效评估报告显示,43%的国家绩效评估计划已经完成,42%正在进行当中。[37]在克林顿第二届政府中后期,“重塑政府”改革又开始向社会层面推进,力图改进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特别注重改进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从而真正实现“重塑”政府形象的目标。
1993年至2000年的“重塑政府”改革,既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是取得成绩比较显著的联邦政府行政改革。这次改革在缩减政府规模、改变政府管理方式、引进企业管理方法和市场竞争机制、协调与州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改进联邦政府与社区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改善政府办公环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政府管理文化观念的转变,而且也恢复了政府的信誉。经过“重塑政府”改革,美国公众对于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在经过了30年的下降以后,又有回升的趋势。根据1998年密歇根大学一次民意调查表明,与“水门事件”前后比较,这一时期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上升了近2倍,达到40%。[38]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我们仔细审视克林顿“重塑政府”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时候,仍能发现一些问题。首先,从量化的成果上来看,克林顿政府改革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根据戈尔1993年和1994年的“国家绩效评估”计划,联邦政府预计在五年之内削减超过25万名文职雇员,节省财政开支100多亿美元。[3](p.211)但到1996年克林顿第一届政府结束的时候,甚至到克林顿2000年末卸任的时候,这个改革目标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相反,在克林顿总统任内,不仅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仍然保持近200万左右的庞大的文官队伍,而且还有大约1200多万相当于全日制工作的雇员、通过联邦政府承包合同和项目工作的雇员以及在一些法令下在州和地方政府雇用的联邦雇员,即所谓的“政府影子”。[39](p.1)其次,从改变政府管理文化观念上来看,克林顿政府改革的目标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联邦政府传统的管理文化观念,是在一个多世纪美国官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因为“这种文化观念的改变,就意味着官僚失去他们的传统地位和权力”,[40]所以官僚对改革的抵制也就不足为怪了。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治体制“分权与制衡”的特点,也决定了国会对变革政府管理文化观念的不合作态度。更进一步说,国会之所以反对这种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克林顿“重塑政府”改革是在不断削弱国会对官僚的控制权,换言之,“改革是在扩大总统对官僚的控制权力的过程中进行的,是以牺牲国会对官僚的控制权力为代价的”[3](p.212)。
收稿日期:2008-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