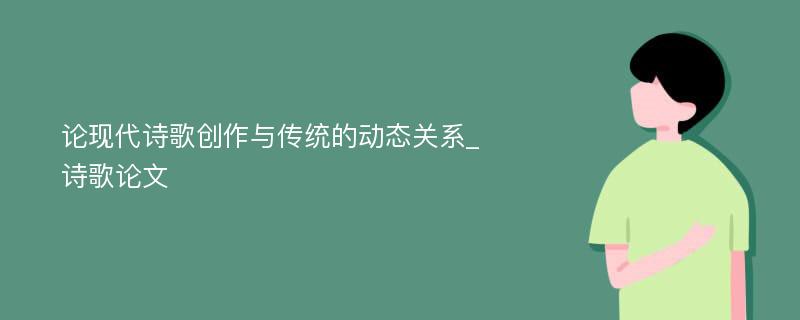
论现代诗写作与传统的能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现代诗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们明显看到诗歌批评界许多人对中国现代诗的存在的“合法性”,又掀起了新一轮的质疑。如果说此前的质疑只认为它“背离了传统诗质,因而没有根”尚显得简单化的话;那么近来同样的“无根化”指责,由于加入了新世纪“全球化”中外文化碰撞和差异性对话的语境,则似乎具有不容分说的正确性。我感到诗歌的“民族性”问题,从理念上认识较为容易,但实际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对文学的民族气质、民族风格的深入挖掘和辨认,说到底还是个写作实践问题。因此,我想从一个诗人具体的写作状态上,来谈谈在新的写作语境下,现代诗人与传统的能动关系,也就是怎样理解诗人写作中的“继承传统与创新”问题。
1
现代诗的“继承与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严肃的诗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认识。“继承”,作为一个理论语汇,除了“文艺政策”意义上的引导外,对具体的诗歌写作而言,其语义是含混的、可选择的。在这里,我首先想指出,流行于世面上的对“继承”的理解,是得到了主流意识、轴心文化圈的支持的。它是指对中国古老诗歌传统的回归和摹仿。这种惟民族主义的“继承观”,含有相当成分的不容分说因素。因此,它的地位总是被认为优于及先于创新,它仿佛总是首位的、本质的、正面和核心的。如果一个诗人从表面的语言效果或诗歌体式上表现了向传统的摹拟,那么,他的诗就被先在地给了意义。他的平庸和懒怠,他的守旧和迟钝,也仿佛可以得到这种先在给定的包庇。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因此,要想匡正这种肤浅的“继承观”(如果它的确称得上是一“观”的话),的确是非常麻烦的事。因为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基础上的理论背景和创作模式,已使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轨程。你要站出来反诘这种诗,立刻就被置于“反传统,反继承”一边。这种得到正统文化强权支持的势力,可以超出文学讨论之外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居“高”临下地结束这种讨论的平等性质。由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诗歌理论界仿佛真的营垒分明,空手入白刃,一方是“遗产派”,另一方是“西崽”。双方都由捍卫自己的观点,发展到赌气,围攻。这种由显示、演示发展到“指示”的“论争”,扩大了人们的盲目,遮蔽了问题的本源。因此,它给了我们热闹,但没有多少启发。
当我们排除了对“继承”这一问题的表面理解后,我们才能真正触及它的内质。广义的传统,并不仅仅是我们见到的文化“遗产”,具体到文学来说就不仅仅是可见的文本。传统既是实体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功能。因此,在我们置身其中的今天的生活中,最寻常、最微小的东西,都含有一定意义上的传统因素。大到人文地理,国家民族,母语渊源,精神文化,人的生存,历史事件,民风民俗等;小到一个词素,一句话,一种表情,一个姿势语或一组动作如此等等。而在现代诗人的写作中,传统体现为诗人与民族气质、与文化、与语言、与族群的能动关系。没有传统气脉的诗将无法在民族中真正存活,所以,我不认为只背弃了古典诗歌艺术形式和审美素材,而得到今天广大读者认同或热爱的现代诗,就真的完全背弃了什么“传统”。传统作为一个无限扩大的“文本”,它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离开我们。有的只是那种不愿正视和承认传统无所不在的幼稚的理论态度。
但是,问题的症结或许不在这里。在一个优秀诗人的写作中,“继承”传统首先是指非常复杂化的、自觉化的对母语及民族气质更深度的理解和发现。因此,我们不可能置身传统之外是一回事,而对它的深入理解、自觉创造,及重新生成的“视界融合”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我可以说,从理论上完全否弃传统的人,和那些皮相地摹拟传统格式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发生内讧的战友。他们从客观上达成合谋:拒绝深入理解“传统”。
2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的诗歌传统是什么呢?在讨论中,任何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核心,正是这个核心,防止着讨论的自由游离。树立并加深这个核心,不但是一个理论家必备的素质,更是他的天职。既然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深入传统(而不是谁在传统之“外”),我们就必须涉及到诗歌传统较为明确的细节含义,特别是过去诗歌模式所遗留下来的价值、原则、规范、经验和知识的总和。于是,我看到了对传统特质的众说纷纭的理解:
▲质实入世
人民性
忧患意识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言志咏怀
缘情说
以史为咏
……
▲冲和淡远
天人合一
言无言
自然泛我化
赋比兴
游仙精神
空灵
乐感
佯狂
意境说
……
前八项其实也可以说是任何民族的诗歌,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共性特征,后十项则基本显示了传统诗歌(又岂只是诗歌)的个性特征。即使如此,我仍然看出了后十项与前八项内部诸多因素彼此的纠葛、互否、运动和更新。钱钟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谈及了在不同的读者眼中,中国诗的正宗分别是王维式的“神韵”系谱,和杜甫式的“现实”系谱。——面对这种复杂微妙的情势,我们如何确立自己艺术创作的,而不仅是发表“宣言”的立脚点呢?如何在这种种的相对性、复杂性面前得到一种自明意识的支持呢?或者,我们深入传统仅仅是为了重温旧梦吗?如果不是,我们又怎样区分什么是创作而什么是描红呢?迷信和教条难道就是那么容易从我们的意识深处排除吗?因此,当我们声称要回归或是“继承”传统时,传统首先站出来说:——“我的特质在哪儿?请先指明”。
我认为,这种其实无法有公认权威的“茫然局面”,只能由真正严肃而优秀的诗人个人出来主持。在诗歌艺术创造中,他们与传统的能动关系,就成为“正典”与创造性生成的“理解”的关系——优秀的诗人应有能力找到通向传统的个人“暗道”。
3
所以,我坚持我一贯的立场,即:对诗人个人的写作而言,“继承”传统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被动的行为。这里,永远包含着对其积极能动的选择、变构、剥离和重新“发现”。传统与现代,是互相打开的。因而,传统只能是“当代”重新理解中的传统,它首要的因素不是自在的、固定不变的,它永远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在内。对传统的“继承”,从最高价值上说,只能是传统意义的重新“生成”过程。传统对我们现代诗人来说,它既不会是可以包打天下的利器,也不只是需要加以克服的消极滞塞因素。它仅是一种无限广大的可能,真正的价值只能相对于我们的智力深度及语言能力的实践而确定。
传统是需要也只能由无数个“当代”反复发现和给定;诗人对传统的意义,是他的写作实践及实绩所赋予的。“继承”活动在本质属性上是与“创造性理解”同时到来的。正由于我们带着某些异质的冲动加入了传统,传统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所谓“继承”传统,实际上当然就首先包括了发展、楔入新的因素,使旧有的传统格局发生变动,包括改变秩序和重新“陌生”化等运动在内。
理论家要做的一种工作也许是“整理传统”,使之类型化、标准化、整体化和稳定化;而诗人,则永远带着合理的主观性、相对性、创化自豪感,去重新加入、解析、生成“传统”中的某一种或几种可能性因素。在后者这里, “继承”永远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不是去“媚”文化意义上的“俗”。在民族杰出诗歌的伟大共时体中,由于其自身内部的复杂性,呈现在诗人面前的传统,无所谓什么本来面目。不是理论宣言或低能的诗评家自以为是的“全面判断”,而是诗人的天才、创造活力和成见构成了他与传统那种能动的关系。他使传统中某一局部因素的价值隆起,而舍弃了另一些,甚至是更极端地排除了它们。这难道真的是反传统吗?如果硬要说,我愿意说这些诗人是在“返”传统,返回他心目中传统最优秀的根子之一。
让我们看看上面我列出的十八项传统概念,我们会得出一个认识:变革,建设,改造,发现,是每代自觉的诗人对传统的基本态度,同时也是传统本身题中的要义。因此,只强调被动摹仿,只寄生于僵化的对传统的认识的人,他们恰恰是“继承”到了反继承的程度。这难道不正是一种盲目守旧(他们却说真正的诗人在“盲目创新”)的态度吗?守旧而盲目,还不如自觉的守旧。我们树立了对传统中诸多因素的取舍、改造和发现这样的能动立场,就决定了传统(至少对我们这种立场的现代诗人而言)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前在的、僵固的东西,而始终是可供选择的、偏离的、流变的双向过程或多向过程。
4
在本文的开头,我强调了我的立场的基点是一个诗人“具体的写作”。现在,我可以进一步说:继承与创新,在这个特定的基点上,不再是两个词,而是二者构成的一个“新词”。由此衍生出的另一个极而言之的说法是,不只是传统决定或造就了杰出的诗人,有时几乎相反,是杰出的诗人“生下”了传统。作为杰出的诗人,他的某部分意识背景和隐语世界必须是独一无二的。它(诗人或诗歌文本)存在于传统之内,同时又制约和改造了传统;它(诗人或诗歌文本)逃避了传统的控制,反而从更高的层次加入并丰富了传统。这里不存在拟古不拟古的问题,只存在通过词语建立另一个生存—文化—个体生命话语世界的问题;不存在是否符合某一类老式读者阅读类型的问题,只存在通过新的创造去同时创造出新的读者的问题;不存在我们能否让“遗产”不朽的问题,只存在传统是否能使今天之诗秘响旁通、内力远出的问题——我们是为揭示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存/生命而写作的,我们又不是鹦鹉。因此,真正杰出的诗歌(诗人),它同传统的关系,就一定是一种奇妙而模糊不清的,张力极大的,可变的和间接的功能场;这种既增补又超越,既深入又剥离,既是共时体的一部分又是隆起的个别性价值……的能动关系,我们在历代诗歌大师身上不是一再地看到吗?文学史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已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可能范围。难道我们还用得着调动更复杂的个人的智力因素吗?
但是,我这里也许不用谈什么大师。就谈谈我们,这些普通的正在写作的诗人。既然对传统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惟一全面的理解,那么,你依据什么说“我继承了传统”?即使如此,又如何肯定你的“继承”是合理的、正极的,而不是负面的、甚至伪装的呢?如果传统中那些已被它自身的运动淘汰了的劣质因素,以及那些阻碍历史进程、沉迷小农经济、甚至对现代人的生存状况起恶化作用的因素,也被你和对诗歌审美性格的沿袭一道“继承”下来呢?因此,对那种只提“继承”,而不能进一步阐明或是有意的缩小、减少、低估传统中矛盾性和劣根性的诗人及理论家,我们在今天尤其应当进行必须的鉴别、评断和驳斥。传统的力量在现代的体现结果是,一部分传统在我们的母语、灵魂和情感经验的内核中,成为血素而不是假发或真发的“辫子军”。另一部分传统“正典”用文本固定下来,成为随时可能被各种“当代”向度打开光芒的,绝对“共时性”中创造和激发的,自由阐释的多元性存在。而具体到一个诗人的写作,最终可靠的东西,就一定主要不是什么理念上是否要“继承”传统的形模,而主要是你以什么方式,什么高度,什么天赋去重新对待和阐释、激活传统的。因此,你的话语能力,自觉程度,理性,意志,天赋,直觉,情感表现力等,并不能先在和天然地得到拟古性“继承”这一立足点的保证。只有被当代“成见”所理解的文学史,才是有价值的有作用的文学史,否则,一切创造都谈不上。
文化艺术的价值从来都是寓于不断的评价或解析之中的,而且只能在无数个“今天”的评价和解析中得到体现。所谓“解释学的循环”理沦,给我们以重要启示。面对传统的价值的理解方式尤其如此。这种创造性的整理、加工和重新变构能力,我们可以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对古希腊、罗马艺术的重新发现、洞开和“生还”中见到。近的说,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叶芝、埃利蒂斯、帕斯、布罗茨基等人的写作中见出。在新时期中国大陆的诗坛上,我们更直接地从杨炼,江河,海子,骆一禾,张枣,柏桦,于坚,吕德安,以及《现代汉诗》某些诗人的创作中,见到了这种能动而深刻的对传统新的认识观。恰恰是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整天高喊“继承”的拟古主义者身上),我感到了东方的博大和幽深,平静与流连光景,语言的疼痛和火光。所谓传统的真实和活力,离开今天的诗人充满个性色彩的巨大变构能力和纵深加入能力,我们能从哪里找到呢?
传统与现代的双向互动关系,就这样活在自觉的诗人精神历史的深处,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启示和气脉、文脉及血脉。用自己原创性的话语的血液,去粘和几个世纪的椎骨,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带着天才而勤谨的能动精神,扩展并加深了传统的语境,找到了通向传统的个人“暗道”,强化了它被诗人意识到的某些本质因素,并最终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今天的一部分。所谓民族特色,所谓东方感的现代诗歌,只有在这种自觉的创造慧识高度下,才具有真实、结实、落实的广阔可能。
最后,让我用克尔凯郭尔的话结束此文。这位哲人是这样说的——
不愿劳动者不得食,只能受到欺哄。而愿意工作的人却能生出他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