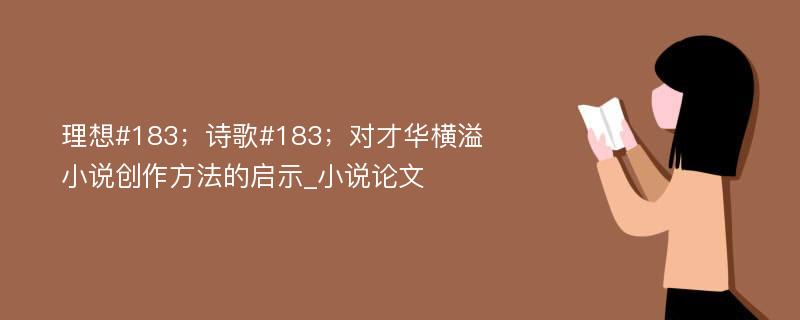
理想#183;诗笔#183;启示 论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才子佳人论文,启示论文,理想论文,方法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当人们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解释时,总以为缺乏写实精神;而当人们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去解释时,又觉得虽然浪漫却够不上“主义”。于是,往往就用“两结合”一言以蔽之。殊不知,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用的是传奇的创作方法[①a],它具有唐人传奇小说的某些特征,但它更接近于明清传奇戏曲与西方传奇的艺术精神。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才子佳人小说作了这样的评说:
《金瓶梅》、《玉娇梨》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状事皆不同,唯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旨意,每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所述人物,多为人才,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
这里,鲁迅先生着重指出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与唐人传奇的“近似”、“非必出于仿效”。但实际上向唐人学习,是明末清初小说的一种创作倾向,所以鲁迅先生在同书的另一处又说:“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根据鲁迅先生的论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明清才子佳人小说虽然“非必出于仿效”唐人传奇,但它实际上却具有一种传奇风韵,即一种受唐人传奇影响又不同于唐人传奇的艺术精神。其“近似者”,一指才子佳人之事,一指文雅风流之笔,即移植唐传奇的题材,仿效唐传奇的笔法,搬用唐传奇的人物;其“不相关”者,一指唐人传奇往往以悲剧的结局而令人扼腕,而才子佳人小说则“终多如意”,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精神;一指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由唐人传奇追求内容的离奇转向了强调表现手法的曲折多变,艺术构思的虚构想象。总其“近似者”与“不相关”者,传奇便成为一种美质,一种内在于“真实世界”的想象力量,一种既不同于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一
传奇表现的是想象和愿望的理想世界。
写实更多关注于对一个熟知世界的再现和解释,写实取材于日常生活,注重实际的可能性;传奇则使那个世界中隐藏的梦幻得以实现,传奇不完全脱离实际生活,但与实际生活有一定距离,它注重理想的可能性,尤其是爱情传奇。因为现实中的爱情是最经受不住摧残的,所以《金蔷薇·夜行驿车》中的安徒生才为了想象中的理想的爱而失落了现实中爱的可能。他说:“只有在想象中爱情才能天长地久,才能永远围有一圈闪闪发亮的诗的光轮。看来,我虚构爱情的本领要比现实中经受爱情的本领大得多。”[①b]善于营筑精神世界的人类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人们熟知的故事,营筑了一个在人们心里持久地存在的世界:一个想象和愿望中的情爱世界。
首先,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一见钟情或“众里寻他千百度”或“之死靡它”,表现的是爱情的至上性,自由性,神圣性,是人类所希望、所追求的一种爱情理想。
素政堂主人题于《定情人》的序中言:
试思情之为情,虽非心而仿佛似心,近乎性而又流动非性。触物而起,一往情深,系之不住,推之不移,柔如水,痴如蝇,热如火,冷如冰。当其有,不知何生;及其无,又不知何灭,夫岂易定者耶?……情有所驰者,情有所慕也。使其人之色香秀美,饱满其所慕,魇饫其所贪,则又何移?不移不驰,则情在一人,而死生无二定也。情定则如磁之吸铁,拆之不开;情定则如水之走下,阻之不隔。再欲其别生一念,另系一思,何可得也!……固知情不难于定,而难以得定情之人耳。此双星、江蕊珠所以称奇足贵也。
这里,素政堂主人先向我们揭示的是爱情生活中的神秘体验——一见钟情。也许在你的幻觉中早已有了他或她了,然而你在现实生活中却不知道他或她在何方,于是你去寻找,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仿佛完全在无意之中,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触物而起,一往情深”而“不知何生”。当《定情人》中的双星带着寻找理想爱情的愿望,“由广及闽,走了一二千里的道路,并不遇一眉一目”“堪作闺中之乐”时,无意遇到了江蕊珠,竟“惊得神魂酥荡,魄走心驰”,“虽在昏聩朦胧之际,却一心只系念在蕊珠小姐身边”,“耳朵中忽微微听见‘蕊珠小姐’四个字,又听见‘彩云在此’四个字,不觉四肢百骸飞越在外的真精神,一霎时俱聚到心窝。忙回过身来,睁眼一看,看见彩云果然坐在面前,不胜之喜。因问道‘不是梦么’?彩云忽看见双公子开口说话,也不胜之喜,忙答应道‘大相公快苏醒,是真,不是梦’”。在《玉娇梨》中,当孑然一身的苏友白忽遇才美双并的淑女愿以终身相许时,他谔然惊喜道:“莫非梦耶?”象这种如梦如幻的爱情体验,决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所能感受到的。
然而,理想的爱情并不仅仅是那种如闪电撞击心灵般的“一见钟情”,还有它的至上性,神圣性和永久性,一旦“情在一人”,则“死生无二”。才子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了寻求、为了忠于自己理想的美好的爱情,可以抛掉世俗的一切,包括被封建知识分子视为贵如生命、终身梦寐以求的功名富贵。《定情人》中的双星为了寻找定情人,放弃科举奔走四方,及至找到江蕊珠之后才回乡应试。中状元之后,宁可舍着性命,远赴海外,拒绝了当朝驸马的为女求婚,信守盟约不为所动。《平山冷燕》中的平如衡自从在旅途中偶遇冷绛雪之后,即放弃功名四处奔走,寻找意中人冷绛雪;燕白颔为了忠于所追求的理想爱情和平如衡远奔京城。还有《玉娇梨》中的苏友白,宁可被革掉案首也不迁就吴翰林的招婿,宁可扔掉新任的推官也要游荡江湖寻找可心的理想的爱人。就象西方中世纪骑士传奇《坎特伯雷故事》中的托马斯先生,他“听了画眉的歌,说不出的相思情怀,他踢起马刺,狂奔起来,‘……世上没有一个值得我爱的女子,我将爱一个仙后;我拒绝所有的凡女,我愿奔过山岭低谷去找仙后’”[①c]。可见,中外爱情传奇的主人公是“同病相怜”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理想爱情放在一切现实利益、乃至生命之上,把自己完全地融进理想的爱情中,而这种融汇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自由的丧失,而是获得最大的自由;也不是自我的丧失,而是获得最真的自我,即生命的自由与爱情的幸福。虽然它凭借了基本的人性冲动,但它也常常以不寻常的笔调记录了一个时期乃至整个人类的某种理想形式。
其次,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的模式表现的也只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性。“才子”,意味着人能够靠天资、智慧、发奋努力和与之俱来的才学,去获取现实人生利益,包括仕途成功和幸福性爱。将至高的社会理想与完美的人生追求溶为一体,这无疑是一种最具理想、最有光彩的人生。然而,现实的无情常使他们空怀一腔壮志、满腹经纶却找不到施展才华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科举情况,看看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的模式同样也是一种理想的表现。
科举到明清大盛,殿试三年一试,一甲三名,第一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以清朝为例,清统治计267年,共举行112科,因顺治壬辰(1652年),乙未(1655年)两科满汉分榜,有清一代状元计114人。江苏状元最多,49名,浙江次之,20名,安徽第三,9名,其它各省或一两名,或连榜眼、探花都没有,难道说这些省的青年男女在近三百年中都不谈恋爱了么?若谈恋爱,未中状元,怎么奉旨成婚呢?看来,仅靠状元高中来奉旨成婚,其希望是多么的渺茫。如果再考虑状元的年龄与婚姻状况诸因素,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才子佳人仅靠中状元后“奉旨成婚”的大帽子来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婚姻模式,无异于寻道于盲。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美梦。可以说,一见钟情,奉旨成婚的婚恋模式不仅仅是被爱火燃烧着的男女们的梦幻,而且也表现了作家的“白日梦”。
当然,这并不是简单重复弗洛伊德的理论:“一篇作品就象一场白日梦一样,是受到抑制的愿望在无意识中得到的实现,因此,每次的白日梦便是一次愿望的满足”。[①d]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实有一个传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古代作家不管是政治上、事业上、婚姻上受到挫折和压抑,都常常借爱情来表现理想和抱负。同样,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作者也是感觉到了现实的缺陷而有意为之。《平山冷燕》序就集中写了怀才不遇的失意作家借写小说来表现自己的才能、自己的理想的创作心态:
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计无所之,不得已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梁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斗牛而天马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
还有干脆就说白:“从来传奇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②d]时命不伦,怀才不遇,不得已只能将“胸中之欲歌欲哭”,借人生幻境之离合悲欢发泄于小说之中,使自己“落笔时惊风雨,开口秀夺山川”的才情得以留名后世。也许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都是作者未曾经历过的,甚至也未曾见过,但却是他们曾经向往的,在作品中描绘出来,从而使自己的生活理想通过传奇的形式在理想的世界中得到实现和满足。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往往强化和夸张了人类行为中的某些特征,正如詹姆斯·福代斯在《对年轻妇女的布道集》中所说的:“在古老的传奇中,激情和它所有的热情一起出现。但在另一面,它是荣誉的热情;因为爱情和荣誉在这里是同样的。男人们都是真诚、宽宏大量和高贵的;女人们都是忠贞、端庄、钟情的模范……他们描绘的人物,无疑,常常都被拔高得超于自然;他们叙述的事件无疑通常也都是以荒谬夸张的手法混合在一起”。[①e]
尽管这样,尽管这想象中的理想的东西看上去不具有任何强力,但却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支柱。人们或在想象中苦恋、单思某一特定实在的理想对象;或在想象中再创造了人类的形象。也许只有这种形而上的慰籍,人们才会得到那种从现实忧伤中滋生出来的欢快。正如安徒生临终时对朋友说:“我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②e]
传奇就是这样,它全神贯注于理想,它预视人类的幸福,它在愿望的想象中重新创造了世界。
二
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传奇是诗的或叙事诗的”。我想,我们对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从传奇的内在精神看,由于传奇作者大多从理想生活中看取人生、看取世界,因此,他们着力刻划的必然是人性中单纯美好的一面,他们笔下摄取的必然是世界中诗情画意的一面;另一方面,从传奇的体裁来源看,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传奇源于史诗,传奇必然有“史”和“诗”的基因,在中国。唐人传奇主要源于历史传记小说[①f],但由于诗的意识的渗透,传奇也必然成为“史”和“诗”融合的产物。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论《幽怪录》《传奇》时云:“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②f]“史才”和“诗笔”相提并论;宋洪迈《容斋随笔》云:“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③f]小说有诗之“宛转”“思致”;还有洪迈在《唐人说荟》凡例中论唐人小说:“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④f]小说与诗律同称“一代之奇”。因此,当我们看到西方传奇、唐人传奇及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诗笔的运用和诗意化的创造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勒内·韦勒克的论断是有根据的。
在源于史诗的西方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韵文写的传奇作品,如早期的宫廷传奇;也可以看到用富有诗意的散文写的传奇,如《克里赛》接近结尾时:
芬尼斯从塔里出来,她走进一座花园。在花园的中间立着一棵嫁接过的树,树上花繁叶茂,有一个开阔舒展的树冠。树的枝条都经过整形,全都垂落下来,几乎触及地面;然而树的主干,生发枝条的主干则挺拔地伸入空中。芬尼斯在这个封闭的院子里,在这个与塔楼相连带围墙的花园里面躺下,她的爱人在她身边。
半闭的闺房,欢乐的殿宇,田园诗的世界,所有这些都表现为诗的意象;同时,在西方传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具有象征意义的诗的层次,如法国中世纪作家吉约姆·德洛里斯的《玫瑰传奇》,以“玫瑰”代表少女,叙述“情人”追求“玫瑰”而不得、后来“情人”经过种种努力,终于获得了“玫瑰”的故事,整个用了隐喻,把对情节和主题的追求转化为诗意的酿造。
同样,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我们也可以读出作为爱情传奇小说的诗化特征,即利用诗词或富有意境的描写,把对情节和主题的追求转化为诗意的创造。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因为男女主人公多是才子和才女,他们对大自然、对人的感情有着独特的细腻的感受,并且因为爱情本身就是诗,诗又最能表现、最能引发神秘奇奥的人类心灵活动,所以作家往往通过人物的诗歌或意境的创造来抒发品尝着爱情的甜蜜或痛苦的主人公的细致的情绪。如《梦中缘》第三回,吴瑞生因堆琼被人拐走,独自在金御史家闭门谢客,不胜寂寞——
一夕,天气清明,微尘不动,东山推出明月,照得个园林如金妆玉砌一般,又听得湖面上一派歌声,吴瑞生郁闷之极,遂着琴童酾了一壶酒,又移了一张小几,安放在太湖石下,在月下坐着,自劝自饮。饮了一回,又起来园中闲步,忽看见太湖石上窖龙中,放着一枝横笛,吴瑞生善于丝竹,遂取出来吹了一曲。此时,夜已二鼓,更深人静,万籁无声,笛音甚是嘹亮,但闻得凄凄楚楚,悲悲切切,就如鹤唳秋空一般。……忽念起烛堆琼前日尚与他饮酒联诗,今日不知他飘流何处,即欲再见一面,也是不能得的,一时悲感交集,偶成八韵高声朗吟道……
从来无巧不成书,这吴瑞生书舍东边,即靠着金御史一座望湖楼。翠娟小姐见今夜这般月色,不胜欣赏,乘父母睡了,私自领着丫环素梅登楼以望湖色。才上楼即听的笛声嘹亮,听了听笛音,即在楼下,低头看,却是一人坐在太湖石下,那里吹竹自饮,翠娟便知是他家先生,这也不放在心上,及听他朗吟诗句,是他句句含心恨,字字带离愁……
于是,翠娟遂动了怜才之心、爱慕之意,忽而“心中说道”,然而“心中大惊道”,忽而“心目自念道”,遂在灯下将吴瑞生月下笛音诗句和成八韵,诗曰:
楼下人幽坐,寂然酒一杯。
徘徊如有望,感慨岂无思。
诗句随风咏,笛音带月吹。
句长情未尽,声短致难挹。
句句含愁恨,声声怨别离。
疑闻孤鹤唳,误认夜猿啼。
宋玉江头赋,相如月下词。
不知浩叹者,肠断却因谁。
这里,有朦胧的月色,有悲切的笛声,有才子月下吹竹自饮的情态描写,有佳人楼上闻笛动心的心理描写,既意韵悠长地渲染出这位失恋才子寂寞凄清,也表现了多情佳人“凤凰台上忆吹箫”的复杂感觉,从而使作品涂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一种哀感顽艳、迷离恍惚的诗意效果。在《春柳莺》中,“毕小姐丝桐露调,石秀才玉箫断肠”,同样也有一种情景交融、意味深长的诗情画意。正如《春柳莺》凡例所言:“《春柳莺》虽偶然寄笔属稿,……却浅而有味,淡而弥永”。
当然,“传奇是诗的或叙事诗的”,说的不仅仅是作品局部的抒情氛围的渲染,更主要的是作者能把小说的生活结构深化为情感结构,从而把对情节和主题的追求转化为诗意的酿造。《定情人》的双星在第一回中说:
吾之情,自有吾情之生灭浅深,吾情若见桃花之红而动,得桃花之红而既定,则吾以桃红为海,而终身愿与偕老矣。吾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则吾以梨花为水,虽不愿与之同心矣。
这里,作者明显地把“桃花之红”和“梨花之白”作为两种象征意象。“桃红”,乃定情人之象征,“梨花之白”,则为无情人之象征;“桃红为海,”乃情海不枯渴,情意不褪色;“梨花为水”,则落花流水情去也。作品就是按照这样的情感结构来构思全书的,双星先是“蒙众媒引见,诸女子虽尽是二八佳人,翠眉蝉鬓,然觌面相亲,奈吾情不动何?”此乃“情若见梨花之白而不动”;至遇蕊珠,则“情若见桃花红而动”,然后“得桃花之红而即定”,最后,“以桃红为海,而终身愿与偕老矣”。于是,在作品的描写中,作者经常把这种“情旨”化为诗意的场面,如第三回:
江蕊珠见双星年少清俊,儒雅风流,又似乎知窍多情,也未免默默动心,虽相见时不敢久留。辞了归阁,然心窝中已落了一片情丝,东西缥渺,却又无因无依,不敢认真。因此,坐在拂云楼上,焚香啜茗,只觉比往日无聊。一日看诗,忽见“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忽然有触,一时高兴,遂拈笔书下句来作题目,赋了一道七言律诗道:
乌衣巷口不容潜,王谢堂前正卷帘。
依掠向人全不避,高飞入帘了无嫌。
弄情疑话隔年旧,寻路喜窥今日檐。
栖息但愁巢破损,落花飞絮又重添。
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少女江蕊珠遇到一位可心的少年之后,那种微妙的、虽不炽烈但已点燃了的爱情火苗,只轻描淡写几笔,但诗意地把少女的青春气息、浪漫情怀、多才善感表现出来:先虚写“未免默默动心”,次则直揭矛盾,既有心“不敢久留”,又无意“落了一片情丝”,而且这情丝又“东西缥渺”,有如《牡丹亭》“游园”中的“袅睛丝,摇漾春如线;”再叙发展,写那无计可消除的“比往日无聊”的心绪。然后,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总括上叙,生发下情,以江蕊珠诗为引线,安排了一对“似曾相识”的情人以诗传情、以“桃红为海”的故事。同样《飞花咏》也是以咏飞花诗作为贯串全书的一条象征性的感情线,最后是“飞花飞去又飞还,依旧枝头锦一团”。还有《玉支玑》中的祖传美玉“玉支玑”,其温润无瑕的特征,也成为贯串全书、象征感情和人格的意象。实际上,才子佳人小说的书名及作品的人名,大多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一种诗的意象。象这种传奇小说的意境创造,既有浪漫小说的意、情和思想,又有写实小说的境、景和形象,它体现了作家的主观情志和客观物境的交融,它淡化了小说的情节主题,可以称这为“有情的写实”或“象征的写实”。这种感觉就象清人周克达在《唐人说荟序》中评说唐传奇一样,“其人皆意有所托,借他事以道其忧幽之怀,遣其慷慨郁伊无聊之况,语渊丽而情凄婉,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
三
那么,这种介于理想与现实,浪漫与写实之间的传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样式?是悲剧,抑或喜剧?如果是悲剧的话,为何又有大团圆的结局?如果是喜剧,为何又有悲剧性的磨难?吉利恩·比尔的论述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
传奇引导我们通过一个复杂的冒险的迷宫,但它们并不激起令人不快的困惑焦虑。它们差不多总是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幸福的结局在传奇中仍然是典型的……传奇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样式,它提供喜剧,它包括受苦。然而它没有喜剧的集中或悲剧的结局。通过它的艺术加工,同样通过个别的故事,它赞美生命活力、自由和幸存。[①g]
这里有三层意思,第一,传奇是一个复杂冒险的迷宫,它包括受苦,但没有悲剧的结局,亦即受难与再生的模式;第二,传奇差不多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它提供喜剧,但没有喜剧的集中,亦即田园诗的大团圆的模式;第三,传奇通过个别的故事,它赞美生命活力、自由和幸存,亦即满足愿望的模式。显然,这三个模式是随意虚构的空中楼阁,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传奇的内在特性,即清黄越在《平鬼传序》中所云:“传奇之作也,骚人韵士以锦绣之心,风雷之笔,涵天地于掌中,舒造化于指下,无者造之而使有,有者化之而使无……令阅者惊风云变态而已耳!”因此,当我们从传奇性的角度去阅读才子佳人小说时,就会理解其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及启示意义。
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有的才子佳人都要履艰涉险,都要经受严峻的考验。或颠沛流离,如《飞花咏》中的昌谷和端容姑,秀才昌谷因祖父有兵籍而被迫从军,使其倾家荡产,亲人离散,恋爱无望;同时地痞流氓宋脱天抢走了端容姑,又使端家骨肉分离,这是第一大难;以后昌谷在途中过继给唐希尧,容姑逃走被救,认凤仪为父,又使昌谷与容姑见面,就在这次见面中,两人才真正开始了纯真热情的恋爱生活,不想因唐希尧的侄子为谋夺家财,不但害了昌谷,也害了唐希尧,而凤仪也由于得罪了权臣宦官而被发配榆林驿,在发配途中父女失散,这是第二大难;最后由于昌全收养了端容姑,端居收养了昌谷,两人真正开始了新的生活。或生死考验,如《定情人》中的江蕊珠受到赫炎的逼婚、东宫选妃的折磨,最后投江殉情被救;《铁花仙史》中的夏瑶枝也被点选进宫,途中船被大风吹翻,夏瑶枝遇苏诚斋救活,收为义女;又如《玉支玑》中的管小姐,为了抵御卜成仁的抢亲,制造了一幕假自杀的惨剧;《梦中缘》中的翠娟被郑一恒投在荒山漫野的枯井中遇救等等,这些佳人们在象征意义上都死过一次,随着她们生命的复活,她们的爱情生命也得到了新生。正如天花藏主人在《飞花咏》咏中所说的:
疑者曰:“大道既欲同归,何不直行,乃纡回于旁蹊曲径,致令车殆马倾而后达。此何意也?无乃多事乎?”噫!非多事也。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也。
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就是通过这种受难与再生的模式强烈地表现出对爱情、对青春、对生命的珍惜和赞美,它的启示意义在于:爱的实现往往是与受苦和牺牲联系在一起的。
“传奇总是关心着愿望和满足”[①h],同样,才子佳人小说也是通过具有喜剧意味的形式,获得愿望和理想的满足,甚至许多实际上是不可逆转的悲剧,他们也尽量缀上一个大团圆的田园诗般的结局。尽管这种形式在它自身的时代投其所好却令后代的人们难以卒读,尽管人们对才子佳人的模式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模式体现了一种形式上的“和谐”和“优美”,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就是通过这样的模式,为人们营筑了一个具有人性的和谐的理想世界。虽然缺乏悲剧效果,但并不意味着缺乏审美效果;大团圆的叙述格局,也同样有着情感体验和审美指向的独特效果。就象西方文学批评家曾指出,莎士比亚通过中世纪传奇的叙事模式,包括受难和幸存的模式,再生模式,田园诗的模式,满足愿望的模式等,从而使充分的人性形式第一次得到表达的真实。[②h]
总之,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决没有被现实完全破坏,它既为作品提供了叙述的形式,也提供给它相当大的想象的能量。它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详细情节组成,以暗示理想的强烈程度为人们领悟。它不同于现实主义的真实,因为它看取世界是片面的、诗意的;它又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奇幻,因为它传的是人生之奇。它是写实和象征的不稳定的混合,它是悲剧和喜剧的兼容式的组合,它是一种具有内在美质的创作方法。
注释:
①b 引自康·巴夫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第184页
①c 译文见乔叟《坎特伯雷故事》方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①d 转引自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
②d 天花才子《快心编》凡例。
①e 转引自吉利思·比尔《传奇》第81页
②e 引自康·巴夫斯托夫斯基《金蔷薇·夜行驿车》
①f 参看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
②f ③f ④f引自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第20页,第21页
①g 吉利恩·比尔《传奇》第44页昆仑出版社
①h 吉利恩·比尔《传奇》第19页
②h 吉利恩·比尔《传奇》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