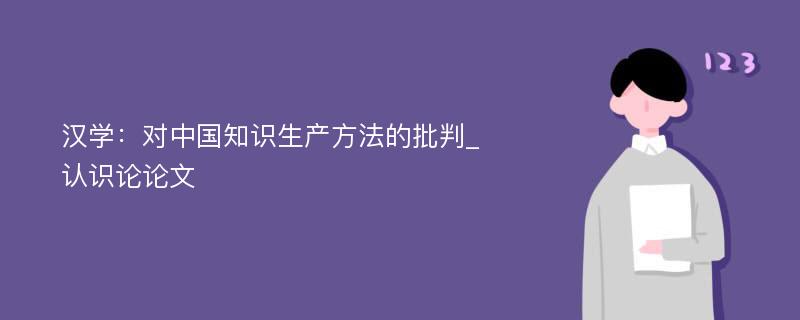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方法论之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方法论论文,中国论文,主义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学主义(Sinologism)作为一个新概念,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知识生产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它与汉学或中国研究有关,但不是汉学或中国研究的一种形式,而指的是一套以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做中国学问的综合体系。汉学主义既是一个知识系统,又是知识生产的一种实践理论。前者主要包括了中西方研究中偏离中国文明实际状况而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现象,而后者则涉及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和中国在生产关于中国文明的知识时所采用的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整体上看,它作为一个知识系统,是建立在西方为中心的种种观点、概念、理论、方法和范式构成的总体基础之上的,其理论核心是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为中心的一种隐性意识形态。在已发表的拙文中,笔者对汉学主义的概念、定义、兴起、谱系、本质,以及与其它思想观点的关系和表现形式等问题已有较为详细的探讨。①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探讨汉学主义赖以产生的背景和心态,思维定势与方法论,以及一些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如何在他们的著作中奠定其方法论的表现,并试图提出摆脱这种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的建议。
汉学主义的早期心态
汉学主义产生于西方人试图建立一个旨在将中国吸收在内的全球化思想体系的过程之中。早期汉学主义呈现出温和的形式,它试图将中国在生活、宗教和思想方面的巨大差异融入一种由利玛窦开创的、以迁就主义政策为导向的广泛知识体系之中。然而,即使是早期的妥协策略,也没有完全摆脱后来主导一切中西冲突的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正如利玛窦自己所承认的:“我按照对我们有利的方式,解释孔子的著作中那些模棱两可的东西,藉此尽力将我们的观点转化成这位中国文人领袖的思想。”②这种策略的最终消亡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标志着西方思想和认识论占支配地位的开始,预示着笔者称之为“汉学主义”——即西方思维习惯对中国的思想支配——的兴起。
17世纪后期,在莱布尼茨探讨中国问题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明显的西方文化霸权心态和思维习惯的痕迹。他承认,中国在实用技艺和自然事物的把握方面几乎是和西方平等的,却认为西方在精神追求方面比中国优越:“在知识的深度和理论基础方面,我们占有优势。除了我们可以声称为我们独有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有关无形物质的知识,对于那些由思维从材料——即数理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的理解,我们也远远超过他们。实际上,这一点在中国天文学和我们的天文学的竞争中得到了证明。由此,我们认为中国人不懂得心灵的光辉,不懂得实验的艺术,他们满足于一种我们的工匠都能普遍掌握的经验几何。”③这里,我们注意到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中存在一种普遍倾向:即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尽管所知有限,却会毫不迟疑地评头品足,骤下定论,断言中国文明缺这少那。
18世纪中期,努力将中国置入西方世界体系成了西方主要思想家的头脑中最关心的问题。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知性思考中,以不同的方式系统地尝试着将中国纳入其中。伏尔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国孤儿》④和世界历史巨著中,都保留了理想的中国形象。在或许是首部世界通史中,他将最显著的位置给了中国,以展示中国历史的两章作为这部鸿篇巨制的开篇。他赞美中国,却将其描述为一成不变的文明:“这个国度维持了4000多年的辉煌,而没有经历任何法律、礼仪、语言、甚至时尚和服装风格方面的实质变化。”⑤而同一时期的孟德斯鸠则已经走出了18世纪中期对中国的痴迷,转而对其大失所望。这个时候,把中国看作一个古老、落后、疲惫、排斥一切变化的国家的观点出现了,此后一直影响着那些试图将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西方思想家。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那种支配中西学术研究、并最终发展成笔者称之为汉学主义的思维习惯。
作为最早将分类比较法扩展到人类社会政治形式的思想家之一,孟德斯鸠也许是首位以汉学主义研究方法探索中华文明的西方思想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投入大量时间学习中国文化,还和一个随法国传教士来欧洲、名叫黄嘉略的中国人⑥结为好友。孟德斯鸠研究中国的方式带有明显的后期西方思想家的特点,他对中国的兴趣不在其本身,而是为了构思创建一个全球的政治和思想体系。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首次尝试着审视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的多样化存在形式。在这部作品中,孟德斯鸠把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分为三类:君主制政府(以世袭人物如国王、女王、皇帝为首的自由政府)、专制政府(由独裁人物领导的奴役政府)和共和制政府(由公众选举出的领袖领导的自由政府),三者分别遵循荣誉、恐吓和美德的原则运转。这三个原则决定了每种政府的性质和功能。荣誉原则促使君主制政府建立严格的等级机构,恐吓原则促使专制政府实施一种要求无条件效忠和顺从的社会秩序,美德原则促使共和制政府推进国民之间的相互平等。⑦他拒绝接受传教士们将中国视为理想国度的描述,在他的中华帝国研究的结语中,将中国归为专制国家:“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其原则是恐吓。”⑧
任何有足够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会同意,荣誉、恐吓和美德三项原则在中国历代王朝政府中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就会动摇孟德斯鸠建构起来的宏大体系。预料到曾经去过中国的传教士们会质疑他所建立的理论,孟德斯鸠先发制人:“我们的传教士把庞大的中华帝国描述成一个混合了恐吓、荣誉和美德原则的可敬的政府。如此一来,我建立的三类政府原则将是空洞无据的。”⑨他借助中国社会现实维护自己的理论,驳斥传教士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缺乏他所定义的那种君主制中必不可少的荣誉观念:“我不明白,在不受鞭笞就无所作为的人中间,怎么能谈得上荣誉。”在共和制政府至关重要的美德方面,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也是欠缺的,因为“我们的商队,非但没有向我们描述传教士们所提及的那些美德,反而可以给我们大讲官吏的强盗行径。我可以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安森男爵作证”。⑩他竟然不相信曾经在中国长期逗留、有足够时间观察中国社会现状的传教士,而去相信那些抱着牟利和征服目的来到中国的商人和海员,真是一大讽刺。他竟然将乔治·安森,一位因非法进入中国而没有受到中国官员礼遇的英国海军军官,当做所谓的中国问题权威加以引证,则是更大的讽刺。在某种意义上,他请安森作证不是一个随意的行为,因为安森“象征着大不列颠扩张主义新的咄咄逼人的一面,自信十足、好勇斗狠、急于欺负弱小、无法忍受耽搁”。在比较中国的和西方的统治者时,他写道:“他[中国的国王或皇帝]不会像我们的君主那样,认为如果治理不好国家,来世将会过的不快乐,今生会不强大、不富有;他只是知道,如果这个政府不够好,他将会失去自己的帝国和生命。”(11)孟德斯鸠完全不知中国人关于来世和报应的观念,似乎对传统中国王朝的基本政治原则,即优秀的统治者由上天赋予统治的权利,专制的统治者则被上天剥夺统治权的“天命论”一无所知。
他从政治理论角度对中国的分析,展现了西方认识论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即一种源于西方政权研究的目的论方法。在他建构的理论中,政府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大小:“领土狭小产生共和制;中等国家产生君主制;而庞大的帝国则注定要产生握有专制权力的统治者。”(12)既然中国有史以来一直是庞大的帝国,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建立在恐吓,而不是荣誉和美德原则之上的专制国家。根据他的理论,“专制政府中一定没有监察官”。(13)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又不符合他的理论。中国王朝政府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监察御史制度,御史的唯一职责就是批评统治者错误的政策和品行,并提出矫正措施。作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政治制度,监察制度在中国历代王朝政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1年共和革命之后,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五权分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4)监察制度的存在,彻底否定了孟德斯鸠视中国为专制国家的观点。因此,他不得不有所让步,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不符合这条规律。在政府刑罚问题上,孟德斯鸠注意到中国重教化而轻刑罚,因为“刑罚越苛,革命越近”。他不得不在笔记中再次承认:“今后,我应该说明,中国在这一方面属于共和制或君主制。”(15)孟德斯鸠在其书中把中国列入专制一类,却一次次地将其作为君主制国家讨论。(16)
史景迁在评论孟德斯鸠与中国的关系时指出:“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诸多评论,散落分布在他那篇幅冗长、精心创作的作品中。但是,渐渐地,它们累积成了一种对中国的控诉。这证明他越来越反对他最初曾经吸收的耶稣会教士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越来越接近笛福小说(他或许曾经读过)和安森的叙述(他肯定曾经读过)中那些尖刻的批判。”(17)读了孟德斯鸠的书,其内容似乎证实了史景迁的话。孟德斯鸠多次表达了露骨的成见。比如,他写道:“很奇怪,生活完全由礼仪主导的中国人,却是地球上最不道德的民族……古代斯巴达准许偷窃;而中国准许欺诈。”(18)
查看了孟德斯鸠书中所有涉及中国的地方之后,我在他对中华文明的描述中发现了一种模式。他对中国事物的扭曲,并非如许多学者所想的那样,遵循欧洲从颂华到恐华立场的转变趋势:而是由他试图建立一个宏大的世界文明知识体系的愿望所决定的。这一体系的建立,需要构建一种理论框架控制中华文明令人困惑的复杂性,并以设想的理论解释其与西方文明的差异。将中国放入专制国家的鸽笼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研究中国多年,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还是不足以解释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再例如,他注意到了一个中国政府特有的属性,即宗教、法律、道德观念和礼仪风俗的融合。(19)虽然他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还是表明了他无法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运转机制。他将这种融合当做坏事,因为“基督教几乎永不可能在中国立足”。(20)他将基督教无法在中国传播的原因,归结为基督教宗教信仰与中国礼教的根本差异。前者要求一切统一,后者则要求各自分离。在此,他的观点又一次自相矛盾了。如果中国把宗教、法律、道德观念和风俗礼仪融为一体,他又怎么能得出中国礼教具有分离性的结论呢?然后,他借助理论框架,进一步试图掩盖其自相矛盾之处:“而且,既然我们明白了这种分离性与专制主义精神存在普遍联系,我们便可以从中找到君主制政府——任何一个温和的君主制政府——可以更好地与基督教结盟的原因。”(21)他认识论中的意识形态模式,在这一论点中已暴露无遗了。
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评判方式
孟德斯鸠开创了将中国融入其中的宏大知识体系传统,为汉学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18世纪末德国的约翰那·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效仿他,创作了一部人类历史哲学巨著(其中一章是讨论中国问题的),进一步扩展了汉学主义的领域。与孟德斯鸠相比,赫尔德的态度表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首先,他彻底舍弃了前代思想家们普遍接受的对于中华文明的正面看法。赫尔德以诗人的想象力,运用近乎夸张讽刺的笔调,在书中每一章都写满了不可靠、不准确的信息。其内容几乎涉及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包括地理、人口、政府、家庭生活、道德观念、社会风俗、语言、艺术、发明、宗教,甚至国民性格。他忍不住对每条信息都大加评判,而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方式介绍信息。笔者本文探索的目的不在于揭露错误和偏见,因此不打算详细描述他对中华文明的事实是怎样进行扭曲的。我只想引用这部专著的结束语,说明一下他的价值评判:“带着鞑靼式的骄傲,她(中国)瞧不起那些背井离乡,以最实在的商品交换价值微小的货物的欧洲商人。她收了欧洲商人的银子,却回报以数百万磅喝了令人萎靡不振的茶叶,以此腐蚀整个欧洲。”(22)综观这一章,其内容告诉读者:中国由半野蛮的暴君统治着;其文化制度非常幼稚;这片土地上没有科学或发明;中国人不懂得欣赏艺术和美;他们是虚荣、贪婪和虚伪的人格象征;他们的道德观念被幼稚的顺从思想主导;他们的语言是一种象形文字的原始形态;整体而言,中国是“一片以半蒙古式的形态立于世界边缘的废墟”。(23)
发展至此,汉学主义已经变成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族群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一种形式。赫尔德的态度表现出了露骨的族群中心主义,甚至是种族主义的倾向。这些倾向,此后发展成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在这部集中了他的人类和历史本质思想的著作中,赫尔德把中国文化的劣势归因于中国国民性格的软弱:“这个民族的性格是历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未与其它民族融合的蒙古人种民族会被其发展至巅峰的政治教化所塑造成什么样子,或者不会被塑造成什么样子。”(24)他的族群中心主义思想贯穿全章,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用来描述中国的意象和比喻之中。他把中国比作“一只冬眠的睡鼠”。他还以更为耸人听闻的意象来刻画中华民族,把中国说成是一具“绸缎裹身、绘着象形文字、涂着防腐油的木乃伊”,由“一成不变的幼稚制度”所支配。(25)也许,这是西方知性思考中第一次出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观念。在赫尔德看来,即使中国人希望在文化上更加优越,他们也“永远无法变成希腊人或罗马人。中国人过去是什么样,就永远是什么样:是一个天生的小眼睛、塌鼻子、扁额头、稀胡须、大耳朵、鼓肚子的民族”。(26)中国式的教育加重了这种民族性格的劣势:“中国人追求的教育模式与他们的国民性格凑在一起,导致他们原地踏步,毫无进益。”(27)
奇怪的是,赫尔德分析中华文明时狭隘的种族歧视,与其拒绝刻板的种族理论时的宽广心胸形成了对照。他一方面为德国的语言、文学和艺术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另一方面却又警告说:“国家荣誉是骗人的诱饵。当它攀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用铁箍扣住人的脑袋。受其禁锢的人如陷迷雾之中,只能看到自己的形象,感受不到任何外来的影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正是他看待中国的方式,而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成见和偏见,因为他对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信心十足。在书的前言中,他写道:“我读过几乎所有关于这一课题的材料。自青年时代起,每一本新出的有关人类历史的书籍,对我都是一座被发现的宝藏,希望从中为我的巨著找到一些材料。”(28)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自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看法既不含敌意也不带轻视,纯粹是表现中国真实本质的客观知识:“我对中国人特性的展现,不带有任何敌意或者轻视色彩。任何一句话都来自最忠诚的中国拥护者,都可以从中国社会风俗的每一层面找到上百个支持的证据。”(29)他的话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他那个时代,一种研究中国问题的意识形态模式已经形成,并且逐渐转变成西方汉学知识生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套用既设模式的方法论
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汉学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坚持以西方化的感知、概念、抽象和归纳方式研究中国及其文化资料。这种独特的思维习惯表现在拒绝或不愿按照中国自身的方式看待中国问题。在这一方面,卡尔·魏特夫的中国与中华文明研究值得特别分析。魏特夫是一位通晓汉语的西方思想家,曾主修过中华文化,并且亲身去过中国观察中国社会。他的重要著作《东方专制主义:集权的比较研究》直接取材于中国,体现了典型的东方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由于其东方主义的倾向,该书充斥着常识性错误、信息错误和机械地套用西方理论而产生的成见。在此,我只分析其中一些突出的细节。
在考察中国传统宗教和政权的关系时,魏特夫得出结论:“总而言之:在中国官方信仰中,统治者和各阶层高级官员负有关键的宗教职能,尽管绝大多数官员和皇帝本人通常忙于现世事务。因此,传统的中国政府体现了一种贯穿始终的——而且非同寻常的——神权政治变体。”(30)虽然用了些限定词,他还是将传统中国政府定义成了一种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与世上其他神权政府只有度的差异,而无质的变化。这种观点和另外一种将中国与欧洲的差异归因为历史上缺乏神职人员的看法相互冲突。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读者很容易就能看出,他对中国政权和宗教信仰的阐释是罔顾事实和不合逻辑的。但是,对于把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作为学术课题进行研究的人来说,这种错误论述是无法用缺乏中国历史和文化知识来解释的,而必须归根于笔者称之为汉学主义的研究态度与方法。
魏特夫把个人观点应用于中国研究的做法,一度受到著名汉学家,如李约瑟的严厉批评。李约瑟直率地批评将魏特夫对中国的看法是对中国历史基础知识的无知。他有理有据地指出:传统的中国政府机构整体而言不是专制,也并非由神职人员主导;魏特夫的研究没有考虑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类似政府机构。(31)笔者主要关心的不是魏特夫对中国的看法是对是错,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魏特夫是位能够读懂汉语、终生对中国兴趣不减并且致力于中华文明研究的西方思想家,他怎么会提出那些低级荒谬的观点呢?在我看来,魏特夫的问题不在于他缺乏中国历史基础知识,而是他不得不将中华文明强行纳入一套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统一理论中。魏特夫的理论是建立在东方专制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他设想出一种发达的、借控制供水来控制臣民的“水利文明”。他坚信这些“水利文明”——虽然不是全部出现在东方国家,也不是所有东方社会的特性——和西方世界的文明有本质区别。在他的观念中,世界历史上的大部分古代文明,如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以及哥伦布发现的美洲新大陆之前的墨西哥和秘鲁,都是水利文明帝国。他的理论并非独创发明。事实上,他的核心思想取自马克思和之前的其他西方思想家,并增添了他自己的概念化表达。
作为汉学主义登峰造极的一种形式,魏特夫的个案在汉学主义的发展谱系上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因为他的观点不仅继承了孟德斯鸠、赫尔德、黑格尔等人的思想,而且还是其他几位重要西方思想家对中国的看法的节点。在此仍然以所谓“水利理论”为例进行分析。马克思不是水利理论的第一位阐发者。他吸取了之前一些历史学家的思想,在一篇题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的短文中,提到了以水利生产模式为基础的亚细亚形式的政府。他写道:“自远古时代起,亚洲普遍存在的只有三个政府部门:一是财政部门,或叫国内掠夺机构;二是战争部门,或叫国外掠夺机构;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这种政府兴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气候和领土。东方的气候和领土状况,决定了运河和供水渠道的人工灌溉是东方农业的基础。马克思区分了西方和东方的用水方式,将其当做东方集权政府的经济基础:“节约和共同用水的根本必要性,在西方促使了私人企业自愿联合……在文明程度太低、领土面积太大,难以实现自愿联合的东方,则需要集权政府的干预。”马克思的确暗示了集权政府是“亚细亚式的专制政府”,但是他把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看作专制主义,(32)并不比亚细亚式专制政府好。事实上,他发现集权政府的崩溃是国内经济和人民的灾难,如他所说,“由此,所有的亚细亚式政府都必须执行的一种经济职能,即公共工程建设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一旦忽略灌溉和排水,这些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从其他角度无法解释的事实,即为什么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土地现在都成了荒芜不毛之地了。”(33)恩格斯支持马克思的观点,将其当做研究东方政治和宗教史的关键,却也像马克思一样小心地将中国排除在外。他像马克思一样批评英国疏忽灌溉,致使印度和中东农业彻底衰败。(34)魏特夫引用了马克思在有关印度问题的文章中简短阐述的观点,稍加修改并将其强加于一切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为了确立自己的理论有效性,他不得不对其他文明材料进行篡改,使之适应他自己的范式:俄罗斯极权主义概念取自亚洲;虽然缺乏灌溉的证据——或许是因为灌溉的痕迹在时光流逝中消失了——印度河文明还是被定为水利文明。大多数水利文明国家发源于沙漠地区,而中国符合他的理论,因为治水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
魏特夫为了将中国纳入其水利社会理论,他把马克思的公共工程理论,即通过灌溉来控制水源应用和分配的公共工程,扩展成了所有公共工程的理论,包括防御系统、宫殿、地下陵墓,却依然称之为“水利专制主义”。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会带来彻底的寂寞和猜忌,不仅影响到皇帝,也会使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怀疑其他所有的人:同僚、邻居、甚至是家人。这里,他又一次用自己的理论衡量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大范围的朋友、亲人和家人相互猜疑只出现在“文革”期间。甚至在那个时候,家庭关系对饱受迫害的人们来说,依然是最后的精神依托。他完全忘记了现代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来自西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援引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受害者的范例,认为这位因得罪汉武帝而被处以宫刑的中国历史学家,其命运比现代专制主义受害者要好,因为他不必公开受辱或当众忏悔。(35)他这种比较的讽刺之处在于,“集权管理政府”是西方的发明,而不是东方的产物,因为其原初理念来自杰若米·边沁为现代监狱所设计的“全景监控塔”,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年》中有栩栩如生的描绘,后来又为福柯借用来作为贯穿整个现代西方社会的“监管连续体”(cameral continuum)的比喻。
魏特夫对中国专制政治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资料的客观分析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思想理念基础上。他相信,尽管世界上的极权主义有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古代的外在区别,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源于东方。史景迁一语中的地指出:“他长期以来一直研究的中国,在魏特夫的意识中和现代极权主义的运转混为一体了,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还是纳粹主义,也和民主政治令人不安的轻信特性溶合在了一起。”(36)基于这种观点,他没有区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和西方现代专制主义,断言古代中国混淆了道德、礼仪和法律之间的界限,没有独立的宗教信仰。他还认为,既然以恐吓代替了荣誉作为主导观念,那么中国的专制政治与西方的君主制度是不同的。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的政府理论的影响,还可以清楚地辨别出汉学主义思想的谱系及其发展模式。
1962年第二次印刷时,魏特夫在其作品的前言中,讨论了指导他研究东方专制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和方法论策略。他的前言不仅透露了他个人研究中具体存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也揭示了非西方文化研究中普遍采用的西方式办法。在这篇前言中,他承认自己对提出重大创意和创立广泛体系很感兴趣:“运用宏大的结构化概念,从而建立识别社会结构及其变化的重要模式。”他强调这种方法的价值,因为西方思想家们,从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思想家,一直在运用它。但是在笔者看来,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是西方认识论存在问题的地方。魏特夫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西方有关中国和其他文化的知识生产中采用的错误认识论。他的方法以先入为主的概念为指导,以西方形而上学定性的认识论为基础。他强调重大创意的价值,却没有看到其问题:“一位认为所有的实验器具,都必须自己从头发明的科学家进入研究工作时,可以是头脑空空——但是,他离开时仍会是头脑空空。一个经过现实验证的重要概念,如果予以正确应用的话,其扩展潜力是极大的。它植根于过去的经验和观念之中,很可能会随着新发现的经验资料发展。”(37)魏特夫承认他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和中西方专制主义对比研究是以“重要概念”或“宏观分析原则”为导向的。他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提出重要概念和进行现实验证的方法,致力于揭示基础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观念。(38)表面上,他是在提倡一种在研究非西方社会时强调所谓客观真理和科学观察的观点,而这种所谓客观真理和科学观察正是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批判过的对象。魏特夫对非西方文化的探讨,特别是中东穆斯林文化,带有典型的东方主义色彩。但是,颇令笔者吃惊的是,他的观点在赛义德的书中没有受到批评。
魏特夫的研究,代表了西方人努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将中国和中华文明纳入全球系统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简单描述如下:西方学者和思想家倾向于建构一种以西方社会及其资料的观察和研究为基础的模式或系统,并将这个建构起来的模式或系统当做中国社会及其资料研究的指导方针。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纯粹是生搬硬套西方化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资料。如果中国资料符合他们的模式或体系,那很好。如果不符合,他们就会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畸形的,或者通过篡改中国资料以适应该模式或系统。他们对这个模式或理论信心十足,将其看作一个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遍应用性的科学体系。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坚定信仰不仅扭曲了对非西方文化和资料的认识,而且把认识论的问题转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将认识论凌驾于研究资料之上。
“理想类型”的方法论
汉学主义是建立在有问题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而有问题的认识论衍生出有问题的方法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伯特兰·罗素的一番话颇能揭示出汉学主义方法论问题。他从相反的方向,即把中国和中华文明理想化,走向汉学主义。罗素和发明“白种人的负担”一词的罗德亚德·吉卜林是同一时代的人。然而,罗素与吉卜林不同。他敏锐地意识到西方对待中国的霸权态度是不可取的,他写道:“我们深信,我们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比别人强。所以当碰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时,我们便想当然地认为对他们最大的善举莫过于让他们以我们的方式生活。这简直是天大的错误。”(39)他的评论触及了支撑汉学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基础,界定了汉学主义的核心方法论问题。这种错误的方法论,要为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存在的误述和扭曲负部分责任。
在开展中西对比研究的西方重要思想家们当中,能够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保持距离、不对中国文化作出赞美或贬损的价值评判者寥寥无几,马克斯·韦伯便是其中之一。与其他西方思想家一样,他的目的是找出东西文化不同发展轨迹的原因。但是,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不对非欧洲文明进行价值判断或评价。他研究中国,采用的是一种以他的“理解”(Verstehen)理论(又称之为理解社会学)和实证理论(又称之为人文主义社会学)为基础的方法论。韦伯似乎意识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文明有其局限性。他的这种意识,体现在他相信社会、经济和历史研究决不能完全靠归纳和描述。但是,他也同时提出,研究者应该始终以一种他称之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工具,处理调查对象。理想类型由特定现象的性状和要素构成,却并不意味着要对应任何一个个案的所有特性。他怀着这种意识,对中华文明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试图解释在资源丰富、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兴起。韦伯考察了中国历史、社会、经济、宗教及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将其与西方的相应元素进行比较,把中国没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归咎为儒家思想的统治、帝制官僚体系、中国城市的自然特性,及其精神领域的本质等。韦伯的许多见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中国宗教》出版后的一个世纪证明了它们的正确性。(40)20世纪90年代中期,韦伯的许多观点再次被认为是正确的,尽管“他的许多经验主义言论过时了”。(41)
不过,当我们考察韦伯如何将系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理论应用于中国传统时,我们会发现问题。他断言:“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首先要在宗教领域内寻找。”(42)当这个观点应用于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新教信仰的文化传统时,存在着严重的破绽。因为它就等于说东方社会——其主要宗教是儒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其他土著宗教——的人们必须信奉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伦理,才能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的进程。一些东亚社会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转型,这使他的观点显得十分荒谬。他的论断中所隐含的荒谬性表明,以“理想类型”为基础的方法论存在严重的缺陷。
在韦伯的众多独创观点中,他的“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西方思想家构建涵盖所有已知人类文明的所谓“普遍历史”的重要概念之一。但是这一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正是汉学主义方法论的不足。韦伯的“理想类型”指的是分析性构建或范式,它们试图赋予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无序行为以一种人为的连贯性从而方便找出独特的行为模式。韦伯承认,理想类型并不是现实的写照或复制品,而是通过单方面强调现实,从研究者认为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材料中抽象出来的“有用的虚构产物”。(43)韦伯虽然承认“理想类型”的运用是一种抽象过程,却还是坚持认为:若要了解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理想类型”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现象与物理现象不同,它们涉及必须用“理想类型”进行解释的人类行为。韦伯自己写道:“一个理想类型是由单方面对一个或更多观点的强调,以及对大量分散的、孤立的、或多或少存在但偶尔又不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现象综合而形成的,这些现象按照那些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被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44)阐述这个理论时,韦伯犯了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普遍会犯的错误:那就是,从单个概念出发考察一个复杂的文明集合体,尽管这个概念是通过归纳分析欧洲传统中的社会现象总结出来的。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点,最初是通过分析西方资料抽象出来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一个“理想类型”。该论点的出处揭示了其主观性质。即使对调查问题有所帮助,当它被用来分析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情形毫无关联的社会时,依然是一种“人为概念”。我们承认,韦伯把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归咎于几种因素的做法,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说他所指出的失败主因,即缺乏特定的宗教道德规范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不确切的。与在他之前的西方思想家一样,韦伯还是陷入了先构建理论,再将其作为概念框架用来研究中国资料的误区。换句话说,他也未能免俗,也试图强行将中国纳入西方理论体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反驳了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经济发展状况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兴起是因为基督教伦理信奉努力工作和为上帝服务、履行现世职责的道德价值。(45)是宗教力量,而非经济力量,提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思考方式。正如他那大胆的观点一经发表就引来了无数的争议,此后也一直备受攻击的那样,同样的是,他对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宗教学解读也引来激烈的批评。分析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的最终原因时,韦伯强行将中国纳入了他通过分析西方材料构建起来的理论。
在《西方中的东方》这本饶有趣味的书中,杰克·古迪考察了包括韦伯在内的几位社会历史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的研究,反驳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有其内在必要条件的观点,提出东西方在贸易活动方面其实差异甚微。在这本书中,古迪对韦伯提出的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批判。(46)这里,我只提供自己的简单评论。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中国佛教是印度佛教的汉化形式。佛教是中国历史上信奉最广、实践最多的宗教信仰。如果说儒教和道教思想中没有韦伯视为资本主义崛起所必需的思想要件,佛教思想无疑并不缺乏宿命、来世、禁欲、功德、履行现世职责等观念。这些都是与加尔文主义相似的理论思想,韦伯将其看作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形成所必需的精神前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探讨宗教与资本主义社会学的作品中,韦伯几乎将中国佛教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理由是“中国佛教对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即经济思维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47)这样断言佛教对中国人的经济思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有点过于简单化了。他虽然在讨论儒教和道教问题时简单地提到了佛教机构,但他完全忽视了佛教——尤其是社会上世俗形式的佛教信仰——对中国政治、政府、公众、社区事务、慈善活动、宗教组织以及农民起义的影响。在一本关于印度宗教的书中,他对宗教社会学进行了论述。因此,他避而不谈佛教及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令人费解的。基于中国佛教含有类似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成分,他的疏忽让人不得不怀疑是故意为之,以免与自己的总体观点发生冲突。即便是被韦伯当做中国未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的儒教,也已得到了当今学者的广泛认可。他们认为,儒教推动了远东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实现现代化、取得令人惊叹的工业化和资本的增长。亚洲国家的家庭结构是韦伯心目中资本主义崛起的另一障碍,如今被认为有利于培养资本主义企业的团队精神。(48)儒教是否促进了东亚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个问题引起了公众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由此产生了所谓的“儒家假说”,该假说认为,体现在政府领导、竞争教育、自律的劳动队伍、平等与自力更生原则、自我修养等方面的儒家伦理观念为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崛起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和强大的动力。(49)企图从儒家思想中找出与韦伯的新教伦理完全对应的观念,是肤浅而轻率的。但是,忽视儒家伦理在汉字文化圈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同样肤浅而轻率的,因为在汉字文化圈里儒家思想的精神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科学主义的方法论
我们可以把汉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称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科学主义方法”。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主导支配地位,许多西方学者借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衍生出一系列所谓科学的、客观的中国问题研究方法。这个准科学范式所存在的问题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认识不足。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中,很少有人充分注意到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统一体,包含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受自然客观规律支配、而是由历史人物主观选择决定的诸多变量。另一方面,这种科学方法在方法论上是不彻底的。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科学研究者对调查对象必须采取客观的态度;研究调查对象时,必须运用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概括观察对象的抽象原则需用归纳法,而检验这些抽象原则正确与否则要用演绎法。此外,研究者还需要同时运用归纳和演绎法进行深入观察,对这些原则进行改进和完善。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知识体系和普遍历史的西方思想家们,很少应用归纳法。因为他们之中能读懂汉语的寥寥无几,故而无法接触第一手汉语资料。他们研究中国的学术成就主要是通过演绎法取得的,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研究是一个将现有西方知识应用于或强加于译成欧洲语言的汉语资料的过程。因此,他们的中国知识往往只是西方知识的影子。在此,我们看到了文化研究中一种有趣的情形。过去,人们相信中国是西方的终极“他者”,但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中国变成了西方的第二个自我。在勾画第二个自我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往往依据西方的自我形象作出价值评判。
赫尔德的研究方法体现了汉学主义的一种方法论:即相信所有学科皆有科学客观性。他以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方式,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人类文明。自他伊始,研究中国的西方思想家们开始将中国看作西方科学探索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对象。我们可以在赫尔德对人类历史的定义中看到这种认识论的方法:“我年轻的时候,当科学的曙光带着所有的美丽——这种美丽在生命的中午就大大减少了——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经常想,既然世上一切事物都有其哲学和科学,那么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广义的人类历史问题,是否就没有自己的哲学和科学呢。”(50)赫尔德相信,形而上学、道德、物理、自然历史和宗教——都是根据一种伟大的既定计划、以一定的模式而发展的,他有时把这种大计划称之为“大自然”,有时煞费苦心地解释成上帝“创世的有机力量”。(51)虽然他谦虚地声称自己的专著还算不上是人类历史哲学,他相信这样的努力会在19世纪末有所斩获。他的前言实质上是对人类历史书写的理性思考,表现了他对知识生产问题的认识论反思。它向读者传达的信息是:“历史哲学”意指对人类历史的科学客观的描述。他的观点不仅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还提出了有关历史撰写的客观性谬论——一种一直以来受到新、旧历史主义强烈抨击的主张。他确信,从上帝设计的大计划出发,能够找到一种人类历史的普遍计划。他的这种观点成为许多西方思想家研究世界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的信念基础。
赫尔德研究中国知识的方式凸显出一个在汉学主义中特别显著,在大多数西方学者对待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态度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特征:那就是,按照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方式,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文明。此后,更多的欧洲思想家致力于将中国纳入他们预设的科学体系中,并对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置身于人类历史发展主线之外,提出了许多看法。在英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也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勤劳、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但是,这个国家似乎长期停滞不前了。五百多年前旅居中国的马可波罗对其耕作、勤奋和人口稠密状况的记述,几乎和当今旅行家们的描写没有什么区别。”(52)他试图将中国引入他的政治经济体系,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与其人口稠密有关。斯密依据非常有限的资料,忽视马可波罗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和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骤下定论,并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依据论断中国落后的根源。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孟德斯鸠对他的影响,因为这位法国思想家也认为中华文明的本质和现状主要是由其庞大的人口所决定的。
汉学主义的智性殖民
汉学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纯西方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其表现是在西方以外的人们的大脑里进行认识论的殖民。在这方面,汉学主义具有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汉学主义表现在,那些已经将西方视角内化的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思想框架看作分析中国材料唯一可行的方式,无视中国材料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背景,强行将其纳入西方框架体系。汉学主义的终极形式,表现为一种或明确或隐含的对待知识的观念。这种观念把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当做唯一正确的方式,把西方知识体系看作唯一客观的知识。汉学主义是一种从看似客观、公正、普遍、永恒的西方价值观出发的价值评判方式。因此,对于中国和华裔学者来说,汉学主义已经成了中西关系研究中认识论殖民的一种形式。它深深植根于西方和远东(曾经采用汉字作为其书写系统基础的汉字圈)社会与文化的无意识之中,阻碍了中西之间的互相了解。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以及普通民众,都在其可见或不可见的控制之下。除非能够彻底认清这种认识论殖民;否则西方或中国都无法了解对方的本来面貌。汉学主义的外延含义,对归属于所谓中国领域的远东文化和传统,也是适用的。
其次,汉学主义是一种认识论的惰性。作为一种惯性,汉学主义是遏制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人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约束力量。其内在逻辑要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向西方寻求学习效仿的榜样和支持。汉学主义暗示西方的模式和观念,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还是经济的、法律的、审美的等等,都是唯一正确的。即使在中国学术领域内,中国学者也需要寻求西方学术的支持和认同。这种例子很多,笔者只想分析其中几个。3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随之而来的,是对西方认识论及其衍生理论或明或暗的信仰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度,将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所谓“崇洋媚外”的趋势推向了顶峰。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我们就会明白从清末“自强”运动、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新阶段和1989年以来的新时期后期,无论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还是鲁迅的“拿来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洋为中用”,还是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中国人一直专心致力于吸收、消化和抵抗西方思想、观念和理论,不屈不挠地探索怎样才是处理西化问题最有效的方式。结果,有些中国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已养成一种历史的惰性,不再愿意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不再愿意用自己的耳朵去聆听,不再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不再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新。相反,他们完全依赖于西方的眼光和思维以及重复西方的思想和理念,过去的一百多年基本上是一个按照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行自我认识论殖民的时期。
突破汉学主义的方法论
笔者的汉学主义研究发现了一些中国知识生产中存在的观念问题。即使学者们决心以科学、客观的方法处理中国知识,他们所创造出的中国知识本质上还是主观的。怎样才能创造出真正客观的中国知识呢?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认知识生产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私人化特点。在这一方面,斯宾格勒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智慧。与大多数汉学家和西方学者不同,斯宾格勒坦率地承认思想家的历史哲学带有主观性,思想观念也会因其背景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从长远来看,真理对一个人而言,就是自打出生就已经在其心目中形成的这个世界的形象。真理不是他创造出来的,而是他在自己内心深处发现的。真理是他的自我重现:是其存在的语言表达形式;是构成一种就其生命而言无法更改的原则的个性内涵,因为真理和他的生命是同一的。”(53)斯宾格勒也承认,他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现的真理总是带有个人色彩,甚至是由个人的存在所决定的:“那么,我就可以说我所发现的问题实质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对下一时代的主流思想来说也是正确的;但它本身,如与其血统来历所附带的条件分离了,就不可能是正确的。”(54)他指出任何一种历史都带有片面性,从而进一步反驳了历史的客观性观点:“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了解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历史只是眼前所能看到的一面,是一种关于历史与命运哲学的新见解——同类中的首例。”(55)
真正科学的中国知识生产过程应该与诠释学的诠释循环相似。这是因为中国在许多方面,与其他文明一样,不是科学观测的静止客体,而是一部内涵深刻、有待翻阅理解的巨著。阅读中国这部作品时,我们总是从一种影响阅读与理解的主观立场出发,因此需要采用一种建立在循环释义基础上的诠释学方法。当然,诠释过程也不可能毫无偏见。事实上,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诠释努力总是从他称之为‘偏见’的初始概念开始的,而这种偏见是理解的必需条件。”(56)在海德格尔对历史诠释学的探讨中,“偏见”是实现本体论目标的“理解的前结构”,(57)是前景或前理解的一种形式。伽达默尔为了证明“偏见”这一概念的正当性,论证说:“承认一切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偏见,赋予了解释问题真正的动力,”偏见“未必意味着错误的判断”。他还说,偏见“可能有积极的价值,也可能有消极的价值”,(58)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59)他推崇海德格尔重构的施莱尔马赫的循环释义概念:“对文本的理解永远取决于前理解的心理期待活动。整体与部分的循环交替不会在正确的理解中消逝,相反,它从中得到彻底的实现。这种循环……既不主观也不客观,将理解描述成传统活动和译者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60)
在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中,学者和思想家们似乎过于相信他们的“偏见”的“合理性”,忽视了伽达默尔的观点,即“现代科学遵循笛卡尔式的怀疑原则,凡是可以质疑的东西,都会存疑”。(61)他们往往忘记了,一个真正的诠释过程,其内在逻辑是“偏见”或“前理解”逐渐得到修正和改善,最终成为对文本的真实看法。而且,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总是从偏见或前理解开始。这种偏见或前理解,是建立在现有的西方知识基础上的。解读中国这部鸿篇巨著,往往不采用循环解释。没有了循环解释,即使那些思想家自认为是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他们的研究方法也算不上是真正科学。他们相信自己的方法论是正确有效的,当这种信心高涨至关键节点的时候,认识论问题就转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
在中国知识生产过程中,摆脱汉学主义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以诠释学方法处理知识。这种方法要求我们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中国知识。中国比一部巨著还要复杂得多。若要通读、理解中国这部巨著,诠释学理论——经典的或现代的——还是稍嫌不足。以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为例,他提出部分与整体的循环解释是可以全面实现的,因此,其观点暗含了一种完成意识。他还提出循环诠释有其“完成的前概念”,一种“所有理解的形式条件”,这进一步证明他的理论存在着一种完成意识。(62)但是中国这部大书永远不可能是一次完成构思或创作的,它随着历史发现和新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如今的中国已经被纳入了全球化进程,情形更是如此。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自觉地意识到超越汉学主义、反对汉学主义化的必要性。摆脱了汉学主义的影响,中国研究才能真正成为全球知识体系的一个学术分支,才能推动全球化朝着有益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参见顾明栋:《汉学与汉学主义》,《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的认识论意识形态》,《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
②Paul K.T.Rule,K'ung-tzu or Confucius?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Sydney:Allen and Unwin,1986,p.1.
③G.W.Leibniz,Writings on China,translated by Daniel J.Cook and Henry Rosemont,Chicago:Open Court,1994,p.46.
④伏尔泰的戏剧改编自13世纪中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
⑤Voltaire,An Essay on Universal History,The Manners and Spirit of Nations from the Reign of Charlemaign to the Age of Lewis XIV,4 vols.,Dublin,1759,Vol.1,p.9.
⑥Montesquieu,Geographica,in André Masson,ed.,Montesquieu,oeuvres completes,Paris,1955,II:927.
⑦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nne M.Cohler 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Book 3,On the Principles of Three Governments,pp.21 -30.
⑧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p.128.
⑨⑩(12)(13)(14)(15)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pp.126-127,127,124,71,82,116.
(11)Jonathan Spence,Chan's Great China:China in Western Minds,New York:Norton,1998,p.54.
(16)五权分立体系中有仿照美国政体设立的立法院、行政院和司法院,另外还有两个仿效传统中国政府设立的机构:负责选拔官员的考试院和检查政府廉洁效率的监察院。孙先生希望这种分权形式有助于捍卫人民的权利。
(17)Spence,Chan's Great Continent,New York:Norton,1998,p.92.
(18)(19)(20)(21)Montesquieu,The Spirit of the Laws,p.321,318-319.
(22)Johana Gottfried von Herder,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translated by T.Churchill,London,1800,p.298.
(23)(24)Herder,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p.297,294.
(25)(26)(27)(29)Herder,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p.296,293,294,297.
(28)Herder,Preface to 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p.vi.
(30)Karl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pp.95-96.
(31)Joseph Needham,Review of Karl A.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Science and Society,1958,Vol.23,No.1,pp.61-65.
(32)Karl Marx,On Coloni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72,pp.36-37.
(33)Marx,On Colonialism,p.37.
(34)Engels' Letter to Marx,June 6,1853,On Colonialism,p.314.
(35)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p.159.
(36)Spence,Chan's Great China,p.213.
(37)(38)Wittfogel,Preface to Oriental Despotism,p.iv,v.
(39)Bertrand Russell,The Basic Writings of Bertrand Russell,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7,p.554.
(40)参见杨庆堃为韦伯的《中国宗教:儒教和道教》所写的《引言》,C.K.Yang,Introduction to Weber's 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New York:Free Press,1951,p.xiii.
(41)Tu Wei-ming,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5.
(42)Max Weber,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translated by Ephraim Fishschoff,Boston:Beacon Press,1963,p.269.
(43)(44)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Edward A.Shils and Henry A.Finch,New York:Free Press,1949,pp.49 -112,88.
(45)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Penguin Books,2002.
(46)Jack Goody,The East in the We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24-48,77-81,90-91,259-60.
(47)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New York:Free Press,1968,p.177.
(48)Tu Wei-Ming,ed.,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L.Berger,The Capitalist Revolution:Fifiy Propositions about Prosperity,Equality and Liberty,New York:Basic Books,1986; Goody,The East in the West.
(49)See Peter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eds.,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1988,p.7.
(50)(51)Herder,Preface to The Outline of a Philosophy of the History of Man,p.7,9.
(52)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776[1977],p.24.
(53)(54)Oswald Spengler,Preface to the revised edition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New York:Knopf,1932,p.xiii.
(55)Spengler,Preface to the revised edition of The Decline of the West,p.xiv.
(56)(58)(59)Gadamer,Truth and Method,second edition,New York:Continuum,1999,p.277,270,277.
(57)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Tu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1972,pp.312ff.
(60)(61)(62)Gadamer,Truth and Method,second edition,p.293,271,293-294.
标签:认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魏特夫论文; 赫尔德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