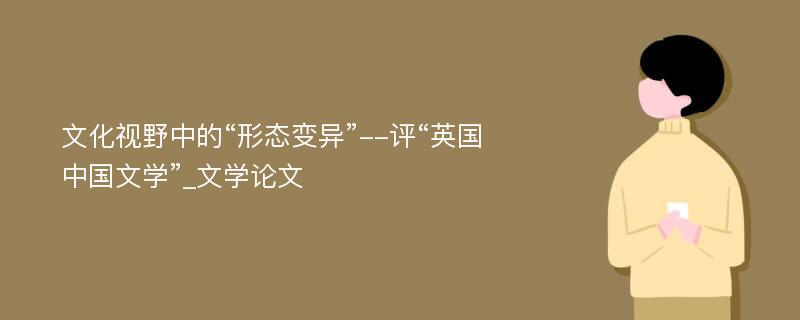
文化视野中的“形态变异”——评《中国文学在英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形态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在英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权威艾金伯勒在十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1985·巴黎)曾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发表了总结性的讲演,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寄以厚望。最近读到张弘先生的近著《中国文学在英国》一书(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切实感到了我国比较文学扎实而稳健的拓进步履。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已经不可能再囿于“欧洲中心论”,而无视中国文学施之于西方的久远影响了。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地位十分重要的中国文学瑰宝,数百年前便以其神奇的光彩辐射到了西方,所以,中国与西方的双向文学交流乃是世界文学研究中难以回避的课题。在这方面,作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组织编著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之一种,《中国文学在英国》(以下简称《在英国》)确实展示了颇为丰富的内容及研究方法的自觉更新。
《中国文学在英国》这样的选题,注定是属于影响研究的范畴的。选题的性质要求作者必须搜集、整理大量的有关英国文学界接受中国文学影响的资料,予以实证性的勾勒,方能使人们充实地览照这样一条独特的文学交流的长廊。在这方面,作者以相当艰苦的劳动,换来了令人欣慰的果实。“从1589年英国人乔治·普腾汉的《诗艺》介绍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算起,中国文学传入英国至今足有四百年之久。”(第1页)这四百年间的有关资料是相当繁富而散在的,而且大多数都是英文文献,这只有靠作者的广泛搜求与精细剔抉了,然后又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角度串成一串“珠玑”。本书作者在大量的文学接受史实中,深入分析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形态变异,作者并不满足于实证性的事实介绍,没有停留于一般的“外缘”研究,而是力求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以探讨文学的本质与特性。这当然比一般的史实搜求、整理有更大的难度,但对比较文学本身来说,确乎是一种可喜的进展。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是有着自觉的理论意识的。书中指出:“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田蒲教授说过:‘比较不是目的。’我们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进一步认为,比较之目的在于把握文学的特性。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一定是本体论的追求。关于文学的特性的说明,可以像通常那样是概念判断式的,也可以是现象描述式的。这种现象描述式的把握方法,不再急于解答‘文学是什么’的传统问题,相反首先关注‘文学是什么样的’。换句话说,关于文学的特性,完全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从文学的存在方式去把握。”(第351页)这种理论意识对于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是重要的前提,同时,作为方法论特征,也在全书的论述过程中得到了贯彻。作者在论述英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精品的译介时,多能在中西审美观念、价值体系的交融与碰撞中,探索其作品内在审美机制在传播过程中的种种错位,并从文学的文体特征等艺术视角加以细致剖析。如对霍克斯的楚辞研究(第128—131页),对于翟理思的唐诗介绍,对于布吕昂特的词学译介,等等,皆是显例。这当然也是得益于作者那种深湛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作者原来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国学功力颇为不错,后又出国进修比较文学,这样的知识结构,自然能使这类选题做得较为得心应手而又颇为深入。作者自觉追求通过比较文学途径,来把握文学特性的意识,在该书的成功中,还是起了统率作用的。
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在全书的体系建构中,作者力图用形态学方法以补充影响研究中传统的历史方法之不足。为此,作者在书中专辟了《余论:影响研究的形态学方法》一章申明这种理论观念。作者对于比较文学中法国学派代表人物基亚的历史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这是一种历史学的发生学的观点,注意研究的是传播与接受的发生过程,……这种历史学的不足之处,是专注于历史过程而忽略了形态研究,最大的谬误莫过于认为文学的传播等于从一国到另一国的简单搬迁。”(第353页)为了补此不足,作者力倡形态学方法,也就是注重比较传播过程里文学形态的相同与不同之处。”(第354页)作者从比较文学大师们如梵·第根、巴登斯贝格、伽列等人的理论著述中理出了形态学的思路,并加以明确倡导,作为影响研究中与历史方法相对的新的方法命题提出,这对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的独特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作者还未能来得及具体细致地就比较文学中的形态学方法进行明确界定与阐述,但是作为一个方法命题的倡导,且有此书的实绩作为基础,对于使影响研究这种传统研究范围的拓进、使比较文学从内部焕发新的生命力,恐怕是功不可没的。
然而,这部书并没有对“历史方法”弃而不顾,而是使之与形态学方法得以有机结合。前两章《朦胧中的光和影》、《从地平线走来》,就以历时性的思路描述了从十七世纪开始,英国人开始接受中国文学的历程,这两部分用大量的资料来把握了动态的发展,使读者感受到了这种进程的轨迹。接下来第三章《诗之华——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第四章《诗之魂——中国古代诗人在英国》、第五章《东方的罗曼史——英国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译介》、第六章《在多重的帷幕后——英国对中国戏剧文学的译介》等四章,是分别就诗歌、小说、戏剧这几大类体裁的精品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而作的评述。依我的理解,形态学方法最为集中体现在上述几章之中。以文体分类进行论述,可以就文体的审美特征(外在的及内在的)进行具体的、内行的分析,更能以具体的方式描述出文学的特性——当然不是那种“文学是什么”式的抽象本体论命题,而是具体的文类所表现出的美学特征。这比“眉毛胡子一把抓”地将各种文体搅在一起谈,不仅线索更为清晰,而且更能把握文学的特质。各类文体合而言之为“文学”,有其共有的文学共性,但这种文学共性已是高度抽象化的了;各种体裁之间都有各自独特的形式的、内在的审美特征,这是较为具体的。作者大概是从把握各类体裁的独特的美学规律的角度来使用“形态学方法”这个命题的吧?就本书的现有样态来看,作者颇为娴熟地以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小说、戏剧等几类文体美学特征的理解与把握,来分析英国学者译介中国文学成果的得失的。
作者通过大量的具体论述,强调了“形态变异”的观念。作者有意识地汲纳了接受美学的合理因素,并且内化到研究过程之中。他试图站在英国人的立脚点上、借英国人的目光来返观中国文学;又由于自己以中国学者的文化积淀与视角,便处处审视出英国人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选择倾向。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审美意识,……造就了英国人迥异于中国人的“接受屏幕”,因此,他们在译介中国文学时,便形成了与中国人的欣赏与评价之间的某种反差与错位。作者在全书写作中,是着意揭示这种“变异”关系的。譬如对于赋(作者将赋放在诗一起论述),中国人大多不太感兴趣,除专门研究者外,很少有人读赋。但在英国,赋的研究与译介却甚受重视,而且研究方法也与中国学界习惯不同。作者重点介绍了克内契格斯的赋学研究成果,并指出“克内契格斯对汉赋形成的研究,很大成分上源于西方的修辞学传统。”(第134页)作者归结到“中国文学批评一向重质轻文,作品的内容据首要地位,文学语言是附属的形式。赋恰恰讲究文学修辞,在夸张的形式下表达一点不多的意思,何况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形式这文学又都是死去的。西方的文学批评则恰好相反,相当重视文本的本身,以致于‘质’反而被放在次要地位。特别二十世纪以后,语言文字相对独立的机制成了文学批评乃至哲学研究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汉学家把注意力转向文学形式发达的赋,是不难理解的。无须奇怪,这里又一次见出中西文化的差异。”(第140页)这正是作者对“形态变异”方法的进一步说明。再如,介绍戴维斯的陶渊明研究,指出其把陶渊明的诗歌理解为对存在意义的探寻,“与其说是对他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不如说是从西方现代观念出发的重新塑造。”(第167页)对于英国的《红楼梦》、《镜花缘》的翻译研究,对中国戏剧的译介,也都从“形态变异”的角度出发指出传播过程中的某种选择与错位。
说到底,这种“形态变异”是根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乃至于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民族人们审美观念、价值选择上的差异,何况又是中国与英国这样遥居地球东西两端的呢?但“差异”是与“共同性”相对而言的,没有共同性也就谈不上“差异”。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之所以可以彼此渗透交融,可以比较,正是因为人类的发展走着大致相同的历程,各民族的心理体验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且,古往今来,民族间的交往融通,无论是鲜花鼓乐式的或血火刀剑式的,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文学,又从来都是文化的精灵,因此,要真正地比较不同民族的文学之异同,就不能不对其民族文化的特质与发展,有较为深刻中肯的了解。《中国文学在英国》一书的特色之一,还在于作者对于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对于英国的文化传统,都做了相当丰富的描述。并且,这些又都是与英国人接受中国文学过程的直接文化渊源的揭示联系起来的。如第二章中对于英国传教士与外交官所起的文化媒介作用的详细介绍与辩证分析,便使对于文学传播的论述显得根基深厚,令人信服。
作为一部比较文学专著,在很多方面也还有待于完善。我以为关于“形态学方法”问题,目前书中的分析与建构还是较为粗糙,有待于进一步精密化,这样,可以使比较文学的理论建设大大提高一步。形态学包含了各种文体的分野,但远不止于此。而且目前的艺术形态学的理论建树,可以作为比较文学的方法借鉴,使之更为科学化、细致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