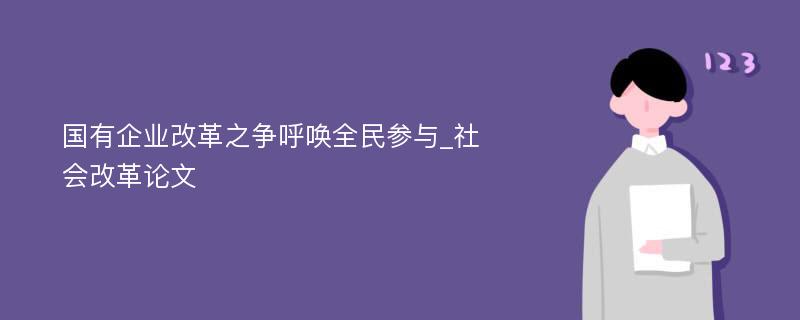
国企改革争论呼唤民众参与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民众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郎咸平来了,他对国企改革的言论一出,民众几乎一呼百应。一些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的回应不仅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同,反而激起社会的反感,这到底是郎咸平和他的支持者们及民众太过情绪化,还是国企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确存在偏差?如果改革出了问题,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这场讨论能不能将改革导向更加良性的公正的方向?这场争论进一步显示,如今社会对重大公共问题的参与欲望,参与势头非常强烈,政治体制如何适应民意和改革形势?在中国改革杂志社近日召开的国企改革的小型座谈会上,孙立平、杨鹏和钟伟等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不要曲解郎咸平的主张
钟伟: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郎咸平的话包含以下意思:
现在的国有企业MBO是有问题的。在国外,经理层收购企业的时候必须向员工进行动员,承诺将怎么安置员工,以后企业发展战略是什么,等等。而现在中国的 MBO整体不过是精英的合谋,过分不顾及员工的利益,员工被完全排斥在参与改制之外。郎咸平的话是对的,他表达的情绪完全是有民意基础的。这个问题在南斯拉夫处理得很好,就是员工持股,将企业优先卖或分给员工,而不是将企业优先卖给企业高管层。因为企业搞垮了,责任在高管层。
他说停止国有企业改革,并非是说国有企业不要改革,而恰恰是说国有企业观在不要这么卖了。这也适应民意基础,我也是赞同的。按现在国有企业的改法改下去,会是什么结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参与程度不够,尤其是底层参与程度不够。
他讲的大政府强调法治,个人责任制。看美国的情况,作为联邦政府、大国治理结构,在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无处不在,建立了两大体系:一是以乡镇自治为基本的联邦司法体系,是可靠的有效的;二是无处不在的税收体系。政府一方面在司法方面从严立法,在税收方面绝不留情,美国大政府大的有道理。他认为,那就是法治。中国要走的,不是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无为而治。大政府也不是回归计划,恰恰是两点:法治和税收。而中国恰恰欠缺法治和税收。政府没有充足的税源,只能零敲碎打;法制不够,黑社会来补充。郎咸平主张的大政府和其他学者主张的小政府,到底哪个可行?
在法律缺位和民众参与缺位的前提下,国有企业可以暂时不搞产权改革,搞信托责任。就是承包制,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也有道理,如果国有企业经营者比如四大银行的行长真的实行聘用制,就没有这么多问题了。
产权改革不是万能的,民营企业是私有的,也有管理差的;国有企业即使不动产权,也可以改革的相对比较好。
不要把国企改革的公平问题复杂化神秘化
孙立平:国有企业改革搞成现在的情形,是不是真的法律缺位,法制建设落后到这个程度?不一定。比如关于财产权,宪法和民法都有最基本的规定,从制度的法律化到社会的共识,都有基本的东西。能不能因为某些人使用国有资产更有效率就将它抢了分了?既有的规则是明确的。
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建设,说难是难,说它容易其实就是个技术操作的问题,不应该不健全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举个例子,经济适用房问题,有人开奔驰买大房子,社会反映了一二年之后,才开始制定规则,到现在有法规了,其实就是限制户型。这办法老百姓都想得出来,政府却用了五六年才想出来,说得过去吗?整个中国的法制要健全,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很多规则包括国有企业体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则的制定并不是那么艰难繁重的事,是政府想不想做的问题。再简单的事也不干或也不及时干,这是不作为,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承担责任。
真正的法制建设,来自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来自于各种群体利益的相对的均衡。我们真正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基本形成框架了,开始成为主导的、支配性的机制了,但必须和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权利却相当缺失。这些权利包括游行、示威、罢工,组织农会等。从西方的市场经济看得出来,没有这些权利配套,是非常混乱的坏的市场经济;有这套权利,穷人变不成富人,弱势群体变不成强势群体,但不至于太不像话。没有这些基本的权利,社会的一股力量非常霸道,社会力量严重失衡,法制建设无从谈起。所以,中国社会的问题关键是权利的问题。
人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问题。精英可能更关注改革的问题,民众更关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搅在一块,越来越混乱。必须明白,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反对国有资产的流失,不一定反对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方向;相反,坚持国企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意味着一定要容忍国有资产的流失。
把事情技术化,不要一直在玄而又玄的层面上讨论问题。不要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公平问题神秘化。知识分子就老犯这毛病。比如“三农”问题,知识分子讨论的结果是“三农”问题没解,但是从技术上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农民种粮食,一亩地补几块钱,就比原来强点;费改税,把费合到税里去,费少点,农民就又好点;把农业税取消了,国家把农村的教育承担起来了,农村的公路政府来修,农民又好点。什么叫公平?这就是现实中的公平。
国企改革同样如此。必须坚持最基本的几条:如果是送,别白送,卖点钱;如果是卖,别贱卖,卖得价钱合理点;一些人无偿得到这么一大块资产,另外一些人却失业下岗生存困难,这样的反差突现出来。国资委得制定规矩,卖国企的资金,得规定一个比例划转到社保基金里去,以便改善失业下岗职工的补偿问题。现在卖国资的收入用于社保的比例是很少的。
国企改革,程序至关重要
钟伟:现在最糟糕的事情之一是缺乏程序正义。公众利益的保障没有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程序。我举个例子来佐证。
一个基金公司到监管部门申请批准,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最后就差发文公布,但是监管部门的一个领导对这家基金公司略有不满,就迟迟不发文,每次基金公司打电话,都说还没打好公告,竟然一页公告拖公司半年,公司为此赔了2000多万。就算前面的评审程序都是完整的,打字员没有在两小时之内打完公告并张贴出来,就没有程序正义。
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如此。国有企业改革有哪些方式,这些方式将会怎么被履行、职工如何参与、如何监督、如何获得补偿等等,把每一个细节、环节都详细列举出来,就不会导致太多的不正义不合理。
让理智而非情绪左右社会的变革
杨鹏:目前争论的几类观点分歧很大,但最后都把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归结到政府,要么批评政府,要么支持政府,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要解决政府问题。从人类历史考察,当社会各个专业领域碰到的问题在本专业都解决不了,都要回归到政治、政府的时候,政治改革就不能不进行了。
左有左的情绪、右有右的情绪,他们看似理性的话语背后搀杂着情绪。以前社会参与低的时候,理性里不附含激情,情绪不容易激化;现在参与开始了,面对面的博弈出现了,显然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情绪激化期,郎咸平无非是在这个情绪开始暴发点上捅个洞。我并不觉得情绪化不好,这是一个正常的历史演化过程。但用理性引导情绪难,在人类历史上,经常是情绪左右着社会的变化。
现在多元社会形成,各个集团的意识开始出现,精英内在分裂。从这次宏观调控引发的争论看,有区域的立场、阶层的立场,区域分化了、阶层分化了。正如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社会已经区域化,政治势必分化。认为精英团体是一体的,其假设前提不存在。所以,控制谁、怎么控制,在集团内部的立场取向就会有差别。当然,一旦碰到重大问题,最后还是会逼出原则和办法的。在这个逼的过程中,社会充满着风险。
钟伟:我对社会局势的发展不乐观。情绪有时会战胜理性的。社会贫富悬殊,如果底层的情绪上来,就是黑夜政治,白天我低头,你给我开工资,到晚上砸你家玻璃等等,白天晚上是两个人,白天是顺民晚上是暴民。暴力出现是对社会正当性的最糟糕的评价,觉得社会没有道义了,所以诉诸暴力。
农村也是这样。我特别强调宅基地、农村集体用地、承包责任田发放不同的产权证。集体用地是集体的产权证,产权证上写上所有社区成员的名字。
现在一些精英和一些地方官员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政权意识,在重大问题上只有目标而没有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员行使权力的弹性是非常大的,从极左手段到极右的无政府主义,各种可能性都有,这才是充满风险的。
民众参与最关键
杨鹏:显然,中国很多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归到宪政层面,问题是谁来推动?举个教育的例子。
我把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权。中国刚解放时私立教育接近一半,解放后很快国有化,权力被收到政府。第二阶段是养权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学校并不被一视同仁的对待,其中2%~3%的学校建成重点学校,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来养这些重点学校,以致出现争夺重点学校、择校的现象,名校出现爆炸性的收益,教育因其特权泛滥而变成了暴利产业。
如今进入了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出了两个政策,一个政策是高等名牌学校办独立学院。高学费入学,录取分数降低,但发和主办学校一样的文凭。规定独立学院必须民办,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官员和校领导的关系户实际成为股东,利用名校的教育师资举办,但实行两套财务。另一个政策是重点中小学办民校。对那些比较差的中小学,一些地方政府则积极推动所谓民有化。现在名校办民校的学生已经占了一半左右,有接近一亿左右的孩子交了高学费上学。这两个政策的实质,是利用垄断权力瓜分名校的资源,以改革的名义,将教育乱收费合法化了。
其实,郎咸平们并不是简单地冲着有钱人,而是冲着因为有权而有钱的群体去的,整个社会的矛盾激化点直接对着权贵资本。权贵资本成了社会怨恨和冲突的焦点。没有几个人是反市场经济的,反的是不公平的坏的市场经济。
权力不受约束,权利和权力不对称,会是什么法治?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制定是征求了民校经营者的意见的,但后来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却写进了高等名校办独立学院,加上民办学校不能发学历文凭了,这一下使80%的民办教育崩溃了,剩下的20%也是勉强支撑,这涉及到将近300万孩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搞宪政,怎么搞?
宪政就是限制官员的权力,但是没有外力的强力推动,有哪股力量愿意限制自己的权力?
钟伟:一言蔽之,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民众参与,分享改革的成果。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也是民众的一部分,他们也享有跟民众同等参与的权力。
怎么参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很危险。美国为什么会有民主制度,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认为有三点基础:一是美国有非常富裕的自然资源;二是美国有非常良好的法治基础、契约基础;三是美国的民情是基于宗教信仰的乡镇自治的传统的。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中国搞自下而上的民主,到最后可能是极左政治。圆桌是不能开的,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对此要有共识,一定要承认,现在要特别关注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要谈的是民主政治,尤其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至少要有让民众表达自己意见和利益的畅通的渠道。惟此,改革才有共识。
孙立平:历史上,改革就是贵族让权的过程。我对宪政还有些信心。宪政的可能性来自很多方面,比如矛盾和冲突的逼迫是一个很现实的动力。最近宁夏银川出租车司机罢工问题的解决,政府违法的抓,同时政府也道歉,实际是正视了罢工的现实存在。这可能是逼出来的结果,是宪政的一个可能性。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承认分化的利益的合法性;利益表达要合法法,要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