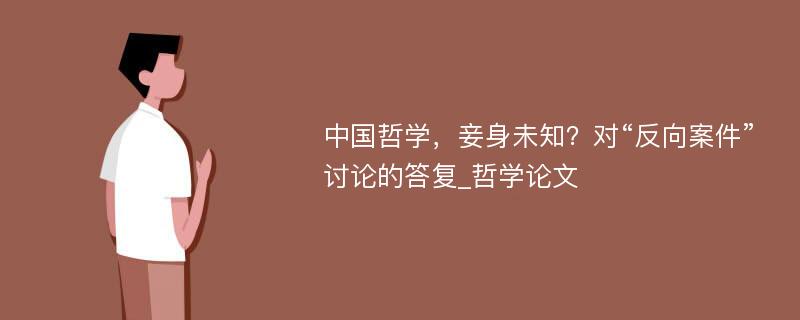
中国哲学,妾身未明?——关于“反向格义”之讨论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未明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以下简称“拙文”)引起一些讨论①,《南京大学学报》要我对讨论文章作一些回应。我感谢他们推动学术讨论的热忱,愿意借此机会回答一些问题,并引出相关讨论涉及的更根本的问题。
拙文有两个主题。一是根据古代和近代的思想史发展的事实提出“反向格义”的概念,二是通过两个典型实例说明反向格义会遇到的困难,即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术语所难以避免的枘凿不合的现象。文章是对事实的回顾和分析,只是希望引起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并未涉及中西哲学之关系问题的全面讨论,但是一些朋友很快将问题联系到“要不要”学习西方哲学、借鉴西方哲学的问题。这似乎是很自然产生的问题,但笔者却未免感到有些遗憾。一百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要不要”、“该不该”的题目上徒费口舌,而不能自觉地深入到“学什么”、“如何学”、“目的何在”、“标准何在”等具体问题上。这里似乎是一个怪圈:围绕着“要不要”、“该不该”的讨论往返辩难,无法深入一层;因为不能深入一层触及新问题,就只能不断地重复“要不要”、“该不该”这样浅层次的不可能有新成果的老问题。
也有人将拙文提出的问题与前几年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相提并论②。那一次讨论中发表了很多有深度的关于中国哲学之历史、性质、特点以及方法的文章,可谓硕果累累。笔者也获益匪浅。但是严格说来,所谓“合法性”的提法却是一个不当的问题或“假问题”。从理论上说,所谓合法不合法的说法毫无来由,根本没有一个“法”,何来“合法”不“合法”之判断?如果所谓“合法性”是legitimacy一字的翻译,那么译为“正当性”可能稍好一些。从事实上说,中国哲学在目前海内外的学科体系中已经确立。在中国大陆,中国哲学已经是法定的二级学科,在香港与台湾,哲学系、中文系、宗教系、历史系都有人在研究和讲授中国哲学或相关科目。在欧美,越来越多的大学开设了中国哲学或相关课程,以“中国哲学”命名的英文刊物、百科全书、教材、手册已经很多,有些还正在编写,即将出版;以“哲学”、“比较哲学”或“世界哲学”命名的书籍、刊物很多都包括中国哲学,有的还包括非洲哲学和阿拉伯哲学等。无论说中国哲学合法或不合法,正当或不正当,都不会改变这些既有的事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显然,真正重要的是在“中国哲学”的名义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做。
不够准确的问题却可能比精确的学术课题引出更广泛的关注。“合法性”的说法反映了中国哲学在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某种尴尬地位,涉及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和名称出现的历史及动因,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以及这一学科的性质、身份、方法、目的及标准等实质性问题。这正是“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真问题,大问题。景海峰说:“(合法性)更多的是一种借用。这一意涵曲折、甚至可能引起某种误会的表达不一定很恰当,但它附带的挑战性意味和刺激性感觉却也能很好地传达出议论者们内心的困顿之情状和其焦虑的强度。”③ 其说较为全面。笔者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基本建设工作。关于合法性的讨论和反向格义的讨论中出现的各种不同的、相反的意见就说明对“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性质、身份、目的、标准还缺乏最基本的专业共识和自我意识。一个学科对于自己的性质、目的、方法等问题都缺少基本共识如何可能建成一个严格的专业性学科呢?④ 名人名作的不断出现使我们忽视了这些基本问题,将自己习惯的做法当作中国哲学理所当然的方法和规范使我们忘记了这些问题,这就造成了“中国哲学”成为一个几乎说不出共同标准和基本方法的没有“门槛”的“现代学科”,于是任何无知之徒都可以在“不同理解”或“另一种诠释”的名目下对中国哲学典籍随意乱说。⑤ 长此以往,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还有多少专业性和严肃性可谈呢?
这里要回应的对于拙文的公开讨论都是对笔者观点或论证有所补充、扩展和批评的意见(完全赞成的意见自然不必回应)。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讨论文章按照对“反向格义”这种现象和做法的态度(而不是按照对拙文的态度)分为两类。第一类对“反向格义”的现象和方法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并对笔者的观点有进一步的发展或批评,以张汝伦、张祥龙和郭晓东为代表。第二类观点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反向格义”的做法,可以以龚隽、李晨阳、方旭东和彭国翔为代表(为行文简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略去先生、教授等尊称)。读者不容易搜集和阅读这些讨论文章,所以笔者会先扼要介绍上述讨论文章的主要观点,然后再作回应。本文第一、第二两节分别讨论上述第一和第二两类观点。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观点中分别以郭晓东和彭国翔的观点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代表,本文第三节即以此二人的观点相对照,借以引出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性质和身份问题的分歧。第四节则专门讨论中国哲学最主要的两种身份的不同。
一、“反向格义,可不慎乎?”
在所有的讨论文章中,张汝伦的文章最长、内容也最深思熟虑。张文提出,近代中国哲学的建立,是按照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基本认识,“顺理成章”地用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中国思想。一般哲学史和对古代思想的研究都会按照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等等这样的西方哲学特有的分类进行论述,并用这种分类框架来套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这“是一种比一般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种反向格义的基础上,一般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才得以发生作用或产生影响。”⑥ 他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研究中一切反向格义乃至“汉话胡说”的根本原因,若不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将本体论问题作为哲学的首要问题,人们也许就不太会将精神与物质、唯物与唯心等概念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中。按照西方哲学门类来划分甚至切割中国古代思想曾经是很普遍的做法。这属于拙文所没有讨论的广义的反向格义。张文提出这种做法是狭义的反向格义的理论根源,这是一种病理诊断,笔者并无疑义。
不过,笔者有一些观察和思考。第一,张岱年师年轻时曾经有意避免套用西方哲学的门类概念。他的《中国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是“宇宙论”,下面则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第二部分是“人生论”,下设“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以及“人生问题论”。第三部分是“致知论”,下设“知论”和“方法论”。其中多数章节不是套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概念,而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资料中作出的归纳。这是张先生有意避免套用西方哲学门类划分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他晚年说这是年轻时的幼稚之举,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由此值得思考的是他的努力为什么会失败,他为什么会放弃这种努力,我们今天是否应该重新继续他早年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否可能成功?要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呢?笔者提出这些问题供有心人思考,或许可以减少后来人的一点曲折。第二,套用西方哲学分类概念的确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作为“顺理成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做法并非一无是处,这种做法下产生的作品并非全无价值。问题在于现在和今后如何做。我们是否有可能或应该放弃这种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分类框架?如果不放弃是否有可能纠正对这些概念的误解之后再使用这些概念?笔者也注意到,张本人参与组织编写的教材已经避免了西方哲学分类的标题⑦。笔者欣赏这样的尝试和探索,但笔者认为我们可能还是应该探索使用一些既符合中国哲学特点和实际,又更具有概括性的现代分类概念,比如功夫论、致知论等,以便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张汝伦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哲学研究有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好谈本体论。”但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对本体论以及相关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等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是格义式的误读。而所谓反向格义所用的是经过误读的西方哲学概念。张文的主要篇幅是对这些基本概念之意义的考察和分析,同时重点分析了熊十力和牟宗三思想体系中的不当之处。他的主要观点是熊、牟二人分别误读了西方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等概念,又用这种误读的西方概念来重新诠释和构建中国古代哲学。他说:“现代中国谈形而上学的人,大都不但对西方metaphysics的深刻内容不求甚解,对它自身的批判发展更是一无所知。……以自己未必靠得住甚至想当然格义过的西方哲学概念去反向格义中国哲学,不仅无法使西方哲学思想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的‘他山之石’,反而使我们在对中国本土哲学的理解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两个方面都受到损害,更不用说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哲学了。”
张文还批评牟宗三混淆了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等不同概念:“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在一般中国传统哲学中,还是特别在明道和朱子那里,宇宙论是一个中心问题吗?如果不是,牟宗三为什么要以宇宙论观点来解释明道和朱子,以及他们哲学的差异呢?一个立刻就可有的答案是:他先把本体论理解(格义)为宇宙论,或将两者混为一谈,再用来反向格义中国哲学。……这与他们将形而上学、本体论和宇宙论混为一谈有关。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牟宗三。在他那里,‘道德的形上学’就是‘本体界的存有论’或‘无执的存有论’,就是本体宇宙论。”
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呢?张文强调:“只要用了这两个出自西方哲学的术语,就说明使用者承认中西本体论或者形而上学之间至少存在着‘家族相似’,否则根本不必用这两个外来的术语。既然是‘家族相似’,这个‘似’在何处或如何为‘似’就大有讲究。实际上,只要用了西方哲学的术语,就不可避免以西方哲学思想作为‘似’的标准,尽管只是经过我们格义了的西方思想。用我们格义过的西方术语来反向格义中国哲学,其结果必然是中西皆失,而不是中西会通。”张文最后的结语是“反向格义,可不慎乎?”此为警戒之语,似乎并没有完全否认借用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可能性。
张文给笔者的最大印象是,他再次提醒我们中西兼通之困难,而自以为中西兼通是多么危险,以中西兼通的口吻做文章很可能是大胆误用。值得思考的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是否有可能对西方哲学的掌握达到高度准确的水平?通一经一家已经不易,能通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一方已是值得庆幸的成就,要兼通中西何尝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几人能准确地理解西方哲学同时又能将西方哲学概念恰当地用于中国思想呢?面对这种困难,我们该有何思考呢?
第一,应该提倡严谨的治学态度,尽可能避免误解误用西方哲学的术语,避免将误读当作创造。在个别情况下,误读的确可以产生意外的新成果,但误读毕竟不能作为创造之正途。
第二,每人的学术志向、目标不同,知识结构不同,某些人要做中西会通的工作是应该得到鼓励的。但是,首先应该通一家一方,再去通另一方另一家。在作比较或借用西方哲学概念和理论时,最好能得到相关专家的帮助和把关。
第三,笔者曾经提出,牟宗三不是一般的诠释者,而是思想的建构者⑧。如果不将牟宗三的著作看作是对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的比较客观的诠释,而是将它们看作20世纪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创构作品,那么他对西方哲学概念的误解、误用可能就不算那么严重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创造新思想,必须对中国和西方的概念加以改造。这就涉及笔者近年来所讲的两种定向、两种标准的问题⑨。如果从体系创构的角度来评价牟宗三,那么讨论和评价的重点可能就不是对概念是否有误解或误用,而是其新体系是否严谨,是否能够自圆其说,是否有理论意义或实践意义⑩。当然,这绝不是提倡对西方哲学概念的误用和轻率的学风。
第四,根据两种定向的理论,笔者认为,如果为了创造新思想而对中国或西方理论和概念进行改造,那么这种努力应该是自觉的、明言的,而不是误会的、不自知的、或有意加以掩盖的。郭象的时代可以通过误读《庄子》而创造一种新的逍遥游理论(11),今人也靠误读来创造就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了。这是现代学者和古代文人的不同,现代学者应有自觉的领悟。
与张汝伦观点部分相似的是张祥龙,他从不同角度将问题向前推了一大步,涉及了最基本的方法问题和所谓“概念”问题。他认为“反向格义”的根源在于“对概念化哲学方法的价值的过高估计”,而现在研究中国哲学都重视所谓“概念”、“范畴”的分析,这本身对中国哲学就是不恰当的,故建议借用现象学等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他问道:将“中国哲学思想”称为“概念系统”是否合适?这么称呼是否有方法论的后果?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意味着一般的普遍的观念(a general or universal notion or idea),与特殊事物是对立的。而且,一般认为概念有自己的内涵与外延,也就是有某种静态的意义独立性和客观性。……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中,也有站在概念哲学立场但又想提高中国古代思想的哲学地位的,就大讲‘中国哲学的范畴’。但这么‘反向格义’的后果并没有提高中国古代思想在严格的概念哲学家中的地位,反倒是如刘笑敢所意识到的,产生了各种弊端。……所以,我的愚见是:现代反向格义的方法论的来源是对概念化哲学方法的价值的过高估计,认为这才是搞哲学的正宗或原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一定要以它为基准,不然就是搞的思想史或其他的什么史了。其实,……概念化的方法只是一种搞哲学的方法,而且在我看来还是比较过时了的、弊端很多的方法。西方人可以坚持它(现在英美大学中流行的还是以概念哲学为主),但一旦搞中国古代的哲理思想,这个问题就很突出。”(12)
张祥龙一方面对概念分析的方法提出怀疑,一方面提倡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他曾发表文章,认为现象学是西方哲学中少量的能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有孕育力的对话”的流派。而传统的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则是“以征服者的姿态,以它现成的方法和系统化门类来宰制和切割‘中学’这块‘蛮荒之地’,告诉到那时为止还只会读‘诗云子曰’、佛禅老庄的人们:什么是哲学,什么东西属于‘中国哲学’。”(13) 祥龙的建议很有意义。借用新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哲学总是值得鼓励和尝试的。但是,因为大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都能成功尝试现象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我们还不可能马上放弃概念分析的方法。从严格意义来说,中国哲学的术语系统的确不同于西方的概念系统,特别是不同于康德、黑格尔之类的自成严密系统的概念体系。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来说,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类似的术语或概念系统,比如天人、知行、义利、理气、有无、道器等等,都是哲学思考的理论结晶,是构成思想文化网络上的纽结。这些虽不是西方近代哲学式的概念,往往缺乏明确定义、内涵或外延,但与西方的概念仍有可比性,至少功能类似,都是表达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虽然抽象程度不同。笔者以为,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概念”一词是泛化后的用法。概念的泛化是始终存在的、无可避免的现象。比如religion(宗教)一词,本来专指基督教,后来泛指一神教,此概念逐步“泛化”,包括了佛教、印度教、道教等。如果严守religion本义是基督教,亚洲本土没有这种宗教,那么就要说亚洲没有“宗教”了。显然,现在没有人再坚持这种狭义的“宗教”概念。大家所说的都是泛化了的“宗教”概念,并随之有了各种新的宗教定义。
笔者也知道,即使以“泛化”以后的概念为标准,中国哲学中的术语也不一定都可以称之为“概念”,比如“为天下先”、“恶乎待”、“逍遥”、“齐物”恐怕连“泛化”的概念都称不上,所以笔者尝试提出构成哲学概念的四个标准,即名词化,有固定形式,用于普遍性论述,以及用作判断的主词或宾词(14)。我曾就此事问张岱年先生,他认为哲学概念当然是名词,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的同行对这个问题还缺少基本的自觉和共识。无论如何,张祥龙提出的是一个真问题,值得重视。
二、“‘反向格义’不应该成为一种‘法病’”
上节讨论的观点是在基本否定“反向格义”之做法的前提下提出的进一步思考。这一节专门介绍和回应另外一种观点。这些观点都对“反向格义”的做法有所同情,或并不完全否定之。龚隽提出“我们哲学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内在于传统文本和问题开展的。中国传统文本中那些不能纳入到西方哲学结构中来进行论述的问题和材料,则很轻易地作为非本质性的哲学命题打发掉了。……那些可以翻译成西方哲学问题的问题,才构成所谓‘中国哲学史’的问题。这当然是现代性处境中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反向格义’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书写中不可逃遁的‘共业’。以西方哲学来进行比照的‘反向格义’,都不免流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在讨论中国思想史写作所讲到那种‘解释上过度决定’,但作为一种解释性学问的哲学研究,运用外来观念于传统文本的解释时,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冒险。它需要对话式的表现和不同场景之间的联想、调解和转化,‘比附’似乎必然成为某种摆脱不了的‘超余意义’。我们只能从解释的‘恰当性’,而不是本质主义意味上的‘客观性’和‘原本意义’来理解和评判这种‘格义’的合法性。……即是说,‘反向格义’不应该成为一种‘法病’,而只有‘格义’恰切与否或程度好坏的差别而已。这样做的难度当然很大,要求学人对中西方哲学都有较深刻的养成,对自己传统思想的写作也要有相当的书写经验与策略才行。”我个人比较理解也比较赞成这种意见,从历史事实来说我们不必也不应该完全拒绝借用西方的思想概念来关照和解释中国哲学传统,但应该对这种“冒险”有一种警觉意识,看到其难度的同时追求一种“恰切性”。
李晨阳也主张不能彻底否定“反向格义”的现象,但是由于长期在美国任教,他的视角以及提出的问题就比较独特,值得在此讨论。李晨阳认为拙文并没有完全否定借用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而是提倡谨慎的态度和做法。这比较接近笔者的立场。他指出目前的格义在中西之间是双向的,而不仅是单向的,比如“Tao(道)”和“yin-yang(阴、阳)”等字也已经进入英文。这当然是事实,也是未来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不过,就目前来说,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专门讨论一下李晨阳提出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15)
第一个问题是反向格义有无成功的实例?这要看成功的定义以及具体情况。如果以作品比较流行,受到某些赞扬为标准,那么似乎成功的例子不少。但是如果以理论上比较严格、恰切,那就需要就具体实例来分析。从广义的反向格义来说,有些成熟、谨慎而老练的作者可能会做得比较圆熟和成功。不过,即使很多人公认成功的实例,从另外的角度或另外的人来看就未必算成功,比如很多人认为牟宗三是成功的典型,而张汝伦就有比较严格的批评。就狭义的反向格义来说,即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直接定义和解释中国思想中的术语,要恰切是很难的。作者一定要意识到中西两方哲学术语产生背景不同,在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同时可能还有不少不同之处,要把相同与不同作全面的比较,才可能比较准确。不过,一旦这样做,可能就超出了狭义的反向格义的范围。用“自律道德”来解释儒家伦理似乎是不少人都认可的,但是否算成功呢?一般说来,儒家讲为仁由己,与道德自主是相似的。但严格地说,西方的“自律道德”是理性自觉的结果,而孟子的恻隐之心是生来就有的本能,要将康德与孟子的思想作深入比较,二者之不同会更明显,要作狭义的格义,说孟子哲学就是“自律道德”,那必定会牵涉背后的不合之处。如果要准确,必须多加解释和说明。那就又超出了狭义的反向格义的做法。显然,成功与不成功也有一个标准宽严的问题。按照张祥龙的标准,如果中国连西方式的“概念”都没有,哪里还会发现可以用来对中国思想术语直接进行格义的现成的西方概念呢?
李晨阳的第二个问题是笔者对反向格义的反思是否适用于西方的作者。如果我们将格义理解为用已有的熟悉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外来的不熟悉的思想概念,那么西方人用西方概念来解说中国的术语就是一种“格义”,而不是“反向格义”。但是,两种思想文化发展历史背景和特点的不同,造成双方的概念术语很难一一对应,这样“格义”也仍然是困难的。但文化交流又必然要求某种程度的格义,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做,而不是能不能做。李晨阳认为问题在于“哪一种外来的概念适用于中国哲学,而引入这些概念时,步伐应该有多快。”他在给笔者的电邮中进一步解释说:“作为我们今天做中国哲学的人,完全不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和概念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怎么用,用多少。我个人认为,我们至少应该考虑到两个方面。第一,会不会对挖掘、深化和发展哲学思想有利。第二,是不是容易被人们接受。在这两个方面,时间和循序渐进都至关重要。过快就会跟已有的哲学脱节,就会失去读者和同道者。无异于‘拔苗助长’。举步不前,就会落伍于时代,无异于‘守株待兔’。在这两者之间,人们有关过多过少,过快过慢的讨论,则常常是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找到相对适宜的区间。”(16) 就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来说,笔者完全赞成这种观点。但是,就对象性的学术研究来说,虽然也可以借用西方哲学作参照,但问题的重点就不在于是否循序渐进,而是在于研究者的理解和诠释是否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根据。这涉及下面所要谈到的中国哲学的身份问题以及不同研究导向的问题。
方旭东对笔者的评论是就笔者近年所发表的有关中国哲学之研究方法问题的很多文章的“批判性思考”(17)。笔者对他肯花时间读这些长文并发表认真的评论非常感谢。我认真考虑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对我的一些文字有所补充和说明,这些思考的结果已经写入了笔者的新书(18)。他对笔者关于反向格义的说法先做质疑和推论,然后再自问自答,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相信,作者本意不是要走这种极端。推其本意,似乎只是要提醒我们在习以为常、漫不经心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体系来研究中国哲学时(特别是用西方对立二分的哲学概念对应和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术语时),要先想一想能否这样用,要先有一个严格的自我审查程序,这样,我们就能大大避免狭义的反向格义所遇到的困境。……顺着作者的思路,可以设想,他会提出以下说法:固然我们的思维与言说方式已不可避免西方的影响与痕迹,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在具体研究中国哲学的某个思想时,对于西方哲学的成说,究竟是放开使用还是小心慎用甚至勿用,还是可以区分的,研究者还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到此为止,他的推论和结论都是我大体可以赞同和接受的。要理解别人的意思并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旭东已经做得很好了。
方旭东的评论和推论中有两点是有相当普遍性的,是值得深入讨论的。第一点是他强调:“实在说来,我们固然可以做到不使用某一支某一派的西方哲学概念与理论框架,却无法做到不使用一点西方哲学概念与理论框架。这是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概念与理论框架已经深深渗入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这是一个谁也遏制不了的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可改变的命运。”第二点是他在文章最后说:“这种挺立文化主体性的使命意识自有一种悲情,值得推赏与携手共奋。”这两个问题或评论是经常听到的。下面要讨论的对拙文的两种评论也涉及到这些问题。对此,笔者会在第四节略加申说。
三、“经学子学”还是“比较哲学”?
以上第一节讨论的观点对“反向格义”的做法是以批评为主的,第二节所讨论的观点对“反向格义”的现象是有所同情或谅解的。在这一节,我们将集中对照两个来自不同方向的、立场更鲜明的批评和主张,并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郭晓东批评“反向格义”的立场最坚决,态度最彻底。他认为拙文仍然有“言不尽意的地方”,似乎将讨论仅限定于“对中国哲学在学理上的误解而已”,没有提出重建一个“新的典范”的问题(19)。拙文曾经提出,“以一个现成的现代的(实际上来自西方的)哲学概念来定义或描述老子之道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任何一个明确的、分析式的现代哲学概念都无法全面反映或涵盖这样一个浑沦无涯、贯穿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笼罩于宇宙与社会人生的古老观念。逻辑分类式的定义更无可能,因为老子之道不属于任何一类现代学科中已知的知识体系中的概念。面对这种困难,我们可能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继续借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术语,但同时指出这一西方概念用于中国古典语境时的局限和问题。另一种是尽可能不用西方或现代的现成的概念,以避免不必要或错误的理解和联想。”(20)
郭晓东对笔者的做法有所不满,他批评说:“我们注意到,只是为了‘不拒绝西方现代哲学的洗礼’,刘教授才无奈地主张用‘普通’的词汇来诠释传统的思想,在这里现代性的诉求似乎又占了上风。”郭晓东进一步追问:“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反向格义’之不足道,为何不重新回归到我们本有的模式,用我们自身的语言表达自身的思想?……古人曾经使用的概念与术语对今天来说没有失去其有效性,他们的问题意识对今天而言同样也没有失去其有效性……中国哲学要解决其‘合法性’危机,要摆脱其‘反向格义’的宿命,今天看来似乎只能回到其本应的问题意识中去,即回到中国思想传统本身的问题中去。既然我们所用的‘中国哲学’之名,指的是过去经学与子学曾经思考的那个东西,那么,我们不妨就让它‘名’符其‘实’,在‘中国哲学’之‘名’下,回归到经学与子学中去。”郭晓东这样说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哲学”继承了传统的经学和子学,而“经学和子学曾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要表达者,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之主要承载者,因此,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而不是那种所谓的‘哲学在中国’,也就必须作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承载者,成为中国精神的主要表达者。”所以,“中国哲学如果还有必要存在的话,它一定不能只是单纯的知识建构,它不能看作一种纯‘学术’的研究。”
显然,郭晓东的愿望是良好的,中国哲学中的儒释道的确在某种程度或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这一点下文还会申论。但是,尽管古代思想家或古代经学和子学中提出的问题及其问题意识在今天仍然有效,“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已经说明它不再是传统的子学和经学,我们已经无法回到私塾、书院、学堂和国子监的时代,无法真的用传统的语言表达传统的思想。劳思光先生曾提到唐君毅和牟宗三并非不重视“现代化”问题,“但就中国哲学的发展取向讲,他们对‘现代性’观念却缺乏适足掌握及理解;这就成为他们的主张中一个关键性的盲点。”(21) 劳思光进一步指出,欧洲文明已经造成了一个“现代世界”,“这个世界有其光明面,亦有其阴暗面;但不论它‘好’或‘坏’到什么程度,它即是我们所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这些当前存在的人讲,它是一种客观性的‘所与’(given)。如果我们不想涉及某种形上学或语言上的纠结,我们可以避免称它为‘Objective World’[客观世界];但至少应该承认它是‘Objectivated World’[客观化的世界]。这样一个已被建立成客观存在的世界,成为我们一切主观的自觉努力的限定条件。这是我们谈及任何实践性问题时决不可遗漏的认识。”(22) 我想在这里把劳先生关于唐、牟的这些话送给晓东也许是合适的。
与郭晓东主张回到经学和子学去的主张非常不同的是彭国翔的观点。彭文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之不同于传统的以‘经学’和‘子学’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哲学’,正在于其诠释和建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参照是‘西方哲学’。”(23) 彭文反复强调,“就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性而言,现代的‘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比较哲学’。”彭文的另一主张是应该以“援西入中”的说法代替反向格义的说法,因为“所谓的‘反向格义’,正是对运用西方哲学来诠释中国哲学这一基本取径的指谓和质疑。”他提出“援西入中”有正面的积极的和负面的消极的两种模式,而“反向格义”只是其中的负面模式。正面的积极的“援西入中”可以以牟宗三为“范例”,他的著作对于“儒释道三家的义理系统来说,无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专精深透的诠释。”“牟宗三先生对于西方哲学的造诣之深广,恐怕要远远超过一些中文世界中甚至专治西方哲学的学者。”彭文的观点与前面所讨论的张汝伦和郭晓东的观点适成对照。笔者无意对任何个人的观点作简单的评价或取舍,而是希望能够正视在中国哲学这个学科之性质和方法上的严重分歧和认识上的困难,有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避免理所当然地坚持己见和“聋子式”的讨论和对话。
彭文进一步提出:“第一,在目前运用现代汉语从事中国哲学写作时,不用西方或现代的现成概念是否可能?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刘教授这里所谓两种处理方式是以引用西方哲学必然导致中国哲学的困境为前提的。但是……‘援西入中’可以有正面与积极的方向和方式,‘援入’西方哲学不一定只会给中国哲学带来困境,更有可能给中国哲学的诠释和建构带来发展和丰富的资源和契机,……如果过于担心‘援入’西方哲学所可能给中国哲学带来的负面后果而试图尽量摆脱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甚至试图与之‘老死不相往来’,则不仅有‘因噎废食’之虞,更不免‘逆水行舟’而有违应有的发展大势。问题恐怕并不在于‘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狭义的中国哲学’,而在于实际上不懂西方哲学的确严重限制了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在目前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互动沟通日趋深入的情况下,试图在拒斥西方哲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并且,只有在与西方哲学深度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真正富有特性的观念结构和价值系统而非单纯的话语形式,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最终才能够得以建立。”
国翔对于“援西入中”的积极作用似乎有些简单乐观。笔者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在引入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时误解误用或简单套用的弊端。对此,国翔喜欢借用安乐哲(Roger Ames)的说法,认为“零售式”(retail)的援入就是好的,而“批发式”(wholesale)的援入就是不好的。笔者感谢安乐哲有所回答。但这种比喻并不能解除人们的疑虑。什么是批发式的?按照国翔的说法就是“单一的整体性”的“援西入中”,但有谁可以将一个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单一的整体性”地援入来解释一个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呢?谁能用“整体性”的康德来解释孟子思想呢?如此说来所有“援西入中”的实际工作大概都是零售式的了。这样,“零售”和“批发”的比喻就不能说明问题。比如,单独用物质或精神、实然或应然这样的概念来定义和解释老子之道算不算“零售”?而这种零售式的“援入”仍不免是所谓“负面、消极的援西入中”。国翔又说,要达到积极的援西入中,就要“深入双方传统,真能做到游刃有余”,“于中西传统皆能深造自得之后方可水到渠成”,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负面的消极的“援西入中”。这话自有其正确的道理,但笔者相信相反的道理也是正确的:对于中西双方了解越是细致深入,越不敢轻言中西会通和中西比较;对双方知之越多,越能发现知之不足,越不敢自诩“深造自得”,也就越不敢轻易将“援西入中”当作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
四、中国哲学:现代学术还是民族文化?
实际上,郭晓东和彭国翔的观点之不同涉及到了更基本的问题,即“中国哲学”四个字意味着什么,或曰“中国哲学”的性质为何?身份为何?晓东认为中国哲学实质上是经学和子学,因此仍然是民族精神的“表达者”和“承载者”,国翔则强调中国哲学已经是现代学科,本质上只能是“比较哲学”。晓东认为要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就必须“重新回归到我们本有的模式,用我们自身的语言表达自身的思想”;国翔认为,“试图在拒斥西方哲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二者观点之不同反映了一种相当广泛的分歧。
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比较实际而稳妥的分析或许可以陈来的表述为代表。他认为“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24) 这种表述充分照顾到历史、理论和事实,反映的是20世纪的历史现实,而不是国翔与晓东心目中的“中国哲学”的理想化内容。
赵敦华所说的中国哲学与以上诸说又不相同。他将中国哲学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的中国哲学指“传统中国的哲学”(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广义的中国哲学指“现代中国的哲学”(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前者指以中国传统为底子或本位的哲学,后者指在现代中国发生的、或用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切哲学形态。”(25) 这个定义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对举,给人留下的一个悬念就是“传统中国的哲学”是不是“现代中国的哲学”的一部分。按照他下文所说,胡适、冯友兰等创立的中国哲学史开创了中国哲学的“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现代形态”。那么,这种“现代形态”还算不算“以中国传统为底子或本位的”呢?也就是算不算“传统中国的哲学”呢?如果不算,那么就等于宣布“传统中国的哲学”已经死亡和终结,与现代中国的哲学无关。如果认为这种新开创的“现代形态”是“传统中国的哲学”的某种延续,那么所谓“狭义的中国哲学”就不仅是“传统中国的哲学”,而且同时也是“现代的中国哲学”。赵敦华的定义方法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断裂,而陈来的定义则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与继承。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哲学则是已经进入“现代的中国哲学”之中的“传统的中国哲学”,它不纯粹是传统的,也不纯粹是现代的。
中国哲学实质上是“经学、子学”还是“比较哲学”的分歧反映的正是“中国哲学”之性质或身份的模糊不清。晓东强调的是中国哲学的“传统”与“民族”的方面,国翔强调的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和“学术”的方面,二者难以调和,但也不必调和。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所谓“中国哲学”虽然是现代之名,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资源和重担;虽然称为“中国”之学,却已经在按照“西学”的乐曲节拍起舞。古代的思想文化虽然已经进入现代世界,却不愿意局促于现代学术的西服革履之中;不愿意安坐在学者的书房中对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沉默不语,却又不适应现代西化的语言表达。这是矛盾和尴尬,困境和两难,但也是契机、挑战和使命。
面对困境和挑战,应该思考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将“中国哲学”重新逼回传统的躯壳之中呢?或者是否应该将之塞入西学的框架之中呢?显然,这两种可能性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实现的。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期待中国哲学死而后生,化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亦古亦今的单一的新形态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期待现代学术形式与民族文化精神完全合一呢?对此笔者是有深刻怀疑的。“中国哲学”所继承和传承的实际内容是多样的,实际功能是多元的,在所谓“现代中国”中,儒释道的多种功能和多种身份无法化而为一,也不应该化而为一。郭晓东和彭国翔的分歧代表的就是中国哲学之多重身份之必然冲突的反映。理论上,双方各有坚强的理据;感情上,双方各有自己的濡沫之求;实践上,任何一方都无法让另一方的诉求销声匿迹。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双方的立场各有其合理根据,各有其存在发展的必要和空间。因此,要深入讨论有关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如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问题,就要首先明确中国哲学的多重身份,应该充分解放中国哲学,让它的不同身份得到足够承认,适当分化,合理展现。在不同身份明确和分化的前提下,对于面向西方哲学应该“学什么”、“如何学”、“目的何在”、“标准何在”的讨论才有意义和可能,在“中国哲学”的名义下,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才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哲学作为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新酒的思想理论与文化形式,至少隐含了两种身份。第一是现代学术的身份,第二是民族文化的身份。对这两种身份是否应该加以明确区分呢?笔者认为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两种身份之性质、功能不同,从事这两种不同身份的工作的性质和要求也不同,混为一谈,是无谓的争论无休无止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仿照西方学科体系而建立的,其直接对应体是西方大学中的哲学科,其设置背后的理念则是西方式的学术标准和学术方法,笼罩在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根据这种理念,狭义的“中国哲学”应该是纯学术研究的科目,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西方哲学一样,基本上应该取价值中立的立场,不论研究对象是哪一种民族,哪一个国家,作为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则不必强调其种族和国别特性,不必涉及现实社会人生及个人信仰。将孔子思想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对象,研究者就应该将自己对儒家学说的信仰崇奉或厌恶不满放到一边,“尽可能”根据历史文献对孔子思想进行客观的对象性的研究,避免因个人的情感好恶影响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现代哲学家会将孔子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发展为现代或西方意义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的这一角色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学科”的身份。在现代中国,与“中国哲学”四个字有关的专业工作者绝大部分在这个“身份”和职业下工作、谋生、追求、创造。
但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儒释道之经典和思想,其内容与西方学科分类体系难以完全对应。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儒学,而儒学以及道家和佛教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认同的对象,因此,它又不可能是西方纯学术意义的现代学科。在这方面,所谓“中国哲学”与其他民族的宗教和神学有某种模糊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姑且将中国哲学的这一角色称之为“民族文化”的身份。有一个时期,每个研究中国哲学的人都首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儒释道进行“客观的”研究和批判。这时“中国哲学”四个字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意义很稀薄。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发展,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渐渐增加了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学的价值认同,这就增强了中国哲学之“民族文化”以及民族精神之象征的身份,关于建立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主体性”的口号就是要求强化这一身份的反映(26)。将孔子思想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那么就要以提倡和维护为主,以继承、发展和更新为主,不能接受冷漠的貌似客观的研究,不能允许将孔子思想改塑为现代或西方意义的与中国人之生命和生活无关的纯哲学理论。显然,中国哲学的“现代学科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这两种角色是有明显冲突的。坚持中国哲学之民族精神之载体的功能,就会批评纯学术立场与中国文化之精神无关、与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无关,掏空了儒释道本来的精神生命。坚持中国哲学之现代学术立场就会批评前者的主张不懂基本的学术规范和要求,将价值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将个人感情(或称之为民族感情)掺入学术研究。这种分歧反映了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身份混淆”和“角色分裂”。
其实,中国哲学还有第三个身份。以儒释道传统为核心的中国哲学还是普通的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营养,是获得生命力量和生活方向的精神源泉。所以,很多人虽非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学者,但是他们却需要儒学、佛学或道家为他们提供精神生活的指南和力量。普通人也需要涉猎儒释道之学说和教义。这样,“中国哲学”的实际内容就又有了“生命导师”的身份。(27) 不过这一身份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很密切,可以暂存不论。(28)
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术或一门现代学科是以西方的学科体系为参照而建立的,所以当我们承认中国哲学是一门现代学科的时候,似乎就必须承认借用西方哲学或“援西入中”的必要性或合理性。但实际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将中国哲学看作现代学术中的一科,其研究方法目的仍然是多样的。最简单地来说,至少有以历史的客观性的研究为主的导向和以理论发展创新为主的导向两种不同侧重的研究(29)。现代学术研究中这两种导向可以看作是从传统的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发展而来的。两种定向即诠释一部作品时的文本的、历史的定向与当下的、自我表达的定向(30)。就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来说,不仅应该继承,而且应该突破对一部或几部经典进行诠释的形式,从对象性研究和理论性建构两个方向进行更严肃、更深入的研究和创造。下面我们分别从两种导向的角度来讨论如何借用西方哲学的问题。
对于历史的客观性导向的研究来说,当然也可以参照或借用西方的视角、概念或方法,但必要性不一定很高,借用的空间也比较小。很多人,包括上面提到的方旭东和彭国翔质疑,难道我们现代人有可能不用西方的概念术语来研究中国哲学吗?笔者的回答是,就无意识的层面来说,就绝对的意义来说,当然没有可能,因为我们的普通语言表述中都无法避免西方传入的概念和术语。但是,就自觉的学术研究来说,就努力避免套用西方哲学概念和术语来理解、定义、解释和阐发中国古代的思想来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这方面的成功的代表作也并非凤毛麟角。张岱年师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一例。张岱年喜欢逻辑实证论,因此他的文章著作都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但是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很少借用西方哲学概念来解说中国古代的思想,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的这部成名作不成功或水平不高。另外一个典型实例是信广来。他计划写三部书。第一部是关于孟子的,已经出版(31),第二部是关于朱熹思想的,即将完成。他说,他的这两部书主要是研究孟子和朱熹自身的思想,因此尽可能避免使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解说孟子和朱熹。他的第三部书才会以一个现代哲学家的身份来讨论儒家伦理,那部书才会使用现代哲学术语来研究儒家思想。他关于孟子研究的英文书中,竟然一个“philosophy”(哲学)都没有用。但他也有在西方哲学概念下讨论中国哲学的著作(32)。可见其对于用不用西方哲学术语、何时用、如何用是有高度自觉的。他长期在香港、英国和美国接受哲学教育,所修的课程都是关于西方哲学的,尽管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孟子的,但他在伯克利的教职是西方伦理学的,他申请工作所提供的论文和演讲都是关于康德哲学的。他的书都由世界著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本人长期在北美著名大学当院长和校长,其学术地位在西方是得到广泛承认的。他的成功的自觉实践也说明,研究中国哲学不一定必须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或概念,也不应当以是否借用了西方哲学概念来作为一种研究是否成功或水平高低的判断标准。当然,广泛的、多学科的、包括西方哲学的训练显然是有益的或必要的。
关于胡适、冯友兰借鉴西方哲学来研究中国哲学之利弊,陈少明也有很好的分析。他说:“它的意义在于,在比较形而上的层次上,建立了比较、会通中西文化的专门学科。这是一种不叫比较的比较研究。但是,它与佛学传入中国初期那种比较不同。那时的中国学者是用老庄或玄学的观点理解佛学,佛学是被解释的对象;当代学者是用西学解释中学。开始的时候,由于那些留洋的学者原本有较好的古典文化修养,在诠释传统时仍注意对象的完整性。后来则是两种训练均不足的一代,用自以为了解的西学去解释变得陌生了的古典。当两种思路不吻合时,被肢解的必然是古典。结果就是我们的当代哲学无法从传统吸取有益的资源。也许这是古典传统为取得其现代形态所付出的代价。”(33) 显然,加强中国与西方哲学两方面的训练,以更慎重的态度对待借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哲学理论的做法应该是摆脱狭义的反向格义之困境的必要条件。
中国哲学研究当然也可以以理论发展创新为主要导向。这种导向的研究不必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哲学的术语,但可以借用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理论向度、命题和概念来深化中国古代固有的思想理论问题,或嫁接,或发展,或修正,或批判,或更新,从而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哲学理论、概念、命题,回答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时代的问题,丰富和充实传统思想中固有的内容。就这个方向来说,借用西方哲学的空间更大,灵活度更高,“援西入中”似乎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容易成功。尽管这种现实的、创造的取向可能更需要、更适合借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借用西方哲学是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方法或条件,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精义也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文化资源,借用佛教哲学或其他传统的学术、宗教理论来发展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是有益的途径。至于在这个方向上不借用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成功也很难做必然的判断,但思想理论的创造拒绝接受其他外来刺激和借鉴总是不明智的态度。就中国哲学理论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这一点来说,李晨阳反对“守株待兔”和“揠苗助长”的立场是值得玩味体会的。
对两种定向或导向的说法,最常见的质疑就是是否可能严格区分。笔者的回答是,在一般情况下,两种定向或研究导向的区分并不困难,个别情况或特殊情况下区分的困难是难免的,但这不足以说明我们应该完全放弃两种导向的自觉意识。笔者发表过的文章已经引用很多实例说明区别两种定向或两种导向已经是很多同行都意识到并论述过的,只不过所用术语不同而已(34)。这里我们可以再以陈少明的说法为例说明两种定向或导向是有必要和可能的。陈少明在研究齐物论时就清楚地意识到:“一篇《齐物论》,三千方块字。古往今来,解人无数。而在这数不清的注疏解释中,也可分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基本倾向。一是通过文本逻辑结构的分析,揭示作者的思想意图。一是借助作品主题的评释,表达论者的个人见解。前者是注庄,后者是论庄,即讨论庄子提出的思想问题。虽然不是每个注释者都对两者有自觉区分,且对此区分有自觉者,也不能保证在相关的著述中,真能严守两者的界线,但是,强调这一区别仍然是有意义的。不同的思考方式有不同的思想功能,同时也有不同的衡量尺度。注庄者得以守原文言述结构为原则,而论庄则应对论题的探讨提供新的思想观点。”(35) 他的书中前十三章都是对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即第一种倾向的研究。到了第十四章,他自觉地转向第二种倾向的研究。他说“提出对《齐物论》主题的再解读属于后者,它不必是庄周原意的追寻,而是在文本的启发下,联系现代精神生活的某些问题,进行独立的哲学分析。但它仍得以我们对庄子的理解为基础……”(36) 这种对于研究方向和目标的自觉意识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准的基本前提,是值得一切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注意和实践的。
两种导向的说法反映的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现状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并非要将所有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律纳入两种导向之中。纯粹客观的哲学观点的比较式研究就不必列入两种导向之中,纯粹哲学问题的讨论可以兼及中国和西方哲学内容,也不一定要纳入两种导向中的某一方。中国哲学的研究大可在扎实深入的思考探索中开拓新的方法和角度。比如黄勇讨论意志软弱是否可能以及讨论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课题时都以二程的资料为主,却摆脱了平行比较、或以西释中、或援西入中的既有模式,完全集中于对哲学问题本身的讨论(37)。这既不是纯粹将二程当作研究对象,又不是利用二程的资料建构自己新的思想体系,而是不分中西的哲学理论的探讨。这应该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模式,或许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模式。
现在来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哲学的另一种身份,即作为民族文化的身份。中国哲学的这种身份在很多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那里都是明显的和重要的,郭晓东不过是笔者偶然遇到的一个例子而已。对于中国哲学的这种身份,笔者有充分的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将现代学术和民族文化两种身份合为一体在现代学术体制里是行不通的,而且对两种身份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一个大学教授不应该假借学术研究之名来传播个人的宗教信仰或价值信念。现代学术研究要求一种对对象的客观探求的态度。对于孟子或老子,不论我们是喜欢或不喜欢,都不能影响我们研究的严肃性。如果因为不喜欢就竭力批评,因为喜欢就竭力歌颂,这就不是学术研究的态度,其写作与讲授与学术研究也就没有关系了。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的儒学或道家,信奉者自然有一种崇敬或信仰,这是无可厚非的。民族文化的信奉者可以不讲学术,只讲弘扬和捍卫,不喜欢以至不允许别人以一种纯学术的客观的态度来解说儒家或道家的思想。这样极端的态度可能是大多数中国哲学的研究者都不赞成的,但是将对民族文化的崇敬与对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以“结合”的名义混淆起来却不是很少见的。
对于中国哲学的民族文化的身份来说,是否可以或者应该借鉴西方哲学呢?郭晓东似乎是会反对的,彭国翔似乎会赞成。但问题恐怕不是赞成或反对所能解决的。作为民族文化的儒释道之学,如果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就很难在短期内大规模地引入外来文化进行自我改造。但是现代的民族文化也不可能与世界隔绝。用劳思光的话来说,我们只能处于“在世界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而不能处于“与世界对抗的中国”(China against the world)(38)。
关于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劳思光提出一个“客观功能”的概念。他说:“所有文化主体性是主从的问题,是哪一种价值观念、哪一种制度的理想,能够占有主要的地位;但是这一点正是一个客观功能的比较的结果,所以这里有一个自然竞争的过程。你如果重视自然竞争的过程,你会明白,我们对文化主体性能不能保持,那看我们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发挥多少功能,它如果发挥功能很高的话,那它的主体性自然就保持的较多,因为它比较有做主的地位。可是如果你那文化本身的功能只有这么多的话,你进入某一个历史的情境的时候,就可能不能发挥那个主要的功能,那个时候,你也不能勉强要求你要保持主体性,所以你要做主宰,你也不能勉强要求这个东西。”(39) 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民族文化,重要的问题就不是要不要在民族文化中引入外来元素,而是如何让民族文化发挥更好的社会功能,能够达到或超越其他文化的社会功能。这样,所谓要不要在民族文化中引进西方文化就有了一个新的判断标准,那就要进入另一个论题。这些问题太重大,太复杂,本文也已经太长,只好在这里戛然而止了。
显然,笔者并非提倡“某一种”具体原则,而是希望大家对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的基本属性、特点、目标和方法的复杂性有一些深入的思考。笔者也绝非幻想大家可以形成“某一家”共识,但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互不理睬,绝非促进学术健康发展之正途;不同观点之间的漠视、轻视、鄙视更不是文化多元繁荣之征兆。反向格义的问题或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要深入,就要考虑中国哲学的不同身份以及与此相关的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不同导向和目标,就要承认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理解和谅解。至少,中国哲学多重身份混淆不清的状况应该有所改变了。
(作者附言:本文承蒙陈静、干春松等校阅初稿并提出意见,在此致谢。)
注释:
① 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又载于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反向格义与全球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6页。
② 郭晓东:《也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及“反向格义”说的回应》,朱刚、刘宁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0-328页。
③ 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30页。
④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归之于关于中国哲学之研究方法的理论讨论可能更恰当,可简称之为方法论问题。“合法性”的问题无论有无结论,都难以永远讨论下去,但一个学科的“方法论”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却需要并可以不断讨论下去,而且永远有探索和改进的余地。
⑤ 这可以熊良山的《道德经浅释》(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为例(参见任继愈的批判文章:《关于道德经》,李申、陈卫平主编:《哲学与宗教》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⑥ 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以下张氏之引文均出自此文,不另出注)。
⑦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⑧ 参见刘笑敢:《儒家不能以道家为忌——试论牟宗三“以道释儒”之诠释学意义》,《人文学报》(台湾“中央”大学)第24期(2001)。
⑨ 参见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⑩ 这方面,张汝伦也有评论,认为牟的理论体系是有漏洞或难以自圆其说的。
(11) 参见刘笑敢:《郭向之自足逍遥与庄子之超越逍遥——论诠释方向之转折及其评价标准问题》,《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注释,诠释,还是创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6-151页。
(12) 张祥龙的回应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注释,诠释,还是创构?),第394-395页。
(13) 张祥龙:《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古代思想》,《普门学报》(台北)第22期(2004)。
(14) 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7-139页;又见《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新诠》,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77-78页。
(15)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注释,诠释,还是创构?),第399-400页。
(16) 引自李晨阳2008年2月9日给笔者的电邮,征得同意而摘要引用,略去了括号中的解释语。
(17) 方旭东:《通过诠释以建立哲学:内在机制与困难》,《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以下引自此文不再出注)。
(18)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出。
(19) 郭晓东:《也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朱刚、刘宁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以下引自此文不再出注)。
(20) 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21) 劳思光:《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代发刊词)》,《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反向格义与全球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2) 劳思光:《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代发刊词)》,《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反向格义与全球哲学),第6页。方括号中的字为引者所加。
(23) 彭国翔:《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再反思——“援西入中”及其两种模式》,《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以下引自此文不再出注)。
(24) 陈来:《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4期。
(25) 赵敦华:《“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中国的哲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引自《新华文摘》2005年第20期。
(26) 郭齐勇云:“现在是到了‘中国哲学’学科自觉与主体重建的时候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注释,诠释,还是创构?],第391页)郭晓东云:“最关键的问题是文化主导权的问题。”(《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二辑:注释,诠释,还是创构?],第402页)景海峰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焦虑,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它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景海峰:《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第210页)
(27) 叶嘉莹及很多人讲过在人生困境中,在监狱中靠《论语》的精神智慧帮助自己度过灾难。于丹读《论语》和《庄子》的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著作,她本人也不以《论语》和《庄子》之研究者自居,我们不必对其苛责。她的演讲和书籍能获得学术著作无可相比的广泛欢迎正因为它体现了儒学和道家的“生命导师”或“人生顾问”的功能。不过,如何提高普及工作的水平、发挥传统思想的生命导师的功能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28) 以上关于中国哲学之三种身份的段落取自笔者即将出版的新书《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之引论部分,有所增删。关于三种身份是否有必要区分或如何区分的问题,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笔者新书及《哲学动态》将要发表的笔者在访谈中的回答。
(29) 当然,这里的历史的客观的研究不是追寻本质主义或绝对主义的真相,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种研究取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30) 参见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31) Kwong-loi Shun,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7.
(32) Kowng-loi Shun and David B.Wong,eds.,Confucian Ethics: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f,Autonomy,and Commu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3)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34) 参见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35)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第216页。
(36) 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第216页。
(37) “How is Weakness of Will Not Possible:Cheng Yi's Neo-Confucian Conception of Moral Knowledge,”in Roger T.Ames and Peter Hershock(eds),Educations and Their Purposes:Dialogues across Culture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p.439-456(中文版《意志软弱(akrasia)何以不可能:程颐论知行》载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7-270页);“Why Be Moral?‘The Cheng Brothers’Neo-Confucian Answer,”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Vol.36(2008),No.2(中文版《宋明儒程氏兄弟论“为什么要道德”》将刊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或许有人认为黄勇的做法是援中入西,但笔者认为这样说未必恰当,因为他是以程颐的思想资料回答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并不是将程颐的思想纳入某个西方哲学的体系或框架之中。
(38) 劳思光:《中国哲学之世界化问题》,劳思光著、刘国英编:《危机世界与希望世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1、58页。
(39) 劳思光:《中国哲学之世界化问题》,第61页。
标签:哲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宇宙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