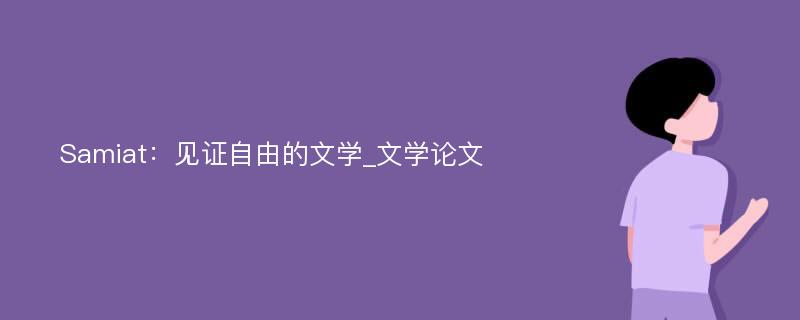
萨米亚特:见证自由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米亚论文,见证论文,自由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位捷克出版界人士曾说,当代捷克文学包含三个方面:官方文学、流亡文学和“萨米亚特”文学。他说这番话是在1989年6月布拉格的一次出版会议上,在座的人全都热烈鼓掌,因为终于有人替他们说出了早已存在的事实。“萨米亚特”是一个俄语词,最早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俄国诗人用来称自己打字装订的诗集,后来成为七八十年代波兰、匈牙利、捷克等东欧国家地下出版物的代称。按照牛津俄英词典的定义,“萨米亚特”是指那些“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但此定义却忽略了一点,即文化的创造自古以来都是采取“非正式”的形式,人类失去这个自由也只是近代的事,因此它很难反映二十世纪这样一个重要现象,当一个政权禁止人民提出任何质疑,毫不在乎他们的内心信念,竭力把他们降低到只能接受假话的水平时,自制的文本便成了作家的表达媒介,被那些渴望得到精神资源的人们看作唯一的安慰。
举世闻名的布拉格之春是由捷克作家为其先导的。在此之前,捷克作家一直处于社会上层,享有各种特权,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按照政治配方,生产“拖拉机文学”。这种耻辱直到昆德拉的《玩笑》和瓦楚利克的《斧子》出版后,才开始得到洗刷。在1967年6月作协四次大会上,作家们纷纷提出创作自由的问题,他们要求除了受刑法制约外,写作应不受任何其他限制。昆德拉认为,当代社会摈弃了人道主义美德,捷克文学正在丧失欧洲的特征。克里玛发言说,检查制度必然会变质为官僚机构,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瓦楚利克则指出,艺术不可能放弃它对政府的批评,二者之间应制定出“客客气气的交往规则”。作家们的言论引发了社会上对改革的公开诉求。一年以后,当捷克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时,瓦楚利克又应一批科学家的请求,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千字》的宣言,要求加速改革步伐,彻底去斯大林化。作家们的言行使苏联领导层大为震怒,以致勃列日涅夫在与捷克领导人谈判时,竟冲他们吼道:“你们的政策竟让所谓自由作家们来发号施令,这简直是发疯!”因此,当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后,全副武装的士兵首先包围的国家机关之一便是作家协会。
此后,在“遗忘总统”胡萨克的统治下,开始了所谓“正常化”时期。许多作家失去工作,其作品也遭到禁止,仅在1982年七七宪章开列的名单中,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二百三十一名!官方的目的很清楚,将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让他们被读者遗忘。一些作家(如昆德拉)离开了捷克,另一些作家留在国内,但只能为抽屉写作。七十年代初,一个被禁作家的小圈子开始每月一次在克里玛家里聚会,互相朗读他们的作品。他们中有捷克文学的重要作家哈维尔、瓦楚利克、格鲁萨、科赫特、克莱门特和乌德等人。后来,瓦楚利克在《施瓦森堡的挂锁》中描述了“萨米亚特”文学的产生,他们先是在朋友间互相传阅手稿,然后发展成请人把这些手稿打出来,编上号码,再按照纸张、打字和装订的成本价,出售给作者本人和那些感兴趣的读者。瓦楚利克还给这种未经许可的书取了个隐喻的名字:“挂锁的书”。他们甚至还请国营工人来装订成册,配上被禁画家的插图,使它显得像真书一样。
为了避免被抓住和被没收的危险,这些作品都是在夜幕下的小房子里打印出来,藏在阁楼、天花板和花棚里,但作者、打字员和装订者仍时时面临警察的搜查、审问和监禁。七十年代中期,“萨米亚特”作品开始流传到国外,于是官方加紧了控制,并且软硬兼施,许诺说只要放弃“萨米亚特”写作,作家们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当然,大多数作家没有顺从。在他们看来,出版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精神生产是人间的法律无权干预的。瓦楚利克回忆到,有一次,国外的一个出版家协会奖给他一万马克(后来证明是误传),警察很快就知道了,询问他是否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他争辩说,“萨米亚特”不是一个出版社,而是沉默作家的一个维权行为。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行为,就像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随他们去吧,但我绝不保持沉默,绝不!”
沉默的墙毕竟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萨米亚特”,有的人还主动跟作者联系,要求被允许复制这些未经许可的东西,一些读者甚至预先付钱来订购。写作依赖于读者的阅读反应,而这种秘密的阅读才真正显示出作者与读者之间两颗心灵的交流。后来,一些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加入进来。到八十年代末,这类书已经出到三百多种,从文学发展到宗教、政治、历史、经济学、哲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对于捷克作家,这种行动不仅是他们用以战胜审查制度的方法,而且是一种文化和共同体生存的象征。他们再不用担心市场的需求,不用考虑到要发表而自我审查,更不用操心能否得到官方的文学奖项,这使他们得以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回复到自由的元写作状态。
官方极力宣扬爱国主义,并用各种福利去换取表面上的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买房子,购小车,出国旅游,但剥夺人尊严的结果,却使整个社会处于压抑、沮丧、顺从和冷漠之中,甚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建立在这种恐惧和自利之上。大多数人出于无望,变得玩世不恭,即使那些曾被斥为反人性的东西又公开复活,也很快就熟视无睹。在官方文学中,则是一种平庸的美学,一种爱国主义和田园生活的抒情和满足。从那些制造出来的盛世狂欢话语中,透出某种恐怖的东西,用哈维尔的话说,这是一种“奇特的几乎是神秘的恐怖,一切都是夸张的、热情的、抒情的、悲惨的或者过于严肃的”。这种主要是由谎言造成的恐怖,促成了捷克“萨米亚特”作品中强烈的道德感。
从十九世纪捷克文学的启蒙时期开始,捷克作家就将文学看作是生活的捍卫者,作品中总是充满当下的严肃问题。捷克人很少有过专门为消遣而写作的作家,也不欣赏作家那种自我放任的存在奢侈。他们始终坚信一个古老的信条,写作可以使人获得自由。由于被逐出公共生活,“萨米亚特”作家被剥夺了许多直接经验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有因为被边缘化而退缩到自我封闭。“萨米亚特”作家从来不写那些虚假的东西,例如远离现实,逃避到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故事中,沉溺于抒情的原乡传说、伪民俗的仿制、做作的拟古或文字的技巧,而是描写时代阴影下普通的真实的人生。
这种对生活本质和人的状况的关注,发誓只说真话的艺术观,正是“萨米亚特”作家所信奉的“生活在真实中”。在他们看来,生活在真实中就是拒绝各种非个人化的权力话语,回到生命世界本身。作为独立的“萨米亚特”文学,应当揭示生活目标与制度目标的冲突,激励人们建立起一种不同于制度目标的平行结构。显然,这不是一场政治层面的反抗,而是一场道德层面的反抗。正如美国作家罗斯在采访克里玛时所感觉到的,在一个谎言社会,“萨米亚特”成为“真实的唯一监护人”。
克里玛的小说很能体现“萨米亚特”的主旨。在《爱情与垃圾》中,克里玛借主人公的话说,应当让生活“上升到碌碌无为和遗忘状态之上,要自己去探索,不从他人那里接受虚幻的和模仿的事物”。这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贯主题:在个人的真实生活中体验世界和存在。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手法,讲述了一个人的情感经历。主人公是个作家,只能在国外发表作品。他的工作是街道清洁工,每天都与一些粗俗而有趣的人在一起清扫垃圾。他有妻子儿女,却与一个已婚的女画家偷情,小说便是围绕着这点展开。通过对周围人的观察,对布拉格的街道、河岸、郊外山坡的描写,主人公的生存状况渐渐浮现出来。他想要过一种“真实的生活”,拒绝杰尔克斯基精神(这是一种极地某部落的语言,只有二百五十个字,可以用来表达一切事物。在主人公看来,许多生活在谎言中的人都具有这种精神),但却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说谎者的角色,不断与情人见面,又不断向妻子撒谎。最终,两人都难以忍受这种欺骗,只能选择分手。如果说,垃圾是世界物质化和道德堕落的隐喻,那么爱情则是在生活中寻找真实的象征。
短篇小说集《我的初恋》基本上是自传性的,其中的《真话游戏》描写一对情人的故事。乍一看,这好像是一场心心相印的恋爱,男人发现了多年来那种宣传的欺骗性,女人发现丈夫欺骗了她,这使他们走到一起。但当男人希望了解其情人时,却感到这个女人始终是个谜,即使他设法跟她玩相互问答的“真话游戏”,也无法看清她。作者有意留下谜团,似乎是在告诉读者,在这个社会里,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种种谎言。
以亲身经历作为作品的情节基础是“萨米亚特”的特点,哈维尔的剧本《观众》,瓦楚利克的小说《捷克梦之书》,也都写到自己在底层的经历,生活的日常性及其悖谬。这一点使人联想到源于十八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诉求:艺术的本真性在于通过亲身经验,形象地表现生活。但是,浪漫主义思维认为价值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人们唯一面对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今天,在许多人眼里,这种思维的实际效果仍然与政治压迫夹缠不清。“萨米亚特”作家恰恰在这点上有所不同,他们保留了中世纪的信仰背景,把价值看作是一种超验的事实,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自传性叙事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理念,以及从个人角度观察世界的重要性,而相信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世界,又使他们得以拒绝任何主观的建构理性和浪漫主义激情,坚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经历了布拉格之春,作家们带着惊愕的眼光,看到自己的国家又一次被掷进一个荒诞的世界。在奥匈帝国统治下,十九世纪捷克作家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这些前辈相比,“萨米亚特”作家的视野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宽广,他们着力刻画的是个人在社会生活里的存在境遇、自我的疏离与异化,因而可以称之为一种个人现实主义的创作。
卡勒尔·佩克的小说《乔治先生》写了一个孤独者,这是一个内心与社会分离的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独自住在公寓里,富有的美国妻子远在国外,每月都给他寄钱来,但当妻子要他出国时,他的平静生活却被扰乱了。过去他想出国,得不到批准,如今他不想出去了,他们又催他赶快办手续。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一天的活动,很晚才起床,刷牙洗脸,喝咖啡,想着天花板上的污渍。然后又描写他穿过街道,漠然地看着发臭的运河,在熟悉的小店买报纸和雪茄,在小吃店吃快餐,然后又是回家,喝咖啡,看报,睡午觉。在酒吧里,他遇到一个喝醉的女人,把她带回家。结果她吐了一床,惹得他大发雷霆,半夜里把她无情地赶走。第二天,主人公又在酒吧里喝了不少酒,最后突然发病死去。
这个人物让人想到加缪的《局外人》,但却没有加缪作品中那种对绝对的激情。克里玛曾说,布拉格像它的现代史上几位总统的死一样,像它曾同时诞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大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一样,充满了悖谬。人们常常把“萨米亚特”文学看作是卡夫卡式的写作,但它其实也是哈谢克式的写作,如像特勒弗卡、邦德、乌德和佩卡等人的作品,都属于那种典型的捷克小说,即捷克哲学家哈耶克所说的“悲伤的欢笑”。
普鲁恰日科娃的《来尝一尝》,同样写了一个道德麻木的故事。一个女人怀孕之后,痛苦地躺在房间里,她的男友却一走了之,去了国外。通篇故事都是她与妹妹的对话,她在房间里的活动,她与男友在电话上的通话。而那个有家室的男人始终没露面,只是给她寄去一张明信片:“这儿的啤酒不错。来尝一尝吧。我爱你。”然后又打电话邀请她出国,并且抱怨这个国家不自由。这篇小说与佩克的小说一样,都是很平常的故事,冷漠而不夸张的叙述,通过一种荒诞的眼光,审视那些灰色世界中的个人。在所谓“正常化”时期,犬儒主义和道德腐蚀成为社会的突出特征。当局为了表面的稳定,强制宣传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但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真正面临的危机却是自我认同。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生活有何价值,他们的内心即使是真实的,他们的行为也永远是被动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有损尊严的事实变成了个人的宿命。
许多作者都在作品中有意显示出社会的背景,以此表明人性的缺失并非与时代无关。那个社会扭曲了人性,而扭曲的人性反过来又支撑着这个社会。然而,正如克里玛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文学家当然要描写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冲突,但却不应当必然地假设这个世界比自己更坏。大多数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生活在谎言中,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着承认它的东西。尽管人们内心什么都不相信,但表面上人人都很顺从,甚至似乎和当局达成了一种游戏规则,至少大家要装作互信的样子。于是,基本道德的崩溃构成了每个人的现实。通过小说的形式,作家们探索了人性最深刻的本质。
“萨米亚特”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但一些作家也复活了捷克的传统小品文。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学类型,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国内外事件及自身状况加以叙述和评论,在恰佩克时代就很流行,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哈维尔、科赫特和克里玛以及其他作家都经常采用这种形式写作,但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家还是瓦楚利克,小品文的形式到了他又有了新的发展。作者虽然常常写的是政治题材,却并没有放弃美学关怀。在他笔下,朋友间的趣事、咖啡馆的谈话、传讯室的交锋、安全人员的蛮横,都写得生动有致,很有一种讽刺、冷漠和顽强的风格。哈维尔曾说,瓦楚利克的小品文“创造了一种原创的形式,在其中他的个人思考、他的观点和经验与主题论述融为一体,并破重新巧妙地安置到艺术的细小结构中,其效果远远超过读者对这一文类的期待”。读他的作品,读者不但会觉得其中的政治思考发人深省,那些描写人的细节也同样使人感到愉悦。
比如,《妖魔》讲述作者在咖啡馆遇到一个天真的伊拉克游客,他们谈到阿拉伯神话里那个宝瓶和妖魔的故事,如果它再跑出来,怎么把它弄回去。他们又谈到旅游,那个伊拉克人说,他去过许多地方,发现布拉格比雅典更自由。这番话使作者哭笑不得,但他不禁又想到,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也许自由的观念会显得更加繁荣,因为在那里,人们更能体会到生活目标对抗制度目标的力量,正如文章里最后所说,妖魔又跑了出来,但“妖魔只能在上空盘旋,就像它在荒漠的沙丘上飘浮,却不能改变沙子的本质”。在《发言人的葬礼》中,作者本打算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却接到警方的传唤,并把他带到警察办公室。两个警察坐在旁边聊天,也不来询问他。作者为了消磨时间,只好一边阅读一本讨论捷克民族性的书,一边想像着葬礼的情形。书中内容与葬礼想像交织在一起,意味深长。葬礼结束,警察宣布说他可以回家了,当作者赶到墓园时,只看见空荡荡的墓地,作者最后写到:“你不可能真的错过一个葬礼,只有活着的人你可能错过。”作者善于把感情内敛在冷静的叙述中,然后在结尾笔锋一转,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哈耶克称他的作品代表了“将政治升华为文学的东欧写作”,确实是精当之论。
瓦楚利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为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个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边缘化。也许,这就是“萨米亚特”作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其名著《论出版自由》中,曾经这样说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二十世纪的捷克作家再次践行了这一信念。他们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