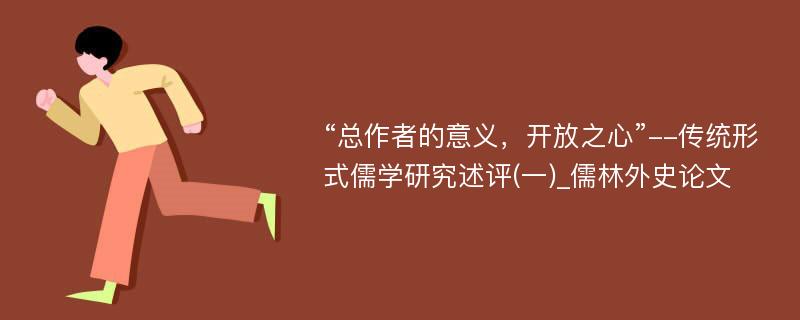
“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以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回顾(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林外史论文,之心论文,之意论文,形式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学术界均回顾每一领域的百年研究状况,借以总结既往、拓展未来。承学界同道不以葑菲见弃,每以回顾《儒林外史》研究状况稿件相约。首先是大连国际小说研讨会主办者林辰来函,乃为之撰写《二百余年来〈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文约二万字,摘要与全文分别刊于《稗海新航》(大会论文集)及韩国《中国小说研究论丛》第Ⅵ期。1999年应韩国启明大学建校45年之邀前往做学术报告,其时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邀请笔者在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做《五十年来〈儒林外史〉研究概论》报告,演讲全文刊于1999年9月出版之《中国小说研究会报》(总第40期)。归国后又应徐子方之邀为东南大学学报撰写《二十世纪〈儒林外史〉研究之回顾》(1999年第4期刊出)。与此同时,又对《儒林外史》研究中某些专题进行反思,先后发表《二十世纪〈儒林外史〉主题探讨之回顾》、《吴敬梓思想研究述评》、《〈儒林外史〉研究三题》等文。此际,有弟子及友人建议将笔者自己的研究历程也做些回顾,于是又发表《〈儒林外史〉前言有四稿》、《跋涉“儒林”三十载》、《吴敬梓思想面貌寻踪记略》、《吴敬梓研究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回顾对〈儒林外史〉既往研究成果的研究》—等文。今再就以传统形式整理《儒林外史》的工作,做一专题回顾。
明人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这非常精辟地铨释了评点书籍的目的。十余年前,当《新批儒林外史》出版之际,一位朋友曾以此为题撰写评介文字。十年来无此朋友消息,今仍以之为题,有思旧之意。
20世纪80年代后期,前江苏古籍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前来舍间,以传统批评形式整理《儒林外史》一稿相约,此正是笔者欲为而一时未敢为之事,于是便欣然同意。
“欲为而不敢为”,这正反映了笔者的研究状况和时代的学术风气。自1971年由于工作需要以《儒林外史》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课题之后,便在研读作品的同时,对有关资料和既往的研究成果进行同步探析。笔者在这一研读过程中,深感清代几家对《儒林外史》批评较之一些笔记中的三言两语的评说尤具价值。四家评本对于书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悲一喜的批语,可谓体察入微;对于书中的字、词、句、段、回的评论又极为具体,这是理论研究文章所无法替代的,同样也不是一般“套式”赏析文章所可望其项背的。然而,这种形式的批评,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它内在的不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逐渐湮没无闻,无人问津。笔者再度拾起这种形式重操此“业”,有何家出版社愿为、敢为之出书?这就是笔者“欲为而不敢为”的缘由。正当此际,江苏古籍出版社前来以此相约,正好解脱笔者之困惑,也正显示出出版社主事者的眼识。以传统的批评形式研究古代小说,自“五四”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极为少见。在《新批儒林外史》(以下简称《新批》)问世数年之后的1993年,徐柏容在其所著《书评学》第五章第三节中说“……评点这种方式也渐被人弃而不用了”,他认为“倘若以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审美意识来运用评点方式,它还不失为一种好的、有特色的书评方式”。他又说:“这一点,也不是从来无人看到。‘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出版社想出版《水浒》的新评点本,曾印过几回试稿,可惜一直未见其蒇事。倒是1990年(应为1989年)江苏出版了陈美林的《新批儒林外史》,但愿这是评点式书评重新繁荣的一个好的开始。”也正说明拙作是近百年来尤其是近五十年来的这一形式被重新“开始”运作的成果。其后,漓江出版社组织一批作家对几种古代小说进行批评,如高晓声就将他批评的《三言精华》赠我,以作为他向我索取《新批》的回报。2001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卷中说:“陈美林在研究古人评本的同时,还借鉴这一传统形式,对《儒林外史》进行了独具特色的‘新批’。该书于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一连再版六次(连初版为七次),至今仍畅销不衰,可说是利用传统形式研究《儒林外史》的新尝试和新收获。”
“同时进行”,诚如上述引文所云,对于既往评本的研究与对于传统的批评形式的新尝试是同步进行的。如果笔者对传统的评点形式一无所知,是不敢贸然接受约稿的。其实,笔者在接受这一任务之前,就于80年代初为应邀参加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撰写了《试就卧评略论〈儒林外史〉的民族特色》,先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后又收入《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论文集。此文是在《新批》出版前发表的。其实当时的一些研究成果也陆陆续续累积并写成初稿。在笔者批评《儒林外史》的过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新批》见书后,又先后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如《新近发现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略议》(《文献》1990年第3期)、《〈儒林外史〉卧评略论》(《河北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又收入《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儒林外史〉齐评略议》(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16号,1993年11月)和《〈儒林外史〉张评略议》(《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又,以上五篇文章均收入笔者论文自选集《清凉文集》。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研究,率尔操觚鲁莽从事,随意批评,必然唐突吴敬梓、支解《儒林外史》。诚如文龙批评《金瓶梅》所言:“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所附)笔者曾总结传统批评形式的几项内在缺陷,这就是:“零散而欠系统”,“随意而欠客观”,“蹈袭而欠创新”(见笔者《重视小说评点的研究,促进小说评点的繁荣》一文,原刊于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第35号,1998年9月,又收入《清凉文集》)。笔者在进行新的尝试时,力戒此弊。除了对既往评本进行研究以外,对作者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著作也必须有深入地研究;对作品的产生时代、思想主旨、艺术特色,尤其是它的结构、讽刺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相互制约的特色,也必须有细致的探讨;对吴敬梓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学创作也要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没有这些研究和知识准备,自然也是无法运用这一形式进行“恰到好处”的批评的。而笔者在作《新批》之前,已就上述几方面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也出版了一些著作如《吴敬梓研究》等等。我想:《新批》之所以得到学界的承认和首肯,也并非轻易可以得到。正如香港《大公报》1990年6月4日《评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一文所云:“他在多年探讨《儒林外史》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小说评点之长、结合今天读者的要求,熔学术探讨和艺术鉴赏于一炉,推出他的新著,再次受到学术界的注目与好评。”题为《传统形式的新收获》的书评中也说:“陈美林是研究《儒林外史》卓有成就的学者。这部《新批》十万言的评点,处处表现批评者的审美目光以及对这部小说的系统认识。”(《中国图书评论》1993年第6期)
“地地道道的评点”。既然是运用传统形式,就必须用“旧”似“旧”。在出版社约稿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选择批评中哪些形式运作。明万历十九年(1591)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出现的批评形式有:释义、补遗、考证、论曰、音释、补注、断论等,大致可分为注解与批评两大部分。其后,出现的一些小说评本注释部分逐渐减弱,而批评部分渐次加重。大略而言,批评的形式包括序、读法、述语、缘起、弁言、小引、发凡、回前评、回后评、文中夹批、文上眉批、文旁旁批,有的作品还加圈点,等等。面对这些纷繁杂出的批评形式,笔者斟酌再三,择定前言(相当于序言、读法)、夹批、回评三种,另加注释。与编辑同志商定,即按此种形式进行。最后交稿时,出版社某负责人突然决定不要注释,便以前言、夹批、回评三种形式的《新批》呈现给读者。所有注释撤去后,有些文句必须注释,读者方能知晓,便采取变通形式,改注为批,如第七回进士王惠说:“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此处如不加注释,一般读者是难以明白王惠的信口胡柴,也难以领会作者的委婉讽刺。既然总编不要注释,只能移此注为夹批。如此作法也自有根据,因为小说“评”其实乃由“注”发展而来。如上引之万卷楼《三国志通俗演义》即评、注兼有,该书周曰校“识语”即称“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里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因此,笔者在《新批》中将个别本应纳入注释的条目改入夹批,目的仍然是为了方便读者。虽渊源有自,但仅能偶一为之,大量的注释被弃却,不能不说是一缺失。自1989年该书首次付印后历经十余年方才弥补缺憾(详下)。不过,由于笔者采用的这几种形式,确为传统批评所常见,因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6月13日发表的书评《喜读〈新批儒林外史〉》一文中肯定“《新批儒林外史》的确像评点,是地地道道的评点”。该书“采用了夹批和回末总评”,这是传统批评中“最适当的两种”;该书的“夹批主要为段、句、词加评,间有串评,回末评则为全回文字综评,并兼顾前后串述,相互配合和补充,我以为恰到好处”。
“新的思想观点,新的审美意识”。这是徐柏容后来在《书评学》提出的运用传统形式的见解。形式可以借用传统的,内涵必须现代化。他认为既往的评点,在对作品内容和艺术批评时,常“不免带有头巾气”,也“脱不开八股迂腐之气”。这也是笔者在操作之前所戒避的。在操作之前,笔者对卧本、齐本、黄本、张本分别进行了研究,在操作《新批》的同时仍不断研究这四种评本的得失,力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在《新批》“批点说明”中即明确表示“综观以上各种批评,虽然亦不乏有价值的见解,但由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诸因素,已不能以之为今日读者导读,有必要重新批评。此批点本分夹批、回评两种,着重点出作品思想内涵、分析艺术特色,偶或以史证文,亦或勾稽本事”,而其目的在于“力求有助于欣赏和研究”,也就是本文题目所显示的“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如何与作者创作意图沟“通”,用什么去“开”启读者欣赏思维?如众周知,任何时代的研究者在整理文化遗产时必须根据时代的需求、运用新的审美意识来评价;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于既往的文化遗产也同样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来选择和接受。同时,在运用传统批评形式的同时,必须赋予它以新的批评内涵。即以《儒林外交》的主旨而言,既往的评论家有多种见解,如卧评本闲斋老人序中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评评语也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一回);张评在“识语”中也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齐本东武惜红生叙同样认为“其命意,以富贵功名立为一编之局”;黄评认为“功名富贵四字开卷写一总甲,末卷写一妓女,可谓淋漓尽致矣”(五十四回)。总之,清代四种评本均将此书之主旨归结于“功名富贵”。及至“五四”运动前后,又出现“反科举”论,50年代将“反礼教”说与“反科举”说并举;到了“文革”时期又有“知识分子丑史”说;拨乱反正以后又有“痛史”说等等,不一而足。那么,我如何认识这部小说的主旨呢?我曾撰写《对〈儒林外史〉思想主题的几种不同认识》、《〈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出路的长篇小说》、《试论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及其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索》以及《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探寻》等文,虽然有的文章发表在作《新批》之前,有的发表在其后,但我的观点则是一致的,这在《新批》中也体现出来,首先在《前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反映了几乎整整一个朝代的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生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在对全书的夹批与回评中也贯串这一见解,不一一列出。又如就这部小说的结构而言,在清代学人的批评中,对这部小说的结构很少有微词,但至“五四”前后,颇有学人对之进行非难,如《缺名笔记》作者认为它的“布局,不免松懈”,武断地认为“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云云。胡适亦有类似批评。这其实是以某些西洋小说的构架观念来范围《儒林外史》,是极其欠当的。笔者在作《新批》之前,即发表《试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中人物的进退场》等文章,对这种评论有所驳正,同时对这部小说结构的创新之处有所揭示。在《新批》“前言”中也充分肯定这一结构(当然,也不讳言其不足)。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5.11)的书评中已然注意及此,说:“对于《儒林外史》的每一个章回,陈美林教授都附有回后评,……在回评中陈美林畅论各回的思想,并对回与回之间的联系,也不时加以剖析,使读者对全书前后情节的关联、整体主题的理解,更加易于把握。同时,陈氏的回评对于全书的布局也不时点到,尤其对于作品中的时间设计,在回后评中多处论及。这方面过去很多研究者注意得很不够。”再如,就人物性格描写而言,笔者也曾再三研讨文本以及前人评论,结合自己的理解,运用新的审美观念对作者所描写的人物的某些深藏不露的性格有所展现和讨论。例如对于匡超人的堕落变质,卧评首先指出是所遇匪人使然,并引司马君实“好好一个老实苍头被东坡教坏了”所云,认为匡超人“一出门即遇景、赵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进而认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自后的评本、论著,均奉此为不刊之论。笔者在80年代初发表《论〈儒林外史〉人物的性格》也强调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至巨,并引《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分析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在《新批》中也同样指出社会环境对匡超人的变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如仅强调环境的作用,未免片面,沦于简单化的社会批评。笔者同时也批出匡超人性格的双重性:“古怪”、“勤快”、“勤学”、“乖觉”、“乖巧”、“贫寒”、“孝思”等等,点出作为涉世未深的农村少年匡超人的淳朴善良与精明乖巧两方面的性格特征。对他与马纯上言谈时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心机也予揭示:“匡二之心术于此已渐露矣。”这就表明他的堕落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有他个人独特的性格恶性发展的因素。这就有别于旧评对他的分析。《新批》中类似者尚有,不再罗举。总之,形式可以是传统的,但内涵则必须是时代的。
“校点”要“考虑文学作品的特性”。评点或批点,不能仅重视“批评”而忽略“校点”。笔者在进行批评之前,先行认真校点。首先是选择底本。程晋芳在写《文木先生传》时仅有抄本而无刻本,传中所云“人争传写之”足以说明。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是书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扬州府教授时梓以行世”。金棕亭即金兆燕,其任扬州府教授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四十四年(1779)间事。但这一刻本迄今未见。目前可以见及的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前有闲斋老人序。其后虽有多种刻本问世,但均以卧本为祖本。由于卧本校刻不精,有必要重校读一过。乃以潘氏抄本、群玉斋本、齐省堂本、申报馆本、增补齐省堂本、亚乐本、张慧剑本分别为校本和参校本。而在“校”的同时也注意“点”:不仅点出句逗,还考虑文学作品的特性,体察作品的内容和人物活动的环境,再下标点。如第九回《娄公子捐金赎朋友,刘守备冒姓打船家》中,刘老爷的船家谎称:“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谁人不晓得?”娄府船家道:“娄三老爷现在我船上,你那里又冒个娄三老爷出来了?”并且“开了船板:‘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三公子走在船头上……”云云。“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一句,各家均作为作者的叙述语言标点,而《新批》本则作为小说中人物即船家的话语而加引号,这样方与下文娄四公子所说:“船家,你究竟也不该说出我家三老爷在船上,又请出与他们看,把他们扫这一场大兴,有何意思!”“船家道:‘不说’,……”云云方始吻合。又如第二回《王孝廉村学识同科,周蒙师暮年登上第》写王举人初次与老童生周进相见,对之甚为轻视,先后两句问话,在《新批》之前的各刊本均作“你想就是先生了”、“你这位先生贵姓”,笔者则点为“你,想就是先生了”、“你这位先生,贵姓?”如此,便更为显豁地表露出王举人对周童生之轻视、卑视神态了。凡此细微处,如不仔细体察作品内容,自然也难以“恰到好处”地标点。香港《大公报》书评也说“《新批》的校点,亦有足以称道之处”,“不仅分出句逗,而且考虑到文学作品的特性,充分发挥不同标点符号在文学描写方面的辅助功能。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就不再一一例举了”。
“笔墨凝练,富有色彩”。批评的语言,笔者在作《新批》之前曾斟酌再三,决定既不用旧评式的半文半白语言,尽量排除生僻典故,但也不用过俗的白话,尽量将“的了吗呢”拒之笔下,而采用近古白话,以便与《儒林外史》本身的语言风格相接近。《人民日报(海外版)》书评所言“旧评点往往东拉西扯,拖沓芜杂……以至一般读者读来难免兴味索然”。而对于《新批》的语言运用则做了充分肯定,说它“遣词用语,精扼准确;片言只语,观点鲜明;不故弄玄虚,又了无枝蔓;理论见解往往渗透在富有感情意味的分析之中,鞭辟入里的品评中常常体现出引人注意的理论色彩”;并且“留有余地,启人思索”。《对外大传播》的书评也认为笔者的评点,“文笔犀利,幽默风趣,言简意赅,妙语如珠……可谓‘评人评鬼,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常常只有寥寥数语,便得点睛之妙”。书评还举出一些例证,这里就不引用了。《新批》出版十数年中印行七次,不少读者对它的语言也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新批》是“地地道道的评点”,与其所运用的语言也大有关系。
《新批》出版后,学术界有多篇评论文章,除前文称引的香港《大公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图书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外,尚有《文教资料》(1989.6)、《文学遗产》(1990.2)、《文献》(1990.3)、《书讯报》(1990.7.2)、《明清小说研究》(1991.2)、《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2)、《古典文学知识》(1991.3)、《书与人》(1994.3)等十余种报刊予以评介。高翔《近代的初曙——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一书中,将《新批》列为参考书之一。瑞士学者安如峦在其所著《〈儒林外史〉中的隐士观念及形象》(德国·波鸿·1994)、日本学者须藤泽一在《儒林外史论》(日本汲古书院1999.8)、韩国学者赵宽熙在《儒林外史研究》(2000.9)中均有征引,并列为重要参考书之一。国立新加坡大学辜美高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商伟教授都购此书供研究生参考。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新批》面世后受到读者欢迎和学者重视的情况。(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