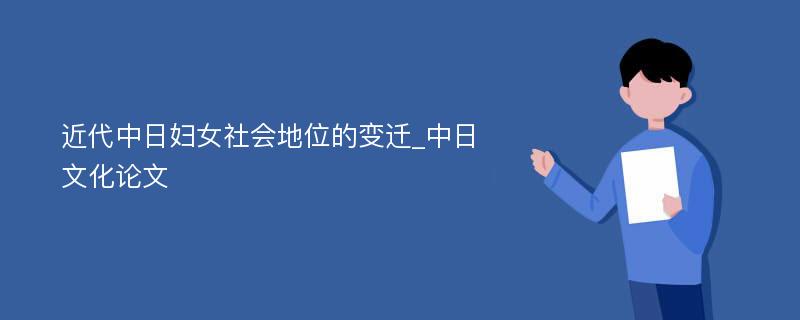
近现代中日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社会地位论文,近现代论文,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女性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深受禁锢,处于极低的社会地位。两国女性的觉醒始于近代。在20世纪的这100年来, 她们没有一天不在反思历史和社会加在她们身上的不平等,没有一天不在为自身的发展,为男女平等的实现及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努力着。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通过对两国女性为争取男女平等所经历的痛苦而漫长的历程的把握,来揭示中日两国女性在社会家庭的地位以及女性的自觉上所存在的差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明治维新”与中日两国女性的觉醒
1919年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变革,也是一次深刻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国女性“孝妇、贤妻、良母”的观念在这一剧烈的社会、思想变革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撞。它将中国妇女从几千年来封建家长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唤醒了她们作为女性的自觉。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女性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民主平等的思想,反思历史加在中国女性身上的“孝妇、贤妻、良母”这一性别角色,主张女性首先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实现婚姻自主并参与社会,而不是专门承担“孝妇、贤妻、良母”这一角色。
“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文坛上享有过盛名的女作家庐隐(注:庐隐,“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生于1899年, 代表作《海滨故人》。1934年去世。),便是这一时代进步女性的代表之一。她在《今后妇女的出路》(注:选自《庐隐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一文中为我们描述了一种家庭中理想的男女关系:家庭是男女共同组织成的,对于家庭的经济,固然应当男女分担;对于家庭的事务,也应当男女共负。……男女间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而没有依赖的生活。庐隐所代表的是在“五四”精神的洗礼下,一批大胆冲破传统的封建意识的羁绊,要求个性解放、追求理想、具有叛逆性格的知识女性。那么,她们眼中的日本女性地位及女子教育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试举例说明。
1922年春天,庐隐同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19名女学生去日本、朝鲜做毕业旅行。她们在日本体验了异国风情,也参观了一些女子学校。庐隐在她的游记散文《扶桑印影》(注:选自《庐隐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日本女子教育,最大的缺点,就是专让她做贤妻良母,而不叫她做人,在日本今日国家无事高唱太平的时候,女子的责任固然没有中国今日女子所负的责任大,然而间接于人类的幸福,多少也有些阻碍,因为人类的幸福,是根据大家平等大家自由,而日本女子贤妻良母的教育的结果,使女子退居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抹煞她们自由天赋的人格,在同一世界里同一人类中而分出高低不平的界限,人类还有幸福吗?我所以到京都市立高等女学校参观,看见她们‘贞淑’两字的校训,不禁喟然长叹了。”关于日本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她写道:“日本男女关系极不平等,……女子对男子和中国所谓三从——从父、从夫、从子的旧道德一样。所以日本的女子今日所处的地位,实在可怜,没有人格,没有自由,简直是个奴隶!”
同行的还有一位王世瑛,她不但是当时文坛知名女作家谢冰心和庐隐的好友,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一员。在她以一星女士为笔名的《旅行日记》(注:连载于1992年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中同样可以找到有关对当时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以及女子教育的描述。“日本普通女校,都注重家事。……女子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就是出嫁,服务家庭。”她们参观了一些女子学校,在那里的女教师只占一小部分。原因是当时女性在社会所处地位较低,习惯势力对女教师持怀疑态度,女性自身也都认为“服务家庭是女子唯一的天职”。
由此可以看出,在知识女性层面,中日两国女性的自我认识显示出了明显差异。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促使中国女性的觉醒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根本性的变化。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女性苦苦思索着妇女的出路问题。当时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中国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然而,简单地走出傀儡家庭难道是妇女解放的出路吗?鲁迅在他的小说《伤逝》中借主人公之口说道: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作为一位极为清醒的思想家,他以深刻的思想及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中国的娜拉在走出家庭后,如没有在社会上赢得经济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的。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促使了新一代知识女性的觉醒,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女性,但同时也显示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如果不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还相当漫长。
“文明开化”的西方清新自由的空气吹到日本妇女界是在明治时期,比中国要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女子教育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束缚女性思想言行的旧风俗、旧道德受到了冲击。启蒙思想家认为,传统道德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点无视女性的个性和要求,已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国家要发展,关键在于提高全民素质,而女子肩负教育子女的责任,所以,只有培养出有文化的母亲,才能提高一代人的文化素质。为此,明治政府采取的重要方针就是大力发展女子教育。政府在1871年向国外派遣了第一批女留学生;1872年颁布《学制》,赋予全国的女子同男子一样有同等的就学机会;在全国范围内不但建立了许多女子中等学校,也建立了不少女子高等学校。相当一批女性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为提高日本全民素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也应当看到,明治维新后的女子教育的目标是要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识的母亲,也就是“贤妻良母”教育。正如庐隐等人在游记中记载的那样,女子师范学校所设的学科有裁缝、礼节、家政、育儿。当时的教育内容也明确体现了这一以“贤妻良母”为中心的教育方针。明治以后的教育偏重女性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忽视女性作为一个社会人所负担的责任。
2、妇女地位的变化及日本女性的觉醒
明治时代,日本女性有了离婚诉讼权,妇女的法律地位比封建时代有所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由完全从属于丈夫的关系,发展为“男主外女主内”的表面平等和对立的关系。女性的生活空间拓宽了,一些女性就职于政府、学校、医院、公司。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结婚后基本都回归家庭,做了贤妻良母。
20世纪初,虽然涌现了一批以谢野晶子为代表的进步女性,她们要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号召妇女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她的《贞操论》批判了旧的婚姻道德的虚伪,不仅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周作人翻译介绍,发表于1918年的《新青年》上,对中国的妇女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这一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得到广大日本妇女的认同和参与,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妇女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在规模和影响力上都不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日本女性的觉醒和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也不如“五四”时期中国女性那么广泛和高涨。
新中国成立、日本战后与中日妇女地位的变化
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从法律上保障了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提倡女性为社会服务、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在提高妇女就业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所提倡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等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得到了贯彻执行。女性参加工作,与男子有着同样的社会地位,并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比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出许多。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她们中有科学家、干部、企业家、医生、教师、高级管理者等,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和男子一样的巨大作用。在这一历史变革中,中国女性的思想观念被赋予了时代色彩。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职业女性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参加工作,走向社会,有着独立的经济地位是进步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反之,不投身社会工作,做专职家庭主妇则是落后于时代的。
然而,我们也同样看到,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于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及个人意识之中,几千年封建思想及文化的残余是不可能通过一场变革而得到彻底消除的。表面上实现的“男女平等”其实是以女性对自身性别意识的漠视为代价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作品中恋爱题材成为禁区,京剧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几乎都是没有妻子和恋人的。中国女性以男性社会的角色标准规范自己,淡化了家庭角色意识。夫妻双方忙于工作,女性很难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孩子的教育,而家庭教育的薄弱有碍于一个民族的素质的提高。有些孩子走上了犯罪道路也与缺少母亲的悉心照顾和严格的家庭教育有关。还有,在相当长的时期,无视男女体力、生理上的差异,不现实地要求女性与男性同工同劳,让女性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对女性的解放”。
2、战后日本女性
战后日本社会历经一系列变革,妇女解放作为战后民主改革的中心课题之一,是伴随一连串的法律制度的制订而发展的。1945年妇女被赋予选举权。1946年日本女性第一次行使了选举权。战后也进行了教育改革,1945年出台了《女子教育刷新要纲》,大学共学,为女性打开了通往大学之门,将女子从贤妻良母的教育下解放了出来,与男子在同一立场接受教育。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为女性参政权的实现、接受教育的权利提供了保障。《宪法》第14条在立法上规定了妇女在社会上与男子平等,第24条规定了男女在家庭中平等。继承制度的改革也提高了女子的经济地位。
战后的民主改革使日本妇女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解放,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也依然占据统治地位,重男轻女、妇女受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妇女地位依然很低。大多数女性一旦结婚便放弃自己的工作在家当家庭妇女。男女学生的升学率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妇女就业困难,拥有文凭的女性在工作岗位一般从事从属性工作。在工资上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当前中日两国妇女面临的困境
1、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女性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由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引起了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改革给中国女性带来了更多的经济参与与机会,提供了更多新的机会和多元选择,拓宽了就业领域,强化了竞争意识,也使中国知识女性受到了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的冲击。中国女性又一次审视自己,不再一味追求表面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是苦苦地思索“女性是什么”,提出“女性的出路”问题。她们由对自己性别的模糊到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女性性别。她们既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同时也渴望做一个贤妻良母。
在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女性自觉自愿承担社会、家庭的双重责任。据1995年在对北京大学女性的问卷调查,绝大多数北大女性认为走出家庭、走向社会是实现女性自身价值的体现。她们努力充实提高自己,以求成为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的高层次完整的女性。她们既追求自己的事业,又不推卸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务。
与日本女性不同的是中国女性一直秉承“五四”精神,对自身价值在社会上的体现更为重视,有着更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我们也看到当今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带来了中国职业妇女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变化,使妇女承受来自社会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我国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不可能为每个家庭提供很多经济收入,社会服务性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家务劳动社会化明显滞后,职业妇女承受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担负着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据统计,中国女性普遍家务劳动时间比同年龄段男性多1.1~1.4个小时。事业、家庭兼顾使得许多职业女性身心疲惫,面临困惑。进入90年代,国有企业下岗女工增多,这就意味着要有一部分职业女性重归家庭,做专职家庭主妇。习惯了做职业女性的中国妇女回归家庭难免产生一种迷惘和深深的失落感。
2、当今日本妇女问题
当今日本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不仅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排名较后,甚至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高度的经济发达与整个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呈现极大反差。日本社会依然存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也落后于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家庭主妇是女性的最终和最佳选择,相夫教子是女性的美德,“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多数日本男子观念依然陈旧,结婚后,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认为妻子工作是给自己丢面子。日本社会的就业机制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大部分女性在工作中只是从事一些接接电话、打打字等从属性工作,极少有机会参与经营和管理工作,也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用人单位很少花费时间精力培养女性,使她们难以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因此,日本女性在工作中缺乏一种自我价值实现感。另外,企业在不景气时,首当其冲被裁减的还是女性。
现在日本女性的就业模式普遍呈M型,M两端是妇女就业高峰期,妇女婚前就业,结婚生小孩后退职,孩子长大后再就业。然而,再就业的日本女性由于长时间与社会脱节,往往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或符合她们专长、能发挥她们才智的工作。
近年来,日本女性要求走入社会、实现自己价值的呼声渐高。已婚有孩子的妇女外出工作人数逐年增加。1980年25岁至29岁有工作的妇女占同龄妇女的37.7%,1981年为50%。日本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的分工观念开始转变。城市家庭主妇走出家门打零工的人数年年递增。结婚退职的妇女减少,平均持续工作年数延长。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和家庭生活的电气化,以及女性独立性的增强、经济的独立,不愿结婚而选择一个人自由自在生活的职业女性增多,结婚不要孩子的家庭也比原先增加。另外,希望从事专门职业的女性增加,“长期雇佣”、“工龄工资”这一日本的雇佣体系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开始动摇。有些企业实行改革,论资排辈逐渐改为对个人能力的注重。这一变化无疑给女性带来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现在,考取某种资格、争取从事某种专门职业的女性正在增加。据统计,1996年有6%的药剂师,50%的初中、小学教师以及20%通过司法人员考试的人都是女性。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女性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变迁而逐步提高。这与两国女性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也看到,女性要想达到一个社会人、一个女人、贤妻和良母的完美结合,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种充实的、不断提高的、体现自身价值的理想生活距今还有相当的差距。妇女解放、女性地位的提高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情,也是全人类的事情,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认同和变革,有赖于男性的理解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