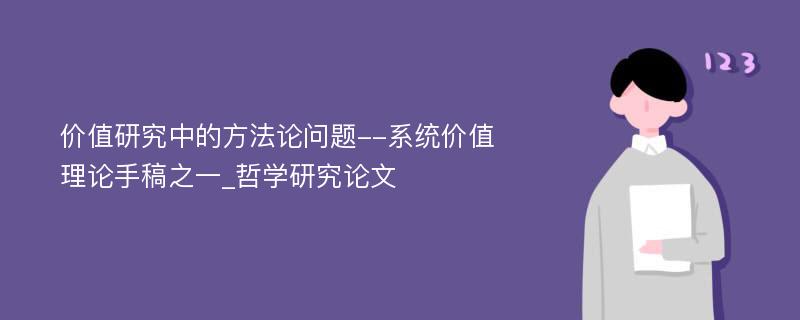
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系统价值学论稿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价值论文,系统论文,学论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价值问题的提出和价值学研究的全面展开,迄今已经十六七年了。但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我们就会遗憾地发现,在价值学和价值理论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譬如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生成变化规律、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我们几乎都没有太大的进步;我们所收获的只是将原初的1、2种价值定义,增加到10余种之多,(注:参见鲁品越:《价值的目的性定义与价值世界》,《人文杂志》1995年6期;邬焜:《一般价值哲学论纲》,《人文杂志》1997年2期。)而且目前还有继续增加之势。这样,我很担心价值学如同美学一样,将逐年积累成为一种价值定义史、价值问题学,使这些定义或问题的归纳疏理分类本身成为学问如孔乙己会“茴”字的几种写法一样,而价值学本身却将因缺少理论生机而走向衰亡。有鉴前辙,笔者认为,当前价值学研究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对现有诸多定义进行甄别评析,或苦思冥想再增添新的定义,而是要跳出现有的研究格局,对整个价值学研究本身作些反思。
上篇 价值学研究中的传统方法例析
我国较早进行价值学研究的李德顺同志,对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曾有过反思,并指出,当前“存在着一种缺少马克思气质和时代气息的、有时可称为‘前马克思式’的思维习惯,即不是站在马克思已经达到的基点上,而是总要回到马克思以前的成果和水平。”(注:见李德顺《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价值问题》,《南京社会科学:经济·哲学版》1996年1期15页。)我认为,这种“前马克思式”思维习惯,并不表现为对马克思价值学研究成果的无视——马克思毕竟没有专门进行过价值学研究——而在于对马克思系统研究方法的忽视。因此,尽管在每一篇价值研究论文中,马克思皆会数次被尊请出来,但其方法却大多是前马克思的。
首先是演绎法,或称经典演绎法,即把整个研究的起点放到对马克思有关价值问题的论述上。十多年来,几乎马克思著作中所有涉及到“价值”的地方,哪怕是只言片语,也都被发现或发掘出来,变成经典语录而一再被阐释、征引,作为各类价值定义的根据或推演的前提。其中,马克思有关“价值”的最“著名”的论述:“‘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406页。)李德顺等同志早已指出那恰恰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马克思不同意把商品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属概念的道理很清楚,因为这种“价值一般”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演绎出来的同价概念。瓦格纳企图用这种推演将“商品价值”变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派生物,以抹煞“商品价值”的特殊社会本质。因而,无论这一表述多么合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也不能拿来作为马克思对一般“价值”概念的定义。(注:参见李德顺:《价值论》15-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既然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价值”不能作为马克思价值一般定义,一些同志便试图从商品价值中推导价值一般的定义。“依据马克思抽象商品价值的思路,哲学的‘价值’范畴可界定为:客体所包含的主体的劳动、创造和奉献。”“马克思说:‘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马克思之所以不把非劳动产品视为有价值,这是因为只有劳动产品才蕴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注:见赵守运、邵希梅:《论哲学“价值”的本质属性》,《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1期71-73页。)作者的结论本身具有合理性,但却同样是靠偷换概念完成的,即把价值,具体地说是把文化价值混同于商品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人与人社会关系问题”的是商品价值,商品价值只是劳动产品内含的文化价值(物化劳动)在特殊经济环境(系统)中的获得的特殊价值属性,并不是劳动产品所必然具有的价值属性,换一种经济环境,譬如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便不具有商品价值。另有一位学者在“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关于价值问题的诸多论述”后,发现了一段“很受启发”的话:马克思在批判赛米尔·贝利时说,“……正是这位自作聪明的人,把价值变成‘物的属性’,而不是把它看成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并由此得出自己的价值定义:“所谓价值,就是客体所包含的主体与社会劳动的关系的状况”,且自信地认为,“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进行一般到个别的演绎,可以顺理成章推演出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中的价值个别概念”。(注:见方明:《对“价值概念”的哲学透视》,《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1993年3期11-12页。)事情若果真如此,我们当然应当庆幸这一“马克思的价值定义”的发现。但遗憾的是,经作者改造的这一定义,使马克思原文中“(商品)价值”为“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这一明白的表述变得使人不知所云,而且,经不住“诸多学科”中随便一种价值现象的证伪。譬如,纯粹自然美或自我牺牲行为,皆为典型的美学和伦理学中的价值现象,试问,它们中“所包含的主体与社会劳动的关系”何在?
演绎法走不通,另一些同志便径直采用归纳法,或曰经验归纳法。价值现象是人们所普遍熟悉的存在,即使毫无哲学素养的人也会从直觉中得出价值与主体需求满足有关的认识,因此“尽管在表述之间有具体的差别,甚至有原则的分歧(有人把价值当作实体,有人当作属性,有人当作关系),但在根本的思路上,他们却是共同的,基本一致的,这就是立足于客体对主体的需要的意义来理解、界定和判断价值”。(注:见潘于旭:《“需要”问题与价值论的“难点”》,《哲学研究》1993年1期47页。)前述所谓马克思关于“价值”的定义之所以一再被“发现”和滥用,其实也是用“六经注我”方法来强化这一经验性定义而已。但这一经验性定义的最大缺陷是将价值构成的主体客体化、物质化,使其在对人的价值对社会规范价值等价值现象的阐释上,面临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正如有同志所指出的:按照这一规定,“‘人的价值’这一命题”是“有明确而严格的含义的,它只能是指作为价值客体的人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他人或社会的付出和贡献,这里的‘人’只有作为客体存在,才能成为‘价值对象’或‘价值物’而具有价值,否则,它的价值是谈不到的。”(注:朱德真:《当前价值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晋阳学刊》1996年6期38页。)这样,真正应成为价值主体的人,其价值却只能在其“客体化”的付出和贡献中存在和实现,这种看似符合“社会主义”伦理的价值定义,其背后隐蔽的结论却是极不社会主义极不人道的,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意弃杀那些没有奉献“价值”的婴儿或老人。从这种客体化“效应”或“需求满足”价值定义中,进一步合乎逻辑的推导,便是将价值从人类社会推向自然界,得出泛价值论定义。如邬焜先生便在“吸取‘效应论’的合理内核”基础上,给出“价值乃是事物(物质、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观形态精神)通过内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实现的效应”的新定义,并认定物质之间同样存在价值现象。(注:见邬焜《一般价值哲学论纲》,《人文杂志》1997年2期22页。)既然在人类社会没有发生之前,宇宙中价值便早已存在了,价值便从属人的世界降格到非人的宇宙中去了,哲学价值学也大半要变成自然物理学了。
从上述“前马克思式”研究方法及影响甚大的经验性价值定义中,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克思的名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16页。)因此,作为对旧研究方法的反拨,一些同志试图从马克思实践唯物论出发,寻求新的价值定义,这便是“实践价值说”。但同样遗憾的是,由于论者也是从套用实践概念出发,因此,所给出的结论实际上仍是一种在马克思招牌下对“效应说”的翻版:“实践价值的含义是指实践对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人对客体价值的需要又引起了一种新的需要,即实践需要,改造客体的需要。人只有首先满足了第二种需要,才能使第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实践价值不同于一般的客体价值。一般的客体价值在于客体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而实践价值则在于:实践能使客体形成价值。因此,实践是一种创造价值的价值,是一切价值之母……。”(注:刘福森:《价值、主体性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研究》1993年5期46页。)实践能创造价值,实践有价值,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但不能因此把实践的价值与客体价值混同起来,把实践也归结为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实践不是主体的对象,而正是主体自身的活动、主体自身价值的体现;为满足对客体价值的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正是主体价值的付出和确证;因此,怎么能把实践说成是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对象呢?作者是因把实践“要求”置换为“需要”而陷入逻辑混乱的(“需要”主要面对客体,“要求”则兼对主体;实践通常是“要求”而不是“需要”)。同时,作者将实践作为由客体价值需要而引起的“第二种需要”,实际上倒置了因果关系,也抹煞了实践、抹煞了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因为人类所区别于动物的,正是通过实践创造了整个感性世界,也创造了属于人类的价值需要。显然,这种“实践价值说”恰恰是违背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
值得提及的是,一些同志机械套用马克思的实践学说,无限拔高实践的意义,结果却导向一种“无价值实践说”。笔者完全同意朱德真同志的批判:“这种理论打着马克思的名义,却完全违背马克思的愿意,把实践说成一种毫无功利目的、完全没有物质价值的活动,其意义只在于把人的本质对象化到客观世界中,使自然打上人的印记。……这种无功利目的、无物质世界的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实践论。”“这样的实践,不是小男孩的儿戏,就是耕费人力、财力的有害活动,是不应当提倡的。”(注:见朱德真:《当前价值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晋阳学刊》1996年6期36-37页。)的确,实践可以创造价值,也可以破坏价值。实践只有依靠一定的价值导向才能创造价值;价值论的引进,就是对传统的“认识——实践论”体系的一种反拨,它在今天尤其具有极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下篇 价值学研究中的系统方法及例析
从上述对价值学研究方法的简要分析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走出价值学研究的困境,需要进行方法论的“革命”,引进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笔者认为适宜于价值学研究并应当引进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研究商品价值时所采用的系统方法。
首先对马克思系统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前苏联学者В.п.库兹明。值得称道的是,库兹明并不是从马克思著作中所使用的“系统”、“有机系统”等概念中推导出马克思的系统思想,他“有意识地拒绝任何把现代系统方法的结论、观念和概念从外部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上去的作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留给我们关于系统性问题的现成方法论理论的专门著作,但是,他们留下了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和许多系统地具体地解决在研究社会这一整体时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范例。”(注:В.п.库兹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中的系统性原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17-18页。)正是从这些范例中,库兹明发现并创造性地总结出马克思的系统方法。
库兹明研究马克思系统方法的贡献,不在于对一般社会系统结构功能的分析上,而在于对复杂社会系统所产生的新质的揭示。库兹明指出,客体具有三种基本的质的存在形态:自然质、功能质、系统质。前两种质为我们所熟悉,譬如桌子,其构成的木料具有自然质;作为人化自然物,它具有社会功能质,即使用价值;而它的第三种质,体现为桌子商品价值的“质”,则具有某种神秘性:“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87-8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了这使商品成为神秘东西的一种新质,一种既不同于自然质,又不同于社会功能质的新质,这种新质就是社会系统质,也即体现为商品交换价值或商品价值的特质。
其实,对于商品价值的这一特质,我们早已熟知:商品价值既不取决于物的自然质,又不等于商品的功能质(使用价值),它反映了物之外,生产者之间以社会总劳动为中介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关系,从系统论角度讲,也就是整个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即商品社会系统的体现。一件劳动产品之所以具有商品价值,只是由于它不自主地处在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中罢了。因此,商品的升值与贬值,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取决于其自身自然质或功能质的变化(比如不是霉变或构造损坏),而在于整个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变化,在于商品系统变化规律价值规律。比如一件服装,一旦被视为时髦或挂上名牌,便要高价出售,尽管其内在质量不变;一台崭新的机器,置放数年之后其商品价值却因“技术折旧”而大大降低,尽管其内在质量不变;一台崭新的机器,置放数年之后其商品价值却因“技术折旧”而大大降低,尽管其功效如故。由此,便造成这种社会系统质在现象上的复杂性:它没有被物化在具体事物中,有时甚至不以具体事物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它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而只有借助于科学的系统分析方法才能揭示。正因如此,马克思的系统方法对于现代科学,尤其是对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譬如价值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假如没有系统论及系统质的知识,那么在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时,难免会走上简单化、片面化的道路,并最终导致理论的僵化,在价值学研究上同样是如此。
尽管我们从事价值研究的同志大都能自觉地划清价值与商品价值的界限,也渴望从马克思商品价值学说中获取理论营养,但由于实物中心思维方式的束缚,所以没能从马克思的研究中获得方法论启示,而是依然把价值简单地视为客体固有的自然质或社会功能质。今天,在我们重新从系统论角度考察时,便会发现传统价值学研究视界的狭隘和立论基础的僵化。任何事物身上所体现的价值,都如同商品的价值一样,具有两重性甚至多重性,在具有自然质或社会文化功能质之外,还具有社会文化系统质。即使我们把价值研究范畴缩小,囿于功利价值、效应价值,也是这样。譬如放在家中的一把普通椅子,它的结构决定了它固有的功能价值或观赏价值,椅子就是椅子,没有其它价值。但在特殊场合,譬如被放到绞架下,它便会成为杀人或救命工具,其社会价值便决非寻常。还是这把椅子,如果它曾在某位名人故居置放,或在某次重要会议上为领袖坐椅,则其社会历史价值将顿时倍增,成为珍贵的历史或革命文物。这些,与椅子本身的固有功能几乎没多大关系,其社会文化价值变化全在其所处的客观环境或社会文化系统。服装的价值同样如此。名牌服装,不仅其商品价值倍增,而且穿着者也会身价倍增。但这倍增的“身价”仅仅存在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对特定社会文化圈外的人们或根本不识名牌的人们来说,它并不存在。
由此可见,只有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我们才能够揭示出价值现象的异常复杂的构成本质及其生成变化规律。价值是伴随人类出现而出现、伴随人类系统存在而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无论我们把价值视为“善”也罢、“好”也罢、“美”也罢,它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是人类生命存在意义的体现。此前,曾有同志经过认真推导,得出价值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的命题,指出价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规定性,即人之为人的终极根据之所在。”(注:何中华:《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29页。)其实,这一命题像美学中的美一样,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约定、一种人类“语言霸权”。为什么在宇宙万灵之中,唯有人类生命有崇高价值,而猪牛羊生命的价值却在于它们对人类的“无私奉献”?对此我们无话可讲、无理可辩,只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是站在人类立场而不是站在动物立场上发言。因此,如果一定要给“元价值”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价值便是事物(包括观念形态存在的精神客体)结构、功能、属性在人类社会文化经济系统中所具有、所获得的体现人类生命本质或有利于类或个体生命存在发展的功能、属性的总和。由于这个定义是一种人类性的约定,所以,它不能从价值现象中归纳出来,也不能从经典哲学理论中推导出来。同时,也正由于价值是存在于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中,体现类生命多重本质的一个概念,由于价值的载体即事物的结构、功能或属性存在着种种差异,因此,价值的构成便不是单一的,而是系统的、多质的。通常我们所说的功利价值、效应价值只是价值的一种显性存在形态,除此之外,还有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商品价值,以及价值取向、价值环境等等许多价值概念。这些分类价值概念如同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一样,彼此之间既不同质,又不可共度,与元价值不存在种属关系,因此,也不可以从种属关系中逻辑推演出来。限于本文题旨和篇幅,对于“元价值”定义及诸多价值的分类研究只能暂付阙如。(注:本文部分观点的详尽论述请参见拙著:《审美鉴赏系统模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其下,我只简要谈一下前文已提及的“文化价值”概念,因为这一概念的欠缺是造成许多价值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作为人类世界区别于原生自然形态的一个概念,“文化”本身便是一个名词化的动词概念,其最基本或最原始内涵,即“人化”。“人化”之“文化”,所反映的是人类能动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本质,及改造与被改造、创造与被创造之主客体关系:在主体方面,“文化”是指人的创造能力和素质的教养生成;在客体方面,“文化”是指创造物所生成的属人性质。显然,无论作为主体还是作为客体之“文化”,都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或最重要的价值因素。因此,对主体来说,“文化价值”表现为类或个体的综合文化能力和素质,即通常所说的“本质力量”;对客体来说,“文化价值”则表现为物化其中的类或个体的创造性能力和素质。赋予这一特定内涵的“文化价值”概念,其实并非笔者杜撰或首创,它在一些论者笔下时常出现:“陈列在博物馆中的一把石斧,当我们的祖先出于当时的直接需要而制作它时,根本不会想到它对现代是有什么意义。但我们今天参观它时,却是当作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里程碑、文化价值的一块‘化石’来看待。”(注:方军、刘奔:《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10页。)这里的“文化价值”,就是指石斧所物化的先民们的创造性本质,只是论者对它缺少理论自觉而已。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正像商品价值不等于使用价值一样,文化价值也决不等于文化功利价值,不等于通常所说“劳动创造价值”的“价值”。通常所谓劳动创造的“价值”是指石斧满足“直接需要”的文化功利价值或使用价值,而不是石斧内含的这种文化价值。今天,虽然石斧的功利价值完全丧失,但其文化价值却日益珍贵,而那些具有极强文化功利价值的文化客体,譬如一把新的钢斧反倒可能不具有多少文化价值。这正表明了文化价值与文化功利价值在质上的区别。
由文化价值概念的引进及其与文化功利价值的“两分”,我们便很容易解决商品价值的特殊之谜。我在前文已经阐释过:“商品价值只是劳动产品内含的文化价值(物化劳动)在特殊经济环境(系统)中的获得的特殊价值属性,并不是劳动产品所必然具有的价值属性”。换言之,商品价值是文化价值在商品社会系统中所获得的一种新的系统质,是劳动产品所处系统转换而产生的新的价值形态。当商品离开商品交换系统之后,其商品价值便随之消失,但其文化价值却依然存在。两者的具体定性,主要依据劳动产品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性质。这便是系统价值学优势,它没有传统价值学中诸多“例外”、“特殊”或唯有靠偷换概念才能自圆的理论困境。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产品价值论文; 社会属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产品概念论文; 产品属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