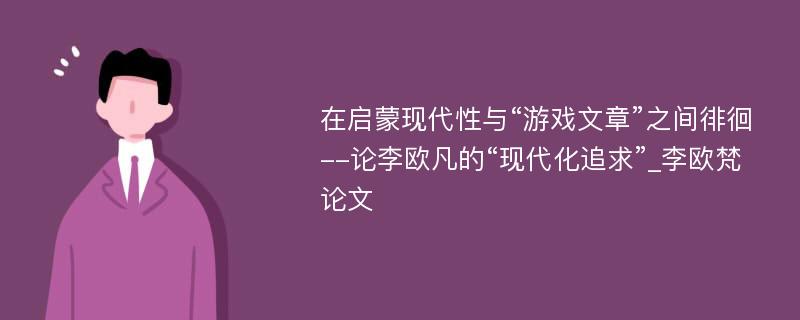
在启蒙现代性与“游戏文章”之间游移——略议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文章论文,游戏论文,略议李欧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界”的出现与启蒙“空间”的开创 “现代性”可以说是李欧梵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从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开始,再到《现代性的追求》《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都是其致力于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重面孔的研究实绩。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欧梵以现代性的多副面孔,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性的“颓废”面孔,去消解“五四”以来的“感时忧国”以及“左翼”的革命叙事。 早在李欧梵为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写“中国文学”这部分内容时,他就已经开始用“现代性的追求”来概括从1895年到1927年这三十余年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了。在李欧梵关于“现代性”的理解中,他首先注意到了“物质”对于“现代性”产生的重要意义。李欧梵所谓的现代性生活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出版印刷、文化媒介、街道建筑、商业等一系列的内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孕育、催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多数的现代中国作家,因为背负着“感时忧国”、关心民众疾苦等社会历史使命,而无暇顾及这种现代性的物质生活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五四’作家为了启蒙、为了改良、为了写实,都写了很多农村的东西,比如鲁迅就写了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沟通,这是‘五四’的思想模式决定的。可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文学模式并没有顾及它背后的产生环境,它的产生环境反而是以上海为主的半中半西的都市文化,尤其是印刷文化,只有在这里,才有所谓现代性的物质生活的基础。”①李欧梵算是比较早的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向前移至晚清的一位学者。在他看来,在清末民初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的文学已然是具备了“现代性的”若干形态了。而印刷、媒介的发展则成这种初具现代性“萌芽”的文学产生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周策纵在他的《五四运动史》中,就曾谈及晚清时的一些报刊,对于推动白话文推广以及促生“文学革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一些有学问的改革者和外国传教士们在出版杂志、报纸和发表其他作品时,开始使用白话文。”②李欧梵也认同周策纵的看法,并且在他的研究中具体地探讨了晚清以来的媒介,尤其是报业的发展,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认为,晚清以来,出现的“非官方”的报纸,不仅有为那些致力于“改良”的志士仁人提供了广开言路、广议时政的“政论性”刊物,而且在通商口岸创办的一些“非官方”的报纸,还别辟蹊径,创办了“文学副刊”。这些文学副刊,在“正刊”众议时政,进行政治的言说之余,文学副刊则在家国大事之外,开始关注“消闲”“游戏”等娱乐性的内容。随着这些文学副刊阅读者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其上刊载的文学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学”③。在这股新的“大众文学”的浪潮中,最有影响力的算是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在《新小说》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大力倡导新小说,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一个无以复加的位置,为日后的文学革命,也算是创造了重要的舆论影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量支配人道故。④ 伴随着新的媒介的产生,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日渐稳定的读者。报刊的发展与读者的要求,也培育出了一个稳定的作者群体。这些作者发展壮大,构成了李欧梵所说的“报刊文人”,这些“报刊文人”的产生,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铺垫了重要的基础,“在现代白话文文学随着‘文学革命’出现之前,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已经取道报业的后门,偷偷潜入通商口岸的文学界。随报附送的或是独立的文学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读者群不断扩大,为‘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的人开拓了一个市场。”⑤ 在晚清文学中,社会小说是晚清社会的重要小说样式。社会小说抨击时政、揭露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在批判晚清社会、政治的乱象与病象的过程中,也不忘以一种“乌托邦”想象,呼吁晚清政府改革弊制,挽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在对社会的批判与讽刺中,晚清一代的作家身上,也渐渐地凝聚起了一种历史使命或社会责任感,“清末小说的主题是社会讽刺,对社会和政治所持的批评观念也融入作家内心情感所具有的一种主体自觉之中。社会的基调和情感的旋律通常结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情绪上的高度,并且证实作者目的的严肃性。”⑥这种创作的“严肃性”在晚清一代好多作家身上都有体现,即便是那些写言情小说的通俗作家,也有着浓烈的家国情怀。⑦尽管,李欧梵认为,这种“严肃性”并未成为多数言情作家的创作态度。但是,这种“严肃性”还是为日后的“五四”新文学倡导改良社会、革新政治留下了一份生发的土壤。《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商业气息与通俗趣味的夹缝中创办起来的。随着《新青年》相继而起的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学灯》、《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一系列倡导新文学、刊发新文学的文学杂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晚清时代的报业发展,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媒介”和平台。“五四”新文学也开始逐渐引领起了当时的文学潮流。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壮大,围绕在不同杂志之间的作家、学者,也因为各自的思想观念、文学见解、社会理想等方面的不同,进行着组合聚集,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借用李欧梵的说法,就是“文学界”在这个时期内已经开始形成、出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文学界”的出现,是晚清报业发展为“五四”新文学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和贡献。“媒介”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它为“五四”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言论“公共空间”和发展“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以“媒介”为核心的言论“空间”形成,就为“五四”新文学获取自身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平台。与此同时,“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使文学成为一种在商业上确实可行的行业。他们是现代文人直接的原型。新文学运动表示了原始文人大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⑧ “文学界”的出现,意味着“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壮大,“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都“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他们心怀“感时忧国”的精神,针砭时弊,图新政治。爱之深,恨之切,这些作家在批评时政的文章中,难免有时用语过于激烈、激进,其所言所想,已然超越了当政者所能接受的“言论尺度”。辛亥革命终结了晚清政府的统治。新生的民国政府未等站稳脚跟,就为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搞得名存实亡。虽然民国初年,在政治上呈现出了一片混乱的战局,但也正是这个军阀混战的动荡时代,为“五四”新文学作家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言论空间”。然而,当北伐战争的结束,国民政府再次“统一”了全国,政治统治、控制的有效性的范围和强度,都较北洋军阀时代更大、更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对于“言论空间”的控制和审查日益加强。“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言论空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保持晚清以来开创的“批评空间”,就是李欧梵关注的“空间”的现代性的第二个问题。 二、“批评空间”的开创:从“启蒙”向“游戏文章”的游移 李欧梵以《申报·自由谈》为例,详细探讨了“批评空间”(“公共空间”)⑨的开创及其被压缩的过程。李欧梵认为,《申报·自由谈》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论政”风气的影响。虽然是受到了“文人论政”之风的影响,但是《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仍然不是那种金刚怒目、愤世嫉俗式的风格,它的风格从其设定的专栏的名称上就可窥见一斑。这些专栏的名称主要有“新乐府”“新丑史”“新笑史”“海外奇谈”“忽发奇想”“轩渠杂录”“新回文诗”等,出现次数最多的专栏则是“游戏文章”⑩从专栏的名称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字该是轻松随意,在嬉笑中见讥讽,在戏谑中见批评。这些嬉笑怒骂的文字,很受当时读者的欢迎,它表明了晚清一代学人与民众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切。(11)李欧梵则认为,这些“游戏文章”代表了晚清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这些“游戏文章”的论述方式,也标志着知识分子开始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社会’这个新的领域,而将之与民风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已经在开创一种新的社会空间,而从这种新的空间基础上建立‘新民’和新国家的思想,所以梁启超早年才把小说和群治的关系列为重点。”(12)李欧梵认为,到了民国初年,“游戏文章”的言论尺度越来越大,其针砭时弊内容猛烈,用语辛辣,嘲讽尖锐,甚至直指袁世凯和议会: 巍巍议院,二次成立,衮衮诸公,以身作则,不有表示,勿乃旷职。嗟我国会,萎靡不振,已非一日,徒托空言,亦复何益?为此登场,涂其新剧,大声疾呼,攘臂而出,神威大震,圣武莫匹。物虽无知,诚亦能格,桌椅翻身,墨盒生翼,欢声如雷,以手加额,容光焕发,国旗同色,牺牲同命,尚且勿恤,区区头颅,又何足惜。流血主义,实有价值,唯其如此,乃显能力,匪鸡与狗,匪蚌与鹬。堂哉皇哉,一般政客,口号文明,手造法律,代表国民,万中选一,不畏神圣,施以踣击,岂非英雄,岂非豪杰,凡我同胞,能不啧啧……唯我国会,世界独一,谓予不信,请观战绩。(13) 从上面援引的文字中,放言论政者的言语相当激烈辛辣,极尽嘲讽之辞。即便如此,这样的文字,依然能够见报,我们也足可见到当时言论尺度之大胆,言论环境之宽松自由。放在今日,亦不敢奢望。所以,李欧梵认为,这种“游戏文章”“已经造成了一种公论,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公开政治论坛,也几乎创立了‘言者无罪’的传统。”(14)在笔者看来,尽管这些“游戏文章”尖锐地讽喻、批评时政,剑指执政当局的最高层,其勇气可嘉,其对呼唤民众的觉醒也有作用。但是,“游戏文章”毕竟是“曲笔”,它还未能达到“直言”的程度,其受到的限制依然存在,所以,笔者不大苟同李欧梵据此种“言者无罪”的传统进行的一番猜测。李欧梵甚至还认为,这样“言者无罪”的传统若发展下去,“中国现代报纸所能扮演的‘公共空间’角色可能绝不较美国独立前的新英格兰报纸为逊色。”(15)但是,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胜利,军阀割据的局面结束,全国再度“统一”。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国民党开始加强对言论的审查,由晚清“游戏文章”所开启的“批评空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言论的尺度逐渐收紧,“批评空间”日益缩小。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反抗。而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则成为了他与国民党的言论审查制度进行反抗的武器。但是,在李欧梵看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所开启的这个反抗的传统,不仅没有继续扩大晚清“游戏文章”开创的“批评空间”,反而让“公共空间”的言论自由尺度进一步丧失。 三、是“破坏”,还是开创?:鲁迅的“自由谈” 在李欧梵看来,鲁迅在给《申报·自由谈》投稿之前,根本不知道“自由谈”中文章的主体风格是怎样的。所以,鲁迅给“自由谈”写的杂文并未延续以前“游戏文章”的风格,是一种“创举”。“创举”一词,在此似乎并无褒奖之意。李欧梵只是想借此语,委婉地批评鲁迅的杂文,不顾“自由谈”的论政传统,更不顾晚清“游戏文章”开创的来之不易的“批评空间”。然而,鲁迅却对李欧梵念兹在兹的“批评空间”和“游戏文章”多有不满。他在《伪自由书》的前记中,就表达过自己对“自由谈”时评风格的看法:“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很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绝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16)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不仅是知道“自由谈”的文章风格,他也深知当时“言论空间”所受到的诸多审查与限制。既然对于时事的限制和杂志的风格都已经是心知肚明,那么鲁迅为何却要执意去写那些带有“创举”意义的杂文呢?对此,鲁迅也有一番夫子自道: 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17) 鲁迅投稿的目的,已经在“前记”中说得清楚明白,为“朋友”,为“寂寞者以呐喊”。为朋友,主要是受郁达夫之邀,帮黎烈文的忙。(18)“为寂寞者以呐喊”,就是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寂寞者”也好,“沉默的大多数”也罢,他们几乎都是在这些“媒体”上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人,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鲁迅所要做的就是要为“寂寞者”言。(19)在鲁迅看来,为“寂寞者”言,就是不唠叨,就是要直来直去,要言不烦,将要表达的想法说得清楚明白,打到痛处,击到要害。而这种“不留情面”的风格,也是符合鲁迅本人的“老脾气”的。“不留情面”难免就要触及某些人的利益,伤及某些人的情面,更是会发生在一些国民党官员的身上。触及到了当政者的利益与情面,文章自然就要被“审查”。李欧梵以鲁迅与国民党《中央日报》副主编王平陵笔战为例,说明鲁迅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审查,也不能“挺身而出”,也不能“秉笔直书”。李欧梵引了王平陵“回骂”鲁迅的文字,说明鲁迅的“弯曲”和“装腔作势”,王平陵骂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作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弯儿。”(20),接着他又引了鲁迅回应王平陵的话:“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21)引了鲁迅与王平陵的论战文字之后,李欧梵接着说道:“这话(用的是他一贯的譬喻技巧)说得十分动人,自比植物,但是也自承说话弯曲,因为,如果痛快地直说,就不必在文中玩弄各种文字的技巧了。而文字——特别是鲁迅的文字——和它所描述的现实的关系,不可能完全是直接透明的‘反映’,而必须是‘折射’的,弯曲的。”(22)然而,当我们回头看看鲁迅与王平陵论争文章的全貌后,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不是在“弯曲”“吞吞吐吐”,而是在更大的问题上,那就是如何看待“左翼”的问题上。这个最为重要的矛盾与分歧,却为李欧梵所忽略掉了。 在鲁迅看来,不通的文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者写得不通,一种是“不准通”“不敢通”或“不愿通”。前者是能力水平问题,后者是客观限制或主观态度问题。鲁迅在《不通两种》一文中,想批评的是“不准通”。他借《大晚报》上一篇“不通”的新闻报道,批评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制度。他说:“希奇的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不过其实也并非作者的不通,大抵倒是恐怕‘不准通’,因而就‘不敢通’了的缘故。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而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方法,来粉饰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23)在这里,鲁迅不仅“直接”批评了国民党的文化审查制度,还言及了“为艺术而艺术”家、“民族主义文学”者。“民族主义文学”是国民党提出的一种官方文学主张,这种文学主张提出后,遭到了“左翼”文学的批评。到此,问题的实质就出来了:国民党与“左翼”。王平陵作为国民党的官员,在回应鲁迅的文章,自然能够抓到问题的关键: 听说现在的鲁迅先生已跑到十字街头,站在革命的队伍里去了。那么,像他这种有闲阶级的幽默的作风,严格言之,实在不革命。我以为也应该转变一下才是!譬如: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作势,吞吞吐吐,打这么多弯儿。在他最近所处的环境,自然是除了那些恭颂苏联德政的献词之外,便没有更通的文艺的……不过,现在最通的文艺,是不是仅有那些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不免还是疑问。如果先生们真是为着解放劳苦大众而呐喊,犹可说也;假使,仅仅是为着个人的出路,故意制造一块容易招摇的金子商标,以资号召而已。那么,我就看不出先生们的苦心孤行,比到被你们所不齿的第三种人,以及民族主义文艺者,究竟是高多少。(24) 在回应的文字中,王平陵终于说出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站在“十字街头”的“革命队伍”,还有彼时中国共产党推崇的“苏联”。鲁迅与王平陵,共产党与国民党,苏联与英美(25),都是彼此对立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与王平陵之间的笔战,就不再是单一的“批评空间”的问题了。所以,李欧梵说鲁迅在“自由谈”上的文章破坏了晚清“游戏文章”开创的“批评空间”,就不在是一个单纯的言论“自由”的问题了。在这里,李欧梵对“批评空间”的看法,已经裹挟了他对“左翼中国”和“左翼文学”的认识。在他试图对“左翼中国”和“左翼文学”进行消解的时候,他才会对鲁迅在“自由谈”上的杂文发出这样的疑问:“鲁迅的《伪自由书》,是否为当时的‘公共空间’争取到一点自由?他的作品是否有助于公共空间的开拓?”“因为当年的上海文坛上个人恩怨太多,而鲁迅花在这方面的笔墨也太重,骂人有时候也太过刻薄。问题是:骂完国民党文人智慧,是否能在其压制下争取到多一点言论的空间?”(26)禁锢只有靠反抗才能挣脱。言论自由也好,“批评空间”“公共空间”也罢,都是靠争取来的,反抗是对抗压制最好的手方式。鲁迅所以在写给“自由谈”的文章中“弯曲”,就是因为官方的新闻、文化审查制度。等到没有了这个审查制度,“弯曲”似乎也就会自然消失了。鲁迅的“弯曲”不就是李欧梵所说的“折射”吗?如此地“弯曲”的文字,还要被审查制度删减,不去反抗,还要继续“弯曲”“折射”到何种程度为止呢?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李欧梵批评鲁迅对由晚清“游戏文章”开创的“批评空间”的非建设性作用,其指向的还远不只是鲁迅一个人,他指向的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在构建现代中国文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激进主义”态度。“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精英主义”的姿态期望以文学、文化来启蒙民众,进而达到变革社会政治的目的。但在,李欧梵看来,“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态度,实在是夸大了知识分子自身在社会政治中的作用,“总觉得自己可以说大话、成大事,反而不能自安于社会边缘、像早期‘游戏文章’的作者们一样,一面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来作时政风尚的批评”,一方面也藉游戏和幻想的文体来参加‘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缔造”;同时,他还认为,“五四”知识分子以“呐喊”式的文学,批评时政、启蒙民众的做法,对于文学自身功用的理解也是“激进”的,“文字不是枪杆,它的作用在于营造一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从而逐渐在文化上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27)李欧梵之所以会有上述的看法和立场,这都源自于他对“革命”的看法。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的革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革命,其面对固有的社会文化、现实政治,采取的都是一种“激进”(28)的态度。而这种“激进”的态度,无疑会在冲击破坏旧有体制的过程中,将旧有体制中已经存在的一些可以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一起摧毁了。在李欧梵的理解中,激进的革命不如温和的改良好。正是这种“改良主义”的姿态,才会让他对由晚清“游戏文章”开创的“批评空间”如此的看重,对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的反抗姿态采取批评的态度。 ①李欧梵,季进:《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86页。 ③李欧梵认为:这种“新的‘大众文学’就是在这些文学副刊与‘小报’中成长、兴旺的。担任编辑的是一群可以被称为‘报刊文人’的人,他们对西方文学和外语略有认识,但却有着更为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这些刊物的特色是充斥着过量的假翻译和诗歌,还有那些宣称要唤醒民众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但同时也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文章。”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5页。 ④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⑤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6页。同时,李欧梵还认为,“清末文学刊物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给‘小说’以主导地位。无论是杂志的命名还是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的体裁,小说都占据首要位置。”参见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81页。学者孟悦在《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如何利用现代的技术和文化资本,将印刷也转换为出版业的过程。孟悦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为什么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媒介,在推动“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作用。参见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⑥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88页。 ⑦开启了言情小说先河的吴沃尧,在《论言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一文中,曾经说过:“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并不是那俗人说的‘情窦初开’那个‘情’字。要知俗人说的情,单要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那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作痴。跟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费用其情的,那个只可叫作魔。……有许多些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 ⑧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6页。在李欧梵的理解中,在传统社会中,所谓“原始文人”文人的称谓带来的只是社会声誉,而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一个诗人或一个散文家从不用他的作品赚钱,他也不愿意为了商业用途而写作。因此,文人最高尚的形式只是一个士大夫,有着较高雅及文学性的一面,而文学更经常地只不过是一种消遣或嗜好。”参见《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⑨李欧梵认为,“公共空间”的“公共”,“在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而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参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02页。 ⑩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02页。 (11)李欧梵认为,晚清的作者用“游戏文章”的形式来诉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从‘正面’来说,如何‘造就新国民’——如何营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正是梁启超这一代苦苦思索的命题,而梁氏用以传播新国民思想的工具就是民办的报纸。不到十年工夫,这一种思潮已经时髦到可以作为报纸副刊游戏文章的题材,这也足证当时新潮流影响之速。”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07页。 (12)(13)(14)(15)(22)(26)(27)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04页,第104页,第104页,第110页,第115页,第115、116页,第117页。 (16)(17)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第4页。 (18)鲁迅说过,给《自由谈》写文章,主要是因为郁达夫相邀,“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人地生疏,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见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9)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见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 (20)(24)王平陵:《“最通的”文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页,第24页。 (21)(23)鲁迅:《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页,第23页。 (25)王平陵在《“最通的”文艺》一文中还说,苏联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我们回溯到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文学。音乐、美术、哲学、科学,那一件不是已经达到国际文化的水准。他们有了这些充实的根基,才能产生现在这些学有根基的领袖。我们仅仅是渴慕人家的成功而不知道努力文化的根本的建设。”但王平陵的“文化建设”,是直接指向欧美的,“欧美的名著,在中国是否能有一册比较可靠的译本,文艺上的各种派别,各种主义,我们是否都拿出一种代表作”,参见王平陵:《“最通的”文艺》,《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8)在李欧梵看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在文化媒体上比晚清发达繁荣得多,都市中的中产阶级读者也更多,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也都具备,但是却没有产生一个“公民社会”。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从鲁迅的杂文中得到印证:这种两极化的心态——把光明与黑暗截然划为两届作强烈的对比,把好人和坏人、左翼与右翼截然区分,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做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参见: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17页。李欧梵还认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加入文坛的青年,他们对旧有体制和旧文化的态度,同样是激进的,而“《新青年》的出版使他们的激进主义具体化和普及化。每一个人都在读这本杂志,大量别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杂志开始出现。日积月累的创作欲使他们爆裂。”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家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5页。标签:李欧梵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晚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