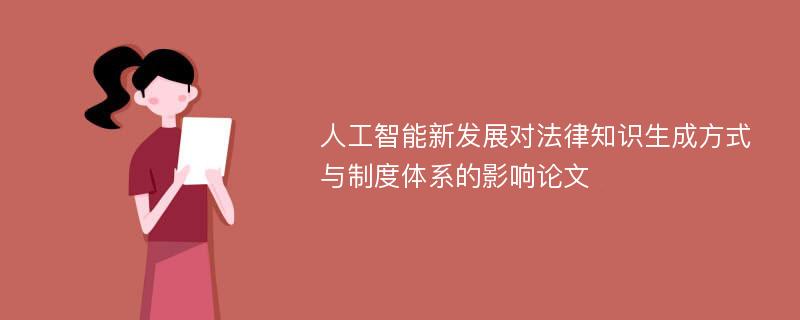
人工智能新发展对法律知识生成方式与制度体系的影响
高志明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 人工智能实际是信息与知识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产物,是信息与知识组织方式发生的巨大变革。人工智能新发展可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变化,包括大量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将被重新定义,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亦隐藏着巨大社会风险。作为人类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知识系统,可能出现本体论、认知论、发展论、方法论等方面的转变,可能出现向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物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等自然科学乃至未来学等学科交叉与整合的转向,可能出现基于大数据库、大信息库、大知识库分析而进行充分信息条件下研判的方式转型。人工智能对现代法律制度体系的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可能至少包括法律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利体系等,网信立法一方面要促进现在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要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予以充分考量,特别是要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关 键 词] 人工智能;法律知识系统;知识生成方式;制度体系
人类祖先发明了可以记录与传播的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符号系统是人与人建立联系的纽带,藉此符号系统人的意识世界与物质世界建立起联系,也藉此符号系统人与人之间得以沟通与交流各自的认知(知识),而基于各种符号表征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信息流,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意义之网”。而知识、信息的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媒介,计算机使知识、信息可以存储在电子或光子载体上,并能进行高速运算;同时,互联网技术以能量场的方式解决了信息传递的空间效率问题,成为信息、知识传递的高效媒介。人工智能随着人类电子化数据的积累与信息链接效率的提高而兴起,并对人类的知识系统包括法律知识系统产生深刻影响。
一、人工智能的新发展
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来界定,一般认为,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也研究其他生物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应用系统的一门新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语言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专家系统和机器人等。[1]6人工智能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约在20世纪30至60年代,人们开始探索将知识、信息转换到电子计算机中,并利用电子的正负运动进行运算。1950年,阿兰·麦席森·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即判定机器是否属于人工智能的主要标准:如果第三者无法辨别人类与人工智能机器反应的差别,就可以论断该机器具备人工智能。1956年8月达特矛斯会议确立了人工智能的概念,此后的十几年时间是人工智能掀起的第一波浪潮。此后人工智能经过了两波的起伏发展。互联网经过21世纪初10多年的发展,使得以前有限的、静态的知识、信息变成无限的、动态演变的知识、信息,大数据库、大信息库、大知识库日趋完备,与此同时,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也进一步发展,更加先进的通信技术加速了世界上人与人的联结,信息生产力巨幅提升,人们通过信息联结的信息生产关系也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人工智能应时而生。现在的人工智能通过网络信息抓取与分析而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甚至深度学习能力,语音识别技术、图像识别技术、新一代专家系统、人工智能写作技术等体现了人工智能挑战人类脑力劳动的强大优势。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江苏省历来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与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院大所均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跃、成效显著。
人工智能实际是信息与知识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产物,而互联网的发展使知识、信息等又转换成电磁、光等形式,通过互联网又形成了大数据库,人类知识、信息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算法,可以理解为针对特定问题进行识别、运算、解答、决策的方法与程序。现在的人工智能是知识生产力的解放,是以前人类知识组织形式的解构与新的建构。现在人工智能在知识量、信息量层面已经有了基础,技术研发者要做的主要是不断改进算法,解决机器模拟人的智能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解决机器深度学习中信息表征、模拟神经元联结、进化、不确定性与不同情境下的类推等问题。[2]66,67
人工智能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工业革命将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信息技术把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人工智能则是要将人类从繁重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如今,人工智能新技术结合教育、医疗、家居、机器人、电子商务等各行各业,正走入大众生活,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3]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认为,未来30年,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等领域要重新定义:对于零售业,以前零售是卖货,未来零售是做服务,所有物流、产品流、经营流、服务流,必须合在一起;对于制造业,新制造将会彻底改变原来的流水线、标准化、规模化、集装箱、低成本,人工智能使机器越来越聪明,机器会越来越会自我学习,定制化则是将来的趋势;对于金融业,未来新金融必须建立各种各样以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4]
还有一种思路是,直接创设新的法律规则,把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称为“电子人”或“智能体”。比如,2016年5月31日,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动议,要求欧盟委员会把正在不断增长的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工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electronic persons)”,并赋予这些机器人依法享有著作权、劳动权等“特定的权利与义务”,也建议为智能自动化机器人设立一个登记册,以便为这些机器人开设涵盖法律责任(包括依法缴税、享有现金交易权、领取养老金等)的资金账户[10]。这一动议颇具未来性,但是,界定人工智能为“电子人”只是给了人工智能一个“名份”,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电子人”的权利根本没法落实。
科技在人类的文明进步中总是扮演着最活跃、最革命的角色,人工智能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加大了人类危害自身的可能性,这即是技术的负面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的失控。传统社会治理体系无力解决工业社会过度发展而产生的社会问题,这即是法律的确定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的背离。[5]史蒂芬·霍金于2017年11月6日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网络高峰会上表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潜力,像是协助复原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破坏、根除贫穷与疾病问题,并“改造”社会每一个层面,但他也承认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除非我们事先做好准备并避免潜在风险,否则人工智能可能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糟的事件。因为它会带来危险,像是制造致命的自主武器,或是成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亦可能对经济造成巨大破坏。”[6]关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确实不可等闲视之,主要是要防止人们滥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行为。技术本身并没有价值判断,而关键在于人们对技术的利用、在于人们怎么样利用技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秋水》)我们不是人工智能,又怎么可能知道具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会不会伤害人类呢?是非善恶的分别心属于人类,智能体是否也会具有这种价值判断?技术一般来说都是中性的、不涉及价值判断,而人对技术的使用往往具有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善者用之则为善,恶者用之则为恶。因而,问题不在于人工智能,而在于人类自身。当然,如果“超人类智能”一旦被滥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也是巨大的,甚至远远超过原子弹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实际上,我们要规范的是人们的技术利用行为,而不是简单规制技术本身,当然,也要防范技术不确定对人类带来的安全风险。
就法律主体制度而言,现在一些学者讨论可否赋予人工智能以一种法律人格,比如叫作“电子人”或“智能体”。人工智能体现为抽象的“虚拟人”和具身的“机器人”,但实质都是由一定的计算机程序所控制。人工智能能否具有法律人格,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自主意识”。如果人工智能在人的可控范围内,则人工智能可被视为物,包括虚拟物与具体物,其不具有法律人格,只能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或权利的客体。从这种界定上讲,所谓人工智能侵权实际是个伪命题,只能说是计算机程序存在“bug”、出了问题,或者用户操作不当,要承担侵权责任的不可能是人工智能本身,而应当按照产品质量责任进行处理。但是如果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深度学习能力,乃至具有了“自主意识”,可以与人类“平起平坐”,那么或许可以赋予这种“智能体”以法律人格。但是,一旦人工智能具有“超人类智能”,人类的整体智能面对如此“超人”也要“甘拜下风”,那可怎么办?实际这个问题就没法讨论下去了,因为如此这般的话,可能要讨论的就不是这种“超人类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的问题了,而是这种人工智能已经演变成“智神”了,已经步入神坛,人类恐怕只有顶礼膜拜的份了。实际上,后面的情况是人类不希望出现的,人类必须在可控范围内发展人工智能,否则出现人工智能失控于人类的情况,法律恐怕也早已显得苍白无力。
人工智能新发展对法学研究职业将带来冲击。法学研究是知识事业、知识工作,而基于形式逻辑思维的所谓理性建构的法学大厦,在人工智能面前可能脆弱不堪。因为在这方面,人工智能可能比人的学习能力、分析研究能力更胜许多倍,因为人工智能有大数据库、大信息库、大知识库,人脑对知识的学习、记忆与存储能力有限,而且人脑神经元细胞的逻辑运算能力也比不上人工智能的电子正负运行物理逻辑。易言之,人脑在知识与逻辑的处理方面没法与人工智能抗衡。将来的法学研究行为未必还依赖于职业的学者、专家,可能会出现一种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趋势,而研究成果的质量不仅不打折扣,还可能比现在更加优良。特别是一些基于数据、信息、知识分析进行的法学研究,人工智能的优势更加明显,论文机器人可能比专家还要“专家”。但是,超越可以表征的知识与逻辑的问题,人工智能一时恐怕还不能取代人的研究。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强大的专家系统,取代传统知识性研究、逻辑性研究的同时,也将开拓法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维度与新境界,法学理论研究可能会出现关注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本身与规律的转向。
二、人工智能引发法律知识生成方式新转变
在司法领域,司法知识、信息的生成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革,与互联网、大数据结合的“智慧检务”“智慧法院”正在兴起。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把现代科技作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新引擎”,检察信息化建设走过了“数字检务”“网络检务”“信息检务”阶段,已经升级步入了“智慧检务”阶段。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应用统一业务应用信息系统,以司法办案为中心,覆盖所有检察业务,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各项业务办案实现一个标准、一个程序、一个平台,实现了办案信息网上录入、办案流程网上管理、办案活动网上监督、办案数据网上统计。[8]“智慧法院”充分利用司法大数据,可以实现“智慧审判”。最高人民法院优化完善形成了五大网系:法院专网贯通至全国3523家法院和9277个派出法庭,实现全国法院干警一张网办案、办公;基于法院专网建设专有云,为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法院提供资源服务;依托互联网建设法院开放云,全面支撑司法公开和诉讼服务;按需拓展外部专网、移动专网、涉密网资源。[9]国家司法审判信息资源库已汇聚多类信息资源,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司法审判信息资源库。在审判执行数据方面,汇集全国法院1.22亿案件数据、800余万份电子档案和600余万份电子卷宗;外部数据方面,实现了对全国公民身份信息、道路交通事故数据、组织机构代码信息、律师信息、渔船信息等外部数据协同应用。[9]当然,人工智能在司法当中,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恐怕很难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决者,否则,就成了新型的机械式司法。
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对法学的知识生产与获取方式将会带来巨大变革。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类认知的升级经历了三个知识公式:中世纪的欧洲获取知识的公式是:知识=经文×逻辑,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就阅读相关经文,再用逻辑来理解经文的确切含义;科学革命后获取知识的公式是:知识=实证数据×数学,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就收集相关的实证数据,再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人文主义时期获取伦理知识的公式是:知识=体验×敏感性,体验是一种主观现象,包括知觉、情绪和想法,敏感性包括注意到自己的知觉、情绪和想法,以及允许这些知觉、情绪和想法影响自己,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需要连接到自己内心的体验,并以敏感性来观察它们。[7]213,21418世纪人文主义的兴起,使人类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走向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而21世纪数据主义则可能从以人为中心转向以数据为中心。[7]352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技术革命之后人类获取知识的公式就是:知识=大数据×算法。未来法学知识的生成将很可能高度依赖大数据与相应的算法,而不再单纯是各种教条,也不再简单考虑人情与舆情等人文与社会因素。
人工智能浪潮来势汹涌,人文法学、社科法学或许不足以面对人工智能将要带来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法学研究也可能会出现“自科法学”这一转向,一种基于技术理性的法学研究转向可能会应运而生。法学研究需要各种视角,“自科法学”并非要取代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与范式,而是在以往法学研究方法与范式的基础上,向前更进一步,以使法学研究更好地适应技术突飞猛进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当然,“自科法学”仅是一种初步的提法,其本身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需要在法学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中逐步实现其理论自洽。包括自然科学乃至各种知见本身也存在局限,但又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不断突破各种局限,去接近所谓真理性的认知。
法律是一种知识体系,逻辑固然在法律实践中很重要,但法律的生命还在于经验甚至还有具象与直觉。法律制度往往都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若将人工智能仅仅视为一种技术,则对现在的法律制度体系难以造出根本性冲击。易言之,技术发展虽然会影响社会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渐进过程的,我们不能简单地随着技术的变革而轻易改变既成规则,而一般应当以法的适用中的法律方法来协调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法律作为一种规范体系,也只是人类的一种有限知识;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也是一种只能研究有限问题的学问;法治,作为一种治世之法,也只是一种有限的方法。技术本身也有生命周期,上一波还叫互联网+、O2O,转瞬之间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又风潮袭来,下一波又会是一个什么技术概念取代现有的技术概念?人工智能恐怕也不是人类“最后的发明”,只不过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而已,远不是人类技术发展的终点。实际上,现在的人工智能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也还是在不断演进中的技术。因而,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法律先“应作如是观”,关注其对社会的影响,可视情况先以政策对其发展进行调节。而从未来人工智能对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可能性来看,人工智能对现代法律制度的影响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可能至少包括法律主体制度、客体制度、权利体系等。所以,法律一方面要促进现在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要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确定性予以充分考量,特别是要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三、人工智能引发法律制度体系新变革
严寒的冬季已是冰封水面,为了让鱼儿安全越冬,我们建议在结冰前把增氧机移向料台附近,每天定时开机半小时左右,这样以保证增氧机附近即使在严寒的冬季也不结冰,以达到冰下水体长期通风换气、提高水体溶氧的作用。另外,对渗水的池塘,要定时加注新水,保证冰下水的深度最好在1~1.5m之间。加水时一定要从下而上加水,切莫形成二茬冰,防止鱼类冻伤冻死。同时在大雪天气要合理地清扫积雪,保证冰下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
四、诱杀害虫。即利用害虫对某种物质或条件的强烈趋向进行诱杀,如利用灯火诱杀小蛾、金龟子成虫,饵木诱杀天牛、象鼻虫,用昆虫性诱剂诱杀害虫,主要有桃小食心虫、金纹细蛾、梨小食心虫、苹果小卷叶蛾、桃蛀螟等。
月亮已转到西天,无牵无挂的,好像随时都会落下去。隔河石浮村那边,破空传来几声嘹亮的鸡鸣。我朝那边望过去,富水河上水汽蒸腾,一片苍茫。我感觉筋疲力尽,浑身酸软,就瘫倒在毛毛的新坟上,昏昏沉沉地困着了。
就法律保护的对象或权利客体制度而言,人工智能应当属于法律保护的对象或财产权客体,这方面应当没有多少异议,因而无需多论。问题是,人工智能也能成为“造物主”,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创造物)又要如何保护?这方面讨论较多的就是人工智能“写作”的生成物或创作物是否享有著作权的问题。尽管一般把著作权与版权等同,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即版权,但是应当区分著作权当中的作者权与版权的不同;作者权是大陆法系的传统,保护的是基于作者创作行为产生的权利,包括基于创作行为产生的身份权与财产权;而版权是英美法系的传统,重在保护作品版本涉及的经济利益,而不特别关注作者的身份利益。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类似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这个“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别人家的“孩子”还好看、还可爱、还聪明,那么当然也要获得保护。可是,这个“孩子”并非自然“孕育(创作)”而来,其“父母”是谁?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是否享有著作权的问题可以分解为:是否保护其中涉及的作者利益与版本利益两个层面的问题。换言之,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这一问题:一是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值不值得保护的问题,二是对其如何保护的问题。对于第一方面,如果人工智能“写作”的生成物或创作物为受众所认可,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存在值得保护和需要保护的经济利益,而且不侵犯其他作品的版权或著作权,则对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物或者创作物就应当考虑加以保护。具有自主学习能力、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的生成物或创作物可能不亚于人的作品,可能就值得保护;而对于基于模板、模块、算法的机械生成物,则一般不值得保护,甚至其本身还可能存在侵权问题。对于第二方面,如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这是个难题。既然不宜确立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即人工智能不具有主体资格,则人工智能不可能成为权利主体,那么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的权属如何确定?属于相关人工智能的开发者还是操作者?抑或属于二者共有或分别享有?这无疑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须针对具体情形加以分析。由于这种“创作”活动是人工智能的行为,没有人的创作劳动,因而人在创作方面的利益根本不存在,按大陆法系作者权传统,保护作者利益就行不通,但是可以按照英美法系保护版本利益的传统,强调保护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物或创作物版本利益,那么就看这个版本是谁“制造”出来的就可以了,也就是要看是谁操作人工智能弄出来的,那么版本利益就属于操作者,其可以被视为作者,至于人工智能程序本身则按计算机程序或发明专利进行保护。
至于著作权作品创造性的判定,不管是人还是人工智能写作,都要看是单纯依赖符号的形式上的数据重组,还是直接依赖内容的实质上的信息重组。语言与逻辑本身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表征,但这种表征终究有局限,因而依赖符号系统与逻辑思维的人工智能必然也存在局限。人类的思维、意识活动很多是难以言表的、难以表征的,只可领悟,难以确切描述。甚深智慧、智能可能是难以言表的,如“达摩西来无一字,全凭心意用功夫”,对这“心意”,人工智能如何读取与表征就是一个难题。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或DNA计算机也许是要探索这个问题,但尚需时日。
人类的知见有限、思维有限,基于有限知识与局限逻辑的很多创作创造活动并不见得有多么高深、多么高明、多么“高大上”,很多所谓创作成果只不过是形式的重组、符号的重组。比如撰写论文,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常常强调要阅读大量的参考文献,这样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推进一步。而对于不认真读书的人撰写的论文,我们总觉得其撰写出来的文章很“无知”,其实是文献量不够,没有阅读充分的文献,因而其知见也是片面的。而依赖大数据库、大信息库、大知识库的人工智能则能更好地进行这种知识再组织,这种移花接木式的知识重新组织,实际效果不亚于很多人的创作活动的成果。比如,使用网上“爆文采集器”生成一篇“爆文”只需10秒钟,而这种文章从形式上与内容上都达到甚至超过一般创作者的水准。[11]但这种通过广泛采集拼凑、文字替换的“洗稿”行为,实际是对人类“创作”或“创造”行为的挑战,而不简单是对人类法律制度的挑战。
四、进一步展望
就权利体系而言,人工智能是知识生产力提高与知识生成形式、组织形式的变革,知识世界发生了变化,权利体系也可能要发生相应变化,但是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因而只能暂且搁置。另外,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网信法将加快成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网信法学是正在迅速构建的重要法学学科。网信法是信息社会中与信息技术关系密切的权利义务规范,其属于领域法的一种。目前来看,网信法至少应当包括信息公开法、信息安全法、信息技术法、信息产权法等子部门,人工智能法总体上可归入信息技术法之中,但也与信息安全法、信息产权法等存在一定的交叉。对信息进行法律调整的规范原理,在法学研究中,无疑非常欠缺。而人工智能法实际是网信法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对网信法的研究深入,也将逐步形成体系。对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不外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人工智能新技术健康有序发展、发挥其正面效应,二是将其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设定在可控的范围内、避免其负面效应的出现。对于这一波人工智能新科学技术浪潮,中国会积极跟进甚至是引领其发展,政府已经制订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规划,而将来还会制定相应的人工智能规范。
参考文献:
[1]李连德.一本书读懂人工智能[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2][美]佩德罗·多明戈斯.终极算法: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世界[M].黄芳萍,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3]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N].福建日报,2017-09-11(9).
[4]马云.刚刚开始的数据时代[N].光明日报,2017-07-23(7).
[5]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2017(5).
[6]赵衍龙.霍金:AI恐成人类史上最糟事件 要懂控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EB/OL].2017-11-08.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1/11364698.html.
[7][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8]王治国,等.检察信息化建设正式升级步入“智慧检务”阶段[EB/OL].2017-09-26.http://news.jcrb.com/jszx/201709/t20170926_1800677.html.
[9]蔡长春.最高法大力推进智慧法院建设 全国法院干警一张网办案办公[N].法制日报,2017-11-18(3).
[10]胡裕岭.欧盟率先提出人工智能立法动议[J].检察风云,2016(18).
[11]饶丽冬,等.起底“爆款文章”产业链:10秒炮制一篇爆文月入3万[N].南方都市报,2017-05-05.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Gener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and Institutional System
GAO Zhi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066004)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ctually a product of greatly improved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vity, and a tremendous change in the way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re organized.The new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y bring about huge social changes, including a large number of repetitive mental labor repla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tail, manufacturing, financial industry and other fields will be redefined, and the uncertain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is also hidden.As a legal knowledge system for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there may be changes in ontology,cognition,development theory, methodology, etc., which may appear in cognitive science, brain science, neuroscience,biology, informatics, computer science, etc.The shift of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even future studies may lea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hods based on large databases, large information bases, and large knowledge bas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sufficient information.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modern legal system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This influence may include at least the legal subject system,the object system,the rights system,etc.On the one hand, the network legisl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uncertain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especially to prevent the risks brought by human intelligence abus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Legal Knowledge System;Knowledge Generation Mode;Institutional System
[中图分类号] D90;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478(2019)01-0083-06
[DOI] 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1.012
[收稿日期] 2018-08-12
[作者简介] 高志明(1978-),男,法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剑明
标签:人工智能论文; 法律知识系统论文; 知识生成方式论文; 制度体系论文;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