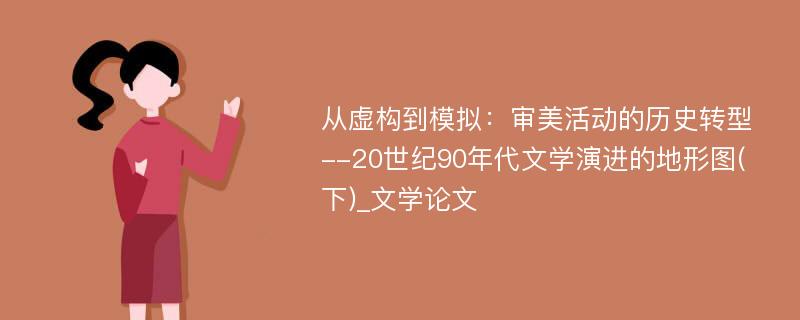
从虚构到仿真:审美能动性的历史转换——九十年代文学流变的某种地形图(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形图论文,能动性论文,之二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鲍得里亚德基于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展开激烈的批判。这种立场其实并不独特,事实上,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都持这种立场,例如,查尔斯·纽曼早在1985年对后现代主义下的积极定义就指出:“‘后现代主义’蕴含一种对经过电子技术的渗透而在战后美国达到顶峰的原子化的、麻木冷淡的大众文化的理性抨击。”〔11〕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些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阿德尔诺和本雅明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者,充满了对高科技社会的激进批判,对于他们来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在英雄消遁的前提下发起的一场对盲目革新的信息社会的非历史主义的反叛。”(查尔斯·纽曼语)这一点似乎令人难以理解,西方的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似乎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就持怀疑态度。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早年的浪漫派诗人和艺术家,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者,甚至像伽达默尔这种写作《真理与方法》宏篇巨制的思想家,也说道:“科学家应该凭良知对他们自身的局限性有足够的认识。”对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或科学至上主义?)的怀疑不过是西方惯有的一种人文传统而已,对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来说,科学技术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当然谈不上过剩,也谈不上对人和社会的直接压迫。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却使中国社会以较快的速度享用西方高新技术的成果,在基础科学和研究探索领域谈不上与西方先进成果接轨,但在消费领域却是越来越趋向于同步。没有人否认中国还相当落后,大多数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人们也难以否认也有不少人已经提前进入小康,还有一些人已经奔向大康。在消费领域超前接触西方输入的高新技术,这并不是对中国当今社会夸大其辞的描述。在中国数个发达的大城市里,高新技术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也许并不输于西方发达国家多少。因此,如果说鲍得里亚德是在把高新技术作为现实仿真化的主导因素,那么,这用于理解中国社会现实(当然是指超前进入现代化的那些社会状况)在高新技术影响下的某种生活现实,也未尝不可。
但中国的情形显然不能等同于西方,也不是强行要与西方作同步对比。它的特殊性显而易见,但我不是一个东方中国“特殊论者”,我决不漠视那些特殊性,但也不把这些特殊性看成是寻求理论对话的绝对鸿沟〔12〕。在我看来,特殊性并不是与普遍性绝对对立的,恰恰相反,特殊性是对普遍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里,我以为鲍得里亚德的观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性,只不过以“仿真”的概念来理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学时,需要考虑的是更加复杂的历史情势,而不是单纯从唯科学主义的角度。而是在科学、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边作用中,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特别是“现实”本身的虚构化,审美幻象化,或者说“仿真化”。
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一方面是平庸,刻骨的平庸;另一方面却是奇迹迭出,到处是突飞猛进的景观。作为全球经济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国家,中国正在给疲惫的二十世纪末注入兴奋剂。世界关于中国的想象,中国关于自身的想象正在迅速展开。按照鲍得里亚德的观点,“城市现在不再是政治—工业中心,而是符号的领地,是媒体和代码的领地”。就算中国的城市打些折扣,依然是政治的中心,但也不可避免是政治与符号相混淆的领地。正由于这种特殊性,中国社会现实的符号化更具有“仿真”或“幻象化”的特点。中国在九十年代快速城市化和消费化,使得中国的城市也迅速进入文化幻象的时代。光怪陆离的写字楼,大型现代化商场,广告,休闲读物,周末版报纸,滚动式的电视节目,卡拉OK,点歌,体育竞赛,时装以及多媒体电脑的日益普及……等等,城市生活已经完全为符号和幻象所重新结构编码。例如,中国的数个大城市的空间已经迅速审美幻想化了,过去不过是用于居住和工作的空间,完全按照实用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空间,现在却是为各种现代化的新型建筑材料所重新编码,特别是玻璃钢的广泛运用,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发达地区正在构筑一些超级的幻象空间。这些空间与那些低矮的平房、粗陋的阁楼、混乱的工棚等等相得益彰,使得相互间都失去了实在的真实性,如同电影的布景和道具一样似是而非。它们并不仅仅是物理时空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城市,而且以中国最新、亚洲最高、世界最大……等宏伟叙事,使这些空间打上奇特的关于中国,中国关于自身的二十一世纪的想象。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事例而已。事实上,外部世界的图景、信息和节奏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这一切必然要反映在文学上。尽管从八十年代末以来,人们就在慨叹文化步入低谷,文学委靡不振,但文学和文化的各项实践都在毫无节制的展开,足够丰富的事实和现实场景表明文化并没有溃败,相反却在蓬勃发展,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意识形态文化或经典文化生产的方式在扩展。人们有理由抱怨精英文化陷入困境,也可以理直气壮指责文化工业的粗制滥造,但不能不认识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正在以不可抗拒的方式推进文化和文学的生产。商业主义文化霸权正在把触角伸向各个领域,人们不是一直在慨叹传统文化霸权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过于狭窄吗?现在,商业主义以它混乱不堪而又生机勃勃的姿态打开历史之门(感官的、愉悦的、狂欢的?)。
尽管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能和西方作简单的比拟,但“仿真”这一历史特征却不难从当今中国的现实和文化生产实践中看出。由于当代中国相当复杂的现实情境,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与文化总是处在多边作用的结构关系中,在这些关系中决定了当代文化生产的特殊方式。一个在文化生产方面最大矛盾在于,同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并不是同代人,人们在说根本不同的语言,一些占主导地位的霸权话语生产了一系列的超级能指,却始终无法表达真正给出所指。大量的无所指的能指超量复制,这是使现实符号化的最大根源。现实本身被遮蔽和遗忘了,人们不需要现实,也无法真实地把握现实,人们都满足于生产能指,人们以为有了能指就能重建现实。但事实是,人们重建了庞大的符号化的现实。
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社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进入一个“仿真”的时代。“仿真”的现实,或者说现实的仿真化,也就是说现实完全符号化了,现实只有变成符号才能被理解和把握,人们只有抓住符号才能抓住现实,现实已经没有本质可言,现实由各种各样的似是而非的幻象构成,现实就是“超现实”(surreality)。现实本身就是一部庞大的超级的虚构小说,一切虚构文学作品与这个仿真的现实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它除了以仿真的方式对现实幻象进行复制外,别无良策。然而,分享这个幻象化的超级现实,虽然可以使当代中国的文学叙事有能力创造各种各样的奇迹和神话景观,但它毕竟显得被动无力。
尽管说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面对着一个符号化猛烈扩张的仿真时代;我们意识到文学只能在既定的给定的历史前提下展开必要的实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现时代的写作主体也只能抓住剩余的想象去与各种压制性的力量对抗;但不等于文学叙事只能在同一平面上追随现实,把文学叙事降低到被动的仿真过程。文学可以而且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奋起反抗,并且寻求新的出路。当然,简单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形式主义都无力真正反抗迅速的仿真化,但不管是把当代现实看成是平庸无聊的,还是神奇变幻不定的,依然都有可能从中发掘出一些锐利的、坚韧的局部事实。 超级现实主义(hyperrealism )或超现实(surrealism)二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前者是绝对逼真地表现局部事实的绝对真实,后者是总体上把符号与现实剥离,重新给现实编码)都可能抓住那些破裂的事实和幽闭的时刻,重建文学令人震惊的现实。
注释:
〔1〕当然,“现实”在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优先性, 既与艺术起源可能植根于人类的模仿天性有关;也与现实主义作为十九世纪反对浪漫主义的一项运动有关。在中国,当然又是俄苏文学传统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影响的直接结果。
〔2〕参见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中译本见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第59—60页,三联书店,1988年。
〔3〕这种描述很可能是同语反复的。 因为并没有一个本源的第一义的“现实”存在于话语叙述体系之外,当我们谈论现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关于指称现实的各种事实——而事实总是被语言叙述出来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假定存在一些未经特定的话语体系重建的事实,在构成总体性的现实之前,它们确实发生过。这样,我们在理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分辨出社会现实系统与话语表意系统。前者由社会事件、活动和实践过程构成;后者则是由语言符号构成。但在总体性上描述、把握和重建现实,则只能通过语言符号或话语系统。因此,在这里,我使用“现实潜本文”这种说法,即是指存在于话语表意系统(叙事系统)背后的内在力量。“现实潜本文”这一概念来自杰姆逊的“历史潜本文”(historical subtext),语出《政治无意识》。杰姆逊所说的暧昧混乱的事实背后的不可理喻的决定力量,即是历史辩证法,也可以理解为“历史潜本文”。
〔4〕很显然,“文学本体论”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说法。 这个概念看上去像是在强调现代主义式的文学的本体论——神学梦想,亦即文学有着自身存在的本质,文学语言就是一个充足自主的世界。形式主义和现象学美学一直在强调这种观念。但文学本体论经常也与文学的文本观念相混淆,因为文本观念也强调文本的独立性,像德里达所说的那样,文本之外无他物,似乎文本就是一个充足的存在客体。但文本观念强调语言表意策略的开放性和差异性。语言符号的差异性意味着文学叙述话语拒绝存在的本体论——神学梦想。但在中国八十年代中后期,对“文学本体论”强调似乎主要是与文学反映论相对,指强调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尚未上升到文学作品(或文本)存在的自主性问题。
〔5〕王蒙:《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 原载《文艺报》1988年,本文引自《王蒙文集》第六卷,第339页。华艺出版社,1994 年版。
〔6〕在这里,有人可能会对我的逻辑推论持怀疑态度, 因为我一再谈到“现实”是被虚构出来的。而我又在这里使用现实(历史),似乎我又承认实在性的先验的现实存在。显然,在理解“现实”这一范畴时,又有必要引入历史,现实其实不过是历史在现在时的显现。古典历史观(例如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精神的演化过程;在新历史主义观(如克罗齐)看来,历史不过是当代精神的总汇;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历史不过是语言修辞的结果;而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杰姆逊)看来,历史是隐藏在事实或事件迷雾背后的不可理喻的力量,所谓历史,其实质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杰姆逊等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虽然是从反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其实是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调和。惟其调和,对历史的解释相对不那么偏激。这种解释历史的方式,可以用于我们解释“现实”这一范畴。现实是一切事实、事件和现象的存在总汇,它可以先于人们的认识存在,但它一旦要进入人们的解释视界和理解视界,它就被特定的知识和观念所界定。现实确实先于认识而存在,但现实只有在特定的认识系统才能被理解和掌握。因此,我在这里不断地谈到现实依据的意义在于,这些事实、事件和现象都存在,但总是在特定的描述、解释和理解系统中才确立它的总体意义。
〔7〕这与其说是“现实”本身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不如说是人们现实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8〕鲍得里亚德(Baudrillard ):《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第50页,London,1993。
〔9〕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参见王岳川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鲍得里亚德:《象征交换与死亡》,第74页。
〔11〕查尔斯·纽曼:《后现代氛围——通货膨胀时代的虚构行为》,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12〕我采取这种论述方法,很像是要以西方作为理论参照系。这显然是再次落入一些人指责的罗网。我们在理解当代中国现实时,总是不得不去借用一些西方的概念,这对于那些“东方主义者”(这些东方主义者明显不同塞依德的东方论者,后者是对东方带有特殊想象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前者恰恰相反,正是一些对西方怀有特殊想象的“东方特殊主义者”)来说,这种做法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崇洋媚外。但我坚持认为人文学科并没有那么强的民族性色彩,特别是现代人文知识国际化的趋势,使我们更有必要在同一理论层面上展开对话。另一方面,现在那些标榜回到民族本位的本土化论者,也不见得就回到国粹的渊源,只要稍加辨析,不过是在运用那些人们已经熟知的十九世纪西方的经典知识而已。因此,在理解现时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时,广泛汲取一些西方的理论知识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