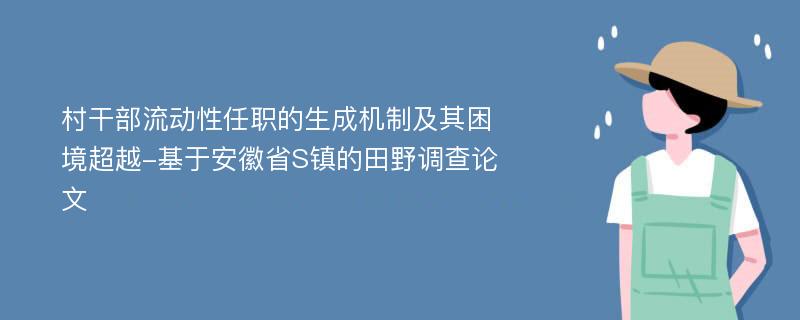
村干部流动性任职的生成机制及其困境超越
——基于安徽省S镇的田野调查
王惠林,李海金
[摘 要] 农业型村庄的村干部呈流动性任职的发展趋势。流动性任职突破了由户籍为本村村民担任村“两委”干部的条件限制,村干部成为调剂性资源,在镇域范围内流动。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是在农村社会陷入治理主体缺位,进而引发系列治理问题背景下的实践探索。它顺应了农村治理事务“质”“量”结构变迁的内在需要。流动性任职构成基层政府培养、选拔村干部,建设农村治理体制的重要方式,填补了农村治理真空,并以强制度关联激活了村干部的治村责任。然而,它也面临与既有村庄社会结构存在张力、去权威性、因缺乏灵活变通性造成治理失效等困境。非体制精英的吸纳和群众路线是流动性任职村干部积累社会性资源、实现有效治理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 村干部;流动性任职;农业型村庄;村级治理主体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现象率先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兴起,并逐步向中西部农村蔓延。流动性任职是指村干部突破了由户籍为本村村民担任的条件限制,其作为调剂性资源,在镇域范围内流动。流动方向共分为两种:一是垂直流动,包括乡镇干部下派到村里担任村干部和村干部上调至乡镇部门任职;二是水平流动,是指村干部跨村交叉任职。学界对此现象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村干部流动性任职的本质及其生成机制。现有研究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认为流动性任职是村干部职业化和村级组织行政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本质是国家权力通过强化对地方代理人的控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渗透[1]。如贺雪峰在苏南农村调查发现,村干部“由土变流”使得村级治理由自治转向行政化逻辑,体现出乡镇对村级人事任免和调配权的掌控[2]。张雪霖、王金豹在广东、上海农村调查发现,职业流动系统的开放是乡镇对村级组织实行的行政激励措施[3]。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主要缘于外力的形塑和驱动。同时,学界集中讨论了江苏、上海、广东等东部发达地区村庄村干部流动性任职的实践,而鲜有学者关注农业型村庄村干部的流动现象。笔者在全国不同农村地区调研发现,一般农业型村庄与发达地区村庄由于经济发展程度、村庄利益密度、人口流动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在村干部流动性任职的形成机制上也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农业型村庄的村干部流动性任职虽然也体现出一定的行政化逻辑,但是其治理逻辑更为突出。内生动力在这一实践探索中占主导位置,村干部流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填补因村级治理主体缺位而造成的基层治理真空。本文以安徽省S 镇① 依据学术规范,本文对文中的地名、人名进行了技术处理。本文所用实证材料,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调研。 的乡村治理实践为例,在系统描述农业型村庄村干部流动性任职基本实践样态的基础上, 试图分析其内在生成逻辑,揭示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并依此提出对策建议,以推动其进一步完善。
S 镇位于安徽省南部,全镇总人口31587 人,其中农业人口为30324 人;其下辖13 个行政村,1 个社区。2012年S 镇开始试行村干部的流动性管理,至2014年在全镇范围推行。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平行跨村任职,包括职位升迁或保留原职位不变。如WXY 原是X 村的会计,2015年被调至P 村担任村支书;2016年P 村书记被调至H 村担任书记。二是乡镇干部下派至村里担任村主职干部或村主职干部通过考试或被聘任至乡镇职能部门任职。如,2015年S 镇党委组织干事被下派至K 村任村支书,身兼两项职务。该地政府规定,连续任职两届及以上的村主职干部可参加定向的公务员和事业编考试, 考试通过者仍任原职或进入乡镇职能部门,但享受相应的待遇。又如,WDN 原是W 村的村支书,2014年考取事业编制,但仍留在原岗位,享受事业编待遇。目前,S 镇13 个行政村中有10 个村的主职干部由流动性任职村干部担任,其中乡镇下派4 人,跨村流动6 人。之所以选择该镇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因为该镇的相关实践探索起步较早,发展也较为成熟,能够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村干部流动性任职的一般样态;另一方面,该镇农村具备农业型村庄的典型特征,如地方财政支持力度有限,村集体经济资源匮乏,属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人财物的流出地等。
二、治理主体缺位、治理事务转型与流动性任职的形成
与已有研究表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视角不同,在一般农业型村庄,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是需求诱致性变迁的产物。
(一)传统型治理主体的退场
这里的传统型治理主体是指既充当“国家代理人”又充当“村庄当家人”的“非脱产”村干部。传统型治理主体的治村动力主要来源于社会性激励和经济性激励两种途径。有研究表明,“非脱产”村干部之所以能在较低的“误工补贴”水平下保持工作的积极性,主要原因是人情、面子、社会声望等社会性价值的激励,基层治理也主要围绕非正式激励机制而展开[4]。然而,当前无论是正式激励抑或非正式激励均处于失衡状态,造成传统型治理主体的退场。
第一,村干部的职业化变革造成经济性激励机制的失衡。村干部的准职业化近年来在全国呈普遍化趋势,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行政管理制度的实施,如常态化的办公会议制度[5]、坐班制、考勤制[6]等。村干部由原来的“半脱产”和兼职化状态转向彻底的脱产化和专职化,这意味着村民在担任村干部的同时,不得不放弃其他获取经济收入的机会。地方财政能力的限制及村集体经济的空壳化造成农业型地区难以承担起职业化村干部和公共规则运行的高昂成本,突出地体现在村干部无法获得与其职位相匹配的工资收入。其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村级治理的半行政化,即地方政府将村主职干部纳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之中且强化对村主职干部的行政规范管理,而其他村干部仍保留着兼业、不脱产的“农民”底色[7];二是在低于当地农民务工收入的条件下,村干部成为“说不上话、办不成事”的人,村级组织沦为“维持会”。这两种倾向的职业化变革不仅未能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以S 镇为例,该地从2008年开始对村干部实行专职化管理,要求村干部与其他副业相脱钩。村干部的收入由村集体发放的“误工补贴”转变为政府财政发放的固定工资,且收入水平呈上涨之势。其中,村主职干部的收入由954 元/月上涨至2900元/月,副职干部的收入由700 元/月上涨至2554元/月。然而,这样的工资却未能达到当地农民外出务工的平均水平。据调查,当地农民进厂务工年收入为5~6 万元。在村民的观念中,村干部并不是一份十分体面的工作,“只有没有本事,在外面找不到饭吃,被市场淘汰下来的人才会回村当干部”。在流动性任职实行之前,村干部主要由两类群体担任:一是负担不重的低龄老人;二是待业青年。村级治理也呈现出维持型特征。
第二,社会性激励机制的失衡。面子、声望、威信等是社会性激励机制的重要构成要素,一般存续于流动性较小、边界较为封闭的乡土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逐步卷入市场化浪潮之中,稳定封闭的村落共同体转换为“流动的村庄”[8],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转换为“半工半耕”“半耕半副”的兼业模式。农村文化在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交融中逐渐走向多元化[9]。在这种环境之下,社会性价值及激励机制面临难以再生产的问题。一方面,村民失去了积累社会性价值的途径;另一方面,社会性权威的治理能力也遭到不断削弱。
要达成重建农村治理秩序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村干部的个人力量,尤其是在缺乏必要的正式治理资源的农业型村庄,村级组织只有整合和调动起弥散在群众之中的社会性资源和力量才能弥补正式资源的不足。某种程度上,流动性任职的村干部对村级组织和群众的动员能力决定了它达成预期治理目标的程度。然而,外派的村干部不仅不具备组织、动员的优势,而且在诸多方面还面临挑战。
(二)经济机会空间的压缩与新兴治理主体的离场
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村治学者在农业型地区调查发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在造成大量农村青壮年流向城市及引起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同时,也意外地腾出了适当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市场获利空间,使得一部分无法外出或无动力外出的村民成为坚守在村庄的中坚力量,以此填补了农村人、财、物流出所留下的农村社会秩序的真空[10]。他们由此提出了“中坚农民”的概念,并主张将这部分农民培养成新兴的治理主体。“中坚农民”是指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体的,主要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且收入水平不低于外出务工又可以保持家庭生活完整的村民。这部分农民具备的两项重要特征使其能够成为合格的治理主体。其一,利益关系深嵌于村庄,具有强烈的维护农村生产生活秩序的动力, 因此成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最积极的参与者和维护村庄秩序的最重要骨干[11]。其二,社会关系高度嵌入村庄,与村民有紧密的人情关系和社会互动。这一方面使其在治村过程中可充分调动各种非正式资源,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其能够自觉接受村庄道德规范和公共舆论的约束和监督。“中坚农民”之所以能留在村庄,与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秩序和基层市场的获利机会紧密相关。
第一,选任与培养村级治理主体,填补农村基层的治理真空。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一般能发挥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解决村级治理主体后继无人的问题;二是提升村干部的适应能力和综合素质;三是向上流动渠道的开放对村干部形成正向激励。在农业型村庄,前两者的作用尤为突出。例如,S 镇X村的村支书WCN 今年57 岁,共担任了20年村主职干部。WCN 的个人能力较强,又属村里的大姓,在当地颇有威望。在WCN 的带领下,X 村不仅维持了良好的治理秩序,而且成为全镇的明星村,大量项目资源落到该村实施。然而,X 村即将面临的棘手问题是,一旦WCN 退休,村里难再选出一位如他一般工作能力强、群众基础深厚的村支书。为了化解这一难题,镇政府未雨绸缪,早在2014年就将该村年轻的WXY 作为村支书的后备人选,WXY 是该村的会计,虽然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但是工作能力有待提升。镇政府先是将其调至P 村担任村支书,随后又将其调至H 村。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锻炼、培养WXY;另一方面,H 村也面临与X村类似的情况,即前任村支书退休后,难以选出合适的接替者。因此,WXY 的调入除了实现培养目标之外,还具有维稳性质。镇政府的计划是下一次换届选举,再将WXY 调回X 村以接替WCN。
然而,随着近些年以龙头企业、种养专业大户为代表的资本化经营主体的下乡,农村的经济机会空间被大量挤占,“中坚农民”因此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进而无法转化为新兴的治理主体。以S 镇为例,2014年之前,外出务工的村民将农地以非正规的方式流转给亲戚、朋友或同村村民耕种,流入耕地的农户一般因文化程度较低或父母、子女需要照料而无法外出务工。他们只需支付少量租金,如200斤/亩/年水稻,就能达到40~50 亩的种植规模。据统计,几乎每个村民小组都有4~5 户“中坚农民”家庭,80%左右的村民小组长、村干部由“中坚农民”群体担任。外出务工农户与留村务农农户形成良性互动,一方面,留村务农农户通过流转外出务工农户的农地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维持了体面且完整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外出务工农户不仅能收获少量租金,而且农地也不至于荒芜,如果其退养回村,可继续耕种。然而,2014年以后,S 镇开始引进农业企业,以正规合同600 斤/亩/年水稻流转农地,截至2018年,S 镇共引进了14 家农业企业,平均规模为500 亩,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一家养虾的企业,面积达3000 亩,并且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下一步将继续上涨地租价格,主要目的是挤压“中坚农民”群体。原因有二:一是农药化肥污染水质,影响其生态农业发展;二是部分农民插花耕种,妨碍其连片经营。面对高额地租,原来通过自发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难以再流转到农地,他们或成为农业企业的雇佣劳动,或被迫外出务工。
(三)农村治理事务的转型
农村治理事务转型为流动性任职的村干部实现有序治理提供了空间。农村治理事务结构可分为事务的量化结构和质性结构。量化结构是指事务的数量和分布情况;质性结构是指事务的类型和规则化程度。近年来,农村治理事务的“质”“量”结构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而出现较大程度的变迁。
第一,在事务的量化结构上,农业型村庄青壮年的大量外流使村庄整体呈现出留守型、“空巢社会”[12]的特征,村庄内生性事务呈不断萎缩化的状态,在数量分布上也较为稀薄。例如,S 镇农民自1998年开始外出打工,2000年左右外出务工的农户比例达到90%以上,务工地点集中在苏浙沪等地。2014年全镇完成农田整治,80%左右的农地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统一发包给农业企业经营。农田整治一方面充分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加剧人地分离程度;另一方面进一步简化村级治理事务,如村级治理的对象由分散的个体农户转变为少数种养殖大户,使农户之间围绕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矛盾纠纷也大为减少。
第二,在事务的质性结构上,村治事务的规范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随着政府由汲取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近些年国家下派到农村的治理任务及惠农资源不断增多。为了加强对村级组织完成各项工作情况的监督,基层政府将行政考核办法引入村级治理,对其工作提出了“台账化”“痕迹管理”的要求。如S镇对村级工作实行“双千分制考核”,村庄发展和党建各占1000 分。发展部分包括村务公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减轻农民负担等共计24 项;党建部分包括组织工作、党风廉政建设、武装等共计11 项。所有工作都要求年初有计划、年中有汇报、全年有总结,并配有相应的会议记录和图片。村干部的绩效工资与考核结果直接挂钩。
这些事务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以外生性事务为主, 即大部分事务与农村社会内的各种利益关系、人情关系无过多的关联,而是主要派生于行政意志。此类事务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并不需要依靠地方性知识或社会性资源进行处理,照章办事的公共规则化治理方式反而能发挥较好的效果。因此,对村干部是否为本村人及嵌入村庄的程度依赖性较低。二是村治事务的“痕迹化”、文牍化对村干部提出了年轻化和知识化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传统“泥腿子”干部的退出。例如,当地一位工作30年的老干部向笔者反映,“我不想干了,不想操这个心。我没有文化,才小学四年级的水平,也不会写字。上面要求写各种材料,弄各种报表,我弄不来,眼睛花了,也看不清楚字”。
由上述可知,村干部流动性任职是在传统型治理主体退场,新兴治村精英又因经济机会空间的压缩而离场,农村社会陷入治理主体缺位背景下的实践探索。其主要目的是要解决村级治理主体的继替。在以安徽省S 镇为代表的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构成基层政府培养、选拔村级治理主体,维护农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方式。实践证明,村干部作为调剂性资源在镇域范围内的流动对农村治理体制建设发挥重要功能。
由图6可知,组分DI经过G-75凝胶层析后,获得4个峰。对收集的各组分进行ACE抑制活性测定。见图7。组分DGIII的ACE抑制活性是最高的,抑制率为13.62%/40 μL。并对组分DGIII进行冻干浓缩后,ACE抑制活性为(98.3±1.24)%,IC50为0.08 mg/mL。
第二,以强制度关联激活村级治理主体的治村动力。流动性任职建立起了基层政府与村干部之间的强制度性关联,乡镇政府通过掌控选任调配权及考核与报酬相挂钩的方式,既规范了村级权力运行,又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激活了村干部的治村动力。上级的治理压力形成了村级组织的治理责任,使其具有配置资源进行村级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13]。如一位村干部坦言,“给你碗,就归你管”,“要让老百姓满意,让上级更满意”。
1.7.2 大鼠肝内CD4+CD25+Foxp3+Treg表达情况 将大鼠肝内最大的结节取出,用10%福尔马林固定24 h,用水彻底冲洗,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常规浸蜡包埋。在切片机上切为4 μm厚的组织切片,烤片,将石蜡切片脱蜡至水,PBS洗涤2~3次后微波抗原修复,分别滴加一抗、二抗,DAB显色,脱水、透明、封片后在镜下观察。Treg细胞的典型表现是胞质和胞膜上有棕褐色颗粒,细胞结构清晰,随机选取5个高倍视野(×400)下的阳性细胞数,计算平均值。
三、村干部流动性任职的治理实践困境
据村民介绍,2000年以前,S 镇的红白喜事皆由熟谙传统礼仪规范、认真负责的长辈张罗,在为村民义务帮忙中,社会性价值得以再生产,这部分村民往往被推选为村干部,实现由社会性权威向政治性权威的转换和融合。而2000年以后,市场化的婚庆司仪代替村中长辈,成为红白喜事的主持者。酒席、宴会也不再需要本村人张罗,而是全权交给流动酒家。除此之外,村中长辈也无法再凭借人情、面子等社会性资源实现有效治理。以矛盾纠纷调解为例,在以前,社会性权威是介入家庭矛盾纠纷的合法主体,其充分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和声望,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摆平农民家庭及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而如今,其对村庄矛盾纠纷的调解能力呈下降趋势,直至不再牵涉其中。在此背景下,传统型治理主体也逐渐失去了治村的动力。
(一)流动性任职村干部与既有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
在当下互联网时代,标准化研究机构无论是发布相关通知,还是展示工作成果,抑或是提供各种信息和服务,门户网站都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门户网站的设计情况也就直接体现该机构品牌的建设情况。按照目前32家标准化研究机构的门户网站设计情况,以名称的相符性为界,可以将门户网站分为三类:第Ⅰ类,网站名称与标准化研究机构名称一致;第Ⅱ类,网站名称与标准化研究机构名称不一致;第Ⅲ类,未建立门户网站,或网站设计不明确、基本功能较欠缺,或网站访问不稳定,或难以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网站地址等。32家标准化研究机构网站分类情况见图3。
传统型村干部治理村庄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国家授权和自下而上的村民认可。村民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互动中积攒社会威望,从而被推举为村干部。总体而言,社会威望的积累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先赋性的血缘关系;二是通过红白仪式、村庄公益性事业积累权威。正如杜赞奇提出,有“面子”的乡村领袖将其权威建立在发挥某些社会职能、担当某种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如像乡村郎中那样治病救人、向村中宗族活动捐款、调解争端等[17]。这部分具有较强社会威望的村干部在处理村庄事务时,能够使村“两委”成员和村民充分信服,因此其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实现农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治理过程上,“简约治理”并不简约,甚至可能纷繁复杂,它包括对农村社会内部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的调动、各利益主体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等[18],以此达成治理效力。内生于村庄之中的传统型村干部具备整合与调动资源的优势。
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了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农民在家庭以上创造了功能性组织,从而在乡村社会之中形成一个双重认同与行动单位[14],其中,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组织、村民小组或行政村。相较于家庭的“小私”,宗族组织、村民小组或行政村构成一个基本的“大私”,即“自己人”单位。“自己人”单位有内外之别的区分,即单位以内的是“自己人”,单位以外的是“他人”。农民在单位内外也遵循差异化的行为逻辑,“自己人”以内是义务本位,遵循互利、互惠原则,这极大地降低了合作和组织成本,有效满足了农民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15]。“自己人”以外是权利本位,这意味着“交往时可以坚守个人利益、维护个人权益,而无需顾及他人感受”[16]。在“自己人”单位以外达成互助、合作的成本较高,其首要的是解决基本的信任问题。虽然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影响,实体的基于血缘、地缘和社会交往关系而形成的“自己人”认同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观念层面的“自己人”认同却依然存在,并影响农民的日常行为,这种认同在面对陌生人、“他人”时会得到进一步强化。
如S 镇的LXL 在担任村干部过程中就遭到原有村庄社会结构的排斥。LXL 原是L 村的文书,2016年调到Y 村担任代理村主任,在接下来的换届选举中被选为正式的村主任。Y 村原村主任在位时培养了接替其职位的本村后备干部杨某。鉴于杨某的人品、能力问题,镇政府否决了将其推上村主任职位的提议,而是从L 村调来了LXL。Y 村围绕原村主任培养的后备干部形成了一支与LXL 相对抗的“反对派”,他们在村庄中捣乱,导致村级组织难以开展工作。村民对此也颇有异议,“为什么要你来当我们村的村长,难道我们村就选不出一个人?”在勉强维持一年后,镇政府只能将LXL 调离Y 村,由该村村民担任村主任。
(二)流动性任职村干部的“去权威性”
项目施工实际安全保障水平是项目安全状态在考核期内的量化体现。安全保障水平越高,项目越安全,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就越小。以施工安全保障水平指标评价体系为基础,对各项指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获得项目施工实际安全保障水平。
而流动性任职村干部只具备自上而下的国家授权,却缺乏生长于村庄内部的社会性权威。这导致其无法调动人情关系网络、面子资源及地方性知识治理村庄,在村级组织内部难以产生公共性,导致组织内个体的“私利”占据上风,村庄共识和公意难以得到伸张。如X 村的WXY 在调入H 村时即面临上述处境。H 村在1998—2008年之间分别由本村村民ZJS 和QFB 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二人在村中极具威望,村“两委”班子非常团结。2011年,两人卸任后,村级组织内部矛盾丛生。一是新任村支书与村主任之间的矛盾,村主任好赌且不听村支书的劝阻,二人互不信服且心生嫌隙;二是妇女主任汪某和治保主任周某的矛盾,两者皆为女性,汪某为人踏实且性格腼腆,比周某早一点进村,而周某与之相反,强势、泼辣,会拉拢关系,虽然她比周某晚一些进村,却先进村“两委”班子,这让汪某不服,二人明争暗斗。在这种情况下,镇政府将WXY 从P村调到H 村接替村支书,试图调和村组织内部的矛盾。然而,作为外派干部,WXY 非但未能平息争端,反而加剧了村“两委”班子的分裂。WXY 做事认真,但是在村中却无有力的支持者,几位老党员、老干部还对其颇有微词。WXY 与性格谦和的汪某关系较近,引起周某的强烈不满,认为村里的许多事务WXY 没有与其商量。周某认为,“WXY 是个称职的干部,但不是称职的书记”。目前,该村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村干部各行其是,村主任和妇女主任只管本职工作,其他需要“两委”成员相互配合的综合性事务一概不管;治保主任无所事事,只负责完成少量的文字材料工作;村书记WXY 成为村里最忙碌的干部,由于其难以调动起其他村干部,因此不得不包揽一切工作,事事身体力行;而其他干部的反应是“反正他要自己干,就让他自己干吧”。
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是农业型村庄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即它既不完全是建立在传统礼治秩序基础上的乡土社会,又不是完全建立在现代公共关系基础上的公民社会,却兼具两种社会形态的些许特征[19]。总体上看,农村治理事务的规范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然而传统型治理事务,如矛盾纠纷调解、计划生育、村庄发展,却并未完全消逝。这类事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连带性,即其难以就事论事,而是连带着各种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具有关系嵌入性特征。处理此类事务的关键,在于理顺事务背后的各种连带关系,并且因为其主要发生在村庄内部,所以需要依托于特殊主义的地方性知识进行处理。二是偶发性,是指事务的发生频率,即其并非经常性地发生,也无固定的规律可循。三是弥散性,即此类事务弥散在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难以制度化和常规化。X 村书记WCN 经历的一起矛盾纠纷事件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出该类事务的上述特征。“2014年的一个傍晚,河西村民组的两户村民因为鱼塘分鱼的事情发生纠纷,两户村民各自叫来十多个亲戚、朋友,双方都不肯让步,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当时我正在吃晚饭,听到有人喊‘不得了了,要打死人喽’,我放下碗筷,立即冲向不远的现场,大吼一声,‘你们在干什么,谁要是动手我就找谁,有什么事情说不开的! ’一下子控制住了场面。避免小矛盾演变为大的恶性事件。后来,两家人都向我道歉并表示感谢,‘那天多亏了书记在家,及时赶到现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三)规则化治理方式与传统型事务的错配
村干部的流动性任职也是现代国家公共规则向农村社会渗透和输入的过程。规则化治理在基层政府与流动性任职村干部的双向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基层政府掌握村干部的任免权和调配权,村干部不得不严格遵循上级行政意志和规则办事;另一方面,按程序办事构成“流官”村干部的重要免责机制。然而,规则化的治理方式在对接农业型村庄传统治理事务时,却由于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造成治理的失效。
由表3和表4可知,各因素对提取辣椒红色素含量影响的主次顺序为:粒度>酶解时间>SSL的添加量>料液比>酶解温度>酶添加量,而其最优水平组合为A2B3C3D1E1F2,即酶添加量0.8 %(W/W)、酶解时间2 h、酶解温度55 ℃、料液比1∶5(g/mL)、SSL的添加量0.6%(W/W),辣椒粒度为粉碎后过100目筛,此时,辣椒红色素的含量为31.25 mg/g。
建立完善政府对企业收益分配的宏观调控机制,合理平衡各行业工资收益,适当缩收益差距,调动各行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得整个社会各行业全面发展。对于非自然垄断行业中由于行政垄断造成的企业间不合理的收益差距,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市场化竞争来进行调控。加快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做好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助工作,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的就业制度、公平的收益分配制度等,不断对收益分配进行完善。加快工资立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发展与完善,适应新体制要求的企业收益分配机制也在慢慢形成,所以制定符合职工利益的《工资法》迫在眉睫。
流动性任职的村干部必须首先融入农村社会,这是它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它往往会遭到来自既有村庄社会结构的阻挠,这一阻力主要来源于同一行政村或自然村的村民所产生的“自己人”认同。
由上述可知,这类传统型事务并不适应遵循普遍主义、精细化程度很高的公共规则化治理方式,因为“真正要实行规则之治,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规则之治的治理对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性”[20],并且规则治理只有运用于反复出现且频繁发生的事务才能产生最大的治理效率[21]。除了上述治理能力的限度外,规则治理还会消解流动性任职村干部回应农民需求的动力,即在处理事务时只遵照程序办事,遵循不出错的逻辑,而并不关注农民的内在需求及其满足程度。
制作:1.猪肉去筋膜,切成大薄片,猪蹄去毛,清洗干净入开水锅中汆一下,剁成5 cm见方的块,放入高压锅中加水上火压至刚熟,捞出冷却。猪蹄筋发好,入开水锅中煮软,从中片开。大枣泡一下,择去杂质,洗净。水发香菇、木耳去蒂洗净。撕成小朵。黄豆芽、菠菜择洗干净,沥水。葱洗净,拍破,切节。豆腐入开水锅中汆一下,切成条。以上各料除猪蹄、红枣、蹄筋外,均各分成两份装盘,上桌摆好。
四、困境超越:精英吸纳与群众路线
综上所述,流动性任职的村干部要嵌入村庄,实现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如何实现组织内的整合与动员;其二,如何赢得农民的认可,提升村级组织处理农村事务的能力。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积累和调动社会性资源,而威望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
(一)精英吸纳
这里的精英主要是指在村庄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可将其称为非体制精英或社会性精英[22]。这部分群体与普通村民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备政治社会影响力,而其与体制精英的不同则主要在于影响力来源和组织化程度的差异。非体制精英的影响力来源于村落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如源于宗族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等。由于对这部分群体并无正式的授权,群体边界较为模糊,组织化水平也较低,但是非体制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却处于核心地位。如仝志辉、贺雪峰研究指出,非体制精英与普通村民关系的稳定性程度决定了村庄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而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达成协议成本的高低决定了村庄正式权力运作的效力[23]。对流动性任职村干部而言,要调动社会性资源,关键问题是如何识别和吸纳这部分非体制精英。
农场基本已经普及大型气吸式精密播种机或高速气吹式精密播种机加之机手作业水平较高,可以一次完成开沟、精量播种、覆土、镇压等作业,播种质量、高保苗效果好合作社和一般农户;农户自用“小机械”无法达到标准垄栽培模式标准化播种要求。
农村社会中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群体是农村基层组织可以动员以协助流动性任职村干部有效治理村庄的社会性资源。他们中的一部分产生于大集体和农业税费时期,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获得了治理村庄的体制性身份,还有一部分年轻时在外工作,年老退养回村,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其具备开阔的视野、较强的人际交往与组织协调能力。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从未真正脱离村庄,对村里的人和事都比较了解,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同时,他们中的大部分群体属于“负担不重的老年人”,即已为父母养老送终,子女都已成家,因此并没有过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有时间、有精力、有参与村庄公益性事业建设的热心。如果能调动起这部分群体的积极性,村级治理可再次实现体制精英与非体制精英的联合。可采取两种方式对非体制精英予以动员。一是正式动员机制。担任过村干部及其他职位的老党员、老干部一般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以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为主体的正式动员方式往往能发挥较好的动员效果,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社会价值生产能力趋于弱化、非正式激励机制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二是半正式的动员机制,即将社会精英整合和吸纳到理事会、乡贤会等民间社会组织之中, 并赋予这类组织以一定的治村合法性, 使其在村“两委”的指导下参与村庄治理。
年轻人是旅游的主力军,年轻人有着极强的表达欲,他们通过拍摄上传短视频来吸引关注,相互比拼视频创意、内容、音乐、特效,全方位、动态化的展示景点,让更多的人通过线上短视频就了解到城市景区的全貌。观看视频的网友还可以在评论区实现与主播、观看者评论互动,对所拍摄内容进行点评、询问景点具体位置名称、旅游体验等。
(二)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流动性任职村干部积累社会威望、获得村民认可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流动性任职村干部在深入群众、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中获得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群众基础直接转化为村干部的社会治理资源。因此,社会威望的积累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与群众基础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强化的过程。流动性任职村干部可通过以下方式践行群众路线。
其一,常规的群众工作。具体表现为在日常交往和细小琐碎事务的处理中与农民形成紧密互动。村干部通过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务工作,与其建立有机连接,获得农民的认可和信任。这些认可和信任是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S 镇一位村书记所总结,成功的流动性任职村干部一般具备两种能力。一是解决问题、服务群众的能力。要始终牢记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是村干部的归宿和落脚点。二是善于倾听,尤其是在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陈述事情的发生经过时,有可能露出破绽,帮助村干部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同时,矛盾双方的“气”在讲述过程中得到充分释放,使得问题解决过后不易反弹。
其二,分类治理的群众工作。群众路线包涵着矛盾分析方法和分类治理方法,即群众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既有积极分子,又有落后分子和少数极端的顽固分子。因此,群众路线既包括对积极分子的组织动员,又包括对落后分子的批评、引导和教育,还包括对顽固分子进行必要的惩罚。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村庄整体公共利益的提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18]。对于极少数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损害村庄公共利益的谋利型钉子户,应坚决采取说服教育和必要的惩罚措施,使这部分有损良善秩序达成的“刁民”转变为有政治性、有担当的“良民”,而不能一味地妥协和退让。只有如此,村庄的公平正义观念才能得以重申,公共规则才能得到确认和输出,流动性任职村干部也才能赢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参考文献]
[1][7]杜姣.找回“自治”: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8.
[2][21]贺雪峰.治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3—36,202—203.
[3]张雪霖.村干部公职化建设的困境及其超越[ 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
[4]申端锋.治理转型下村干部不胜任难题——兼论乡绅模式的终结[ J].探索与争鸣,2014(7).
[5]印子.职业村干部群体与基层治理程式化——来自上海远郊农村的田野经验[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6]王惠林,杨华.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8][12]陆益龙.流动的村庄:乡土社会的双二元格局与不确定性——皖东T 村的社会形态[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9]陆益龙.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J].人文杂志,2010(5).
[10][11]贺雪峰.论中坚农民[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13]杨华,王会.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4][15]贺雪峰.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J].天津社会科学,2006(1).
[16]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1—22.
[17]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8—130.
[18]李祖佩.分利秩序——鸽镇的项目运作与乡村治理(2007—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79—287.
[19]王惠林.微自治:中国特色农村治理实践创新[D].华中科技大学,2018.
[20]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93.
[22][23]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8.
[作者简介] 王惠林,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李海金,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4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9)02- 0111 -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差异研究”(18ASH00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项目“微自治: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研究”(MX1810)
[责任编辑:戴庆瑄]
标签:村干部论文; 流动性任职论文; 农业型村庄论文; 村级治理主体论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