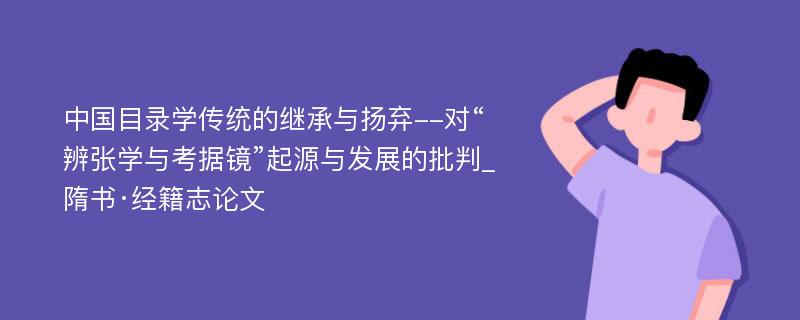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源流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是世代相承,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传统的积淀既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因而,对于传统的批判、继承、创新具有永恒的意义。
1 什么是中国目录学的传统
尽管中国目录学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许多长期积累,世代相承传、逐步形成的特点;但是,人们对中国目录学的传统——以多层次的形式呈现着、流传着,有别于其它民族的目录学质的规定性却有着较广泛的共识。这种共识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三重认同。
第一重认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源远流长。
《目录学概论》称:“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是在广泛分析研究前人的书目和目录学著述的过程中形成的。后世学者有关目录学的著述,均受到他提出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的深刻影响”[1]。
乔好勤先生认为:章学诚“总结了一千多年来的书目工作实践经验,吸取了历代目录学家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他的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古典目录学理论体系”[2] “代表了我国古代目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对近现现代目录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
第二重认同:“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核心。
《目录学》言:“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形成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思想体系”[4]。
余嘉锡先生说:“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之簿藉、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仅便检查者异也”[5]。
钱亚新先生提出:“我们相信‘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也是要求达到的最高境界”[6]
第三重认同:“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的传统。
《目录学概论》言:“中国目录学著称于世,素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7]。
彭斐章教授认为:“‘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形成了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应当成为我们民族的光荣与骄傲”[8]。
乔好勤先生亦认为:“‘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无疑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的精华和优良传统之一”[9]。
由上述三重认同,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蠡测:长期积累、世代相承,并以多层次的形式呈现着、流传着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中国目录学的传统。
2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结构
“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中国目录学的传统,它有自己的结构,这个结构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并表现出特定的功能。因而解析其结构,进而探究其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在特质和基本精神。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结构是怎样的?显然,要规定一个众所乐受的结构是很困难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形式繁多,没有一个公分母”[10]。因此,每个研究者只能各尽所能,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结构进行探讨,以逼近“真理”。
笔者认为:中国目录学传统由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三个层面构成。即:1.物质的层面,或称表面层面,它主要包括经过书目工作者的主观意志对书目工作对象——文献加工而产生的物——书目、索引、文摘等。2.制度的层面,或称中间层面,它包括由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投影而反射出来的书目制度,书目工作制度等。3.心理的层面,或称里面的层面,它包括由观念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等所反映并复制出来的书目心理状态。三个层面,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的“道器”范畴来概括,则物质的层面可称为“形而下”之“器”,制度的层面和心理的层面则可称为“形而上”之“道”。三个层面之间,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融贯,构成了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整体结构。
倘若我们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结构三个层面的关系和“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行双向解析的话,我们不难得出如下两点推论:
2.1 道器关系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哲学基础。
“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章学诚的终身任务和中国二千年目录学思想的精华,它是在章学诚的有关“道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章学诚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二者既互为表里,又同以关于道器关系的命题作为哲学基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篇》中提出了“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的著名哲学命题,并对道器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一方面,“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对于自然规律来说,“未有人而道已具”,“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对于社会规律来说,“天地之前,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也”。另一方面,他不仅提出“道寓于器”,而且肯定“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所以“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11]!这样,章学诚就明确地阐述了事物和它的规律的关系——客观存在的事物是第一性的,事物的规律是派生的,没有器就没有关于那个器的道。故仓修良先生说:“:这表明了他继承了荀子、柳宗元、陈亮、王夫之以来许多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哲学体系。‘道不离器’,……这一命题反映了章学诚‘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观点”[12]。当章学诚将这种不彻底的唯物论思想推之于目录学时,“道不离器”则成为其目录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章学诚《校雠通义》的第一篇即是《原道》(并且在初稿中曾直接标题为《著录先明大道论》),首先揭出了《原道》的重要意义:“由刘氏之旨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辩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13]。而在《枚雠通义·序》中,章学诚更是开宗明义地揭示了目录学之“道”:“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4]。也就是说,“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作为“器”的书目之“道”,而此“道”的最终目的乃是“宣明大道”。
2.2 “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是中国目录学传统整体结构的核心。
为了宣明“大道”,章学诚在目录学领域,一方面从“形而下”的“器”——历代书目的发展中总结归纳出“形而上”的“小道”——“辩章学术,考境源流”;另一方面又将其“折衷诸家,究其源委”所归结出来的“小道”——“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寓之于“器”,并对类例、类序、叙录等均提出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要求,试图“知言君子,或有取于斯焉”[15](事实证明在章学诚之后的君子多取于斯焉)。正因为如此,“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既是章学诚目录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思想的核心,还是中国目录学传统整体结构的核心。
3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特点
初步判定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中国目录学传统的核心,对于我们把握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特质,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样,明辩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特点,又可深化我们对中国目录学传统的认识,启迪我们对其与目录学现代化关系的思考。
受中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所经历的是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目录学毫无疑问也是从一条特殊的道路上发展过来并影响于后世的,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书目工作与学术研究相摄。书目工作与学术研究互相涵摄,学术研究包涵书目工作,而书目工作本身也就是学术研究,二者纠缠不清,这是中国传统目录学发展的特殊性之一。
从中国先秦社会来看;一方面,由于“学术统于王官”,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史官、博士之类;另一方面,由于书目工作的客体——文献也是“官守其书”,书目工作的主体亦是史官、博士之类。正是由于这二者主体的合一,使书目工作从一产生开始就与学术研究相互涵摄。《校雠通义》说:“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私门无著述文字,则官守之分职,即群书之部次,不复别有著录之法也”[16]。即是对这种相互涵摄关系缘起的说明。
秦汉以后,尽管学术已普遍下于私人,但是举凡大规模的书目工作活动都与大规模的学术研究活动相统摄,官府书目活动也好,私家书目活动也好,大抵都未能逾此藩篱,只是多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已。
书目工作与学术研究相互涵摄,相资而行,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书目工作周而复始,久盛不衰;另一方面又使得书目工作相得益彰,颇为社会所关注、重视。
第二,目录学与史学相摄。目录学与史学相互涵摄,史学包容目录等,目录学本身亦是史学,治史学以治目录学为基础,而治目录学又以完成治史学的任务为目的,二者盘根错节,缠绕不清,这是中国传统目录学发展的另一特殊性。
由于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基础的书目工作源于史,即《隋书·经籍志》所言:“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17]所以,张尔田先生说:“目录之学何昉乎?昉于史,……”[18]。也就是说目录学起源于史学,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正确的论断。中国古代目录学不仅胎息于史学,而且从其一产生开始就与史学息气相关。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诸多方面予以求证:
其一,在书目类型的划分上,中国古代一直将目录划归史部。自阮孝绪《七录》、魏征《隋书·经籍志》将“簿录”附列于史部开始,《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将“目录类”附于史部,直到《四库全书总目》将目录分为经籍、金石二种列于史部,中国古代书目类型的划分和学科范畴的归属大抵都是如此。
其二,在各类型书目中,素以“其体最尊”而著称的史家目录,自《汉书·艺文志》始,不是寓于正史之中,就是寓于别史等其它史书之中,成为史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目录之书又多以表现为史学之书为重。正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在评价《七略》时所说的那样:《七略》“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19]。
其四,治目录学者素以治史学者为功至巨。在中国古代治目录学者大抵都可称为史家,而治目录学成就最著者乃是史学家。古代的班固、郑樵、章学诚是这样,近现代的姚名达、余嘉锡、王重民等又何尝不是如此?
其五,目录学与校雠学二位一体,既为治史的事功之学,又共同完成一定的史学任务。尽管“目录之学,由来尚矣!《诗》、《书》之序,即其萌芽。及汉世刘向、刘歆奉治校书,撰为《七略》、《别录》,而其体裁遂以完备。自是以来,作者代不乏人,其著述各有相当之价值”[20]。但是,由于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所谓的书目工作与校雠工作并无二致,因而,目录学与校雠学亦无界限的划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古代目录学代表作的《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本身就是以“校雠”来命名的,还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上它们本身也是二位一体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二者同属治史的范畴,大凡史家无不是通校雠学者,而明清时期尤甚。故姚名达先生说:“目录学之成词,始见于清乾隆间王呜盛之《十七史商榷》。其在古代则与校雠学形成二位一体,名实近似,缭绕不清”[21]。张尔田言:“目录之学,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事乃与史相纬”[22]。
目录学与史学互相涵摄,治目录学是为了治史学,而治史学又必须先明目录学;目录学完成史学的部分任务,而史学思想又贯穿于目录学始终,二者纠缠不清,相资而行,因而使得目录学在古代倍受社会推崇,其学术地位较之今日目录学之地位则尤为显著。唯其如是,中国目录学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中国目录学传统内在蕴含着的区别于其它民族目录学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并予以初步地辩析。
3.1 着眼辩章学术,忽视学科建设
中国古代目录学一直是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轴而发展的,因而特别强调“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甚至在《校雠通义》一开篇就直言不讳地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3]。毫无疑问,着眼“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是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基本上相适应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许多以学术史而著称的书目。《目录学》说:“《汉志》反映了秦以前的中国学术文化,《隋志》反映了汉至隋代的中世中国学术,而《四库全书总目》则是对中国文化学术进行的一次彻底总结”[24],所言极是。但是,也正是因为“所谓‘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者,实在近乎学术史的任务”[25],目录学的学科建设被长期而广泛地忽视了。对此余嘉锡先生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吾国学术,素乏系统,且不注意于工具之述作,各家类然,而以目录为尤甚。故自有目录之学,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盖昔之学者皆熟读深思,久而心知其义,于是本其经验之所得以著书。至其所以然之故,大抵默喻诸己,未尝举以示人”[26]。学科建设的严重忽视使得中国目录学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后人之所加于向歆者,较之向歆之所已发明而实践者,究属戋戋有限,与二千年之长时期比照,惭愧抑不胜矣。至于专门研究校雠目录之书,尤屈指可尽。吾人欲知此学之原理为何,方法为何,仅可从散在各种目录之字里行间寻绎之,或可得其一鳞半爪,然后组织成为有系统,有条理之学术焉”[27]。“再可以说一句,自刘歆创《七略》后,虽有郑樵章学诚等加以精讨,但其范围,只是平面的发展,并没有直线的进步。换言之,自西汉至今日,虽已有了二千年的历史,而目录学一科,仍就是在一个圈子内打走围,正如同其它学术一样没有进步”[28]。以致今日,所谓的中国目录学史仅为书目发展史,毫无思想史可言。
3.2 重道轻器
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道轻器——重精神轻物质,重义理把握轻器物制造。一方面,“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目录学理想,这不仅是因为古代目录学家们大多以通过类例,类序,解题等来追求至善至美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小道”境界,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还以这一“小道”来最终“申明大道”,也就是为古代社会的正统“大道”服务。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难从许多“因器而显道”的例子中得到应证。如从类例上看,尽管七略四库在数千年中类目不乏变化,但是,代表占统治地位“大道”的“经”则千古不变始终位居各分类法之魁首。时至今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书目应具有思想性(或阶级性),但是,如果以思想性(或阶级性)作为最高目的,也就丧失了书目本身。另一方面,“器”又被中国古代目录学家所轻视和排斥。由于“申明大道”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目录学任务,人们对一切不能或未能很好地“申明大道”的“器”往往持讥议和排斥的态度,《隋书·经籍志》对诸家目录的抨击就是典型的例证。荀勗的《中经簿》,上承《七略》,下开四部,至为重要,而《隋志》谓其“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29]。其于荀勗之不满,溢于言表。此后自东晋义熙至宋、齐、梁、陈、隋均有官撰目录,而为书皆只数卷,并不著解题,《隋志》又讥其“不能辩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己”,并言“博览之士,疾其浑漫”[30]。既便是宗刘之作——王俭的《七志》,阮孝绪的《七录》,因其“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隋志》讥其“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割析辞义,浅薄不经”[31]。对此,刘纪泽先生曾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由是言之,则凡目录不著解题但记书名者,故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即有解题者,若其识解不深,则为美犹有憾。盖王俭之《志》,惟详于撰人事迹,于旨归论谬,少所发明,阮氏《七录》,或亦同之。故虽号博览之士,卒难辞浅薄之讥,观其一则曰,‘于作者之义,无所论辨’,再则曰,‘不述作者之意,未为典则’,则知凡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帐簿式之目录,盖所不取也”[32]。余嘉锡亦言:“唐时目录家,如毋煚、释智升之徒,其所主张,率同斯旨”[33]。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目录学对不能遵循“辩章学术,孝镜源流”这一宗旨之“器”——书目采取鄙夷、讥议、排斥的态度,所以中国古代目录学自汉以后在制度的层面上一直是在一条死胡同中发展,并无多少革新进步。故姚名达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总结道:“我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分类之纲目始终不能超出《七略》与《七录》之矩矱,纵有改易,未能远胜。除史部性质较近专门外,经子与集颇近丛书。大纲已误,细目自难准确。故类名多非学术之名而为体裁之名,其不能统摄一种专科之学术也必矣。编目之法,仍依类别为序;同类之中,多以时代为次。活页编次之道,检字引得之术,编号插架之方,皆素不讲究,殊不便于寻检,非熟于目录学者莫能求得其所欲见之书。……,其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34]。所言极是。
3.3 重书目的学术价值,轻书目的情报职能
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核心的中国目录学传统的又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重书目的学术价值,轻书目的情报职能。尽管章学诚等亦提出过书目之功能在于“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但是,由于目录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由于传统目录学重道轻器,人们是很难通过书目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刘纪泽先生在《目录学概论》中曾引述过许多名人俗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而终难得其要旨的例证:“顾黄氏之言曰:“余从事于此,逾三十年,自谓目录之学,稍窥一二,然阅历益久,知识益难,曾有所见古书录之辑,卒不敢以示人者,以所见之究未遍也’(序汪刻郡斋读书志》)。又云:‘流光荏苒,著述粗疏,即一目录之学,涉手愈知其难,遑论其他哉’(跋湘山野录)。顾千里《题钞本集古文韵》亦云:‘夫书之为物至多,人生读之难遍,以榭山之博览,弗知北宋本之尚存,如仆者虽知别有南宋本,而垂老始获一见。’近江阴缪氏,自谓寝馈于目录学者垂三十余年,而俗然犹以为未足,然则目录之学,亦岂易言哉”[35]。就连在《十七史商椎》中充分肯定“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的著名史学家王呜盛也不得不直言不讳地承认:“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36]。由此可见,目录学既然不能被通儒名家所轻易掌握,一般人士自然更是可望而不可及,所谓的“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也就不过是痴人梦呓罢了。
书目并非本质意义上的书目,而是地地道道的学术史,自然难以指导读书治学,更毫无情报职能可言。顾实所言:“清儒金榜曰:“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信哉,金氏礼学卓卓,故能为此言也。……然不通《汉艺文志》,诚不可以读天下书;而不读天下书, 亦不可通《汉艺文志》’[37]。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3.4 崇古守旧
受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制约,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着贯穿始终的先王观念和传统崇拜思想。这一特点反映到中国目录学领域就是在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上存在着鲜明的崇古守旧特点。
且不说自向歆以后,历代皇朝整理藏书、编制书目均以“如汉代故事”来标榜效仿,就是所谓的中国古代目录学集大成者章学诚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崇古守旧者。对于这一点目录学家吕绍虞先生曾作过十分精辟而与众不同的论述:“其实,他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远远不及郑樵。郑樵总结了向、歆以后一千多年来目录学方法上的经验,并且大胆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学诚则处处以‘古’字当先。谓郑樵‘于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古人最重家学’,‘古者同文称治’,‘古者校仇书’,‘古人校仇’,‘以进于古人之法度’。他说:‘鄙人不甚好古,往往随人爱慕而旋置之,以谓古犹今耳。至于古而有用,则几于身命殉之矣’。大概他对于刘略班志认为是古而有用的东西,所以不惜化费精力和时间加以研究。……,在当时没有人重视这部《校仇通义》,后世也没有多少人研读过它,至于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更难说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新颖的见解,可为后人学习之资”[38]如果说古人崇古守旧乃是情理之中的事的话,那么近现代人如此崇拜传统,格守陈规则不可理喻。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核心思想,也是要求达到的最高境界”[39]。“以言目录学之范畴,最宜借用章实斋之解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此二语言简意赅,实可谓为不易之定论”[40]。今天,在许多人都已认识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不过是良莠并杂的历史产物的情况下,仍有不少人称之为“优良传统”,这也未免太崇拜传统了。
诚然,崇古这一特点对于中国目录学历史的积累。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同时又使衰暮之气弥漫于目录学界,造成墨守陈规,不思革新的陋习。因此,往古是值得借鉴的,但不值得也不应该膜拜,更没有必要格守。
3.5 妄自尊大
由于上述诸特点的作用,使得中国目录学传统在深层次的心理层面上又始终存在着妄自尊大的特点。一方面,被誉为中国古代目录学大师的郑樵、章学诚尽管其贡献不可磨灭但他们多少总表现出不自觉的妄自尊大。郑樵深居夹漈山苦读三十年’夏不葛亦凉,冬不袍亦温,肠不饭亦饱,头发经月不栉,面目衣裳垢腻相重不洗”以致亲友们把他看作“为痴,为愚,为妄”[41]。他立誓“集天下之书为一书”,但是其《通志》“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现其有何等价值”[42]。而郑樵在《通志·序》中对“二十略”的自我评价是:“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43]。其狂妄自负已跃然纸上。他要求书目应“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可是其《通志·艺文略》则距此十万八千里。章学诚亦何尝不是妄自尊大呢?吕绍虞先生对此曾作过一针见血的评述:“学诚对校仇同文史一样,自负不凡。他说:“惟文史、校仇二事,鄙之颇涉藩篱。以为向歆以后,校仇绝学失传’。又说:‘至于史学义例,校仇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标著之名’。这是何等自负的口吻”[44]!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影响,今人总是在不自觉地拔高目录学的学术地位,夸大书目的作用。不是引清人王呜盛之语“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来渲染目录学之重要,就是引金榜之语“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来夸大书目的作用。其实,目录学并非“学中第一紧要事”那么重要;“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也未必尽然,要一般人士都明目录显然是不切实际也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不读天下书,亦不可通《汉艺文志》”,明目录十分不易,而且还因为许多不明目录者也未必终是在乱读。惠世荣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一个目录学研习者,总想找出一些例子说明目录学之重要,证明它是‘治学门径’、‘成才之路’等,这种努力过去有,现在也不乏其人。近有意细读《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传》及《诺贝尔医学奖金获得者传略》二书,想从中寻出一些蛛丝马迹。不料,结果却大失所望。简言之,这些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当代最高的所谓‘治学者’和‘人才’了吧,都似乎未精通什么目录学,也好象都未‘从目录学入手’,这个事实确实令人有些泄气。掷下书来,冷静思索一番,忽有所悟……。说句挖苦的话,如果上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一开始听从我们有些‘目录学家’的‘教导’,仅留心于目录之间,恐怕其中大多数人至今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熟知几种目录盒子的老图书馆员罢了,如何能够对人类文明作出那样大的贡献呢?有一种错觉,似乎对本学科强调得越重要,说成是法力无边,才会使别人敬畏。其实这往往适得其反。卖瓜时吆喝几声是必要的,但要警惕成为王婆”[45]。诚然,科学技术的增长与书目文献的增长的确存在着正比的发展关系,但来自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都表明现代科研工作者的情报意识和情报能力普遍低下,而科学技术仍然在按几何级数迅速发展,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目录学和书目文献的作用进行冷静而富于理性的思考。
4 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中国目录学的传统已成为既定事实、但应如何批判地继承,这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对此,哲学家丁宝兰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正如任何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一样,人们也不能选择一出生就被包围着、被感染着的传统文化。当然,人们的后天生活可以有选择地学习其他文化。不过,尽管他们极力要同传统文化相决裂,但看来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假洋鬼子’始终还是真的炎黄子孙”[46]。
诚然,要完全割裂中国目录学的历史,象倒洗澡水连同盆里的小孩一起泼掉一样抛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并不是僵死不变的,关键的是在于我们能否赋予它新的含义,作出符合现代化书目工作需要的科学解释”[47]。这似乎是一条发展传统的途径,但是,迄今为止仅美籍华人钱存训先生一人曾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过一点新的解释。他说:“中国学者对于目录学的观念,向来重视其中著录的内容。 所谓‘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实际是一种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这与现代所谓‘统计书目学’的理论极为相似,即从分析书目的内容,进而追溯文化的成长”[48]我们正期待着更全面更科学的新的解释。
笔者认为对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的继承与扬弃的关键不在于进行新的诠释,而在于创新。
4.1扬弃“学术史”的任务,把当代目录学建设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即:“(1)在科学研究方法上广泛地吸收信息论、控制论、 系统论、计算机科学、数学等与目录学联系紧密的理论和方法,开拓目录学发展的新领域,充实完善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科学化现代化。(2)在学科领域的开拓上,突破传统的束缚,以书目的情报价值为中心,将目录学置于整个社会信息系统之中,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研究目录学和社会文化、现代科学技术、读者的情报需求规律、文献的发展规律等方面的联系和整合效应。(3)在科学的交流与融合上, 广泛地引进和吸收国外当代目录学理论与方法的优秀成果,把中国当代目录学理论和方法从揭示一国或一个民族语言的书目工作规律上升到揭示全人类书目工作规律的新高度”[49]。
4.2 扬弃“申明大道”的任务, 将中国当代目录学建设成一门致用的科学。目录学作为一门应用科学应立足于通俗易懂、简洁实用,无需纯粹地追求体系的自我完善和高大玄奥的理论,否则又会重演“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的覆辙。正如姚名达先生所言:“目录学成为最通俗之常识,人人得而用之,百科学术庶有孚乎!”[50]
4.3 革除传统目录学的那种重“论”、“史”轻“法”, 拥有“富饶”的理论和“贫困”的实践的固疾,吸收解题、互著、别裁等传统书目工作的优良方法,把中国当代目录学建立在现代化书目工作的基础之上。即:(1 )将中国当代目录的发展建立在书目工作自动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之上,以以计算机、现代通信技术等为主体的书目工作现代化为研究重点,将MARC、CD—ROM 情报检索系统和网络等理论和方法真正纳入目录学的学科体系之中,并予以完善化科学化。(2 )打破中国目录学对文献的产生和发展、种类与类型、特征与作用等的静态定性描述研究的格局,把对文献的静态定性描述研究上升到对文献发展变化规律的动态定量预测研究之上,充分地研究“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把中国当代目录学对文献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3 )突破传统目录学囿于狭义“书目”工作的桎梏,把书目工作上升到二次文献工作的新高度,研究一切不同类型不同载体的二次文献,使中国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在解决不断增长的巨大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的矛盾中具有更广泛更深刻的指导意义。(4 )从对传统书目工作的总结性研究和对现代书目工作的描述性研究转向对现代书目工作的概括性指导性研究和对未来书目工作的预测性研究,使其从现有的微观书目控制的目录学体系升为宏观书目控制的目录学体系,使中国当代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站到世界书目控制的前沿,真正地弘扬祖国的目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