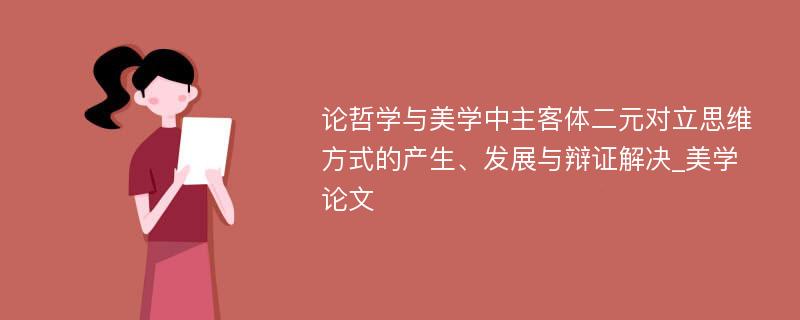
论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产生、发展及其辩证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主客论文,思维模式论文,学中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什么是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什么是哲学、美学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呢?我觉得存在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只要把存在划分为主体与客体,就是二元对立;一种认为划分主客体并不就是二元对立,这种一分为二,可能走向二元对立,也可能走向和谐统一,关键在于承认不承认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否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沟通、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拒绝这一点就是二元对立,肯定和实践这一点就不是二元对立。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观点。有学者说:“主体性哲学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论基础上,这种本体论把存在分割为主体与客体两部分,古代哲学以客体作为主体的依据,近代哲学以主体作为客体的根据,它们都不能避免二元论的弊端。”(注:杨春时:《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这就是说,只要把存在划分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那就是主客体二元对立,这样的主客二分的历史,就是二元对立的历史。不同的是,古代的对立以客体为根据,近代的对立以主体为根据。事实是这样吗?逻辑是这样吗?答案可能很不相同。
我觉得客观存在是统一的,也是差异的、矛盾的。差异、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处不在的,统一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万事万物的差异、矛盾的性质、形态是不同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立的,一种是非对立的,或者说是杂多的。二元对立是指差异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截然相反的,如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肯定与否定、前进与后退、正与反、是与非、阴与阳、黑与白等。同时,对立的双方又互为依据,失去了正,就没有反;失去了美,就没有丑。非对立的杂多则不具有这种本质上的不同,如酸、甜、咸、辣,又如红、黄、蓝、白,其性质各自独立,彼此不受影响,失去了红,仍有黄、蓝、白,失去了酸,仍有甜、咸、辣。黑格尔作为辩证法的大师,对我们仍有意义。尽管20世纪以来,批判、否定黑格尔成为一种时髦,谁不骂几句黑格尔,似乎就不现代,就不后现代,就不够时尚,但深入剖析一下近代、现代、后现代的哲学和美学思潮,便会发现它们最致命的弱点,恰恰就是丢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落入了极端对立的桎梏。现在呼唤回到黑格尔,回到马克思,回到辩证思维,也可能是适时的。黑格尔早在《小逻辑》中就论述了杂多和对立两种不同的矛盾形态。他说:“异第一是直接的异或杂多(die Verschiedenheit)。所谓杂多即不同的事物各自独立,其性质与别物发生关系后互不受影响,而这关系对于双方是外在的。由于不同的事物之异的关系是外在的,无关本质的,于是这‘异’就落在它们之外而成为一第三者,即一比较者。”(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59页。)又说:“异的本身就是本质的异,有肯定与否定两面:肯定的一面乃是一种同一的自我关系,亦即坚持其自身的同一,而非其自身的否定。而否定的方面,即是异之自身,而不是肯定。于是每一方面之所以各有其自身的存在,乃由于它不是它的对方,同时每一方面均借对方而反映其自身,只由于对方的存在而保持其自身的存在。因此,彼此本质的异即是‘对立’。在对立中,相异者,不是任一别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别物,这就是说,每一方面只由于与另一方面有了关系方得到它自己的性格,此一方面只有从另一方面反映回来,方能自己照映自己。另一方面亦然。这样每一方面都是对方自己的对方。”(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63页。)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差异、相互矛盾的,而差异、矛盾大体划分为两大形态,一是“杂多”,一是“对立”。前者是外在的异、非本质的异,后者是内在的异、本质的异;前者之间是相似与不相似的关系,彼此独立,互不相涉,后者则是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是“正相反对”的关系。一方的存在是由于它的截然相反的对方的存在而产生的,失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
不仅事物的矛盾有非本质的杂多和本质的对立,而对立也有绝对的对立和辩证的对立之分。绝对的对立认为,既然对立的双方是正相反的,那么彼此之间就不可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更不可能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如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在主观和客观、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有他提出的时间与空间等一系列二律背反的命题,大体上都处在这种对立之中。这种绝对对立的不能沟通的观念,是真正的即我们所说的主客二元对立。这种绝对对立的观念,在西方影响深远,根深蒂固,可以说自康德以来的西方近代哲学、现代哲学和后现代哲学(除去谢林、黑格尔、马克思等人)都贯穿着这一根本的观念。在它们那里,压根儿就不相信客体与主体等对立双方之间,能够沟通,能够和谐,能够统一。所以,当存在主义寻求消解二元对立的途径时,首先要把客体世界设置为主体自身,这样主客体的关系就变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这样一来,主体与主体之间就可以相互融合、相互沟通了。“主体间性”的提出,正反映了绝对对立观念之深。而辩证的对立则与此相反。它认为矛盾的双方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不但截然相反,而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相互融合、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它们之所以可以和谐统一,恰恰因为相互对立,在相互关联的对立中,埋下了相互融合、和谐统一的种子。它们对立地产生与发展,同时又实现了相互融合、相互转化、和谐统一。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辩证的对立统一观念,对于长期陷入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的西方近现代文明来说,是很难读懂的,也是很难理解的,恐怕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还是很难被接受的。应该说明的是,这种辩证的对立不是西方某些人所说的绝对的二元对立。不能一提主客二分,就说是二元对立,甚至把辩证的对立也说成是绝对的二元对立,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也说成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恰当的。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又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问题还可以进一步,不但有两种不同的对立观念,而且对二元对立的解决,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强调斗争的方法,一种是强调协调的、和谐的方法。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强调斗争,而毕达哥拉斯则主张和谐。一般地说,西方的传统更强调斗争,而中国的传统更强调和谐(当然在中国也曾有过偏于斗争的历史)。前者突出对立,激化矛盾,主张以斗取胜,认为斗争是发展的动力,不斗争矛盾就不能解决,事物就不能发展;后者则淡化矛盾、缓和对立,协调沟通,以和取胜,认为“和实生物”,和则万事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对于和解来说,主客体的对立性就更加淡化、更加微弱了。而一味的强调绝对的二元对立,则会拒绝和解、和谐的解决方法,丢掉中国的中和、和谐的传统,甚至不能适应时代的精神和需要。
二、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不是从古就有的
应该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末,人类逐步走出自然界,并同动物逐步分离。那时,人与自然还没有明显的界限,主体与客体并未分化,客体是主体,主体也是客体。人类的幼年时期与一个人的孩童时期一样,都把世界看作是人自身,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正是他们的典型杰作,如我国的蛇身人首的女娲、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等,真实地记载了人与自然的合一,说明了原始人还没有真正的人的意识,还没有人的自觉。动物图腾的广泛存在,也说明原始人结成的社会群落,常把自己看成是某一动物的后裔,是龙或凤的同类,惟独还没有人自己,但这种主客未分的合一,是原始的,是未开化的。若向往这种未分的状态,要保持这种状态,那就不可能有人类的诞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人的独立化、主体与客体的分化,并不全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文明的不祥之兆,而首先是有伟大的历史功绩的。可以说,人从自然走出,人把自己与禽兽分开,正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开端。舍此,原始人就会永远留在远古的混沌中。
从远古到古代,从原始群落到奴隶的、封建的古代社会,从人兽同体到人的独立,从主客浑然到主客二分,是人类文明创造和发展的关键一步,但这种主客二分有三大特点:一是主体与客体有明确的区分,客体就是客体,主体就是主体,自然就是自然,人就是人,甚至人已开始羞于与禽兽同类,“禽兽不如”这句话逐渐成为人类最大的耻辱。第二,这种主客二分并未走到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生相克、相互融合、和谐统一的。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水、火、气,德谟克里特说是原子,人与万物具有同一性,它们源于共同的宇宙本体,又复归于自然本体,这也是一种天人合一,是存在论上的天人合一。柏拉图创造了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他们都把人放在理念发展和宇宙结构的整体中来理解,同样也是天人合一的。这种主客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在中国古代更为显著。老、庄首创自然哲学,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念,而作为万物之一的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尊重自然,亲和自然,“要无为而为”,顺应自然,要“以天合天”,皈依自然,“天地与我同在,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是何等的亲密无间啊!与老、庄偏于自然相较,孔、孟儒家则偏于社会。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偏于善的伦理哲学。他们认为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核心,提倡“仁者,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的相爱相助。儒家的大同世界就是一幅人人相爱、天下和谐的人间美景。这种思想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到明代李贽出来,首倡“童心说”,才逐步冲破这种和谐的观念,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第三,这种统一以客体为基础,客体存在是绝对的,主体依附于客体,主体未能得到充分的独立的发展。人依附于自然,个人依附于群体、社会,人的自由、人的自满自足是建立在有限的基础上的,因此古代和谐美的理想和艺术是素朴的有限的和谐。第四,人从自然中走出,为了要生存,要发展,面对这个从中走出的自然界,反而感到陌生、惊奇、神秘、可怕,因而,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便成为古代哲学思考的首要问题,认识论哲学也便成为古代哲学的一大特征。在认识中,主观能否符合客观,思维能否符合存在,人的认识能否符合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古代哲学家也提出了和谐统一的主张。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说:“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我国古代的老子也认为,通过“心斋”、“坐忘”、“涤除玄鉴”,可以获得一个澄明的世界。孔子虽然很少讲认识论,但在他“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经验中,也可看出人是能够认识外界事物的本质规律的,并达到主体的自由。古代哲学不但在存在论上讲“天人合一”,主客体统一,而且在认识论上也讲主客观统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总之,古代哲学是在一元论的基础上讲主客二分的,这种主客体关系是素朴的、和谐的、统一的,它还不是在二元论基础上产生的绝对的主客对立,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不能说,古代哲学也存在主客二元对立,那样就会违背历史,违背实际。正是在古代哲学的主客体素朴辩证统一的基础上,产生了古代素朴的和谐美与和谐的古典美的艺术,产生了古代素朴和谐的人与对象、主体和客体的审美关系。从客体对象说,对象是和谐的,不是分裂对立的,对象客体对人只呈现出它的和谐的、美的形象,而遮蔽了它的崇高的、丑的、荒诞的面目;相对于分裂、对立、多元的近现代来说,它是单纯的、贫乏的、不复杂的。从主体方面说,人的心理结构也是单纯的、和谐的,它没有经过感知、意志、情感、理性和无意识的裂变,它还没有感知、欣赏和容纳崇高、丑、荒诞、悲剧的能力,所以古代艺术对丑是排斥的,古代绘画很少描绘丑,即使间或遭遇到丑,也是将丑美化,纳入到整体的古典和谐之中。古代人难于欣赏主客体之间尖锐对立的崇高,对荒山大漠、悲惨绝望,不是视而不见,就是将其壮美化。古代人把压抑的崇高,把非经一跃方能进入自由境界的崇高,描绘成豪放的、挺拔的、洒脱的、一直处于自由境界的壮美,这也就是中国古代艺术只有优美与壮美两种和谐美的类型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只有大团圆式的“古典悲剧”而没有严格的近代意义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和谐美的对象与和谐的未分裂的主体的审美心理,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构成了古代素朴和谐的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这种关系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不是多元的;是单纯的,相对近代是不丰富的、不复杂的、不够深刻的;是有序的、稳定的,相对于近代不是无序的、激荡的、开放的。它只能构成和谐的古代的审美关系,而不能构成近现代的二元对立的崇高的、丑的审美关系和后现代的荒诞的多元审美关系。
三、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近代的产生与发展
真正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是从近代开始的,而这时的二元对立绝不是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谬误。其实恰恰相反,若没有主体的彻底自觉和独立,若没有形成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就没有近现代文明,没有康德,甚至没有黑格尔,没有德国古典哲学,没有马克思。同样,也就没有近代的崇高美学、现代的丑的美学和后现代的荒诞美学及无差别美学。主客二元对立是近现代文明的助推器和催生婆,不能一笔抹杀。
近代主客二元对立与古代主客一元统一的哲学,正好形成了完全相反的特征:第一,古代哲学以客体为基础,是一种客体哲学。近代哲学则从客体转向主体,康德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结束了古代的客体哲学,开创了近代的主体哲学。康德哲学的精神,实质上是研究人如何从自然人、感性人,经审美人,到达社会人、理性人。自此,主体、理性的地位逐步攀升,一个大写的人日益独立于天地之间,神的光环日益暗淡,人代替了神,成为宇宙的主宰。第二,与古代的主客和谐统一的素朴辩证哲学不同,近代的主客处于绝对对立的状态,主体与客体本质上根本不同,相互没有联系,不能沟通,不能互补,不能融合,一句话,不能达到统一。主客是二元的,它们之间的对立是根本不能解决的。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大陆理性派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是他一个著名的命题,他把人的本质规定为“思”,即思想,他把主体人的思想实体与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水火不相融地对立起来,由此认为世界是由人与物、思想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构成的,第一次形成了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第三,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自笛卡尔以来不断发展,日趋极端化和绝对化,大体经历了近代、现代、后现代三个时期(注: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一个时期大约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到康德哲学的综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美学上是从柏克到康德的崇高美学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学,在艺术上是从浪漫主义的呐喊反抗到现实主义的解剖、批判。从培根经霍布斯、洛克到休谟,强调了认识的感性经验方面,提出了归纳法,形成了经验主义哲学;从笛卡儿到斯宾诺莎,强调认识的理性方面,发展了范畴、概念的演绎法,举起了理性主义的旗帜。两军对垒,各执一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把理性派先验的概念范畴和经验派后天的感性经验结合起来,但他不但没有克服二者的对立,反而把这一对立更加深化了,因为他的先天综合判断,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物自体”是不可知的,从而把思维与存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划上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第二个时期,大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从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的形成发展,到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创造。科学主义重视工具理性,强调科学技术,压抑、贬低人文科学、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则相反,它重视人的意向、生命和本性,批判和抗拒现代科技对人的物化、单面化、碎片化。两者对立,但也有共同之处。一是双方都是片面的,都各讲一面的道理,都在自己的领域作出片面的但又是独创的贡献;二是两者都是非理性的。本来科学是讲理性的,是讲本质和规律的,但20世纪的科学主义思潮,却以感性经验为标榜,这从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经英国穆勒、斯宾塞,奥地利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到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和结构主义,都抛弃形而上学,力图建立经验基础上的实证科学,因此它们不过是近代经验派的哲学的现代演化。与此相应,美学上是丑的升值,丑冲破崇高的外壳,彻底扬弃和谐的因素,登上了现代文化主角的宝座;艺术上是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向全世界的蔓延;而文学批评是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本论到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嬗变。本来,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本主义本应是理性的思潮,但20世纪的人本主义却偏于研究人的非理性方面,从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偏向人的意志、意向、意欲开始,经尼采的超人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弗洛依德专注无意识、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哲学,一步一步地向人的本能深化,这一方面丰富了对人的主体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理性的人坠落到感性本能的深渊。在美学上,这一切表现为叔本华的意志论美学、尼采的超人美学、柏格森的生命美学、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美学、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等。与人文主义比较起来,科学主义更为强大,更占优势,特别是分析哲学几乎风靡欧美,独霸一时。分析哲学大体上有三大特征:一是以经验为基础,二是以分析方法代替黑格尔式的思辨方法,三是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分析哲学的精神之父维特根斯坦,创构了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事实”构成经验,语言和科学就是表述这个经验世界的,哲学就是运用逻辑的方法对科学和语言所陈述的这个经验世界进行分析。因此,分析哲学以分析的方法取代演绎的逻辑思辨,又以语言分析为关键。它认为,语言运用的正确与否,是造成一些哲学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因此,正确地运用语言,就会消解由于错用语言而产生的假问题。同时,语言的结构又不是随意的,它是按照逻辑规律组织起来的,这样一来,语言分析又必须深入为逻辑分析。在分析哲学的精细分析中,发现了日常用语的不精确。因此,弗雷泽、罗素等人致力于创造一种人工语言,以提高语言陈述的精确度。总之,分析哲学就是一种排斥人的、纯经验的、纯客观的哲学。与科学主义执着于经验、语言、逻辑之外的客体不同,人文主义却紧紧地抓住意志、意向、生命、无意识这些人的主体特性。人本来是感性与理性结合的生灵,20世纪的人文主义却只对意欲、本能、无意识情有独钟;人本来也是从自然界诞生的,人文主义却试图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反而认为世界就是主体的创造。叔本华作为意志论的代表,可以说是人文主义的滥觞。他认为,“世界是我的意志”,意志就是自在之物本身。尼采进一步提出权力意志,认为世界本身就是权力意志。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则认为世界是一种“意识之流”、“生命之流”,把客体说成是主体的意识和生命本身。而到了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已经不见了客体宇宙,剩下的只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了。其中,尤重于“本我”,这是一种生命冲动,是性本能,是完全先天的潜意识的。这个与客体彻底决裂的主体,也算走到了尽头。主体和客体的裂变和对立日益尖锐,既带来片面的开拓、丰富和创造,又带来了极端化的褊狭和弊端,这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发展第三个时期的基本特征,也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导倾向。从客体方面说,客观世界由绝对实体(理性本体),经现象世界(感性本体)蜕变为一种平面的、破碎的、混乱无序的世界(荒诞世界)。康德的物自体是一种绝对的、理性的本体,是一种自在之物;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则把由“原子事实”构成的经验世界,作为宇宙的本体,它已失去了康德的理性特色;而到了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逻辑主义,则进一步把世界平面化、无序化、破碎化。从主体方面看,由理性主体经过感性主体而异化为分裂的个别主体。从康德追求社会的人、理性的人,到尼采高喊“上帝死了”,也就是理性的人死了。尼采期待的“超人”和柏格森倡导的生命主体,都是张扬的感性的人。到福科的“人也死了”,则连感性的潜能也耗尽了,最后是“主体的黄昏”,余下的只有多元的单个的人。在美学上便是由崇高经丑向荒诞的演进,在艺术中便是由近代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经现代主义而向后现代主义的嬗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也随着这种主体与客体的日益疏离而不断发展,不断改变。在近代崇高和近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里,主客体由对立、斗争而趋向于和谐,趋向于统一,即使在主体遭遇挫折、失败乃至牺牲的命运中,他仍然抱着必胜的信念。在丑和现代主义艺术中,感性的人失去了普遍的理性,无法把握日益疏离的客观世界,他困惑,他无奈,但他仍在绝望地挣扎,仍有一颗未死的心,主体与客体处在一种无法解决的对立、纷争、激荡之中。在荒诞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主客体是两个极端的矛盾结合体,一个是主客体的对立走到极端,一个是主客体对立的消解也走到极端。荒诞剧、黑色幽默是前一个极端的代表,而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特别是大众艺术、消费文化则反映了后一种倾向。在这里,分裂、对立的现象世界,同时就是一个多元的相对的世界;耗尽一切潜能的非理性的个体的人,也是多元的相对的人。二者构成的正是德里达的后现代的、多元的、相对的解构关系。这两个极端,正是后现代矛盾集合体的必然产物,是这个矛盾体命定的两面,但它的历史走向,当前似正在由对立的极端,一百八十度地急转弯,日益走向无差别式的消解的另一个极端。崇高与荒诞作为过渡形态,有其近似之处,即两者既是对立的又趋向和谐,但它们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崇高是理性主体的高扬,是理性痛苦而又乐观的凯歌;荒诞则是感性主体的消亡,是感性主体的无奈、尴尬、非悲非喜的荒诞剧。本来对立已经发展到混乱的极端,却幻想它突然间就化为无差别的美妙人间,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
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日益极端化,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日益分裂,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开始思考弥合和消解这种对立的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道尔诺较早地关注到这个问题,提出“主体与客体同一”的一元论,反对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认为这种“同一”就像阴阳两极产生的磁场一样,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动向。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意向性”理论,这种意向性包括意向主体、意向对象(客体)和意向活动三个方面。显然,他企图用意向活动连接乃至弥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断裂,可惜这种意向活动只是一种意识活动。假若他再向前跨出一步,向主体的意志实践活动靠近一步,将取得更为积极的成果和影响。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力图以存在论,特别是以人与自然、感性与理性尚未分化的“此在”,来消解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存在主义者还提出“主体间性”理论,把人与自然界、人与他人的关系都说成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他们认为主体与客体世界是不能沟通的,但把客体看作主体,主体与主体就可以沟通了,就融合了。其实,客体对象世界是否定不了的,把它说成是主体,它并不就是主体。同时,把你、我、他之间都看成是主体间性,而不同时是互为主客体,也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主体间性”概念不久在西方现代哲学中就不再提了。如在杜弗朗的美学中,被海德格尔等人所抛弃了的客体(对象)和主体这一对范畴,又重新恢复了它们的地位。存在主义不仅没有消解二元对立,反而加剧了二元对立,加剧了主体的衰亡。康德的主体是理性的主体,是普遍的社会的主体。海德格尔由康德的抽象主体,走向感性生存着的“此在”。雅斯贝尔斯则由海德格尔的主客体未分化的但又非某个体的“此在”,走向“我”这一非知识性的个体决定论。如叶秀山所阐释的那样,这个“我”不是由因果律决定的,不是“我”的过去决定“我”的现在,不是“我”的现在决定“我”的未来,而是“我”吸收了过去和将来,“我”自己决定“我”是什么(注: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这种“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决定论,把个体主体突现到首要的地位。解构主义的德里达,则在否定客体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一切本质、中心,把一切都归于个体主体的虚构,它用主观、相对、多元勾销了绝对性和普遍真理,由二元对立发展为多元解构。当然解构主义也有它否定权威、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它对传统的挑战同时为新的美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总之,他们拒绝客体存在和理性认识论,拒绝知识哲学,只强调主体存在、个体生存的本体性。就这样西方的近现代哲学,便在消解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努力中,悖论式地走到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极端。看来西方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靠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来消解二元对立注定是不可能的了。
四、马克思对主客二元对立辩证的科学的解决
马克思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主客体对立作出辩证的科学的回答。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引入了劳动、实践的观点,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次,从发生学、历史发展阶段论的历史视角,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主体与客体分裂以及对立和统一的辩证过程。当然,在当时愈来愈严重的形而上学思维的笼罩下,西方现代哲学家很难理解也很难充分重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伟大意义和丰富的科学内涵,以致于马克思之后直到海德格尔、德里达的西方哲学、美学,仍在原来的轨道上愈走愈远,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成为一个巨大的理论悲剧。
马克思认为主体和客体的产生与划分,都是从劳动实践开始的,正是劳动实践创造了人,创造了主体,使人脱离了动物界,使人获得了自由的本质;又正是劳动实践,创造了“第二自然”,创造了属人的自然,创造了人的客体世界;还是劳动实践同时创造了主体和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使陌生的客体世界成为主体的对象,同时也使主体成为对象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不仅主体与客体的划分、裂变、对立是在劳动实践中产生的,而且劳动实践也内在地规定着二者的同一性、和谐性。主体与客体、人与对象世界为什么能够和谐统一呢?这是因为劳动实践本身是一种二重化的活动。在劳动实践中,一方面,人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同时依据自己主体的目的和要求,来改变自然、创造世界,使世界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自我确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劳动不仅引起了自然物的形式的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他的目的”(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页。),这样被改造了的自然界便成为人类的创造物,“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成了“人自己”。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在意识中理智地发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实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己。”(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97页。)这就是说,正因为对象客体是“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是“人自己”,对象才成为人的对象,客体才成主体的客体;另一方面,劳动生产不仅使自然人化,也使人对象化,也创造着人类自身,也创造着理智、意志、情感以及各种感觉能力。马克思说:“社会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6。)这也就是说,正因为人是对象化的人,人是在人化的自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主体方可能成为客体的主体。这样一来,通过劳动实践,客体成为主体的客体,主体成为客体的主体,主体和客体方能真正地相互沟通、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相互转化,才能从本体论上、从发生学上科学地辩证地解决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达到和谐的统一。而存在主义的“主体间性”理论,只是把客体设想为主体,以实现二者的结合,这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诗意的解决、审美的解决,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落后于马克思的,是轻视或忽视马克思的结果。怎么能把它当作是超越马克思的最合理的学说呢?
更为重要的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解决,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实践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7页。)理论上的解决,并不就是历史的现实的解决,因为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产生,并不只是头脑中形而上学思维在作怪,更重要的是还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人与社会关系的裂变与异化等更为根本的因素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尽管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叶就对主客体二元对立作了理论上的回答,但在马克思之后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仍在继续发展。可以说,只要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只要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终结,只要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仍然存在,那么,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观念便不会真正的彻底的消解。从这个角度看,海德格尔的出现,存在主义消解主客体的悖论,“主体间性”的神话,就不是某个人的失误,就不是某个人的极限和悲剧,而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和必然,这是谁都难以逃脱和超越的。只有历史的超越,才可能有现实的个人的超越。
马克思正是从这种历史的现实的条件出发,从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认为只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丰富产品,资本制度的根除,人以个性为基础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构成,才可能提供这一历史解决的可靠条件,这种主客体二元对立才可能彻底地得以解决。只有到那时,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文的对立才可能现实地根本地达到和谐统一。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与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迷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页。)他又说:“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8页。)他认为这种统一的关键在于人成为了社会的人,人与人结成了新的和谐社会:“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正是在主客体既对立又和谐的基础上,产生了辩证和谐美学和社会主义艺术,产生了人与对象既对立又和谐的审美关系。在这种新型的审美关系中,审美对象各构成元素的组合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而人作为审美主体之审美心理诸因素的构成也是既对立又和谐的。辩证和谐的客体对象与辩证和谐的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相对应,形成了现代人的审美关系。它既具有古代素朴和谐关系的单纯性,又具有近代崇高关系的复杂性、丰富性;既具有前者的和诣性、一元性,又具有后者的对立性、多元性;既具有前者的有序性和稳定性,又具有后者的无序性、激荡性和开放性;它是一种最丰富、最全面、最和谐的崭新的审美关系。从这个观点看,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既不能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那样,到远古的人与自然、主客体尚未分化的“此在”中去寻找,也不能像生态主义那样,只向自然界、生物界的平衡、和谐中去寻找。西方当前出现的生态主义有三个特点:一是以自然为本,二是反人类中心主义,三是认为人是自然界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人和动物是完全平等的。它是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极端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产物,因而它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批判人的主体的无限膨胀,蛮横地摧残奴役自然,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以自然为本的反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反对以人为本的,是反人文主义的。西方有人称其为新自然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因而,生态主义同样是极端片面的,与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彻底统一不可同日而语,更难由此直接引申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来。真正的生态美学只有用自然和人文统一的和谐美学予以吸收和发展才是可能的。
标签:美学论文; 二元对立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辩证思维论文; 二元关系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二元结构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小逻辑论文; 哲学家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