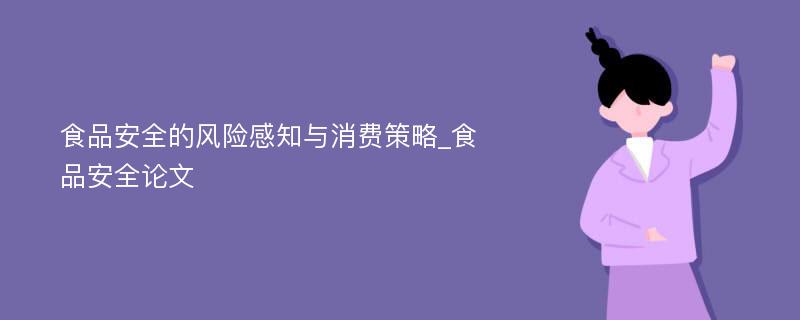
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与消费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食品安全论文,策略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R15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4)03-0107-08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述评 近年来,由于政府失灵与市场失效,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从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到双汇“瘦肉精”事件,从蒙牛学生奶“中毒”事件到“染色馒头”事件,不一而足。如果说2003年SARS爆发是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标志的话;那么,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则使消费者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风险社会就在身边。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对中国人、社会与国家构成了一种新的、紧迫性和多面向的挑战,这一挑战涉及超越食品安全、营养和健康的诸多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1]。 与传统工业社会中危险是可感知的逻辑不同,风险社会中“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并且只出现在物理和化学方程式中(比如食物中的毒素或核威胁)。”[2]正是由于现代风险的不可感知性,消费者具有严重的知识依赖性。他们的风险感知(而非客观风险本身)将会成为其行动的先导。而且,与工业社会中的“我饿”逻辑不同,现代风险社会是由“我害怕”逻辑驱动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个体化进程的推进,恐惧与焦虑必须由个体来处置。因而,在风险社会中对恐惧和风险的处理成为必要的文化资格。在具体的消费实践中,消费者会运用一系列的消费策略以应对风险。那么,消费者风险感知会受到哪些机制影响?他们会采取何种消费策略来应对风险? 对于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背景下的风险感知与消费策略,国内外学者均进行了研究。国内方面,王志刚通过对天津市个体消费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女性、月收入高、学历高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心程度高[3]。马缨、赵延东则通过对北京968个样本的OLS回归分析发现:公众对政府和科学家的信任能够提高他们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食品安全事件会显著降低公众满意度[4]。王俊秀对全国51100个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对食品安全满意度存在地区、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5]。张金荣等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的定量研究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主观建构因素和人为放大效应,对食品安全责任归咎存在加重政府责任而弱化个人和企业责任的现象[6]。 国外方面,Knox认为,消费者的风险感知需要在其嵌入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中来进行分析[7]。其主要包括:消费者自身的特质、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以及大众媒介。消费者自身特质方面,Buchler等基于在澳大利亚的定量数据发现:年收入低于25000美元,以及没有完成高中教育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更关注食品腐坏或过期这类传统风险;女性、有更高教育和年纪更大的更关注以食品添加剂为代表的现代风险[8]。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方面,主要涉及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以及专家与大众在知识上的分野。Kjaernes等认为,在过去十年,消费者对食品的不信任已经作为一个急迫的问题而提上了政治议程。他们使用比较和制度分析视角对欧洲七国消费者食品信任/不信任进行了经验研究[9]。大众媒介方面,Reilly和Miller以疯牛病为例探讨了食品在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兴起中的角色,认为必须超越简单的以媒介为中心的解释,而是要认识到媒介运作是媒介和社会制度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10]。 在消费策略方面,国外学者倾向于先依据一定标准将消费者类型化,然后再对某一类或所有类型消费者进行分类研究。Wansink依据消费者对食品风险感知和厌恶程度的高低将消费者类型化为四大类,每一类具有其独特的消费策略[11]。Halkier通过对丹麦消费者的质性研究发现,在处理与环境相关的食品风险时,消费者的态度是“好恶交织”的,这与消费者的身体体验相关。在研究的基础上,Halkier将消费者食品风险处理类型化为三类[12]。Brunel和Pichon则认为,传统的风险减少模型及其替代命题在解释消费者相关风险策略时存在缺陷。有鉴于此,他们将风险和消费者的策略均分为两类,并建构出消费者风险减少的策略模型[13]。 综上所述,国内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研究使用的是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大规模收集问卷来找出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关键变量。但对消费者是如何感知食品安全风险的,以及他们会采取何种消费策略来规避风险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这样,消费者具体的行为与认知逻辑就成为一个有待打开的“黑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的研究是嵌入在其丰厚的理论积淀基础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发现关键变量的定量研究,更有深度的案例研究。总之,在深度案例研究基础上来发掘消费者感知和策略机制将成为国内未来新的研究路向。本文即是以2010年8月—2011年8月在广州市的案例研究为例来探讨在食品安全风险背景下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与风险策略。之所以选择中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资本和适度的经济资本,而且对消费敏感。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我们能更好的把握消费者风险感知与风险策略的一般规律,从而为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二、风险感知及其影响机制 社会科学中有关风险的认识论主要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范式。现实主义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危害、威胁与危险,且能被独立于社会与文化过程而被测量;建构主义则认为,没有本质上就是风险东西,而是受到社会与文化调适的,是历史、社会与政治偶发的“观看”方式的产物[14]。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对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风险感知。案例研究表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主要受三大机制影响: (一)健康主义:从否定性身体到自恋性身体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身心关系是一对极为重要的关系。哲学家都是在身心合一的情况下讨论身与心的互相影响;在二者关系中,大多更重视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推进“赶超型”现代化建设,国家必须加强对社会一切生产要素的控制,包括最重要的资本——劳动者及其身体。身体成为国家规训的最重要载体,任何对身体的过分迷恋都会被贴上“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标签而被污名化。但随着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国家与市场不再仅仅看重身体的生产(劳动)功能、更将其看作消费的核心载体。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裹挟下,劳动的身体转变成欲望的身体,人们的身体观也经历了一个从轻视到自恋的演变过程。 对拥有适度经济资本和高文化资本的都市中产阶级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在他们的消费实践中,身体已成为一种需要不断投资的资本——身体资本。而在对身体的关注中,健康是其核心。在现代医学体系的规训下,中产阶级逐步形成了一种健康主义身体观[15]。即对身体(健康)任何损害都是不允许的,都会引起本体性恐慌,这尤其体现在不可控的外部风险方面。并且这种“在社会上被看做‘健康’和‘疾病’的东西,在医学垄断的框架中,丧失了其预先注定的‘自然’品质,变成一种在医学工作中可以得到生产的东西。”[2] 以前,那么穷,谁会把身体看得那么宝贵呢。能吃饱就不错了。……现在时代不同了,社会这么好,生活条件都好起来了,人们的寿命也比以前长了很多。……现在的人那,那可是把身体看得比什么都要宝贵。哪怕是身体上一点小小的毛病,你比如说是一个小小的感冒或者是发烧什么的都要花很多钱去大医院里面看。要是以前的话,要么就躺在床上拖上几天;或者,喝点姜茶什么的就熬过去了。(案例16) 由于食品与健康密切相关,中产阶级对食品安全风险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形成了以健康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风险认知。要求食品必须绝对安全,任何对健康实际或潜在的威胁都是无法接受的。但在风险社会中,完全安全的食品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对食品安全风险的容忍度和可接受性。这样,就形成了消费者以社会理性为基础的风险感知与科学社群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风险评估之间的张力。 (二)专家系统:从统一到分裂 对于风险感知与风险评估之间的张力,消费者是无法独立解决的。在此情况下,独立运转的市场几乎是失灵的,因而需要政府干预。为了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现代社会逐步发展出一套制度性信任机制——专家系统。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社会需要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系统来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给以“科学”回答。之所以专家系统受到现代社会的青睐,是由于他们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专业知识,易于产生信任感。 但专家系统本身也面临着困境。以转基因食品为例,对于其安全性(包括转基因食品本身的安全性以及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是否安全),专家之间就存在较大争议。一派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转基因,以“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张启发为代表。该派认为我国面临着“人多地少,生态脆弱”的困局,为了突破这些困局,第二次绿色革命势在必行。而转基因技术则使第二次绿色革命成为可能,因而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16]。另外一派以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学院和国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薛达元教授为代表,该派认为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上要慎之又慎。因为,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上尚存在着不确定性,“目前安全并不能够保证若干年后仍然安全”。有鉴于此,他主张以国际通行的“预防原则”来处理转基因技术问题[17]。 可见,专家系统是分裂,而非统一的。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人们不仅对专家所提供的知识产生怀疑,更对专家从事活动的动机与目的本身产生质疑,质疑专家所提出的建议并不是针对问题本身,而是为自己(或者所代表的利益团体)获取更多利益。 现在的专家都是一些“砖家”,他们一点良知都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只要给他们一些好处,吃了对人体有害的东西,他们也不管,也要我们这些消费者放心吃。而他们自己呢,则可能不会去吃那些东西。你比如,有些专家说转基因食品,像水稻什么的吃了对人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他们吃不吃呢,我想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反正我是不相信那些所谓的专家建议的。(案例27) 这样,作为制度化信任机制的专家系统便处于“悬置”状态,专家系统的分裂使消费者陷入到“到底该信任谁”的窘境之中。既然专家系统不能提供一致性的权威信息,中产阶级必须独自面对食品安全风险,从日常生活接触最多的媒体着手来寻找与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 (三)媒体霸权:从阐释者到立法者 媒体(主要包括电视、网络以及杂志等)是消费者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最主要方式,这对拥有高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当某一食品发生问题时,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往往率先报道。这既践行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又满足了公众知情权。但媒体也是一个“场”,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提高点击率、收视率或发行量,各媒体展开了争夺眼球的“信息战”。 但我国媒体从业者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与食品安全报道所需的专业水准之间仍有较大距离,报道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报道内容完全失实;(2)混淆关键概念;(3)夸大问题程度;(4)解释说明不够;(5)互设议程,以讹传讹[18]。这样,媒体便对食品安全风险进行了放大。 问:那您觉得这些信息可靠不可靠呢? YN:我觉得它报出的现象是有的。那是不是仅仅是这个东西有问题,那就不一定了。问题都是通过媒体报道出来的。但是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如果(媒体)报道有这个问题,我是不会去买的。 问:假如媒体报道有误呢? YN:这种情况我已经有戒心了,我就不会去买的了。比如说超市里面的饮料,统一的什么果汁,华润万佳在回收,那我就肯定不会去买。……但这种东西是不是有问题,我也不能肯定。……但只要新闻报道出来了,不管信息是真是假,我都会去避免。我就不会去买这方面的东西了。我可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吧?! 访谈资料显示,消费者对媒体的可信度是存疑的。但由于食品安全与健康密切相关,而专家系统又不能提供一致性的权威信息,中产阶级只得坚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风险观而跟着媒体走。媒体取代专家系统,成为食品安全信息的“立法者”。随着食品安全信息的不断发布,中产阶级消费者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与焦虑当中,成为名符其实的焦虑型消费者。 三、策略性消费:主流食品系统①内的策略应用 对中产阶级消费者来说,食品安全焦虑使他们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纾解焦虑,他们“公责私揽”,将国家公共消费责任的一部分,由自己或家庭来承揽,使用策略性消费来应付食品安全风险[19]。之所以称为策略性消费,是指消费实践主要是在主流食品系统内的策略运用,而不涉及主流食品系统之外的行动。 (一)减少策略 对中产阶级消费者来说,减少策略主要体现在外出就餐和食品购买两大面向上。外出就餐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出就餐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纷纷离开家庭进入职场,家庭就餐次数开始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外出就餐成为获取乐趣以及社交性的重要方面。但一系列食品丑闻(尤其是以媒体密集报道的“地沟油”丑闻为代表)使中产阶级消费者对外出就餐产生了诸多顾虑。 问:有些餐厅您刚才是说,会有地沟油,那您平时就是怎么看这个事件? LHR:如果我认为,尽量少在那边吃是最好的。 问: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尽量少在外面吃? LHR:哦,尽量少,对的。 问:去大型的餐厅会不会放心一点? LHR:这个我也说不得,因为大型的……因为现在做生意很多人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这个很难讲的,我也不敢说,就是说,反正为了避免(不安全)就尽量少一点。 与外出就餐一样,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食品购买也是随食品安全丑闻及其媒介报道起舞的。当媒介报道了相关食品的丑闻之后,消费者便减少该食品的购买。例如,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纸做的包子》报道,多家媒体随之对此进行了转发。该事件很快便进入广州中产阶级消费者的视野;随后,消费者减少了一切与包子有关的食品购买。事后证明,该新闻是一起人为炮制的假新闻。 (二)挑选策略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食品是极为单调的。这种单调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食品品种与数量相当少,并且食品定额供应,消费者选择极为有限;另一方面,食品购买渠道也是相当狭窄的,消费者只能在数量极少的供销社与国营食品商店凭借票证来购买相关食品。为了买到品种少得可怜的蔬菜,消费者在前一天晚上就把他们的菜篮放在食品柜台前排成长队争购。 但随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食品市场获得了再生。不仅食品品种极大丰富,食品零售渠道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消费者可以依赖其经济实力与饮食偏好在市场上自由选购所需的食品,而这一切成为消费者“挑选”的基本前提。食品安全丑闻发生之前,消费者就使用挑选的策略来获取自己所需食品。只是在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之后,中产阶级消费者挑选策略使用得更加频繁,挑选的动机也更加与食品安全属性相关。 问:您对蔬菜中的农药残留怎么看?您怎么应对的呢? RYF:这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长期积累会影响身体健康。现在也很难判断哪些蔬菜农药多,哪些少。但是现在买蔬菜就找有虫眼的,因为个人觉得有虫洞的可能就是没有打农药的,但是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我买鱼或者鸡的时候,我一般要买活的。死的我不要,觉得不太放心。而且,我不要太大的。太大的我怀疑是吃什么饲料催大的,怕吃了不安全。现在这东西呀,都太大了。大得有点假,我们以前的时候那些吃的东西哪里有现在的这么大呀?!(案例21) 当然,中产阶级消费者挑选策略运用所需的知识主要来源于长期食品购买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知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些知识到底能否有效应对食品安全风险,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故不再赘述。不过,对消费者来说,挑选策略使用还是有其限度的。正如QLP(案例28)所言,“我丈夫让我别买杀好的鸡,就是对外面不放心,让买活鸡。但是这个活猪你能买吗?活牛你能买吗?……没办法,还是天天要吃。” (三)品牌策略 在策略性消费技术中,品牌化可以说是挑选策略的一种延伸。依据著名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的定义,所谓品牌就是一个名字、称谓、符号或者设计,或是上述的总和,其目的是要使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 对中产阶级消费者来说,其品牌化策略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延续性的品牌使用,也就是对某种品牌建立信任感之后长期的使用该品牌;另一种是当一种品牌产品产生安全风险事件(丑闻)之后,消费者便使用另外一种品牌商品来替代以前的品牌。例如,YN(案例22)谈到其朋友的品牌化追求时就说道,“我身边有一个长期吃有机蔬菜,超市定期送给她。她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而且也是比较重视健康的。然后她常年吃‘一号土猪’肉。她小孩在幼儿园都不吃肉的,回家里煲汤都是用‘一号土猪’的。”除了品牌化具体产品之外,品牌化的购物与饮食空间也是消费者的重要选择。 我女朋友的一个同事经常要坐很远的车到天河那边的吉之岛去买食物的。她就特别相信吉之岛的品牌和那里面卖的相关食品,说那里的东西吃起来尤其让人放心。(案例26) 当一种品牌的产品发生安全丑闻之后,中产阶级消费者可能发生品牌替代的消费行为。在这方面,婴儿奶粉选购尤为明显。2008年9月11日,《东风早报》刊登了一篇《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查,该问题是由于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渗入三聚氰胺而引起的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截至2008年9月12日至17日8时,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6244名。其中,4917名患儿症状轻微,生命体征稳定;留院观察治疗患儿1327名。一系列婴儿奶粉丑闻的曝光,使中产阶级消费者逐渐丧失了对国内婴儿奶粉品牌的信心,作为对丑闻的回应,他们转而纷纷去香港或国外购买婴儿奶粉②。 我们家小孩吃的奶粉都是从香港买回来的。做父母的可要为小孩的健康负责任。没办法,国内的婴儿奶粉曝光的问题太多了,不放心,不敢给小孩买。你想,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小孩子的一辈子都可能被毁了。……没办法,有空的话,我们就去香港那边拖奶粉。买国外牌子的,吃起来放心。如果我们没空的话,别的亲戚或者朋友什么的如果去那边买的话,我们也让他们给我们带一些回来。(案例25) 访谈还发现:中产阶级消费者信任的不仅仅是国外婴儿奶粉品牌本身,更重要的是国外的食品监管制度。由此可见,要重整中国国产婴儿奶粉品牌,除了提高奶粉本身的质量与品质以外,让消费者恢复对中国食品监管制度的信心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人际信任策略 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建立在熟悉性基础之上,人们经由熟悉性而建立起对食物的信任[20]。但随着社会的城市化,我们逐步步入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建立在法律与规范基础上的制度信任。制度信任能够降低社会复杂性,提高行为的可预期性,降低交易费用。但制度信任也有其脆弱性,这主要体现在制度信任难以建立起来,而且一旦遭到破坏便难于恢复。由于人们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和专家系统的普遍不信任,消费者转而采取重回人际信任的策略,以确保购买(消费)到更加安全的食品。当研究者询问研究对象日常烹饪所需的食品是如何购买时,案例17和22如是说: (烹饪的食品是)在农贸市场买的。我买鸡的时候看鸡的精神状态,声音叫得很洪亮。要活的,而且不要太大只的,可能没吃太多添加剂。并且基本上是固定的摊位,我要看看摊主是不是健康,很可信的。就想和他熟点,熟了,建立了感情,你不知道(食品的好坏),他知道,他就会给你介绍一些好的。(案例17) 超市和菜市场。我会看一看档口,卖菜的那个人,杀鸡的或者是宰鱼的那个人,我看他本身是不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看看他是否比较顺眼。档口里面比较干净,我就会更多的选择。有时候我也会去跟风。就是很多人都去买的,我就会觉得大家会比较信任。就像中国人到饭馆吃饭一样的。(案例22) 不过,这种重回人际信任的策略也是有限度的,适合集贸市场、小食店、士多店及街边摊贩等这种非制度化的消费场所。一旦步入制度化消费场所,如大型餐厅、超市及购物广场等,人际信任的影响力便趋于消解。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广州市的案例为基础探讨了中产阶级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风险背景下的风险感知与风险策略。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风险感知受到三大机制的影响:(1)健康主义;(2)专家系统;(3)媒体霸权。健康主义身体观使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风险意识空前提高,但由于专家系统是分裂的,因而无法为消费者提供一致性的权威信息。媒体便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媒体霸权得以形成。在媒体的密集报道下,消费者陷入空前的焦虑之中。为了纾解焦虑,消费者主要采取四大策略来回应食品安全风险。这四大策略分别是:(1)减少策略;(2)挑选策略;(3)品牌策略;(4)人际信任策略。 总的来看,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风险策略是有限度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焦虑。这既与客观的食品风险相关,又与消费者的风险感知模式分不开,甚至会出现政府数据显示食品安全合格率逐年提高和公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明显下降并存的局面[21]。这一现象启示我们:在加强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既要加强对客观风险的治理,又要加强对主观风险的治理。对于如何加强客观风险治理,学界已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之所以要加强主观风险治理,是因为食品安全不仅具有客观性、更有建构性。在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中,既要治理“危害”(hazard),又要治理“愤怒”(outrage)。但可惜的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治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硬治理,主要通过科学与监管两大工具对客观风险进行治理,而忽视软治理。食品安全软治理是一种以信息为主要工具,以风险交流为主要手段,以重构信任为主要目标的新型治理模式。其中,制度化的风险交流机制处于核心地位。 为了更好的进行风险交流,首先必须了解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基本特点。正如本文的案例所显示的,消费者的风险感知与科学社群的风险评估之间存在差异性。其次,要使专家系统运转起来。随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逐步从“九龙治水”的分段监管到“一龙治水”的大部制改革,整合出权威性的专家系统,并用一个声音发出权威信息成为可能。第三,要加强媒体治理。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可能启蒙消费者,也有可能放大食品安全风险。因而,应当将媒体治理也纳入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通过专家系统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向消费者提供科学信息,从而提高消费者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效能。 注释: ①所谓主流食品系统(mainstream food system),是指大规模生产与销售以及大规模消费的商业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一般没有直接联系,交往更多是以非人格化的匿名方式进行。对消费者来说,食品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由谁生产的以及如何生产的,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②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婴儿奶粉丑闻曝光之前也有大批消费者到香港或国外购买婴儿奶粉。只是,婴儿奶粉丑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消费者更大范围加入到从香港或国外“拖奶粉”的行列。标签:食品安全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食品安全监管论文; 食品安全标准论文; 国家食品安全城市论文; 感知风险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