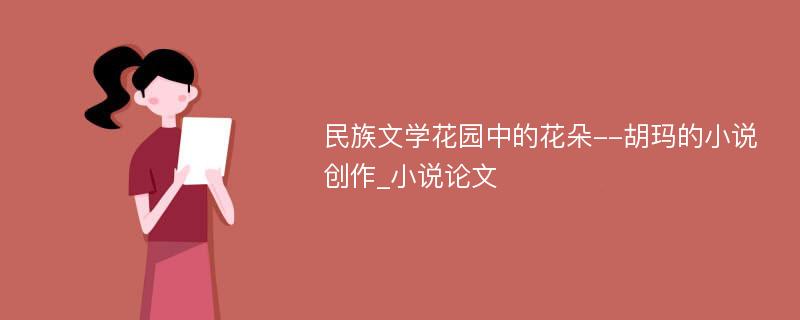
民族文学花园里的花朵——夏木斯#183;胡玛尔的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园里论文,花朵论文,民族论文,小说论文,文学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主要成员的哈萨克族的文学,占据着一定的地位,我国哈萨克族作家以他们独特的文学创作为哈萨克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花园中增添了美丽的花朵。夏木斯·胡玛尔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夏木斯·胡玛尔1952年1月出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一个富牧家庭。1959年—1966年在木垒县读小学和初中。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初中毕业后的夏木斯被迫回乡参加劳动。1974年,夏木斯的命运出现了重大转机。这一年,他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被允许推荐报考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被新疆大学物理系录取,奇迹般地从一个富牧的儿子变成了一名炙手可热的“工农兵学员”。而一旦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夏木斯便开始迈着坚实的步子踏上了命定的文学之途。1978年大学毕业后的夏木斯在新疆教育出版社工作。1982年以后又调到新疆文联《曙光》杂志编辑部任编辑,此后他先后担任《曙光》杂志副主编、主编,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等职务,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4年,他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处女诗作《新乡》,大学毕业前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希望之火》(1980年)。此后,他的创作激情如喷发的火山不可遏制,先后发表了包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评论、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短篇儿童小说集《白山羊和青山羊》(1984年),中篇小说集《一滴血》(1988年)、《克拉玛依的故事》(1991年),中短篇小说集《长满篙草的原野》(1992年),电影文学剧本《相逢之后》,以及长篇小说《博克勇士》(1987年)、《流不尽的眼泪》(1989年)、《英雄加尼别克》(1998年)、《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1999年)、《突格勒克可汗的传说》(2003年),文学研究论文集《文学与真实性》(2002年)等。
夏木斯的小说创作深受读者和文学评论家们的好评。他的短篇小说《故乡》、中篇小说《长满蒿草的原野》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获得了自治区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一等奖;长篇小说《博克勇士》1989年获得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长满蒿草的原野》、长篇小说《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均被译成汉语出版,长篇小说《博克勇士》被译成维吾尔语出版,许多小说作品都被译成了其他兄弟民族的语言来发表。
1980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希望之火》是夏木斯小说创作的成名作。作品以一个16岁的少年的成长为主线,反映了解放前哈萨克草原上的多种关系。主人公哈马西曾在有杀父之仇的巴依家里放养,受到各种折磨。因为人微言轻,他无法和那些富人们讲道理,因此不得不沉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用孩子的方式进行反抗,例如扔石头,有机会的时候给对方肚子上踢一脚,用头顶对方一下等等。而在那些友善的大人面前他仍是一个喜欢听故事、喜欢提问题、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少年。在挣扎、斗争的成长过程中,他认识了自己生活的世界。作品中另一个人物是与巴依名为亲戚实为后者雇佣的长工的乌玛尔,作者对他与巴依之间的斗争描写得极为生动风趣,为作品增色不少。这部小说对少年反抗的描写颇具特色,语言朴素而真实,对“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不良文风是一种变相的抵制。
夏木斯文学作品的主体部分是小说。早期的作品多为短篇,如《一次午餐》、《一片绿》、《被锁住的门》等,选取的多为生活中一件小事,故事情节较为简单,寓意也较为浅显。后来,夏木斯创作了许多以反映故乡面貌以及儿时生活的回忆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感情真挚细腻,语言朴素清新,擅长以儿童的眼光和心理来观察和感悟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①
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儿童短篇小说《在故乡》,以孩子的眼光和口吻细致地描写了充满生机而又丰富多彩的草原生活,表现了孩子们聪明、淘气、纯真、善良的天性。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如写爷孙俩乘车进山的背景时,用了这样的比喻:“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像鸟一样轻捷地飞奔着,一路上把长着剪刀尾巴的白雨燕一只只都甩在了后面。”在描写牧场上几家毡房的大人孩子们得知远方小客人已经到来时,用于这样的比喻:“屋子里像开了锅的奶茶一样沸腾起来。”这些比喻抓住了儿童观察认识事物的特点,使小说不仅风格清新自然,而且具有浓郁的草原生活气息。
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短篇小说《眷恋的歌声》则讲述了一个令人忧伤的故事:少年哈则孜(“我”)的同桌叶斯泰的父亲被错划成右派而劳改,母亲又被下放到偏远的山村。看到叶斯泰体弱多病的母亲一次次被揪斗,看到母子二人在一间冰窖一样的房子里痛苦地哭泣,听到叶斯泰满含眷恋和伤感的思乡的歌声,“我”想方设法从自家里偷来了煮好的羊肉,送给陷入绝境的叶斯泰母子。小说通过对两个少年之间交往的描写,揭露了“极左”思潮在人们的肉体和精神上造成的创伤,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孩子们纯洁善良的美好心灵。②
短篇小说《圆圆的毡房旧址》是夏木斯写于90年代的另外一篇有代表性的儿童小说。这篇小说写“我”在告别故乡十年之后,终于离开城市的忙碌、喧哗,走上通往故乡的崎岖山路。看着被岁月的风雨和疾逝而去的时代冲刷得日渐模糊的毡房旧址,“我”不禁追忆起苦涩而又难忘的童年生活。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草原上一片荒芜、悲凉的景象。牧民个人的畜牧被生产队强行充公,连没断奶的小羊羔也不放过。“我”家的褐色儿马拼命挣扎反抗的场面,母马绝望哀伤的眼神,为了一勺奶含泪而去的奶奶,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而当“我”从往日的思绪中走出,望着故乡已经花开枝梢的刺梅和满山满坡的嫩草,吸吮故乡清新宜人的空气时,顿时感到新时代的喜人春风早已吹尽了过去的无数辛酸。小说的构思新颖,语言哀婉动人。
中篇小说《长满蒿草的原野》是夏木斯儿童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一篇。这是一篇以刻画敏感、纯真的儿童心理见长的佳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马合萨提的小男孩,这个可怜的小不点儿从一降生,苦难就伴随着他:他生下没多久,母亲便去世了。奶奶照看他6年后,也告别了人世。父亲娶了继母之后,伯父和婶婶收养了他。他只能跟年老的爷爷普夏合拜一起做事,一起生活。这个寄人篱下的小不点儿像一只惊恐的鸟,整日里提心吊胆——伯父醉酒后的打骂和婶婶“男人一样粗重的嗓音”震慑着他。因家里穷,又无劳动力,未满10岁的马合萨提被迫辍学当了牧童。但马合萨提内心渴望着上学,在爷爷的护佑和恳求下,他得以回到生父家并上了学。但这个来自荒野穿着破旧的瘦弱小男孩,在学校常常受到同学的奚落、取笑,回到家又遭到继母的歧视和冷落。他幼小的心灵在这冰冷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丝温暖,他更加想念住在伯父家的爷爷。爷爷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爷爷温暖的怀抱是他唯一的“避难所”和“安乐窝”。对爷爷的思念,终于使他“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偷偷地爬上了一辆进山的卡车”去找爷爷。但卡车半路上坏了,他又不敢惊动司机。好久不见汽车启动,它有些害怕了。他抓着汽车的缆绳艰难地爬下来,凑近车窗,驾驶室里却空无一人。风雪像疯狗一样狂叫着,原野上一片雪白,厚厚的积雪已淹没了车轮。小不点突然发现了司机的一串脚印,心里一阵狂喜。于是他沿着脚印朝前走,时而爬上一个坡,时而又掉进雪坑,原野一片漆黑,他终于走不动了。他太累了,太困了,于是睡着了。无情的风雪就这样吞噬了他。从此,他再也不会被醉了酒的伯父拧耳朵,再也听不到继母刺耳的叫骂声,再也看不到爷爷慈爱的微笑了。小不点马合萨提来自原野,自生自灭。作家以写实的笔法,希图通过这个令人揪心的故事去呼唤人性,呼唤亲情,去唤醒人们那麻木冷酷的心。小说情节曲折,寓意深刻,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显示出作者扎实的生活底蕴和创作技巧的日渐成熟。③
夏木斯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是长篇小说创作,随着作家生活阅历的积累和对本民族命运思考的深入,他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到目前为止他已正式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其中四部都是历史题材的长篇。这些历史长篇展现了哈萨克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悲惨的生活道路,体现了哈萨克族艰苦朴素、英勇进取的民族精神。他的历史长篇《博克勇士》于1987年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内容丰富,气势恢宏,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涵盖力,出版后曾多次再版,深受读者欢迎,成为夏木斯·胡玛尔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曾获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小说反映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真实历史,描述了旧时代封建势力和贪官污吏残酷压迫贫困牧民,激起民愤,杰出领袖博克带领贫苦牧民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英勇反抗,辗转战斗于阿勒泰青河、博格达以及南疆地区、藏北高原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哈萨克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博克的艺术形象。博克是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一位哈萨克族英雄,他出生于贫困牧民家庭,从小聪明智慧,文武双全,立志为广大民众谋幸福,把本部落的所有人看成自己的兄弟,不分贫富,平等待人,特别同情受苦受累的穷人。由于出众的人品和极强的组织能力,博克与1887年出任博格达地方的乡衙,他致力于减免税收,发展农商,改善人民的生活,赢得人民的爱戴,阿勒泰、塔城民众纷纷投靠博克。当时哈萨克族人民承受着重重压榨,生活非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上层阶级惟恐博克的力量和影响越来越大,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便向乌鲁木齐将军诬告博克蓄意谋反,使他遭受牢狱之灾。出狱后,博克意识到封建政权欺压民众的凶残而腐朽的本质,为了给民众找到一个自由安宁的地方,日夜奔波,他带领着阿吾里(牧村)的300户人家到处逃亡,曾到过新疆奇台县,又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一带,最后又逃亡到西藏地区,可是依旧找不到安居的乐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受到追杀。封建统治者和地方上层势力相互勾结,处处设下陷阱,追杀围剿这支敢于反抗的牧民队伍。在西藏,博克因病去世,追杀他的反动军队把他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把他的头颅砍下来,拿到迪化示众,企图以此震慑群众。曾得到博克帮助的汉族官员罗光明大义施救,勉力将博克的头颅还给其子,后安葬于富蕴。作者在作品中深刻谴责了封建势力的野蛮压榨,也揭示出多数民众引颈待戮的愚昧麻木。博克勇士生前想的是为受苦受累的哈萨克人民创造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努力奔波了整个一生,最终因为当时的反动势力,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英雄,他的英雄事迹代代相传。作者依据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生动描绘了19世纪游牧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广博的历史知识,独具匠心地将哈萨克族民俗民情巧妙地融于广阔的历史长河之中。④
作者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用具有历史的和民族特色的典型环境来展现了哈萨克族人民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承受重重压力,以坚定不移,艰苦朴素的民族精神获得最后胜利的过程。作者为了突出博克的艺术形象,真实地描述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除了着重塑造博克这一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外,也刻画了苏肯、塔里夫、哈迪夏、罗光明、阿斯木汗等众多人物的鲜明形象。作品的结构完整、语言贴切,作品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真实无误。小说以其深沉的历史感和对民族的挚爱之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为此后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⑤
作家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则描述了哈萨克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下的生活状况,反映哈萨克牧民定居、畜牧改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情景。作品以巧妙的艺术表现手法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成功地表现了一部分哈萨克人在时代变化中的思想感情。
综观夏木斯的创作历程,扎根现实生活,勤于观察思考,是他不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堪称当代哈萨克文坛上的常青树,是当代哈萨克族最为活跃、成绩最为突出的作家之一。
注释:
①③吴孝成、赵嘉麒主编:《20世纪哈萨克文学概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226页。
②贾合甫·米尔扎汗主编:《哈萨克文学史》(第四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3页。
④夏冠洲等主编:《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小说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⑤赛力克·哈吾努拜:《细雨》(文学评论集),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