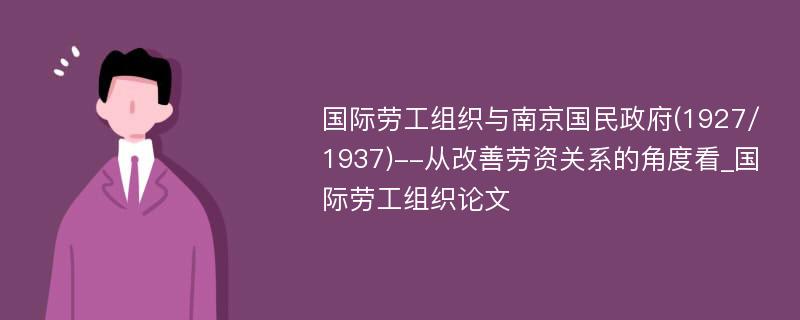
国际劳工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从改善劳资关系角度着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劳工组织论文,国民政府论文,南京论文,劳资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劳工组织①是会员国之间协商与制定劳工政策的专属机构,也是各会员国内部政府、资方与劳方联络与沟通的纽带。中国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会员国,曾派遣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力争加入理事会,并且批准过若干国际劳工公约。惜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未给予必要的重视。详细剖析这一过程的某些重要断面,可以重现作为劳资争议最高仲裁者与制订者的国民政府在国际保工立法运动中的态度,有助于从某一侧面发掘政府处理劳资争议的动机与立场,进一步厘清南京国民政府、资方、劳方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动机
汤玛士来华是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组织的转折点。
根据凡尔赛和约,国际劳工组织1919年成立于日内瓦。作为一个行政完全独立的组织机构,其宗旨是以国际合作促进国际保工立法,用和平手段解决世界劳工问题。
国际劳工组织包括国际劳工大会、理事院、国际劳工局三大机构。国际劳工大会为劳工立法机关。会员国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国际劳工大会,并有权派政府代表2人、劳资代表各1人出席。理事院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最高机构。原定理事24人,1934年增到32人。其中,政府代表16人,劳资双方代表各8人。理事院每年开会4次,其任务为管辖国际劳工局,选任劳工局长,编制劳工局预算,制裁会员国违背公约等事宜。国际劳工局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执行机关,该局长也是国际劳工大会的秘书长。
中国作为凡尔赛和约的参与国,也是当然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会员国。北京政府于1923年在日内瓦设国际劳工事务局,任命萧继荣为局长。1928年中国实现政治统一后,国民政府并未与国劳组织积极接洽,当年,与北京政府相同仍只派政府代表出席国劳大会。国际劳工局首任局长、社会学家汤玛士利用出访日本、印度之便访华,改变了国民政府对国劳组织的消极态度。从1928年11月15日抵达哈尔滨,中经奉天、北平、汉口、南京,到12月3日离沪赴日,汤玛士先后拜会阎锡山、白崇禧、工商部长孔祥熙、工商部劳工司长朱懋澄、上海社会局长潘公展等党政军界要人,重点参观中法大学、上海市工会、浦东职工新村,并且出席南京工整会、上海各工会、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等团体举办的谈话会。在日本短暂停留后,汤玛士又到广东考察工厂与工会。经过与汤玛士交换意见,南京政府、劳方出于各自目的,均对出席国际劳工大会抱持乐观心态。②国民政府自此开始重视与国劳组织的合作,除第16届(1932年)外,均派三方代表出席12届(1929年)至23届(1937年)国劳大会。
当时的国民政府,踌躇满志,对外谋求国家独立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注重塑造扶助农工的新形象。国民政府转而重视国劳组织,即归因于汤玛士的宣传与承诺有益于南京政府当下工作的开展。从废约方面来看,政府与工方对汤玛士寄予厚望。北平社会局希望汤玛士在关税自主与在租界内推行劳工法两方面援助中国。汤玛士在不同场合多次向舆论界表示“愿尽个人全力”相助。③从汤玛士本意来看,他更多是出于维护劳工利益的动机,但毕竟给国民政府提供一个新的外交策略。彻底废约固然不易,但如果能依靠国际劳工组织在租界内实施工厂法,也是废约的重要一步。
中国方面并不满足于此,希望能通过国劳组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在上海召开的包括市党部代表、朱懋澄、7大工会及各界80团体200多代表参加的欢迎汤玛士的集会上,代表们明确表示要求汤玛士支持中国废约的正义呼声。南京与上海工会也投书汤玛士,申明“欲望工人地位之提高,即应设法消灭不平等条约。”汤玛士也应合各界要求,声称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最近期间,当有取消希望”;安慰各界:列国领袖亦“必能接受中国正当之要求”④。国际劳工组织俨然是国民政府实现废除不平等约的同盟军。
汤玛士在华期间,高度肯定了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与民生主义“为工人造福不浅”⑤,强调孙中山的大同主义就是国际劳工局的努力目标。此类话语既宣讲了中国政府与国际劳工组织的亲和性,又标榜了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与其保工的正义性。同时,他还强调国际劳工局与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这种投合国民政府的政治取向,是国民政府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基础。
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国民政府也能争取工人的支持。汤玛士极为同情中国工人的悲苦境遇,其言语代表了劳工的利益,迎合了劳方的心理。他不仅申明国劳局的职权就是改善工人生产与生存环境;告诫工人既要与外国资本主义展开不懈斗争,又要防止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号召工人要组织并参加工会;呼吁国民政府早日颁行劳工法规;而且还要求中国工人参加与监督国劳组织的工作;利用国劳大会联合世界各国工人,打倒“害世界工人”的资本帝国主义。⑥汤玛士确实博得了工人的信任,工人甚至把他当作解决劳资纠纷的“万能之救星”⑦。法商电水工会要求汤玛士帮助解决本公司的劳资纠纷。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也曾请汤玛士索还省港罢工时资方所欠海员的失业赔款,并争取海员总会香港分会的合法地位。汤玛士对此自然是爱莫能助。
回到日内瓦后,汤玛士惟恐国民政府不派劳资代表列席国际劳工大会,特致电工商部长孔祥熙,不惜极尽璜词,称颂国民党与大同主义,恭维孔祥熙。⑧
如此看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选派劳工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可谓满足汤玛士的要求,顺应工人的意愿,以此增强政府的威望,何乐不为。但更直接原因则是要把国际劳工大会变为声讨不平等条约的讲坛,让工人成为争取国际力量支持国内废约运动的生力军。历届中国劳工代表向国劳大会呈交的提案与发言均以此为中心议题。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汤玛士所认定的劳工行为规范,合乎国民政府“劳资合作”的原则。汤玛士宣扬工人结社,但更强调“工会必求秩序”;鼓励工人“努力奋斗”,却要求工人拥护政府,通过劳资会议磋商解决自身待遇。⑨孔祥熙因此承认汤玛士“所发表主张与本党政策每有符合之处”,同意“予以相当容纳”⑩。此点较明确地反映出国民政府接纳汤玛士本人与国际劳工大会的真实心态。
由此而言,政府加强与国劳组织的沟通与合作的首要目的是争取国际道义上的援助,提高国际声望,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其次才是了解与采纳国际保工的新举措,调整劳资关系,实现劳资合作。
派遣完全代表出席大会,本身可以消除漠视国际劳工组织的不良影响,重树国际形象,提高国际地位。中国政府1929年第一次派三方代表出席第12届国际劳工大会,政府代表朱懋澄即被选为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934年第18届大会,中国政府第一次被选为理事院政府组理事,劳工代表安辅庭被选为劳工组次副理事。1937年第23届大会,中国政府连任政府组理事,林康侯被选为雇主组副理事,劳工代表朱学范被选为劳工组次副理事。国际劳工局还先后聘请陆京士、赵班斧、邓裕志等人充任工余咨询委员会、联合海事委员会、妇女工作通讯委员会委员。(11)特别是在历届大会上,中国代表极力宣传中国保工立法的成绩,益于塑造中国的新形象。汤玛士来华真正开启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交往的大门。1930年7月,汤玛士的秘书陈宗城奉命在南京成立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1931年8月,国际劳工局会同国联宣布仿苏俄五年计划,制定预备发展中国的十年计划,扶持中国实业发展。(12)该计划亦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惜无下文。
二、政府、资、劳代表选举与三者关系
参加国际劳工大会首先牵涉到各方代表选派的问题。
政府代表选派一般均由工商部与其后的实业部提名,由行政院会议复议产生。自1929年第12届到第18届劳工大会,国民政府虽然亦派外交官与会,但更注重调派主管官员出席大会。譬如:朱懋澄以实业部劳工司司长身份,参加过第12、14、15届三次大会。其后任李平衡与实业部劳工司科长包华国,参加过第19到23届大会。担任18至23届政府代表顾问的罗世安与包华国等,曾在北京政府驻日内瓦国际劳工处主持劳工事务,经验丰富。政府顾问龙詹兴为劳工问题专家。第12届、第17届政府代表萧继荣虽为驻法国公使,但曾是北京政府驻日内瓦国际劳工代表处处长,参加过第4届、5届、6届劳工大会,也算是劳工法专家。仅第12届派驻法公使高鲁、驻瑞士公使吴凯声出席。1932年第16届大会时,因沪战引起政局动荡,政府派国际联合会代表办事处长胡世泽与驻法公使馆一等秘书谢东发为政府代表。也是基于这一原因,政府未派雇主与劳工代表出席该届大会。
雇主代表的选派开始多为全国商会联合会推选,由行政院委任。陈光甫、吴清泰、严庆祥与顾问何廷桢均由该会推举。这种指向性很强的选举法,引起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不满。在第12届代表选举之时,该会便极力争取代表资格,但直到第17届大会前夕,其资格才为实业部认可。当年所选代表严庆祥、顾问何廷桢,即为中华工联会与全国商联会共同推定。第18届大会前夕,两会应实业部之命会同遴选代表,并推定商联会王志圣为代表,呈请国民政府加委。(13)两会之间从此达成某种默契。第19届大会前夕,王志圣注意征求中华工业联合会意见。
工人代表的遣派,除第15届杨有壬外,一般为国民党中央指派,由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定。但工方代表身份在第17届大会前,一般并非工人,而是官员。第12届劳工代表马超俊时为广东建议厅厅长、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14届代表方觉慧虽为南京总工会主席,但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训练部部长。方觉慧秘书则为工商部法规委员祝世康。其实,雇主代表如陈光甫也有双重身份。他既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又是蒋介石委任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法规定,劳工代表应由劳工团体产生。1933年3月,沪市总工会就此分向中央民运会与实业部呈请核准。这一动议为国民党中央所采纳。自第17届大会起,劳方代表改为由中央指派重要工业区工会负责人轮流参加。李永祥、安辅廷作为工会干部出席了第17届、18届大会。直到1936年第20届大会前夕,中央民众训练部始正式制定选派劳方代表方案,并提经国民党中央常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照办。该方案将劳工代表资格具体化:(1)现役工人,曾任工会理监事满5年以上者;(2)加入国民党满5年以上者;(3)初级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4)身体健全,年龄在25岁以上,45岁以下者。中央民众训练部饬令上海、汉口、广州、青岛特别市党部各推荐1名候选人,并指定天津及交通部门2名候选人,复经中央常会最后确定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为该届代表,海员工会赵班斧为助理代表兼秘书。(14)
由于每届改派不同人选,劳工代表多缺乏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朱学范注意到英、法、荷、瑞士等国的劳工代表曾多次出席大会,“劳工大会的生命,便操纵在他们的手中了”;强调为便于与各国劳工代表加强联系,不应频繁更换劳工代表。(15)中央民训部为此订定《国劳代表派遣办法》,规定自第22届起代表可连任三届。劳工代表的顾问与秘书,同样由中央民运会与其后的中央民训部遴选精通英文或法文并熟悉国内外劳工状况者担任。
南京政府虽然选派包括政府、雇主、劳工在内的完全代表团出席国劳大会,但三方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团结。第12届大会前夕,劳工代表马超俊在粤,雇主陈光甫在沪,雇主顾问夏奇峰在瑞士,直到日内瓦才会合。马超俊对国际劳工局将朱懋澄列为中国代表团第一代表甚为不满,在各国工人代表谈话会上,“大骂欧洲外交官不知国体,不知党义,不知三民主义”。朱懋澄等人又因马超俊“与胡汉民接近”,“均甚敷衍马”。(16)
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议案,一般均由实业部负责征集、审理。比如:为确定第20届大会提案,实业部曾分别函令各省市党部、海员、铁路特别党部详加研究,并兼采福建、山东、青海、汉口等省市党部及中华海员特别党部的意见。(17)有时因会期较紧,实业部亦缺乏必要的准备。第13届劳工大会议题侧重海员,工商部与外交部电达驻法公使高鲁、驻瑞士公使吴凯声,提请大会关注中国自主领海权与外国船主尊重中国劳工法两议案,却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要求香港地方当局发放失业赔偿、改善海员待遇、恢复香港分会的提案置之不顾。(18)
朱学范为此叹喟:劳方代表中“专家太少”,而国民政府对劳方代表事先又无“充分批示机宜”,导致代表“每感不遑应付之苦,以至不能在大会中及各国代表问,获得较好及较高之地位。”(19)
中国代表到日内瓦后,对国际劳工组织与各国代表有更直观的了解。陈光甫对汤玛士的处事能力不以为然,嘲讽汤玛士徒拿干薪而无实绩。(20)
国际劳工大会各会员国代表名额分配方法,原本是为平衡政府代表与非政府代表的力量,同时平衡劳资双方的力量。但因代表只要通知议长,指定顾问为自己的代理人,该代理人即有表决权。大会投票实行1人1票制,而非1国1票制,实际上政府代表人数一般占全部代表的半数,大会议案如无政府代表认可,往往不可能通过。因此,时人有谓“希望在这里造成拥护劳工福利的武器,这不仅是愚昧,而且是滑稽。”(21)就中国代表内部而言也是如此。12届到23届大会,仅第14届大会的资方、劳方代表与顾问人数超过政府代表。进而言之,无论是从代表的选举与审批,还是从向国劳大会提交的议案来看,资方与劳方多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决定权操之于国民政府。尽管劳工代表一如外国工人代表,也是“和平改革派的工团领袖”。但劳方与资方代表的选择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与国民政府的亲疏向背所决定。国劳大会中劳资两方抨击本国政府的情形,从未在中国劳资代表中发生。第19届大会劳方代表王锦霞曾指出,“大会出席代表,虽以国家为单位,然其实际组织,则政府、劳、资,划然为三组集团,各国政府代表之言论,常不为其劳资代表所赞同,而劳资两方尤有敌对之势。”(22)其言论似对中国政府的“一言堂”表示不满。
奥古斯坦·瓦格那在《中国劳动立法》一书中早就犀利地指出,“中国不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既有感兴趣于国际劳动会议的雇主协会,又有组织完善的劳工协会;出席国际劳工大会的雇主与工人代表均是名义而已。”(23)其评论尚称客观而中肯。
三、中国政府批准的国际公约
从1928年到1937年,国际劳工大会共通过37款公约、27项建议书。其中,国民政府批准实施的公约为12项,予以采用的建议书1项。
政府最初批准的国际公约,大多仅由实业部自行审核,毫不顾及劳资团体的态度,甚至相关机构也每每不明公约的旨意。国民政府批准最低工资公约,即因此深陷被动境地。
国劳大会规定,会员国至迟必须于1 8个月内将本届大会通过的公约送交本国立法机关审查,以定是否批准,再通知国联备案。如若批准,会员国必须开展立法工作,奉行公约。若会员国未将公约交付本国立法机关审查,或批准公约而迁延不实行,或违背约中条款,则要接受理事院或海牙国际法庭的处理,甚至经济制裁。1930年5月,工商部未听取各方意见便仓促批准最低工资公约,并拟具最低工资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立法院鉴于实际情形,决议缓行。国民政府因未实行所批准的公约,屡遭国际大会与国劳中国分局的指谪与敦促。行政院不得已于1934年2月公布国营企业最低工资暂行办法九条,以资搪塞。(24)
自1932年底,政府开始谨慎对待国际公约,一般先行征集各方意见后,再行拟具提案,提交行政院会议讨论决定是否批准公约。第16届大会后,国际劳工局将修订的“船舶起卸工人灾害防护公约”送达中国政府。实业部得到该公约条款后,致函中央民运会、交通部、各省市党部、各省实业厅及各特别市社会局征询意见,并咨上述各机关转饬各码头工会及总工会或有关公司、行栈提出建议,直到收到各方11份同意函后,始于1935年1月草拟提案,呈送行政院审议,迨立法院议决后,复通知国联中国批准实施该项公约。国民政府批准第19届国劳大会通过的“禁止雇用妇女工作于一切矿场地下公约”,中经近9个月较为广泛而审慎的调查。(25)批准公约的行为本身可以提高政府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信誉。既然实施上述公约没有任何阻碍,国民政府当然顺水推舟。
诸会员国均重视理事的竞选,以问鼎国劳组织的核心机构。实业部为应对第18届大会改选理事会,1933年下半年便着手清理与批准公约,藉以提高国家威信。到1934年第18届大会召开之前,国民政府除颁布“国营企业最低工资暂行办法”外,另批准“工业工人每周有一日休息”、“农业工人之集会结社”、“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关于工人灾害赔偿应受同等待遇”公约。此后是项工作持续开展。1935年10月,实业部分别函咨交通部、中央民训部,并通知中国商船驾驶总会等团体,针对“遣送海员回国”、“关于船舶遇险或沉没之失业赔偿”、“规定海上雇用儿童之最低工作年龄”、“关于海上雇用儿童及青年之强制体格检查”、“规定雇用火夫及扒炭之最低工作年龄”、“便利海员受雇”、“海员雇用契约条件”7个公约,回复意见。实业部综合各方意见,建议对“关于海上雇用儿童及青年之强制体格检查”、“便利海员受雇”公约从缓批准外,予以批准其他五个公约,并将审核意见呈报行政院。嗣经行政院会议议决、立法院审议、外交与劳工法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将“关于船舶遇险或沉没之失业赔偿公约”、“便利海员受雇公约”暂缓批准,其它5项公约可予批准。
国民政府正式批准12项国劳大会公约外,实业部也曾向行政院提请批准若干国际公约而为立法院所否决。1933年,行政院咨立法院批准的国际劳工大会公约中,原有“工业工人每周有一日休息”、“农业工人之集会结社约”、“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关于工人灾害赔偿应受同等待遇”、“雇用妇女夜间工作”与“女工生产前后之雇用”5个议案,后两项为立法院议决缓议。1934年,第18届国劳大会通过“修正妇女夜间工作”、“修正工人职业病赔偿”、“规定自动玻璃机厂工作时间”及“保证被迫失业工人之赔偿与津贴”4种公约。经实业部详加研究,仅将“保证被迫失业工人之赔偿与津贴”公约呈准行政院咨送立法院审理。该议案同样为立法院所否定。1935年,实业部将“修正船舶起卸工人灾害防护”、“非工业工作中童工雇用年龄之规定”公约提请审查,立法院仅批复前者。
国民政府面对国际保工热潮,在1928—1937年间共批准12项公约草案,占同期国劳大会通过议案的32.4%。1935年4月前,各会员国所批准公约占全部公约的23.5%(26)。两相比较,国民政府的成果值得肯定。不过,检阅具体议案,政府所批准的国际公约草案于调整劳资关系似无裨益。“航运重大包裹上标明重量公约”、“船舶起卸工人之灾害防护公约”、“禁止雇用妇女于一切矿场地下工作公约”,丝毫不牵涉劳资利益。“农业工人集会结社权公约”与中国现实俨然离题万里。有关海员事项的5项公约,与“中国海商法”、“海员管理暂行章程”、“整理中华海员工会办法”、“中华海员工会组织规则”等法规中所规定条款内容基本相同。“海员雇用契约条件”仅能为受雇于外轮的船员提供保护依据。“外国工人与本国工人关于灾害赔偿应受同等待遇公约”,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在国外的侨工,不如说是将在中国的洋职员所享受的特权合法化。与工人利益切实相关的“工业工人每周应有1日休息公约”(此前已写入工厂法第15条)与“最低工资公约”不过具文。按该公约所订“办法”及修正工厂法中条文要求,工人最低工资“应以各厂所在地之工人生活为标准”。然而劳工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在中国极为普遍。如此而言,该标准难以改善工人生活。劳工实际上得不到正常的休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难怪当时有人提议设立永久工资审议会具体掌控最低工资标准。(27)以上有关保护妇女、儿童的公约草案涉及的范围过小,大量的棉纺织厂中的女工与童工未能得到必要的保护。
与上述公约相对照的是,同一时期,一些与劳工利益更为直接的国际公约,如:“限制煤矿业工作时间公约”、“工商业工人自由职业工人及在家工作之工人与家庭佣仆之强制老年保险公约”、“雇用妇女夜间工作公约”、“工人职业疾病赔偿公约”、“非自愿失业工人之赔偿与津贴公约”、“每年假期给资公约”、“纺织业减少工作时间公约”,却未能为国民政府所批准。其它盟国情况与中国亦基本相当。时人在1936年曾如此评论国劳组织的功效:“就各国批准公约的情形来看,实在不能使人满意”(28)。
国民政府所批准的公约,更是缺乏防范劳资争议的功效,不可能真正改善劳工生活与生产处境。这不完全是国民政府之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国劳大会通过的公约本身特点所决定。至1935年上半年止,国劳大会通过公约草案共44项,其中以赔偿、保险为最多,计有21件。1927—1937年间通过的37件公约中,赔偿、保险有11件。而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维持合理的生活工资等为凡尔赛和约劳工编所规定的原则,均未体现在已制定的公约中。
其实,资方代表中有较为开明者。王志圣即主张保障工人权益,认为假期给资、缩减工时不容置疑。(29)严庆祥在第17届大会上,原则上赞同减少工作时间的动议。相反,政府对此较为消极;(30)且于1936年底拒绝国劳局邀请出席该局举办的“印刷业及其相关各业与化学工业减少工作时间三方专门预备会议”。朱懋澄出席第15届国劳大会前,向舆论界谈及此行一个重要目的是呼吁废止妇女夜工,但并未将此作为正式议案提交大会。(31)其原委当然是因政府反对而作罢。
四、结论
始自20世纪初,无论是西方工业社会,还是从传统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中国,劳资冲突均是社会矛盾中最为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巴黎和会采纳国际劳工立法委员会的建议创设国际劳工组织,其初衷就是藉国际合作消除劳资纠纷,促进保工立法运动的开展。
国民政府顺应国际潮流加入国际劳工组织虽然有化解劳资矛盾的目的,但该动机毕竟从属于废约与提高国际威望的首要目标。同时,无论是从政府、劳方、雇主代表的选举与审批,还是从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议案以及政府批准的公约草案来看,雇主与劳方多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决定权操之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从本质上不愿因加盟国际劳工组织而引起资方的反感,其政策的制定偏于资方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外学者当时就指出,中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20年,“在改善劳动状况方面是失败的”,“在调节工业状况方面几乎没有切实的结果,1919年前的情景,在20年后依然如故”(32)。
与之相应,国民政府对国际劳工局的直接干预也置若罔闻。陈宗城及其后任程海峰与代理局长王人麟,颇得劳资双方信任,以劳方代言人的姿态,鼓励工人自我奋斗,批评国民政府、雇主漠视劳工的态度。(33)国际劳工局助理局长莫勒脱、海外部部长伊士曼,也曾于1934年3月与1936年4月分别来华,考察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与政府、劳、资三方广泛交换意见,委婉地对中国劳动立法与实施提出批评。(34)国际劳工局扶助中国劳工的立场不可能改变国民政府护持资方的政策取向。总之,国民政府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有助于国际声望的提升,却无益于劳资关系的改善。
注释:
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际劳工组织主要有:国联指导下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运输总工会等三大组织。本文考察的是第一种组织。
②⑩(11)秦孝仪:《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实业方面》,革命文献第75辑,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21~22、21~22、159页。
③④《国际劳工局长汤麦来华使命》,《申报》1928年12月3日第4张第13版。
⑤⑦《中国急需劳工法》,天津《大公报》1928年11月22日,第2版。
⑥⑨《京市工整会欢迎多玛》,《申报》1928年12月1日,第3张第9版。
⑧《国际劳工局将在中国设分局》,《申报》1929年4月25日,第3张第9版。
(12)《国际劳工局宣布的中国十年建设计划》,《东方杂志》第28卷第20号,1931年10月25日,第1页。
(13)《本届国劳大会我资方代表已选出》,《中央日报》1933年3月2日,第1版。(下转第66页)(上接第106页)
(14)(17)《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央民众训练部工作概况报告》,1936年编印,第51页。
(15)朱学范:《国劳大会及意德劳工状况》,《上海邮工》第2卷第8期,1936年10月31日,第29~30页。
(16)(20)上海档案馆:《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2、99~100),99页。
(18)《国际劳工局长复海员总会函》,《申报》1929年10月28日,第4张第14版。
(19)朱学范:《出席第二十二届国际劳工大会报告书》,《中华邮工》第2卷第9、10期合刊,1936年12月31日,第46页。
(21)吴蕉桐:《所谓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农工》第1册,1935年10月,第294页。
(22)《我国出席国劳大会劳方代表报告书》,《中央日报》1935年9月3日,第1张第3版。
(23)(32)转引NYM WALED,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The John Company,New York.1945.p.145,pp.145,146.
(24)(26)吴知:《国际劳工大会与中国》,天津《大公报》1935年6月12日,第3张第11版。
(25)谢嘉:《中国最近批准几项国际劳动公约之经过》,《劳工月刊》第5卷第10期,第1,2、7~8,9~13页
(27)侯毓华:《最低工资之研究》,《中国实业》第1卷第5期,1935年5月15日,第892页。
(28)张左企:《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中华邮工》第2卷第(1、2、3)合刊,第40页,1936年3月15日。
(29)王志圣:《第十九届国际劳工大会报告》,《实业季报》第2卷第3期,1935年9月30日,第31、32页。
(30)《国劳会我国不允减工时》,《纺织时报》第995号,1933年6月15日,第2411页。
(31)《朱懋澄昨赴日内瓦出席十五次国劳大会》,《中央日报》1931年4月28日,第2张第4版。
(33)《劳工管理》,《纺织周刊》第2卷第15期,1932年4月22日,第363页。
(34)《国劳海外部长伊氏谈海外劳工现状》,《申报》1936年4月30日,第3张第11版。
标签:国际劳工组织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工会论文; 劳资关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申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