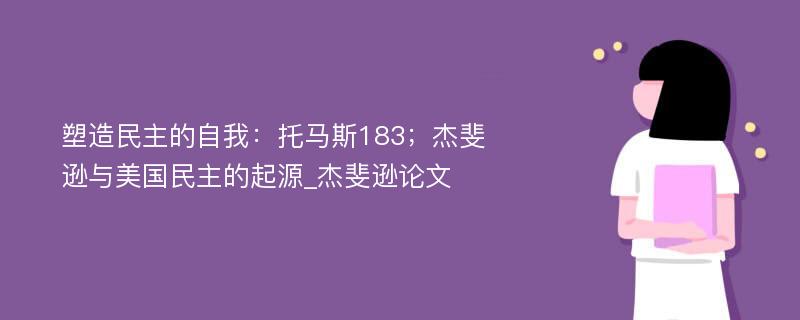
塑造一个民主的自我:托马斯#183;杰斐逊与美国民主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民主论文,美国论文,起源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托马斯·杰斐逊对民主的逐渐成形的理解,是伴随他在弗吉尼亚改变旧体制、为他所热爱的这个邦国以及整个合众国塑造一种新共和秩序的活动而出现的。对于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来说,美国的革命事业带有深刻的个人色彩,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当杰斐逊同大陆会议其他成员一道“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起誓时,他就塑造了一个关于其自我的新观念,这与他想象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是同步的①。
本文旨在从个人的维度阐述杰斐逊对革命的共和事业的奉献。回顾过去,杰斐逊签署他所起草的《独立宣言》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信仰转变的经历。这位革命的共和派变成了一个新人,从英帝国及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腐败而专制的旧体制中破茧而出。这位觉悟的革命者回首往事,认为这个殖民地的过去陷于朦胧的黑暗与无知当中。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第一段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十分醒目地表明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的连续性似乎突然就消失于无形了。用“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集体声音的表达,则以同样的方式抹去了作者的存在。当所有真正的美利坚爱国者从杰斐逊的稿子里读到这些句子时,他们仿佛睁开了双眼,找到了自己的声音②。但是,如果说杰斐逊本人消失了,那他不啻是对自己及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产生了强烈的意识。他的自传式文字或有意或无意地描绘了一个新的共和的或“民主的”自我的凸显过程。
杰斐逊的《弗吉尼亚札记》最初起草于革命战争期间,当时共和实验能否成功尚不确定。这本书无异于一幅焦虑的革命者的自画像,虽然是无意为之,却透露出许多信息。杰斐逊在40年后为教诲家人及子孙而写的《自传》,概述自己的公共生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从私人生活上移开。不过,杰斐逊决意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建造一堵“隔离墙”,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对杰斐逊来说,革命的全部意义在于取得家内领地的自主权,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新的共和派人士能进行自我塑造,新的共和派家庭能自我再生产,从而使美国自治政府的伟大实验得以更新和永存③。这个新共和国的真正的公民身份,并不是像某些倡导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古典和新古典人士所坚持的那样,仅只是确立于公共政治生活中。恰恰相反,杰斐逊倾其毕生精力力图去协调个人隐私和公共服务之间相互渗透、问题很多的边界,这表明现代共和主义,或者说是我们所谓的“民主”,有赖于塑造关于自我和公民身份的新观念。对杰斐逊而言,“民主的自我”是奠基于《独立宣言》中提出的基本原则之上的④。
一 共和信念
亚伯拉罕·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的《葛底斯堡演说》中回顾说,“87年以前”,托马斯·杰斐逊与其他革命先辈一起“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新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以雄辩的语言所表达的原则,乃是自治政府的原则。当1863年内战威胁到国家生存之际,这个原则仍如同在1776年一样是“不证自明”的。林肯告诫那些活着的同胞要再度献身于那些立国的原则,以确保“那些死去的人不会白死,这个上帝福佑的国家能获得自由的新生,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能永世长存”⑤。
这就是忠诚的共和派的信条,是把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永恒真理。杰斐逊写下了原初的词句,但他不承认自己在“原则或观点上的原创性”。在距他1826年7月4日去世仅有一年多一点的时候,杰斐逊对亨利·李谈到,《独立宣言》的“目的”并“不是要发现从未被想到过的新原则或新观点,也不仅只是说一些此前从未说过的东西,而是要用人们能够赞成的平实词句,把这一问题的常识摆在世人面前”⑥。杰斐逊只是说出了任何一个挣脱了旧体制的专制主义桎梏的开明人士都会说的话。美利坚人赞同这些永恒的真正原则,以此承认自己是独立的人民,通过解除“把他们与另一”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纽带”,并“在世界各国之中”取得适当的地位,从而掀开了自身历史的篇章⑦。
革命的爱国派唯有援引“自然法和自然神”这种超越世间万物的权威,才能为新国家伸张合法性。这不过是因为美利坚人同所有人一样,“被其造物主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于是得以声称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大陆会议要求殖民地居民在信念上跨出一大步,相信他们对自治政府的诉求符合自然法,因而得到了神意的应允。自治政府必须有超越其自身的资源。在那个时代,民众政府仍然让人联想到混乱、无法无天和暴民统治的形象,因此革命的共和派不得不从人民之外来为出于人民利益的主张寻找正当的理由。于是,杰斐逊便抹杀自我,不承认自己是《独立宣言》这一“美利坚圣经”的原创作者,旨在避免把它个人化而减损其权威性⑧。在旧式的君主统治体制中,教会和国家中的世俗权威和神权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其统治神秘化,让人相信他们并不是“生而平等的”,而是如杰斐逊在其最后一封公开信中所说,“人类的大多数”乃是“生下来便在背上装了一副马鞍”,而“受青睐的少数人”则“承蒙天恩,生来便穿着马靴,带着马刺,准备合法地骑在他们身上”⑨。
人民的正当要求若要得到伸张,首先必须使上帝回归其适当的位置,作为自然秩序的终极和超然的创造者,而不是作为人类事务中一个偏心的、反复无常的参与者,把“受青睐的少数人”提升到尊贵的、像神一样的地位。人之受到尊敬,是因为他们忠于上帝所认可的共和原则,而不是因为出于利己的目的而宣称享有神授的权力。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布:“这些原则构成了明亮的指路星辰,一直在我们前头闪耀,曾引导我们经历了一个革命和改革的时代。我们贤智之士的智慧和英雄们的热血,一直都倾注于实现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应当成为我们政治信念的信条,成为教导我国民众的课本,成为检验那些我们所信赖的人的工作的试金石。”⑩
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阐明了自己的信念,用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表达了那些他希望能将公民同胞们“同心同德”地“联合”起来的原则。可是,即便说“1800年革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一个“太阳下的新”事物,美国人也开始更加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联盟只有假以时日才能完善(11)。只有爱国的美利坚人始终忠诚于他们的政治信念的信条,也就是那些曾经激励革命的“贤智之士”和“英雄们”的永恒真理,共和主义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
杰斐逊的生涯是由过去与未来之间方向相反的拉力所塑造的。一方面,他回望“1776年精神”,当时英王乔治三世在殖民地的臣民们明确地表达和确立了自由政府的准则,把他们自己变成了美利坚人。在建国战争的艰苦考验中,革命之父们树立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爱国标准。可是,另一方面,杰斐逊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共和主义信念指向的是光辉的未来。他对“人类社会辉煌的进步和人类生存条件的巨大改善”所寄予的希望,同基督徒对“耶稣基督在整个世界毁灭前再统治一千年”的憧憬如出一辙(12)。
每当美国人想到民主时,他们总是跟随杰斐逊的引导。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一方面安顿了他们的过去,开启了他们作为一个有原则的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又预览了他们那千年至福般的未来,那时原则与实践最终合而为一,美国的历史就变成了全世界的历史。民主本身是永恒的,它将带领美国人和其他自由的人民走向“历史的终点”(13)。美国“例外论者”借助于上帝与自然,基于超越一切的价值构建了一种国家叙事。这些价值最初激励过杰斐逊及其革命的同伴,后来又在若干代人的时间里回响在赋予边缘和受排斥的群体选举权和权力的运动中。林肯在1861年写道,《独立宣言》关于“全体人的自由”的原则,其特点在于“‘说得恰到好处’的那句话已证明乃是我们的‘金苹果’”。这是“为所有人扫清道路的原则,给所有人希望,因而也就给所有人进取心和勤劳精神”。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联盟,还有宪法,乃是银质的装饰,相续环绕在它的外框”。有关宪法解释的激烈争论的历史,一个长期饱受党派与地域冲突摧残而正在崩溃的联盟的历史,使得美国人更加迫切地感到,不能忘记杰斐逊的“明亮的指路星辰”和林肯的“金苹果”:“装饰是为金苹果而制作的,而非金苹果为装饰而制作。”(14)
本文的意图在于表明,杰斐逊的民主观念乃是构成美国历史的具体情势和偶然因素的产物。我借用林肯的意象以重新描写那个“金苹果”,并不是要把这一信念当作假相来戳穿,而是旨在说明杰斐逊确实把它作为信念来信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不打算通过杰斐逊的藏书室来从西方政治和宪政思想的伟大传统中去追溯其观念的源流。杰斐逊决定与革命的爱国者站在一起,并不令人惊奇。这确实是早已注定的事。他把在可能而且必要之时与英国的决裂归功于人民的常识,这是十分正确的。
作为一个忠诚的共和派,杰斐逊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他之奉献于革命,认同于“1776年精神”,这在他一生中乃是起界定作用的时刻,是新与旧之间、黑与白之间的枢纽。杰斐逊同他的美利坚同胞一起摆脱了殖民臣服的枷锁,伸张其与生俱来的权利,通过失去“旧我”而找到了“新我”。历史学家们有理由怀疑弗吉尼亚的革命转变,因为旧时的统治精英,包括杰斐逊本人,成功地保持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可是杰斐逊坚信,随着新共和体制的出现,一切都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爱国者固然热爱自己的“乡国”弗吉尼亚,但对曾以同英王的联系为荣的“老领地”,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怀旧之情。与此相反,杰斐逊在构想一个腐败的“旧体制”作为其新共和国的陪衬和反面样板时,夸大并嘲弄了弗吉尼亚那种招摇卖弄的英国特色(15)。
二 《弗吉尼亚札记》
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它构成一幅民主化的蓝图。尽管杰斐逊从未完全接受“民主”一词,但他认为有必要持续不断地把有警惕性和有美德的公民调动起来,以保证弗吉尼亚和美国的共和主义革命取得成功。自由的弗吉尼亚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于那些土生土长的“贵族”,他们在独立之前摆出了想要独占财产和权力的架势,这就给了杰斐逊及其爱国的同伴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机会。
于是,杰斐逊在共和制的弗吉尼亚清除贵族制残余的尝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779年,这位锐意改革的立法者提出“一整套”法律:废除长子继承制和限定嗣续法,确立宗教自由,要求实行全民教育。他希望借此“铲除过去或未来的贵族制,一丝一毫也不留,并且为真正的共和制政府打好基础”(16)。杰斐逊在自己唯一出版发行的著作《弗吉尼亚札记》中,扩大了对旧体制的抨击,倡导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并将他们迁移到国外,进行彻底的宪政改革以便为新共和国奠定更稳定、更持久的基础。杰斐逊作为一名改革家至多是成败参半的:促进知识传播的法案一直没有制定,解放奴隶的前景变得遥遥无期,起草新州宪法以促进县政府民主化的动议遭到了断然拒绝。但杰斐逊始终保持信念,即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也是如此。
杰斐逊对新国家的革命前景的深切忧患,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有充分的体现。这本书是他最为经久不衰却又是无意为之的一部自传体著作(17)。正如在回顾他在《独立宣言》成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一样,杰斐逊又把自己融入了人民(这次是弗吉尼亚人民)当中,同时也把自己同那些没有启蒙开化的人区别开来,因为后者缺乏实现本州的宏伟目标的美德和进取心。这位激进的共和派条件反射般地认为自己与人民是一体的,反对他们的“贵族”压迫者,但对人民本身也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因而对他本人为革命的奉献也有同样的忧虑。在他自己的文章里,尽管在人称所指上看不到他个人的明显痕迹,但这位焦虑不安的共和主义道德家却有十分鲜明的显现。
《弗吉尼亚札记》概述了关于杰斐逊所热爱的“乡国”,也是美国革命结束时联盟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州的情况和看法,其写作缘起是为了回应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马布瓦的一系列“提问”,此人把这些“提问”散播于美利坚各个新共和国的头面人物中间。由于把自己与弗吉尼亚等同起来乃是杰斐逊自我理解的核心,因此他对马布瓦的回应就格外带有自我显现的色彩。杰斐逊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最为持久和最具系统性地描绘了弗吉尼亚的革命性转变,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他对共和主义的救赎潜能的信念。不过,他也从未掩饰对子孙后代可能无法实现革命理想的忧惧。
在1781年年底起草回应马布瓦的第一篇稿子时,杰斐逊还是一个年轻人。虽然杰斐逊当时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大陆会议担任《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在弗吉尼亚则是一名锐意改革的立法者,但他作为战时州长的不佳表现仍给他未来的前途蒙上了阴影。1780年12月,投敌分子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入侵该州,由于缺乏宪法权威和政治资源来组织有效的抵抗,杰斐逊和立法机构只得从该州首府里士满逃到夏洛茨维尔;巴纳斯特·塔尔顿接着又猛然地袭击了夏洛茨维尔,迫使他们再次慌忙逃走,这位陷入困境的前州长便躲到他那靠近林奇堡的波普勒·福里斯特种植园避难,立法机构则在山外的斯汤顿重新开会。不过,尽管弗吉尼亚的抵抗严重不足,但英国的威胁还是很快被消除了。英军指挥官查尔斯·康沃利斯将军在约克敦陷入了法军和美军共同设下的陷阱,他的投降(1781年12月19日)使英国反对革命的战斗意志大伤元气,转而寻求和平的解决之道。尽管弗吉尼亚议会做出决议,要“取消和撤除所有不应得的责备”⑻,但共和制的弗吉尼亚几乎被从地图上抹掉,杰斐逊的生涯也蒙上了无法抹掉的污点。虽说这个邦国得以幸存,但无论杰斐逊还是他的弗吉尼亚同胞,对这一愉快的结果都无寸功可言,只有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大陆军是个光荣的例外。
当杰斐逊写出《弗吉尼亚札记》的草稿并在随后几年对其加以修订时,弗吉尼亚的前景重现光明。弗吉尼亚位置居中,版图和人口都超过其他任何一州,在已获独立而成为一个自治国家的联盟中,注定要担当领头的角色。杰斐逊对“提问”的许多回应都富于远见,带有积极向上的劲头,表明他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而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典型模式中,从广袤的领土、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无限的资源着眼,未来是可以预测和规划的。不过,弗吉尼亚人是否具备足够的美德和爱国精神去实现本州的理想,这类根本问题一直困扰着杰斐逊。马布瓦提出的问题引导杰斐逊从两方面探究弗吉尼亚州宪法的可行性:一是从常见的现代意义上推敲1776年州宪法,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思考政治体在宪法和特性上的缺陷。
在《弗吉尼亚札记》中,杰斐逊的作者身份并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它仍然是一部极富个人色彩的作品,成书于他的世界和个人生活均发生划时代变化的时期。他在1781年就已抑郁寡欢,转年妻子玛莎·韦利思·杰斐逊的去世又给了他毁灭性的打击,致使其抑郁加深。稍后,他接受了新的公共职位,先是担任弗吉尼亚在邦联国会的代表(1783-1784),接着又出任新国家驻巴黎的代表(1784-1789),这才使他的情绪得以好转。《弗吉尼亚札记》初版于1785年,是一个私人性的法文版,本意是只在小范围发行;只有1787年在伦敦推出第一个英文版(斯托克代尔版)后,它才有了广泛的读者(19)。杰斐逊本不愿出版这本书,但又担心删节和误译原文的版本出现,导致外界对他产生误解。除了以公务人员身份撰写的一些著名的政府公文外,杰斐逊此后也避免发表自己的文字。杰斐逊不愿出版《弗吉尼亚札记》,表明他意识到其中某些章节,尤其是关于奴隶制和弗吉尼亚宪法的内容,可能会引发争议,过多地暴露他个人的观点,并因此损害他的公共形象。他的自我意识还十分明显地体现在他对斯托克代尔版的扉页插图的选择上,用的是一幅他那当过测量员的父亲彼得·杰斐逊同威廉—玛丽学院教授乔舒亚·弗赖伊于1751年共同绘制的弗吉尼亚地图。当杰斐逊同时把自己同他的父亲和弗吉尼亚等同起来之际,为子的孝心与爱国主义也就融为一体了。
杰斐逊在依次回答马布瓦的提问时,着重强调了三大主题。他首先回答了一系列关于弗吉尼亚自然地理的问题(第1~7问),这可以视作是他对弗赖伊—杰斐逊所绘制地图的足以流传的阐释,也可看作是那幅地图的散文版;他接下来回答了第8~11问,概述并分析了弗吉尼亚的人口;在回答第12~22问时,他对弗吉尼亚的政府、法律、风习和公共统计数据作了探讨;《弗吉尼亚札记》最后以回答第23问结束,涉及弗吉尼亚早期的历史(杰斐逊认为这还不够充分),并附上了弗吉尼亚重要政府文件的目录。依托于弗吉尼亚未来发展的简要说明和有助于了解其过去的资料汇编,杰斐逊对当时的弗吉尼亚人以及他们是否具备实现美国革命理想的能力作了含混模糊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构成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弗吉尼亚的前景看来是无可限量的,但前提是弗吉尼亚人能把握它们。在杰斐逊开始写作《弗吉尼亚札记》时,这个邦国的领土主张还没有得到其他各邦或外国势力的承认,其北部和西部以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为界,覆盖面积达121 525平方英里,这一广袤的地域“比英国及爱尔兰诸岛大三分之一”(第1问)(20)。河流(第2问)将是弗吉尼亚内陆发展的关键,一旦波托马克河与密西西比河水系连通,就更是如此。大自然眷顾弗吉尼亚人,但他们也有责任去开发利用这些优越条件。他在第6问中详细列举了矿产、植物和动物等资源,其暗含的意思正在于此。杰斐逊还驳斥了欧洲某些著名的动植物学家的说法,后者认为新世界的动物物种,包括人类,都在不断退化。他收集了不少资料,证明美利坚人跟旧世界的人一样高大,或许还更加高大一些。这个新国家已经产生了一批“天才人物”,包括“世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的乔治·华盛顿,集科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天文学家戴维·里滕豪斯,他们充分显示了这个国家里人的发展(21)。不过,即便是这些爱国的论辩,也还是暴露出杰斐逊的忧虑。后来的各代人能达到革命一代的那种高标准吗?美利坚人能顺利地利用其自然优势吗?弗吉尼亚能将其有效管辖扩大到彼得·杰斐逊和他的儿子托马斯所绘制和描述的边界极限吗?
弗吉尼亚的未来取决于其人口的规模和特征。杰斐逊的数据表明,弗吉尼亚的人口每“27年零3个月”便增长1倍,这意味着弗吉尼亚的人口密度终有一天将赶上“英伦三岛”。但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人口呢?太多的非英语移民将构成弗吉尼亚的“复杂多样、缺乏凝聚力和散漫松懈的大众”,这些人对“英国宪法以及其他来自于自然权利和理性的”原则一无所知(第8问)。弗吉尼亚为数567 614的总人口中,还包括259 230名“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奴隶”。杰斐逊在此前几问中所赞扬的那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对奴隶人口的增长起着违背常理的作用:“我们国家的这一污点增长太快,跟白人人口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22)奴隶比那些未被同化的移民更糟糕,因为正如杰斐逊后来所声称的(第14问),“他们”在奴役中“所承受的伤害”使他们成为弗吉尼亚白人的天敌(23)。
尽管杰斐逊在详细地谈论弗吉尼亚前途不可限量的美景,但当他从该州土地和居民转向其政府与法律时,一些令人困扰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弗吉尼亚作为一个独立的邦国,可以控制其人口的增长及其特征,可以向其他各州主张并伸张领土的权利,可以决定将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可是,杰斐逊特别担忧《宗教自由法案》的不确定的未来。该法于1779年出台,是旨在完成弗吉尼亚共和革命的一系列广泛的法律改革的一部分:“在这场战争结束时,那些还未被挣脱的……桎梏,仍将长期束缚着我们,而且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直到我们的权利在某次动荡中一举恢复或者彻底丧失。”(第17问)(24)如果立法机构不能解放奴隶并将他们迁往国外,就会“造成动荡”(第14问),从而危害弗吉尼亚共和制的未来(25)。杰斐逊对这个邦国的担忧,与他本人在1781年下半年遇到的事业危机发生了“共振”。
英国的入侵表明弗吉尼亚宪法存在根本性的缺陷。1781年6月,立法机构曾考虑设立一个“独裁官”,使之在紧急时刻行使超常的专制权力,这样便会取代宪法设立的执行官(即杰斐逊本人),并摧毁共和制(26)。“仅只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人民的背叛”,而且确实是“对整个人类的背叛”(第13问)(27)。根据1776年宪法,众议院的权力过分集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专制主义的倾向,因为“173个专制者肯定和一个专制者一样压迫人”(28)。宪法本身是一个自我任命的革命大会制定的,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或批准。弗吉尼亚人非但没有修补这些缺陷,反而带有十分轻易地牺牲自身权利的倾向,会倒退到某种比君主制更坏的状态中去。
也许正像杰斐逊的战时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弗吉尼亚人缺乏必要的精神和美德持续进行共和主义实验,实现《弗吉尼亚札记》为他们展现的光辉的目标。奴隶制对于弗吉尼亚的繁荣的核心意义更加深了他的忧虑。一方面,杰斐逊很清楚,私人财富和公共收入取决于“土地和奴隶两项结合所产生的价值”,会继续在每一代人时间里就翻一番:奴隶对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弗吉尼亚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第22问)(29)。但是,另一方面,这位共和主义道德家“为我的乡国惊恐战栗”,深知公正的上帝终有一天会首肯“命运之轮的回转”。奴隶的解放将会因“其主人的同意”而实现,抑或是会在一场血腥的种族战争中得以“解决”(第18问)(30)?
在回答马布瓦的提问时,杰斐逊假设了多种不同的角色和声音,于是就构想出若干个不同的“弗吉尼亚”,同时也暴露了他自己在事业特别困难之际的深刻的矛盾心理。他对弗吉尼亚国民性的关注,在随后有关“风习”(第18问)和“制造业”(第19问)的各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论法的精神》(1743)的作者、伟大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及其追随者看来,一个民族的习俗或风习,对任何统治体制的宪法来说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31)。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杰斐逊在讨论风习时,着重强调了蓄奴制对奴隶主阶层的退化效应:“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全部交往,就是永无止境地发泄至为狂暴的情绪”和“从不间断的专制暴虐”。更坏的是奴隶制对年轻一代具有道德堕落效应,使之“在暴虐中受到哺育、接受教育和日常锻炼”(32)。只有当转向讨论制造业时,杰斐逊才恢复了对人民的信心,因为“那些在地上劳动的人是上帝的选民”,是“大量的真实美德的特殊保有者”。这时,他笔下的弗吉尼亚人成了农夫,而不是蓄奴的专横之徒,他们拥有美德,正好与欧洲“大城市”中那种腐败而依附于人的“暴民”形成对照(33)。杰斐逊在论及动物的体形大小时,再一次将有美德的新世界与堕落的旧世界对举,这表明他恢复了对美国革命拯救弗吉尼亚乃至整个人类的可能性的意识。
《弗吉尼亚札记》是一幅作者在其人生关键时刻的自画像,比他在1821年所写的《自传》揭示了更多的东西。当然,杰斐逊在回答马布瓦的提问时,并不知道他自己或整个弗吉尼亚邦国的故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杰斐逊在希望与恐惧中备受煎熬,以其《弗吉尼亚札记》向读者展示了对美国革命经验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重要洞见。他的最大愿望,也即其共和主义的基本信条,就是年轻一代将会受到“1776年精神”的激励,去实现革命的理想。
三 “地球属于活着的人”
杰斐逊在回顾“殖民地平静而单调的生活”时,对他自己或他那一代弗吉尼亚人都没有清楚的认识。他在1814年对他的年轻邻居爱德华·科尔斯说,他还是一个富于理想精神的年轻立法者时,曾下定决心要对奴隶制做点什么。但是,杰斐逊“很快就发现”,从当时统治这个地区的“上一代人”那里,是“什么也不能指望的”,因为这些人把奴隶视为“同他们的马和牛一样的合法从属物”(34)。革命改变了弗吉尼亚,它在使帝国分裂的同时,也使两代人之间露出了断层线。因而新弗吉尼亚邦国之独立于“老领地”,恰如联合诸殖民地之独立于英国。杰斐逊在1789年9月对詹姆斯·麦迪逊说出了这样的名言:“一代人之于另一代人,正如一个独立的国家之于另一国家。”(35)
杰斐逊是一位弗吉尼亚的爱国者,对其“乡国”怀有强烈的热爱。可是,他和他的革命同伴们一起同时又宣布与“上一代人”断绝关系,而这“上一代人”乃是弗吉尼亚人的父辈,他们塑造了大都会旧体制的地方版本。弗吉尼亚少数大家族积聚广阔的土地和大量的奴隶,模仿英国相同阶层的优雅做派,以此谋求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并使之永久化。对这种正在兴起的地方“贵族制”的憎恶,激发了杰斐逊的激进共和主义;而这种“贵族制”的扩散特性和目标的模糊性,更使他怒火满腔(36)。事实上,虽说弗吉尼亚的大多数地方精英并不总是拥有杰斐逊那样的热情和信念,但他们毕竟都站在了爱国事业一边。因此,杰斐逊的改革能量发生了转移,具备了非个人化的特点,所针对的主要是精英统治在法律和制度上的支柱,包括土地法、英国圣公会的正统地位、寡头性质的县法院等,而不是那些一直效忠于英国王室和抵制革命的实际的“托利派”弗吉尼亚人(37)。
杰斐逊与父辈们的争执在言辞上是无所不包的,致使他将整整“一代人”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杰斐逊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动血雨腥风的代际战争。相反,杰斐逊努力在代与代之间划出界线,特别是相信“代”、而不是特定的家族可以作为整体而存在于社会的观念,恰恰是旨在促进和平。后续的世代可以是一些“独立的国家”,但父辈们可以大度地放弃对年轻一代的权威,以确保他们之间持久的和平。而且,他们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也可以是欣然接受弗吉尼亚和美国的独立,从而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服从一个由平等的人所构成的共和国里大多数人的意志。杰斐逊在代与代之间划出界线,目的是要在正义和持久的基础上把他们联合起来。《独立宣言》却划出了另一条界线,出于相反的目的而把美利坚人和不列颠人区分开来,使之成为分立的人民,“战时是敌人,而和平时期则是朋友”(38)。
如果把杰斐逊为弗吉尼亚制定的代际和平方案同《独立宣言》的好战而嗜血的言辞并置在一起,就能清楚地看出他力图塑造一个“民主的自我”的那个领域。杰斐逊毕生致力于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界定和创造一个位置,这对他逐渐演化的关于我们今天称作民主的观念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故事,其开端是一个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英王臣民转化为一个自治的共和制邦国的公民。杰斐逊把自己界定为一个他自己发明的地方旧体制的反对者,认为他所属的阶级,包括他自己,具有种种反共和制的贵族式冲动,对弗吉尼亚及美国的独立构成危害,他要在想象中洗刷掉这一污点。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看成一个新的共和主义者,与他的公民同胞平等一致,不再受过去这个“阴魂”的纠缠。这是一种独立与自主的幻象,受到了那些终身折磨他的伤人的个人负债感的掩盖,或许还受到了它们的激发(39)。
个人独立使得共和政府成为可能,而杰斐逊则把对它的威胁外在化。他把自己对“贵族制”的变化不定的看法投射到外国敌人的身上,其最初的敌人是英王和他的跟班,最后还包括数目不断增加的受到英国势力和样板腐蚀的国内敌人。这些即将露头的暴君和独裁者,体现了威胁到共和政府在弗吉尼亚、合众国以及整个文明世界获得成功的一切东西:他们应当死掉。杰斐逊似乎同样乐意牺牲其爱国同胞的生命,因为“爱国者与暴君的鲜血”乃是浇灌“自由之树”的“天然养料”(40)。他那种浸透着鲜血的语言是抽象而非人化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不见血的,因为他意在对人类历史作一番大扫除。杰斐逊在1793年写信给威廉·肖特说,为了推进自由的事业,“我宁可看到半个地球变成荒原”;进而言之,如果“每个国家都只剩下”一个“亚当和一个夏娃,只要他们是自由的,也比目前的状况要好一些”(41)。他于1816年向老朋友亚当斯预言说,虽然数百万条生命已在欧洲的战场上失去,但在欧洲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自治之前,“鲜血还会像江河一样流淌”(42)。
杰斐逊在自由和奴役、朋友和敌人之间划的界线,是铭刻在鲜血之中的。相比之下,把共和的爱国者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是基于原则而承诺维护他们自己及彼此的权利,承认彼此都是平等而自主的公民。共和的宪法保证公民个人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边界内获得支配权,使得可以同时促成自我塑造、社会性和文明进步的共识性联合成为可能。因此,杰斐逊的共和信念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朝外指向的是一个危险而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在这里爱国者们互相召唤,要用最终的流血牺牲来为子孙后代赢得解放和自由;朝内则指向自我的领域,由每个公民的自然权利来加以界定和强化。
向外看,公民们需要保持警惕,觉察到对权力的滥用和对其权利的蚕食。不过,在杰斐逊的共和国里,等级制被取消,平等盛行,没有什么更高的权力可以向下窥探任何人的家庭私事。杰斐逊在思考联邦制时很清楚地意识到,自治不仅是社会的最大需要,也是个人的最大需要。他曾对约瑟夫·卡贝尔说过,只要“把这些共和国一分再分,划分成从全国性的大单位一直到所有的从属单位,最后止于每个人自己对自己农场的管理,并把每个人的双眼所能照看的事情置于他自己的手中,那么一切都会办得最好”(43)。
杰斐逊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标出了自我的领域。杰斐逊在关于每代人的主权的观念中,划出了家庭内部的边界;在关于家户独立的观念中,划出了家庭之间的边界;在关于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中,划出了公民中间的边界。他以此将个体性的自我从构成传统政治体的从属和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中解放出来。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要对旧体制施以共和主义的打击,有赖于某种关于个体的新的、抽象而脱离实体的观念,这一个体在理论上与其他所有个体都是平等的,有能力对不断趋于完善的联盟表达同意。共和派诉诸自然权利的做法,抹去了传统的社会与政治纽带的神秘性,揭露了一个曾经显得有机而天然倾向于专断、虚假和暴虐的世界。平等的原则消除了个人的屈从,使“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拥有主权,并获得其权利。
构成作为人民的个体公民的平等权利,以及人民依照“自然法和自然神”而行使的合法的、自发的权利,乃是杰斐逊的共和主义信念中的基本信条(44)。这些公民的特征是通过否定和抽象化来界定的,使他们脱离实体,剥去他们身上那些使旧社会秩序变得可以理解的差异和区别的标记,从而使得所有人一律平等。为了把他人“看成”平等的人,忠诚的共和派必须将目光从他人的私人事务领域上移开,而聚焦于“他自己的眼睛所能照看到的事情上”。
私与公、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区别,在杰斐逊的自我理解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划定并加固防卫性的屏障,以抵御对其私人权利的可能到来的猛烈攻击,把共和国作为一个基于形成中的原则和情感的真正联盟,为它想象出一个和平而免于冲突的未来,以此来替他自己创造的空间。但是,杰斐逊从未相信这样一个联盟已经或可能完全企及。无论富有经验的改革家如何“用斧头砍去伪贵族制的根子”(45),旧制度都不可能被彻底铲除。有警惕性的公民应当时刻戒备,将再生的“贵族制”苗头连根拔除,永葆“1776年精神”的活力。正如杰斐逊的语言所表明的,“贵族制”代表着一种对共和国的显而易见的实体性威胁:他心目中的“贵族制”敌人是“真实的”,是有实际形体的人,是使得他义愤填膺、怒火中烧的实在对象;而他那些共和派“友人”绝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杰斐逊深信,美国获得独立的1776年,乃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关键的年份。但由于旧制度不可能只限于弗吉尼亚的过去,因此他不得不阐明有可能颠覆共和实验的“贵族制”冲动的持久性。杰斐逊素有恐英的毛病,而对美国人美德的担忧更是激发了他对英国的憎恨:在从前的母国反对美国独立的反革命密谋中,在它对前殖民地臣民的阴险有害的“影响”中,旧体制继续存在了很长时期(46)。因此,革命的共和派难免就会认为,对共同事业的奉献摇摆不定,无异于对英国王权及所有英格兰事物恋恋不舍。他们还喜欢把他们要在自己身上加以抑制的倾向投射到他人身上。通过宣布独立,杰斐逊和他的爱国同伴一起拒绝了旧帝国大都市对他们自己的强大吸引。杀死国王是、或者说应当是一种信念转化的体验,对臣服的各殖民地和个体的臣民都是如此,因为前者变成了若干独立的共和国,后者则变成了公民。但是,表面的清晰性和决定的终极性引发了普遍的疑虑。爱国者们能相互信任彼此说过的话吗?他们能跟《独立宣言》签署者一道“相互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神圣的名誉共同起誓”吗?
《独立宣言》启动了以平等权利和经人民同意的政府为平台的美利坚实验,致力于以新体制来为其成员获得“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7)。不过,这种关于主权自我的耳熟能详、过于早熟的现代颂词,正好与呼唤牺牲的革命号召形成对应。旧的臣民必须死掉,新的公民才能存活,而且公民只有甘愿为共和国的生存而做出最后的牺牲,才能了解自己,才能认识其同胞。杰斐逊向民主派的演变反映了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在由平等者构成的国家里实现自我的升华,一是倾向于个人权利、道德责任和自我主权等强有力的观念。这些对杰斐逊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必然要求。恰恰相反,只有那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国者,那种从旧体制中脱颖而出的新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共和派,在其共和主义得到保障的私人领域里塑造自我,进而培养共和主义的信念。杰斐逊对共和主义的信奉无外乎是一种信念,一种他在新国家前途未卜的晦暗而不确定时刻仍在反复重申的信念。
四 《自传》
杰斐逊想要作为一名忠诚的共和派而被人铭记(48)。他的并不多见的自传性随笔,他为自己设计的墓碑,都聚焦于他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成就。他撰写的碑文并没有逐一列举自己所担任过的职务,而是强调了自己在对一个自由的人民发言并推进其思想启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即“《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者,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始人”(49)。杰斐逊所留下的遗产是“起草者”和“创始人”的遗产,子孙后代将永远铭记他,感激他帮助他们重新找到了自然权利,开启了自治的实验。杰斐逊与这个新国家具有如此完全的同一性,以至于它的继续存在就是他最终的纪念碑。
那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革命爱国者,使得他们的美利坚同胞追求幸福、塑造自己的身份成为可能。杰斐逊希望生前身后都保持这种“特性”,这要求他拒绝和抑制那种可能把自己抬到高于其国人的野心,避免重新创造那种他一直设法废除的不平等体制。在共和国里,公共人物无私地将自己的精力用于公共福祉。但是,如果以公谋私的行为不得不受到抑制,杰斐逊就能培育一种关于私生活中的自己的更强劲的意识,安稳地待在权利的保护屏障之后,遮挡住别人窥探的眼光。他的墓碑永久性地标出了公共人物的成就与个人隐私的神圣领域之间的区别,仅只是记下了他生于1743年,卒于1826年美国的第50个独立纪念日。不过,杰斐逊选择在墓碑上列举的公共成就,也充分显示了自我塑造的紧迫性:《独立宣言》中的自由人,将会寻求因不受约束的良知而成为可能的思想启蒙和自我理解。
杰斐逊在去世前几年撰写了一部片断性的《自传》,供家人私下传阅(50)。他在简短地谈到父系的家世和轻描淡写地提及母亲简的伦道夫“家系”之后,这位反“贵族制”的杰斐逊就转向了重点讲述其自我造就的父亲彼得所取得的成就。彼得·杰斐逊“意志坚强,判断合理,热切求知”,通过“大量读书而改善自我”,由此克服了正规教育不足的局限。彼得是一个激励托马斯的榜样,他给儿子提供的教育也是他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彼得于1757年去世,托马斯刚刚12岁,此后他的老师们就成了替代性的父亲,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廉—玛丽学院的法学教授乔治·威思,“一个年轻时最可信赖和最受敬爱的导师,一个终生的挚友”(51)。
杰斐逊关于代际传承的观念,包括父亲及导师培养子弟以代替他们的位置的想法,源于他的童年经历。当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投入走向前台时,代际之间那些更为复杂和含混的交接,比如土地、奴隶和债务的移交等,就退到了幕后。岳父约翰·韦利思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又是种植园主和买卖奴隶的商人,凭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可观的财富”,在1773年去世时,给女儿和女婿留下了其地产中的“很大”一份,“大致相当于我自己的家传财产,这样就成倍地改善了我们的境况”(52)。在杰斐逊的回忆中,他的父亲和岳父有一个突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夸耀显赫的家系,都克服了受正规教育不足的局限而自我创业。
对父子关系的集中关注转移了对母子纽带以及把弗吉尼亚少数大家族联结起来的关系的注意。杰斐逊之所以轻描淡写地提及其母亲的家庭,很可能是出于对她在1776年3月去世前持续控制其父财产的怨恨(53)。但在我看来,杰斐逊对他的母亲说得相对较少,更有可能是他对老领地“贵族制”的基本态度的结果。杰斐逊在想象中将自己从乡绅的家系中剥离出来,转而强调理想化的父子关系,以此宣告他个人的独立。于是,这位共和派父亲就能向往某种对家户领地的家长式主导,而不受更广泛的家庭义务的束缚(54)。他在蒙蒂塞洛有许多依靠他为生的人聚集在他周围,他便能把自己想象成“所受福佑并不稍逊于那些最受福佑的家长”,不仅保证他的女儿及其丈夫和孩子、而且还保证他的奴隶得到福利和“幸福”(55)。对杰斐逊来说,家长式主导乃是贵族专制的对立物,是一种不附带家系束缚的父爱的温情表达。因此,乔治·华盛顿乃是他的国家的共和之父,而不是一个家族王朝的创建者;塞缪尔·亚当斯乃是“自由的宗主”,本杰明·富兰克林则是法国和美国共和派共同的“宗主”(56)。
杰斐逊对家长制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对内指向家庭的领域,也就是自我的领地;对外则要使王朝式的冲动在廉洁无私的公共服务中得到升华。这两方面的区别对杰斐逊来说乃是绝对的。家庭生活是不受侵犯的私人领地,杰斐逊和那些依靠他为生的人在这里可以过着欣欣向荣的日子,不受他人的窥探和外来干扰;与此相对照,公共生活则是透明的,处在那些小心维护其权利的自由公民的警惕的目光之下。杰斐逊在《自传》中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三缄其口,反映了家庭隐私对他的个人发展具有核心意义。在关于婚姻的讨论中,他对妻子玛莎只字不提,反而着重强调了他岳父的性格与财富。只有当叙及1782年11月重新担任公职一事时,他才提到在两个月前失去了“我生活中最珍爱的伴侣,我和她相亲相爱,始终如一,使我在过去十年里生活在长盛不衰的幸福之中”(57)。玛莎的婚后生活被置于括号里,放在她的结婚日期和去世日期之间,甚至与家庭成员隔开。为了确保他们关系的私密性,杰斐逊还销毁了两人之间的通信(58)。
杰斐逊的《自传》并没有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当然,他预想的读者早已了解家里的这个人,无须杰斐逊来帮助他们保持他们自己的记忆。但不清楚的是,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何以觉得他的家人需要对他早年的政治生涯了解如此之多;由于对他们的阅读兴趣不放心,很可能导致他把叙述中止于1790年3月,其时他抵达纽约,出任华盛顿第一届政府的国务卿。也许杰斐逊需要再让他的几个女儿确信,她们在这个日子以前的个人牺牲,乃是为了一桩更重要的事业,而给她们的童年留下印记和创伤的多次搬迁和扰攘,同样也是他个人的牺牲。杰斐逊在《自传》的字里行间所描述的那个公共人物,因此就会占据这个他一直缺席的私人空间,出现在一种破裂而混乱的家内生活中。也许杰斐逊是想就自己未尽为父之道对女儿们表达歉意,也许是反过来想让她们对他表示同情,因为公共服务的要求残酷地将他拽出了家庭的怀抱。
杰斐逊在后期的家信中以生花妙笔描写田园诗式的家内生活,把家庭的舒适与“党派冲突的激烈和骚乱”对举,进一步发挥了《自传》中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对举的观点。当这位家长最终返回蒙蒂塞洛时,他的福气的圆圈就会变得完满。杰斐逊在1792年对女儿玛莎说:“如果不是把你的幸福看得比我自己的更重,我就会嫉妒你现在这种宁静的生活。但这种生活也该轮到我了。”(59)与此同时,当杰斐逊真的在蒙蒂塞洛打发光阴时,他远远地想象过的那种宁静的家内生活却经常受到干扰。在1790年代中期他短暂“退休”以前、其间和之后,他的政治“友人”经常造访,他不断与他们进行政治交谈。没有必要重新唤起家人对这段时间的回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把《自传》继续写下去。相反,更为急迫的需要是写出关于革命及其后果的名副其实的共和派历史。为此目的,杰斐逊收集了大量能够反映1790年代党派斗争的真实历史的政府文件、信件和笔记。不管怎样,总得有人来讲述这段历史,并且要将它出版,以有所裨益于子孙后代(60)。
杰斐逊的《自传》尽量少谈他的家庭生活,以突出地强调家庭隐私对于他的自我界定的关键意义。正如蒙蒂塞洛的女主人、他女儿玛莎所经常抱怨的那样,他的私人家庭领地和公共政治世界之间的隔墙实际上是可以穿过的。某种理想化的家内生活为这个异常敏感的政治家提供了歇息和庇护的希望,他在这里能“守望那些为我劳作的人的幸福”(61)。杰斐逊在心里建造了一个想象的家,一个“宁静的”内心空间,在这里他能够摆脱公共政治事务的烦扰,这恰恰是因为他的身份,也就是他对自我的意识,是根植于他的激进的共和信念之中的,故而无可避免地是公共政治性的。起草《独立宣言》使得杰斐逊很早就攀上了一个高峰,《自传》则揭示了他奉献于革命事业的极端个人化和自我界定的一面。
正如杰斐逊对亨利·李所说的那样,《独立宣言》“意在表达美国人的思想”,从“那个时代的协调一致的看法”中汲取了“它的全部权威”(62)。可是,就在杰斐逊和他在大陆会议的同事们想象性地把他们的单独身份融入一种新的美利坚人身份对,他却成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共和派,致力于伸张他自己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位《自传》作者在将近半个世纪后回首自己当初在《独立宣言》起草中的作用时,质疑了一些签署者的诚意,同时却又坚持认为自己对共和信条是矢志不渝的。“那种认为我们在英国仍有值得保持交往的朋友的懦怯之见,仍在很多人头脑里作祟”,导致一些谨慎的大陆会议代表在审稿时删掉了杰斐逊原稿中“谴责英国人民”而可能“得罪他们”的词句。与此相应,北部和南部那些奴隶贩子和奴隶主的卑鄙的利己之心,也导致大陆会议清除了雄辩有力地谴责英王“奴役非洲土著居民”的那段文字(63)。但在审议修改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为普遍,杰斐逊在《自传》中煞费苦心地展示了这一点,他提供了全部原稿的副本,并插入了大陆会议的改动(64)。杰斐逊批驳由大陆会议实际通过的《独立宣言》,这样就把他自己与在大陆会议上作修改的人区分开来,重申了他与“人民”的同一性。《独立宣言》的文本或许受到了玷污,但杰斐逊原本要代表美国“人民”来表达的“精神”和“1776年原则”,仍然是纯洁无瑕的。
在想象中重返费城,翻出《独立宣言》起草过程中不满的旧账,这对杰斐逊有多重意义。到杰斐逊写作《自传》时,他被视为《独立宣言》的唯一作者,受到广泛赞誉,他本人也很乐于接受这一荣誉,并把它刻在墓碑上,而那些审议修改《独立宣言》的人则早已踪迹杳然。在1790年代,造反的共和党人挑战上层联邦党人的强势她位,把《独立宣言》弄成了一个神圣的文本,把它的作者弄成了一个偶像式的人物,于是造成了对《独立宣言》的最初崇拜(65)。正是由于杰斐逊如此彻底地占领了这一阵地,他才能对自己的作者身份轻描淡写,而向那些损害过其文本的谨慎而表里不一的大陆会议成员大报随时间推移而加深的宿怨,并重申他与“人民”的同一性。
《自传》会向家里的读者解释随后的党派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导致杰斐逊有若干时期不在家,而且还反复打破蒙蒂塞洛家里的宁静。改动《独立宣言》的原稿乃是“原罪”的标记,是在新国家刚建立的时刻就背离了共和主义的纯洁性。杰斐逊对共和信念的忠诚构成他关于其权利和自我意识的基础,它要求为公共福祉而做出牺牲。于是,这位自称是不得已的爱国者,便被从家里拖入公共政治世界,甚至还把公共政治世界带回家来。这些据说是彼此区分的人类事务领域却是互相渗透的,这反映出杰斐逊把自己与美国“人民”并为一体。在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史中,他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同大陆会议全体成员抗衡的个体,坚持认为自己的意图是纯洁的,并贬斥他人的意图,同时却又否认任何“原则或看法上的原创性”,把自己与美国“人民”完全等同起来(66)。因此,私人家庭领域,亦即杰斐逊进行自我塑造的领地,它的神圣性与其说是一个前提,倒不如说是一种前景,是一种对共和政治在更美好的未来所能取得的成就的憧憬。
五 民主的前景
现在看来,杰斐逊作为一个激进革命者的“证明文书”未免可疑,但他却从未怀疑过自己。教会和国家中旧体制统治的受益者不会很情愿地放弃其特权,而愚昧无知的普通民众“偶尔会……甘愿充当为他们自己打造枷锁的工具”,这是不足为奇的;贵族对支配权的渴求具有普遍性,因而是共和国的“天然之事”,这甚至也可能是实情(67)。不过,虽说革命精神有时可能会“蛰伏起来”,但自由的“人民”最终决不会忘记自己,因为它的存在有赖于对“我们政治信仰的信条”的忠诚。杰斐逊怀疑的是别人的诚意,而不是他自己的诚意。在更大的光明照耀大地之前,共和改革的方案也许会遭遇失败,伪贵族们也许会一时抓住权柄,就像他们在1790年代末上层联邦党人得势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只要美利坚人珍视对“先哲们”和“英雄们”的记忆,那么自由的圣火就将继续燃烧。
杰斐逊并未能免于绝望和抑郁的几度光顾,但他从不承认这些黑暗时刻是他自己的欠缺与弱点的表征(68)。杰斐逊把自己彻底地等同于共和革命,条件反射般地将所有偏离他对共和信条的理解的东西视为反革命。杰斐逊承认,他的主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所有私人事务中是无私、诚实而可敬的”,同时他又把汉密尔顿描述成一个危险的反共和主义者,“受到了英国样板的蛊惑而误入歧途”(69)。1792年9月,杰斐逊要华盛顿总统相信,他与财政部长之间的对抗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受到了他自己的纯洁的共和原则的激发:汉密尔顿的“体系”与杰斐逊的有所不同,它是“出自于与自由作对的原则,旨在使他所在部门的势力凌驾于立法机构成员之上,从而瓦解和推翻共和制”(70)。“贵族式的”汉密尔顿,一个反动的天才人物,正是共和派杰斐逊的反面类型。他们在华盛顿第一届政府里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冲突,这使杰斐逊更加坚信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和派。
杰斐逊的个人独立,无可避免地同美国独立的宣布和维护联系在一起。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同其他签署者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公开放弃了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效忠,自视为造反派和叛徒,同时又将自己的身份融入他所协助构想出来的“人民”的身份之中。同英国的决裂导致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殖民地臣民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新国家的自治的公民。这也是杰斐逊转变的时刻:一个革命的共和派变成了一个新人。
①第二届大陆会议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Barbara B.Oberg and J.Jefferson Looney,eds.,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Digital Edition),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http://rotunda.upress.virginia.edu/founders/TSJN-01-01-02-0176-0006,[发布日期不详]2013-01-28。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取自本人正与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合写的《最受福佑的家长》(The Most Blessed of the Patriarchs)一书。另参见拙文“托马斯·杰斐逊与美国民主”(“Thomas Jeffers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弗朗西斯·D.科利亚诺编:《杰斐逊研究手册》(Francis D.Cogliano,ed.,A Companion to Thomas Jefferson),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威利—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12年版,第397~418页。我和戈登—里德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讨论杰斐逊旅法岁月对其民主思想发展的影响,不过本文并不涉及这个主题。
②美国“例外论”可以追溯到杰斐逊关于美国“人民”的说法[参见布赖恩·斯蒂尔:“发明‘非美’”(Brian Steele,“Inventing Un-America”),《美国研究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即将出版);又见彼得·S.奥努夫:“美国例外论与国家认同”(Peter S.Onuf,“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美国政治思想》(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2012年第1期,第77~100页]。
③布赖恩·斯蒂尔:《托马斯·杰斐逊与美利坚国家身份》(Brian Steele,Thomas Jefferson and American Nationhood),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3~90页。
④我的解释得益于杰伊·弗利格尔曼(Jay Fliegelman)的杰作《宣布独立:杰斐逊、自然的语言与表现的文化》[(Declaring Independence:Jefferson,Natural Language,and the Culture of Performance),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另参见本人现在看来有些过时的评论文章“学者眼中的杰斐逊”(“The Scholars' Jefferson”),《威廉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第50期(1993年),第671~699页。
⑥“葛底斯堡演说(1863年11月19日的定稿)”[“Gettysburg Address(Final Text),Nov.19,1863”],罗伊·P.巴斯勒编:《林肯选集》(Roy P.Basler,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9卷本,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1953-1955年版。http://quod.lib.umich.edu/1/lincoln/。
⑥“杰斐逊1825年5月8日致亨利·李”(“TJ to Henry Lee,May 8,1825”),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Merrill D.Peterson,ed.,Thomas Jefferson Writings),纽约:美国文库1984年版,第1501页。
⑦《独立宣言》,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⑧波林·梅尔:《美利坚圣经:〈独立宣言〉的形成》(Pauline Maier,American Scripture:Making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纽约1997年版。关于杰斐逊的自谦,可参见杰伊·弗利格尔曼:《宣布独立:杰斐逊、自然的语言与表现的文化》,第72~73页。
⑨“杰斐逊1826年6月24日致罗杰·韦特曼”(“TJ to Roger Weightman,June 24,1826”),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517页。
⑩“杰斐逊1801年3月4日第一次就职演说”(“TJ,First Inaugural Address,March 4,1801”),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11)“杰斐逊1801年3月21日致约瑟夫·普里斯特利”(“TJ to Joseph Priestley,March 21,1801”),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12)“杰斐逊1821年9月24日致约翰·亚当斯”(“TJ to John Adams,Sept.24,1821”),安德鲁·A.利普斯科姆、威廉·埃勒里·伯格编:《杰斐逊文集》(Andrew A.Lipscomb and William Ellery Bergh,eds.,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20卷本,华盛顿1901-1904年版,第15卷,第336页。
(1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版。杰斐逊在总统任职后期写道:“一个国家的最大福佑莫过于始终默默地享有幸福,而不给历史留下值得一书的东西。这便是我对自己国家的最大愿望,在迄今为止的过去20年里,我们幸运地享有这种状况,而欧洲却经常处于火山爆发般的震荡之中。”[“杰斐逊1807年3月29日致迪奥达蒂伯爵先生”(“TJ to Monsieur Le Comte Diodati,March 29,1807”),安德鲁·A.利普斯科姆、威廉·埃勒里·伯格编:《杰斐逊文集》第11卷,第181~182页]
(14)“宪法与联邦片论”[“Fragment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on,(c.January 1861)],罗伊·P.巴斯勒编:《林肯选集》。http://quod.lib.umich.edu/1/lincoln/。
(15)罗纳德·L.哈岑比勒:《“我为我的乡国而忧”:托马斯·杰斐逊与弗吉尼亚乡绅》(Ronald L.Hatzenbuehler,“I Tremble for My Country”: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Virginia Gentry),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2006年版。
(16)托马斯·杰斐逊:《自传》[TJ,Autobiography(1821)],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44页。
(17)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札记》(TJ,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威廉·佩登编,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希尔1954年版。
(18)“弗吉尼亚议会1781年12月12日决议”(“Virginia General Assembly,Resolution of Dec.12,1781”)。转引自1796年弗吉尼亚总统选举人竞选的相关文件[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19)关于《弗吉尼亚札记》的出版史,参见威廉·佩登编:《弗吉尼亚札记》,“导言”,第ⅹⅰ~ⅹⅹⅵ页;另见杜马·马隆:《杰斐逊和他的时代》(Dumas Malone,Jefferson and His Time),6卷本之第2卷《杰斐逊与人权》(Jefferson and the Rights of Man),波士顿1948-1981年版,第93~106页。
(20)(21)(22)(23)(24)(25)(27)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札记》,第4,64,84~87,138,161,138,126、128页。
(26)关于这一主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杰里米·D.贝利:《托马斯·杰斐逊与行政权》(Jeremy D.Bailey,Thomas Jefferson and Executive Power),坎布里奇2007年版。
(28)(29)(30)(32)(33)托马斯·杰斐逊:《弗吉尼亚札记》,第120、176、163、162、165页。
(31)孟德斯鸠(查尔斯·塞孔达):《论法的精神》[Montesquieu(Charles Secondat),The Spirit of the Laws(1743)],安妮·科勒等翻译整理,剑桥1989年版。关于国民性的讨论,参见尼古拉斯·奥努夫、彼得·奥努夫:《国家、市场和战争:现代史与美国内战》(Nicholas Onuf and Peter Onuf,Nations,Markets,and War:Modern Histor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8页。
(34)“杰斐逊1814年8月25日致爱德华·科尔斯”(“TJ to Edward Coles,Aug.25,1814”),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344页。
(35)“杰斐逊1789年9月6日致詹姆斯·麦迪逊”(TJ to James Madison,Sept.6,1789),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关于这一著名信件的权威性研究,参见赫伯特·E.斯隆:《原则与利益:托马斯·杰斐逊与债务问题》(Herbert E.Sloan,Principle and Interest: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Deb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6)关于革命时期弗吉尼亚乡绅阶层的生动描述,参见查尔斯·罗伊斯特:《迪斯默尔沼泽公司的辉煌历史:乔治·华盛顿时代的故事》(Charles Royster,The Fabulous History of the Dismal Swamp Company:A Story of George Washington’s Times),纽约: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1999年版。
(37)我此处的解释大量借鉴了R.S.泰勒·斯托默:“宪政理智、革命情感:1701-1776年英属弗吉尼亚形成与解体中的政治文化”(R.S.Taylor Stoermer,“Constitutional Sense,Revolutionary Sensibility: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Virginia,1707-1776”)(博士学位论文),弗吉尼亚大学2010年。
(38)《独立宣言》,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39)参见赫伯特·E.斯隆:《原则与利益:托马斯·杰斐逊与债务问题》。
(40)“杰斐逊1787年11月13日致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TJ to William Stephens Smith,Nov.13,1787”),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41)“杰斐逊1793年1月3日致威廉·肖特”(“TJ to William Short,Jan.3,1793”),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42)“杰斐逊1816年1月11日致约翰·亚当斯”(“TJ to John Adams,Jan.11,1816”),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376页。
(43)“杰斐逊1816年2月2日致约瑟夫·C.卡贝尔”(“TJ to Joseph C.Cabell,Feb.2,1816”),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380页。
(44)《独立宣言》,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45)“杰斐逊1813年10月28日致约翰·亚当斯”(“TJ to John Adams,Monticello,Oct.28,1813”),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308页。
(46)关于英国的“影响”和杰斐逊仇英心理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彼得·S.奥努夫:《杰斐逊的帝国:关于美利坚国家身份的语言》(PeterS.Onuf,Jefferson's Empire:The Language of American Nationhood),夏洛茨维尔2000年版,第80~108页。
(47)《独立宣言》,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48)关于这一主题的最佳论述,见弗朗西斯·D.科利亚诺:《托马斯·杰斐逊:声誉与遗产》(Francis D.Cogliano,Thomas Jefferson:Reputation and Legacy),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见罗伯特·M.S.麦克唐纳:“杰斐逊与美国:形象形成中的若干片断”(Robert M.S.McDonald,“Jefferson & America:Episodes in Image Formation”)(博士学位论文),北卡罗来纳大学1998年。
(49)1826年自撰碑文(Epitaph),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706页。
(50)“杰斐逊1821年1月6日至7月29日起草的自传”(TJ's Autobiography,drafted Jan.6~July 29,1821),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101页。
(51)托马斯·杰斐逊:《自传》,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3~4页。关于杰斐逊早年生活的最佳论述,参见杜马·马隆:《杰斐逊和他的时代》,6卷本之第1卷《弗吉尼亚人杰斐逊》(Jefferson the Virginian)。
(52)托马斯·杰斐逊:《自传》,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5页。
(53)正如肯尼思·A.洛克里奇在他的《论家长制狂暴的来源》(Kenneth A.Lockridge,On the Sources of Patriarchal Rage,纽约1992年版)中所坚持认为的那样。
(54)杰伊·弗利格尔曼:《浪子与朝圣者:反对家长制权威的美国革命》(Jay Fliegelman,Prodigals and Pilgrims: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gainst Patriarchal Authority),坎布里奇1982年版。
(55)“杰斐逊1793年11月27日致安杰莉卡·斯凯勒·丘奇”(“TJ to Angehca Schuyler Church,Nov.27,1793”),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杰斐逊后来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儿孙中间的落伍的老家长,耕耘着自己的土地”[“杰斐逊1795年11月30日致爱德华·拉特利奇”(“TJ to Edward Rutledge,Nov.30,1795”),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56)“1800年2月27日杰斐逊致奥古斯特·贝林”(“TJ to Auguste Belin,Feb.27,1800”);“杰斐逊1801年3月29日致塞缪尔·亚当斯”(“TJ to Samuel Adams,March 29,1801”),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57)托马斯·杰斐逊:《自传》,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46页。
(58)关于杰斐逊婚姻生活的最佳论述,见安德鲁·伯斯坦:《杰斐逊的内心世界:忧伤的乐观主义者画像》(Andrew Burstein,The Inner Jefferson:Portrait of a Grieving Optimist),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9)“杰斐逊1792年3月22日致玛莎·杰斐逊·伦道夫”(“TJ to Martha Jefferson Randolph,March 22,1792”),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此处的分析得益于简·刘易斯:“家庭社会的赐福:托马斯·杰斐逊的家庭与美国政治的转变”(Jan Lewis,“The Blessings of Domestic Society:Thomas Jefferson's Famil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彼得·S.奥努夫编:《杰斐逊的遗产》(Peter S.Onuf,ed.,Jeffersonian Legacies),夏洛茨维尔1993年版,第109~146页;另见比利·韦森:《玛莎·杰斐逊·伦道夫:塑造一个共和派女儿和种植园女主人》(Billy Wayson,Martha Jefferson Randolph:Fashioning a Republican Daughter and Plantation Mistress),夏洛茨维尔,即将出版。
(60)弗朗西斯·D.科利亚诺:《托马斯·杰斐逊:名誉与遗产》。
(61)“杰斐逊1793年11月27日致安杰莉卡·斯凯勒·丘奇”(“TJ to Angelica Schuyler Church,Nov.27,1793”),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62)“杰斐逊1825年5月8日致李”(“TJ to Lee,May 8,1825”),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501页。
(63)托马斯·杰斐逊:《自传》,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8页。进一步的讨论见彼得·S.奥努夫:《杰斐逊的帝国:关于美利坚国家身份的语言》,第137~142页。
(64)托马斯·杰斐逊:《自传》,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9~24页。按时间顺序(1776年6月11日至7月4日)排列的《独立宣言》不同草稿的权威版本,见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研究《独立宣言》起草的著作很多,重点参见罗伯特·帕金森:《人民的敌人:新美利坚国家的革命战争与种族》(Robert Parkinson,Enemies of the People: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Race in the New American Nation),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希尔,即将出版;杰伊·弗利格尔曼:《宣布独立》;波琳·梅尔:《美利坚圣经:〈独立宣言〉的形成》。
(65)罗伯特·M S.麦克唐纳:“杰斐逊与美国:形象形成中的若干片断”。
(66)“杰斐逊1825年5月8日致亨利·李”(“TJ to Henry Lee,May 8,1825”),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1501页。
(67)“杰斐逊1799年3月12日致托马斯·洛马克斯”(“TJ to Thomas Lomax,March 12,1799”),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另参见“杰斐逊1813年6月27日致约翰·亚当斯”(“TJ to John Adams,June 27,1813”),安德鲁·A.利普斯科姆、威廉·埃勒里·伯格编:《杰斐逊文集》第15卷,第279~280页,其中写道:“人有不同的观点,并且由于这些不同的观点而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在社会最初起源时便是如此,在允许人们自由思考和自由言说的地方的一切政府里,也是如此。目前使合众国激荡不安的政治党派,在各个时代都曾存在过……事实上,辉格派和托利派的说法,不仅属于文明史,也属于自然史。”
(68)毛里齐奥·瓦尔萨尼亚:“我们最初的野蛮主义’:托马斯·杰斐逊道德经验中的人对自然”(Maurizio Valsania,“‘Our Original Barbarism’:Man vs.Nature in Thomas Jefferson's Moral Experience”),《思想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65期(2004年),第627~645页;瓦尔萨尼亚:《乐观主义的限度:托马斯·杰斐逊的双重启蒙》(Valsania,The Limits of Optimism:Thomas Jefferson's Dualistic Enlightenment),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9)“1818年2月4日所编‘言论集’”(“The Anas,Feb.4,1818”),梅里尔·D.彼得森编:《杰斐逊作品集》,第671页。
(70)“杰斐逊1792年9月6日致乔治·华盛顿”(“TJ to George Washington,Sept.6,1792”),芭芭拉·B.奥伯格、J.杰斐逊·卢尼编:《杰斐逊作品集》(电子版)。
标签:杰斐逊论文; 独立宣言论文; 弗吉尼亚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美国史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托马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