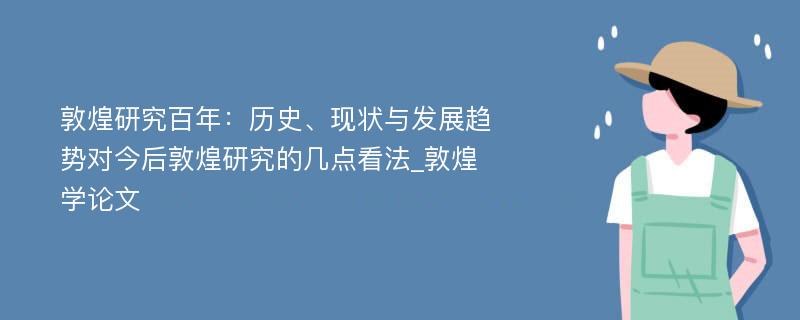
敦煌学百年: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2.对未来我国敦煌研究的一些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发展趋势论文,现状论文,看法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缘起
南京师范大学刘进宝教授是个有心人,他约集了一批我国在敦煌学研究上颇有造诣的学者搞了一个笔谈敦煌学,承蒙不弃,笔者也在刘教授罗网中,且多次催稿,辞不获己,只得勉强应命,却十分为难,若仅写笔者熟悉的“书仪研究”,恐失之过窄;若写国际敦煌学如何发展,又不是愚钝如我所能承担的;思之再三,只好就本人所知、所做、所想的一些事情和问题,写出一些真实想法,且不去管对错与否,只管真实就好。一是践刘教授之约,二是供同道与读者参阅。
在同行中,我戏称自己是“三无”人员,即学校内一无对口专业,二无学生(研究生),三无专题研究经费,乃敦煌学界的一名散兵游勇而已。但同时,我要感谢上苍给了我太多的机缘,使我至今钟情于敦煌研究而痴心不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被王永兴、张广达先生领进了学术之门,毕业后,又经宁可、沙知先生及邓文宽学长之荐,在先师周一良先生门下问学十七载,其中,80年代末,一良师去美国探亲,我又得经常向周绍良师请教,1998年底至1999年初在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处当了三个月学生,而从1985年开始,参与《敦煌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得以向季羡林先生、唐长孺先生、段文杰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及陈国灿、樊锦诗、姜伯勤、李永宁、李正宇、施萍婷、朱雷等诸位先进求教,从这些师长那里,我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也逐步进入了“敦煌学”的殿堂。在中国敦煌学的圈子里,邓文宽、方广錩、郝春文、黄征、荣新江、王素、张涌泉、郑炳林等又成为我在学术上的畏友和诤友,并从与他们的交往和阅读他们的著作中获益良多,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中,你不好好干也难。因为你不努力去做,就无面目去见老师,更无法与朋友们交流,正是这种学术上的因缘,才使我这名游骑有勇气继续在敦煌研究的路上走下去。
以上两段多余的话似乎与“研究”二字无关,但从我国敦煌研究的历史上看却别有意味。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先驱者们,正是凭着一种对学术的追求,克服重重困难,为我国的敦煌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50年代中,向达、王重民、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王庆菽等六教授所著《敦煌变文集》刊出,这是我国敦煌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正如向达先生在此书“引言”所说:“我们六个人都是用业余和会后的时间从事于这一工作的。有的人往往是午夜以后,还在那里丹黄杂下,不以为苦。”检阅一下目前的敦煌学学术史可以发现,1979年以前我国的敦煌研究多处于这种“业余”的情景(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和临摹除外)。
二、过去与现在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使我国的敦煌研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内地的敦煌学者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果,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专职研究人员队伍壮大。
二十五年前,敦煌文物研究所是大陆地区唯一的专职研究和保护敦煌的机构,目前,它已扩展成研究院,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敦煌石窟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实体,人员达数百人。除敦煌研究院之外,吐鲁番也成立了吐鲁番研究院,已形成规模。兰州大学成立了敦煌学研究所,并成为教育部文科研究基地(与敦煌研究院合作),目前已培养出数十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都有专门的敦煌学研究机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也以敦煌文献的研究整理为主要方向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都招收以敦煌研究为主的硕士、博士生。中国社科院有跨所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承担了院级重大课题。南京师范大学也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招收以敦煌学研究生为主的硕士、博士生。这里仅举出了部分机构和学校,即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内地拥有一支相当数量的敦煌研究专业队伍。
除研究机构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后,在其资助下成立的三个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和兰州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得到健康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专门机构的成立,为敦煌学的发展从人员、设备、资料、经费上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敦煌学刊物和著作出版相对顺利。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著作的出版一时称为“老大难问题”。只要翻翻那些年出版的敦煌学专著的“前言”或“后记”即可,无须繁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敦煌学专著的出版相对来说顺利多了,仅以笔者有限的耳闻目睹来说,英藏敦煌文献除四川人民出版社已印出的汉文非佛教之部外,其余佛经部分的出版已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法藏、俄藏、北大藏、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博物馆藏等敦煌文献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出,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在出版敦煌古藏文文献,浙江藏、甘肃藏敦煌文献也已刊出,可以说,除了数目不大的散藏外,大宗的敦煌文献(尤其是汉文部分)基本出齐,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相对而言,专业研究的敦煌学书籍出版也渐趋顺利,如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1种13册);甘肃教育出版社的《敦煌学研究丛书》(12种)及《走近敦煌丛书》;民族出版社的《敦煌学博士文库》、《敦煌学研究文库》,甘肃民族出版社的《敦煌研究院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等,这里仅举其规模较大者,单本和多本的敦煌学著作的刊布也较20世纪80年代顺畅了许多。就目前的出版大势看,只要有好的书稿,出版已不是难事,这对于敦煌研究的发展将非常有利。
第三,敦煌研究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
我们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敦煌文献的刊布也已取得重大进展,几种专业刊物(《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敦煌学》(台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人员、资料、阵地均已具备,敦煌研究在此基础上正向纵深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90年代末完成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和《敦煌学大辞典》,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直接领导和组织的两项“工程”,也可以看做是20世纪中国敦煌研究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敦煌研究目前发展的状况如何呢?笔者仅举三例以说明之。
例一,郝春文教授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编)已经公开出版五卷,这部著作将英藏敦煌文献中非佛经之部逐件释录,目的是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校订成为像《二十四史》标点本一样便于使用的可信从文本,虽然工作量很大,全部完成尚待时日,但这项工作正在扎扎实实进行,书正在一卷卷陆续刊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例二,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领导下的《敦煌文献合集》,拟将敦煌汉文文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书成有日。张涌泉与郝春文的工作虽然貌似不同,但都是耗时费力为敦煌研究打基础的工作。
例三,笔者在敦煌研究中,二十多年来集中于敦煌本书仪研究,基本上将敦煌本书仪的大部分做了分类录校整理,也写了一批研究论文,近几年来,吴丽娱据此进行的唐代礼制研究、史睿进行的礼制研究、张小艳进行的书仪词语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将敦煌本书仪研究引向深入。
当然,中国敦煌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例证还很多,如林悟殊先生对三夷教的研究;如王卡、王承文、刘屹、万屹等对敦煌道教的研究;如许建平对敦煌经籍的研究;如冯培红对归义军官制的研究;如陈明对医药文献的研究;如余欣对“神道”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总体还是个案上,我国目前的敦煌研究正在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中国官方语言中有两句话,叫:“成绩说够,问题说透”,要将“成绩说够”,非这篇小文所能承载,只是点到为止;而“问题说透”,更非此篇小文作者所能胜任的,所谓“问题”,也仅是对我国敦煌研究发展的点滴想法而已,遑论“说透”。
三、未来
2006年秋,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转型期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何谓“转型”?笔者理解,就是如何把敦煌研究推向前进,使研究更加深入,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要“转型”,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重视基础工作。
如本文说“成绩”部分所言,敦煌汉文资料的大部分已影印出版,但“胡语”部分则刚刚开始,仍需努力。张涌泉、郝春文的工作正在进行中,盼其早日完成。更重要的一点是,多年来,学界盼望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早日面世,考古报告属于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学深入的基础资料,因为没有坚实的一手资料,许多研究工作难以深入,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从2002年起,即注意到莫高窟96窟、130窟的大像及榆林窟第6窟大像,想做一些相关研究,但时至今日,连一份有关大像各部分准确尺寸的资料都难以获得,使研究很难深入。
第二,重视佛教文献的研究。
敦煌藏经洞中,90%以上为佛教典籍,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薄弱。其实,自清末民初起,我国的著名学者已将佛教与佛经纳入了研究视野。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先生更是在佛教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继承好这一学术传统。中国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安公(道安)说:“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武则天时,薛怀义等进《大云经疏》,九人赐“国公”,全国各地皆建大云寺,神会助平安史之乱,禅宗南能一系则全国风行,政治与宗教关系可见一斑。另外,宗教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普通民众生活密不可分,众多敦煌文献即是明证。
敦煌佛教典籍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除入藏的经、律、论外,疑伪经占相当数量,这些“中国化”的疑伪经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至于中国僧人所做“论”、“疏”、“赞”、“义”等等则更具中国特色,深入研究这些文献,无疑具有广阔的前景。
笔者对佛教、佛学基本上是门外汉,只是在学术研究上偶有涉及,不敢深入。前几年,我发现敦煌写经中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中的宫廷写七卷本《妙法莲花经》和一卷本《金刚经》,乃是武则天为其逝去的父母发愿所写,并复原了置于经前的两篇以武则天名义撰写的发愿文字。宫廷写经直接颁到敦煌,全国其余州县亦当如此,这该是多么大的影响!更深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所出佛经,可以看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什么时段以什么经典为主,什么时段官方提倡的是何种经典,这些经典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生活有何种联系等等,深究下去,一定会对佛教与中国中古社会的关系有深入的了解,一定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中古社会的变动。其实,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活动》开了一个好的先例,沿着此路数走下去,将敦煌佛教典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做通盘思考,必定会有突破。
第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敦煌学”一词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此不赘。但众多学者所认同的是,敦煌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等众多学科的资料。敦煌研究,本来就应该把敦煌石窟、敦煌所出土文献及敦煌史地综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可惜近代的学科划分过细,往往使研究者很难做跨多个学科的研究。笔者以为,解决的方法大约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学科把基础研究做好,如石窟要有考古报告,壁画要有线描图,文献要有准确的释读等等;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联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还是以笔者个人研究的体会为例,如敦煌写本中,《老子》或《道德经》及其注疏本很多,若单从宗教观点看,说明敦煌陷蕃前,也曾流行道教,换一个角度,唐代前期,《老子》曾经是科举考试中必考科目,他就成了与儒家经典相同的经书,成为读书人考试的必读书。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老子》及其注疏在藏经洞中存留较多的原因。究竟何者为主因,则要进一步探讨。再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武则天利用宗教、尤其是佛教为其当皇帝制造“政治气氛”,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大云经疏》、《宝雨经》、《华严经》的敦煌写本与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里《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宝雨经变》、《华严经变》的壁画有何联系?《大云经疏》、《宝雨经》、《华严经》的敦煌写本与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里的塑像间有何关系?与96窟、130窟弥勒大像及榆林窟6窟大像有何关系?再扩大而言,与现存我国西北的石刻与泥塑弥勒大像有何联系?深究下去,将历史、考古、艺术、宗教等做一综合的思考,将有新发现,这样做不是很有趣味吗?
第四,重视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敦煌自古即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重中之重,自藏经洞发现之后,文物外流,敦煌研究开始即具有国际性特色。时至今日,敦煌在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我国第一批人类文化物质遗产,敦煌研究更具有鲜明的国际特色。西起欧美,东至日本,代不乏人,要推动新时期敦煌学的深入,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大陆地区召开的多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欧美、日本及我国港、台学者参加,而在英、法、美、俄、日、加等国及港、台等地区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都有大陆学者莅临。近年来,中英、中法、中俄合作出版敦煌文献,中英合作的“IDP”(国际敦煌学项目)已经运作,2003年春,更是成立由中国(含台湾)、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组成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委员会主要是协调各国敦煌学者的学术活动。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敦煌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以促进这个学科的长盛不衰。
其实,谈敦煌学的过去与未来,是一篇内容十分丰富的大文章,本文的主旨是立足于现在,即“路在脚下”,又要放眼未来,即“路在前方”,脚踏实地,一步步将我国的敦煌学推向更高的阶段。
(附记:因为是“一些想法”,本文中提到的一些机构、一些人、一些著作、一些研究,可能有重大遗漏,排序也可能不尽妥当,选择更难说妥帖,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绝无孰轻孰重、你先我后之意,至于“想法”,也只是一人之言,聊备一说而已,望同道及读者谅之。)
标签:敦煌学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敦煌研究院论文; 张涌泉论文; 吐鲁番论文; 佛教论文; 敦煌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