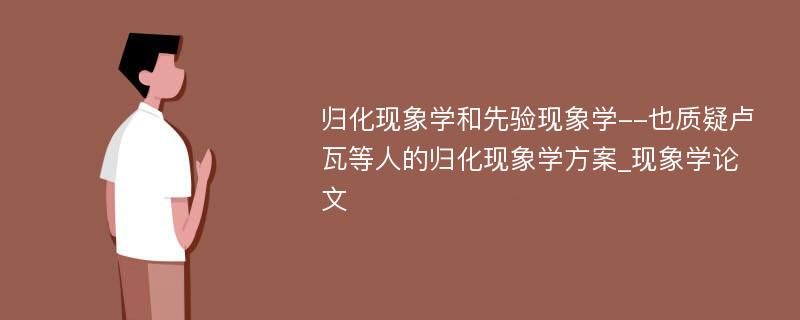
自然化现象学与先验现象学——兼质疑鲁瓦等人自然化现象学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自然论文,等人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4)05-0026-06 近年来,在关于心灵和意识的研究中,将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及心灵哲学)结合起来是一种明显趋势,出现了例如“自然化现象学”的倾向。一些自然化现象学的提倡者要求放弃胡塞尔现象学的反自然主义,从而将现象学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然而在胡塞尔现象学明确反自然主义的先验哲学背景下,现象学的自然化如何可能?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本文将对鲁瓦(Jean-Michel Roy)等人倡导自然化现象学的动机和理论考虑加以阐述,在此基础上,论证关于现象学自然化的考虑并未正确面对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观点,尤其是未考虑到胡塞尔的先验哲学动机,进而指出晚期胡塞尔对先验现象学(特别是先验主体性)的思考有助于缓和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自然化现象学的宣言 在《自然化现象学:当代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中的问题》的导言中,鲁瓦等四位编者明确地提出了自然化现象学的“宣言”。他们所倡导的自然化现象学与当代认识科学的困境有关。作为一种崭新的交叉研究,当代认知科学在心灵与认知研究方面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忽视了意识的体验维度,无法很好地解释现象性或显现问题,自身也遭遇了“解释鸿沟”的困境。所谓的“解释鸿沟”指的是,第三人称的经验科学所把握的大脑神经生理过程与第一人称层面的意识体验之间的断裂。“大脑的神经生理过程如何能产生主观的意识体验”的问题困扰着认知科学,使其难以提供一个既能解释意识的主观体验,又能解释其神经活动的研究框架。 在鲁瓦等人看来,胡塞尔现象学对意识体验、现象性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分析和描述,它能提供外在观察者视角所无法通达的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认知过程与现象显现的关系,因而能够为解决“解释鸿沟”问题提供帮助。但利用现象学填补“解释鸿沟”的前提是将其“自然化”,也就是把胡塞尔现象学“整合到一个解释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可接受的属性都与自然科学所承认的那些属性是连续的”[1](PP1-2)。鲁瓦等人显然不是为了重新解读现象学,也不是单纯地强调现象学的重要性和有用性。相反,他们的自然化现象学是以自然主义为导向,企图将现象学对意识结构描述的丰富成果整合到认知科学中,从而为心灵和意识提供一个自然主义的科学说明。 在强调现象学的有用性的同时,鲁瓦等人也意识到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立场以及现象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张力,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构成问题。在他们看来,胡塞尔虽有诸多反自然主义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均基于他对科学的特定理解。胡塞尔将现象学规定为描述本质学,它试图把握体验或意识流的模糊的、非精确的形态学本质,因而在根本上不同于那种试图把握精确的、理想的本质的公理本质学,如数学和几何学。同时,现象学所要求的“严格性”和“描述性”与数学-自然科学所追求的“精确性”和“理想化”也是截然不同的。[1](P31-32)由于其公理化性质,物理学无法正确处理物理实在与现象特性之间的关系;而对意识体验之形态学本质进行数学的、几何学的描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认为在胡塞尔看来,现象性的物理学和几何学的描述本质学都不可能成立。[1](PP40-41)鲁瓦等人认为,胡塞尔正是在反对将现象学描述成果形式化为数学语言的科学立场上来反对自然主义的。 然而根据鲁瓦等人的自然化宣言,将现象学数学化恰恰是自然化现象学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步骤。要将胡塞尔现象学整合到自然科学的框架之下,就必须克服数学与现象学之间的严格对立,否则,“自然化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一个绝望的研究项目”[1](p42)。在他们看来,这个对立源于胡塞尔的误解,即他将数学-物理学在特定时代所具有的偶然局限性误解为无法克服的绝对局限性。科学的新进展已使胡塞尔时代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进而使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显得过时和无效。据此,鲁瓦等人认为,将胡塞尔现象学与其反自然主义分割是可能的,将现象学描述成果转化为形式的数学语言的自然化现象学也是可能的。 在范围上,鲁瓦等人更关注现象学对意识体验描述成果在认知科学中的作用,他们所企图自然化的现象学是本质描述意义上的现象学。但现象学不只是本质描述的现象学,它还意味着具有认识论关怀的先验现象学,因而德·普雷斯特(Helena De Preester)认为还应该将先验构造概念也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这种方案显然更为激进,不仅要求放弃反自然主义立场,而且要将反自然主义与先验主义立场完全分开,并发展一种能与自然主义兼容的无主体的先验主义。 鲁瓦等人的构想为我们研究认知与心灵提供了新方向,然而这种激进的自然化方案却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及其先验哲学动机。胡塞尔不仅仅出于科学动机而反对自然主义,他的反自然主义“主要是基于一些哲学理由,确切地说是基于一些先验哲学的理由”[2](P335)。对于自然化现象学来说,真正的挑战和困难并不在于能否将现象学数学化,而在于如何化解现象学的先验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的分歧。由于将焦点置于克服现象学与数学的冲突,鲁瓦等人不仅忽视了现象学的先验维度,也错过了考察先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关系这一自然化现象学的基础问题。在此意义上,他们的方案并没有真正有效地将胡塞尔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结合起来,而只是企图“用一个说明性的解释来取代现象学所提供的先验澄清”[3](P14)。这种激进的路径可视为奎因式的自然化认知论的延续,最终可能使现象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甚至为其“吞没”。 二、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 胡塞尔毕生都在与自然主义做斗争,他的反自然主义贯彻其整个现象学生涯。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指出,自然主义倾向于将一切存在都视为在时空中遵循因果规律的物理自然,主张将一切存在都还原为自然物或物理物。对于自然主义者来说,意识等心理现象只不过是随附于物理物的伴随物或副现象。[4](p8)在方法论上,自然主义还试图将自然科学当作一切认识的原则和方法,并主张哲学应以自然主义的实证科学为基础。这种自然主义其实就是科学主义,它认为一切事物都能被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科学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这样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哲学方法以及哲学自身的合法性。胡塞尔认为哲学不应该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它应该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和立场。当然,胡塞尔并不反对自然科学本身及其巨大成就,他只是试图指明自然科学的界限,反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普遍化,并为哲学进行辩护和“正名”。 对于自然主义的特征,胡塞尔指出,自然主义“一方面将意识自然化,包括将所有意向-内在的意识被给予性自然化;另一方面是将观念自然化,并因此而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4](PP8-9)。对于自然主义将观念自然化的企图,胡塞尔延续其《逻辑研究》中反心理主义的立场,明确反对将观念还原为心理或物理的实体或过程,反对将逻辑规则视为心理事实或偶然的规则,并指出将观念自然化的企图是自身反驳的,它最终将导致怀疑论。 同时,胡塞尔也反对意识的自然化以及意识的自然主义解释,并企图在自然主义之外提供一套意识现象学的方案。在他看来,意识的自然主义解释歪曲了意识的性质。具体来说,自然主义的经验科学(如心理学)倾向于将意识当作世间的自然事实(如自然实体或对象),并像解释自然物那样诉诸因果关系和经验事实来解释意识。然而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当主体具有某种意识时必然具有某种感受,比如手被烫到时或看到红玫瑰时的感受。尽管经验科学有可能揭示意识(如知觉、回忆等)的神经相关物,为意识活动的神经生理过程提供因果解释,但它却无法满意地解释意识的第一人称的主观感受性,比如它无法从外在观察者视角来解释主体看到晚霞的感受如何。更关键的是,自然主义没有看到意识的先验维度。[3](P5)胡塞尔认为,意识是一切对象得于显现的先天条件和最终“视域”,只有在意识活动中,对象才能显现或被给予,比如我眼前的红苹果是在感知活动中被给予的,“半人半马”是在想象活动中被给予的。因此我们不能脱离意识活动谈论意识对象,更不能简单地将意识视为世界中的普通物理对象。正如莫兰(Dermot Moran)所言,“意识不应该被自然主义地视为世界的一部分,因为意识首先是为什么有世界呈现给我们的原因。对于胡塞尔来说,意识并非在本体论意义上创造了世界……而是说,世界通过意识而才得以开放,才有具意义或者才得到揭示。离开意识就无法想象世界。将意识视为世界的一部分,将意识物化,忽略了意识的基本的、决定性作用”[5](P144)。在此意义上,胡塞尔要求与意识的自然主义解释区别开来,从对象回到对象被给予的方式,即回到意识体验本身,对意识之结构做出描述。 为了更彻底地克服自然主义(包括心理主义)和意识的自然化,胡塞尔还揭示和批判了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及其形而上学实在论设定。他指出,自然态度是未反思的朴素态度,它自身觉察不到自身之为自然态度。这种“前理论”的态度倾向于将一切事物都视为已给定的、实在的东西。自然态度以朴素的态度对待世界,而自然主义则从数学-自然科学视角看待世界,它倾向于将世界“绝对化”为理想的物理世界。但两者都对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做出了承诺,相对于自然主义来说,自然态度的承诺更一般、更原初。胡塞尔还将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联系了起来,认为两者是欧洲危机的根源。他指出,客观主义将世界预设为完全独立于主体的、等着被发现的外在客观领域,将认识当作获得关于世界的客观有效真理的过程。对于胡塞尔来说,自然态度、自然主义以及客观主义面临的共同问题便是其形而上学实在论承诺,它们都在直接经验之外未加反思地将世界的存在设定为理所应当的,“朴素”地预设了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实在。 针对自然主义的实在论立场,胡塞尔实行了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还原是一种态度的彻底反转,它要求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悬搁”或“中止”自然主义的实在论立场,以消除其对意识研究的干扰。但这并不是对实在的排除,而只是对实在的态度的转变,即获得一种“非自然”的先验态度。现象学还原促使我们“发现”了被自然主义以及客观主义所“遮蔽”的先验主体性,使我们“获得”了先验主体的纯粹意识“领域”,从而使本质描述的现象学转向为先验现象学。伴随着现象学还原实行,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更加彻底了,也更明显地表现出了先验的特点。 基于上述考察,笔者有理由认为鲁瓦等人将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等同于反数学形式化是对胡塞尔的误解。虽然胡塞尔强调现象学与数学-自然科学的差异,也反对将意识体验的结构进行数学形式化,但他的反自然主义远不止于此,还包括反对科学主义、反对意识的自然化以及揭示和批判形而上学实在论等方面内容。另外,那种割裂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与其先验态度内在关联的观点也是对现象学还原的误解,事实上正是凭借这一方法操作,胡塞尔才实现了先验现象学的“转向”。 三、先验现象学及其启示 胡塞尔现象学的任务不仅是对意识结构进行本质描述,更是一种先验哲学的事业。对于现象学的自然化来说,我们无法回避现象学的先验维度及其与自然主义的分歧。但需要注意的是,晚期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并没有完全固守先验与经验的严格界限,而是企图弱化两者间的分歧,这为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留下了可能性。 作为一种先验哲学,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追问可能经验和认识的可能性条件,并将一切认识回溯到最后源泉,即“我自己”或者“主体性”。胡塞尔反复强调,先验主体性是客观性和世界之可能性的先验条件。这就是说,一切存在都是先验主体赋予行为意义的,客观世界之所以能被理解,世界之所以有意义,都在于先验主体性。而且先验主体性总是构造着的主体性,据此,胡塞尔赋予了主体性绝对的在先性,认为一切存在都依赖于主体性。我们可以想象无世界的主体,却无法想象无主体的世界。就算世界消失了,主体也不会消失,因而没有主体就没有世界。应当注意,胡塞尔所谓的“依赖”不是指世界的实存依赖于主体的实存,也不表明主体性是世界的原因和根源,而是将主体性视为世界显现的必要条件;而他反复强调的“构造”也不是指“创造”或“产生”出对象,而是使对象如其所是地呈现或揭示出来,使其有意义(即意义赋予)的过程。正是在承诺先验主体性的绝对在先性的基础上,胡塞尔才反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那种脱离先验主体以及先验主体和世界的意向关联性的(即实在论的)世界解释。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虽然有很强的“自我学”色彩,但这并非其现象学的全貌。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他对先验现象学的理解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如先验现象学范围的扩大。他“不仅谈论先验主体性和先验交互主体性,还谈论先验经验(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先验生活、先验事实、先验过去和将来、先验合理性、甚至先验非理性等等。还存在着关于人格、儿童、成年人甚至是精神错乱之人以及其他超出‘常规性’界限的东西的先验解释”[6](P201)。这些变化都反映在其对先验主体性这一核心概念理解的变化上。 在广为人知的《观念Ⅰ》中,胡塞尔开始注意到了但并没有特别明显地强调身体的构造性角色,先验主体性显然是无身体的绝对主体性。然而其遗稿却表明他没有忽视身体问题,并主张先验主体必须是身体的主体性。在《观念Ⅱ》中,胡塞尔重视身体在知觉经验中的构造作用,并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身体:作为对象的躯体(或物理身体)和作为主体的鲜活的身体。在探讨现实性构造问题时,他指出,“一个存在着的世界不仅需要认识主体的存在,在其中还需要拥有肉身存在的认识主体”[14](P140)。他强调,“依照我们已给定的观点,关于事物世界的经验之可能性预设了:在经验者在世界中拥有身体,只是在这点上,经验者自身才属于经验的世界”[14](P133)。这就表明,身体不仅仅是被构造的,也具有构造性功能,它是一切关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的前提条件,现实世界的构造需要涉身的主体。主体即便是先验的,也需要以肉身的方式存在。由于“构造性主体是涉身的,而且由于这个身体性主体通常已经将自身解释为属于世界的,就必须再一次断定,关于无世界的主体是很成问题的”[8](P106)。由此可见,胡塞尔所强调的涉身主体不是无身体的纯粹意识主体,它不是无世界的抽象主体,而是嵌入于世界并赋予意义于世界的主体。 对于胡塞尔来说,先验主体也不是独一的、封闭的主体,而是朝向他者开放的主体。关于他者的经验是现实世界构造的必要条件,现实世界的构造不是由独一的涉身主体完成的,只能通过诸主体间的共同体才得以发生和实现。尽管胡塞尔常以独一的自我为分析起点,但其先验现象学并非唯我论。在方法上,现象学还原“悬隔”了外部世界和其他主体,从而“获得”了作为一切存在意义之源泉的先验主体性,这使现象学具有了一些唯我论色彩。但对于整个先验现象学来说,唯我论只是现象学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彻底的现象学还原将导致先验交互主体性的显现,唯我论的现象学必然朝向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发展。在《笛卡尔沉思》中,胡塞尔集中地探讨了“主体间的单子论”,他并没有忽视他者问题和交互主体性问题,而是将交互主体性把握为先验主体性之可能性的先天条件,认为主体性只有通过与其他主体性的关联,只有在交互主体性之中才成为可能。对于胡塞尔的先验交互主体性,梅洛-庞蒂曾评论说,“如果先验是主体间性,如何才能避免先验与经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为在有他者的场合,他者从我那里看到的一切——我的一切事实性——都被重新整合于主体性之中,或者至少被当作主体性定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先验就落入了历史”[9](P107)。 显然,晚期胡塞尔对先验现象学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为人熟知的“自我学”的先验现象学。通过将身体、他者、交互主体性、生活世界、历史等问题纳入先验哲学范畴,他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先验哲学的范围,从而撼动了先验视角与经验视角之间的严格对立,使两者之间少了一些矛盾而能共存和互补。这对于我们讨论自然化现象学的可能性,重新思考自然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关系、现象学与经验科学的关系,整合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等基础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通过对身体和交互主体性等问题的讨论,胡塞尔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观念Ⅰ》时期的绝对观念论的思想,认为先验主体不是一个无身体的“观察者”,或者无世界的、孤独的抽象主体,而应理解为嵌入于生活世界、社会、历史的具体主体,它在本质上关联于其他涉身主体。相比于笛卡尔-康德式的先验主体性,晚期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更具开放性和优势,可以为先验现象学与其他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出发点。当然,胡塞尔所关注的身体和交互主体性问题与当代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广阔的对话空间。对于正兴起的涉身认知来说,胡塞尔以及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也有助于澄清涉身性概念及其性质,理解身体以及世界在人类认知中的作用,也是化解先验主义与自然主义分歧的一种可能路径。在交互主体性问题上,神经科学家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等人对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移情解释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能够支持胡塞尔的移情理论。扎哈维(Dan Zahavi)和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认为胡塞尔等现象学家的交互主体性理论能很好地理解社会认知的本质,并能替代心灵理论的解释模式。梅洛-庞蒂进一步主题化和深化了晚期胡塞尔对先验主体性的反思,他格外强调主体性的身体性特征,并依据胡塞尔对身体的区分而区分了现象的身体和对象的身体;格外重视主体性与世界的紧密关联,认为主体性是嵌入于社会和历史的。梅洛-庞蒂甚至还提出“自然主义真理”,试图重新界定先验哲学,超越经验与先验、主观与客观的简单对立。也正是这个原因,许多自然化现象学的倡导者更加钟情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 总之,任何形式的自然化现象学都需要面对现象学的反自然主义及其先验主义立场问题。本文虽强调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及其先验主义立场,并质疑鲁瓦等人的激进的自然化(数学化)现象学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自然化现象学的可能路径的否定,更不排斥现象学对认知科学等经验科学的启迪和贡献。本文还企图表明,晚期胡塞尔对先验现象学的扩展和对先验主体性的反思有助于现象学与经验科学以及其他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相对于鲁瓦等人的激进自然化方案,扎哈维和加拉格尔所提倡与践行的温和自然化现象学路径则更明智。他们意识到胡塞尔的反自然主义与先验主义立场,坚持现象学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合法性,并主张自然化仅意味着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和合作。在他们看来,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能够相互约束和相互启蒙,不仅现象学描述对经验科学是有用的和必要的,而且经验科学也能带给现象学启发和挑战。如加拉格尔所言,这种温和自然化现象学并非现在才出现,在整合现象学与心理学、神经科学等经验科学方面,古尔维奇、萨特、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都做了诸多有意义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何尝不是一种自然化现象学。标签:现象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胡塞尔论文; 数学论文; 科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