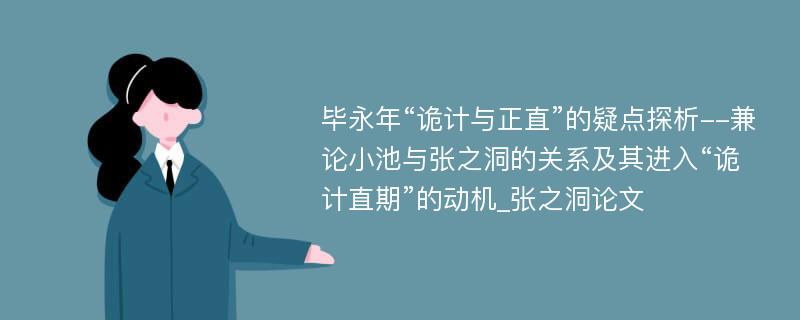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疑点论文,动机论文,小田论文,关系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8)02-0113-09
一、问题的提出
《诡谋直纪》实际上是以毕永年名义所写的关于戊戌政变的日记。它逐日记载了毕氏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日在北京的活动与见闻,尤其是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四日他在南海会馆下榻期间耳闻目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重要人物在戊戌政变爆发前的紧张活动。1985年9月4日杨天石于《光明日报》发表《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率先运用《诡谋直纪》论证了维新派确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接着,汤志钧发表《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新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随后,《诡谋直纪》标点本在《近代史资料》刊出。汤先生还将此文辑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一书中。
杨天石、汤志钧都认为《诡谋直纪》是真实可信的,指出它“记录政变前夕,后党环视,阴云密布,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节,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①。承蒙杨、汤二位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提供毕氏此文,故笔者在撰写《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时运用《诡谋直纪》来讨论“局势的恶化与康有为的挽救之策”②。换句话说,当时笔者对毕氏在戊戌政变期间所写日记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可是,过了10多个年头,房德邻在《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一文中,却对毕永年戊戌政变前后所写的日记表示怀疑。房氏文曰:
我认为《诡谋直纪》的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因为毕永年在追写这份“日记”时,或者因为记忆不清,或者因为有某种目的而改写历史,从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如:“日记”七月二十九日记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袁世凯已于两日前到京,而事实是袁世凯应诏于二十九日晋京。再如,“日记”说八月初三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一起说袁世凯勤王,说康有为向袁讲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但事实是谭嗣同独自一人说袁。至于日记所记康有为等密谋围园这一中心事件,也不可径直作为信史。③
房文提出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故而,在2003~2004年东京大学举办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时,我们将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复制件,印发给每一位学员,让大家参酌讨论。然后,又对照外务省所藏原件,仔细考订,反复琢磨,深感房德邻对《诡谋直纪》的质疑值得重视,而毕氏所写日记,确有可疑之处,故再撰斯文,予以考察,以期增进对此问题之讨论。
二、毕永年的日记,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出了差错
毕永年《诡谋直纪》既有许多重要疑点,那么,可否断定它完全是伪造的?从其内容来分析,似乎难以遽下此结论。因为毕永年确实同戊戌政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说,他还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
毕永年,号松甫,松琥,湖南善化人,拔贡出身,与谭嗣同、唐才常志同道合。杨天石在《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一文中,对其一生经历有全面考述④。毕永年于戊戌年确实曾赴京师图谋变政,杨文引述熟谙戊戌辛亥史料的冯自由所记,揭示毕永年在百日维新后期前往京师的具体情形。其文曰:
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捕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力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⑤
可见,毕永年确实曾经预闻戊戌密谋,只是因为靠袁世凯围园杀后绝“不可恃”,才拒绝执行康有为的计划。因此,说《诡谋直纪》出自毕永年之手,内容真实可信,亦自有其依据。不过,冯自由上述记载的依据,似乎是在毕永年到达日本之后,才听毕氏口述的。
日记是记载作者个人的见闻与经历的文字,日记的价值取决于它的真实性,尤其是在重要时刻的记事要准确无误。具体到《诡谋直纪》而论,又确实存在许多疑团。最可疑之处,是该文在戊戌政变最重要环节上记述失实。毕永年八月初三日的日记称: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乎?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是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⑥
此处该文作者已写明康有为甚忙迫,一夜未归,似乎与谭嗣同、梁启超一同与袁世凯会商了。从语气上看,毕永年是在推测。而这种推测,显然是局外人之谈。
更使人可疑的是《诡谋直纪》又接着记曰:
初四日,早膳后,谭君归寓。仆往询之,谭君正梳发,气恹恹然曰: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仆曰:“袁究可用乎?”谭曰:“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仆曰:“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仆曰:“事今败矣,事今败矣。此何等事,而可出口中止乎?今见公等族灭耳,仆不愿同罹斯难,请即辞出南海馆而寓他处,然兄亦宜自谋,不可与之同尽,无益也。”午后一时,仆乃迁寓宁乡馆,距南海馆只数家,易于探究也。⑦
毕永年此日所记,有问有答,非常具体,但是却有两处十分明显的错误:其一,毕永年说谭嗣同“气恹恹”,“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似乎谭嗣同不想去夜访法华寺动员袁世凯,是康有为硬逼迫他去的。这与戊戌政变中谭嗣同勇于冲决罗网,敢于任事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其二,《诡谋直纪》记载,毕永年初四日早问谭嗣同说:“昨夜尽以密谋告袁乎?”谭曰:“康尽言之矣”。此种说法严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我们无法相信毕永年竟然会说出这样的错话。
众所周知,谭嗣同初三日夜访法华寺,乃戊戌政变期间维新派活动最关紧要的一幕,而《诡谋直纪》所记载的“诡谋”细节,却与重要当事人的记述格格不入。
我们不妨看看戊戌政变重要当事者康有为本人的记载:
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经划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复生入城后,卓如至金顶庙容纯斋处候消息,吾稍发书料行李,是日尽却客。……至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⑧
上文中的容纯斋,应该是指容闳。容闳,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人。少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二十七年(1847)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终生“舍忧国外无它思想”,戊戌政变时正在北京,且与维新派多有往还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对八月初三日的应付政变的活动经历,记载得如此详细。其关键情节,则是谭嗣同初三日夜只身访法华寺,梁启超到金顶庙的容纯斋处,而康有为则在南海会馆料理行李,为出走作准备。康氏记载与《诡谋直纪》所述康、谭、梁“一夜未归”,完全风牛马不相及。
再有,康有为叙述政变前维新派的活动,把他身边有关系的人几乎全部提到了,却始终没有提到毕永年的名字。这似乎表明,戊戌政变时毕永年并非维新派圈子中的重要人物。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曰:“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为皇上如何人也?……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乃叮咛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⑩。
对于谭嗣同八月初三日夜晚独自访法华寺的事实,袁世凯《戊戌日记》八月初三日记载:
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责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11)
由此可知,无论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还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均记载是谭嗣同一人前往说袁,而梁启超则在金顶庙等消息。
毕永年如果真是身历其事,他似不会有初三、初四之日记。因为《诡谋直纪》从初三日开始,即认为是康、谭、梁三人均往法华寺劝袁;初四日又有“康尽言之矣”这样大错特错的记载。这种反常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果像《诡谋直纪》所记,毕永年的确于八月初四日在南海会馆下榻期间问过谭嗣同八月初三日夜的活动,依据常理,谭嗣同一定会以实相告,而不会把他一人夜访法华寺的事情,说成是他同康、梁一起去访问袁世凯。谭嗣同在万分危迫情况下绝不会以假话欺骗挚友,因为这与他对朋友肝胆相照的豪放性格不相符合。
对这一关键环节上的重大失误,房德邻的文章认为,“杨天石已指出这一错误,并认为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12)。在我们看来,问题似乎不是这样简单。须知,《诡谋直纪》此处分明是在叙述“诡谋”之重要环节,而并非在作“猜测”。“猜测”二字把问题说轻了。在别的地方出差错,可以说是“疏忽”、“猜测”,在关键处出现这样的误记,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毕永年没有问过谭嗣同关于夜访法华寺的情况,故而,他只能够主观“猜测”当时的情节。
三、关于《诡谋直纪》原件的笔迹问题
日记作为一种重要史料,通常是当事者本人所写。我们在对《诡谋直纪》考察时,对照日本外务省档案馆所藏原件,还发现了该日记笔迹存在严重可疑之处。而这些可疑之处,则与《诡谋直纪》的作者究竟是谁有直接关系。《诡谋直纪》的笔迹有两个可疑之处。
其一,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所保存的《诡谋直纪》原件文字并不长,可是,短短千余字的文章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笔迹:一种笔迹是此文题目与作者:“诡谋直纪,毕永年”。这7个字是一种行书,写在《诡谋直纪》的封面;而它的正文部分,共有8页,则全部用工整的柳体书写,抄写得极为整齐,不难看出是专业书手的作品。全文简洁明了,文从字顺,显然是经过反复斟酌的文字。那么,在这两种字体中,有没有毕永年所写?哪种字体是毕永年写的?
为了证实毕永年的笔迹,我们对东京的有关图书馆与档案馆进行了多方调查,终于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宪政资料图书馆找到并复制了毕永年的两通手札。
第一通手札全文如下:
北平先生足下:
久不相见,渴念殊深,惟德业益宏,无任翘企。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
秋风多寒,伏惟珍重千万,不尽欲言,敬请道安。
小弟毕永年谨上启。
在此信封之背面,还署有“英十月二十九日,香港安永生”等文字。由此可以断定此信写于1899年10月29日,他当时在香港。为安全起见,毕永年化名为安永生。信中所云“弃贵馆之委任”,是说毕永年曾被聘为日人在武汉所办《汉报》笔政,后弃之而去香港。信中的高桥先生,据杨天石考证,当指“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13)。
收信人宗方小太郎(1864~1923),号北平,与中国关系至为密切。据日本有关所载,自光绪十年(1884年)以来,他长期在华活动,号称“支那浪人”、“军事侦探”(14)。由于宗方小太郎对毕永年、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曾予以同情与支持,因此被毕永年视作无话不说的挚友。
东京大学法学部宪政资料图书馆所藏毕永年的第二封信之内容如下:
北平先生足下:
沪上两次赐书,均已收到。拜读之余,益增感激。先生如此不辞劳瘁,为支那力图保全,况彦本父母之邦,敢不竭虑捐身,以副先生相知之雅乎?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有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且有留闽十余年,深悉情形,广联声气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除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部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彦之鄙念如此,先生幸垂察焉。
如贵邦人尚有以缓办之说进者,愿先生勿听也。彦决然一身,久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惟此痛恨胡虏,欲速灭亡之心,辄形诸梦寐,不能自已。先生知我,伏祈谅之。敬请道安。
小弟松彦谨拜启。
英七月十五日。
信封署名安永松彦。由于此信内容涉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筹划1900年的福建、广东起义,故可断定此信写于1900年7月15日,“安永松彦”应是毕永年化名。毕永年的这两封信都化名安姓,故革命党人内部常有人称其为“安兄”者。杨天石在《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中曾引用过毕永年这两通信札的有关内容,却没有将其笔迹与日本档案中的《诡谋直纪》笔迹予以对比考察。
其实,如果将外务省所藏《诡谋直纪》原本,与上述两通毕永年手札笔迹比较,即可得出结论:本文上述《诡谋直纪》的第一种笔迹,即“诡谋直纪,毕永年”,与毕永年本人手迹完全相符合。也就是说,整本《诡谋直纪》,只有封面的“诡谋直纪,毕永年”7个字是毕永年亲笔所书。而《诡谋直纪》的正文部分,则是另外一个书手抄写。
其二,由于《诡谋直纪》的内容,与谭嗣同动员袁世凯围园有关,故而短短千余言中,袁世凯或袁之姓氏,在此文中出现多达31次。其中,袁世凯的姓氏分别出现于原文第1页有3处,第2页有7处,第3页有12处,第4页有2处,第5页有3处,第6页有1处,第7页有3处。令人费解的是,抄件中居然将所有的“袁”字,误写为“逺”字。最后,除第3页一处逺字未作改动外,其余30处均将误书之“逺”字划去,旁加正确的“袁”字。
从上述对《诡谋直纪》原件字体之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诡谋直纪》决不像小田切万寿之助向他的上司都筑报告的那样,出自毕永年手写之稿件。
这一特殊的抄写现象,可以证实《诡谋直纪》全部文字,并非是由毕永年亲笔书写,而是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雇人抄写,这位书手似乎缺乏有关中国时政的基本常识,以至于不知道袁世凯的姓氏究竟是哪个字。
《诡谋直纪》封面,有毕永年所写的书名及他本人的签名,这又说明,这篇文章写好之后,经过毕永年之认可。
四、小田切与《诡谋直纪》之关系
2001年房德邻对《诡谋直纪》的质疑,认为是毕永年在政变后与康有为、梁启超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因此,其内容并不可靠。房文发表后,汤志钧又写了一篇《关于〈诡谋直纪〉》的答辩文字,汤先生写道:
最近看到房德邻同志的《维新派“围园”密谋考》,他经过认真考虑用较大的篇幅考核了“《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待之时”。房同志的结论是很有见地的,如果是当时的“直纪”,又为何将时日误系?所以房同志说:“从《诡谋直纪》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变法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
《诡谋直纪》写于“戊戌变法后”是否它就没有史料价值呢?不是。评价某一史料的价值,不能单看它是“追述”,还是当时日记,而是看它是否提供了史料,这些史料是否有参考价值。(15)
总之,汤先生认为,即使房德邻提出了怀疑,但是《诡谋直纪》仍然是值得信赖的。然而,汤先生的答辩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汤先生答辩文的前部,还列举了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湖南地方近况及毕永年〈诡谋直纪〉送达之件》,附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先生之意在于说明,《诡谋直纪》是经由正式外交渠道呈递的文献,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我们对小田切报告的看法与汤先生不同。我们认为小田切给日本外务省次官都筑馨六的信件,说明他代递《诡谋直纪》是有其深刻用意的。或者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小田切是有其特定的政治目的的。
拙著《戊戌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一文中,曾经详细论说了在百日维新期间,张之洞背着清政府与小田切商定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由日本派参谋训练一支军队,兴办军事、民用企业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等事宜,这个规模宏远的计划送到东京之后,曾受到日本政府各方面的重视(16)。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戊戌政变的突然爆发,张之洞与小田切的合作计划受到严重影响,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张之洞本人亦受到守旧派的怀疑与攻击,其地位岌岌可危。带头攻击张之洞的是守旧派的头面人物徐桐。
张之洞早年出身清流,与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关系颇为密切。在张之洞的一些未刊信札中,有不少称颂徐桐“正色立朝”,“为人表率”等歌功颂德之词(17)。徐桐还于戊戌春季专门向光绪帝推荐张之洞来京,咨询有关事宜(18)。但是,当他发现张之洞倾向新政,取法日本后,便向慈禧上书,要求对张严惩。徐桐的奏章,反映了清政府内部的守旧势力,是把张之洞视作康、梁同路人的。守旧派认为,张之洞的派留学生出洋及其他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说来,是早晚会危及到清政府的长治久安大计的。守旧派愈是这样来指责张之洞,张之洞则愈要起劲地反对康、梁,愈要显示他与康、梁绝不是一个营垒的。只有这样,他才能让慈禧放心。
非但如此,由于康、梁等人流亡在香港、日本等地,极力攻击慈禧、荣禄等守旧势力的倒行逆施,从而更加惹怒了清廷。于是,慈禧等人下令让各地督抚及驻日本公使李盛铎千方百计将康、梁捕获严惩,或者就地处决。张之洞为了讨好慈禧,并摆脱戊戌政变之后所处困境,亦向小田切求助,希望他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维新派人士赶出日本列岛(19)。
据小田切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给日本外务省专门致函,谈到张之洞的上述要求:
张之洞要求我秘密地通告日本政府:康及其党派停留日本,不仅伤害了两国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亦妨碍他实现由日本派教习训练军队的计划。他希望能将康有为、梁启超驱出日本。
张之洞还说,如果日本准备接受中国学生,他希望帝国政府通过驻清国特命全权公使,通知总理衙门,要求他们通知南洋大臣、北洋大臣和湖广总督,尽可能早地送我们的学生出去。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张之洞真的打算送多于50名的学生出日本,但他犹豫自己的责任,因为他担心一些危险,会降临到他头上。(20)
由小田切此件亦可看出,张之洞在戊戌政变后的复杂心情:他虽然憎恨康、梁,却与慈禧、刚毅等守旧派不同。张氏只是要求把康、梁驱逐到欧美而已。小田切对张之洞与康、梁严重对立的立场是了若指掌的,他在两者之间无疑是站在张之洞方面的。
后来,随着清廷内部的守旧势力日益猖獗,张之洞面临的压力亦日趋严重。张之洞为了在政治上摆脱困境,故对康、梁的仇视亦有加无减,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把梁鼎芬所编造的《康有为事实》寄给小田切,再由小田切向日本外务省呈递(21)。
小田切的报告詳细叙述了张之洞在戊戌政变之后,所遭遇的困境,以及他强烈希望将康有为等人由日本驱除出去的愿望。如小田切本人所述,在戊戌政变之后的三个月间,他曾在武昌府和总督会过五次面,因此对张之洞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真实可靠。日本外务省在收到小田切的报告之后,非常重视,迅速作了处理。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在小田切的报告后面作了两条批注:其一谓:应允诺张之洞所提议的将《康有为事实》登载在报纸上,并且应该将刊登此文的报纸,通过小田切氏转交给张氏,供其阅览。其二谓:我相信应该将日本政府对于康氏的意向,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告诉驻北京公使矢野和小田切氏。而且关于报纸的登载等事项,也应按照张氏的希望进行(22)。
都筑批注中所说“日本政府对于康氏的意向”,即是想方设法动员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外务省同意都筑的意见,按照小田切之报告所提出的建议,接受张之洞的要求,在日本报纸上广为刊载《康有为事实》。从张之洞到小田切,再从小田切到日本外务省,他们对康有为的立场几乎是相同的。即希望把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形象丑化,使其在日本没有同情与支持者。从而达到促使康有为尽早离开东瀛的目的。但是,康有为等在日本确实有不少支持者。因此,想劝他们离开也并非那么轻而易举。于是,各派势力都在想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小田切才同意将《诡谋直纪》转呈外务省。
小田切在进呈《诡谋直纪》时还向外务省写了一份报告,通过这个报告,能使我们更加了解小田切对康有为之立场。其中有些话颇值得玩味。小田切报告说:
目前在日本逗留中的康有为等人,已不顾日本官民中的同人一派对其意向的详知,也不顾已接受退出日本的劝告,而仍然滞留日本,日复一日,其原因无非是尚有一缕希望寄于湖南地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毕永年等回到日本后将实地情况详告后,康有为或许多少能够接受现实、转变方向的。(23)
显然,小田切对康有为等维新派不顾“退出日本的劝告”,仍然留在日本,是持反对态度的。接下来小田切的报告又称:
康有为等寄给同人的书信到达,毕永年拆阅信件,书中有唆使毕等人,使其开发事端的语言。阅信后原先对康有为存留疑心而持宽容态度的同人大为激愤。所以,毕永年将已对平山周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标题为《诡谋直纪》。毕将《直纪》交平山周阅览,平山又给下官看。从《诡谋直纪》中看出当时实况,见其中还有颇有供参考、有价值的内容,急忙抄写后,即刻呈送,敬请查阅。(24)
小田切的这段文字是解说《诡谋直纪》的产生来历以及向外务省呈递之经过。
按照小田切的说法是:首先,康有为的信件,使毕永年等人激愤,于是“毕永年将已对平山周隐秘了很久的政变当时的实况记述下来,标题为《诡谋直纪》”。小田切的这段话有几个地方值得怀疑。其一,小田切说是毕永年自己把“实况记述下来”的本子交给他,然后,他又“急忙抄写后”送往日本外务省,然而,如本文以上对《诡谋直纪》笔迹的分析,如果真是照毕永年自己把“实况记述下来”的本子,何以能把所有袁世凯的姓,均误作“逺”字,而且错误多达31处?其二,如果小田切真有毕永年自己记述的原件,按照我们在日本外务省所看到的凡属外国寄回的密报,几乎尽用原件,以求信与真。梁鼎芬的《康有为事实》,亦属原件呈递。我很奇怪,小田切为何多此一举,为什么要对《诡谋直纪》“急忙抄写后,即刻呈送”?
小田切雇人抄写说明,《诡谋直纪》的形成过程,远比小田切所述复杂得多。
为了将康梁逐出日本,小田切还于明治32年3月24日向日本外务省呈递了张之洞的另外一份电报。其文曰:
张之洞来电写道:《清议报》系康梁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政,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是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惑人心,必欲中国立时大乱而后已,险恶已极。所说各事,皆是虚诬,贵国人想未知之耳。其种种饰辞,总言彼党系于忠于皇上,奉密诏求援。然于夏秋间,康有为在朝任用之时,即称大清国为“大浊国”,又拟立谭嗣同为伯理玺;又力诋中国为不足与有为;又于《清议报》内载有瓜分中国策。夫(国?)家已无可为矣,民主已另立矣,疆土已促各国瓜分矣,不知置皇上于何地?奉诏求援者,固如是乎?此等奸谋妄语,不攻自破矣。中国地方,固不能容其传播;中东和好,贵国亦不应准其在境内捏造是非。(25)
小田切和张之洞的这一系列活动目的都是相同的,即把康有为形象丑化,以达到驱逐康梁出日本的目的。
五、结论
毕永年《诡谋直纪》之内容,既有如此多的可疑之处,而呈递过程又不无可疑。所谓《诡谋直纪》,实际上是把毕永年与平山周等人有关毕氏戊戌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日在京见闻的谈话,归纳整理,按日记的形式予以编排,形成了现在我们见到的《诡谋直纪》。其目的则在于使日本政府更加了解康有为过去的“不当”行为,以达到张之洞与清政府所再三要求的,驱逐康有为离开日本的目的。只有了解了当时张之洞的处境,才能把小田切进呈《诡谋直纪》的真实目的搞清楚。
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守旧派的活动,称作“诡谋”,已表明了此文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因此,我们使用《诡谋直纪》时,一定要认真考求,要有分析,不可一概视为信史。
注释:
①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②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28~429页。
③(12)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北京:《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13)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实发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61、58页。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
⑥⑦(25)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编号1-6-1-4-2。
⑧⑩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1、52页。
⑨孔祥吉:《略论容闳对美国经验的宣传与推广——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1)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0~553页。
(14)(16)神谷正男编:《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东京:原书房,昭和50年版,市古宙三解说。
(15)汤志钧:《关于〈诡谋直纪〉》,北京:《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6)(19)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08、108~111页。
(17)《张之洞未刊函稿》,致徐桐函。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春季档。
(2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国兵制改革》,第1卷,编号5-1-1-14,第104页。
(21)(2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清国亡命政客渡来之件》,张之洞近状及其对戊戌政变之意见的报告。
(23)(2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支部,编号1-6-1-1。
标签:张之洞论文; 谭嗣同论文; 康有为论文; 毕永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永年论文; 清朝论文; 袁世凯论文; 梁启超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