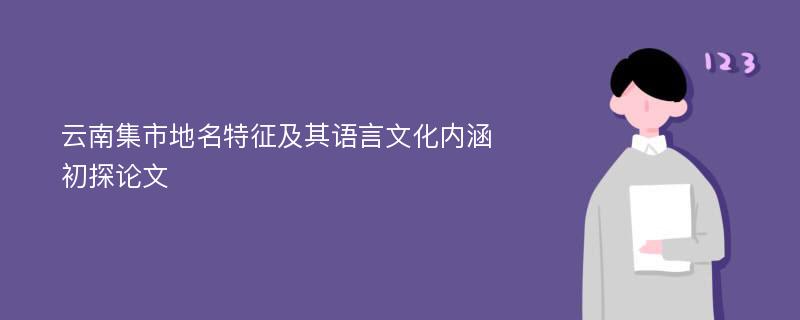
云南集市地名特征及其语言文化内涵初探
牟成刚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99)
摘要: 集市在云南主要称“街”,这是滇域较为突出的地域特征词。据考证,云南的“街”,当源自古蜀语“亥”,亥者“痎”也,乃周而复始之疟疾,因集市与之在循环义上关联而通,而滇域又多以道路成市,道路又与“街”相关,“亥(痎)”和“街”古音同,后便代之以“街”而名之。云南以“街”为通名的集市至迟元代即已出现,明清以来渐盛,其专名构成上具有自然性、直观性、原始性、民族性和重复性特征。滇域街子的集日循环,在民国及其之前主要用地支(属相)确定街日,以十二天为基数进行循环,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用星期确定街日,以七天为基数而循环,街期上具有短而密集的特点。“街”是集市适应云南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所产生的特殊地域称谓和演变类型,它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滇域文化内涵特征。
关键词: 云南;街子;地名;内涵;初探
云南商品经济在历史上发展较缓,故集市起步较晚。明清以来,集市交易逐渐覆盖全省,数量颇丰,可因其多以“街”成市,随路而商,“街”也便因此而成为集市的通称,以致滇域随之涌现出大量以“街”为通名的集市地名。地名被喻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它与特定区域内的地理及历史文化密切相关,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文章根据滇域集市地名实情,结合语言文化接触理论,辅以移民及相关史料文献,对滇域集市的地名特征及与之相关的语言文化内涵试作探析,以期人们对滇域“街子”文化有一个深入而全面的理解。
一、云南集市的地名类别及主要特征
地名一般由通名和专名组成,通名为地名定类,专名为地名定位。通名标志着人们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认识和分类,反映地名的类属关系;专名是人们对具体地域最初的理解和认识,体现地名的得名缘由。[1](P31)云南集市地名在通名和专名上都有突出的地域特色。
(一)通名的类型及特征
云南集市通名有“街”“场”“圩”等,其中以“街”为其主要命名特征。据统计,滇地共有以“街”结尾的集市地名279个,注 集市在云南普遍称“街”或“街子”,但其作为集市地名的通名时一般只称“街”。本文集市数据主要依云南省地图院《云南省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统计而得,因地图限于篇幅未必能穷尽列出,且有些双音节及以上的集市地名在日常称呼上并不一定都加通名“街”(如广南的牡宜街也可称“牡宜”,富宁的谷拉街一般只称“谷拉”)等,故在云南实际通名称“街”的集市地名会比统计的数字更多些。 分布范围遍布全省,而又以滇中、滇南和滇东南最为集中。“场”一般指“适应某种需要的比较大的地方”,[2](P149)云南以“场”结尾的地名有42个,但绝大多数并非指集市,如楚雄姚安的“前场”便源自元代之后滇中偏西进入昆明的前哨要道而得名(偏西的大理云龙、鹤庆有“后场”), 文山广南杨柳树有“猪场”是因土地下放之前为集体养猪之地而得名,红河绿春和腾冲均有“马场”,但都指养马之场所而非集市通名,这类非集市通名的“场”亦可称“厂”,如广南五珠的“老厂”就系“因居住老场地得名,后演变为老厂”,[3](P123)但此类“场”“厂”都不属于集市通名称呼。“场”在云南作为集市通名主要局限于滇东的曲靖和滇东北的昭通偏北一带,曲靖毗邻贵州,昭通接壤川南,川黔至迟自明代始便称集市为“场”,因地缘人际交往及语言接触影响之缘由,滇东和滇东北存在称集市通名为“场”的情况并不奇怪,如滇东曲靖富源有牛场、鸡场、马场口、顺场、羊场边,罗平有老鸡场、沾益有小鸡场,宣威有羊场、鸡场、兔场、虎场等,滇东北的镇雄有牛场、盐津有新场等,据统计,滇东和滇东北一带至少有15个称“场”的集市具体地名。值得注意的是,因地域主体文化的内聚,这些称集市为“场”的区域,现在新开的集市一般常常用“街”作为通名,如曲靖罗平同样有马街、富源有龙街,昭通镇雄有上街等。因此,云南的“场”并非都指集市,需要仔细甄别,如丽江玉龙和曲靖富源都有“小羊场”,但前者是牧养之地,后者方为集市通名。滇域称集市为“圩”(读如普通话的“喝”)的比较少,目前仅见1处,即文山广南的“底圩”,此地壮汉两族居住,据壮语命名,“底”壮语为地方,“圩”壮语为街场,“底圩”即“意为赶街的地方”。[3](P39)广南位于滇东南与桂西北的百色市毗邻,明代谢肇淛《滇略》(卷四俗略)记载“市肆岭南谓之墟”,与之同时代的徐霞客也在其游记中提到集市在“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4](P1801)由此可见,岭南的广西等地的集市通名称“墟”也算是历史悠久了。“墟”在南方也有写为“圩”的,意指农村定期的集市,[1](P129)“墟”和“圩”属同词异字,如广西百色就有阳圩、新圩等。实际上,滇东南广南、富宁一带在明代及之前曾长期隶属桂地,因受岭南称集市通名为“圩(墟)”的接触影响,如今偶见其地残留集市称“圩”的现象并不难理解。
根据以上分析,“街”显然体现了集市通名在云南的主要特征,虽然也有“场”“圩”等用名,但其在数量上和文化认同上显然都不能与“街”相提并论。据笔者调查,云南集市称“场”“圩”的这类地名因历史形成的缘由,至今一般较为稳定,但在这些区域现在新开的集市其通名一般均已用“街”,如昭通昭阳地区对赶集市的称呼就出现了新老派的差异,即现在老年人一般称“赶场”,年轻人一般已称“赶街”;滇东南与广西毗邻的广南、富宁一带基本没人再称“赶圩”,全都称“赶街”,甚至仅有的地名“底圩”也很少有人知道“圩”为“街”意,大多以为只是一个普通地名,以致人们去底圩赶集还称之为“赶底圩街”。由此可见,“街”作为云南特有的集市通名,在滇域内具有极强的文化认同感及整合功能。
为了验证前面标定式(7)的重复性,本文利用了297×10-6、694×10-6、1 100×10-6标准气体在25 ℃温度下每隔一分钟测量一次,连续测量10 min,测得10个数据,绘成图13(a)所示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曲线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为了验证实验系统的稳定性,对浓度为495×10-6的CO2样气进行了长期多次测量,每隔3 min测1个数据点,待测得10个数据点后,间隔半小时,继续测量,重复多次,结果如图1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在±50×10-6左右,达到了预期水平。
云南集市曰“街”在滇域有记录一般认为起于元代,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市井”者,古之街市也,这是目前所知云南称市为“街”的最早记录。后,明清时期有关“街”的记录便渐多起来,明谢肇淛《滇略·卷四俗异》:“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亥,滇谓之街子”,明徐弘祖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去黔入滇,在随后两年的游览日记中提到在今滇东、滇中、滇西北一带有街子,如滇东曲靖马龙有兔街子,滇中寻甸羊街子、狗街子、牛街子,滇西的宾川有牛井街,洱源有牛街子,永平有狗街子,腾冲有新街等。[4](P2471)由此可见,至明代街子已广泛分布于云南地域。
(二)专名的构成及理据特征
理据即“理由”或“根据”,[2](P795)专名的理据就是指地名专名形成的理由和根据。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地形沟壑纵横,坝子盆地极为有限,域内九成以上为山地高原。一般来说,区域文化的孕育离不开具体地理环境的影响,云南存在包含地理、动物、方位、功能、序数等信息的集市专名,而这些集市专名均蕴含着丰富的滇域人文地理文化内涵。
GEO静止轨道卫星具有轨道高、覆盖面积广的特点,采用GEO卫星对地面信号进行透明转发,可以为卫星信号可覆盖区域的用户提供服务,不仅扩大了信号的服务范围,更降低了系统的建设难度和建设费用,受到通信、导航、时间频率传递等领域研究者的青睐[1-3]。
除此之外,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语言资源丰富,这在集市专名中也有体现。街市专名用少数民族语言命名的情况在滇西、滇南、滇东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比较常见,如滇西镇沅里崴街(“里崴”为傣语回头河)、景谷勐主街(“勐主”是傣语人心向往的地方)、普洱蛮别街(“蛮别”乃傣语鸭子,后为避俗,1958年更名为今文化街),红河屏边戈纪街(“戈纪”为彝语荞地下面)、滇东南广南牡宜街(牡宜为壮语小寨之意)、富宁毕街(毕乃壮语鸭子)等,云南至少有20个少数民族语言做专名的街市称呼,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民族特色。
自抗扰控制是我国韩京清研究员提出的一种非线性控制策略[5].该技术不依赖于系统具体的数学模型,它继承了传统PID控制的优点,克服了其不足之处.同时自抗扰控制技术也体现了现代控制理论的思想,利用扩张状态观测器对系统的内部扰动和外部扰动进行估计和补偿.考虑到自抗扰控制的上述优点,同时结合单级倒立摆控制系统对控制性能的要求,本文针对存在扰动因素影响下的单级倒立摆摆角控制问题,采用自抗扰控制方法设计单级倒立摆控制器.
一般来说,农村集市需要有固定的日期,滇域历史上经济文化较为落后,农村区域性的小集市众多,当地民族为了能够直观记住不同的集市日期,便会用与时间相关的概念作为街市的专名。例如以属相命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属相对于农村人来说司空见惯,其缘由是属相即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同时又是农村记录推算时间的一种方式。十二属相在云南可以纪时,每个属相一天,十二天一个轮回循环纪时,例如2009年1月1日属狗,[5](P2)则次日属猪,对于历史上经济文化都较为落后的云南民族来说,用与动物相关的属相纪时显然要比“枯燥乏味”的天干地支更方便,笔者小时就经常听老一辈的人说某天属鸡某天属狗之类的,并且以此占卜吉祥,因此,过去在云南农村,属相是一种流行而重要的纪时方式。利用十二属相做街的专名在云南的滇中、滇东、滇东南一带较为普遍,据统计,滇域用十二属相及与之相关的集市专名有87个,其中鼠街4个、牛街8个、虎街7个、兔街3个、龙街11个、马街10个、羊街17个、猴街4个、鸡街9个、狗街4个、猪街6个,此外,以蛇命名的集市专名有4个。十二属相在云南唯独没有以“蛇”直接为集市专名的,因为当地人对蛇很是忌讳,过去“见蛇不打三分罪”是滇域民族的共识,因对蛇忌讳以致大年初一忌讳见与蛇形似的绳子,当地人对蛇的忌讳由此可见一斑。蛇在云南一般被委婉地称之为长虫,故滇西南涧有长虫街,滇中禄劝有长子街、团街(蛇蜷缩之形),个别地区甚至反其意而用之,如今“云南景东县就称‘蛇街’为‘小龙街’”;[6](P244)云南民族还忌“虎”,牟定和广南就把虎街称为“猫街”,只是不似蛇那么严,寻甸、红河、南涧、弥渡仍直接称“虎街”(宣威称“虎场”)。属相集市专名还部分存在雅化的现象,如猪街在姚安、屏边称“朱街”,曲靖、昌宁、广南称“珠街”,狗街在昌宁称“耇街”,鸡街在广南现更名为“曙光”(鸡鸣见晓之意)。十二属相一般与十二地支对应,故在云南也有用十二地支做街的专名,如楚雄有子午街、牟定有戌街、泸西有午街、弥渡有寅街等。更有甚者,直接用序数做街的专名,据统计此类街的专名在云南有20个,主要集中在滇中一带,如南华有一街,南华、晋宁、安宁、易门分别有二街,楚雄有三街,通海有四街,南华有五街,石屏、呈贡、晋宁、易门、双柏有六街,大姚、楚雄有七街,安宁有八街,楚雄、通海有九街,易门有十街,安宁有一六街,序数专名街以月份为循环期,月内逢时间序数开集,如一街即赶初一、十一、二十一,其余依次类推,一六街在月内逢一逢六开集日。以上用属相、地支、序数为专名的集市地名,相对来说,直观易记,特别是以时间序数做集市专名的,不假修饰,原始朴素,这在其他地方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这类与时间概念相关的集市专名具有直观性和原始性特征。
云南街子基本都属于定期集市,即具有“固定的集场和集期”。[34](P17)定期集市一般都具有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主要体现为时间的循环性,即街日在某一时间段内呈现出周而复始的环型运行特点。滇地因街子形成的时间、分布的地域等存在差异,故街子的集日循环时间各地并不完全相同,或十二日一市或七日一市等,但均体现出街日周期的地域差异特色。
云南山高谷深,地势切割剧烈,植被繁茂,自然资源独特,故地名的命名自然会与自然环境特点相关,因应滇域地理特点,以致“山、坝、梁、坪、沟、川”等与山水相关的词汇得到了云南街子专名的青睐。例如,与水相关的有禄丰川街,川乃水也,星宿江流过今川街狭长的峡谷,人居此形成集市而名之(星宿江此段也名川街江),宾川平川街、新平双沟街、广南西洋江街、墨江龙潭街等专名均因水而得;因山而得名的集市专名较为频繁,如镇沅山街便因山直接命名,山埂于滇一般称山梁子或山岭,墨江和麻栗坡就有梁子街,砚山有长岭街,因街市居于山腰故凤庆和新平便各有一个腰街(会泽称“半边街”、宁洱称“把边街”);云南大块平地有限,少量的坝子便成为人们居住和集市形成的天然恩赐,镇沅田坝街、大坝街,开远平地街,砚山平远街(地平而空旷),西畴龙坪街(地平似龙)、宾川鸡坪街都属此类专名;滇域山高涧深,地理空间有限,方位主要以纵向的“前、后”为特点,在滇东北昭通朝阳区北部的洒鱼河畔上下游就各有一个街子,位居上游者谓之“上街子”,反之则为“下街子”,滇西漾濞有“上街”和“下街”,也因其分别位于漾濞河的上下游而名之,有些甚至点出方位的依托对象,如墨江的塘上街就是因街市居于水塘边上而得名,虽然今石林东北也有“西街口”(因原为师宗县西部集市而得名),可此类大时空方位集市地名在滇地非常有限。云南还有一些街市专名是直接以自然植物命名的,如滇西宁洱梅子街,滇东南文山的古木街、追栗街(追栗,原为“锥栎”,树名)。可见,云南街的专名多与自然环境相关,遍布全省,而尤以滇西、滇西南、滇东南为盛,反映了人文与地理环境的相互选择与适应的关系,不假修饰的自然性可视为此类街市专名命名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内涵较为丰富。
器乐合奏教学是学生团队的整体教学形式,以齐奏,合奏为主,它不同于其他的音乐教学能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必须以课堂形式对学生进行统一训练,让学生跟上集体的节奏演奏,旨在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增强他们的群体协调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云南的街市专名具有突出的自然性、直观性、原始性和地域民族性特征。此外,重复性也是滇域街市专名的主要特征之一,因为云南域内地理切割剧烈,山高谷深,隔山“鸡犬之声可闻”,但因自然交通阻隔,彼此来往很少,“家乡宝”观念突出,活动范围有限,以致现在看来空间直线距离很近,而彼此地名却多有重名,但在过去云南这类较为封闭的特殊地理环境中,这样的地名重复并不会给当地人们的理解和交流带来影响。
为了得到风室的数值模型,参照70 MW或100 t/h锅炉所配的横梁式链条炉排供风系统的三个风室设计试验台,并通过试验台测量数据与数值模拟数据进行比对,对数值模拟的准确性进行验证。
(三)通名和专名的结构特征
汉语地名中通名和专名的关系“最常见的是通名语素和方位词、数量词或一般名词的组合”。[1](P33)云南街市地名绝大多数都是“专名+通名”的结构形式,即专名在前,通名在后,如“鸡街”“腰街”等,反之“通名+专名”的现象则非常少见,据统计,目前“通名+专名”仅有3处,即滇东北彝良“街上”、巧家有“街子上”,滇东南富宁“街子”。我们认为,“通名+专名”是后起的集市地名,这类地名一般都有原名,例如巧家东部的“街子上”原名苞谷垴,垴者土丘也,即种玉米的土丘,后因交通便利渐成集市,民国时期每月逢“二、七”赶集(时称“苞谷老”),[11](P526)滇地集市泛称“街上”,后便以此代之(但作为行政称呼仍保持“苞谷垴乡”,其驻地为“街上”)。云南集市专名从是否可以单称上看分两种情况,即如果专名是单音节词,一般不能单说,如猫街不能单称“猫”,反之则可单称(联绵词和少数民族多音节词除外),如把滇东南砚山的平远街简称“平远”并不会引起误解。
二、云南集市地名的源起及其内涵
(一)“街”的语源考释
但理解云南的集市通名“街”也需要谨慎,因为有些地名没有“街”却是集市,有些地名有“街”可又不是集市。滇域民族众多,有些原有地名后来形成集市,这样的地名往往就会尊重传统,一般不会再冠以通名称某街(人们日常赶集可称赶某街,但作为地名只用原名),如滇东南广南的黑支果逢属相之鸡、兔日赶集,但地名并未称“黑支果街”,因为黑支果原本是一个小村子(因有黑果树而得名),到20世纪50年代成为黑支果乡的驻地方才成为集市,其地名至今为“黑支果”,实际上此类没有通名“街”的集市在云南是常见的现象。反之,滇域一些称“街”的地名也可能不是集市,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市地点迁移到别处或集市因故中落以致“街”名存实亡,如广南的牡宜街原为集市(牡宜公社驻地),但后来乡镇中心驻地迁至其西南部4公里的黑支果村后,牡宜街固定集市便逐渐中落以致最后失去了“街”的功能,现在已多称牡宜而少称“牡宜街”(黑支果因乡驻地而后成固定街市,但仍称“黑支果”,并未冠“街”名,可参上述);另一种是少数民族命名的原有地名与汉语的“街”相同或近似,后来汉语音译为“街”,这类地名尾字虽为“街”,但自然不是集市,如滇东南的广南有“者街”,但不是集市地名,这里为壮族聚居地,壮语“者”意为“地方”“街”意为“毛木树”,者街即“因村旁有毛木树而得名”,[3](P60)其与集市之“街”毫无联系。因此,对云南冠“街”的地名内涵需要联系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综合理解。
学界一般认为,云南在宋代及之前难通汉语,原因是这一时期虽有少数汉民因经商、驻戍等迁入云南,但数量极少,且在短时间之内都融入夷民之中,特别是“自唐中叶南诏独立后,在长达六百年的时间内,云南处于中原的版图之外”,[13](P614)至南宋后期,中原“与大理政权的官方联系基本中断”,[14](P124)以至在今汉族聚居的滇东地区当时都要“三译四译,乃与华通”,[15](P13)宋代及之前汉语在云南的使用之少由此可见一斑。可据历史记载,云南在宋代及之前与中原文化的联系“从未中断”,[16](P78)滇域夷方对汉文化具有推崇的心理,以至以白蛮为主体的地方统治集团“传统习惯上有一种心态,认为借用汉语多的人文化水平高”,[17](P74)把说汉语和识汉字看成是一种有身份的象征。根据研究,宋元之前汉语在云南虽多被夷化,但并未消失,它“通过与白语等夷语融合隐藏的方式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12](P99)例如白语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古汉语词汇”,[18](P22)这是最有力的例证。但云南官话方言形成于明代,且源自江淮官话,而“街”在江淮官话方言中并不用作集市的通名,同时云南“街”作为集市通名早在元代就有记录,那说明此前传入云南的汉语应该是一种有别于江淮官话而更为古老一些的方言,云南的“街”应与这种方言有渊源。
根据考证,云南官话方言最早也当形成于明代,其语源上为以南京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在“西南滇域的延伸性地域演变方言类型”,[12](P105)但“街”作为一个汉语词汇,显然不是明代及之后才使用于云南的,因为江淮官话地区的集市通名大多称“集”而不称“街”,其次“街”在云南被用作集市通名至迟在元代就有记录,那么说明它的使用应该早于明代。云南在宋代及之前主要为夷人“自治”,“直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之前,这里已经没有汉语的地位”,[13](P614)而元代以军事方式移民云南的汉族数量有限且多与蒙古等少数民族共同屯戍,故“汉语在元代不可能成为云南大范围内各民族的通用语言”,[12](P99)“街”似乎不太可能在元代突然出现,从语言记录的滞后性来看,既然作为集市通名的“街”于滇至迟元代就有记录,那么它在宋元之前就应该已经出现,明代移入云南的江淮方言显然不是其语源。
宋代及之前,云南南北向的交通格局决定了汉族移民及汉文化主要源自古蜀地域,元代虽开通东西向的普安大道,但此时期东边的移民并未大量迁入滇地,仅有的六千戍滇军士仍主要为蜀籍,因此,宋元及之前“云南当时的土著汉语的来源主要是古川蜀汉语”。[12](P100)但通过调查四川集市的命名,会发现今四川所用集市通名主要为“场”,而并非云南的“街”,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二·地理志)记载“蜀谓之场,滇谓之街,岭南谓之务,河北谓之集”,《丹铅总录》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可见四川至迟在明中后期,“场”在蜀地就已用作集市通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稍后成书于天启年间(1621至1627)谢肇淛《滇略》(卷四·异俗)提到 “市肆岭南谓之墟,齐赵谓之集,蜀谓之亥,滇谓之街子”。这样看来,明中后期前后相差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蜀地当时有“场”和“亥”两种不同的集市通名称呼,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现象。纵观今四川、贵州到湖北一地的集市通名多曰“场”,再结合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事实来看,“场”在四川作为集市通名的出现应该是明清以后较为晚近的事情,而“亥”应该是宋元之前的集市通名词汇。四川地理条件和位置特殊,为历朝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两代因战争和天灾等因素,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但落后的川西和川南一带受到兵灾战乱的影响要小得多,明清两代的湖广移民主要填的是川东区域,川西和川南一带移民相对较少,古蜀语存留要多些,语言上体现为入声不读阳平,我们一般把川西和川南的这些蜀地方言称为“老四川话”。[19](P297)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指出集市在“西蜀谓之亥”,进一步明确了“亥”的使用范围,说明当时这一词在川西地带保留着,而云南和蜀地在宋元及之前,因五尺道、灵关道、蜀身毒道等南北交通的联系,一直关系紧密,汉族移民及汉文化都受到蜀地的极大影响。因此,云南把集市通名称为“街”或“街子”,追溯之应与古蜀语相应称之为“亥”属同源。
[74]Economic Survey of Burma, 1956, Rangoon: Superintendent, Union Govt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1956, p.35.
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当地集市的自发形成与道路具有天然的联系。滇域系云贵高原的组成部分,平均海拔二千米以上,其高低相差达六千多米,高山峡谷相切,“高原、山地面积占云南省总面积的94%”,[28](P51)坝区仅占6%,典型的高原山地环境以及高山深谷相切的地貌,使得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自历史至今都一直显得较为缓慢。“集”之本义乃“聚集”,“市”为“买卖之所”,“集市”就是“农村或小城镇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2](P608)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商品交换形式”,[29](P43)人、物品和场所是其形成的必备条件。集市场所在北方及江南多为人们有意识地划地设置(甚至会考虑政治性和安全性),地点的设置与道路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需在相应规定的地点聚集交换物品就可“集”,随后可因“集”而形成交通汇集的市镇;但在经济和交通条件落后的云南则相反,这里一般是先有便捷的交通要道,最后因顺“路”方能自发形成“街子”。云南地势起伏较大,沟多谷深,河流对地表切割强烈,隔山喊得应,望山走死马,域内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的、立体的小型自然生态区,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相对低平的山间坝子及其边缘地带,受地形的阻隔,这些散布的村落“与外界由一条或数条通道连接,处于半封闭状态”。[28](P6)滇域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比较有限,人们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商品交易不活跃,但物品的交换总是需要的(例如食盐就需要交换),可这种交换还处于比较低级的状态,物品交换选择的“地点必须是在交通要道,四周农村最容易到达的中心”,[30](P206)如果是交通不便的“死角”地带,则无论如何是难以形成集市的,因此,道路与集市在云南的关系就非常密切,集市依托道路生存,道路因集市而繁盛,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那么,既然云南的集市依道路而生存,似乎可称“道市”或“路市”,但会与日常中的“道”和“路”相混,而“道”在唐代是监察区名称,“路”在宋元是行政区称呼,故集市如称“道”或“路”在当时还会与行政区划单位重合。明代汉族移入后,似乎亦可称“集”,但局限于滇域的地理环境,农村赶街的人数往往有限,称“集市”又显单薄。街者,本道路也,唐慧琳《一切音义》卷四引《声考》说“街,都邑之大道也”,因“街道上常有集市,所以街又引申表示集市”,[31](P143)这样“街”之道路就与集市有了关联,而且这种关联在云南显得更为紧密,故云南称沿道路自发形成的集市为“街市”似乎更为妥切些,而“市”一般指比较大的商品交易场所,这对于滇域乡村临时之物品交换地来说好像显得“名不副实”,故简称“街”(抑或“街子”),这样一来,既免除了集市称“道”和“路”等的尴尬,同时又与“街”自带意义相符,更重要的是与云南原宋元及之前集市称“亥(痎)”的底层词汇读音完全相同,故“街”入乡随俗并代替之,成为云南集市的通名称呼。
那么,集市在西蜀何以谓“亥”,它于今云南又是怎么变为“街”的,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说明它们的渊源。明陆深嘉靖二十四年(1545)《俨山外集》(卷十八·豫章漫抄)提到“市井之区谓之亥者,不知何所取义”,引说“西蜀谓之痎,解之者曰,如疟疾间而复作也”,最后推测“南中诸夷谓之场,每以卯丑酉日为市,故曰兔场牛场鸡场,岂用亥日为市,故谓之亥云”; 明代的《五杂俎》(1616)(卷三·地部)解释“西蜀谓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疟也,言间一作也”。据这些记载反映,“亥”原本为“痎”,乃古隔日循环发作的疟疾,而西南的农村集市并不发达,在古代也是隔日或几日依次循环,集市抑或多赶亥日(今曰猪街),于是自发地尚无确定通名的初级集市,便与“痎疟”或十二地支“纪日”之“亥”有了关联,于是集市通名便称之为“亥”,渐至普及,亦称“亥市”。唐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舟中示舍弟五十韵》诗曰“亥市鱼盐聚,神林鼓笛鸣”,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解释“蜀有痎市而间日一集”,明方以智《通雅》之“天文”卷载“亥音皆,言如痎疟间日一发也。讳痎,故曰亥市。一说以寅、申、巳、亥日集市俗称亥市”。至此,“亥”便由个别的专称(痎疟名或地支名)转变为一般集市的通名了。根据前面的分析,“亥”与“街”读音是相通的,但字义并不相同。“街”在《说文解字》 中指“四通道也”,即“四通八达的道路”,[25](P173)后有街巷之义,通道和街巷自古及今都是人员极易来往聚散之地,故后又引申为街市,“街”作为集市之称其实也很早,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之“不苟”中有记载“公孙枝徙,自敷于街”,这里的街即指集市。[26](P1200)至此,“亥”在指集市这一意义上便与“街”同,在山高谷深的西南地区,作为集市的地方与“通衢大道”的“街”意义更为密切,[注] 云南以街命名的集市多处于交通道路方便的地方,故集市与道路关系比较紧密,三岔路口或多条路汇集之地一般均会自发形成集市街,如果这类道路更改,就会在新的道路汇聚地重新形成所谓的“新街”。 而“亥”的常用意义更多的是纪日的地支用名,因此“街”最终代替“亥”成为蜀滇区域的集市通名,根据前面所述的文献记载,这种更替至迟在元代之前就已完成。据研究,“中原王朝在宋元之前,主要以川蜀为据点而治滇”,故云南在宋元之前,汉语和汉文化主要受川蜀一地的影响,集市称“街”追根溯源在当时应来自蜀语,但如今集市谓之“街”已几乎成为云南独有的称呼,明末清初李实《蜀语》记录“村市曰场,入市交易曰赶场”,又清刘献廷《广阳杂记》载“蜀谓之场,滇谓之街”,说明川蜀至迟在明晚集市就已称“场”并延至现在,原因就是四川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时期,因战争和天灾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于是自明初开始朝廷就迁湖广之民填实四川,受湖广方言文化的影响,现在川黔及湖广一带基本都称集市为“场”;而云南偏安一隅,历史上并未遭受大的战争,宋元之前的原著人口结构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故“街”(当时也或称“亥”)作为集市的称呼就在云南存留了下来,后自明代伊始,汉族大量移居云南并至迟在明末人口就已“超越所有土著的总和”,[27](P111)但原土著民族的分布仍基本维持原来的格局,这就非常有利于原有集市地名称呼的延续保留,虽然明代及之后,江南湖广籍移民带来了汉文化,但“客随主便”,云南原来集市称“街”的通名早已“先入为主”并得到当地族群的认同,故其便在后世一直得以延续并扩展至滇域全境。
(二)“街”是滇域特殊人文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知,“街”作为集市的通名,其在云南源远流长,作为词汇的意义来说,它尚保留着宋元及之前的历史层次。明代及之后,滇地的“街”并未因移民而被江南一带的“集”和湖广一带的“场”所替代,除民族分布的相对稳定保证其生命得以延续外,还与云南的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是滇域人文地理环境选择的结果。
但“街”和“亥”的读音在今天看来相去甚远,难以相通。街,中古音为古膎切,音韵地位是见佳开二平蟹;亥,中古音为胡改切,音韵地位为匣海开一上蟹,二者韵母虽同为“蟹”摄,但声母有异,即“街”属见母而“亥”属匣母,但见匣两母在古代的发音部位是相同的,即都属舌根音,区别主要在清浊(见清匣浊)。见匣这两个声母在古代可以通转,如“古”为见母,但由其充当声符的“胡”则属匣母,“亥”为匣母,但由其充当声符的“痎”则属见母。据此看来,古代“见匣母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之互通,殆无可疑”,[20](P21)故“街”和“亥”在古代通读见母k具有合理性;又,明代方以智在解释蜀集曰亥时,在其《通雅》之“天文”中专门指出“亥音皆”,而《中华字海》释“街”时明确标出“街音皆,两旁有房屋比较宽的道路”,[21](P480)两相对比,可说明“亥皆街”三字在当时是完全同音的。因为,“皆街”二字的古代音韵地位完全相同,即同属蟹摄开口二等平声皆韵见母,“皆”于今成都话中白读为“kai44”(与“街”同音),[22](P46)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成都话中“皆街”都只读“kai55”一个音,[23](P21)而云南至今“皆街”二字仍完全同音(如昆明话都读“kai44”)。[24](P21)据此可证,云南的“街”和蜀地作为集市的“亥”,在古代完全同音,故它们二者因读音相同(意义也相关,后述)而致以“街”替代“亥”便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
一般来说,“云南农村中最重要的贸易机构是街子”,[30](P195)坝区的街天也会呈现出人流上万的闹市,但在坝子仅占6%的云南来说这种可称“市”的街子实在有限;云南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滇域的街子绝大多数为乡下的山地街,人数一般不会太多,可街子却都能经久维持,因为对当地人来说,街子是“物品交换”不可或缺的场所。云南在古代是西南蛮荒之地,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又决定了滇域内部呈现出彼此相对隔绝的封闭、半封闭的人文环境,以致此地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对都较为落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除滇中昆明、曲靖,滇西保山、大理,滇南蒙自等坝子外,其他地方经济文化都显得比较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是其主要特点,因此缺乏发达的集市贸易活动,简单的日常需要通过顺“道”易物即可满足。据记载,分布于滇南绿春、金平和滇西南勐腊的苦聪人(属拉祜族),新中国成立前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食余之少量的家畜、家禽和猎物是他们用以与人交换的物品,“最初的交换场所是在靠近村寨的路上,东西放在路边,人躲在附近的草丛或树林中,易物双方互不见面”,[32](P252)路过之人如需,则随意在易物处“随意放下一些布匹、铁制生产工具或其他日用小百货,带走他们的山货,便完成了交换过程”,[33](P65)这种交易的方式也称“默市”, 涉及交易人数可少至两人,日期和地点持续并固定下来后,便会逐步形成时称的“草皮街”,如果后来予以专名称谓,便是今之街子。云南人口分散,日常苦于生计,沟通交流不能过于频繁,但物品的交换总是需要的,特别是盐、生产工具等物品需要交换而得,故需要固定日子和固定地点,交易时多为物物互换,各取所需,但不见得都是等价的,如过去苦聪人“一头二三十公斤的猪只能换两件旧衣服,三个松鼠干巴换半公两盐,一条狗换一件旧衣裳”[32](P252)等。云南街子上的交换虽然并不总是完全等价,但各取所需,都满足了自己的日常需要,故“斤斤计较”的商业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合这里的“街子”特点。因此,云南的乡下山地街,自古以来便重在交换各自所需的物品,以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盈利往往退居其次,故街子上的物品一般不会太多,赶街人数也有限,目的简单,大多晨聚午散,但其绝非可有可无,因街子对滇域山地人们的生活极为重要,它调节着当地物品所需的简单平衡。
(三)“街”的周期及其循环解释
滇域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平衡,即使在小范围之内也是如此,例如坝区要好于山区,平缓土山又好于陡峭山地,彼此相距甚至只有数里之地,可相对来说经济文化相差明显,这决定了集市在滇域出现的时间并不等同,有先有后,大小不一,这从集市的专名上也有着突出的体现。云南与时间相关的集市专名有35个,其中老街13个,新街22个,“老(旧)”和“新”体现了集市出现时间的先后关系,如滇东北鲁甸新街于“民国四年在此设街场,县长命名为福兴场,1950年定名新街”,[7](P71)其西巧家有老街;滇东南西畴有老街“原名鸡街,后集市迁今鸡街,将原鸡街名老街,以示区别”,[8](P45)同时西畴的兴街旁边还有老街,兴者本新也,后谐兴旺之意而改“兴街”,此外当地还有新马街和老马街,老马街为原马街,后集市迁至它地(即今新马街),故用 “新”和“老”以别之,富宁东边有宋代建成的老街,紧邻其半公里处有新街,新街为“1934年建村,较老街晚,故名”;[9](P58)又,滇中禄丰有旧街子,原为集市之地,后集市东移至距其4公里的碧城,故现称其为“旧街子”。云南“地无三尺平”,此说虽显夸张但却能形象说明云南的地势特点,崎岖不平、峡谷纵深,因自然条件差异较大,以致当地能形成的集市大小也不相同,集市专名“大”和“小”体现了这种现象。玉溪江川和普洱景东各有一个大街,江川大街原名虎街,后赶集人渐多街域扩大故改名大街,但因云南地域局限,故称街的专名为“大”的非常有限;而“小”符合云南的地域特点,易门、嵩明、文山、寻甸、峨山、禄丰、瑞丽、景洪等均有“小街”,如嵩明东部的小街于明末即成集市,其因地域狭窄而名之,文山小街也“因以前人家少,街道短小而得名”,[10](P164)临沧云县有“晓街”,“晓”者本“小”也,因其居县之东部乃破晓先出之地,后谐音更名为晓街。“新老大小”这类专名直白易懂,符合人们自然认知的心理特点。
民国及其之前,云南一般主要以十二天为基数循环确定街日,这体现了云南街日在元明而后民国之前的主要循环特点,究其原因与当地较为独特的地域纪日文化背景关系密切。清代及其之前,我国的纪日主要以天干地支纪日为主,1912年(辛亥革命次年)民国引进公历,但在农村地区依然习惯沿用传统的纪日法。天干地支纪日六十天一个轮回循环纪日,可这在云南并不盛行,因为在明代汉族大量进入云南之前,滇域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便有用十二兽历纪日的习惯,明代汉文化强势进入云南,天干地支纪日也被带入纪日,但地域偏僻、文化落后的当地民族很不习惯六十日一个循环的纪日方式,而十二地支则与当地的十二兽历纪日循环相符,当地民族更易于接受十二天为一个循环的纪日方式,而地支又与十二属相相对应,故移入滇域的汉民族也能接受,故纪日以十二日为基数的循环方式,便得到云南各民族的接纳而盛行。云南这种用十二地支配合十二属相(兽)来纪日,大概是后移入的“汉民族与彝语支民族大约在相互折衷、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终于确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纪日工具”,[35](P58)即是两种不同纪日方式相互妥协的结果。据统计,滇地在民国及其之前,近九成的集市是以十二天为基数进行循环的,这在一部分集市的命名上至今都还能体现出来,如大理寅街、牟定戌街、泸西午街铺和寻甸虎街、昌宁耇街、广南马街等集市的名称过去就是因以十二地支(属相)循环赶街而得。但明末清初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十二天一市的集日逐渐不能满足人们交换物品的需要,于是便出现集日折半的情况,即在原来十二天一市的基础上,折半为六天一市,当地俗称“空五赶六”,如寻甸的牛街和羊街均赶丑未日,昌宁的珠街(“珠”乃“猪”之雅化)赶亥巳日,耇街(“耇”为“狗”的雅化)赶戌辰日,广南的黑支果街赶酉卯日等。实际上,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云南集市已多发展为六天一街为常(个别集市后来甚至出现“空二赶三”的情况,如洱源新州街赶子午戌日,罗陋街和姜寅街赶申子辰日,千户营街赶寅午戌日)等,但当地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六日或三日纪日法,其仍以传统地支(属相)纪日的十二天为基数进行循环,所谓“六天一市”或“三天一市”的情况,只不过是在十二天这个地支(属相)纪日基数内的再折中循环罢了。
广西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与其他相关部门及产业、行业企业之间的协作、联动机制还未完全建立,比如与土地、水、电、管道燃气、银行、保险、医院、教育培训机构等部门及产业链上中下游各厂商之间,目前彼此只做到了部分协调,许多需要协调的领域还处于协商和探索阶段。
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云南的街日循环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即主要以七天为基数,采用星期作为主要的纪日方式,滇域这种街日循环基数的巨大变化,自有其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因素以及纪日文化的认同背景。星期以一周七日的方式循环纪日本是西方的产物,它早在明代便随传教士而逐渐进入中国,清末至民国初期得到官府的认同,要求学校和官府遵循星期工作休息循环纪日制度,但在民间的接纳和影响有限,故对当时的街日确实没有太大的影响,民国新增集市“仍按十二属相轮排为各集市日”。[36](P409)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农村集市开始萧条,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期间甚至一度停滞,1961年后在国家“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的政策引导下,集市又逐渐兴起,可好景不长,随后“文革”开始,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革”期间,云南农村集市街日由地方政府确定,如昌宁“规定全县统一同一天赶街(逢10赶街),各公社的社员只准许在本公社赶街,一段时间甚至禁止赶街”。[37](P252)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国家指导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城乡集市贸易方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36](P409)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将近30年期间,云南的集市基本上不能正常开展,集日确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从根本上打破了过去以十二天为基数的街日循环惯例,1979年以后集市恢复促进物品交流,但过去十二地支(属相)的短期纪日方式人们已较陌生,而以七天为基数的星期纪日方式此时已被大众接受,故过去的老街子和后来新开的街子,其集日确定便多以七天为基数进行循环了。滇域此类街日循环变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元谋的猴街在过去赶申日,但其于“1981年改为星期三赶集”,[38](P252)此地过去牛街赶丑日、羊街赶未日,后来都改赶星期日了;广南杨柳树街兴起于1991年,经村民与当地乡政府协调,直接定星期二为其集日。现如今,滇域近百分之七十的街日是以七天基数进行循环的,这一方面是人们适应星期纪日方式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新时期地方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因为相对较短的集日循环,更有利于促进商品的交换和流通。
滇域自明清以来,作为街日循环的补充,当地的部分街期还有以十天为基数进行循环的,这类循环方式主要以天干或旬日来纪日。据道光《威远厅志》记载,今景谷县附近当就有街子按天干排列,五天为一街期,如威远街赶戊癸日,抱母街、孟戛街和勐班街赶戊癸日,勐住街、茂篾街和忙卡街赶甲己日,骂木街赶乙庚日,翁烘街赶丁壬日,景谷这些街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中曾一度停止赶街,后也出现过改为七天一街的情况,但绝大多数在“1978年以后恢复传统街期”,[39](P338)滇地甚至还有以天干命名的街名,如保山隆阳区就有辛街(原名“丙辛街”,赶丙辛日)等。相对天干而言,旬日纪时更方便百姓记忆,上中下三旬构成一个月,能与农事搭配,在滇池西部的安宁、晋宁、楚雄及抚仙湖附近玉溪等地,较为集中地存在以一到十进行命名的集市,街日以十天为基数赶上中下旬相应的日子,如楚雄中山区的六街就赶农历一个月中的初六、十六、二十六这三天,街期就是以十天为一个循环。但需要注意的是,街期以十天为基数的循环方式在云南虽然一直存在,其占街日总数约为百分之五左右,它显然不是云南街日循环的主流类型。此外,也有以年为基数进行循环的,如大理和文山的“三月街”于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举行,楚雄的“秋街”在立秋举行,但这些“年街”更多的是一种节日庆祝类聚会,并不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故不属这里讨论的范畴。
这样看来,街期在云南循环主要以短而密为特征。所谓“短”,即街期一般不会超过十二天,改革开放后以七天为主。街期“密”是指在这个正常的循环时间内,随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需要,又会折半再次择定街期,如十二天折半赶两次街(即六天一街),七天一星期之内也可赶两次或三次街(如禄丰猫街、腰站街即在周三和周六两次赶街,羊街则在周六、周一和周日赶三次街),[40](P328)甚至有隔日为街的情况,这已是如今常市的雏形了。
结 语
集市在云南称“街”主要源自古蜀语的“亥(痎)”,周而复始的循环及因路而市的环境,加之古音相通,让它们彼此关联,以致最后以“街”代之,即滇域的集市名称经历了由“亥(痎)”到“街”的演变。可以说,“街”是集市在云南与这里特有的地理特点和人文经济方式相互选择和适应的结果。云南地理山高谷深,坝区有限,街子式的集市“不过是临时性的集合,本身只是一个地点,依着交通的方便而定”,[30](P263)故山“路”就成为早期集市的寄生点,街本义乃“四通之道路”,[41](P1525)关联相生而终成集市之名,路街市于此相宜焉。云南的街子多而密,街期短,规模有限。因这里的地域偏僻,域内山谷切割剧烈,居民彼此相对封闭,而物品交换又是客观需要,故街子分布较为密集,如广南的马街和老街相隔不过10公里路而已,也正因如此,集市重名和街日重复较多,可对当地世居之民来说并不会由此引起歧义或有不方便之嫌。街期短,一方面是指街期的循环短,一般多以五至七天循环为主;另一方面是指集日当天交换物品的时间有限,一般是晨聚午散,因为在滇域这种“隔山喊得应,望山走死马”的自然环境中,路上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商品交换多以油盐牲畜为主,交换的形式较为单一,故滇地街期短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商品交换形式密切相关。
云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街子只是人们交换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场所,它并不以经商为主要目的,故“不需要天天做买卖,所以这类集市场常是隔几天才有一次”。[30](P265)此外,相对于经商获利的其他集市来说,云南的街子还具有浓郁的人文氛围,它具有沟通人际感情、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当地很大一部分人赶街子并非为了交换或买卖物品,而是利用这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去会友聚亲,听点奇闻逸事,看点稀奇古怪,然后心满意足地各自返家,劳作如常,这就是当地所谓的“赶闲街”。因此,滇域的街子不仅是当地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交换场所,也是维系当地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一个纽带,对云南街子的功能及文化开展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地农村经济的历史发展脉络,为现在的地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借鉴,也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和理解滇域的人文地理文化内涵。
以表1所示问题为例,编码方式如图2所示,包括机器选择链和工序顺序链。解码时,为了尽可能将工序插入到对应机器上最早可行的时刻加工,从而减小最大完工时间,采用主动调度的解码方式[22]。
[参考文献]
[1]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 中科院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广南县人民政府.广南县地名志[Z].内部资料,1986.
[4]徐洪祖.徐霞客游记(第三卷·滇游日记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历书》编委会.2019年历书[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
[6]张明仙.珠江源头方言词汇与地域文化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
[7]鲁甸县志编委会.鲁甸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8]西畴县人民政府.西畴县地名志[Z].内部资料,1987.
[9]富宁县人民政府.富宁县地名志[Z].内部资料,1988.
[10]文山县人民政府.文山县地名志[Z].内部资料,1988.
[11]陆崇仁.巧家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
[12]牟成刚.云南汉语方言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J].学术探索,2018,(6).
[13]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简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4]杨永福.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
[15]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16]马曜.云南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17]杨应新.《白语本祖祭文》释读[J].民族语文,1992,(6).
[18]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9]牟成刚.西南官话音韵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0]王礼贤.见匣两母古通说[J].学术争鸣,1994,(1).
[21]冷玉龙.中华字海[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2]北京大学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
[23]杨时逢.四川方言调查报告[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
[24]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云南省志(卷五十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25]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7.
[26]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7]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8]明庆忠.云南地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29]李良品.历史时期贵州集市形成路径的类型学分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6).
[30]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31]傅东华.字源[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
[32]红河州民族志编写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
[33]张家荣.云南“街子”[J].西部大开发,2006,(11).
[34]韩大成.明代的集市[J].文史哲,1987,(6).
[35]张宁.云南十二兽地名初探[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4).
[36]祥云县志编委会.祥云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7]通海县史志编委会.通海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38]元谋县志编委会.元谋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9]景谷县志编委会.景谷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
[40]禄丰县志编委会.禄丰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41]辞源修订组.辞源[M].成都:商务印书馆,1993.
Study on the Place Name Characteristics of Yunnan Fairs and Their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MOU Cheng-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99, Yunnan, China)
Abstract :Fair is mainly called “Jie” in Yunnan, which is a word of quit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ccording to our textual research, it originated from the ancient Sichuan dialect “Hai”, which is recurrent malaria and connected with the “Jie” in the sense of circulation. In Yunnan, fairs are mainly formed by road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Jie”. The ancient sounds of “Hai” and “Jie” are the same, and later they were named “Jie”. Yunnan fairs with “Jie” as its common name appeared in Yuan Dynasty at the latest, and it had been flourishing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roper name is characterized by naturalness, intuition, primitiveness, nationality and repetition. The gathering-day cycle of fairs in Yunnan area was mainly determined by Terrestrial Branches (Shengxiao) befo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by twelve days as the bas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treet days were mainly determined by weeks and circulated by seven days, quite short and dense in its period. The “Jie” is a special geographical appellation and evolution type produced by the bazaar adapting to Yunnan’s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t has special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of Yunnan region.
Key words :Yunnan; fair; place name; connotation; study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规划项目(SKPJ201829)
作者简介: 牟成刚(1980—),男(彝族),云南广南人,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汉语方言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72.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5-0096-10
〔责任编辑:黎 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