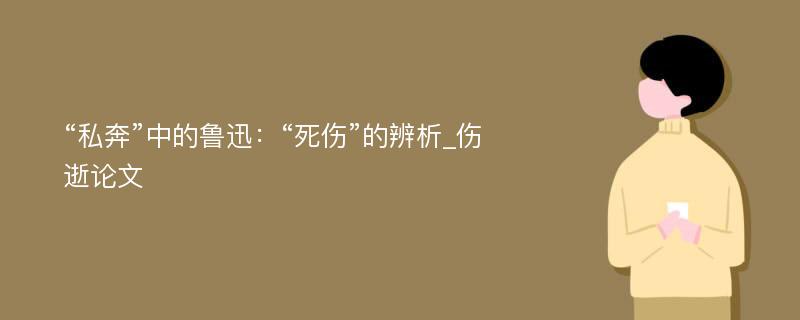
“私奔”套中的鲁迅:《伤逝》之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0054-07
《伤逝》是鲁迅写的惟一一部有关爱情婚姻家庭悲剧的小说。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妇女问题由来已久的关注,同时还是鲁迅对此问题所做的思考、探索与努力有了新的收获与起步的标志。它“不但是那个时代斗争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鲁迅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面镜子。”[1] 24由此,《伤逝》一直是人们研究与探讨鲁迅女性观的一个重要范本。对此范本的解读者与研究者层出不穷,代表性的旧论新见概而述之有二:一是直接引用小说《伤逝》中男主角涓生所表述的思想言论,如经济基础论、爱情更新论等,再辅以鲁迅本人观点“社会解放论”,以铁证鲁迅之思想本源;① 二是把鲁迅现实婚恋关系,拿来实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与关系,如子君形象为“同居前许广平同居后朱安”论,甚而还有指说是写另一个和鲁迅有情感关系的女学生许羡苏的,以此坐实鲁迅因对在自己生命中出现的这三个有特殊关系的女人,或出于不安,或出于内疚,或出于婚后恐惧症等复杂微妙之心理,乃作此文以洗白自己对原配夫人的冷漠,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警示新人(指许、苏)切勿重蹈旧辙,暗示要对旧人(指朱安)负责到底等等。② 把小说人物等同生活原型的阐释方法,显然没有超越语言内之物,从而无法统观并释读出文本所蕴含的语言外之物——话语类型、意识形态乃至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结构与背景,既无法真正理解作品的意义问题,更无法反观意义的产生方式。而这正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文本需要人们解读与挖掘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摆脱“小说者说”对文本研究的强大影响,从文本自身内在结构分析出发,就会发现《伤逝》在整体叙事上,在人物的塑造与情节铺陈中,存在着明显的叙事破绽与逻辑缝隙。如从女主人公子君的形象塑造上来看,子君的思想、性格到言行、做派,在与男主人公涓生同居前后都出现了反差巨大、截然不同、判若二人的断裂与不统一。同居前的子君,自信、勇敢、有理想,追求新思想,渴望新生活,充满朝气;她可以大无畏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可以在讥笑、猥亵和轻蔑的世俗眼光中,目不斜视地、镇静地、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地骄傲来去;她让处于寂静、空虚、焦躁中的男人公涓生充满期待,并因为她的来临而骤然生动起来。可是,“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的修养;这散发着强烈自我性、革命性、先锋性的精神气质;这比涓生“还透澈,坚强得多”的性格,却在同居后倏然无存,真可谓来有踪则去无影。从后来的这个子君形象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麻木不仁,没有思想,不会表达,更没有追求,只会沉默着煮饭养狗喂鸡的旧式妇女,看不出任何经过现代教育的新女性痕迹,她让涓生感到沮丧、厌恶甚而绝望。如果说人们确实看到听到的只有男主角涓生单方面的喋喋不休——它一方面将子君罩严在他的话语下成为一个沉默的影子一直到死;一方面把作者哀她不幸,怒她不争的心态,表现得路人皆知——只是出于“手记”这种文本形式的特有效果,那么涓生在求宽恕的语义下,充满贬损对方的语气;在自我忏悔的语表下,充塞训导对方的语意,则是任何情节性变因与文本形式都无法遮掩的了。由此悖反语言行为而产生了言不由衷的效果。正是这种言不由衷的“虚伪”感,给叙事者极力要在文本中营造的真诚性语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与割裂;而这种语境的割裂与矛盾,则直接带给叙事本身无法克服的悖谬感;而叙事的悖谬感则直接带给《伤逝》疑义的存在与解读的迷惑性。
笔者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对《伤逝》疑义的指出,并不是怀疑其作为鲁迅最具代表性、最具社会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研究价值的作品之一的身份,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些疑义的存在,才使《伤逝》隐含着丰厚的远不止于与故事表层因素相关联的那些信息,同时,它也才真正挑战了人们的解读与认知。如果人们能够正视《伤逝》叙事中明显存在的这些逻辑破绽与意图悖谬,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势必会被提出:作为一个具有思想家、五四新文化旗手、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作者等多重精英身份的鲁迅,为何会在这样一个短篇小制中,留下诸多显而易见的叙事缺陷?这个事实本身蕴含了什么,说明了什么,意味了什么?小说艺术大师米兰·昆德拉曾说过:“每一时代的小说都和自我之谜有关。”[2] 22但现在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如果一个时代的小说之谜呢,它又会与什么有关?它显然蕴藏着超乎研究作者与其“语言内之物”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伤逝》的叙事之谜,才真正使它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绝不多见的研究范本。
从《伤逝》故事层面上来看,它的叙事是通过现代个性与妇女解放双重话语背景下的“私奔”行为来实现的。私奔,“旧时指女子私自投奔所爱的人,或跟他一起逃走。”[3] 1085在此释义的基础上,结合从“旧时”一直绵延于今的私奔行为特征,我们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定义:私奔可指一对男女两情相悦,却为权势或环境所不容,私下从原有的生活环境与秩序中逃离的行为。据此,我们还可归纳出“私奔”的二点要义:第一,私奔在古典情境中特指女性所发生的行为;第二,私奔成为婚恋自主的代名词,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下具有叛逆性与革命性。
“私奔”作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反常事件,在满足人们反规心理与破禁欲望上,还兼具有相当的戏剧性。由此,“私奔”才会成为古典文学中的叙事模式,广受创作者与受众的青睐与欣赏。饶有意味的是,“私奔”以明显构成对封建宗法制与道德礼教反叛与对抗的行为,却在封建社会中以文学叙事的形态大行其道,这多少反映了封建社会,对“私奔”行为貌似壁垒森严内里却稀松平常的态度。如果我们对这种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做深一步探究的话,会发现它的逻辑成因在于:“私奔”虽然反叛的是封建礼教的清规戒律,追求的是婚恋自主,但是,这种叛逆与反抗行为,也仅仅是起于情欲而止于情欲。曹雪芹深谙其秘,在《红楼梦》中让贾母专门上演了一出针对“私奔”模式的故事《凤求鸾》的“掰谎记”:“编这样书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贵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想着得一个佳人才好,所以编出来取乐儿。”[4] 684贾母的“掰谎”,一针见血,一是挑明了“私奔”模式的出处:它只不过是出自如此一干男人的移情所致;二是挑明了让女性做出此叛逆行为的始作俑者是男性,男为主动,女为被动。前者之因决定了“私奔”起于情欲而止于情欲的特质;后者之因形成了“私奔”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性别关系特质。
可见,“私奔”所含有的叛逆性、革命性元素,充其量只是表达出男性潜意识里最希望得到的贞洁女人,往自己性开放的欲求奔进了一步而已。女性私奔,在现实中只会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满足男性性欲望的另类行为;在文学叙事中只会在更大程面上成为男性欲望化的虚构对象。因此,古典叙事通常在男女主角完成“私奔”的反常出轨行为后,便就照常入了轨,都做回正常的贤夫良妇去,这是“私奔”修成正果的喜剧版。而在悲剧版中,则是以女子痴情献身,男子忘恩负义,构成一个始乱终弃的叙事。悲剧版表面看上去似在颂扬或同情女子,批判或贬斥男子,但其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其实都不免含有对女性的训诫在内:淫奔女子的下场有多么可悲,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关系是多么不可靠。可见,“私奔”模式的确并非如我们以往所认知的那样,它具有多大的叛逆性与革命性。也许,在客观上它的确具有反父权宗法制之效应,但在主观上可以说是毫无反男权之意图。换而言之,作为女性在封建社会里最具叛逆性革命性的表征,“私奔”模式其实并不构成对男权社会秩序的任何侵犯与挑战,并不具有反性别歧视或压迫的内涵,这才是“私奔”这个有悖封建伦理、伤风败俗大逆不道的叙事,能在封建社会中得到最广泛的欣赏、捧场与流传的潜在原因。否则,有关“私奔”的故事与情节,也不会层出不穷地在墙头马上、柳毅传书、张生煮海、牡丹亭、西厢记、陈三五娘、唐伯虎点秋香、追鱼等等诸如此类的文本中再现、演绎与繁衍,成为古典文学中最令人难忘、最喜闻乐见、最脍炙人口的情景。
以反五千年封建之专制文化,倡导民主科学之现代文化为标志的五四运动,使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个性解放、男女平权、婚恋自主等一系列表征现代文明观念的思想,促使中国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性别关系即是其中之一。对这一时期或以这一时期题材或背景而创作的小说文本进行系统考察,可以发现出现于中的一个相当明显的解放模式,而这个模式是与我们耳熟能详的性别模式联结在一起的:即代表五四新文化的先进人物,把深受旧文化荼毒的、向往新生活的人物从禁锢她的环境中解救出来,前者清一色为男性,后者清一色为女性。因此,二者之间本因人生拯救之命题而生成的社会关系,不得不被揉进了因婚恋解放命题而构成的性别关系之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版的私奔模式。换而言之,这个模式之所以还被命名为“私奔”,正是因为它所含有与古典私奔相类似的、并不因现代变革而改变的既定性别关系与情爱内容,男性在其中成为身兼女性人生与婚恋双重解放的启蒙者、解救者。若析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出于性别角色差异的历史定式,女性对男性从精神到物质,从政治到经济,从心理到体能的全方位依附,使得现代解放模式中的性别关系也概莫能外;其二是出于社会心理的传统定势,即只有婚恋关系才会使这种解救行为,多少吻合了在伦理层面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这个定式注定了他们二者构成婚恋关系的同时,又构成解救与被解救的关系。反之,这个关系必然也蕴含着这样一种定势:是否具有古典式的婚恋关系也决定了现代解救行为的能否实施与实现。
总之,“私奔”模式中蕴含的大快人心的叛逆情结与深入人心的戏剧化元素,加上五四时代社会条件对女性的局限,使得以五四为背景的女性解放——先进男性启蒙落后女性,解救苦难女性的过程,在现代小说叙事中沿袭成几同自古以来情哥哥与情妹妹私奔的模式,不管是先救后爱式还是先爱后救式。
把鲁迅小说《伤逝》置放在上述所论中进行参照比对,可见它具有内含古典元素的中国现代版“私奔”之思想特质与叙事特征。首先它完全吻合“私奔”模式中的“情节”元素:一个女子因与一个男子私下相好而不见容于家长与世俗,女子相从男子离家出走。
其二,它完全吻合“私奔”模式中的“起于情欲而止于情欲的”婚恋元素:女主角子君之所以能“私奔”,是因为她与男主角的婚恋关系,因此她才可能那么大无畏地、目不旁视地从家中昂然出走。当这种关系一旦消失,她轻者胆怯懦弱苟且偷生,重者则缩回旧家庭走向死路。这也即是子君在同居前强烈标榜的自我性、革命性、先锋性的精神气质,为什么会在同居后倏然无存,人物性格、性情、修养、言行出现截然断裂,判若二人的叙事原因。与之相佐证的还有巴金的《家》。《家》中的三少爷觉慧与丫环鸣凤就是因为有恋情关系,鸣凤才寄希望于三少爷对自己的解救,岂知三少爷因忙中疏忽,便使原可以“私奔”来解决的解救未能实施,从而导致鸣风一筹莫展走向绝路。
这个模式还蕴含着另一种形态的必然:即由解救关系发展成为婚恋关系,它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男女婚恋之于现代“私奔”模式乃绝不可少的情形。当时男性性别身份与解救女性者社会身份的重合,解救者与被救者性别身份与婚恋关系的重合,反映出当时的相关情况:五四时期反封建父权制/家长制,倡导妇女解放之最为见效的社会性成果,似乎莫过于青年们所争取到的婚恋自由。如果从小说叙事层面来分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婚恋自由”这个活跃于五四时期最富有时代表征与新文化话语的新鲜事物,其实并非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全然具有现代性,准确地说,它应该是古典式私奔传统与现代个性解放理念相结合产物。《伤逝》女主角子君说着“我是我自己的”,走在向古典“私奔”去的道路上,就是这个结合特质的经典写照。
其三,它完全吻合“私奔”模式中悲剧版的“始乱终弃”的元素。与涓生相好而义无反顾地离家私奔的子君,后来却为涓生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弃,不得已悄然潜回娘家后自行消亡,犹如古典私奔叙事中的李甲之于杜十娘。只是现代版的涓生良心未泯,所以鲁迅一可以不用自己讨厌的因果报应说来结局涓生,二正可因此而生发出通常被人们解读为忏悔、自省与辩白三兼功效的“手记”式文本。
其四,基于上述三者的吻合,它必然吻合“私奔”模式中最为核心的特质,即反父权但决不反男权。对此最明显的鉴别是:无论是修成正果的喜剧版,还是始乱终弃的悲剧版,传统的性别权力与性别秩序在其间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女性身份与角色地位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女性始终被动、无能、缺乏主体性。在此情形下,女性追求婚恋自主的勇敢私奔行为,的确很容易演变为只不过是男性情史中一段浪漫而刺激的插曲而已。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现实中,就已成为反对抑或怀疑女性解放者的一个口实:把大批青年女子解放到社会上来,难道不是在为男性更方便地玩弄女性提供猎物吗?在废弃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后,她们只会更无设防地被男性所勾引,更轻易地做下淫奔苟且之事。而当时跑出家门,脱离家庭支持后的新女性,或出于志同道合,或出于生活所逼,与男性同居成风的事实,也为此类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革命女作家冯铿的作品《一团肉》,驳斥与辩争的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把新女性看作是异性玩具与享用物的“一团像嫩鸡的香艳可口的肉”,“丝毫没有一个‘人’这动物所需要的灵魂的”的男性观点。[5] 360-362
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伤逝》,男主角涓生所具有的性别与话语强势地位,便显得天经地义:忏悔式的修辞结构本身就意味着他在这个“始乱终弃”的私奔故事中,曾占有的主动权与决定权。私奔同居后的子君,扮演的就是一个不思进取,不懂爱情与人生要义,只懂煮饭、吃饭、饲油鸡、叭儿狗,没有思想、声音与灵魂的庸俗主妇,行尸走肉。可想而知,在这样一个于主流价值观中毫无价值的女性形象面前,貌似忏悔者的涓生,当然“只能”拥有实质上的大大优等于子君的思想境界与话语环境。而正是这关键的一点,使得叙事无可避免地陷入最大的悖谬之中:他虽以忏悔者求宽恕的语调起笔,却掩盖不住他满纸居高临下的视角与启蒙者的语气,他是她的精神导师与人生指南,是她生活方式与存在价值的评判者,是她生命与生活质量的掌控者、生死命运的主宰者。自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那个时候开始,他对她连贬带损近乎讥讽的说教独白,事不关己近乎冷漠的评头论足,就充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情节发展中。《伤逝》文本中最脍炙人口的经典格言,如“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我那时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等等。于是,“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当然就顺理成章了。[6] 110-131不过,这种说法实非起于涓生,它只是古代书生李甲们对杜十娘们的现代汉语版,它只不过是再次以经典的形式重现了“私奔”悲剧版中男性人物惯常的想法与做法,鲁迅的《伤逝》也逃不出它的复制。
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女性解放,难道真的就是以这样的“私奔”形态作为标志与结果吗?若果真如此,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中国妇女解放的真正程度与质量。这种怀疑,实际上已被置身当时的一些女作家们,直接反映在她们的文学叙事中。她们曾经也把“私奔”当作奔向解放之路,如沉樱的《某少女》,因此,她们也无可避免地要面对“私奔”以后的故事。因此,我们才拥有可与《伤逝》文本构成比照的来自女作家的叙事:在鲁迅笔下那位被男主角稠密话语笼罩下,真如一团“鲜嫩而没有灵魂的肉”的女性,大肆活跃在她们的文本中,从剧烈的内心感受到不停的思索:“神秘的热烈的爱,感到平淡了……如轮般思想的轮子,早又开始转动……人生的大问题结婚算是解决了,但人决不是如此单纯,除了这个大问题,更有其他的大问题呢……眼前之局,味同嚼蜡,这胜利以后的情形何堪深说。”[7] 224-235她们并不沉溺于私情生活,尤其注意到小家庭之外的“一切,都是在继续地变迁着”。[8] 人们可以从她们自己的叙事中,发现女性版的“私奔”与古典和现代一脉相承的男性版“私奔”,有着本质上与目的上的迥异:她们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不只是为了满足对自我婚恋的支配,更多的是获得对自我生命与人生的支配。因此,尽管她们也为婚恋自由而私奔,但私奔胜利以后依旧存在于其中的、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的性别关系,其实已不能令她们安之若素,甘之若饴。受“我是我自己”思想洗礼后的新女性,根本不可能如他们所想像与期许的那样,重新成为男人的附属品,重新回到愚昧的失去自我的旧女性形象中去。婚前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个性,解放的追求,现代教育的素养,并不会在婚后她们的内心深处荡然无存。也许只有女作家们,才会真实地知道从前那位叛逆的大无畏的少女,在成为少妇后的她们身上该留有怎样的痕迹:她们是如此不安分于回到旧有秩序与正常轨道中的生活,她们失望,焦虑,困惑,思索;她们的私奔也许的确会起于婚恋,但已绝不会止于婚恋,这是现代女性私奔比之古典的不同之处。因此,私奔胜利以后困惑与质疑的小说,才会被现代女作家们大肆书写。
现在,我们把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古典版“私奔”,与鲁迅为代表的含有古典元素的现代版“私奔”,与庐隐为代表的女性版放在一起比较,就很容易看出其中本质性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时代、尤其是性别视角的关系。古典版中的女主角,通常在私奔胜利后即回到传统既定秩序与角色中做贤妻良母,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鲁迅的现代版看到他们私奔后“从此生活得并不幸福”,但却在无法摆脱“始乱终弃”的叙事套路的同时,也延续着强大的男性视角与男性声音,他让曾经大无畏的女性退缩回去。庐隐式女性版突显的是女性的视角与声音,她让沉默的子君发言:她并不是他们笔下的木偶女,她们一旦发现私奔胜利后事与愿违,“幸福生活并未从此开始”时,她们新一轮的思考与求索便势在必然,同时,它还表明,这种独有的内心感受与生命体验,是一直处于引领私奔位置上的男性精英无法体验与代言的,甚至也是无法理解与沟通的,正如鲁迅笔下涓生之于子君的隔膜形同路人。这种情状甚至促成了她们在叙事中自话自说的倾诉式文风,如庐隐《海滨故人》、《胜利以后》、《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冯沅君的《春痕》;绿漪的《鸽儿的通信》;沉樱的《某少女》、《生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有意思的是,鲁迅虽然也用了当时男作家相对较少使用的“手记”式自诉文体,但二者之间却有着微妙而显明的不同:《伤逝》充满着男主角对女主角的主观性评判与训导,而与之相比照的如沉樱《爱情的开始》和《喜筵之后》等,表现的问题相类似,但更多的是对双方争议的言语、观点、场景的客观性再现,没有让男主角成为她们叙事中沉默的影子。这让我们想起华莱士·马丁的发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依靠他们所读之书中的成规来解释世界。”[19] 75把这条定律放在性别分析的层面中来看,它的确很符合男性作家的创作,而一些女作家的创作则可以借用这条定律来如此表述:她们更依靠自己的感受与体验解释世界,包括两性关系。
现代私奔模式的叙事,在体现当时女性解放形态的同时,也潜伏着自古以来性别权力与秩序派生此中的负面效应,女作家在此叙事中呈现出的主动式的反思与反诘,意味着她们对这个模式破解的开始:她们一旦意识到“私奔”并非可以实现她们为之叛逆与革命的目的,实现她们对自古以来性别困境的突破,那么私奔的神话将不会再在现实与虚构中被她们继续复写。这也许才是现代女性意识在私奔叙事模式中体现出来的一大突破,是现代私奔模式真正具有现代性与革命性的地方。
其实,这也是笔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一种可供上述论述参照的史迹:一种从近现代起,被冰心、陈衡哲、白薇、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直至张爱玲、苏青等等一大批在现代文学史上成名成家的女性之人生经历所佐证的事实(这还不包括那些进入自然科学领域里成名成家的新女性名单):她们是通过现代教育的途径,而且绝大多数还是得益于女性长辈的鼎力相助与悉心指引,从而完成个人解放,顺利地进入社会,成功地担当起社会角色的。但饶有意味并发人深省的也正在这里:哪怕这些事实都曾不断地出现在纪实性的散文与其他实录性文体中,但它从来也没能成为虚构类作品中的叙事模式。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至少说明了这么一个事实:性政治观决定了人们对叙事模式的好恶与取舍,它影响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大多数男性作家们对现实、尤其是对女性形象与性别关系,进行了有选择性的想像与塑造,甚至干脆印证了结构主义批评家的这个著名判断:“所有故事都由成规和想像形成”,小说并非是“生活的如实表现”[9] 15,鲁迅的小说似也不例外。
综合上述的参照比对与分析后,我们多少可以接近本命题的核心所在并做出相应判断:《伤逝》为何会出现言不由衷的叙事效果,如果鲁迅意不在构成对涓生的反讽,那么它只有一种可能:鲁迅虽已意识到私奔胜利后存在的问题,也极力要找出这个有关女性解放的问题所在,但男性的立场、视角、思维成规与想像方式,使之无法觉察到自古以来的性政治权力,在私奔模式中的存在与作用,使之不能不在此文本中留下这样的叙事破绽与意图悖谬。《伤逝》真实地体现了处于“私奔”套中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男性文化精英们所具有的性政治观的成色与所到达的限度,并泄露出这种限度使得他们所创作的同类小说,并未到达同时代一些女作家叙事深度的事实。也由此,《伤逝》文本才具有了如此特殊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而在于它是这样表现了。它以文学的形式,保存并提供了为我们解读此文本语言外之物的可能——为我们认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男性精英阶层的性政治观、话语类型,两性关系史与现代女性解放史,提供了独具价值的范本。
注释:
①此类观点鲁迅在其杂文《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同文书店1934年版、《娜拉走后怎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1924年第六期)等文章中都有论及。
②参见陈留生《〈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大学报》2003第2期)、李允经《婚恋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1、2期合刊)、宗先鸿《〈伤逝〉人物原型的变形艺术》(《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第6期)、张江艳《从〈伤逝〉看鲁迅的妇女观》(《新疆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