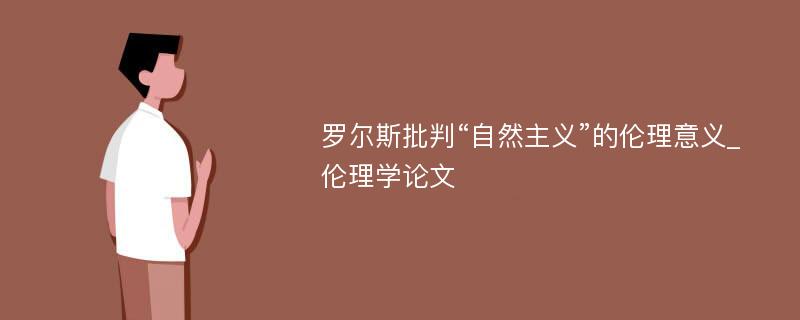
青年罗尔斯批评“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伦理学论文,涵义论文,批评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尔斯是美国乃至西方20世纪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之一,其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有关社会正义、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国际法的哲学理论。他的著作到前两年已基本出齐,而中译本的出版也接近完成。①罗尔斯的思想并没有因世纪的转折而过时,对于在经济上已然飞速崛起,而国内体制与国际环境的问题却显得越来越突出的中国来说,现在是需要更深入和全面研究他的时候。
罗尔斯的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种义务论的观点,他这种观点的最初形成,在200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论罪与信的涵义》中可见端倪。这本书由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编辑整理,其中收集了两篇罗尔斯自己撰写的文字:主要一篇是他1942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论罪与信的涵义》;还有一篇是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电脑中发现的写于1997年的文章《我的宗教观》。另外还有两篇解释和引导性的文章,一篇是科恩与内格尔所写的《导论》,另一篇是亚当斯所写的《青年罗尔斯的神学伦理学及其背景》。
罗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是有其特殊和自足的价值的,尤其是他的学士论文,它不仅可以使我们窥见罗尔斯后来隐晦的宗教思想(即便它们不再直接出现在他后来的主要著作中,也还是会在某种程度上在其后继续起作用),还能够让我们发现有些基本的思想原则其实在他大学期间就已确立。大略地说,罗尔斯在这一期间思想的特殊意义和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通过对自然关系与人格关系的区分,通过对居传统主流的“自然主义伦理学”的批判,明确而坚定地确立了一种贯穿其终身的反对目的论、赞成义务论的思想原则。第二,他强调共同体、强调社会,围绕着共同体来定义“罪”与“信”,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始终执着于探讨社会和政治的正义的开端,尤其是他对“自我中心主义”的犀利批判,不仅反映了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深刻反省,直到今天也仍有其突出的价值和意义。第三,涉及他的精神信仰转折最重要的方面,自然是二战结束时他放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以后不再联系于上帝来讨论道德与政治哲学,使伦理学与宗教分离;而这种转折又是因人间正义问题引起的。而直到今天,上帝与正义、信仰与社会的问题也仍然是困扰我们的思想和精神的重要难题。不过,本文试图主要就罗尔斯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所包含的伦理学涵义来展开分析和评述。
一、基本预设
就像罗尔斯后来在《正义论》中也仍然承认其理论有一些直觉性的确信一样,他在本科毕业论文中也认为,每一种神学和哲学理论似乎都带有某种基本的预设来研究经验,而他也不讳言,他的这篇论文也有四个基本的前提预设,这四个作为前提的直觉性确信是: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存在着上帝,而且这个上帝就是《圣经》中显示的、耶稣基督的上帝。其次是存在着人格,他说这种人格或许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世界上存在着被我们称为人格的东西,也存在着具有这种人格的人。”②第三个基本预设是共同体的存在。而这一“共同体”的概念也包含了“人格”这一概念。共同体也就是具有人格的共同体。“除非我们具有人格,否则我们就没有共同体;而且,除非我们拥有共同体,否则我们也不具有人格。”(第112页)个体的人只有生活于共同体之中才能成其为人。第四个基本预设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与在质的方面与人格的和公共的领域截然不同的自然界。
上面的这四个预设——上帝、人格、共同体与自然——以及相互关系也就是罗尔斯这篇论文的基本概念,构成了他思想的主要范畴。他在此文中所要论述的“罪”与“信”的涵义围绕着这四个概念展开。我们或可如此概括罗尔斯此文的基本思想(可能也包括了一些引申):上帝是根源,上帝创造自然万物,包括创造了人。人具有人格,这意味着人必须和必定是要采取共同体的生存方式,人和共同体几乎可以说是等同的,说到人也就是说到共同体,我们不能设想还有非共同体的人格存在方式,但共同体又的确不是排斥个人和个性的。人类的共同体还必然要包括上帝,这不仅是说人源出于上帝,而且是说他始终要通过信仰和皈依与上帝联为一体。“罪”就是对这一神圣的共同体的否弃,而“信”就是对这一神圣的共同体的承认和复归。如果再将自然包括进来,同时将人与共同体理解为一的话,这似乎是一个神圣的上帝、人与自然的“三位一体”。上帝最高,自然最广,似乎人是某种中间物,但人也就是“我们”,人是具有人格的,是可以结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是上帝的造物中唯一可以努力与上帝沟通和契合的,也是可以努力改善自身和共同体的。这种努力的主动权是掌握在具有人格的我们的手里。“自然”也自然是人所需要的。但人不可将他与自然物的关系搬到与上帝、与人的关系上来,他不能将他人视作工具手段,甚至也不能将上帝视为欲求的最高对象,这里要排斥一种目的论的思维——这种思维被罗尔斯视作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伦理学”而予以拒斥。而在我看来,罗尔斯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作为现代伦理学的两大派别之一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ies)的批判,他由此确立了伦理学的另一大派别——义务论(Deontological theories)的立场并坚持终身。
二、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所奠定的反目的论立场
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自然可以批评青年罗尔斯这些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内容,比如,在生态伦理学看来,以“人格”而非以“生命”为中心来谈论“共同体”,可能会有过于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嫌等。不过,我在这里所关心的主要是青年罗尔斯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所凸显出来的伦理学意义。
在罗尔斯看来,相应于他所说的基本预设,也存在着三种基本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和公共关系;二是人与物的自然关系;三是物与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最重要和基本的区分是人格关系(Personal relations)与自然关系(Natural relations)。罗尔斯认为很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包括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这样的人物,都将自然关系与人格关系相混淆,将人对物的欲求关系推广到人对人的关系上来,因而犯有一种“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错误。③
罗尔斯的这一区分及批判所表现的反目的论立场,鲜明地表现于他用“自然关系”是想标识这一种“经验领域”:一个人在其中欲望、争取、想往或需求某一对象或某一具体过程。这些“活动”可被描述成欲望、想往或争取这类行为。而他用“人格关系”是想标识另一种“经验领域”:一个人在其中力图与另一人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或达到一种确定的和谐。他还认为,为了表明自然本身并非恶的而是善的,罪并非源于欲望和欲求而是来自于灵魂的堕落,区分出自然关系和人际关系也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为了理解罪、信仰和恩典,我们就必须做出这种基本的区分(第115页)。
青年罗尔斯对“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伦理学”的批判,实际也是对目的论的批判。而这种目的论在传统社会中是居于伦理学主流地位的,尤其是目的论中有神论的或无神论的完善论或至善论(Perfectionism)。或许批评的对象总是从更邻近自己的开始,批评更切要的是对自己观点与接近观点的区分,青年罗尔斯也是如此,对于传统伦理学另一目的论的派别——快乐主义的着墨并不多,甚至对无神论的完善论的批评也不是他的重点,他的主要批评对象反而是有神论的完善论。由于他写的是一篇有所立的神学伦理学的论文,因此他更注意与神学目的论、神学完善论的区分。罗尔斯其时虽然浸染于神学,但实际是有点反对神学中的主流的,或至少是和哲学结合、或受哲学影响的那部分主流。他不同意奥古斯丁和阿奎那,认为他们还是受到了古典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太大影响,他认为这种结合并不成功,这种影响必须摆脱。年轻的罗尔斯以他后来行文中不易见到的年轻人的特有锐气说:“一盎司的《圣经》就抵得上一磅(或者一吨)的亚里士多德。”(第107页)
罗尔斯这里所理解的“自然主义”并非“唯物主义”,而是指用自然主义术语来构建宇宙的任一观点。这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神学就都是“自然主义”的了(第119页)。他认为,“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无论是在柏拉图或奥古斯丁那里,还是在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那里,都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将欲望(爱)导向它的合理目标或目的(第120页);所谓的“好的生活”(他甚至不是很愿意使用这一称谓或如此被界定的“善”),并不在于寻求任何对象,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牵涉人际关系的问题。他认为,柏拉图等都认同“善”等同于某个对象,同时又都指出了一个显见的事实:人们实际上并不追求该对象,或者说他们没有能力追求它。这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试图诉诸自然的教育和驯化来作为一种矫正的方式;而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怀揣着对人性的悲观的看法和莫高的期许,认为他们有责任祈求神的驯化和启示。但总体而言,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间只存在程度的差别(第162—163页)。
即便是这些人中最为神学化、最强调信仰精神的奥古斯丁,在那时年轻而虔诚的罗尔斯看来,似乎也还不足够神学化和信仰化。他甚至认为奥古斯丁的基本思想实质上始终是希腊化的,说他之所以接受自然主义的伦理学,是因为在他看来美德就是自然欲望寻求某个具体的对象,并且拥有完美禀赋的人会把这个善当作适于自己的目的来追求。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的不同在于柏拉图相信人有能力实现自我拯救,奥古斯丁则否认这一点,认为人还需要上帝的恩典(第170页)。但就他们都将善或至善视作一种人欲望的对象或目标,并以此来确定人们行为的标准而言,他们都是目的论的。
为此,罗尔斯甚至反对将“上帝”作为人欲望的对象。他说:“对笔者而言,把上帝作为一个对象来欲求纯属不敬,它是在以一种巧妙甚至更危险的形式返归异端崇拜。”故而,即便是把“上帝说成是所有对象中最美的、最令人满意的、最让人欲求的对象”,也还是在“犯罪”(第182页)。这犯罪和迷误的性质就在于:“如果我们将上帝设想为欲望的另一个对象,那么我们就犯了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就把袍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了。”(第121页)亦即,这错误的缘由就是将人与自然物的关系——那的确是欲望主体与欲望目标的关系——扩展泛化到非自然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将整个人的世界都变成了一个“扩展的自然宇宙”。
三、“自然宇宙”与“扩展的自然宇宙”
罗尔斯的“自然宇宙”指的是这样一种世界,其中所有的关系都以自然的术语来构想,而如果整个宇宙都被“自然主义化”,结果就是失去共同体和人格,当然也包括失去上帝的真正本质。但上帝不仅仅是一个最可欲的完满对象,人格和共同体也不能用自然主义的话语来解释。所以,“被扩展的自然宇宙”就排除了人格、共同体和上帝,尽管它可能借用了祂的名义(第119—120页)。
不过,我们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罗尔斯尽管否定这种“被扩展的自然宇宙”,但他并不否定“自然”本身,他甚至说要为自然界辩护,也包括要为不可或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辩护,他说自然宇宙本身是善的而非恶的,世间的恶并非源于自然界本身(第179页)。他认为,人类确实天生具有欲求,并具有对饮食、美、真理,进而对自然万物这个整体的欲望;上述哲学家的错误之处并不在于接受自然,而在于将自然关系扩展至包含宇宙中的所有关系(第121页)。
所以,我们看到,青年罗尔斯反对自然主义实际是在反对目的论,所谓“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实际是指“目的论的伦理学”,尤其是“完善论的伦理学”,而他特别针对的又多是“神学完善论的伦理学”。他终身不渝的反目的论的立场可以说在他青年时期已然确立,这倒使他的哲学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现代伦理学的品格。但其正面的论述其时还不很清楚,或者说,他的义务论立场是明显的,但究竟是怎样一种义务论,尤其是正面的论证还不明显。他主张不能根据人的目的、欲望及对象来确立道德的标准,但如何根据共同体和人格关系来确立这种标准还语焉不详。的确,用目的或结果作为确定行为正当性的标准,在现代社会本身价值目标已经在平等的旗帜下“正当性”地趋于多元的情况下将面临极大的问题,这时,行为的正当性标准不能不主要从人们处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人际关系中的行为本身来考虑。虽然罗尔斯这时所强调的“共同体”和“人格关系”还有一种特殊的基督教性质,但他的早期探讨应该说已经预示了一种不是从个人自我的观点出发,去考虑如何达到一生的目标和理想,而是强调人类社会共同体中的关系和行为的客观道义的方向。
四、综论
综上所述,罗尔斯本科毕业论文的一个首要意义,是确立了罗尔斯一生的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种反目的论的基本立场。他主要反对的还是目的论的古典主流——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非神学的完善主义,也包括奥古斯丁、阿奎那的神学完善主义。而在后来的《正义论》中,他试图用他所构建的“公平的正义”理论替代的,则是现代目的论的主流——功利主义。
罗尔斯还在他这篇早年论文中特别鲜明地刻画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说“自我实现论”、“立己主义”。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在“观念的人”(如艺术家、思想家)那里是真正自我的、小我的;而在“行动的人”那里(尤其是政治家)则会是以“大我”隐藏一己之“小我”。罗尔斯在他生活的时代对后一种所谓“大我”的自我实现论中的一种,即以“优秀种族”为名义的“立己主义”(“纳粹主义”),已经有了强烈的感受和批判,但对另一种以“先进阶级”为名义的“立己主义”却还难有明确的体验和认识。
罗尔斯的正面观点即义务论的观点在他这篇毕业论文中表现为对人格关系的强调,即反对以追求目的为标准来确定行为的正当性,反对以追求善为基调来确定罪与信的意义;而是主张以共同体中的人格关系本身(这种人格关系在他的信仰时期还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来作为确定行为的正当性或者说有罪与否的基准。他后来离开了正统的神学信仰,但并没有离开这种反目的论的立场。
而在青年罗尔斯对人格关系、共同体的强调中,我们认为他已经预示了他后来的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基本倾向与特点,这主要表现为:首先,他始终注意人与人的关系,即他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观察道德、确立伦理的涵义。在伦理上最重要的不是自我追求什么,一个人一生要达到什么目标,而是他和其他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的“他人”的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关系才充分显示出一种道德的意义。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涉及人际关系,不影响到他人,也就基本上与道德无涉。其次,罗尔斯还认为,这种人际关系还应当体现出一种“人格关系”的特点,也就是说,这种人际关系还有一种实质性的涵义,即它和“自然关系”不同(他所说的“自然关系”其实并不只是指人与物的关系,也包括被“物化”了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还应当把其他所有人当人看待;或者说,要“人其人”,以合乎人性和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不把其他人作为手段和工具,作为“他者”来看待,而是作为和“我”一样的“你”,作为目的本身。人际关系应当是一种“你我关系”,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是一种我们必须脱离“自我”,从普遍的乃至“上帝的”观点看待的一种关系。
所以,罗尔斯在此文中强调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对于自我的根本重要性。而罗尔斯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强调社会、强调制度,尤其是强调社会基本结构的重要性,强调制度正义原则对个人义务原则的优先性,应该说和他早期这种对共同体的强调是很有关系的。虽然那时在他那里共同体还是采取与上帝融合的形式,而正义也是与上帝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那时显然对共同体及其正义还有一种很高的期望。而他后来在《正义论》中所考虑的只是一种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基本正义,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他更进一步不仅将宗教信仰,也将具有“广泛理论”含义的道德形而上学排除在我们可以寻求的“重叠的”政治正义共识之外。而在《万民法》中,甚至他所提出的正义原则的某些内容(例如差别原则),也被他认为是不适合用来处理国际关系。
总之,人——共同体——上帝,这或可用作我们理解罗尔斯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的主要线索,甚至也可用作我们理解罗尔斯后来著作的一把入门钥匙。人——这里的人其实在年轻的罗尔斯那里就已经是现代社会中的人,其努力的目标已经不再是个人完善,无论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完善。或者说,更优先考虑的是涉及人格关系的行为和态度的正当性。共同体——由于人并不是孤立的,人本性是社会的动物,是一定要生活在共同体中的动物,所以要对共同体或者说社会给予特别的强调。正是由于这种对共同体的重视和强调,罗尔斯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那就是对于社会正义或正义共识的探讨。上帝——青年罗尔斯曾热烈关注上帝,但后来上帝不再是思考的主题,不再是理由的根据;此后上帝或宁可说是一种后面支持的精神,或许还是一种个人的信念,即仍具有一种可能是作为背景或远景的隐秘存在。
注释:
①严格说来,罗尔斯的专著只有三本:《正义论》(Rawls,A Theory of Justic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The revised edition,1999.)、《政治自由主义》(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万民法》(Rawls,The Law of People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另有一些讲义、论文集,大都有了中译本。
②Rawls,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with "On My Relig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Edited by Thomas Nagel,p.111.以下引用此书改为夹注原书页码,译文参用左稀、仇彦斌、彭振的译稿。
③罗尔斯所言这种“自然主义”的错误与20世纪初直觉主义伦理学的代表摩尔所说的“自然主义的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的异同在于,摩尔是批评试图同自然对象来给“善”下定义,但他并不否定人对善的价值目标的追求。但两人看来都试图在人与自然之间作出区分。
标签:伦理学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奥古斯丁论文; 目的论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正义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