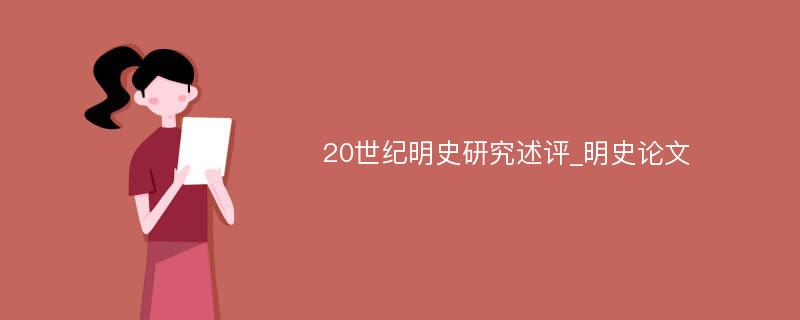
20世纪《明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史论文,述评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史》是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也是历代官修正史中编纂用时最久的一部。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局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年)书成刊印,阅时达95年。撰修期间,凡四次开馆,五换监修,七易总裁,撰修官更进进出出,见于记载的将近百人,其进度旋快旋慢,写写停停,一波三折。史稿改动也较大,从编修人的底稿,到主编的删削增润,以及后续主编的再次加工改动,内容和体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有人说,《明史》也是官修史书中最难产的一部。惟其部头大,用时久,其间人事复杂,内容多变,留给后世的问题也相对较多。
一 《明史》研究的发轫及其发展阶段
《明史》书成之后,当时就得到学者们的肯定,如赵翼指出:“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① 钱大昕、包世臣、李慈铭等也都对明史多所揄扬。但《明史》的缺陷也不是没人看到,对于在撰修过程产生的史稿和后来的官方定本,学者们都有一定的批评,如礼亲王昭琏就指出:《明史》稿于建文诸臣指摘无完肤,而于永乐靖难诸臣颇多恕词,“盖心所阴蓄,不觉流于笔端。从古佥壬不可修史,王司徒言未可非也”②。陶澍也说:王鸿绪于吴人每得佳传,于太仓人尤甚,而于他省人辄多否少可,“几无是非之心”。此为论史稿之失。魏源的《书〈明史稿〉一》、《书〈明史稿〉二》两篇文章,同意礼亲王和陶澍的观点,批评《明史稿》,未能革除“《宋史》以来人人立传之弊”,兵、食等志“随文抄录,全不贯穿,或一事有前无后,或一事有后无前,其疏略更非纪传可比”等 ③,并在自己撰修《海国图志》时,正面指责《明史》的种种失误。④ 但是,毕竟批评本朝官撰史书,还是多数人所畏忌的。
对《明史》的认真研究与评论,当是在清亡之后。其契机是20世纪初的议修清史。1914年清史馆正式设立,为了提供借鉴,刘承斡于1915年即编集刊刻了《明史例案》,内收清代编修《明史》的诏书、上疏、信札、移文、凡例等,把当时可以找见的关乎《明史》纂修的文献搜罗殆尽,为日后的《明史》研究提供了集中的资料。
稍后,专门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问世。《中华小说界》于1915年和1916年连续刊登《〈明史〉稿本》和《万季野修〈明史〉》两文,是今见20世纪最早的《明史》研究文章。此后,陈守实发表《明史稿考证》(《国学论丛》第1卷第1期,1927)和《明史抉微》(《国学论丛》第1卷第4期,1928)两文,前者专门探讨王鸿绪《明史稿》和万斯同《明史稿》的关系,后者着重于批评《明史》定本的缺失。
《明史》研究的兴盛首见于20世纪30年代。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1931)和李晋华《明史纂修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二文的发表,标志着系统研究《明史》的开始。前者按《明史》撰修的阶段并分“史料”、“史才”、“体例之订定及编纂之方法”等专题;后者分十部分,包括四朝诏谕、朝野学者之建议、纂修中之三时期、历任纂修各官姓氏、纂修各官所拟史稿考、《明史》因袭成文之例证、《明史》诸本卷数比较表、钦定《明史》与三修《明史》人名地名改译表等十个部分,都对《明史》的编纂过程作了详细考辨,论述了《明史》修撰的背景和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以前的一些疑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时,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明史》稿本,特别是万(斯同)稿与王(鸿绪)稿的评价问题。围绕王鸿绪是否攘窃的问题,一时俊彦硕学纷纷参与,柳诒徵、孟森、吴晗、张须、侯仁之等大家,都在报刊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个讨论的余波,延及40年代。
在专门的史学史著作中,对《明史》也给予重视,魏应麒(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金毓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的《中国史学史》都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明史》的问题。
1949年以后, 《明史》研究在港台继续进行,黄彰健发表《明外史考》(《史语所集刊》1953年第24卷),李光涛于1958年发表《论乾隆年刊行之明史》(《大陆杂志》1958年第16卷),都是对以前争论不休的稿本问题的继续研究。此后有包遵彭裒辑资料,编辑了《〈明史〉考证抉微》(台北学生书局,1968)和《〈明史〉编纂考》(台北学生书局,1968)两本书,集中了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主要研究论文,其于《明史》研究的贡献可与民国初年刘承乾刊刻《明史例案》相埒。
此外,这一时期港台《明史》研究还有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即黄彰健的三篇考证文章《〈明史〉纂误》(1960年)、《〈明史〉纂误续》(1966年)和《〈明史〉纂误再续》(1967年),发表在台湾《史语所集刊》上,对《明史》内容上的错误纠正甚多。
而在大陆,在1949年以后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明史》研究陷于沉寂,几无佳作。
进入新时期以来,同整个学术研究一样,《明史》研究也在大陆兴盛起来。由李庆的《论〈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1978)和李洵的《〈明史·食货志〉的编纂学》(《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二文发轫,《明史》研究论文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迅速增多。特别是黄爱平连发二文——《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万斯同与〈明史〉的纂修》(《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重新把王鸿绪是否攘窃的问题提出来,并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
此后,《明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如果说以前的研究多注重于编纂过程的梳理和稿本的辨正,那么此时的变化就体现在开始注意撰修者的思想,以及对撰修者和《明史》各组成部分(纪、志、表、传)进行个案研究。汤斌、徐元文等总裁官,姜宸英等撰修官,以及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等与《明史》撰修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学者皆被纳入研究视野;《明史》的《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文苑传》、《道学传》等也被专门研究。
这时期出版的关于清代史学的专题性论著,如乔治忠的《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和姜胜利的《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二书,也较多涉及《明史》撰修问题。综合性史学史著作涉及《明史》编纂问题论述较多的有,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仓修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张孟伦的《中国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尹达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等。此外,陈清泉等编写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为参加明史撰修的万斯同和王鸿绪都写了传记。
综观20世纪《明史》研究的整个历史,大致呈两个主要阶段,即30~40年代和80~90年代。这两个时期取得的研究成果,论著有10余部,论文近300篇。
二 《明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20世纪的《明史》研究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如《明史》修撰的指导思想以及历史观,总裁、史官的分工、进退和贡献,各种稿本的流传与收藏,等等。这里择其要者,略予概述。
1.关于编修进程的阶段划分
《明史》自清顺治二年开馆撰修,至乾隆四年结束,阅时近百年,其间历经四朝,时兴时罢,撰修进程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然对于如何划分其阶段,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一般认为分三个阶段:顺治二年至康熙十七年,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或乾隆四年。李晋华、黄云眉、汤纲等皆持此说,此分法也基本为学术界所认同。但也有不同的分法,如李庆以主掌人为标志细分之为六个阶段:顺治二年至康熙十七年,发轫,但未具规模;康熙十八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主要由徐元文、徐乾学主持;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五十三年,主要由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三人分掌;康熙五十四年至雍正元年,主要由王鸿绪主掌;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主要由张廷玉负责;乾隆四年以后,又进行了修订。⑤ 乔治忠则将一般认为属于同一个阶段的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再分为两个阶段,进而把整个撰修过程分为四个阶段,顺治二年至康熙六年为准备阶段,康熙十八年至康熙四十八年为奠基阶段,康熙四十八年至康熙六十一年是废弛与中辍阶段,雍正元年至乾隆四年为成书阶段。阶段的划分有助于梳理《明史》修撰的具体过程,把握各时期的特点和不同参撰者的贡献。⑥
2.关于监修总裁及重要参与者
王鸿绪是否剽窃万斯同明史稿,这是明史研究中的一大公案。自康熙十八年以后,《明史》监修总裁屡易其人,万斯同以私家学者的身份参与其事,“隐忍史局二十年”,先后协助徐元文、王鸿绪等总裁,审核各撰修官呈交的史稿。对于万斯同的贡献,早在清代就有多人予以肯定。黄百家、刘坊、方苞、全祖望、钱大昕诸人为万斯同写的碑传,以及杨椿、昭琏、魏源等人的论著,都称其尽力明史,死而后已。到了20世纪,梁启超、陈守实、黄云眉、李晋华等更推崇其地位,认为万斯同隐然操总裁之权,徐元文聘请万斯同居其家审核史稿,因而有了万稿;王鸿绪的《明史稿》实际也是万斯同所作或在万氏基础上的改修。朱端强更以“《明史稿》的实际编撰者万斯同”为题发表论文,特别强调万氏的重要作用。⑦ 这大致是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观点。
而对于曾聘请万斯同居家审核《明史》的王鸿绪,长期以来人们却颇有微词。最初是杨椿在《再上纲目馆总裁书》中说:“始万君(斯同——笔者注)在时,于徐公(元文——笔者注)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名世,万斯同助手——笔者注)俱详注其故于目下。王公(鸿绪——笔者注)归,重加编次,其分合视万稿颇异。”“最可议者,王公重编时,馆客某刻薄无知,于有明党案及公卿被劾者,不考其人之是非,问其事之真伪,深文巧诋,罗织为工,而名臣事迹则妄加删抹,往往有并其姓名不著者。盖是非毁誉尚不足凭,不特纪志表传自为异同已也。”⑧ 加上张廷玉《上明史表》中有“经名人三十年之用心”之语,后人遂指王鸿绪之稿出自万斯同,甚者便指王鸿绪攘窃、窜改万稿。陈守实称:“在季野(万斯同——笔者注),既不欲被新朝簪缨,以布衣参史局;所谓‘以史报故国’,原无精于名闻;而鸿绪之‘盗名’‘攘善’,则颇伤雅道。”⑨ 梁启超甚至说:“《明史》长处,季野实尸其功;《明史》短处,季野不在其咎。”⑩ 于是,王鸿绪剽窃成书的说法颇为流行。
为王鸿绪辩白,也是从20世纪开始的。30年代,侯仁之有专文《王鸿绪〈明史〉列传残稿》(《燕京学报》第25期,1939),在肯定万斯同“前后旅京者二十二年,此二十余年中,瘁心史事,积年累月之劳,鲜有终日之暇……其坚苦之志,令人肃然”的同时指出,王鸿绪也在《明史》修撰中有着自己的贡献。他通过把据说是出自万斯同审改的王鸿绪《明史稿》与《明史列传残稿》认真比勘,断定《残稿》是从王稿到进呈稿的过渡稿本,系王鸿绪手自删定的,并称:“二百年来王氏所蒙诬枉,从此可以释然矣”。
黄彰健进一步论证了侯仁之的观点,其于50年代发表的《明外史考》一文,以《明外史》与《明史列传残稿》相对校,得出结论:“修史,自不容易。尤其草创,较继述更难。万氏草创之功,固不可磨没。但由明史列传残稿看来,其遗留下的,却是那样繁冗待删,而且有些记载还需查其出处与考订其真伪,王氏之能编成一书,其功绩不在万氏之下。侯氏之替万氏洗刷,是不错的。”
事过30年,黄爱平以《王鸿绪与〈明史〉纂修:王鸿绪“窜改”、“攘窃”说质疑》、《万斯同与〈明史〉的纂修》二文,强烈质疑传统的王鸿绪“窜改”、“攘窃”万氏之说,在充分肯定万斯同对《明史》贡献的同时,指出王鸿绪也作了自己的一份重要工作。她认为,在封建社会官修之书多以监修总裁署名进呈,王鸿绪身为朝廷大臣,又任《明史》总裁,因此他进呈史稿署自己的名字只是循例之举,而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修史,在上疏中自然不能被提及名字,因此指责王剽窃难以成立;王在上疏中提到的笔削、补缀、就正、咨访,确实是他做的工作,并未抹杀别人的贡献;张廷玉进书表所称《明史》经名人30年之用心,也并非专指万斯同,而是泛指当时参加《明史》撰修的诸学者;万斯同所作的几项工作,如制定凡例、拟定目录、修改史稿,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明史》毕竟是集体之作,《明史》凡例是博采众长制定的,各篇底稿是各撰修官分撰的,史稿的审核和修改也凝聚了众人的心血,因此,正如汪由敦所说,它是“聚数十辈之精华,费数十年之心力”而成的。黄爱平的观点有些在侯仁之、黄彰健的文中已经提出,但她的表述更加明确有条理,特别是在人们多接受梁启超等人的说法的情况下,重新论证此课题,对传统认识有较大的颠覆性。
随后,乔治忠也充分肯定了王鸿绪的作用,指出:“《明史》纂修的第三阶段是靠王鸿绪个人支撑和庚续的,他的三百一十卷《明史稿》为下一阶段《明史》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条件。”(11) 考乔氏此说,似也更多肯定了侯仁之和黄彰健的观点。
关于《明史》总裁的研究,一般多注意王鸿绪的问题,王嘉川撰文则特别彰显两次担任监修总裁的徐元文对《明史》的重要贡献。指出他创议购遗书、征遗献,并在康熙年间达成朝野合作共修明史的局面中起了中间协调作用;他个人出资聘请万斯同居家刊修史稿,并与之共同商榷核定;他领导史馆诸公讨论形成《修史条议》,显示出其领导史局的才能。(12)
孙香兰探讨了汤斌对《明史》的独特贡献,汤斌一生二入明史馆,先后任纂修和总裁,历时八年,既编写也审定,表现了他的史学才华。他编写了包括《太祖本纪》、《后妃传》、《列传》、《历志》等在内的20卷的明史稿。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对明史编纂具有积极影响。(13)
赵连稳指出,黄宗羲欲通过修故国之史以报故国,虽未亲身参加撰修《明史》,却对《明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参与议定《明史》凡例,为《明史》馆提供大量资料,核实考订史实,审定《历志》,等等。(14)
傅荣珂论述了顾亭林与《明史》的关系,指出:“亭林虽未直接参与明史撰修工作,然于明史史料搜藏颇富,掌故亦为熟悉,故历来明史总裁如叶方蔼、徐元文、熊赐履皆欲征聘其为纂修,虽为亭林所拒,然修史体例,纂史诸家必与之商略,且总裁千里移书必相咨问之,明史体例完善,殆由徐元文兄弟之功,而其所自则本诸亭林也。”(15)
姜胜利总结了清代私家对官撰《明史》的贡献与影响,指出受聘与修、提供史料、提出建议和审核史稿是私家在四个方面对《明史》的襄助,而私家的直书思想和求实精神也给予《明史》一定的积极影响。(16)
3.对于分撰诸人及志传稿的研究
对于《明史》诸志,以对《食货志》的研究最早。郑天挺有《读〈明史·食货志〉札记》(《史学集刊》1981年第1期)研究了食货志所记经济史料。继而梁方仲为《明史·食货志》作了笺证(1981年)(17),李洵从史料来源、编修经过等方面探讨了《明史·食货志》的编纂学,论述了潘耒、王原对《食货志》的各自贡献。李洵还有专著《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是《明史》整理的重要成果。何珍如寻绎了《明史·食货志》的编纂源流,对王原《明食货志》、万斯同《明史稿食货志》、王鸿绪《明史稿食货志》、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四种志的承继关系作了分析,指出它们的后者都对前者有继承,而张志在文字上比王、万二志好,在内容上比王志充实;前详后略则是四种志的共同缺陷。(18)
在《明史》诸志研究中,最有争议的当属《艺文志》。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其一,是《艺文志》的源流与作者,一种意见认为,黄虞稷是主要作者,其《干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主要依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二书“实质上是两个目录”不应混为一谈。前者可以王重民为代表,他曾指出: “康熙二十八年(1689)黄虞稷写定了《明史艺文志》稿,交给总裁官徐乾学……黄虞稷自己当然还保留着一份《明史艺文志》原稿,后来采用《千顷堂书目》的名称流传出来。”(19) 后者以李庆的考证最为有力,他指出早在黄氏人史馆之前,就有尤侗、倪灿、陆菜等人参撰,黄氏入馆后也不可能力排众议重撰《艺文志》。他通过对《千顷堂书目》流布过程的图示,说明其与《明史·艺文志》本是两部书,前者是后者的史料来源但不是唯一来源。(20)
第二个争议问题来自《明史·艺文志》在体例上的一个特色,即只著录明代出现的书籍。王重民《〈明史·艺文志〉与补〈艺文志〉》(《图书馆学通讯》1981年第3期)一文指出,最初由黄虞稷起草的《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范围包括明人和宋辽金元人的著作,其规模很大,比明人焦弘《国史经籍志》著录的书多17倍,而后来王鸿绪根据其书改成的《明史稿艺文志》却把宋辽金元部分删去,把明人著作中的“卷数莫考”或书不甚著者也删去,同时也充实了一些明代的书,所以官方颁布的《明史·艺文志》比黄虞稷的原稿整齐美观了,价值却降低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明史对著录原则的改进乃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创新。如金毓黻就曾指出:“《明史》之佳,本非一端,如排纂之得当,附传之得宜,前史有志而无图,《明史历志》则增图以明历数,前史艺文志皆无断限,而《明史》艺文,惟载当代著述,此皆以古今异宜,而深得体要者。”(21) 瞿林东则认为,明史的做法,“显签是受了刘知幾《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22)。
关于传记的研究,集中于《道学传》的设立问题。是否设立《道学传》,曾经在明史馆争论达三年之久,最后是非史馆人员黄宗羲的建议使诸撰修官的看法得以统一。研究者注意到这一现象,魏伟森的《宋明清儒学派别争论与〈明史〉的编纂》(《杭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认为,以往把不立道学传归之于王学的胜利是不妥当的,他分析了当时各派的观点,指出这是程朱学派对将儒家的“道”作为道学思想的副概念的重新恢复。实际上是说《明史》不立道学传,反映了思想界对于道学认识的一个变化。
明史列传体例的一个特色是设立了阉党、流贼、土司三传。陈文毫《读〈明史阉党传〉》(《明史研究专刊》第三期,台北大立出版社,1982)探讨了这一现象。通过研读万斯同、张廷玉等稿本指出,《流贼》、《土司》二传在万稿中已见传目,而《阉党传》是在张廷玉总裁明史时才出现。而其之所以设立是受传统史学的垂训鉴戒以及忠君思想的影响。
4.对《明史》的总体评价
对于《明史》比较全面的评价,多数人认同赵翼和梁启超的观点,认为在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之外,《明史》是质量比较好的一部。同时也对其缺点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述。陈守实指出《明史》之失:① 清帝之禁钳太甚,致事多曲讳。②因学派门户之偏见,致颠倒失实。③ 搜访之漏略。④明清关系多失真相。⑤弘光迄永历之终,史实多缺。(23) 黄云眉也不同意赵翼对《明史》的过高评价,认为他“于《明史》不免回护”,指出:“考唐以后官修诸史,成于众手。监修大臣,著名简端,实无与史事。读史者亦不以史之美恶归之,而《明史》则有总裁攘窃人美,冒为专家。又前代修史,时主多视为奉行故事,不甚措意……而《明史》则有时主之明加督责,隐寓钳制。此皆《明史》特点……有此二特点,而《明史》乃无信史之价值可言矣。”(24) 吴晗总结了《明史》的失误:脱文、错误、事误、重出、矛盾、简失、互易、缺漏、偏据、字误。(25) 这三人的评价基本囊括了学者们的批评意见。
值得提出的是刘寅生的《论“钦定明史”的一统和魏源对明史学的贡献》[《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一文,专门探讨了明史所受官方钳制的消极影响之大。指出“《明史》修撰,殊为清廷重视,几乎年年有上谕,事事有批复。从规定必须满汉大员并领史馆的大事,过问到诸如陪崇祯皇帝上吊的太监名叫王承恩、张献忠的义子被割去耳朵和鼻子这等琐碎末节。如此捆缚的结果,馆臣们固然很难开拓心胸,舒展手脚;即便成书了,没经过‘宸断’只能算是未定稿。”而官方大兴文字狱,思想上的规范禁锢和政治恐怖,使得当时的史学领域,人人裹足不前。
对于《明史》记事内容的具体批评,可以两部书为代表,即台湾黄彰健《明史纂误》和大陆黄云眉《〈明史〉考证》一至八册(中华书局,1979~1986)。
从时代背景、纂修经过、编纂学、史学观点等方面对《明史》作出全面分析的,应是汤纲等人的文章《〈明史〉的纂修及史学思想》(《明史研究论丛》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文章指出:清代入关之初就迫不及待地从事明史撰修,其意图正是想通过对明代历史的阐释,来宣扬封建道学,以抵制反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打着表彰明朝的幌子,来麻痹民族对抗情绪,以缓和民族矛盾,从而达到其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明史》遵循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公认的正统观点,任何个人私见如果不符合封建正统观点,都是不容许的。总的来说,《明史》的思想观点是保守的,它没有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先进思想,而是抱住僵化了的程朱之学不放。但是由于时代的影响和许多先进思想家对《明史》的纂修发生过间接影响,《明史》的叙述只要与清朝无厉害关系的问题,还是比较实际和客观的。“《明史》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不能像清代学者那样评价过高,也要避免多论其缺点,而对优点肯定不足的倾向。”可以说,这是至今为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明史》最全面的文章。
《明史》的研究还有一项重要成绩也不容忽视,即关于《明史》的标点、整理。中华书局标点本,是在郑天挺先生主持下,由对《明史》素有研究的汤刚、付贵久等人完成的。此外还有人为《明史》的某些部分做了标点、校勘、考证、补遗、注释等大量工作,这方面的文章有近百篇,都为以后的进一步整理打下了基础。
以上对20世纪《明史》研究历程的简单巡礼,难免挂一漏万,当然不能反映整个20世纪《明史》研究的全貌,但即便如此,也不难看到这些研究是深入的,成绩是辉煌的。这是经过几辈学者的努力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十几部研究专著和近300篇论文的问世,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明史》、读懂《明史》、进而研究《明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新世纪《明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1世纪的《明史》研究,将继续深化对以前领域和对象的研究,同时应该扩展新的研究领域和对象。
无疑,《明史》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对于《明史》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研究,有分量的文章还不多,不仅比不过对《史记》、《汉书》的研究,甚至比不过《新五代史》等有关研究。对《明史》诸志的研究也还刚刚起步,与《史记》等正史的有关研究也存在一定距离。《明史》作为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其在纪传体上的因循和创造,也未曾得到认真的总结。
进入21世纪以后,《明史》研究的脚步并未停歇。在新世纪之初,就有许多新著问世。研究范围明显扩展,侯德仁的《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编纂》(《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侯辉的《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新疆石油教育学院》2004年第4期)、肖俊侠的《〈明史·兵志〉沿革考》(《河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王志岳的《〈明史·礼志〉编纂考述》(《平原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郭培贵的《〈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等,都扩大了对诸撰修官和诸志的研究范围。姜胜利的《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安徽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乔治忠的《论清顺治与康熙朝初期对〈明史〉的撰修》(《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朱端强的《清顺治朝〈明史〉修撰考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赖玉琴的《论博学鸿儒〈明史〉之独特价值》(《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都对清初明史撰修活动着力探讨,加强了研究问题的深度。这些都反映了《明史》研究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
同时,我们期待着新世纪的《明史》研究更富有生气和活力。21世纪是创新的世纪,即便是在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研究传统课题时,我们也应当展开新的视角。《明史》作为最后一部正史,负载的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我们应当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尝试从新的视角和范围去认识《明史》。比如,能否不再局限于对谁剽窃了谁的论说?《明史》的撰修本是由撰修官初拟、由总裁或其他学者受总裁之托审改的,一个环节也不可缺少,以往就欠缺了对初拟稿的关注,现在的《明史》哪些使用了初拟稿,哪些才是经总裁核定的?注意及此方可捕捉到史馆的思想与史官个人思想的不同,才可以看出官方的思想倾向是什么。(26)
再如,我们能否不再就稿本谈稿本,怎样才能把《明史》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联系,通过研究《明史》了解清代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意识,这也是一个以前所忽视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史记》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应该是《明史》所关注的。透过对《明史》所记内容、取材视角的独特之处的分析,可以了解清代史家的关注点,了解清代史学的特色。
总之,新世纪的《明史》研究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应该是色彩斑斓的,应该在继承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走出新的路子。我们期待着!
注释: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1《明史》,中华书局,2001。
② 昭琏:《啸亭杂录·续录》卷3,中华书局,1980。
③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4《书明史稿》一、二,中华书局,1976。
④ 参见刘寅生《论“钦定名士”的一统和魏源对名士学的贡献》,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由论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⑤ 李庆:《论〈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⑥ 乔治忠:《明史的编纂与清代官方明史学》,《清代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⑦ 朱端强:《〈明史稿〉的实际编撰者万斯同》,《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
⑧ 杨椿:《孟邻堂文钞》卷2《再上纲目馆总裁书》。
⑨ 陈守实:《明史稿考证》,《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
⑩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5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东方出版社,2004。
(11) 乔治忠:《明史的编纂与清代官方明史学》,《清代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12) 王嘉川:《徐元文与〈明史〉纂修》,《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3) 孙香兰:《汤斌与〈明史〉》,《中国历史与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4) 赵连稳:《黄宗羲和〈明史〉编纂》,《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4年第3期。
(15) 傅荣珂:《顾亭林与明史》,《东方杂志》1981年第15卷第3期。
(16) 姜胜利:《清代私家对官撰〈明史〉的贡献与影响》,《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75周年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17) 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
(18) 何珍如:《〈明史·食货志〉的源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19)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后记》,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
(20) 李庆:《论〈千顷堂书目〉和〈明史艺文志〉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1)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67页。
(22) 瞿林东:《说野史》,《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23) 陈守实:《明史抉微》,《国学论丛》1928年第1卷第4期。
(24) 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金陵学报》1931年第1卷第2期。
(25) 吴晗:《明史小评》,《图书评论》1933年第1卷第9期。
(26) 南开大学段润秀博士的学位论文《〈明史〉撰修官现存初拟稿研究》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思维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