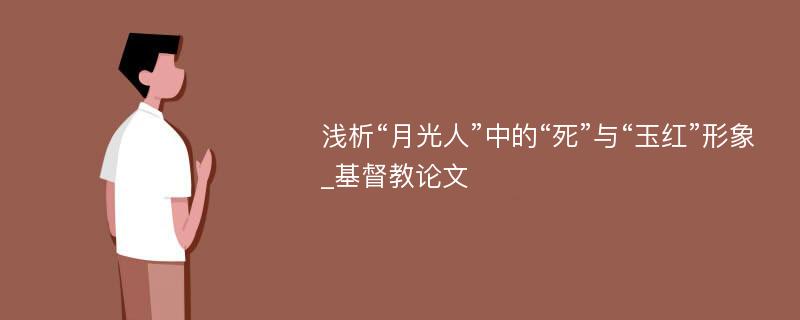
《月光人》中“死亡”和“雨虹”意象之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月光论文,雨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戴维·福斯特的名字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澳大利亚和英美的文学期刊及传媒上,所以去年他的《林中空地》获得澳大利亚最负盛名的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时,许多评论家和作家并不感到意外。一位学者在一篇评论中甚至这样写道:“无论是从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来看,它的质量都一下子使得该奖恢复了它失去的可信度。福斯特获奖也使此奖提高了声誉,其程度至少和该奖带给他的声誉不相上下。”(注: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The Australian's Review of Books,Kerryn Goldsworthy,p.10,no.10 ,1997.)这种评价是否过高姑当别论,它至少可以看出福斯特作为小说家的地位不同寻常,其作品在澳大利亚和其它一些英语国家已经相当红火。
其实福斯特成名相当早。早在1981年,他的《月光人》问世后就几次获奖,受到评论界的广泛称誉,在我国也引起了注意。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辞典》附录“英语国家语言、文学记事”里便列入了它。自它出版以来,它那历史与现实相交错,传统和神秘相融合的题材和手法便成为许多评论家的热门话题。概括起来,这些评论或者视之为流浪汉小说,或者视之为历史小说,或者视之为社会小说,或者视之为寓言小说,从不同的视角对小说作了不同层面的分析和阐释。评论数量之多和类型的丰富本身就说明了这部小说的重要性。但是阅读并翻译这部小说之后,我觉得这些评论言犹未尽,于是想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切入,试图发掘出一点或许是隐含于文本之中的深意,不知能否如愿。
一般评论认为,该小说旨在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黑暗,例如小说涉及的执行“清除法”情况和淘金浪潮就是很好的证明,所描写的苏格兰人、土著人及其他移民的不幸遭遇也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佐证。小说当中有不少反讽和嘲弄都是针砭时弊的,如把酒瓶当作钱币使用就嘲讽了澳大利亚人当中相当普遍的酗酒现象。同时,小说也是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的一种鞭鞑和否定。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充满悲伤情调,让人产生恻隐和同情之心,同时又不乏尖刻嘲弄和批评的小说。在这一基调下,“死亡”和“雨虹”这两个支配性的意象应当和小说的这一主旨相一致,抑或引发痛心的情感,用来构筑悲愤的氛围;抑或用来改进人的思维方式,更新人的信仰。这样,该书被当成一种暴露型或是道德感召型小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不足为怪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沿着这一假定的思路读下去呢?下面我们就用“死亡”和“雨虹”这两个意象对这个问题作些深入的探讨。
在这部小说里,“死亡”意象相当重要,担当着承上启下的组织功能。小说的不同阶段都有死亡的出现,而不同阶段的死亡包孕着不同的意蕴,对小说主题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小说开头就是主人公父亲和前妻的死亡。主人公芬巴此时尚未诞生。他的父亲是个叫拉么克的岛民,生性不甘寂寞。他妻子因难产而死去时,他还在外游荡未归。死亡并没有给他带来悲伤,或许是因为这个岛上经常死人,或许是他指望再娶个妻子。在这种情况下,死亡与其说是悲伤和痛苦,倒不如称之为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当拉么克扒开他死去妻子的阴道,试图弄清那未出世孩子的性别时,作者似乎是在暗示一种对于新生命的期盼。这样那天举行的丧宴上没有任何悲伤气氛就不足为奇了,而拉么克用眼偷瞟他看中的女孩子更是这种习俗的表现。
第二次死亡的时间和第一次相差不远。这次是拉么克本人。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和同伴所乘的大船在返回黑福莱——他和新婚妻子弗洛拉及丈人被部落头目驱逐的地方——途中被海浪掀翻。他死去以后,他的家人,包括他那即将诞生的孩子,很快便得到了黑福莱岛民的认同。他们三个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接待和尊敬,几乎成了圣人,其地位远远高于当初在马格岛的时候。看来拉么克的死亡并非坏事,相反还产生了一些积极意义。似乎可以说拉么克之死是他们为将来所付出的一种代价。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遗腹子芬巴身上。作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芬巴生下来就得到了岛上人的各种关照和爱护,包括新到的神父坎贝尔。尽管坎贝尔同弗洛拉的父亲唐纳德之间有冲突,他对弗洛拉和她的孩子芬巴却很友善。在坎贝尔的帮助下,芬巴受到了严格而完整的基督教教育,并接受了当牧师的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不仅是弗洛拉本人没有想到过的,也是所有其他岛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奇事情。这些描写分明是在颂扬基督教文化的感化作用。
如果拉么克和他的前妻不死,或许就不会有人看到芬巴,更不要说看到他以后的成长了。就这个意义来说,“死亡”意象带有某种结构上的作用,带有某种超越悲伤和不幸的意义。很难想象没有这些“死亡”意象的出现,故事结构如何涵盖芬巴的出生和成长。
坎贝尔的死亡,乃至弗洛拉和她大部分岛民朋友的死亡再次说明他们在英帝国“清除法”的迫害下,如何遭受痛苦,无路可走的情景,也表明了整个社会的积极变化。坎贝尔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去,其死亡可能带有些偶然性。但在那种情况下,黑福莱岛的岛民和其他苏格兰高地人外迁是早晚的事。如果坎贝尔还活着,或许可以拖延外迁的时间,但他绝对无法阻挡这些事的发生,因为它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产业革命造成对羊和羊毛的巨大需求,对肥沃土地和牧场的夺取,这既是当时形势的要求,也是无法逆转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显然更多地表现了这种历史发展进程,客观上有利于历史的进步。那些遭到驱赶的苏格兰移民尽管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并理解这么做的意义。所以他们一到新大陆定居下来,便对当地土著人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里虽有作者对他们挖苦的成份,恐怕也表现了他们的一种无奈。是否可以说暴力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催化剂或者接生婆,死亡则是随之而来的自然结果。
如果说由于坎贝尔和弗洛拉对整个故事进展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他们的死亡采用了轻描淡写的处理方法,那么芬巴之死则使整部小说形成了一个高潮。小说详尽描述了他如何遭到暗杀,最后一章完全是关于他被送往墓地的经过,毫无疑问芬巴之死所受到的重视甚至能与圣人相媲美。的确,他有权利,也有机会赢得即将举行的第一次选举。他作为这块殖民地为数不多的接受过英国高等教育的人之一,学问高深自不待言,他在选举演讲里已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未来领导人的政治才干,显示了他的政治潜力。这块新殖民地上的居民渴望能有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他的死亡对他们确实是个损失,甚至可以说是个悲剧。但这个悲剧是如何造成的呢,是社会对他的不公,还是他咎由自取,还是什么其它原因呢?回顾一下他过去的经历,或许对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能有所帮助。
他虽然在教育和学识上有所成就,却因为受到了驱逐而未能像他许诺的那样对自己的家乡作出什么贡献。他去了新西高地之后除了在地下采金,干些体力活之外,几乎没做过什么。虽然这不完全是他的过错,但他也有一些责任,如果不是他值班时心不在焉,听任大火把图书馆烧了,他也不至于受到驱逐。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察觉到他身上具有一种集家乡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体的奇特行为。他着装的样子、睡觉以及其它生活方式,显然都受到他家乡粗俗生活习惯的深刻影响,尽管他到新桥多年,还是难以适应文明的生活方式,经常受到那些对他的岛民生活背景不怀好意的人的嘲弄。比如说他在维吉尼亚女士举办的晚宴上以及基督耶稣学院他的同学中间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虽然他的内心思想已经为他们的文化所同化,却仍然无法改变他身上的一些本土文化的旧习俗。在他的思想深处对西方文化寄托着某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由于他意识到自己的出身和所处的地位,他并不喜欢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他的前途和西方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他喜欢与否,西方文化都是他惟一的选择。即便他回到家乡也要去当牧师,要靠西方人的宗教思想维持生活。
他以后的艰辛经历使他对西方文化不再有多少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就思想的投入而言,他依然是一位西方文化的热心实践家,他的言行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而不是从前的那种学术和宗教性质的。这方面的佐证是他在一次竞选会上的演讲。
我拥有一个目标,而且只拥有一个目标。就是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必要方式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保住它,永远永远地保住它。(注:《月光人》,叶胜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78—279页。)
他在选民们面前的这番话充分显露了他成为资产阶级政客后的勃勃野心,改变了他作为贫困和受压迫代表人物的形象,同时也表明他在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下变得狂热起来,完全成了一个热衷于摇唇鼓舌的政客。
如果把芬巴早期对生活的认识和他以后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表现作比较的话,其变化显然是很大的。他决定从政当然是个契机,但主要还是因为他所受到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暴露。当政治掮客格罗格斯特里夫最初认准他是恰当人选,找他做工作时,他对投身即将举行的选举似乎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但是,凭着他在新桥受过的教育他自以为满腹经纶,再加上一笔意外之财让他腰缠万贯,这两条明显的优势使他异军突起,他自己顿时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或许比这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几年里他所积累的经验。从新桥的伏案苦读到以后的长途跋涉,乃至新西高地的艰辛生活和繁重劳动,都是这种经验的体现。他不再固守一种信仰,惟基督教文化是从,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接受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成了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从默默无闻的矿工一夜之间成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政客,正是这种变化的表现。虽然由于有了从前经验的积淀,芬巴这时候似乎有些处世不惊,顷刻之间便做好了应变的准备,他毕竟还不够老练,注定要命运多舛。用他的推荐人的话来说,他是个“受命运摆布的人”,是命运给了他机会,也是命运让他受到了挫折。当年命运迫使他登上了横渡大洋的旧船,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赴新西高地的旅途。可是最终当命运之神向他微笑的时候,他却又身不由己,撒手人寰,死于非命。是命运在作弄他呢,还是社会发展曲折、反复的表现呢?这里当然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更多的似乎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宿命论思想,主人公的命运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但从最后章节对他的赞颂来看,他似乎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象征,如同耶稣一样在死亡当中得到永生。这一点在后面再作进一步探讨。
死亡对于活着的人来说通常意味着悲伤和损失,但它同样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产生积极的影响。小说中不同的死亡改变了小说的故事结构,使小说的叙事方向发生变化,或可以说读者也因此而对小说里相关的人和事进行了更为深沉的思考。《月光人》正是由于这些死亡意象,其主题结构才不单单是表现悲伤和痛苦,而成为一部认同社会发展规律,揭示人性归宿的小说。也正是“死亡”意象的出现,过去的事件才得以了结,生命的火花才得以萌生。这些恰恰表明了新陈代谢和精神不朽意识是小说的重要思想,而不单是以揭露殖民统治黑暗为其主旨。
“雨虹”是我们可以用来解构小说预定主题的另一重要意象。
马卡比收下芬巴,当了他的导师,似乎有些偶然性。另一方面是芬巴在数学上的天赋让他感到满意,一方面马卡比当时也正好需要一个学生。作为一名教授,长期不带研究生毕竟有些交代不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志趣完全相同。所以当芬巴提议以光晕作为他的研究课题时,马卡比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还是表现了相当的惊讶和不快。实际上芬巴有关光晕的想法源出《圣经》,表明他意识到他在有关上帝的本体认识上的疑问。他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是想澄清他在信仰与科学关系上的一些困惑。因为光晕的内涵不仅涉及到对光学现象的理解,还牵涉到对上帝的认识,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术语。作者的意图显然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批评基督教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作用。
鉴于这个课题涉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芬巴必须采用科学方法去观察和计算自然现象。他工作努力,也很有成效。他想通过对雨虹现象的观察来了解光晕。他测得了大量数据,不厌其烦地记录了不同的位置、距离、角度、幅度和色彩,为后面的分析奠定了基础。他甚至不用看就可以计算出雨虹的形状和角度,用各种花束摆设出类似雨虹的模式。然而就在他很快就要完成课题时,他却感到困惑起来,无法将研究进行下去,这是因为他弄不清楚光晕是如何形成的。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他们向仙人圈走去时,他向蒙哥说道,“我认为光晕是无法解释的,我想它展现了全能上帝的神力。”(注:《月光人》,叶胜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4页。)
他在面临上帝与科学两者之间谁更为重要的选择上似乎更看重上帝,或者不愿摈弃对上帝的信仰。这里的描写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世纪经院派修士们也曾经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在神和科学之间作出选择。两者必居其一,无法作出妥协。
以芬巴的智力和学问,他当然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也不是不想回避它们,而是无法这样做,因为他的工作和信仰都不允许。他想通过雨虹和光晕的研究来强化自己的信仰。他既有才华又有实干精神,完全有可能完成这个科研项目。然而这个课题的性质却不允许他在信仰和科学之间作出妥协,他不可能一石二鸟,借用一次科研来达到双重目的。就这个意义来说,他的失败早在他选定他的光晕课题之前就已注定,无论怎么努力,他都无法逃脱命中注定的失败。造成他失败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物质条件的匮乏,也不是他的方法不当,而是他的内心无法接受通过唯物主义手段取得的成果。正是在这里,芬巴陷入了一种困惑和无能的境地,心情十分压抑,不得不借助酗酒来驱赶内心的烦恼。他试图通过酒精来建立一种信心,取得一种灵感,以便在科研上获取更多的进展,但事与愿违,酒喝得越多,人变得越糊涂,越无法完成他的科研。简言之,他注定要失败,信仰和科学显然是势不两立,难以两全。
所以,他虽然努力使自己摆脱这种二元论的困惑,坚定自己的宗教信念,却力不从心。作者显然是想凸现芬巴认识论上的局限,书中有一大段议论专门论及这个问题。
皈依上帝和堕落从本质上来说是互相转化的。皈依者应当一方面相信上帝,另一方面又要相信自己。任何缺少信仰的东西都是致命的。……皈依者是个不幸的人,他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出生在一个死亡的文化里。所以除非他的这种转变是自发和全面的,而且他的大多数同胞都和他一样作了转变,这种转变常常是致命的,所以也是禁止的……人的堕落是不允许的,基督的死亡是不允许的,对圣灵的亵渎是不允许的。(注:《月光人》,叶胜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97—198页。)
这段引文分析了芬巴的矛盾心态,揭示了他在科学家和基督教信徒之间徘徊,无法找到自己出路的原因。所谓转变,所谓既相信上帝又相信自己实际上就是他的调和折衷,模棱两可的认识论造成了他的信仰危机。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推算芬巴之所以在研究光环和雨虹时失败是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然而说得更确切些,阻碍他实现自己学术之梦的并非雨虹现象的复杂,甚至也并非完全是基督教信仰的作祟,而是唯物和唯心并存的二元论阻碍了他运用科学和唯物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我们通过对他思想的研究发现,是他的基督教思想削弱了他作为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光晕研究上碰到的困难主要是他的基督教信仰和二元论观念妨碍了他对物质的现象进行唯物的思考,这种信仰不但减慢了他对光晕的研究速度,而且最终导致他的研究完全停顿下来。与此同时他的信仰也因为他研究上的失败而饱受煎熬,受到很大的削弱。实际上,作为光晕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雨虹研究和他的宗教信仰在这里互为因果关系,造成了他的一事无成。最终他不得不听从命运对他的安排,屈从于文化虚无主义。命运似乎是在和他开玩笑,把他投入到困境当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他对生活和信仰都失去了信心。由此看来,对光晕和雨虹的研究非但无助于澄清他的基督教信仰,而且和他开始进行研究时的期望相反,使他的信仰更加淡化,乃至受到了动摇。
但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思想就应当受到批评或者贬低呢?基督教思想是否因此就应当被打入冷宫呢?答案显然又是否定的。芬巴非但没有抛弃基督教信仰,他依然以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无论走到那里,始终不离开它。与此同时,一些不好的东西,例如钱和酒的诱惑,又在不断地骚扰着他。到了新西高地之后,他逐渐从一个纯粹的基督教徒成为一个受到资产阶级功利思想熏陶的实用主义者,更加注重个人的实际利益,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注于精神上的信仰。或许这是因为周围环境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光晕和雨虹研究对他产生的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从政企图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如果说基督教信仰和二元论思维方式束缚了他的科学研究,断送了他对光晕和雨虹的研究成果,他的从政活动则表明他试图摆脱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更多地向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斜。他酗酒,放浪形骸,不拘小节,争夺金块,对上帝变得倨傲不羁,对阳光说“我准备再给上帝一次机会……月光人麦克达菲可不是个受人愚弄的人”(注:《月光人》,叶胜年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但这种转变却又不是对基督教思想的否定,而只是在新形势下对基督教思想的一种改良,这就如同当年加尔文主义并没有否定基督教思想,只是让基督教变得更能适应当时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一样。芬巴最终在竞选过程中因为政治主张而遇刺,成为一个为事业而牺牲生命的耶稣式人物,头上戴上了一个光环。基督教提倡的为信仰献身的精神也因此而得到了肯定,甚至可以说是发扬光大。最后一章中,芬巴被比成黑仙人之子,送往不归之路,新西高地变成了耶路撒冷,烘托出一种神圣肃穆的氛围,也正好印证了小说对基督教思想的肯定和褒扬。
雨虹给芬巴带来了压力和困惑,但对他的土著人朋友阳光来说却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神秘感受。阳光认为雨虹强大无比,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阳光和他的首领以雨虹朋友的名义让芬巴经历了一连串痛苦和严峻的考验。相比较而言,土著人的雨虹比起芬巴的似乎更有力量。这种比较很有意思,芬巴虽然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物质上视雨虹为一种自然现象和研究对象,但在精神上却远非那么简单。如前所述,他之所以选择光晕和雨虹作为研究课题,是因为它对他有双重的含义。除了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外,它还有一层上帝荣耀的宗教涵蕴。就这个意义而言,芬巴和阳光有相似之处,可以进行比较。芬巴落入阳光的圈套所遭受的痛苦表明,芬巴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相对于阳光所代表的土著人文化而言,明显地处于一种劣势地位。但他在接受阳光挑战的过程中,却又在吸取新的力量,充实着自己,从而能够大难不死,获得新生。这种新生正是基督教思想的一种重要内涵,是复活思想的延伸。如同芬巴自己在这场宗教仪式里死而复生一样,他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也有一种脱胎换骨,获得新生的意蕴。
雨虹的描写是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临近结束的时候出现的。第一次凸现了芬巴在信仰和科学问题上所处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后面一次则显现了一种不同文化的反差和对比。然而把这两次雨虹描写放在一起审视,我们是否能够说雨虹实际上已经毁坏或者颠覆了基督教的旧文化,并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新生呢?没有雨虹和光晕的研究及实验,芬巴不会面临思想信仰危机,没有这场危机,他就不会失去信心,放纵自己,也不会有后来的参与政治,更不会因政治观念而丧生,当然也不会成为耶稣式的人物,隐喻基督精神的复活和新生了。毋庸讳言,土著人神话所包含的叛逆精神是由雨虹朋友的代表阳光所传达的,在和代表白人及基督教文化的芬巴较量时明显处于上风。同样,对雨虹所作的科学研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基督教信仰对芬巴进行干扰的缘故。这些都表明那时基督教思想已开始走下坡路,其威望正在下降,其影响在芬巴和其他许多人之间也正在逐渐减弱。芬巴以及和他类似的有文化青年自觉不自觉地要在信仰和科学之间作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雨虹被用来作为一种象征,表现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日趋衰微而需要进行变革,求取新生的趋势。
综上所述,“雨虹”和“死亡”意象一样,显示出了主人公芬巴和基督教文化的弱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揭示,凸现了基督教文化的顽强不息、死而后生的精神。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这部小说在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而绝非完全对其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书中对殖民统治的有些批评非常尖锐,但涉及到过去所发生的具体事情却又显得比较通融,包括在英帝国里所发生的一些后果极其严重的事件,例如在“清除法”颁布后出现的流血冲突,以及土著人和白人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这些在小说里虽有涉及,但不是稍作描述,就是一笔带过。所以恐怕还不能说它是暴露型小说。
其二,小说并没有对过去百余年的黑暗岁月和沧桑变化作任何历史性的评估,而只是以历史作一面镜子,观察、嘲讽人性和西方文明。因此它只是一部带有历史观照和讽刺意味的小说,其重点是建构一种更带普遍性、涵盖面更为宽泛的主题框架,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如对人性的褒贬,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冲突,神秘氛围和传统理念之间的比照等。不能说它没有说教,但这种说教主要是针砭社会时弊,有感而发,并非道德说教。
其三,小说充斥了浓重的文化虚无主义和宿命论思想。这点可以从对宗教信仰,尤其是对基督教信仰信心不足上看出来。主要人物身上所表现的一种听从命运安排、信仰无所适从的倾向具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和负面效应。但这一情况并非是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的完全否定,而只是为了说明适应新的形势、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主人公思想的变化和为理想献身是这一意图的题解和印证,也是导致小说原有主题解构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复活和新陈代谢才是小说真正着眼的地方,也是这部小说区别于其它相同类型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