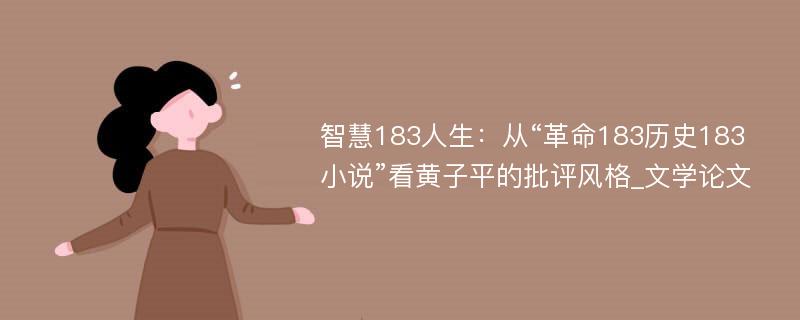
智性#183;生命——由《革命#183;历史#183;小说》看黄子平的批评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风格论文,生命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沉思的老树的精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享有声誉的文学批评家黄子平,于90年代在香港出版了文学评论集《革命·历史·小说》。作者以睿智的眼光,透过历史的烟尘,深刻地剖析了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历史、小说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为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揭开了一个新视角。此评论集,融其智性与生命体悟为一炉,从而形成了黄子平成熟而独特的批评风格。
一、智性的批评
黄子平1983年的《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鲜明地提出了“要在微观基础上展开宏观研究”(注: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意见。他认为宏观研究不仅意味着空间尺度的放大,而且意味着对当代文学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理解,意味着从文学的发展和运动中,从它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联系和中介加以把握。要求在丰富的“历史储存”中来接受、阐述全部新出现的文学信息;要求打破单向的思维和平面思维,采取立体思维,把文学现象看作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80年代的黄子平强调宏观研究时,没有放弃微观的研究,而是自觉地尝试着对文本的形式进行具体细微的分析。西方的新批评也对作品的形式感兴趣,但它把作品当作一种独立自足的体系,忽视作品与外部环境,作品与作家的关系,而《革命·历史·小说》却将宏观与微观的融合浑然一体,充分展示了黄子平先生的智性。那么,评论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作者是怎样让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体现他的智性呢?笔者将从作者的批评方法与批评视角两个方面来论述,一是美感形式与历史感结合;另一是从文化批评的视角细读文本。
黄子平80年代的文学批评就已注意美感形式与历史感的结合。1984年写的《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对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三十余年的发展作了纵向的考察。另外,对作家公刘、艾青、郭小川、林斤澜,以及作品《绿化树》、《别无选择》等都尝试着把握美感形式与历史感的有机结合。如果说80年代作者对两者结合的深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么9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对这种批评方法的应用变得炉火炖青。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形式对历史变动所作的叙述是此书的核心。作者从历史变迁中去论述文学的运动和发展,又从文学的运动发展中窥见历史发展的轨迹,文学与历史,尤其是与革命历史之间互动关系清晰呈现。《革命·历史·小说》这篇文章里,作者选取时间史观为切入点,分析了时间史观与小说叙述方式的互动关系。古代循环史观与讲史小说因果报应,治乱循环的基本编码对应;当代“斩首”时间,取消未来的时间史观又与“红高梁式”的历史叙述和后现代式的平面化叙述对应。革命历史小说遵循着“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的模式构思情节,并依照阶级在时间长线上的“前进”程度安排人物关系。这种小说叙述方式与进化史论彼此应和着。从文本和不同叙述里可见不同的时间史观,而不同时间史观的影响下又有小说叙述方式的变迁线索。两者的互动使美感形式与历史感的结合浑然一体。作者把古代、当代的时间史观与小说叙述方式互动关系的考察,作为考察进化史观与革命小说叙述方式的背景材料,从整体上加深了历史的纵深感,避免提供一种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革命·土匪·英雄传奇》,作者展现了英雄传奇题材中土匪这一人物形象与革命的互动关系。梁启超的“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与定一的“吾观《水浒》诸豪,尚不拘於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对《水浒传》中绿林好汉的两种不同价值评判,成为了“诲盗”转变了“诲道”(革命之道)的标志。此后文本中的土匪形象与革命关系更加密切,先是阿Q式的人物形象的肯定, 继而变成“抢一个共产党人领路”,(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土匪形象与革命的互动昭然显示。80年代中后期“土匪从意识形态的兵营反出江湖”(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英雄传奇题材中土匪形象由“诲盗”——“诲道”——“反出江湖”的逻辑发展,与革命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连。历史感与美感形式的结合又再一次得到充分的表现。此外《革命·性·长篇小说》、《革命的经典化与再浪漫化》,作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历史变迁(主要指革命历史变迁)与小说叙述方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呈现丰富复杂的革命历史原貌。
1986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黄子平提出了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主张。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即要“走进文学”,注重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强调形式特征、审美特征;又要“走出文学”,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民族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联系。这时期黄子平对文化批评视角的关注,还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讨,9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已把文化批评的视角引入了文本分析。文化批评是继形式主义批评之后在西方广泛使用的一种批评,它主要指涉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批评的研究。要求引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种种参数,把文学“文本”纳入广阔的社会语境中去考察。文化批评的早期倡导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途径》里说:“批评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文学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关注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文化现象。”(注:路文杉《救救文学批评》,《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他又认为“二者之间要相互平衡,任何一方排斥另一方,批评的视野就会出现偏差。如果能保持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中,批评家从作品评析发展到更大的社会问题的讨论理论的过程就会更加富于智慧。”(注:路文杉《救救文学批评》,《文艺争鸣》,1998年第1期。 )中国当今的批评界,许多人热衷于从文化视角分析文学作品,而忽视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观照,破坏了批评内部两者的平衡,由此“救救文学批评”的呼声此起彼伏。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一方面从文本形式分析入手,另一方面又引用了文学以外的文化分析因素,把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考察,同时又赋予了自我生命的体悟。《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选取了革命历史小说中常出现的一些来自民间的语词,如道观佛堂、圣地、脱胎换骨、报仇报冤报恩、革命等等,把它们放入具体的文本中分析革命历史小说是如何叙述这些话词。作者把这种片断性进入文学叙事而又“混而析之”的民间信仰文化资源,称为“小说中的宗教修辞”(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分析过程中,作者引入了文化批评的视角,从政治与叙述的关系,考察了当代意识形态与传统信仰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庙宇祠堂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多安排为“阶级敌人”作奸犯科的场所。《白毛女》的歌剧和电影中,地主黄世仁在庄严、圣洁的宗教空间里的禽兽行为,使他在冒犯尚未建立或刚建立的革命秩序和被确认为政治上的敌人之前,首先就成了冒犯民间伦理秩序的敌人,被置于伤于害理、人神共弃的位置。于是民间伦理秩序的稳定成为了政治话语合法性的前提。作者认为以无神论为哲学——神学基础的50—70年代的文学叙事,它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传统信仰文化有着紧张对抗关系,但又无法不从中吸取文学想象的资源,以营构其阅读与理解的可能条件。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如何借助宗教的(神/魔)、(正/邪)得到表达,从而创造在民众中阅读理解的可能。在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中,政治借助民间传统文化使阅读理解成为可能,民间传统文化又趁此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宗教修辞因而存在。政治与民间传统文化以及小说叙述方式的互动关系被揭开。文化批评的视角开拓研究的领域,使人能不断跳出限定的框架,以立体思维的方式去暴露现存文体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的多元性,发现隐藏事物后面的意义。
二、生命的体悟
文学作品的再解读具有开阔视野、去蔽的功能,而如今许多再解读纯粹为了追求新奇,以理论游戏与文学游戏戏弄作品、晦涩费解、枯燥乏味、缺少与他人情感的沟通和交流。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再解读不仅充满了智慧,而且积淀着他个人的生命体验,语重心长的话语间渗透着一种深沉的悲凉,震荡人的心灵。“批评首先是一种阅读,读灵魂,读人生,读历史,读社会,是一种伴随着焦虑和困惑的沉淀。”(注:黄子平《关于(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评论》,1987年第4期。)黄子平在把人们的偏见,自以为是,心理障碍,荒谬生存状态以及各种复杂多元性暴露时,又匆匆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对现实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病的隐喻和文学生产》一文里所揭示出的文学成功的“住院治疗”,使作者深深的优虑:“如果文学家能被‘治愈’,文学(作为知识者对时代、民族的道德承诺的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学)真的能被治愈吗?……社会群体真的可以视作与人的身体一样的有机整体吗?文学真的是医治这种有机体的一种药物吧?文学家的道德承诺与他们实际承受的社会角色之间,真的毫无杆格吧?”(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当代文学写作,正如别的写作一样,将再次投入以叙述捕捉时间的新一轮旷日持久的挣扎之中。”(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对文学、文学家命运的关注始终萦绕在先生的心头。历史不仅意味着已经流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黄子平的再解读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焦虑的功能。而沉载着作者的关切与焦虑的疑问与告诫是他用生命体悟而得的心灵之语。
《灰阑的叙述》是《革命·历史·小说》中最能传达生命感知的文章,黄子平把它放在篇未,为有意为之。“灰阑记”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民族传说,两个妇人争夺一个孩子,最后包公用在灰阑边拔河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不忍心拉坏孩子故而松手的,必是亲生母亲。现代人倾听历史,同时也缘于其特定的时空而向历史发问,德国的布莱希特就作过《高加索灰阑记》,分的询问是:那位抚养孩子的仆人反倒可能比亲生更爱孩子,故松手的反而是她。80年代香港作家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对历史的质询更富有现代意识,她没有纠缠于到底谁是真正的母亲这一说不清的问题,而是在审判过程中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聚光灯照在包青天身上,一节都由英明的包大人包办,而当事人寿郎何以从来没有被询问过呢?小孩的意愿难道就不得尊重吗?西西的小说使得被历史长期遮蔽的寿郎获得了说话的权利,让我们倾听到孩子的声音:为什么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一直要由人摆布?西西出乎意料的发问,质询了传统,质询了传统中的每一个人,使得历史在瞬间敞亮了。西西的质询在作者心中引起了共鸣,通过对文本结构的分析,作者寄寓了自己对弱小者的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关注:“在这喧嚣嘈杂的世界上,谁能听到这些灰阑中微弱的话语?谁愿意倾听它们?谁愿意,肯定他们自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微弱的声音能改变灰阑外的世界,改变权力者们的意愿吗?”(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个人面对历史的渺小,个人面对历史的无奈,以及个人命运在历史沉浮中的无法把握,被作者倾注于笔端,了字句句凝聚着作者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并不意味着对人生的绝望。“本书不想为读者提供又一种固化的文本意义,欲只愿意展示作者——作为基本上由‘革命历史小说’滋养了因而也拘限于其阅读想象力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寻求新的解读可能性的艰难过程。”(注: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禅,1996年版。)黄子平在再解读革命历史小说过程中的艰难寻找,流露出对理解的渴望。现实的关切,未来的焦虑与渴望理解的追寻,交织融汇成一种人生的悲凉,浸渍于字里行间,生命的体悟静静流淌。
在《革命·历史·小说》里,黄子平对革命历史小说的再解读,充满着智性真切的生命感情。历史感与美感形式的结合,便于梳理文学的发展,使其面目清晰可现,增加其厚度;而文化批评提供广阔的视野,具有去蔽的功能,凸现出文学及有关文学的丰富复杂性,增加其宽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生命的感悟打开了情感的大门,消除了读者与文本的隔膜,读者与他一同溶入文本之中细细品尝。在批评界危机四伏的现状中,黄子平先生的智性与生命体悟所形成的成熟、真切的批评风格具有一份独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