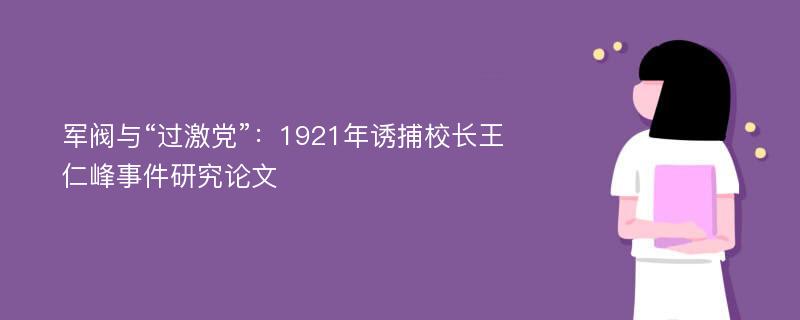
军阀与“过激党”:1921年诱捕校长王仁峰事件研究
周 宁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1921年4月,驻扎合肥的新安武军在市面发现盖有省立二中印章的《自由魂》,遂以“过激党”罪名将校长王仁峰诱捕。此事经媒体报道,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各地皖人积极营救,当局迫于民意压力随即将王仁峰释放。诱捕事件的背后,一方面反映了地方的新旧冲突,一方面也与安徽此时正在兴起的党狱风潮密切相关。王仁峰最终获释,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尽管是北洋军阀专制时代,团体形成的民意表达仍是各方不能忽视的一个力量。
[关键词] 军阀;“过激党”;《自由魂》;王仁峰
“过激党”在北洋时期悬为厉禁。但何谓“过激党”,北洋政府对此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一方面,他们对“过激党”异常敏感;另一方面,他们对过激思想往往又疏于管控或无力管控。1921年,新安武军以“过激党”名义将王仁峰诱捕,随即又迫于民意压力将其释放,多少反映出北洋军阀对待此类事件的模糊心态和处境。
一、王仁峰被捕
王仁峰,字霭如,安徽舒城人,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柏文蔚参加革命,后因试造炸弹,失去左臂。二次革命后,王仁峰回乡创办舒城第二高等小学。[注] 参见舒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舒城县志》,第603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由于办学成绩突出,且有光辉的革命经历,王仁峰在青年学生之中具有较大威望。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倪嗣冲倒台,政局的变动在安徽引发了教育革新的浪潮。省立二中校长汪淮自行辞职,在同乡的保荐和学生的一致拥护下,王仁峰出任省立二中校长。
王仁峰到任后,对二中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颇得趋新人士的厚望。然而仅仅时隔半年,王就陷入了一场牢狱之灾。缘合肥市面发现《自由魂》小说,上面盖有二中图书室印章。后经人告发,认为二中收藏过激书刊,校长王仁峰难辞其咎,有“过激党”的嫌疑。1921年4月13日,新安武军七路二营营长杨其武派人持舒城县知事柯旭初名片,邀王仁峰到新安武军军营会商。王仁峰与柯旭初同乡,且是好友,不察其中有诈,赴会后随即失去人身自由。
平心而论,杨其武仅是新安武军营长,在军中地位并不算高,与王仁峰又无任何个人恩怨,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实施诱捕呢?其实,这并非杨其武的个人决定。王仁峰赴会后,“合肥知事蔡焕飏、七路帮统金志昌、六师校长许拙云及当地劣绅等均在座。比由杨营长取出自由魂小册一本,谓盖有二中图书室戳记,认峰为传播过激主义。有主张将峰枪毙,或解蚌。经峰力辩,彼辈仍悍然不顾,幸得龚瑞生、袁斗枢、马仲武、汪镜人诸人援救,得免于死”[1]。从这段事后王仁峰的回忆,抓捕的现场更像一场公诉与批判大会,几乎所有合肥的政界、军界和教育界要员均在现场。合肥知事蔡焕飏等人为什么非要置王仁峰于死地呢?其实,事情的起因并非收藏一本《自由魂》小说那么简单,诱捕的背后不仅牵涉复杂的人事恩怨,而且与合肥新旧势力的冲突有紧密的关联。
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在安徽得到广泛传播,但从空间看并不均衡。芜湖受新文化影响较深,趋新势力比较活跃,合肥虽然是皖北重镇,但整体氛围相对沉闷。[注] 不仅是合肥,即使是省城安庆,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都很有限。署名“钓叟”的作者说:“安庆城内的学生没有看新书报的,听说安庆商务书馆带了几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去,摆了好久,才有一个第一中学的学生买了一部。”参见钓叟:《芜湖文化运动记》,1920年1卷9期。 1920年安徽的这场教育革新浪潮,合肥虽卷入其中,但更多是被动参与,[注] 芜湖、安庆两地学生教育革新规模大、参与意识强。1920年安徽中等以上学校学潮19次,其中芜湖、安庆10次,合肥仅二中1次,且这次多少又有些被动色彩。有报道称,二中学潮爆发后,经人调停,学生回校上课,“对于校长问题亦冷。后数日闻某校学生,因见二中风潮平息,久之恐汪淮稳固位置,不易摇动,急派同学两人亲至合肥,一则侦探消息,一则鼓吹驱逐。因此二中全体学生,大为感动,同学和好如初,而一方面积极进行。”参见《安徽教育界近闻》,《中华新报》1920年11月1日。 除了省立二中,整体的教育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当二中校长汪淮辞职之初,合肥教育界谋继者不乏其人,其中以合肥教育会会长刘冠卿呼声最高,“后所图不遂,遂抱恨于王”[注] 在抓捕现场,刘冠卿的态度最为激烈,“大放厥词”,“在座诸人,亦莫敢反对”。参见《皖二中校长被捕因果》,《民国日报》1921年4月29日。 。王仁峰上任之后,虽然得到旅外同乡的大力支持,但在合肥教育界毕竟是陌生的外来者。他性格刚介,不善交际,很快就得罪了合肥的一帮守旧士绅。比如,合肥县知事蔡焕飏“欲谋改代为署,要求签名公电省长,王校长以其事为官厅之权衡,雅不愿越俎行事,婉言却之。蔡遂挟恨与劣绅一同串谋,设计陷害”[2]。更为重要的是,王仁峰大刀阔斧的对二中进行改革,“谋画校务的改进,不遗余力,购置新出图书,聘请优良教员,以及校内种种设施,都能着着进行,而且‘经济公开’、‘校务公开’。师生之间,和同一气”[3]。这些举措虽深得二中学生拥护,但在合肥教育界平静的一潭死水无异投下了一颗石子,“合肥的社会太顽固守旧了,看见本校有革新的气象,就不免多生怀恨”[3]。此时市面上发现盖有二中图记的《自由魂》小说,无疑给保守势力报复王仁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究竟《自由魂》小说是否为二中收藏,王仁峰事前知不知情,这些细节已经不再重要,从抓捕现场各方守旧势力云集,不难看出王仁峰被捕是新旧冲突的一个生动缩影。
二、各方营救
新安武军为什么要以“过激党”名义抓捕王仁峰?幕后难道仅仅是地方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吗?张文生迫于舆论压力,将王仁峰移交地方审理,为什么仍然认为其有“过激党”的嫌疑?质言之,军方是在何种背景下逮捕王仁峰?
其实,早在4月17日王仁峰被移交合肥县审理的当天,省长聂宪藩迫于舆论的压力,已经命令合肥县知事蔡焕飏将王仁峰释放。因为此时的王仁峰无异一块烫手的山芋,张文生既然有意将此案与军方进行切割,聂宪藩自然犯不着触犯众怒,继续将王关押。王仁峰出狱之后,一方面由于媒体报道的时差,一方面由于此案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舆论的抗议之声并没有就此平息,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案件交涉的重点也渐渐由“放人”转到”惩凶”之上。省立二中学生发表宣言,要求惩办杨其武,撤换蔡焕飏,将新安武军移驻他处,并明确“今后军人不得干涉教育”[3]。与此同时,二中学生“派代表分赴安庆、芜湖等处”,为王仁峰伸冤,并致电“本省军政长官,严惩驻肥军官,及此次教唆主谋之人,科以摧残教育违法逮捕之罪”[10]。4月24日,旅沪安徽救国代表团、皖事改进会、新新社、皖民公社、自治协会在上海集会,并于次日致电张文生,“将越职拿人之军官,从严惩办,悬为厉禁”[11],以此平抚民心。
当然,王仁峰案件之所以引起舆论强烈关注,并不仅仅是《民国日报》的报道,案件本身可能引发的后果,这也是公众和媒体更为关心的问题。首先,就事件本身而言,《自由魂》是否是二中收藏,能否据此逮捕校长?二中学生发表宣言,就明确指出:“过激二字,国家悬为厉禁,吾恐纵有传播之徒,亦必隐匿名姓,希逃法纲,岂有发散自由魂者,而盖图书室戳记于其上者哉。”[2]该书在市面发现,二中图记又真伪莫辨,教育界的质疑的确不无道理。更重要的是,“岂得紧凭书面印有学校图记,即认为校长之所为”[12]。其次,《自由魂》是否是禁书,收藏阅读过激书刊是否有罪?二中旅京同学会称:“查此书寄自省垣,传播已久,取缔命令闻尔未闻,其非禁书已可概见。”[13]既然“未经法律干涉出版于先,复未经明令禁止销售于后,则购阅之人例不负责”[14]。署名“一苇”的作者投稿《中华新报》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在共和国家有绝对自由,纵使在现代国家最压迫言论的日本,也“只加罪于著书或出版之人,于讲书或藏书人无涉。盖加罪名义在于宣传危险思想,苟不宣传则无关社会”[15]。应当说,这些言论的背后表达了一种隐忧,即何谓过激思想,言论自由又如何保障?在事情稍稍平息之后,安徽地方促进会就致电北京总统府和国务院,要求明确思想和言论禁止的范围:“究应认定何项不准人民加以讨论,及购阅书籍,倘或任意吹求,凡所不快之人皆得以过激二字文致栽害,毁法诬民,恐流毒所煽,国将不国。敝会为维持安宁起见,用敢电请钧处将过激义意详加解释,及犯此项罪名者应具条例,迅赐依法裁决宣布,俾国民知所从违,而陷害浇风庶可稍杜。”[16]再次,军方能否以收藏过激书刊罪名逮捕校长。芜湖学术研究会称:“犯罪拘捕,应由司法衙门依法办理,军队不应越俎侵权。”[7]合肥旅省学生同乡会更是明确指出:“军队既无执行普通法律之权,校长更无受军法裁判之制”,“乃该驻防军队,不察事实,横肆逮捕,实属破坏约法摧残教育”。[14]不仅如此,“如果此风一开,凡居内地之有新智识者将人人陷于危地。今日可藉口一图章以捕人,则异日便可假造图章,或故意递寄书籍,以陷人。今日可自由拘禁,则异日便可自由枪杀。凡教员、学术或新闻记者之流,平日稍获罪军警,则结果皆可以社会党或过激党之名义,为其蹂躏,或丧其生”[15]。二中学生更是声称:“我们校长无故受辱,对于他个人,本来不成什么问题,不过既有了这个例子,将来中等学校的校长,不管他是好是歹,他的去留权,不在省长,不在教育厅,不在学生欢迎与否,全在一个营长的‘喜怒为用’了。”[3]确实,新安武军不经司法审判,擅捕王仁峰,严重践踏了法律程序,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事件连锁反应的担忧。张文生在事发第四天,命令新安武军将王仁峰移交合肥县审理,正是出于避免这种瓜田李下之嫌。新安武军莽撞与蛮横的行为,再次印证了军阀对教育界的摧残,同时也加深了教育界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就安徽而言,这恰恰又成为随后军阀与教育界彻底决裂,安徽1921年“六二学潮”爆发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随着高校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高校毕业生每年都在不断增长,高校培养出的优秀毕业生正在走向社会,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顺应市场的需求也出现人才流动,教师在工作中取得的科研成果也正在被转化成产能应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高校档案馆在这场变革中应该积极发挥档案馆的作用,不能停留在传统的服务功能上,而要提升创新服务的能力,不断满足师生对高校档案资源的新需求,实现高校档案馆更高的服务价值。
在生物医药领域:以稳定性同位素的生物医药应用为核心,形成“稳定性同位素应用技术中心”创新平台,为肿瘤检测、诊断试剂、药物中间体、生命健康、食品安全、营养保健、检验检疫、现代农业、资源环境等领域提供行业技术服务。
得到通过最小二乘法可得到通道特性曲线如图4,取5倍码速率带宽作为参考带宽,GEO-1卫星通道幅频抖动约为6.44dB,群时延抖动约为17ns.图5(a)给出辨识前后信号功率谱对比图,图5(b)为I支路信号相关曲线图形,从功率谱对比图中可得知辨识后信号功率和接收信号功率谱符合度非常高.由于通道群时延特性对信号测距影响较大,通过检验辨识前后相关曲线能够有效地判断通道群时延估计的准确度,在相关曲线对比图中可得知,辨识后信号和接收信号的相关函数在一个码片内重合度达到了99.83%,由此可知最小二乘法通道估计方法能够真实反映信号通道特性.
应当说,公众的抗议和媒体的报道形成了叠合共振,扩大了此案的影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某些报刊倾向性的报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仁峰早年参加革命,为同盟会会员,上海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创办,且一贯对教育界持同情态度,这种党派的纽带和共识,让《民国日报》对此案保持异乎寻常的关注。[注] 从4月20日到5月上旬,《民国日报》几乎是每天不间断地跟进报道。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最初几天,安庆、芜湖两地求援的电报相当简略,王仁峰被抓的具体细节,媒体亦语焉不详。《民国日报》此时的跟进报道成为公众认知此案的重要管道,但其中不乏一些想象和夸大的新闻。比如,《民国日报》记者陈德徵将王仁峰被抓归因于张文生,称:“张文生近来对于皖省教育,异常嫉视,不但禁止各界言论,并且连百姓底读书看书的自由权,也剥夺尽了”。[6]王仁峰思想开明,鼓励学生阅读新书,所以引起了张文生的仇视之心,“便发了一道虎威式的命令,说第二中学看禁书,叫聂宪藩饬合肥县知事把第二中校长看守起来”[6]。应当说,张文生反对新思想、新文化是事实,但就此案而言,事前并不知情,这种有政治倾向的报道,除了鼓动舆论之外,更多的是反军阀的现实需要。
面对教育界的抗议,张文生也自觉由军方逮捕校长过于孟浪,随即复电称:“中等学校刘校长诸君暨教职员联合会均鉴:谏电悉。王仁峰因留匿违禁书籍,发觉被管。现已饬营移县,查明覆夺。”[7]张文生意在将此案划归民事管辖,使新安武军摆脱舆论旋涡。不过在电报中,张仍认定王仁峰有“过激党”嫌疑。这种模糊的表态引起了各地皖人和团体更大的愤慨。4月17日,安徽学生联合会首先以通告形式致函上海全国学生联合总会、全国各界联合会,称:“敝会以事关切肤之痛,呼救已逾数日,王仍被押未放,未知结果如何。黑暗至此,宁有天日,此而不争,则一班武人官僚群起效尤,我全国教育界宁有言论出版自由之一日乎。”[8]安徽学生联合会的公函很快得到上海学生联合总会和全国各界联合的积极响应。4月22日,他们复电称:“驻扎合肥之安武军第三营营长及合肥县知事,因市面发现自由魂一书,擅捕第二中学校长王霭如,莫须有三字之冤狱,复见于今日。本会闻之,不胜愤慨。”[9]他们要求,“除开释王校长外,并处合肥军民官吏,以相当之罪”[9]。
三、党狱风潮
王仁峰被捕之后,杨其武、蔡焕飏等一方面致电安徽军政两长请示处理办法,一方面“派兵把守电局,检查电报”,[4]封锁消息。[注] 应当说,军方的舆论管制取得了暂时成效。王仁峰在4月13日被捕,但直至4月19日以后,此事的报道方才见诸上海报刊。 面对军方的舆论管制,王仁峰的亲朋好友不得不另辟救助的渠道。“旋由王友舒城县知事柯菊初,省议员马仲武,派人到安庆公呈省长,转电张督军,请饬该营释放。”[4]4月15日,在获悉事件大致经过之后,安庆教育界立即紧急行动起来。安徽省教育会和省城校长联合会先后致电张文生,要求释放王仁峰。随后,省教育会代表谒见省长聂宪藩和教育厅长张继煦,请其与张文生做进一步交涉。当晚八时,省城教职员联合会“假教育会大会场,开全体会议,到者二百余人,公同讨论,除电张文生外,公举代表三十余人,往见聂宪藩,不达释放目的不止”[5]。与此同时,芜湖方面也迅速做出了反应。4月16日,教职员联合会致电张文生,要求“一面释放无辜,一面惩治非法,以肃军纪而维教育”[6]。省立五中校长刘希平和二女师校长阮仲勉等人也于当天联名发去谏电,质问“究因何罪,纳入军事范围,请速宣布,以平众愤”[6]。
2.主动探索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根据中央精神,在温州“建立民间融资备案制度”的指引下,着手准备设立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让资金持有者手里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人士进行经营,由国家政策进行引导,可以缓解国家和地方建设资金不足,也减少了资金持有者盲目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It can be calculated that two pole frequencies will merge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flattest gain response with condition(9), which has been studied previously in Eq. [4], and then there will be only one pole frequency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king frequency band.
这里不得不提到早期安徽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问题。五四运动后,北大教师蔡晓舟回到安徽,先后创办《黎明周报》《安庆学生》《洪水》和《新安徽》等进步刊物,并向法专进步学生和学联骨干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他和省立一师教师刘著良以文化书店为掩护,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据周新民回忆,1921年春,由蔡晓舟主持,“在怀宁县学宫开了一次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会。到会的有方乐舟(曾连任安庆学联会会长)、童汉璋(曾任安庆学联会会长)、宋维年(曾任安庆学联会秘书)、王先强、胡养蒙(以上均系一师学生)等二十余人。当时即被警察发觉,被迫提前散会。同年四月间,蔡晓舟又在菱湖公园茶社召开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大会由蔡晓舟主持,刘著良讲解社会主义,并散发一些小册子,其中有关于青年团的文献。这次到会有四、五十人,多是安庆各校学生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中,忽然发现大批军警向会场开发,为了避免牺牲,中途宣告散会,到会同志分途逃走。筹备会和成立会,均经军警干涉,未得终场”[17]398-399。
对于早期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活动,安徽军政当局早有觉察。1921年三四月间,安庆方面就已经开始清查过激主义书刊,“皖省于未发生过激党案前,屡由上海寄到过激书籍,且封面书有省长公署龚某查收字样,经检查信件员窥破,将书扣留,一面呈由警务处,面询省长,究竟公署有无此事。省长以冒捏相告,并令凡省署信件,同附检查,以杜蒙混”[18]。对于进步书籍的传播,当局可以说是高度戒备。由此不难想象,此时市面发现《自由魂》小说,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王仁峰早年的革命经历,更不免让当局怀疑其是有意收藏禁书,向学生传播过激思想。在抓捕现场有这样一段对话,颇能反映军方这种心态的敏感。杨其武在拿出《自由魂》的证据后,“就拿出一付阎王的面孔来,厉声说:‘你现在好了,还在我这个地方倡过激主义呢!上回木匠罢工想必是你鼓吹的了。’我们底校长说:‘我办我的学校,别的事一概不管,哪里知道什么罢工不罢工,过激不过激呢?请你细细地查问查问。’”[19]因《自由魂》而联想到罢工是王仁峰幕后主使,正是这种有罪推理的逻辑,使得杨其武和张文生始终认定王仁峰有“过激党”的嫌疑。
其实,王仁峰被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在王仁峰被捕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党狱风潮正在酝酿之中。4月22日,张文生突然致电安庆军警,要求查封《民性报》《新安徽报》,逮捕蔡晓舟、孙希文等十人,[注] 十人分别为孙希文、蔡晓舟、高语罕、王肖山、孙养臞、周世筠、凌昭、凌毅、洪世奇、李次山。 罪名是“挑拨政界恶感、学界风潮”,“扰害大局,以过激书籍报章,肆意鼓惑”[18]。4月24日,军警分两队前往报馆进行搜查,孙希文等人仓促逃亡上海等地避难。从抓捕名单看,有民党分子,有报界精英,有教育界中坚,还有蔡晓舟这样的中共早期党团骨干。此时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舆论轩然大波,“一苇”在评论王仁峰案时,就一阵见血地指出:“就事实言之,安徽军警实正酝酿一大狱,安庆风潮闻之久矣”。[15]4月26日,上海皖事改进会等团体集议,向张文生提出强烈抗议。[20]随即,旅京安徽团体也迅速做出反应,由北大教授胡适、高一涵、王星拱等领衔,发表通电,称:“合肥军队既已擅捕二中校长王仁峰,督军张文生又复以过激党罪名诬教育界高、王、洪、周等十人,行文通缉,似此藐视约法,摧残教育,蹂躏人权,岂复有血气者所能忍受。”[21]他们表示将“联合京、津、沪、宁教育界同人,一同返皖,偕三千万皖人与蛮横军人一争公理之胜负” 。[21最终迫于民意压力,张文生承认“前次命令为无意识”,[22]“只通缉蔡晓舟一人,其余概无干涉”[21]。
四、结语
纵观王仁峰事件,固然与新旧势力冲突有关,但其之所以被捕,更多的是因为其有“过激党”的嫌疑。一方面,安徽早期党团分子的积极活动,已经引起当局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诸如《新安徽》和《民性报》这样的媒体频频批评军阀暴政,[注] “皖省此次党案,罗织至十余人之多,就中如孙养臞为民性报主任。该报为纯粹民意机关,反对一五附加、八分米厘最力。孙又为民治运动中,旗帜最鲜明者。蔡晓舟为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主持新安徽月刊,对于旧社会抨击最力。因此孙、蔡二君被指为过激派,两报亦相继停版。”参见《皖省党案之源源本本》,《民国日报》1921年5月23日。 不免让当局怀疑这是一场有组织和预谋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撩拨他们敏感的神经。此时,市面发现盖有二中图记的《自由魂》,身为二中校长,王仁峰自然也就难逃其咎。王仁峰尽管被抓,但其是不是“过激党”,当局并没有清晰的判断,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由魂》做有罪推理。他们往往将传播社会主义等同于“过激党”。[注] 一苇就指出:“近年常见官场禁令,辄混社会主义与过激党为一谈”。参见一苇:《合肥中学案》,《中华新报》1921年4月30日 但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在当时一个比较驳杂的思想,其间涉及很多的流派,分支与流派之间也有不同的倾向。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过激思想,不仅太过笼统,也反映出当局对思想无力进行管控。[注] 胡适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参见曹伯言主编:《胡适日记全集》(三),第33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王仁峰被抓之后,安徽教育界一方面与当局积极进行交涉,一方面通过媒体扩大事件的影响。从合肥到安庆,从芜湖到上海,各地皖人迅速动员,并保持密切沟通。他们联合向张文生施压,最终迫使当局将王仁峰释放。应当说,在这场事件中,各方的营救迅速而富有成效。营救成功的背后多少也反映出,尽管是北洋军阀专制时代,团体形成的民意表达仍是各方不能忽视的一个力量。
[参 考 文 献]
[1] 皖人请摧残教育者[N].民国日报,1921-05-04.
[2] 二中学生之第三次宣言时报[N].时报,1921-05-30.
[3] 皖第二中学生拥护校长[N].民国日报,1921-04-24.
[4] 皖省近闻纪要[N].新闻报,1921-04-29.
[5] 皖教育界营救校长[N].民国日报,1921-04-22.
[6] 德徵.张文生逮捕校长[N].民国日报,1921-04-20.
[7] 王霭如被捕后消息[N].民国日报,1921-04-23.
[8] 安徽学生总会之两要电[N].申报,1921-04-21.
[9] 两团体营救合肥校长[N].民国日报,1921-04-23.
[10] 皖二中校长被捕因果[N].民国日报,1921-04-29.
[11] 皖团体请惩擅拘校长[N].民国日报,1921-04-26.
[12] 旅沪皖人对于王仁峰被捕之力争[N].晨报,1921-04-26.
[13] 二中旅京同学会之呼吁[N].时报,1921-05-10.
[14] 合肥社会之黑暗[N].民国日报,1921-04-29.
[15] 一苇.合肥中学案[N].中华新报,1921-04-30.
[16] 皖人对王仁峰被捕案之要求[N].晨报,1921-05-06.
[17]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省档案馆周新民.安徽早期党团组织史料选[M].河南固始县印刷厂,1987.
[18] 安庆军警查封报馆[N].新闻报,1921-04-28.
[19] 天愁.武人诱捕校长[N].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04-22.
[20] 安徽党狱之沪讯[N].申报,1921-05-04.
[21] 皖军阀罗织党狱[N].民国日报,1921-05-15.
[22] 皖省党案之源源本本[N].民国日报,1921-05-23.
Warlords and "Radical Party ":a Study on the Incident of the Arrest of Principal Wang Renfeng in 1921
ZHOU N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Abstract :In April 1921, the Xin'an Army stationed in Hefei found the Free Soul with the official seal of No. 2 High School of Anhui Province in the market. And e principal Wang Renfeng was arrested on a charge of "Radical Party." The incident was reported by the media and aroused strong public concern. People across Anhui Province began rescue work immediately. Principal Wang Renfeng was released by the authority forced by the pressure. Behind the trapping incident, on the one hand, loc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were exposed ,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ing trend of party prisons in Anhui at that time. Wang Renfeng was finally released.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although it was the era of the tyranny by Northern Warlords , the expression of public opinion formed by the masses was still a force that could 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Warlord;Radical Party;Free Soul;Wang Renfeng
[中图分类号] K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2273( 2019) 02- 0017- 05
[收稿日期] 2019- 01- 18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晚清民国安徽学潮研究”(AHSKQ2016D128)
[作者简介] 周 宁(1978-),男,安徽阜阳人,历史学博士后,安徽财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
(责任编辑 陶有浩)
标签:军阀论文; “过激党”论文; 《自由魂》论文; 王仁峰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