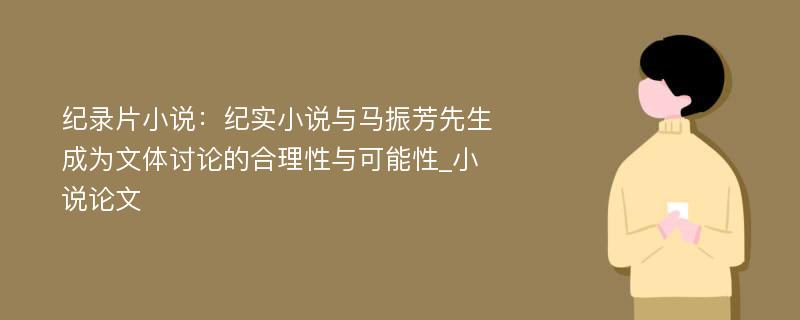
纪实小说:作为文体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关于纪实小说与马振方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实论文,合理性论文,文体论文,可能性论文,说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纪实小说”这一概念能否成立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过。笔者就此作过概述,也顺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见拙作《纪实小说:争议中的生存》,1999年第3期《小说评论》)。最近, 《文艺报》发表马振方先生的文章《小说·虚构·纪实文学》(见《文艺报》1999年10月23日),对“纪实小说”持完全否定的观点。马先生是研究小说的专家,笔者普读过他的小说理论专著。但他的这篇文章,笔者却不能信服。
一、纪实小说创作方兴未艾
马先生文章的一个小标题叫作“‘纪实小说’何处寻”,意思是找遍天下也找不出真正的纪实小说,这一见解未免狭隘。
如果我们着眼于世界文坛,不难发现“纪实小说”这一词语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它在国际上有着相当高的使用频率,世界文坛上有着相当多的纪实小说代表作和因创作纪实小说而享有盛誉的作家。
50到60年代,美国就已经有了纪实小说。1952年,《纽约人》杂志发表了莉莲·罗斯报道一个电影公司事实的纪实小说《影片》。随后,被作者卡波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在冷血中》,成为公认的“新新闻主义”写作的领头羊。同期引起人们关注的作品还有汤姆·沃尔夫的《糖果色桔子皮流线型宝贝》《电冷却酸性试验》,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盖伊·塔利斯的《王国与权力》等等。70至80年代,美国的纪实小说创作得到长足的发展,代表作家是诺曼·梅勒。他又陆续创作了《迈阿密和芝加哥之围》《玛里琳》《刽子手之歌》等多部纪实小说,其中《刽子手之歌》被评为全美1980年度的最佳小说。此后,威廉·肯尼迪的纪实小说《铁草》,戴维·希普尔的《阿拉伯和犹太人》,理查德·罗兹的《原子弹制造内幕》都曾获权威的“普利策文学奖”。美国作家在创作纪实小说时写作态度之认真也是惊人的。卡波特写《在冷血中》,用了五年时间对发生在堪萨斯的一桩凶杀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采访。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以近10年以来美国的第一例死刑判决为题材,访问了数百名证人,调阅了法院的全部审讯记录和诉讼原本,仅资料就采集了一万五千多页!对美国纪实小说的繁荣,葡萄牙著名作家文图拉有这样的评价:“每个民族都应找到自己的现实主义形式。……当拉丁美洲出现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比如诺曼·梅勒或杜鲁门·卡波特却在复制现实,创作报道性长篇小说。”(以上资料和引文参见尹均生《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文艺争鸣》1989年第2期)
前苏联的纪实小说创作也有辉煌的成就。恰科夫斯基的《围困》,卡尔波夫的《统帅》,阿列克谢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等,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著。德国还有以写纪实小说为主的“七○写作社”。日本的著名文学家石川达三、井上靖、森村诚一等,都有长篇纪实小说行世。
我国古代的纪实小说,马先生已用了“比比皆是”的说法,这里无需赘述。仅就当代文坛而言,早期的《红岩》《林海雪原》等,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小说,但有较多的虚构成份,这说明作者当时还没有较强烈的纪实意愿。即使如此,人们还是不愿意把它们和一般的虚构小说等同起来。可以说,这一类作品的纪实性是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因素,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将小说区分为虚构和纪实两大类的必要性。到了新时期,小说家写纪实性作品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但是由于创作思想的差异,他们对生活真实恪守到何等程度,彼此有较大的不同。梁晓声说自己的获奖小说《父亲》“没有虚构成份在内”(《关于〈父亲〉的补遗》,《小说选刊》1985年第6期)。 随后王毅捷也说自己的《信从彼岸来》“决无虚构之处,研究历史的人重事实,这是我的信条。”(《信从彼岸来·致读者》,《小说选刊》1985年12期)即使略有虚构,如刘心武所言“不可能全然没有虚构”(《开好这朵花》,《中国青年报》1986年2月14日), 以及邢卓所言“多有移花接木之处”(《就〈忌日〉的创作答读者问》,《十月》1985年第4期), 也不妨给以宽容。对此,笔者十分欣赏作家胡辛的勇敢和坦诚,她说“还原历史是一种限制中的虚构”(《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文艺报》1999年7月20日)。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说出了一般人不敢明言的真理。
近年来,纪实小说作品越来越多,不仅有短篇、中篇,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很大的长篇,如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和邓贤的《大国之魂》,接受纪实小说的读者也渐渐多起来,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该忽视。
二、纪实小说与一般纪实文学的不同质地
马振方先生在文中一再把纪实文学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对立起来进行比较。其实,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纪实文学是一个系谱概念,它包括许多文体,也包括纪实小说在内。我们可以摘引一些论述加以证明:“它下面包含有报告文学,传记,回忆录;有纪实小说(报告小说,非虚构小说);有社会大特写,文艺特写;有纪实电影,政府电视片等。”(尹均生《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纪实文学的外延较广,诸如传记、回忆录、报告文学、日记、书信、采访记实,以及写真人真事的叙事小说、纪实小说等等,都可以列入纪实文学之列。”(宗原:《关于纪实文学》,载《世界纪实文学》第1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纪实文学,是指那些纪实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回忆录、游记等等。”(王铁仙《新时期纪实文学丛书》序言,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由此可见,纪实小说是纪实文学的一个类属,将它们互相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
在纪实文学内部的分化、演进之中,纪实小说的产生有一定的必然性。
曾在新时期伊始迅猛崛起的报告文学,是当代纪实文学文体的出发点和生长源,讨论纪实文学的文体演进,应从报告文学开始。几乎所有的教科书在谈论报告文学时,都把“新闻性”看作报告文学的第一特征,认为报告文学是兼有新闻和文学两种基本特性的叙事文体,新闻性表现在它的内容因素和写作目的上,文学性表现在它的形式因素和写作技巧上。所谓的“新闻性”,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内容真实,迅速及时,有针对性和指导性。这些特性无疑是促进报告文学繁荣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文革”结束、改革伊始、国门乍开、百废俱兴的时候,报告文学以敏锐的嗅觉捕捉着时代的新鲜气息,径直切入现实生活,为刚从“文革”的文化沙漠走出来的人们提供着最为迅捷的文化滋养。但是,新闻性在为报告文学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也将报告文学置于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反映生活的敏捷,一方面是直扑热点的匆促以及因来不及沉淀造成的浅薄和速朽;一方面是高度的生活真实,一方面是文笔的拘谨和滞涩;一方面是思想性和指导性的突出,一方面又因过于直白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到了80年代中期,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已对过于突出新闻性的报告文学有所不满,于是,越来越多的纪实作家们开始有意淡化新闻性。这样,“当代社会纪实”、“历史题材纪实”和“纪实小说”就应运而生了。前两种文体是纪实文学克服新闻的匆促和速朽的必然产物,而纪实小说则是纪实文学克服拘谨滞涩寻觅艺术灵性的必然产物。因而纪实小说的诞生,应该看作是拯救纪实文学的一种努力。
纪实小说的质地,一般可见的有如下方面:一是内容的细节化。它不像一般纪实文学那样为了躲避失实的嫌疑小心翼翼地不敢张开想象的翅膀,而敢于运用合理想象去填补细节的缺损。二是作者主观抒情成分的强化。在纪实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字不再是“纪实”而是“纪虚”的——作者的主观感受不是现实,但它却是文学艺术不可缺少的因素,否则作品难免拘谨板结。三是表现内容的意象化。这是与前两点有联系的,具体说来,描述意象、比喻意象、象征意象等,在纪实小说中要比一般纪实文学丰富得多。
更重要的在于纪实小说更为文学化的语言。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既不存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之中,也不存在于形象之中,而是存在于语言之中。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是两种功能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学语言是对实用语言“扭曲”、“变形”、“施加暴力”之后陌生化、反常化了的语言,它因此而产生阻抗性,使欣赏者获得了对事物的重新体验。当然,当代有些标明为纪实小说的作品并没能做到这一点,但这不是纪实小说本身的过错。
笔者认为,不管是纪实作家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更具有小说味,还是小说家厌倦了虚构而用小说的笔法去记述真实,都是不该被剥夺的正当权力。至于造假惑众,则不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都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