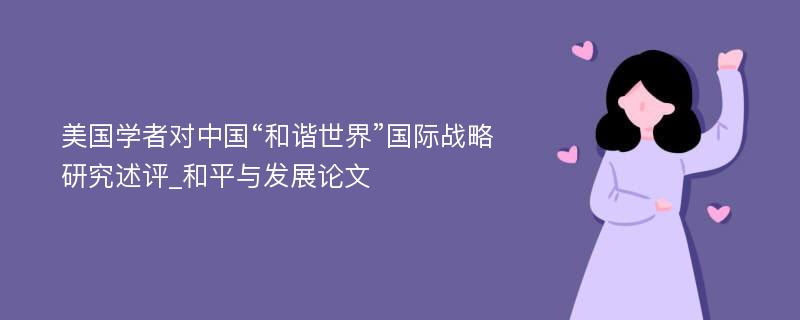
美国部分学者关于中国“和谐世界”国际战略的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学者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55(2009)05-0031-37
自2005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和谐世界”国际战略后,美国学术界就开始关注此课题,不少学者在学术杂志和各种新闻媒体发表论文加以探讨,相关学术著作亦陆续问世。如,2007年,英国牛津出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教授谢淑丽(Susan L.Shirk)的著作《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马里兰州兰哈姆(Lanham)出版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郭苏建(Sujian Guo)和路易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政治系教授华世平(Shiping Hua)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因素》。2008年,兰哈姆出版郭苏建和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简·马克(Jean- Marc F.Blanchard)主编的《“和谐世界”与中国新的外交政策》,加州伯克利出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研究主任戴维·兰普顿(David M.Lampton)的著作《中国力量的三张面孔:实力、金钱与思想》,纽约出版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教授赵穗生(Suisheng Zhao)主编的《中美关系的转变:前景和战略互动》,纽约还出版亚利桑拉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谢尔登·西蒙(Sheldon W.Simon)等人主编的《中国、美国与东南亚:争论中的政治、安全和经济》。2009年,纽约出版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Quansheng Zhao)和查尔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政治学系教授刘国力(Guoli Liu)主编的《处理中国挑战:全球视角》,等等。此外,美国学术界还以“和谐世界”为主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如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Studies)2007年7月14至15日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举办第20届年会,其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新思维”。通过以上种种方式,美国部分学者对中国“和谐世界”国际战略的提出背景、内容和特点、实施的可能性及其作用进行较全面探讨。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简单梳理和评述,希望有助于中国学术界对此课题的更深入研究。①
一、关于“和谐世界”政略的提出背景
美国部分学者认为,“和谐世界”战略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中国领导层”“集体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和世界新形势发展需要。中国领导人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和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背景下提出“和谐世界”战略,既是为彰显其负责任大国形象、明示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亦是从自身和国际安全出发,希望以此促进世界和平。
第一,中国提出“和谐世界”战略,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和平关系,做负责任大国,以对付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密西根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中国如此强调“和”字,是因为它注意到,中国过去10年的成功发展引起其他国家疑虑。中国制定“和平发展”的理论显然是要世界其他国家放心,“是在试图向其他国家保证,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它可以与邻国、与世界大国保持和平关系。21世纪崛起的中国试图把自己跟20世纪崛起的其他国家区分开来——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崛起都分别给世界格局带来极大的紧张,甚至战争。”②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中心主任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和谐世界”理念“成为当今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路线”,“强调中国将不威胁或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此来试图让那些对中国崛起存在忧虑的人士放心,消除他们的疑虑。”③
第二,国际社会并不安全,充满纷乱。中国为国际安全,亦为自身安全,必须有所作为,有必要提出“和谐世界”战略。赵穗生指出:“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国家安全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传统军事安全外,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和有组织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等,已威胁到国际社会。”“为更积极应对国际挑战”,保障“公正和合理的新安全秩序”,亦维护中国安全,中国主张建设“和谐世界”。④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客座研究员、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陈有为(Youwei Chen)指出:“实际上中国希望扮演的世界角色,不是领导者而是平衡者:在这个相互敌对充满纷乱的世界上,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贫国与富国之间进行协调与平衡,力求使世界局势从紧张转为平和,从极端化与恶性化的危机重重往良性的和平与稳定方向转化。”⑤
第三,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对内主张建设“和谐社会”,所以对外主张建设“和谐世界”。这样,中国内政和外交相结合。简·马克和郭苏建指出:2004年后中国政府为解决国内财富分配不均和实现社会稳定,主张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领导层的‘和谐社会’理念颇一致。”“换言之,‘和谐世界’理念是‘和谐社会’理念在国际领域的延伸。”⑥ 纽约州哈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政治系教授李成(Cheng Li)指出:“(当今中国高层)把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国内政策连接在一起,说明中国在国际上促进和平,在国内促进和谐,在台湾问题上促进和解,三个‘和’字联在一起。”⑦
第四,胡锦涛为首的“中国领导层”亦需要制定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战略。简·马克和郭苏建指出:新中国每一代领导人都制定“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政策”,从毛泽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再到胡锦涛的“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理念,就说明这一点。“和谐世界”理念为胡锦涛新领导层领导下的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指导路线和原则”,为当今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采取行动提供依据”,“为改革和改善现有的国际制度提供理论基础”。当然,胡锦涛“新领导层”的“和谐世界”理念与此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尤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有“连续性”,但亦有“变化”。⑧
第五,中国“和谐世界”战略的提出与近年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亦有关。近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陈有为指出:“(中国)和谐外交的基础是实力与自信。没有实力,人家就不会跟你搞‘和谐’。中国是在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万多亿美元,拥有世界第一的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开展和谐外交的。”由于近年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要有所作为,就是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开拓外交领域,展现中国的独特外交风格。”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更要提出“和谐世界”战略。⑨ 简·马克和郭苏建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外交成功,军事力量提升”,所以,“中国政治和知识界的精英感到,他们能够而且应在世界事务中多做些事情。”美国亦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要求中国在帮助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解决如金融平衡等国际经济问题、应对国际环境挑战、处理安全问题等方面更有所作为。所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更要在国际上发出中国的呼声,提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国际战略,亦即“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战略。⑩
二、关于中国“和谐世界”战略的内容和特点
美国部分学者注意到,中国“和谐世界”战略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发展,如胡锦涛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关于“和谐世界”的解释只有四方面,亦即“坚持多边主义”、“坚持(经济上)互利合作”、“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推进联合国改革”。但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关于“和谐世界”的解释却有五方面,亦即“政治上(所有国家)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1) 美国部分学者在如何理解中国“和谐世界”战略内容的问题上基本上认同胡锦涛十七大报告里的这些解释。不过,他们认为,中国“和谐世界”战略最重要内容是以下两点。
其一,文化上,世界多种文明和平共处和相互交流。赵穗生指出:“和谐世界首先意味,作为人类进步强有力的推动力,多种文明和平共处是非常重要的。包容,(使人)摆脱任何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束缚,在使不同的文明能够和平共处方面发挥最重要作用。”(1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杜维明指出:“人类文明的各种文化在相互交流时,包容是最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者的存在方式和他者的信仰,要去理解他们。有了承认才有尊严,有了相互尊重才有相互学习的可能性。”“不同文明之间必须进行对话、进行参照,才能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13)
其二,政治上,世界各国之间平等互利互信,通过对话磋商消除分歧进行合作。陈有为指出:“和谐外交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和平共处,而是提倡在平等互利互信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消除分歧进行合作,以求改善不同理念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谋求国际重大问题的妥善解决。”(14) 赵穗生指出:“将(和谐世界)此概念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意味所有相关国家要进行协商,并非在霸权野心驱使下去推行单边主义。”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国在建设和谐世界方面能够发挥关键性作用”,主要大国关系应“保持均衡”,“朝良性关系方向发展”。(15)
美国部分学者认为,基于上述基本内容,中国“和谐世界”战略表现出如下几方面特点。
一是“不仅想到自己,而且也想到别人”。陈有为指出:“和谐外交的特点,是不仅想到自己,而且也想到别人。”(16) 简·马克和郭苏建引用中国学者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和谐世界并不是只有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种制度的世界,而是这样的世界:它容许价值观念、文化、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存在多样性,容许相互依存、和平共处、相互获益和共享繁荣。虽然世界各国人民存在差异,但是我们能够拥有和追求共同的目标,相互尊重,保持本国的特色,一起和平和和谐地生活。”(17)
二是“多边主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何凯(Kai He)指出:“多边主义”是“和谐世界”理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政策“最令人惊讶变化之一”是中国“逐渐接受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制度现实主义”(institutional realism)更能解释冷战后中国在亚太地区“多边外交”。换言之,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和国际社会处于无秩序状态条件下,“多边制度”已成为中国“新的软均衡战略”(a new softbalancing strategy),亦即“制度均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战略。(18)简·马克指出:中国追求“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意味中国将继续进入国际经济体系,接受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支持日益增加的合作和交流(如果是互利互惠的话)以及多边主义。”(19)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中国在开展“多边外交”、建设“和谐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陈有为指出:“和谐外交的目的,既包含了原有创造和平国际环境的自身目的,又超越了这一目的,也就是要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更大责任,在国际上发挥中国崛起的作用。”中国希望在世界上充当“平衡者”,在有关国家之间“协调与平衡”,力求使世界局势保持稳定。(20) 郭苏建和华世平指出:“新的外交政策强调,中国是爱好和平、以人为本、合作、宽容、自信和负责任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注重运用“软力量”提高其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21)
三是“和谐世界”的重点在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地区。沈大伟指出:胡锦涛所设想的“和谐世界”前景,“建立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亦即‘睦邻、富邻和安邻’的基础之上”。(22) “中国与美国、日本、东盟,并且还越来越与印度一起,共享地区舞台。”中国谋求亚洲地区稳定,“是善意和耐用消费品,而非武器和革命的输出者。”(23)
三、关于“和谐世界”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及其存在的问题
以上简要考察美国部分学者关于中国“和谐世界”战略内容与特点的研究。那么,中国“和谐世界”战略是否具备实施的条件和可能性?中国在推行此战略时将面临哪些阻碍?对于这些问题,美国部分学者试图从国内和国际层面作分析。
就实施“和谐世界”战略所具备的条件而言,美国部分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中国自身还是从国际层面看,都存在诸多有利于中国实施“和谐世界”战略的因素。
首先,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因素决定它今后一二十年内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中国会走和平发展道路。
(1)中国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对美国和世界不可能构成威胁。所以,中国会和平发展,从而具备实施“和谐世界”战略的最基本条件。陈有为指出:“中国经济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同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量人口需求和综合国力相比,仍然远远不够。”“美国经济仍然具有活力,美国科技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的军事力量与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中国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24) 谢尔登·西蒙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给人深刻影响”,但是中国在经济领域“却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并未威胁美国。(25)
(2)中国军事实力极其有限,对美国和世界亦不构成威胁,从而有可能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谢尔登·西蒙指出:“当前中国防务能力有限。”在军事现代化领域,“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和日本在东北亚的力量联合起来,继续维持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的优势。”(26) 纽约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国际形势研究部主任何汉理(Harry Harding)指出:“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这种情况“极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将来是不可能的”。(27)
(3)当前中国与邻国或亚洲国家关系“和谐发展”,从而增加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可能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会高级研究员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对外行为“已相当温和”,其要务是与邻国“和谐发展”,努力使邻国相信对中国有益的事情(亦即经济发展)同样对邻国有好处,“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关系相当好”。(28)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G.Sutter)指出:中国对亚洲国家采取“合作方法”,“寻找与其邻国的共同点”。(29)
(4)新世纪初中国中心任务是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建设,这就决定它不大可能去主动挑战美国,中美两国和平相处是可能的。罗伯特·萨特指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至少现在仍然集中精力进行本国建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中美和平相处是可能的。(30) 赵穗生指出:目前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国内面临艰难的挑战”,如“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公平和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城乡差别”、“财富差别”和“改革和稳定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所以,中国努力与外部世界发展良好关系,“为其现代化计划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31)
(5)中国已加入大多数全球性组织,逐渐融入国际体系,这有助于中国和平发展和建设“和谐世界”。何汉理指出:“在过去25年里,中国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并无根本性不满,因为它从这些体系里获得很多利益。而且,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相互依存,这将阻止北京进行军事冒险,除非是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32) 陈有为指出:“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认同者与维护者,愿意在现有的国际秩序框架下,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寻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33)
(6)中国具有“和谐”等优良传统。所以,新世纪中国建设“和谐世界”是可能的。布鲁斯伯格大学(Bloomsburg University)政治系助理教授丁胜(sheng Ding)指出:当今中国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软实力”思想和“和谐”哲学,提出建设“和谐世界”新战略以“建立起它所希望的国际秩序”。从“中国传统哲学”来看,中国“和平崛起成为强国,并追求和谐世界的这些理论”是有可能实现的。(34) 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中国文化传统,倡导‘和而不同’和‘和为贵’,为中国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谐共存和共享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35)
(7)从奥运会后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更有可能建设“和谐世界”。李成指出:“中国将在奥运会后进入一个新时代”,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和更具包容性。”(36)所以,他断言奥运会后中国更有可能建设“和谐世界”。
其次,一些国际因素亦有助于中国实施“和谐世界”战略。
(1)现有的国际秩序有助于中国建设“和谐世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指出:现有的国际秩序有益于中国的和平发展。这个秩序是“开放性的、互相协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基础”。因此,中国在此国际体制内予以合作具有广泛的经济利益。“简言之,今天的西方秩序难以推翻,易于加入。”(37)
(2)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有助于中国建设“和谐世界”。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欧纬伦(William Overholt)指出:“全球化的中国将不再会谋求改变美国创建的世界体制”,换言之,中国和平发展是可能的;事实上,中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美国友好合作,还与邻国就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协商。(38) 罗伯特·萨特指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导致中国加入更多的地区和国际性组织。所以,新世纪中国在对外关系上会“尽量避免出现大的对抗”。(39)
当然,中国实施“和谐世界”战略将会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这其中既有国内挑战,亦有国际挑战。
1.关于国内挑战
(1)近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但经济实力仍然有限。陈有为指出:“中国的和谐外交还处于初始阶段。”因为,首先,“中国的财力还不足以充当有求必应的财神爷,承担不起普世救援的宏大责任。”(40)
(2)中国国内社会问题较严重。简·马克和郭苏建指出:在构建“和谐世界”过程中,中国国内面临的“明显挑战”主要有政治改革尤其是增加民主和透明度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贪污问题,能源巨大消耗问题,等等,“限制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秩序的能力”。(41)
2.关于国际挑战
(1)中西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存在差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Jing Huang)指出:中西在“政治制度”和“价值理念”方面存在“差异”,并有可能“造成矛盾升级”,甚至“引发战争”。“这是中国在世界上实现和平发展的最大阻力”。(42)
(2)中美两国更要加强合作。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指出:建设“和谐世界”,需要中美两个大国间关系能更上一个台阶,尤其是两国要积极合作,如携手做些具有前瞻性,以科技、环保、节能为导向的,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共享的大事。(43)
中美两国尤其是要处理好台湾问题,因为此亦影响中国“和谐世界”战略的实现。简·马克和郭苏建指出:中国在追求“和谐世界”中“最大挑战”是台湾问题。如果出现台独,“中国也许不得不运用武力干涉,因而台湾海峡可能爆发战争。这样一来,美国就可能卷入。”这样“将严重破坏东亚安全环境,甚至很可能破坏国际环境。”(44)
此外,美国部分学者担心,中国民族主义上升,亦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建“和谐世界”。简·马克和郭苏建指出:中国在构建“和谐世界”过程中“明显挑战”还有伴随国力发展而来的“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它影响中美和中日关系。(45)何汉理指出:“中国企业不仅想获得最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想加入大规模的、有利可图的多国企业行列之中。”中国的一些力量对世界构成了挑战,而其中的“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对世界所构成的挑战则有可能最大。(46)
四、关于“和谐世界”战略的作用
在分析“和谐世界”战略实施可能性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美国部分学者还看到,“和谐世界”战略自提出和实施以来,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
1.“和谐世界”战略能够增强中国“软实力”和“捍卫国家利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中国追求“和谐世界”理念,表明中国“能够为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能够增强中国的‘软实力’”(47) 陈有为指出:由于“奉行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中国成了整个世界外交舞台上最为耀眼的角色”,中国外交在“捍卫国家利益”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48)
2.“和谐世界”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抵制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谢淑丽指出: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崛起”和与邻国“和谐”战略,这表达了他们追求“和平发展”和“(使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愿望。(49) 郭苏建和华世平指出:“中国领导人已清楚向世界表明,中国对寻求地区霸权或改变现有世界秩序都无兴趣。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50)总之,“和谐世界”战略帮助他们认识到,目前中国发展对世界并无“威胁”。
3.“和谐世界”战略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1)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发展。约瑟夫·奈指出:“现在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大参与者,‘和谐世界’的提法表明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51) 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中国对外实施“和谐”战略,和平发展,“给亚太地区带来了发展机遇、和平形势和合作空间”。(52)
(2)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陈有为指出:“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推动中国对外关系发展。“中国与美国建立了高层对话的有效机制,在处理台湾问题、朝鲜与伊朗核危机以及其他国际重要问题中进行磋商协调,使中美关系保持平稳发展的势头。中国同俄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同欧盟成员国的经贸关系与国际合作有所深化,同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日益加强,中国向南亚、西亚、中东、非洲与南美不断开拓新的外交空间。”(53) 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于滨(Yu Bin)指出:实行和谐外交政策以来,中国“逐渐与其几乎所有邻国改善关系”,如,关系正常化,边界线勘定,暴力减少,地雷清除,信任建立,对话坚持,贸易繁荣。“除了双边互动外,中国还设法努力从事多边外交:从被动到主动,从接受管理到维护管理,从参与多边机制到创造多边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关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等)。因而,中国已经赢得它成为东亚外交、经济、安全和文化活动中心的荣誉。”(54)
美国部分学者还着重探讨“和谐世界”战略对中美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积极影响。关于前者,陈有为指出:在“和谐世界”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外交是“一种更为务实,更为切实可行,也更为高瞻远瞩的明智政策。”“由于中国崛起和中国领导的正确政策,美国对中国的评估与对策正在逐渐向现实主义方向转化。”“即使美国保守势力仍然难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但是趋向与中国交往合作,避免与中国进行对抗,“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共识”。(55) 戴维·兰普顿指出:美国与中国“发展和谐关系”,将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我们今天真正挑战是与作为伙伴而非敌人的中国一道建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56)
关于“和谐世界”战略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积极影响,丁胜指出:在“和谐世界”战略指导下,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亦即发展中国家较成功地实施“软实力外交政策”(soft power- based foreign policies),所以,中国在这些地区较受“欢迎”,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里已树立“良好形象”。(57)
(3)为人类未来描绘出一幅乐观积极的蓝图。约翰·桑顿指出: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的确是“一个远大的理想”。(58) 约瑟夫·奈指出:“建设‘和谐世界’则为人类未来描绘出了一幅乐观积极的图景”。(59) 正因此,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主张:美国民众亦要与中国一道,共同努力建设“和谐世界”。(60)
五、结语
综上,美国部分学者对中国“和谐世界”战略的成因、内容和特点、实施可能性和存在问题及其作用都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一系列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观点,说明他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较有成效。
美国部分学者对“和谐世界”战略作如此研究,并非偶然。进入新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国际地位开始有所变化。美国虽然还是惟一超级大国,但国际优势地位逐步削弱,发展模式感召力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发展迅猛,综合国力进一步加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加上美中两国并非“战略盟友”,缺乏战略互信。这使得美国对中国忧虑重重,担心中国发展将严重挑战美国霸主地位。而且,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导致世界秩序急剧波动,甚至引发世界大战。另外,美中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程度和历史传统诸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不少美国人将美国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奉为当今世界惟一正确标准,视社会主义中国为洪水猛兽,以为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势必冲击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因此美国应当防范。还有,全球化背景下,美中两国越来越相互依存,两国利益的相互关联日益加深。所以,美国高度关注迅速发展的中国将在国际上如何使用其迅速增长的力量,甚至忧虑中国会推行亚洲版“门罗主义”。对美国利益的高度关心和自身职业的要求决定美国学术界近年极其关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国际战略走向。但是,美国是多元社会,不仅存在鹰派之类学者,而且亦存在不少正直进步学者。当中国2005年提出“和谐世界”战略后,美国部分学者亦即上述这类学者敢于从实际出发,既结合中国自身国情、中心任务和中国与周边国家、世界的关系,又联系目前中国面临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及开放性的国际秩序等世情,就中国“和谐世界”战略提出一系列较客观的观点。
自然,美国部分学者在上述探讨中亦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和谐世界”战略的思想来源剖析得并不全面。他们基本上将此战略思想来源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其实,像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和谐理想社会的描述,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等等,亦是“和谐世界”战略思想来源。但美国部分学者基本上忽略这些因素。其二,对“和谐世界”战略的内容挖掘得不够深入。“和谐世界”是有原则和谐。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里指出: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但美国部分学者对中国“和谐世界”这些原则有所忽略。此外,“人与自然相和谐”是“和谐世界”战略重要内容。但美国部分学者对此不大重视。其三,关于“和谐世界”战略的作用,美国部分学者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尽管如此,他们毕竟对“和谐世界”战略作了许多可贵探讨,不仅有助于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而且有助于国外学者深入研究此问题,对当今中国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此问题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09-03-15
修改日期:2009-06-12
注释:
① 在如何看待中国“和谐世界”战略问题上,美国学术界存在分歧,大致可分成三类学者。第一类学者认为,中国实现此战略具有可能性,对世界和平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类学者尤其是鹰派学者认为,中国不可能实现此战略,中国的“发展”只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威胁”。第三类学者则持观望态度。本文仅就第一类学者关于中国此战略的研究情况作些梳理。文中“美国部分学者”大体上是指此类学者。
②⑦ 陈苏:《中国强调和平发展》[EB/OL],美国之音中文网,2005年12月22日,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5-12-22-voa18.cfm。
③(22)David Shambaugh,“Chin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The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29,2008.
④(12)(15) Suisheng Zhao,“China Rising:Geo-Strategic Thrust and Diplomatic Engagement”,in Suisheng Zhao,ed.,China-U.S.Relations Transformed: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London:Routledge,2008,pp.24-25.
⑤⑨(14)14)(16)(20)(24)(33)(40)(48)(53) 陈有为:《中国全球外交进入新阶段》[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12月21日。
⑥⑧(10)(11)(17)(19)(41)(44)(45) Jean-Marc F.Blanchard and Sujian Guo,“Introduction”,in Sujian Guo and Jean-Marc F. Blanchard, eds.,“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Lanham:Rowman and Little field-Lexington,2008,pp.2-3,pp.5-6,p.5,p.3-4,p.4,p.16,p.14,p.15,p.14.
(13)《学习孔子,抛弃单边主义——专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N],《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月28日。
(18) Kai He,“China's Peaceful Rise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in Search of a Harmonious World”,in Sujian Guo and Jean-Marc F. Blanchard,eds.,“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pp.65-82.
(21)(50)Sujian Guo and Shiping Hua,“Introduction”,in Sujian Guo and Shiping Hua,eds.,New Dimension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Lexington,2007,p.2. (23)David Shambaugh,“Return to the Middle Kingdom? China and Asia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in David Shambaugh,eds.,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46-47.
(25)(26) Evelyn Goh and Sheldon W.Simon,“Introduction,” in Evelyn Goh and Sheldon W.Simon,eds.,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Southeast Asia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2008,p.3,p.11.
(27)(32)(46) Harry Harding,“China:Think Again”,Foreign Policy,March/April 2007,pp.31-32.
(28)(36) Robert Roy Britt,“Will China Become the No.1 Su perpower?”Live Science,August 15,2008.
(29)(30)Robert G.Sutter,China'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Leadership in Asia,Washington,DC:the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2006,p.4,p.9.
(31) Suisheng Zhao,“Introduction”,in Suisheng Zhao,ed.,China-U.S.Relations Transformed:Perspectives and Strategic Interactions,p.8.
(34)(57) Sheng Ding,“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China's Soft Power Wielding in the Global South”,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ume 13,No.2,Spring 2008,pp.196-198,pp.199-210.
(35)(52)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China Rising: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Response”,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eds.,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Abingdon, Ox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p.10-11.
(37)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8.
(38)欧纬伦:《噪音不会影响中美政策走向》[N],《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9月18日。
(39) Robert G.Sutter,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O07,p.128.
(42)李焰:《“卡特里娜”吹“皱”胡锦涛的美国之旅》[J],[美]《华盛顿观察》周刊2005年第32期,2005年9月7日。
(43)(58)廖政军:《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桑顿——谁先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谁就掌握了参与和推动历史的资本》[N],《人民日报》2007年11月16日。
(47)(51)(59)《中国描绘人类未来积极图景——〈环球〉杂志对话约瑟夫·奈》[J],《环球》2007年第20期,2007年10月16日。
(49)Susan L.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09.
(54) Yu Bin,“China's Harmonious World:Beyo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2,Spring 2008,p.134.
(55)陈有为:《从兰普顿新著看美国的中国观》[N],[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7月24日。
(56) 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 and Mind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p.273-274.
(60)罗丽鸥、黄颂彬:《陈云贤会见美国青年社会学代表团》[N],《佛山日报》2007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