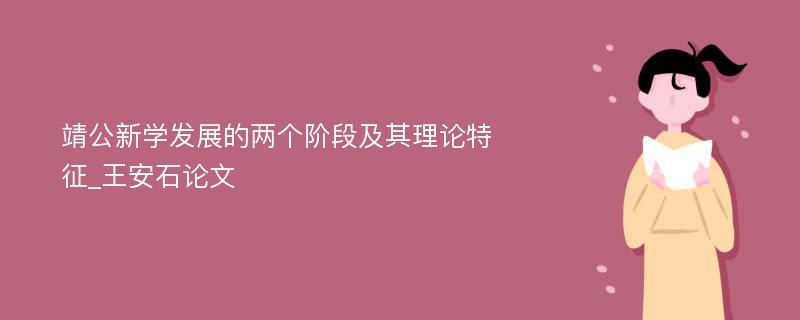
荆公新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理论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阶段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0)01—0022—06
新学主要是指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的思想、学术,亦包括其弟子王雱、龚原、蔡卞、陆佃、吕惠卿等对王安石思想的发挥与发展。因王安石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被封为荆国公,后世亦称荆公新学。新学以王安石等主持修撰的《三经新义》而得名,但新学的内容却并不局限于《三经新义》。它包括在此前后王安石及其弟子的一些学术著作。新学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与理学、苏氏蜀学同时兴起,“独行于世者六十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居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是北宋中后期的显学。然而,由于南宋以后,新学遽然衰落,以至湮没无闻,新学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存,对新学的研究一直未能深入。在对新学理论特点的把握方面,历代学者曾有过种种说法,但都言之不详。本文认为,荆公新学可以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个理论特点非常鲜明的发展阶段。早期新学以道德性命之学为主题,而后期的理论重心则在于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
一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22岁的王安石登杨真榜进士甲科,授扬州签判,正式开始了其“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的仕宦生涯。从此直到治平末年,王安石大部分时间都在地方官任上。王安石初踏仕途之际,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欧阳修等遭放黜,政治改革的浪潮暂时平息而新的高潮尚未到来之时。王安石继承宋初诸儒开辟的事业,以崇高的使命感投入到复兴儒学、挽救社会危机的事业中去。他发奋学习,饱读经书,希踪稷契:“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晞”(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四十四,《忆昨诗示诸外弟》)。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的割据与战乱,再加上佛道的势力的影响,政教驰废,儒学衰微,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呈现出一种失范无序的状态:“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废,而先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欧阳修《新五代史·唐家人传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初。无疑,唐末、五代及宋初时出现的这种风俗陵夷、道德沦丧,儒家价值理想的衰落、崩溃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北宋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确立。很显然,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共同的价值理想,缺乏凝聚人心的道德力量,思想混乱,人心不一,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是不可能确立、巩固的。宋初统治者在采取种种措施巩固中央集权也认识到必须要加强思想文化统治,重振儒家纲常。在这种情况下,对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体系作出有效的论证,收拾人心,重振纲常,就自然成为思想学术界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在这一时期,王安石等新学学者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围绕这一课题而展开的。因此,道德性命之学是早期新学的主要内容。由于新学著作的大量佚失,我们只能从王安石的个别著作及历代学者的一些文字中获取一麟半爪的有关信息。
王安石在担任地方官期间,新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洪范传》、《易解》、《淮南杂说》等都已完成,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洪范传》是王安石为数不多的幸存著述之一。其中有大量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的内容。如王安石说,“盖五行之为物,其时、其位、其材、其气、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声、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无所不通。……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通天下之志,在穷理;同天下之德,在尽性。穷理矣,故知所谓咎而弗受,知所谓德而锡之福;尽性矣,故能不虐茕独以为仁,不畏高明以为义(《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洪范传》)。蔡上翔谓《洪范传》“广大精微”,“其志在垂世立教至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十)这是道出了《洪范传》重视道德性命之学的理论特点的。
王安石在此期间的另一部著作《易解》,现已佚失,无从知其具体内容。但王安石于此时对儒家诸经之中最富哲学意蕴的《易经》发生兴趣,作出训解,则决非偶然,它反映了王安石这一时期内的理论兴趣。而且,虽然王安石自谓“某于《易》,尝学之矣,而未之有得”(《王文公文集》卷七,《答史讽书》),且以“少作未善”,后来不颁于学官。但精通《易》学,又与新学在很多方面处于对立立场的程颐在指导门人读《易》时却认为:“《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二程集》,第 248页)程颐对新学持否定态度而又看重《易解》,说明了王安石的解《易》之作与重视阐发《周易》中性命道德之理的程颐有某种契合之处。
《淮南杂说》是王安石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今天已经佚失。据新学学者蔡卞称,王安石“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二》)清人全祖望亦称:“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宋元学案》卷九十八,《荆公新学略》),引起很大反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孟子》一书是颇重心性道德,大谈“尽心知性以至于命”的,以《淮南杂说》与《孟子》相比况,可见它着重于道德性命之说的理论特点。邓广铭先生就推断说:“当时人之所以把《杂说》与《孟子》相比,……是因其多谈道德性命之故。”[1]
侯外庐先生等在《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还指出,“我们颇疑《文集》卷六十五至七十诸卷,即《淮南杂说》”[2] 这里所谓《文集》指《临川先生文集》,其中第六十五至七十卷,讨论的主要是道德性命之学的内容。这一点从其中《性情》、《原性》、《性说》、《命解》等篇中可以略窥大概。如在《性情》篇中,王安石指出:“性情一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七,《性情》)本篇从已发、未发角度讨论了性情问题,以体用内外合一的原则说明了性情一而不可分的关系。在其他各篇,王安石还探讨了人性问题,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的观点;讨论了王霸义利问题,提出以“心”作为道德行为的判断标准。各篇的内容多与道德性命有关。侯外庐先生等推测这些篇章即《淮南杂说》的观点,足资启发。如果能得以证实,则更可明白无误地说明王安石之学在这一阶段以道德性命为主题的特点。
从这一时期王安石所作的其他文字来看,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也是其思考的中心问题。如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王安石作《虔州学记》,指出学校教育的意义与目的就在于讲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而其度数在乎俎豆、钟鼓、管弦之间,而常患乎难知,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于人心,《诗》、《书》能循而达之。”(《王文公文集》卷三十四,《虔州学记》)在这一时期与友人的书信中,王安石也非常关注道德教化、风俗整饬问题,如在《与丁元珍书》中,王安石就对当时思想混乱、道德风俗不一的状况深表忧虑,并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表明了其理论思考的重心之所在。
南宋度正在为周敦颐所作的《年谱》中记载了王安石与周敦颐两次相交涉之事。其中嘉祐五年庚子(公元1060年)条下云:“先生东归时,王荆公安石年四十,提点江东刑狱,与先生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周敦颐全书》卷一,《周敦颐年谱》)此说最早出于北宋理学学者、程颐门人邢恕,但清人蔡上翔与近人梁启超斥之为妄说,驳之甚详。但即使王安石与周敦颐相交涉之事为妄,邢恕的杜撰中将王安石与被认为是“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序》)。的周敦颐联系在一起,认为二人交流学术,语连日夜,至少在他看来,此时王安石与周敦颐是具有一致的理论倾向的。在北宋末期,人们对早期新学特点的了解当有一定准确性。这样,周敦颐《年谱》中这段很可能出于杜撰的材料也向我们透露出早期新学重视性命道德之学的特点。
实际上,不仅蔡卞指出以《淮南杂说》为代表的早期新学使天下士子“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具有性命道德之学的特点,金人赵秉文也指出:“自王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赵秉文《滏水文集》,《性道教说》)明清之际学者费密还以批判的口吻指出:“一切道德性命臆说,悉本安石焉。”(费密《道脉谱论》,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3 月版)侯外庐先生等说:“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2]这些评论, 都较为一致地肯定了早期新学的治学特点。
二
诚如上述,王安石早期的理论探索主要是围绕重振儒家纲常、挽救价值失落的主题进行,通过对性命道德之理的探求而改变风俗颓坏、教化陵夷的状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初社会的各种危机更加深重,新的社会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王安石在长时间的地方官任上,对社会情况的了解也更为深入,对北宋王朝所面临的现实危机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给仁宗上万言书,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为此,王安石积极倡言改革,并提出了改革的蓝图。王安石深知,没有一个能指导全局的深刻的理论基础,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而在此之后直到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其理论兴趣逐渐发生了转移。他主要围绕如何解除北宋政府所面临的现实危机进行理论探索,希望通过复兴儒学,重新发掘先王经典中的微言奥义为现实社会的改革提供思想指导与理论依据,这是后期新学的主题。
后期新学以《三经新义》为主要内容。《三经新义》的训释与颁行,主要是围绕统一思想及为新法提供理论依据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进行的,具有鲜明的为新法事业服务的性质。
庆历以后,学术思想领域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使学者们摆脱了经传注疏的束缚,思想异常活跃。由于当时学者在解释儒家经典时,各凭胸臆,自由议论,没有统一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标准,由此思想界出现了“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的现象。这种思想混乱的现象引起了当时士人的注意,程颐曾以“方今人执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加以形容。早在地方官任上,王安石就关注这种“家异道,人殊德”的现象,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一旦欲有为于世,则异论四起。思想界的这种纷纭歧杂,产生了“一道德而同风俗”的要求。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讲经筵,主讲《尚书》,第二年参知政事,由其子王雱嗣讲。神宗此时诏王安石进所著文字,王安石上谢表,在谢表中正式提出了训释经义的动议。他希望通过训释六艺之文,阐明先王之道,统一人们的思想。熙宁二年之后,各项新法次第推行,但无一不遭到激烈的反对。思想学术领域更是异论纷然。反对新法的士人往往根据需要,对儒家经典作出符合自己意愿的解释,攻击新法,阻挠新法的推行。宋神宗对这种状况亦有所认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载:
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议者不深维其意,群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故也。(李焘《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条)
所谓“不知义,即未能认识到新法乃稽合先王法度而造立,对新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缺乏认识,“朝庭欲有为时,异论纷然,莫肯承听。”(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选举考》四)在神宗看来,这种状况不仅使变法措施不能顺利推行,而且也对宋王朝的专制集权统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必须训释经义,造成以新的学术为基础的思想统一的局面。新经义的训释已提上日程。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正月,神宗正式向王安石提出颁行新经义的要求:“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可以颁行,令学者定于一。”(李焘《长编》卷二二九,熙宁五年正月条)翌年三月,神宗又说:“举人对策,多欲朝廷早修经义,使义理归一。”(李焘《长编》卷二四三,熙宁六年三月条)修撰新经义,以之统一思想的愿望十分强烈。宋政府有鉴于此,决定设立经义局,训释《诗》、《书》、《周礼》三经义,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吕惠卿兼修撰、王雱兼同修撰,一批士子参与了修撰工作。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元月,三经义修成奏御,不久即颁行天下,作为全国学校的统一教材和科举考试标准,“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至此,新学取得了君临学坛、定于一尊的地位。
从《三经新义》的产生过程看,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改变当时思想学术领域道德不一、纷纭混乱的局面,以新的学术统一人们的思想,为新法事业服务。实际上,在北宋中期,不同立场的学者都在寻求一种适合于时代与社会需要的新经义,他们从各自的立场、意愿出发提出了不同的学术思想,并在学术领域内展开斗争,反对别派的学说。新学学派训释经义,其实质正在于此。
肩负指导全国规模的政治、经济改革重任的王安石,意识到从理论上阐明其变法思想的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力图通过训释经义、阐发古圣先贤的微言奥义,说明变法的必要性、合理性,为新法提供理论依据。这是《三经新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新学学者在经义的训释中,着重阐发了因时变法的思想,指出了改革更易的必然性及变法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王安石认识到,北宋王朝已经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于先王之政故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因此,为挽救危机,就必须变更祖宗法度,推行政治改革。在《三经新义》中,这一思想得到体现。《周官新义》解“以八法治官府”一条时,王安石根据“法”字的字形进行训释说:“法之字从水,从去。从水,则水为物,因地而为曲直,因器而为方圆,其变无常,而常可为平……”这就阐明了必须因时因地而变革的道理。在解“正月之吉始和”一条时,王安石指出,先王盛世,每到岁终,则“今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政事,于是调制所当改易。……政欲每岁改易,故改岁之一月谓之正月”(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在解“王以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一条时,王安石指出,“道有升降,礼有损益,则王之所制,宜以时修之,修法则,为是故也。”(王安石《周官新义》卷六)应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修订成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这样,王安石等就通过训释经义,阐明了权时变法的必要性,为实施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法次第推行后,碰到很大的阻力,反对者攻之甚力,一时议论汹汹,喧嚣于庭。为了确保新法的贯彻执行,王安石等又通过《三经新义》的训解,对各项新法措施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青苗法施行后,反对派对此攻讦不己。王安石除了说明这是援引《周官》成例外,还说明了有关青苗法的法意所本。《周礼》中有“旅师,掌聚野之锄粟”一条,王安石训释道:
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颁以散也。施其惠,若民有难阨,不责其偿;散其利者,资之以利本业者,又散与之。”(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七)
这就通过经典训释为青苗法找到了理论依据。对于保甲法,王安石也加以说明:“保甲之法,起于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齐,子产用之郑,商君用之秦,仲长统言之汉,而非今日之立异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五事书》)对免役法,王安石亦指出:“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五事书》)王安石通过大量诸如此类的训释,为各项新法措施作出了理论上的说明,指出新法是符合先王本意的,有其经典的依据与理论渊源。
总之,《三经新义》说明了变法改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并为各项新法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目的就在于为新法事业服务。这是以《三经新义》为主要内容的后期新学的理论重心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晚年罢相后,闲居金陵。这一时期,遭受严重打击而被迫退出社会政治舞台的王安石倾向于作较纯粹的理论思考。他完成了《字说》24卷,与《三经新义》相辅而行。并作《老子注》,注释佛经,汲取佛道之长,进行不懈的理论探索,使新学思辨水平不断提高,其理论体系也发展得更为成熟。
[收稿日期]1999—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