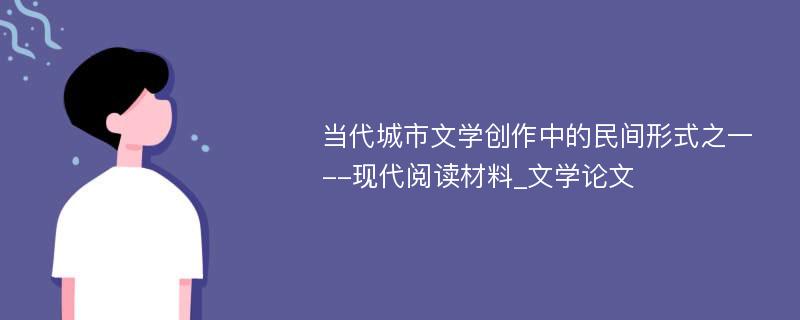
当代都市文学创作中的民间形态之一:现代读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物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形态论文,当代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爱玲以后,都市文学创作基本上处于冷寂状态。由于都市民间价值的虚拟性,它不象农村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较为长远的历史传统,也不可能象农村题材创作中的民间隐型结构那样,以生动泼辣的生命力和自由自在的美学风格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所以,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文学创作中,都市文学是最薄弱的环节。有两部长篇小说似乎还值得一提:《上海的早晨》第一、二部和《火种》第一部。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纯粹的都市小说,只是用现代都市作背景写一段革命历史或政策。它们所涉及的都市风,也只是陈旧生活场景的再现。到了上海的柯庆施强行推广“大写十三年”的创作时代,一些拔苗助长的工人作家写出的“都市小说”,都成了阶级斗争的通俗宣讲教材。
都市小说之不兴,主要是都市民间价值的虚拟性所致;但作为都市文化的民间性依然是存在的,它主要体现在私人生活空间的存在。由于都市人口的复杂多变,每一种层次的家庭都有自身的家族背景,这些家族背景又是与某些城市区域和城市职业联系在一起,形成他们自己的私人社会空间。特别象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几乎包容了各种省份地区、各种社会层次的人群生活方式,没有一种人群可以单独作为上海人的全权代表。这样一些私人性质的社会空间,在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上,既有传统民间价值取向的痕迹,又有现代都市人的生活特征。举一个文学上的例子,王安忆的《文革轶事》是写文革时期发生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一个资本家家庭的故事,在这个家庭里,男人们都因为革命而萎缩了(象征了专制时代政治对民间的专政),但一群女人(不同年纪,不同身份)和一个来自别的阶层的男人却整天聚在一起昏昏然地讲过去的电影故事和旧式都市生活经历,以至发生了男女间隐隐约约的暧昧之情。故事象一枚放大镜放大了文革时代都市中另一个被遮蔽的生活空间:这里不讲革命、不时兴破四旧、不唱样板戏、也不交流学毛选的体会,这里的男女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与时代隔绝的话语空间里,他们不是反对、批判或者嘲讽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而是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尽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回避抄家、批斗、上山下乡等中国式的灾难,但他们可以在某一个生活空间里完全拒绝这类主流意识形态,用他们所熟悉、喜欢的民间方式取代之。我把小说所描写的这类纯属市民私人性质的话题视为都市民间的一种特征,是因为这些话题与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私人话题完全不一样,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经历着一个由迷茫而自我诘难,由怀疑而深入思考,进而讨论、争辩和惊醒的过程,完全是知识分子精英式的广场立场,这才产生了遇罗克、张志新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先驱。都市民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协调成平行的关系,即使在文革时代,民间处于无层次平面状态,它仍然能够在私人性的空间里慢慢生长起来。当然王安忆是在九十年AI写作出《文革轶事》,文革时代是不可能出现这样表现私人空间的文学作品,但象这样潜隐在民间的私人空间是确实存在的。随着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又开始出现了新的流动,带有雇佣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使个人的劳动力使用和劳动力维养成为两个绝然分开的领域,市民私人空间合法化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才有可能使都市的民间文化形态和都市文学的民间性真正成熟起来。
都市民间的再现是以“张爱玲热”为标志的,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说,张爱玲在沟通五四新文学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传统都市通俗小说方面以及在文学中表现都市人的乱世情结、物欲追求和私人空间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后来人很难具有象她那样身临其境的生命真实。八十年代初,由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介绍,张爱玲重新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注意,但仅仅在一些学者中间流行,他们在夏志清的影响下开始对她的作品作分类学上的研究。与此相应的是,上海一批女作家开始注意到“文革”以后资产阶级家族“中兴”的故事,她们描写这些家族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沉浮,描写资产阶级家族和工人市民家庭之间的隔阂和沟通,甚至描写资产阶级家族的形成史和发展史。因为要描写旧式家庭的生活故事,就不得不从知识上返回旧上海的都市场景和生活方式,作家的注意力就开始转移到一些从意识形态的缝隙中生长出来的民间信息。这些故事也写到“文革”,却没有一部是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作家们对描写对象所抱的同情表现得很有分寸,并用嘲讽的态度写出了这些人的怯懦、无能和自私。这种表现方法在无形中逐渐消解了“二元对立”的传统创作模式,将原来的“控诉”型“批判”型话语转向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立场以外的民间日常生活描写。不能排除这些创作模仿张爱玲的潜在因素,但从当时的条件限制,女作家们对张爱玲的理解仅止于对旧上海贵族生活场景的表现而没有抓住张爱玲为都市小说提供的真正灵魂,本来,抓住时代大动荡特征及其给一些家庭和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同样能够表现出张爱玲式的“乱世”精神,现在却与此轻轻地擦肩而过,即使对历史与家族命运的描写,也多半停留在概念的图解上,因而这些作品中的民间意识仍然相当薄弱,并能够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忍和好评。
九十年代初,张爱玲的作品开始进入商业性的文化市场,成为都市里的流行读物。与张爱玲一起走红的还有一些同样被排除在现代文学史著作里的作家: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和钱钟书,这里除了《围城》是缘了电视剧推广以外,大都是靠其文字自身的魅力。尤其是那种公然宣称循世和闲适的小品文与张爱玲更加市民气的散文随笔,为正在被现实苦境纠缠着的都市青年提供了一个逃避的话语空间:前者是为知识分子逃离广场寻找心理平衡的籍口;后者是都市市民的欲望被扩张开去,无论是逃离还是扩张,都代表了知识分子向民间立场的转移。这些文学作品与许许多多非文学性的流行读物一起陈列于都市的街头书摊,成为都市民间文化的景观之一:现代读物。这个概念是笔者于1988年在香港考察都市文化现象时提出的,当时大陆尚不流行,几年后,笔者在一篇谈香港文学的通信里提到它的定义:
这是一种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各种各样的品种,有知识性读物,有消闲性读物,自然,也有文学性读物。他们大都是作为商品而投入读者消费市场,但与教科书、政治文件、专业文献等书籍不一样,与纯文艺作品也不一样。纯文艺和通俗文艺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那么清楚,特别是进入了商品社会以来。但是艺术观念的区别,写作方式的区别,以及审美口味上的区别,仍然是存在的。我这里界定的“读物”之所以不包括纯文艺,是因为“读物”在现代社会中不是一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对立,进而尽到现代知识分子批判责任与使命的精神产品,也不是一种民族生命力的文化积淀,并通过新奇的审美方式表现出来的象征体,更不是凭一己之兴趣、孤独地尝试着表达各种话语的美文学,后者林林总总,都以作家的主体性为精神前导,与现代社会处于潜在的对立之中。或可以说,纯文艺是知识分子占有的一片神秘领地。然而读物,它的存在是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它将帮助人们更适宜地生存。这种帮助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实用性的生活指南,也可以是消闲性的精神消遣。……纯文艺(包括纯学术)的读者市场大幅度减少,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奢侈品;而读物堂而皇之地接管了所有的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与影视文化、流行音乐鼎足而立,左右了现代文化消费市场。
虽然当时笔者还没有研究都市民间的理论,但对于“现代读物”的认识中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读物”包括现代社会中所有的流行文字、图书和报刊,从体裁来区分,由浅到深可以分以下几类:一、连环图画和漫画,它包括图文并茂的生活类指南、儿童连环画、各类画报、图册、一直到类似蔡志忠漫画;二、周刊、小报和各类报纸娱乐、体育性副刊;三、各类通俗性消遣性文字书籍,包括黑幕新闻、名人遗事、星相八卦、生活指导等等;四、文学性作品,包括故事、随笔、小品、以及通俗小说。这里并没有将“读物”与通俗文学等同起来,但“读物”包括了用文学手段来包装的通俗故事。有些很不错的文学作品,如《废都》《曾国藩》等,一旦用通俗读物的方式来包装,也就加入了现代读物的行列。
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分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高雅的文学性作品,不过是为了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市民消闲心理。以人性的三大欲望而言:一、权力欲望,这是男性社会的主要冲动本能之一,在中国,作为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积淀尤为深刻,有作为的男人们的日常消遣主要就是演习争权夺利和尔虞我诈的生存本领。在现代都市里,市民们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所有的聪明才智都使用在单位里的人事纠纷、商场里的不正当竞争、以及里弄街坊间的邻里之争,一大批读物正是为适应市民多层次的需要而出现的:从各种“厚黑学”、政治笑话、处世公关,到政治黑幕秘闻、政坛人物回忆录、政治人物传记,一直到武侠小说、宫闱斗争、历史演义和《曾国藩》一类的历史小说,形成一个由浅入深的完整系列。二、物质欲望,这是现代都市里刚刚兴起的话题,自从股票、房地产等投机性事业开展以来,一阵一阵的发财潮刺激了都市市民的疯狂欲望,从读物的范围看,高层次的作品不多,但低层次的读物则从生活类指南、炒股指导、发财秘诀到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商界巨头的传记以及伴随商业明星的成功而来的现代消费指南等等,应有尽有。三、性爱欲望,都市人的性爱生活早已远离朴素、真纯的人类爱情方式,各种权力和物质的欲望支配了人们的性爱生活,人的正常性爱要求被压抑在层层都市文明底下,只能被扭曲和变态地表现出来,一些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性标记,如咖啡馆、舞厅、卡拉OK、夜总会、甚至连一些餐厅发廊浴室都可以成为色情欲望的代名。作为现代读物,它不能不表现市民的这一欲望:从粗俗的层次说,各种色情画报、文字到性学大全之类,稍高些的层次,是夫妻知识、家庭保健、以及各种女性杂志和女明星的桃色新闻,再高些的层次是用文化包装起来的《素女经》之类的传统房事读物,再上去是琼瑶、亦舒等通俗言情小说和外国色情小说,最高层次还有劳伦斯、昆德拉、《金瓶梅》之类文学性作品,亦自成一个完整系列。除此以外,还有都市人各种心理折射出来的心理欲望:如命运欲望、女权欲望、儿童教育欲望、休闲欲望等等,自成体系地构成完整读物系列,来满足各层次的都市人的阅读需要。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大多数文学性读物仅仅是都市人各类欲望的派生物,并没有独特的审美意义存在,这与纯文学作品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极个别的例外,象劳伦斯、昆德拉的小说,在读物和纯文学两个领域里同时承担价值意义)。
在庞大复杂的现代都市民间文化领域中,现代读物只是其中一个部落,而文学性读物又是这个部落中代表了较高层次的部分。知识分子虽然参与其间,但为了遵循商业市场的成功,就不得不遵循“读物”的规律。其创作立场、审美功能及读者接受方式,都有所变化,娱乐性商业性取代了原创性,作家特立独行的人格立场被包容在民间藏污纳垢的恢然世界中。以贾平凹的《废都》为例。这部作品无疑属于现代读物中的翘楚之作。在创作立场上,它也包含了知识分子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的严肃内容,而且其批判的深度是贾平凹以前的创作所不及的,但是在表述这些内容时,作家则采用了非知识分子化的民间立场:其一、他以采风形式在小说里插入了大量的政治民谣、顺口溜和社会性传闻,用民间的口传文本来表达知识分子立场;其二、他对知识分子在现实环境下感到无路可走的苦闷和自暴自弃心态虽然揭露得相当尖锐,但也不是持“抉心自食”式的知识分子反省态度,而是采取了浮浪的性游戏的宣泄,知识分子连一个崇高的忏悔形象也不是,只是在放浪形骸中实现自我消解。在审美功能上,它的大量潜文本都来自中国传统民间读物,许多陈旧的审美手段甚至语言方式对小说产生了过多的影响,这些传统民间读物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失去了实际价值,只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取向,它们过多地从小说文本里浮现出来,反而造成作品与现实的隔阂。其实,对知识分子由政治绝望转向性的变态追求的文学表现,并非自贾平凹始,远的不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就表现过类似的主题,昆德拉小说的中译本和贾平凹的《废都》在许多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不同者,昆德拉写的是东欧的事,但一些对社会政治的思考能让人生出强烈共鸣;而《废都》写的虽是近事,其情趣则让人感到遥远得很,那就是潜文本里透出来的令人生厌的混浊之气所致。在读者接受方式上,《废都》也改变了贾平凹原来的读者接受心理,贾平凹是个农民出身的作家,从小接受了农村民间文化的熏陶,这在他用文学方式来表现农村世界时,有些民间的隐型结构仍然能派上用场,如“换妻”模式,就成了他表现农村主流意识形态时的民间包装;又如他对商洛地区民风民俗的描写,形成了他的散文作品特有的优美风格,并且掩盖了早就存在于他的作品中的粗鄙化倾向,他的读者主要是都市青年,就好象都市人到野外郊游,觉得处处是佳景,谁也不会注意到风景背后的粗鄙简陋;可是一旦贾平凹写起现代都市的时候,这些传统民间包装的优势再也无法展示出来,再加上使用了读物文化的促销方式(如大肆宣传其性描写等),在都市青年看来不但没有现代都市的精神,反而处处暴露了农民的粗鄙特征,所以原来对贾平凹的作品抱有“美文”期待的读者心理因此破灭,尤其是从新文学传统的知识分子立场来看,这种失望更加明显。
《废都》自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从《废都》的变化可以看到都市文学如何由高雅的精英文化向粗俗的读物文化转化:一、都市文学转向读物文化的过程也是高雅的精英文化发生自我蜕变的过程,有一批作家从都市文学中分化出来,游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二元对立”结构,在都市民间寻找新的立足点,这使都市文学的结构趋向复杂多样;二、现代读物文化也是多层次的,从最低俗的声色犬马文化,到较高层次的文学艺术性读物,其承担的功能并不一样,在较高层次上的读物,依然需要有知识分子去参与,以满足文化层次较高的一部分读物对象;三、即使象贾平凹这样较为优秀的作家,当他向读物写作转化的时候,他仍然需要放弃一些原有的知识分子传统,改为民间的方式表达自己,但由于民间在现代都市的价值虚拟性,它已经不可能如农村民间文化那样富有生命力,因此无论是对旧通俗文学文本的摹仿还是旧生活方式痕迹的再现,都不可能真正传达出现代都市的精神。贾平凹为此付出了代价,是值得重视的。
现代读物无论是为了满足现代市民的哪一类欲望,其实都是以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这方面的满足为基础的,读物仅仅是起到一种精神替代的作用,这种精神替代对读者来说属于个人隐私,并以扩大这类纯属私人性质的阅读空间来满足都市人做白日梦的需要。现代读物文化与影视传媒文化、流行音乐文化一起建构起现代都市文化的民间世界,它们的出现,使都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化出多层次的文化,以取代文化专制主义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控制都市市民的文化状态。从这个意义来说,现代读物文化有它一定的革命性。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读物文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启蒙也是一种有力消解,它是以扩大现代市民个人隐私的卑琐情怀来抵消崇高理想,使人们在自我白日梦中得以陶醉,放弃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和批判责任,来适应日益技术化的现代经济社会。在西方发达的民主社会里,现代读物往往起着使人们无形之中自动放弃民主权力的功能,它仍然起到了专制社会想起的作用。
所以,知识分子对读物的参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香港,知识分子常常为了生存而参与读物写作,但他们从不将这类文字当作文学作品或个人著作来看,笔者曾访问香港文坛宿耆刘以鬯先生,他说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从事读物写作时总是一把辛酸泪,决不承认这些读物为他的作品。在这些香港的严肃知识分子看来,文学是文学,读物是读物,两者不可混淆;而在大陆,随着商品经济和都市文化的发展,读物的迅猛发展吸引了大量名作家加入读物的写作行列,这本来也是自然的现象,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大陆有不少作家以为凡是自己写下来的一定会是文学作品,认为自己有几付笔墨,能俗能雅,还容不得别人批评。这就有些可悲。现代读物在都市文化中自有其应有的地位,但不是文学上美学上的地位,更不是知识分子的价值所在。知识分子通过参与现代读物的写作,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读物的品味,这也不过是满足了一部分较高层次的文学性读物的要求,而且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这是不能回避的。
但是有一种例外值得注意:即前面所举的一些文学作品在读物和纯文学两个领域里同时承担价值。如劳伦斯、昆德拉、纳博科夫的小说,在纯文学领域自然有其重要价值,尤其在展示人性的深度上具有经典的意义,但它们在现代都市流行文化中获得了另一种解释,有关性爱的描写,有关人生的哲理,都被引申出通俗的意义;还有些原来属于纯文艺的作品,但为了促销也当作现代读物来包装,如前面所举的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人的作品,均属此类。这些具有多重性含义的作品,本来就该作多重的分析,既可以从思想艺术的角度分析其人性开掘的深度;也可以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其展示人性卑琐的一面,甚至可以从庸俗的角度对其作出歪曲性的理解。但无论怎样,其作为现代读物的功能,与其在文学上的价值不能相提并论。以张爱玲为例,她的作品在读物市场上所受的欢迎,并不是她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小说,也不是学术研究,主要是她的那些展示私人空间的随笔,这些谈吃论穿的小品正好迎合了现代都市市民要求扩展私人空间的精神需要,一些所谓“小女人散文”的盛兴,正是张爱玲式文字的血缘遗传,这当然也有它存在的意义,但如果把这些文字看作是张爱玲的全部美学价值的证明,那也确实污辱了这位现代都市文化的开创者。
当代都市文学创作中的民间形态是个比较复杂的现象,现代读物不过是其中一种形态,由于它与都市通俗文化的联系密切,所以与知识分子的原有传统处于较为对立的地位,知识分子对读物写作的参与多少是一种自我背弃行为;但这并非是知识分子参与民间的唯一途径,有些坚持纯文学立场的作家们在反省了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后,也有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吸取某些都市民间形态的内容,扩大都市文学的表现空间,使现代都市文学从张爱玲以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注:本文是作者撰写的长文《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第五部分。前四部分发在《上海文学》第10期,可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