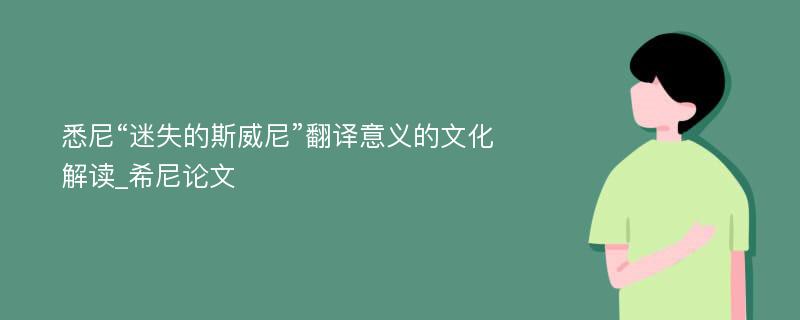
希尼《迷途的斯威尼》译本意涵的文化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译本论文,迷途论文,威尼论文,文化论文,希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6-0103-05
作为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今爱尔兰最重要的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诗名已为世人熟知。在当下国内日益升温的当代爱尔兰文学/文化研究中,希尼的诗歌及诗学最受人关注,研究也最为深入。然而,希尼作为一名翻译家,其翻译成就却没有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翻译作为充满文化和政治张力的场域,为跨民族、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提供绝佳的视角。自1972年到1999年的二十七年中,希尼的主要英译作品有:《迷途的斯威尼》(Sweeney Astray)、《特洛伊的弥合》(Cure at Troy)及《贝奥武甫》(Beowulf)。翻译虽为希尼诗歌创作外旁逸斜出的“副业”,但希尼对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立无不别具用心、深含文化意图,正如希尼自己所说,“一个讲英语的爱尔兰作家把爱尔兰语文本译成英语,所引发的思考往往不仅限于严格的文学层面,历史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考量定会附加其上”。(Heaney,2002:59)
《迷途的斯威尼》是希尼的第一部译作,其翻译工作始于1972年,1983年由户外日戏剧社(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出版。面对一本厚度仅八十五页,却耗时十一年的译本,读者不禁会问:什么原因促使诗人转向翻译?斯威尼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它引发希尼怎样的现实思考,并赋予它怎样的文化意涵?为何希尼一改其作品由伦敦费伯出版的惯例,将译本交由位于北爱尔兰德里郡的户外日戏剧社出版?①导致出版商之易的因由何在?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译本生产的历史文化语境及译者翻译策略的考察,探讨《迷途的斯威尼》译本的政治文化意涵。
一、斯威尼,一个爱尔兰文化困境的隐喻
爱尔兰大量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是爱尔兰文学中的瑰宝。在尚无编年历史记载的时代,产生于爱尔兰中古时期的传奇故事,折射出爱尔兰文化演变的历史痕迹。这些故事大体分成四种类型:记录前基督教诸神的神话纪、描写北方英雄的阿尔斯特纪、记录爱尔兰和苏格兰民间故事的芬恩纪和讲述爱尔兰历史上众多国王故事的国王列传。(陈恕:2)斯威尼的故事属于国王列传系列。
斯威尼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637年爱尔兰历史上的莫伊拉战争。始于口头文学,经过几百年的口口相传,直到公元9世纪基本成型。尽管斯威尼故事流布广泛,广为人知,但斯威尼文稿直到1671年,才在爱尔兰共和国的斯林哥郡被首次发现。斯威尼故事有多种版本,1913年爱尔兰古籍协会(Irish Texts Society)出版的奥克菲(John O'Keeffe)的双语版《疯人斯威尼》(Buile Suibhne),因综合了不同的版本内容、尊重了不同的源文化,被公认为斯威尼故事的正版。
根据奥克菲的版本,斯威尼是达-艾里的国王,圣诺兰·芬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一日,诺兰来到斯威尼的领地筹建一座教堂。斯威尼听到陌生的铃铛声,得知来者诺兰及其意图,他勃然大怒,将诺兰的圣诗扔进湖底,由此得罪了诺兰。在去往莫伊兰战场的途中,诺兰意欲结好斯威尼并祝福他的军队获胜。斯威尼不以为然,并企图用矛射死诺兰,未果,其中一支矛射死了诺兰的随从,另一支仅仅击中了诺兰脖子上的铃铛。诺兰怒而诅咒:斯威尼将像矛一样在空中飞行,最终死于矛下。诅咒灵验,斯威尼赤身裸体逃离战场。发疯后的斯威尼化身鸟形,在爱尔兰上空不断盘旋。从此,它四处流浪,栖息于枝头,被人类追捕。临死前,斯威尼皈依基督教,灵魂得以升天。
1972年,希尼根据奥克菲的版本重译斯威尼故事。然而,是什么因素促使诗人希尼走向翻译?他又缘何钟情于斯威尼故事呢?
1960年代末,希尼出版了两部诗集《一个博物学家之死》(1966)和《通向黑暗之门》(1969)。他诗歌中典型的爱尔兰风情、强烈的民族传统意识和鲜明的重音节奏使他在众多爱尔兰诗人中脱颖而出,成为英语诗坛耀眼的新星。正当希尼初尝诗歌创作成功的喜悦时,北爱尔兰民权运动在欧洲大陆的民运浪潮中风起云涌。英爱新一轮政治冲突爆发,北爱内部的宗派纷争再起。1969年,英军进驻北爱首府贝尔法斯特和第二大城市、天主教徒聚集地德里郡。1972年1月30日,德里爆发著名的“血腥星期天”事件:十三名手无寸铁的天主教民权人士被英军开枪打死,二十多人受伤。
众所周知,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民族纷争由来已久。自17世纪以来,爱尔兰为争取自由,民族独立运动不断。直到1921年,爱尔兰南方二十六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1948年,成立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然而自1921年以来,原北方阿尔斯特地区九郡中的六郡改称北爱尔兰,仍归属英国。这一政治格局使北爱尔兰成为矛盾集中爆发区。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所导致的北爱归属论争成为该地区核心冲突所在。
“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里,身份问题和文化差异问题在阿尔斯特地区变得强烈而紧迫。诗人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身份的政治之中。”(Heaney,2002:60)作为出生于德里天主教家庭、声名鹊起的诗人,希尼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公众期待。人们期待这位公众人物宣示他的身份和立场。1972年8月,希尼举家迁往南方的葛莱莫(Glanmore)。远离政治和宗派冲突的中心,并不意味着诗人逃离责任。物理距离的疏离和心理相对的平静,让诗人寻找新的途径,“寻找足以表达我们困境的意象和象征”。(Heaney,2002:60)
“斯威尼是一种在场,一个寓言,引发我内心的感受,一种无法用其他语言表达的感受。它是投射的梦,或一种可能,或神话,超越了我个人的情感旋涡。它是一个客观对应物。”(Allan:122)首先,斯威尼故事对应北爱宗教文化的冲突。斯威尼与诺兰的冲突以及斯威尼的最终皈依本质上是爱尔兰原有的凯尔特“异教”与后来的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是公元5世纪爱尔兰进入基督教化时期的历史反映,是爱尔兰宗教演变进程的历史写照。更进一层,斯威尼故事中古爱尔兰宗教的历史冲突又恰巧对应着当代北爱尔兰天主教与新教间的现实对立。
其二,斯威尼故事对应北爱地缘归属的冲突。自16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大量涌入阿尔斯特地区,开垦良田,圈建种植园,致使阿尔斯特成为以新教徒为主的地区。持抱联合主义思想的新教徒自然认定阿尔斯特地区属于英国。1921年12月实施的《爱尔兰自治法案》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再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北爱的政治归属。然而,斯威尼故事却提供了另一个事实:阿尔斯特曾属于爱尔兰。从地形学意义上而言,“斯威尼的达-艾里王国坐落于南方的安提郡(County Antrim)和北方的顿恩郡(County Down)”。(Heaney,1984:iii)这两个位于今天北爱尔兰的郡邦都曾属于阿尔斯特九郡之一。在前英国时代,早已是凯尔特人(斯威尼的臣民)的居所,其文化也是凯尔特文化特征。
最后,斯威尼故事对应北爱多元文化结构。一方面,斯威尼时代的爱尔兰,葆有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凯尔特传统,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传统却与“西部苏格兰保持着文化上的类似性”。(Heaney,1984:ii)在斯威尼疯癫后,所有足以信赖的人纷纷背叛,只有鸟儿们和英国疯子阿兰随从接受他。斯威尼与阿兰的联系似乎提供一种巧合:阿尔斯特与英国的联系。不同文化间的对立、相似和联系,在深层次上,映照出北爱尔兰多元的文化构成。
然而,不同于叶芝的传统——挖掘民族英雄故事、重建凯尔特民族形象,希尼选择的是凯尔特民族中的一个“失败者”形象,因为对他来说,“斯威尼呈现出的替罪羊般的、异化的故事更具沉思性、感伤性”。(Forster:99)斯威尼故事实乃北爱文化困境的一个隐喻。在70年代初北爱尔兰政治冲突和宗教纷争的现实语境中,“斯威尼应该是普众基本情感的代言人”。(Heaney,1992:vii)
重译斯威尼故事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二、翻译策略与凯尔特文化认同
“如何将一个产生于中世纪凯尔特文化时代的文本向一个生活于凯尔特文化消亡的当代阿尔斯特人讲述?”(Heaney,2002:61)就目的语接受对象而言,《迷途的斯威尼》直接面向的是多数新教派和少数天主教派的英语读者。接受对象决定了讲述的方式。
奥克菲的斯威尼版本是一个散文和诗歌的杂体。散文重在叙事,诗歌意在抒情。在译诗部分,不同于奥克菲的自由诗原版,希尼采用四行诗节、重押韵的传统英诗形式。下面仅以两节译诗为例:
No skilled musicians' cunning
no soft discoursing women,
no open-handed giving;
my doom to be a long dying.
Far other than tonight,
far different my plight
the times when with firm hand
I ruled over a good land.
(Heaney,1992:95)
这是诺兰的咒语灵验后,斯威尼化身鸟形飞翔过程中痛苦心理的写照。译文的诗歌部分几乎都是四行诗节,押尾韵,但也不乏头韵和内韵形式,遵循英诗的诗学原则。其实,《迷途的斯威尼》的第一版翻译早在1973年就已完成。(Parker:121)但第一版采用的自由诗形式在希尼自己看来“过于仓促和大胆”。(Heaney,2002:64)他很快推倒重来。从1973再译到1983年出版,希尼花费十年的功夫,呈现给读者的第二版采用英诗传统诗行和韵律,无疑出于一种成熟思考和刻意而为:
我希望这本书呈现给联合主义者一个可接受的概念——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这并非略化他们所珍视的信念:阿尔斯特是英国的。同样,因本书回溯到殖民前的阿尔斯特地区的寺院基督教和凯尔特君主制,我希望本书增强一个概念:阿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文化发展是因多数派的数个世纪来的胜利和定居所致。(Heaney,2002:61)
诚然,英国在历经了自12世纪以来与爱尔兰长达四百多年的历史纠葛后,于17世纪在爱尔兰取得“决定性”胜利。1601年金赛尔一役(Battle of Kinsale),爱尔兰军队失利,1607年盖尔大领主纷纷逃亡欧洲各国,凯尔特秩序在爱尔兰终结。(Cronin,1996:54)随后,英格兰和苏格兰种植主大规模进入爱尔兰,阿尔斯特成为英国新教派最集中的地区。
然而,斯威尼却是一个前英国时代阿尔斯特文化特征的历史见证。作为一个意欲改变当代爱尔兰新教联合主义者的文化认知的文本,《迷途的斯威尼》所采用的流畅翻译策略旨在获得打开沟通大门的通行证。事实上,在以英语为通用语言、文化多元并存的当代爱尔兰社会中,“流畅策略对爱尔兰抵抗文化分裂主义是有益的。‘无翻译’原则本身便暗示着一种调节,爱尔兰文学遗产能尽可能适应英语读者。”(Cronin,2003:141)但“翻译都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均反映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操控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Bassenett:ix)希尼对翻译斯威尼故事的寄望——“希望北方的联合主义者或北方的新教徒能认同凯尔特文化”,(Corcoran:261)从本质上说,就是希尼意欲对目的语读者意识加以改写和操控。
在《迷途的斯威尼》译本中,改写的形式有二:文本内的改写和文本外的改写。
首先,奥克菲的爱尔兰语标题Buile Suibhne被希尼改成了Sweeney Astray。“虽然没有原文爱尔兰语音的脆亮饱满,但Sweeney Astray更强调了斯威尼处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迷失状态。”(Heaney,1984)其次,与奥克菲版的斯威尼形象相比,希尼的斯威尼变得更为正面和惹人同情。如第43节,原故事中斯威尼伤感妇人抢走了他的粮食——水芹,因此诅咒妇人:“你抢走我的水芹,你也将/被蓝衣大盗抢劫/饱受良心的谴责/诅咒的神明来到你我之间。”但希尼去掉了最后一节:斯威尼将诅咒延伸到林奇西辰(Lynchseachan)身上。林奇西辰是斯威尼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在斯威尼疯后,霸占了弟媳。显然,希尼的改写使斯威尼发疯后的人物形象中少了仇恨和报复,加上他四处漂泊的凄苦,哀怨声中更惹读者同情。试比较奥克菲和希尼对斯威尼困境的描述:
Gloomy this life,
Without bed or board
to be without a soft bed,
I face dark days
abode of cold frost,
in frozen lairs
roughness of wind-driven snow.
and wind-driven snow.
Cold,icy,wind,
faint shadow of a feeble sun,
Ice scoured by winds.
shelter of a single tree,
watery shadows from weak sun.
on the summit of a table-land.
shelter from the one tree
on a plateau.
(Sweeney Astray,1992:51)
显然,希尼版本中以第一人称自叙方式,更好地传达了斯威尼感受的真实性和真切感。斯威尼形象的改写无疑旨在以流畅策略进入目的语读者视野,同时重塑斯威尼作为凯尔特文化表征的形象,以实现认同的可能。此外,文内改写还体现在译者对爱尔兰地名的处理。在英国对爱尔兰殖民的历史过程中,爱尔兰语、爱尔兰地名一直是殖民与反殖民较量的场所。②爱尔兰地名几近英语化,斯威尼文本中众多古爱尔兰地名已无法找到现实的对应。“在寻找对应的爱尔兰地名时,我发挥了创造的自由”,(Heaney,1984:v)对一个身处后殖民时代的翻译家而言,“材料的消失恰巧是一种历史的暗指”。
文本外改写主要体现在译本的序言和希尼的散文中。“翻译者常以序言、后记、评论来评论自己的文本,以此来增强对自己作品的权威评论”。(Bass nett:22)这一文外的改写方式,被克洛宁称为“前景化翻译行为”(to foreground the act of translation),(Cronin,2003:151)以突显译者的身份和源语文本的异质文化特征。
希尼在他的1983年版和1992年版的序言中,都清晰地表明了他选择斯威尼故事的地形学意义上的考虑。“斯威尼王国座落于今天南方的安提郡和北方的顿恩郡。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住在这一地区的附近,见过众多斯威尼的住地,听闻过众多斯威尼的故事。当我开始翻译时,我已搬到了威克娄,离斯威尼最后的栖息地圣木林不远。”(Heaney,1984:iii-iv)希尼的出生地德里郡,和安提、顿恩郡都曾属阿尔斯特,现归北爱尔兰。因而,地缘政治的考量使希尼在他1984年的散文《赢得一种韵律》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政治意图:
通过对前英国历史记忆的扩展,能在联合主义者间激发起对民族主义者的某种同情,少数派们从凯尔特的梦想之地确立他们失去的权利……我仅仅想提供一个本土的文本,以不至于威胁到联合主义者(毕竟这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发生于今天的安提郡和顿恩郡),同时以助民族主义者(毕竟这个古老故事告诉我们过去的归属,这一所在今天犹在)。(Heaney,2002:61)
天主教家庭出身的希尼,努力彰显凯尔特文化的历史存在,为少数派民族主义者张目的政治和文化意图是显在的。
三、出版商之易与当代爱尔兰民族主义
1983年,《迷途的斯威尼》由户外日戏剧社出版。希尼缘何打破惯例?了解户外日戏剧社能为理解此次出版商之易提供答案。
1980年,戏剧家弗里尔(Brian Friel)和演员瑞(Stephen Rea)在德里成立户外日戏剧社。评论家狄恩(Seamus Deane)、希尼、诗人泼林(Tom Paulin)等六人担纲艺术指导。戏剧社的成立,不仅为了推动北爱舞台戏剧的发展,而是有更大的文化政治意图。选择德里,是因为德里南北向地处北爱与南方共和国的交界、东西向形成北爱东部都市与西部乡村的分野。作为天主教聚集地和宗派冲突之所,其设址的政治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聚焦80年代初户外日戏剧社的舞台剧目和系列出版物:弗里尔的戏剧《翻译》(1980)着力表现英国殖民时期以翻译为手段的殖民方式和爱尔兰语的窘境;希尼的诗歌《一封公开信》(1983)公开宣示自己的“绿色”爱尔兰身份、拒绝英国诗人的称谓;泼林的《再次回顾语言问题》(1983)回首了爱尔兰语边缘化的历史、提出出版爱尔兰方言词典的建议;狄恩的《文明人和野蛮人》(1983)指出爱尔兰民族在英国殖民叙述中被扭曲的事实及重建民族形象的必要。这些无不围绕爱尔兰的文化、身份、政治和艺术问题展开的出版物无疑也宣示了戏剧社作为一个政治和文化团体的存在。作为戏剧社的重要出版物之一,《迷途的斯威尼》的出版与户外日戏剧社“休戚与共”的关系,在北爱尔兰80年代初白热化的宗派冲突中,③显然具有政治文化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迷途的斯威尼》与诗篇《一封公开信》同在1983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虽然《迷途的斯威尼》究竟是否真是希尼殚精竭虑地耗费十年之功翻译而成,还是有意延宕译作的出版,尚不得而知,但与诗篇《一封公开信》出版的“机缘巧合”,及《一封公开信》发表的由来或许会深化我们对《迷途的斯威尼》出版的认识。
1982年出版的《企鹅当代英国诗歌集》收录了六位爱尔兰诗人的诗作,并将希尼列于这一“英国诗歌集”之首。相较于其他五位爱尔兰诗人的沉默,希尼于1983年大声宣称:“我的护照是绿色的/我们从不为/女王举杯……不,‘英国人’是错误的命名。”(Heaney,1983:7)与《迷途的斯威尼》中“暗藏的政治上的调皮”相比,《一封公开信》是希尼最为公开的政治宣言。这首诗是希尼唯一没有被费伯收纳的作品,诗人自己也再无后文提及。但无论如何,1983年《迷途的斯威尼》和《一封公开信》在户外日戏剧社出版,它们与前文提及的户外日戏剧社同年发行的另外两件作品(泼林的《再次回顾语言问题》和狄恩《文明人和野蛮人》)一起,无疑构成一串充满民族主义意识的“信号”。
然而希尼及户外日戏剧社成员们并非偏狭的传统民族主义者。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者力图建立一个去盎格鲁化的爱尔兰,恢复最真实的凯尔特特质。这一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实质上加剧了民族间的对抗和分裂。面对爱尔兰多元文化的现实语境,如何构筑联合的爱尔兰民族,是希尼一代在反思前辈的失败和教训后,需要面对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政治和文学,都应该重写、重读。”(Deane:17—18)当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旨在多元兼容的意识框架下重新书写爱尔兰文化身份。
早在1978年,希尼在《关于约翰·莫瑞兰一个有趣的例子》一文中,就显露出新的爱尔兰文化认同观:
爱尔兰文化是由多种相互冲突的传统组成的。尽管它们形式上相互排斥,但本质上相互依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那些自称是爱尔兰人的人群……无论是盎格鲁-爱尔兰人、天主教盖尔人还是新教种植主,每一种传统都是爱尔兰历史的一部分。每一种传统都是向内的、虔诚的、排他的和局部的。(Heaney,1978:39)
希尼这一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观与两年后成立的户外日戏剧社“建立第五省文化空间”的文化意图和阐述合流。在戏剧社成员们看来,在爱尔兰岛历史上的四省(阿尔斯特省、莱因斯特省、蒙斯特省和康奈驰省)之上,应该建立起第五省——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想象的文化空间,以超越爱尔兰的政治对立。爱尔兰语Coiced一词代表“省”,同时又恰巧是“第五”之义。在某种意义上,戏剧社的“第五省”概念暗合霍米·巴巴在其论文集《文化的定位》中提出的“第三空间”概念——以杂合化的形式空间解构原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间的二元对立,二者在解殖民文化意图上形成通约。
希尼重新定义爱尔兰性(Irishness)的文化平衡意识在90年代得到进一步阐述:“我们无需放弃对爱尔兰的认同,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可伸缩的定义……人们可以在多个文化身份中协调的理念应该受到推崇。我建议北方的多数派也能回应这一平衡的提议,开始在爱尔兰框架之内,而非之外考虑问题。”(Heaney,1995:202)希尼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回首《迷途的斯威尼》的翻译时,再次强调他们这一代作家超越天主教主义和新教主义的必要。“我们这一代作家需要穿越荆棘,而非表现荆棘……穿越荆棘的唯一道路就是重新思考你所知道的,转化你自己。”(Barry:9)的确,在反思20世纪上半叶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中,希尼及其同代以更为宽阔的视野和多元兼容的胸襟规划民族文化的新方向,意义深刻。
对希尼个人而言,选择翻译,是爱尔兰传统的“外出度冬”④式的蓄养,是一种斯威尼式的逃离和飞行。但不同的是,希尼并未迷途。相反,他在70年代的诗歌中,发掘沼潭意象(bog image),以系列沼潭诗审思北爱宗教纷争的历史由来。在新的翻译领域,斯威尼作为另一意象,对应北爱的文化困境。诗歌和翻译作为深层通约的场域,使希尼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进入爱尔兰的文化政治话语。重新定义爱尔兰性,使其成为更具包容性的概念,重新书写“后”时代的爱尔兰文化身份,构筑当代爱尔兰民族文化发展之途,是当代艺术家/人文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承担。与诗歌相比,希尼在翻译中的文化立场更为明晰。
就翻译理论而言,归化式流畅翻译策略,在形式上是对英语诗学原则的顺从,但译本的选择及其后的政治意图,恰巧代表了不顺从、改写和抵抗。在后殖民多元文化并存的爱尔兰现实语境中,爱尔兰翻译中的流畅策略是实现文化和解、抵抗文化分裂主义的有效手段。这与众多后殖民翻译理论家所主张和推崇的异化翻译策略构成抵牾。爱尔兰作为欧洲内部的英国前殖民地国家,在后殖民批评话语体系中兼具普适性和特殊性。一方面,爱尔兰的翻译历史就是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史;另一方面,基于对原殖民文化解构的非流畅化异化翻译在实际效果上加深了爱尔兰新教派文化的疏离感,造成更激烈的文化对抗。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希尼及当代爱尔兰翻译实践为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探索和丰富提供了新的、可深化的考察案例。
注释:
①希尼的所有诗集和著作中,有三本特例:《迷途的斯威尼》和1990年的译作《特洛伊的弥合》是先交由户外日戏剧社之后,再在费伯出版社出版。此外,1983年的诗篇《一封公开信》,由户外日戏剧社出版。这是希尼作品中唯一没有交由费伯出版的作品。
②例如北爱尔兰的第二大城市德里Derry,在英国地图上,标明是Londonderry,但德里街头的路牌上,London字样往往有人为刻意擦除的痕迹。
③1980年1月,因政治诉求问题,北爱再次爆发天主教囚犯监狱绝食事件。
④外出度冬(wintering out)是爱尔兰农村冬季饲养牛羊的方式:冬天以最少的草料将牲畜圈养,等到来年春天,加大草料量,以达到快速长膘的效果。1972年(亦即着手翻译斯威尼之时)希尼发表了他的第三本诗集,该诗集命名为《外出度冬》,暗示出改变和渡过危机之意。
标签:希尼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斯威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基督教论文; 读书论文; 凯尔特论文; 诗歌论文; 天主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