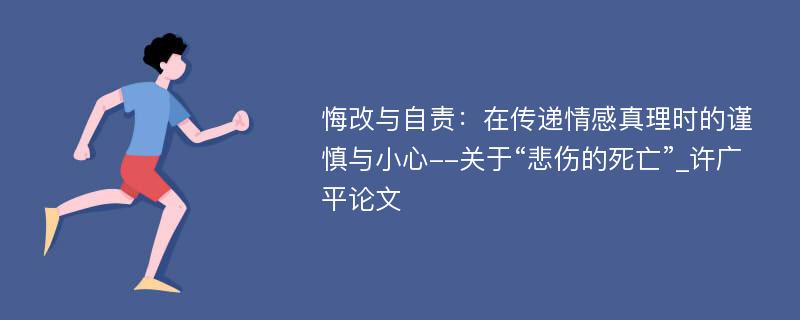
忏悔与自责:传递情感真实的谨慎与多虑——初论《伤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责论文,多虑论文,谨慎论文,真实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伤逝》诞生于“五四”退潮时期,是鲁迅著名的抒情小说。涓生与子君自由恋爱,婚后不久就分手了,子君回到父亲家里很快就去世了。涓生为此非常悔恨和自责。由于鲁迅用做诗的方法来写小说,用意象来传递思想,建构起了小说的“召唤结构”,造成了很大的意义空白,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联想空间,又由于1926年鲁迅曾非正式地表示它不是“写自己的事”(注:鲁迅:《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0页。),因而对《伤逝》 到底写什么,学术界莫衷一是。文学作品是作家的主体对象化的产物,是作家自我观照的结果。作家的主体本质个性通过作品得到肯定和表现。我认为,作为鲁迅唯一的一篇写男女爱情生活的抒情小说,毫无疑问与他自己有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将鲁迅还位,使之从圣人偶像退回到主体的“人”,补上过去神化时剦割的血肉情欲。而这正是以往学界的偏失。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去追寻作品与鲁迅的关系。
一、从时间上来说,作为鲁迅唯一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小说,《伤逝》与鲁迅当时的情感纠葛紧密相关。
“五四”时期,易卜生的《娜拉》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鲁迅以其冷静的态度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娜拉的出走,并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便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妇女要解放,应取得经济权,改革经济制度;这就必须要战斗,要参与社会解放的“剧烈的战斗”。否则,即使出走,摆在其前面的就“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一个月后,鲁迅又创作了小说《幸福的家庭》,描写一对1918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而自由结合的青年夫妇正经受着贫困与不幸,男主人公只得痛苦地用画饼充饥的办法来填补失落的空虚和打发着平庸难熬的日子,进一步表明了上述思想。《伤逝》表现的是不是也属这种思想呢?
我们从创作和面世的时间来说,《伤逝》创作于1925年10月21日,既不是写于1921年中国文坛写恋爱婚姻题材的高潮中,又不是在鲁迅演讲后不久写的,距女高师的演讲有近两年了。在那黑暗腐朽的动荡年代,两年内发生了多少风风雨雨和世事变迁呢?此时,“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解体了,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热潮退落。鲁迅从1925年3月起, 就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去,给予支持和指导,教给学生斗争策略,关注的是学生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注:参见1925年7月30 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7月版,第91页。),这时写的《伤逝》显然不会重弹老调,不切实际。而且,《伤逝》在1926年8至9月(注:参见1925年9月22 日鲁迅致许广平的信,鲁迅于18日寄《彷徨》一本于许广平,说明鲁迅此时才收到。因此,《彷徨》虽8月出版,但真正与读者见面可能在9月,因此,《伤逝》也可能是在8至9月与读者见面。《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03页。)《彷徨》出版时才与世人见面,距创作已有近一年的时间,距女高师的演讲已有近三年的时间。拖了这么久,如果它是继续表明女高师演讲的思想的话,难道鲁迅不知道这会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吗?况且当时与鲁迅约稿的很多,不难发表。与写《幸福的家庭》的情形相比,显然另有他意。这说明它并不是社会政治性的,无时效性要求,而是一种情感的抒发,并不在乎何时与读者见面。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创作这篇小说呢?如果我们深入到鲁迅当时的情感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
我们知道,为了尽孝道,鲁迅于1906年与朱安成亲,这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的生活。”(注:鲁迅:《坟·寡妇主义》,《鲁迅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 第61页。)1920年,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到北京,寄居在鲁迅家里,很快成为鲁迅在女师大时接触最多,相处最熟,感情最深的人。(注: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 月版,第94—103页。)“有时候,鲁迅带着羡苏回来的情况也有”, “有时候晚上很晚还在鲁迅房间里”,“在师生之间好像有了秘密关系,”,“朱安从这个学生身上看到了女人的感觉”。(注:中村龙夫:《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朱安》,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06页。)这无疑给鲁迅苦闷的情感世界送来了一缕清风,给鲁迅平静的感情湖面吹起了向往幸福爱情的涟漪。1923年7月19日,羽信太子为赶走鲁迅, 取南后陷害屈原之法来诬陷他,使兄弟失和,鲁迅于8月2日搬出八道湾。1924年6月 11日下午,鲁迅往八道湾取书及什器,又遭到他们夫妇的无理阻难和谩骂殴打;6 月18日,周作人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破脚骨》一文,恶毒攻击鲁迅。三个月后,鲁迅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以“宴之敖者手记”愤慨地记录了这次谩骂殴打事件。这是“五四”退潮时期,新文化阵营解体了,鲁迅思想上彷徨苦闷,这也就使鲁迅有可能去考虑个人的问题,而这件桃色诽闻的生造,使自省意识很强和性格“多疑”的鲁迅必然会联想到他的婚姻不幸,从而强化了他对旧式婚姻的否定意识。
正在这时,鲁迅应邀到女师大任教。他象磁石一般吸引着一群群青年男女学生,青年学生的蓬勃朝气也影响和感化着鲁迅,催发着他对异性的爱欲。但鲁迅喜欢有“才气”(注:孙伏园:转引自《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10页。)的人。1925年3月,许广平的出现, 就使他走向了摆脱农奴生活的道路。从许广平的第一封求教信起,他们书信往来不断,一个多月后就由师生感情发展为恋爱,7—8月间进入热恋,10月10日就确定了爱情关系。(注: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22页。)就在当天,许广平写下了表达他们爱情誓约的微型小说《同行者》,两天后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1925年12月26日,鲁迅也“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注: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鲁迅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23页。)了《腊叶》。1926年2月, 《国民新报·副刊》(乙刊)又发表了许广平表现他们甜密相爱的散文《风子是我的爱》和微型小说《结婚的筵宴》。《伤逝》写于1925年10月21日,偶然乎?必然乎?显然与鲁迅在人生十字路口抉择时的复杂心绪有关。
二、从写作技巧上来说,小说取名为“伤逝”,且详写婚后生活,略写恋爱经过,这与鲁迅不幸的婚姻紧密相联。
在中国,对妻子的悼念习惯上称为“悼亡”,对朋友的悼念才用“伤逝”。涓生与子君是夫妻,涓生对子君的悼念理应用“悼亡”,可小说却取名为“伤逝”,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表明涓生并未承认他们的婚姻关系,只将她作为自己的朋友看待;而在旁人的眼里,子君也只是涓生的一个朋友。涓生的世交告诉他子君死了时就是这样:“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他死了。”鲁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不幸婚姻中找到答案。1906年,鲁迅与朱安成亲,这是出于无奈,但心里从未承认过这种夫妻关系,从未过过夫妻生活。从定婚起,鲁迅对婚期就一拖再拖,曾明确表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注:鲁迅: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3年3月版,第28页。)。结婚当天即表明这是“母亲娶媳妇”(注:鲁迅: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6页。),花烛洞房夜时,他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即搬到母亲房里睡,第四天就借口功课紧返回日本求学,从此做起挂名夫妻。鲁迅在外经常给家人写信,却从来不给朱安写信,与朱安在一起的时候也从不与朱安交谈,更不去她的房间。他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注:鲁迅: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6页。)。“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注: 鲁迅: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 年3月版,第36页。)。可以说,“伤逝”用在涓生对于子君的悼念是不合适的,但隐喻鲁迅和朱安的关系上则是十分确切的。
在故事的叙述中,鲁迅对涓生和子君的恋爱只是简略的描写,重笔放在婚后生活的描写上。尽管作者力图以出色的心理描写来掩盖其“原初性”的“弱点”,但与婚后生活的描写相比,仍不免显得相当“虚空”、“抽象”、“理念”、“浮泛”,缺少婚后生活描写的那种细腻、具体、深刻、生动。为什么鲁迅要这样写呢?我认为这正与鲁迅的表意有关。如果作品表现的是对个性解放和爱情至上的批判的话,那么,对自由恋爱时冲破封建牢笼的行为和斗争进行比较细腻的描写,则可为后来的悲剧结局作铺垫和渲染,强化主题,可鲁迅的写作意旨不在此。他要表现的是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哀悼。而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并不是自由恋爱而成的。鲁迅这样写,是故意要淡化恋爱过程,使读者不被这表面的“自由恋爱”四个字所蒙敝,引导读者冲出这表层的迷雾去认真体会作者的情意所在。
三、从涓生与子君分手的原因来说,作品所描写的悲剧根源与鲁迅和朱安不幸婚姻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
婚姻爱情的幸福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结合形式,也不取决于双方拥有的物质条件。封建包办婚姻是造成婚姻不幸的根源,而自由结合的情侣也不一定就幸福,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物质条件丰厚、经济富裕的双方结合后仍然享受不到爱情的甜蜜和幸福,而许多贫溅糟糠的结合,往往两心相印,恩爱无比,其乐融融。幸福爱情婚姻的基础在于双方的感情及其依就的思想意识、文化修养、情趣格调、性格志向等内在的精神因素的高度相融和投合。涓生与子君分手根本原因正是双方情趣的不合、思想文化的隔膜。鲁迅在作品中给我们作了充分的展示。恋爱时,他们在一起谈话,子君总是不能理解,只是微笑点头,涓生指给她看墙壁上雪莱的半身像时,她却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旧思想在束缚着她,出于无奈,涓生曾想换过一张照片,但也终于没有换;涓生向她求婚,她很惊慌。在平时,涓生以为可笑的,子君却并不觉得可笑。不久,夜阑人静之时,他们便无话可说,只是“相对温习”,可是后来连这“温习”也渐渐稀疏起来。结婚后,涓生“渐渐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了解更深了,许多先前以为了解的,现在看来却是“真的隔膜”。涓生喜欢花,可子君不喜欢,却养起了油鸡和叭儿狗;涓生喜欢看书,注重夫妻间对话,可子君只是可惜的忙,终日汗流满面地醉心于家庭琐事,“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功夫都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涓生劝她不要这样操劳,她却“神色凄然”;涓生被局里开除,心情比较平静,觉得这是一种解脱,而子君却变化显著。“变了脸色”,声音也“只是浮浮的”。显得“较为软弱”;涓生自信地草拟求职广告,子君却很“凄然”,“实在变得很怯弱了”;涓生着手翻译文稿,需要安静,可除了阿随和油鸡的影响外,子君在屋里总是散乱着碗碟;涓生的思路不能中途打断,可子君每日“川流不息”地叫吃饭;涓生比较务实,子君却爱面子,好虚荣,怕房东太太嗤笑阿随太瘦,在饭菜紧张时还先拿出喂阿随,有时还把自己近来也不轻易吃的羊肉喂它,涓生把油鸡杀了、阿随放了,可子君很颓唐,神色凄惨,态度冰冷;涓生认为生活压迫不算什么,所痛苦的是夫妻之间的隔膜,可子君的识见“浅薄”,想不到,将道理示给她,她不懂或不相信;“她的勇气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这种隔膜,终于逼迫涓生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他们都意识到了这种不合与隔膜的严重性,都试图设法弥补,但往往适得其反。子君近来不仅也间或有“温暖的神情”,“而且对我却温和得多了”,“但这却反而增加了我的苦痛”;涓生把“明告”的真实改作免强的欢容,但换来的是冷嘲;涓生勉力谈想,想给她一点慰藉,换来的却是一个“恶毒的冷嘲”;子君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涓生也“做出了许多温存”,但“子君有怨色”,涓生也因此“觉得难于呼吸”,倍感“苦恼”;涓生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往事,提到文艺,“称扬诺拉的果决”,但子君“所磨炼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还只是一个空虚”: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既不能“携手同行”,更不能“奋身孤往”。可以说,双方都做出了许多努力,但还是解决不了这矛盾,“新的希望只有分离”。在小说中,鲁迅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去描写和展示他们在思想、文化、情趣上的不合与隔膜。正是这种隔膜与不合,形成了一条横亘于他们夫妻感情之间无法逾越和填补的鸿沟,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消逝。
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根源,与鲁迅不幸婚姻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鲁迅和朱安婚姻的不幸,主要不在其结合的形式而来自精神主体方面的差异。鲁迅留学日本,不仅学贯中西,博闻强记,而且思想激进,痛恶封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将,始终冷静地谛视现实,要求革除封建痼疾和社会弊端。而朱安则是一个没有读过一点书、受过一点新教育的旧式小脚女人,见识短浅,思想保守,只恪守三从四德,牵着别人的衣角过活。由于这种差异太大,言行举止相互不能理解和融洽,感情的间隔越来越深,关系始终好不起来。尽管鲁迅曾想“好好地供养她”(注:鲁迅: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6页。), 朱安对鲁迅抱着“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注:朱安: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3页。)这个想法,全力料理家务,但由于他们思想意识、 文化修养、性格志趣隔膜太深,挂名夫妻的关系也维持不下去。涓生与子君的不合与隔膜,不正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真实表现吗?
四、从主体情感来说,涓生那种深深的悔恨和自责的心情,与鲁迅在和许广平恋爱定情时的复杂心理是一脉相承的。
众所周知,在鲁迅与许广平的婚恋中、鲁迅一直是被动的,要不是许广平的积极主动,就根本不可能由师生关系迈向夫妻关系。封建婚姻给鲁迅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但是鲁迅“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注: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60页。),“常常想到别人”(注:鲁迅:《鲁迅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这使得他在与许广平定情时就会有所牵挂,心理上忐忑不安,犹豫徘徊。首先是他会牵挂着朱安,封建包办婚姻使他承受着“没有爱”的痛苦。但他觉得朱安“没有罪”,“不能责备”(注:鲁迅: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44页。)她, 而且还常常替她着想。鲁迅曾想过,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但想起绍兴可怕的习俗,软弱的朱安无力抵挡世俗的无情袭击,就总是说不出口,后来趁机说出来了,看到朱安怆然恳求,便又“携妇迁居”(注:鲁迅:转引自曾智中《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93页。)。现在与许广平确立爱情关系, 对毫无生活能力的旧式女人朱安来说,“一点一点往上爬”(注:朱安:转引自马蹄疾《我可以爱——鲁迅的情与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3页。)的希望落空了,她将如何去面对世人的白眼, 舆论的压力?!同时他还会惦念着许羡苏。许羡苏是一个新式女性,虽然她不象朱安那么弱小,但五、六年来她对自己的至诚至信,怎么能丢得下呢?1932年3月20日,鲁迅在致书母亲时说:“淑贞小姐久不见, 但闻其肚子已很大,不久便将生产,生后则当与其男人回四川云”。(注:鲁迅:1932年3月20日《致母亲》, 《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4页。)说明鲁迅时时都在惦记着她。分手六、七年了还这样,那么当时就更不必说。正是这样,鲁迅在与许广平的恋爱过程中才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在许广平的大胆追求和启迪下,鲁迅才迟疑地迈出了这一步。
在《伤逝》中,涓生刚刚有了“分离”的念头,就“也突然想到她的死”。便立刻自责和忏悔起来;他想明告她,却又不敢;当决心要说时,见子君孩子一般的眼色就“改作勉强的欢容”,当用了十分的决心说出了真实时,他内疚得不敢看子君那“灰黄”的脸色和雅气饥渴的眼光。尔后,他在冷屋中,在通俗图书馆都会想到她,时而“突然想到子君的死”,便立刻自责、忏悔起来,时而又出现子君毫无怨恨地勇敢地觉悟了的幻觉,这时,心理上就轻松起来。子君被接走后,想到他以后将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父亲的威严和旁人的冷眼中生活的时候,涓生就沉重地自责:“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应该永久地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众人们”。当涓生从世交那里听到子君真的死了的时候,便认为“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予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从此涓生“不太出门”。一任“死的寂静锓蚀着我的灵魂”。可以说,涓生这种溢于言表的悔恨和自责的心情是来源于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与朱安离异,与许羡苏“告别”时的复杂心理,是由他“常为他人着想”的道德情操引发出来的,与他当时的犹豫迟疑一脉相承。涓生是鲁迅的自况,子君则是一个综合意象,既隐喻朱安,又暗指许羡苏。
五、从作者所处的环境来说,鲁迅说《伤逝》不是写他“自己的事”,是在多种顾忌下说出的一种言不由衷的违心话。
鲁迅对封建传统思想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他的出身和长子的身份以及传统文化强大的裹挟力,仍使他在思想文化方面与“熟识的阶级”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背着因袭的重担”(注:鲁迅:《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鲁迅说:“我大约还是一个破落户”(注:鲁迅:《鲁迅全集》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页。), “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厌恶他,想除去,而不能”(注: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85页。)。正是“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注:鲁迅:《鲁迅全集》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使鲁迅显意识上猛烈抨击、 彻底否定旧道德、旧习惯,但内心深处仍然受到封建传统的羁绊,在生活实践中往往采取妥协、退让、容忍的态度。同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旗手,鲁迅有很多追慕者和崇拜者,但也产生了很多论敌和反目者,使他受到敬佩和赞赏的同时,又遭受着论敌的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和反目者的子虚乌有的阴险诽谤。这种身份和处境,使鲁迅遇事冷静,处理谨慎。正是上述原因,使鲁迅在处理与许广平的关系时“多所顾忌”(注: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60页。)。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妇之夫,与之相爱,旧道德不能容允,而且又极易给论敌和反目者留下“话柄”,可以肆意地攻击和诽谤。“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剧变而失去力量”(注: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60页。)。正是这种顾忌,使鲁迅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上“不甚竞争”,作出“退让”(注: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185页。),“挣扎着生活”(注:鲁迅:《两地书·序》,《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着。一是想爱而不敢爱。在与许广平的恋爱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既不敢积极主动地去爱她,又不敢理直气壮地接受她的爱;二是不愿过早地公开更不敢过早地承认他们的爱情关系。这可先从鲁迅信中找到依据:
我上船时,是建人送我去的,……我们谈了许多话。谈到我的事情时,据说伏园已经宣传过了。(怎么这样善于推测,连我也以为奇)。所以上海的许多人,见我的一行,便已了然。且深信伏园之说。建人说:这也很好,省得将来自己来发表。
建人与我有同一景况,在北京时的流言,大概是真的。但其人(指王蕴如,周建人后与其结婚,笔者注)在绍兴,据说有时到上海来。……(注:鲁迅:《鲁迅经典文集·鲁迅家书全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月版,第98页。)
显然,鲁迅是不愿过早公开他们的关系的。但仍然瞒不住,旁人多“已了然”,用不着“将来自己发表”,使鲁迅感到惊奇。为了保守秘密,就是在“最显真面”(注:鲁迅:《两地书·序》,《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书信和文章中,鲁迅也“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注:鲁迅:《两地书·序》,《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1926年底,鲁迅致书韦素园时说:“我还听到一种传说,说《伤逝》是写我自己的事,因为没有经验,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的。哈哈,做人真是愈做愈难了。”这种非正式的否定,实际上是在上述多种顾忌下说出的口是心非的话。当时,高长虹之流借恋爱问题恶毒攻击鲁迅,给世人带来了一些影响,他这时不能承认。而且,从信的思想内容的前后联系和这几句话的口气语调也完全可以看出,后面的“做人真愈做愈难”即是对前几句话的自行消解。也正是有上述顾忌,鲁迅在《伤逝》中采取“写神而不写形”的原则,突出涓生、子君爱情悲剧与鲁迅爱情婚姻不幸的“神似”,而不追求“形似”,将涓生、子君的婚姻处理为由自由恋爱而成而不是由封建包办而成的,这就使世人不会立即发现其中的奥妙。而且,写完《伤逝》,鲁迅不是立即拿出去发表,而是在他和许广平双双南下后才与读者见面,个中原因也就是顾忌大多。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作品的创作和面世的时间来说,还是从作品的描写详略或者是悲剧发生的根源来说,或者是从涓生对子君的自责、忏悔的情感心理来说,或者从作者所处的环境来说,《伤逝》都是写鲁迅“自己的事”。这是鲁迅处于特定情境中情感生活的写照。这不是牵强的比附,而是以其内在神韵律动的和谐一致为依据的。由于鲁迅思想上有着浓重的封建因袭,常常想着别人,又顾忌舆论,他不想使朱安等人受到太大的刺激,遭受太大的痛苦,不愿因此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鲁迅谨慎地向外传送出情感秘密信息,寻找着“跨进那里去的第一步方法。”
收稿日期:99—0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