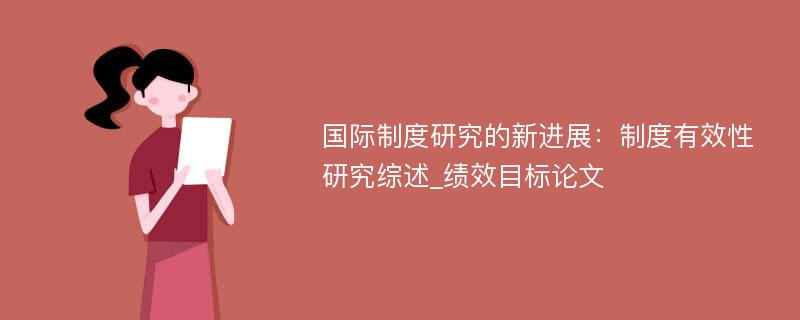
国际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制度有效性研究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新进展论文,有效性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2-0041-09
国际制度理论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发展主要是以国际制度研究为重心的。[1](P2)70年代初,国际机制概念的提出使国际制度研究平添了理论色彩,并使国际制度研究脱胎于早期的具体国际组织研究,尽管当时的研究还是处于描述的阶段。80年代,国际制度研究的重心从描述国际政治相互依赖关系和国际机制现象转向深入分析国家合作的条件。可以说,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制度理论,在80年代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这部分是为了回应社会困境研究以及集体行动问题研究提出的智力挑战,部分是为了回应与美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主导行为体行事能力明显下降相关的政治挑战。[2](P181)90年代中后期以来,理发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浮现并日益占据了理论争鸣的核心,国际制度研究与建构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迥异,它们之间的争鸣激发了学术活力,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界,推动了理论的发展。
近几年来,结合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国际制度理论的研究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考虑到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合法性和道义呼声的日益高涨,并且由于大量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制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对“建制”、“改制”和“转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3](P306—310)制度合法性、制度理性设计以及制度合作扩散开始纳入国际制度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二十年来一直作为制度研究重要领域的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国际制度与国内政治关联性研究及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也逐步深入,日益明晰。可以说,这两方面的研究代表了国际制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二战结束以来,有关国际制度作用已经成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个中心。[4](P729)在一份对国际机制的总体评论文章中,米切尔·朱恩(Michael Zürn)指出机制有效性已经成为分析国际关系的“驱动力量”(a driving force)。[5](P617)罗纳德·米切尔(Ronald B.Mitchell)也指出:“绩效问题已经成为制度研究者及实践者关注的中心。”[6](P79)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扩展和深化了对世界事务本质的理解。可以说,制度有效性是制度理论的核心。制度有效性最新的发展则显示出,制度作为全球治理的供应者,是未来全球治理的核心。
一、作为基本概念的制度有效性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起初都会碰到并思考如下问题:国际社会中一些问题为何比其他问题更容易解决?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会涉及什么条件下合作安排可以建立,以及什么条件下这种安排是有效的。在研究过程中,出于对问题解决的关注以及对成功制度的向往,对于制度有效性的关注愈加明显。在研究初期,相关的概念无序(conceptual disarray)彰显了有效性研究的必要。[7](P227—228)西方学者在有效性研究的相关概念、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有效性的来源、评估标准等方面,有的达成一致,有的分歧不少,呈现了制度有效性研究的丰富画卷。
各位研究者一般都接受了奥兰·扬(Oran R.Young)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定义。他指出,从一般的层面上看,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8](p187)也就是说有效的国际制度安排将引起参与者的行为主体、行为者的利益追求以及行为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的行为者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国际制度的约束。或者说,有效性是指行为者付出时间和力量建立制度,解决那些导致其形成的问题的状态。[9](P3)有效性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an elusive concept),很难做出规范的、科学的和历史的判断。休·沃德(Hugh Ward)等人从国际环境保护机制中得出的有效性是指:与机制规定的变量直接或间接关联,保护环境进程的完整;由机制规定的对环境的当前消耗,不会影响未来的需求。[10](P159)
国际制度研究的三大学派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对制度有效性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新自由制度主义致力于将国际制度作为干涉变量,通过改变机会可能性和有关国家对信息的既有控制,从而协调国家对自利的追求与政治后果之间的关系。但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首要是维持国家利益而不是普遍利益,制度强弱与否依赖于国家的打算。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利益的驱使不仅影响国家的行为,还在于他们所创立的制度形式及制度成员的选择上,因而,制度不可能对国家行为有任何独立影响。这关键性地涉及制度的成员内生性(membership endogeneity)及设计内生性(design endogeneity)。[11](P66—83)建构主义认为权力对国际制度的影响最小,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主要源于建构主义反物质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研究思路。
作为基本概念的有效性需要与两组不同层次的概念区分开来。其一是同属于一个层次的有效性与效果(effect)的区分。效果类似于公共政策领域的结果(outcome),即遵约导致行为体行为的变化,其效果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其二是不同属于一个层次的有效性与效率(efficiency)之间的区分。效率是有效性衡量的一个标准,即衡量在多大程度上问题获得了解决或花费最少的资源改变其行为。比如制度能够经受个人和集体行为经历时空变换而发生显著变化的考验,该制度就有效,但并不能因此得出该制度效率高的结论。效率作为有效性的一个衡量标准,使机会成本成为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但效率在动态变化情况中很难执行。其原因主要在于效率忽视了分配问题,而这恰恰是有效性的重要尺度。[10](P161)此外,绩效(performance)这一概念也经常出现在研究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讨论中。一般而言,绩效的基本含义是功效、功绩的意思,这个词是与成本紧密联系的。在全球治理的语境下,绩效主要是指该治理体制所取得的成果与其建立和运作的成本之比率。[12](P56)概念的区分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础,考虑到翻译和使用这几个专业术语时的随意和混乱,认真区分相关概念很有必要。
作为履行特定功能或解决特定问题的制度有效性,有别于另外两个概念:强度(strength)、稳固性(robustness)。强度是指规定国家行为的规则的严厉程度。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指出,应该从遵约的程度,即对机制规定的遵守程度来衡量机制的强度,[13](P496)但是遵守与严厉的机制之间并不矛盾。总体而言,强度是指对个体成员合法选择的限制程度。机制强度区别于有效性最重要之处在于关注机制自身的属性,而不是机制所产生的结果。强度是有效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有效性的充分条件。衡量机制的有效性要求机制建立之后必须持续一段时间,稳固性是有效性的客观要求。稳固性是指对付挑战及生存压力的功能性完好能力。稳固性是从范围较窄的角度规定一个机制承受外部动荡或外部挑战的能力,从外部影响机制有效性这一角度来考虑的。稳固性由遵约的持续变化程度或规范机制的可能变化来衡量。[14](P193—195)稳固性不能解释为抵制变化的能力,相反,制度的生存能力依赖于其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无论从概念还是经验角度看,稳固性与适应性之间都非常复杂,有效性是稳固性的重要来源,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可以说,有效性需要在弹力程度及适应性之间形成最优平衡。强度和稳固性的有益启示在于,当前大部分研究关注于制度有效性,并不代表可以忽视这两个概念在研究国际制度方面的启发意义。
二、制度有效性的分类划分
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有关制度有效性的多种划分一样,国际关系领域的制度有效性划分也有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从便于理解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分为三种①:一是作为目标获得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as goal attainment),二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as problem solving),三是作为集体最优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as collective optima)。[6](P88)“目标获取”方法是通过对应制度正式目标来评估制度的进步。托马斯·贝尔瑙尔(Thomas Bernauer)采取目标获得评估制度效果,在评估制度有效性时,使其余情况不变(ceteris paribus),考察目标获得的变化程度。[15](P351—377)“问题解决”方法是通过解决导致制度形成的问题来评估制度的进步。与“目标获取”方法比较而言,问题解决的有效性与制度的价值标准紧密相连,涉及范围更广,难度更大。甚至可以说,后者更关注制度在效率、平等、持久性或者制度弹性方面的发展。“集体最优”方法与“目标获取”方法紧密相关,它是指通过界定“理想的”或“完美的”问题解决方法来评估进步。对于这种有效性的划分,可以很好地考察制度变迁。国际制度个案的研究者很熟悉下列这个事例:从排放标准到设备标准的转变导致了船舶污染控制机制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不过,制度变迁对制度有效性的最关键之处就是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因而,通过持续观察解决问题的程度,对于制度有效性研究非常重要。
由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概念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奥兰·扬发展了一个较系统的区分解释:作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as problem solving);作为目标实现程度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 as goal attainment);行为有效性(behavioral effectiveness);过程有效性(process effectiveness);构成性有效性(constitutive effectiveness);可评估有效性(evaluative effectiveness)。[16](P140—162)阿里德·翁德达尔(Arild Underdal)则认为后面两个没有必要做出明确的划分,这两个划分涉及效率、稳定性及平等等差别很大的概念,特别是构成性有效性与问题解决的有效性存在重复。[17](P14)有效性概念的多维视角昭示了制度有效性研究缺少普遍认可及精确的核心概念,因而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从便于理解制度互动的角度看,奥莱沃·斯拉莫·斯托克(Olav Schram Stokke)把机制有效性分为三种:(1)机制通过影响功利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来影响问题解决的行为。(2)机制可以影响问题领域内何为正确和恰当行为的认识。(3)机制可以影响特定行为目标和手段的“认知显著性”。在此基础上,斯托克区分了三类机制互动,即功利性互动(utilitarian interplay)、规范性互动(normative interplay)和观念性互动(ideational interplay),并试图探索决定这种互动是“支持性的”还是“阻碍性的”条件②。
此外,从便于衡量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角度考虑,可以将国际制度有效性分为内部效果、外部效果(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s);直接效果、间接效果(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有益效果、无益效果(helpful and unhelpful effects。[9](P10—16)通过这三组定义,形成了制度效果的区域,从而方便理解制度的有效性。当然这种有效性划分方式还有不少,比如可以根据约束力的形式,把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
不过,这类划分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考虑到国际制度造成越来越广泛的结果,所以应该更加关注交叉机制影响(cross-regime effect)、国内结果(domestic consequences)、系统结果(system consequences)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影响(impacts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18](P3—11)就交叉机制影响而言,有关环境保护的机制有可能对国际贸易方面产生持续影响;就国内结果而言,国际制度常常是发生在成员国国内事务特别是政治进程的结果方面;系统影响表现国际机制的运行可否导致人类获益的结果;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涉及两个对立方面,从保守的意义上讲,这类影响增强了目前盛行的安排,另一方面,却导致了社会进程的持续改变。
三、制度有效性的评估标准
评估一个制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一些成功的标准来比较可观察到或可预测到的绩效。阿里德·翁德达尔认为任何试图发展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的方法论框架,都必须认真审慎地思考如下三个问题:构成评估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目标的标准是什么?通过把目标和标准进行比较,如何实施操作,或者说为了把有效性的分数值归因于特定的目标,应该实施哪些操作进行衡量?[7](P228—229)概而言之,即目标(the object)、标准(the standard)与操作程序(operational procedures)。托马斯·贝尔瑙尔指出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概念引发了下列三个问题:制度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及哪些结果应该成为分析的焦点?怎样依据制度成功或者失败评估这些结果?需要哪些测量操作去评估一个制度的有效性?[15](P335)罗纳德·米切尔也指出,制度有效性问题强调了分析制度因果关系时容易忽视的两点:评估的尺度及如何着手评估。[6](P79)
就评估的目标而言,需要区分三类不同的目标。一类是指那些属于制度自身的效果与那些属于制度形成和运行进程的效果,这样的区分与有效性的最终分值以及最终的政策制定都密切相关。关注制度本身产生的效果好处显而易见,概念上清晰明了,具有方法论上的吸引力,且避免了进程效果(process-generated effects)上的难以捉摸。第二类分析的目标是单个机制与复杂机制的联系体,准确地说,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更多地体现了后者,即有效性是由嵌入其中的制度文本的放大化。[17](P33)国际社会起初的地区性机制效果应该被理解为多重复杂机制运行的结果,在评估目标时,需要认识到特定机制的效果常常是相互作用的结果。由于机制产生了一系列广泛的结果,需要根据这些链条的不同点来衡量有效性,这就涉及第三类区分,即对人自身行为的影响以及由这些行为所引起的问题的效果。由于人自身行为的改变是问题解决的必要条件,大部分评估的目标便集中于行为的改变。当将目标转向一系列结果时,由于专门知识的缺陷、宏观层面把握的困难以及持续时间关注的受限,导致了目前的评估更多地局限于直接目标,而不是制度有效性的最终目的。
评估标准的作用在于获得有效性的分值。奥兰·扬认为有效制度具有的标准为:第一,在合作方有意图的指引下,改变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行为;第二,解决它们被设定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第三,以一种有效与平等的方式进行③。阿里德·翁德达尔则指出评估的标准应该涉及两个方面:应该界定对照实际绩效的参考点(the point of reference)或运行轨迹;提供一个跨问题领域的通常评估标准(metric of evaluation)或衡量单元(unit of measurements)。参考点包括事务的假设状态(the hypothetical state of affairs)及构成“最优”方案的成效。事务的假设状态与集体最优之间并不完全独立,不过后者具有更高的评估标准;而衡量单元的意义在于需要明确对衡量标准的选择。此外,不同衡量标准所赋予的制度分值不能互换使用。[7](P230—234)当前有效性研究的关注点大部分集中于改善非合作结果上,主要是集体最优在方法论上面临着挑战,即评估构成最优方案的问题的改善以及最优状况与实际取得的成效间的距离。[17](P35—37)在这方面,奥斯陆—波茨坦方案进行了初步尝试。 评估标准涉及衡量尺度(a metric of measurement),而衡量尺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最初的衡量标准发端于定序计量(ordinal level measurement):即问题解决角度来考虑制度的成功或失败。爱德华·迈尔斯(Edward L.Miles)将定序计量划分为三种:成功、失败以及涉及个案的居中分类。[7](P235)早期的划分标准非常粗浅,也很直接。20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研究方法不再局限于制度何时有影响,其影响如何发生,而是致力于制度有效性的识别与衡量,论述制度安排与个体、集体行为之间的联系。有的西方学者以普通国家(average state)的行为作为参照物,与其他成员国行为作比较,以期得出其变化趋势,这种考察机制的方法一目了然,也便于操作。不过由于隐藏了许多分析国家行为变化的潜在重要信息,无法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分析联系起来,导致层次不清和结果模糊。
衡量尺度的相关研究经过了二十年的不断积累,其内容越来越丰富,手段也愈加多样。衡量内容包括个案有效性、机制内部的有效性的变化以及跨问题领域机制有效性的变化三个方面。一般而言,单独个案有效性的衡量尺度有排放量、污染物集中程度及捕获程度等;机制内部有效性变化需要长期的跟踪;跨问题领域的有效性评估更复杂,缺少分析单元,常常依据惯例进行评估。在跨问题领域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是粗略地、定性地,而不是系统地、定量地研究。有关国际制度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有效性的一个重点,也是学术成果比较密集的领域。莉莉安娜·博策瓦(Liliana Botcheva)等人从国家行为趋同、趋异视角研究国际机制有效性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国际制度要使国家行为产生趋同,需要国家认识到它们的行为有持续的外部因素限制,同时对于国家行为设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国际制度使国家行为趋异也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没有意识到存在持续外部因素,或不存在持续外部因素限制;二是国家内部各部门和利益集团参与对外政策制定。基于这些结论,衡量成员国家行为的变化给予了有效性研究新的途径和启示。[19](P1—26)
衡量尺度从概念分析转向具体个案的困难在于有效性分值并不能直接观察取得,但可以从一些相关变量中推论出。鉴于有效性必然涉及日后相应的改善,那么没有制度时发生状态必须予以考虑。这一操作程序建立在反事实分析的基础之上,是回答制度存在的状态与制度缺乏时的假设状态是否、在什么方面以及多大程度上不同等问题。反事实分析包括两个步骤,即不存在机制的情况下,何种秩序存在;这种秩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考察秩序的决定因素可以通过简单的直线推断以及创建由决定系统的变量组成的模型两种方法。操作程序的关键在于关注制度如何影响行为,而不是制度产生的效果以及更广泛的结果。
近年来,在制度有效性方面,奥斯陆·波茨坦方案的持续努力引人关注。该方案评估国际机制有效性总体标准包括三个概念:没有机制、对应事实,实际绩效,集体最优状态。国际制度的实际绩效可以通过两个基准测试程序数值来考察:没有机制、对应事实与集体最优状态。最近几年,学者们对奥斯陆一波茨坦方案进行了扩展,具体表现在:衡量多重机制效果、绝对有效性概念这两个方面,以便回应来自诸方面的学理挑战,同时也是符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制度现实④。此外,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标准除了关注政治、经济、生态标准这些所谓问题解决的视角外,最近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过程管理,并作为问题解决视角的补充。
四、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国际关系现实中通常出现如下情况:同一制度在不同情况下的有效性往往不尽相同,不同制度在同一情况下的有效性也往往不尽相同。纷繁复杂的现实提醒研究者关注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缘此,国际关系学者对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论述较充分,这是制度有效性研究的必备方面。尽管如此,学术界在此方面并没有完全取得一致。
一般说来,对影响制度有效性因素的分析主要就是对制度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更容易发挥作用的考察。奥兰·扬将影响制度有效性的因素分为两类:制度安排自身的特性或属性这类内在的因素;特定制度安排运作于其中的广泛社会条件或其他环境条件这类外在的因素,即所谓的内生和外生变量。[8](P199—214)阿里德·翁德达尔认为,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包括:问题的状况(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集体能力(group capacity)以及机制特征(regime characteristics),三个因素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其形成的复杂三角关系决定了制度的有效性。[17](P39—41)
罗纳德·米切尔也指出了制度绩效的诸多方面影响:主导的引领者(Leading Indicators)(包括公共义务和政策输出及经济决定的变化、提高问题及潜在的解决方法的科学理解、创立或加强环境规范)、经济尺度(经济费用、经济利益、成本有效性、成本效用)以及其他非直接的尺度(包括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公平与费用分配、社会公正、文化影响)、善治与功能绩效等都会影响制度的有效性。[6](P93—105)
应该说,有关经济增长与发展、社会公正及善治等问题纳入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分析框架,既是对国际制度现实的深入思考,也为关注和评估制度的行为有效性留下了研究的广阔空间。比如,对社会公正的论述就是其中之一。安德鲁斯·哈森克勒夫(Andreas Hasenclever)等人指出国际制度中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在利益分配及负担承担方面,将原则和规范转化成可证实的义务,如果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有偏见、歧视的方式,则会造成正义缺失。[14](P199—204)他们认为“分配正义的机制在有效性方面具有很强的弹性”这一命题,被核不扩散机制所证伪,因而,制度有效性与分配正义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不公正与稳固性不背离,不公正同样不是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对于制度有效性中的善治,罗纳德·米切尔认为:“在国际层面以及许多国家的认识中,判断制度的有效性不仅越来越关注于其如何取得目标,还在于其参与程度、责任度、透明度、合法化及其他善治标准。”[6](P103)
此外,鲁斯·格兰特(Ruth Grant)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考察了国际制度的责任问题(accountability)。在全球民主缺乏的情况下,随着国际多边组织范围扩大及权威的扩散,如何区分参与(participation)及授权(delegation),避免国际层面的非权威化或非法使用权力。[20](P29—43)他们提出通过提高责任的标准、制裁及信息,避免国际社会的权力滥用,为制度有效性研究提供了不少启发。休·沃德等人则从理性选择视角关注制度能力与有效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国际、国内权力分配及信息传递。因而,在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方面,一方面需要关注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值得思考⑤。
五、制度有效性研究的主要困境
制度有效性研究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不过,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理论及现实的挑战。有学者指出了有效性研究的三个障碍:缺乏可预测的一致、可信的数据;有效性因素与影响制度的其他独立因素并存;制度的自愿参与。[21](P86)此外,有效性的衡量标准争论颇多,早期的国际政治学家就曾指出,需要警惕滥用衡量标准。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很早就指出国际政治研究不能过于迷恋衡量。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制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与人文的争论,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的衡量标准在方法论上遇到了很大阻力。无论如何,赫德利·布尔的忠告对国际制度有效性的研究不无警示作用。[22](P366)
从一个广义的学术争论立场来看,制度有效性的争论涉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的理论核心。总体而言,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即使是很多新自由主义学者对国际制度的自我实施也持有保留态度。而如果涉及国内政治的话,主张民族国家应保留对国际制度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控制权的学者,对有效性更加怀疑。比如,作为国际环境制度领域研究的理性主义代表人物的阿里德·翁德达尔认为,国际制度有效性是问题邪恶(problem malignancy)与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setting)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强调问题邪恶的制度,如果制度自我实施能力低下,则不太可能有效,反之亦然。[23](P3—45)作为建构主义者的乔治·唐斯(George W.Downs)论述了自愿的国际制度是如何产生国际利益的。他认为这些协定能够通过合法化的进程、再定义角色及反思三种途径来重塑国家偏好。这种建构主义立场包含了合法性及角色再定义的效果,使“弱式”国际制度取得与国内政策的决策相一致,避免了制裁或其他的强迫性实施措施。[24](P630—652)而研究国内政治的学者对于由国际组织作为实施政策的工具提出了疑义。有学者认为,成功的国际制度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系统、社会价值及文化框架功能的体现,因而,国际制度的国际化水平越高,那么制度功能越有可能沦为口头上的宣言。[25](P57)
在认识论方面,国际制度起到了改变国家行为的因果性作用,但是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来源过于复杂。使有效性既复杂又具有挑战性的是制度仅仅是国际层面上集体性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发生互动的一组社会学驱动因素中的一个,这些驱动者在不同的个案中呈现不同的价值。[26](P124)认识论上的不一致要求能够发展一个可以把不同的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战略。
在方法论方面,建立可靠、一致的数据库对于有效性研究的归纳分析是必需的。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初步工作,还很难满足学术界的需求。目前,很多预测制度有效性的研究,缺乏可信的数据,存在预测失真的现象。此外,方法论方面的另一个困境是缺少一个通用的指数,使观察者能描绘出个体机制随着时间的变化程度,或者比较和对照不同机制的有效性水平。可以说,这一严重缺陷阻碍了有效性作为解释国家行为变化的因变量的作用,限制了形成一种衡量有效性的尺度,而这种衡量标准对于解释有效性水平随着时间变化或在不同机制间进行比较至关重要。
认识论导致了不同方法论战略,而方法论的差异又造成了对于研究战略及制度设计来说的因果复杂性。方法论方面的可能选择包括:因果机制的集中性、历时性跟踪,揭示模式变化的广泛的比较统计分析以及探索形式的基本逻辑的演绎、准实验技术。[17](P42)这些方法都建立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弥补。并且,这些方法可以很好地弥补当前国际制度有效性的主流方法(深入的个案研究及博弈理论)没有涉及的领域。但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完全解释现实政治中制度效果出现的不同情景。比如,在全球环境保护领域,为什么像南极条约体系、大湖区水质机制以及保护臭氧层机制广泛有效,而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的协议、国际热带雨林机制等则无效,另外像欧洲长程越界空气污染机制、莱茵河倾倒污染物的协议及有害废物的跨界运输等是否有效还存在争论。这一现实既展现了有效性研究的丰富画卷,又促使学术界迎接这种挑战。
六、制度有效性研究的未来趋势
有关有效性的研究趋势,包括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际制度的广泛结果。制度的结果类型包括两个方面:简单的有效性(simple effectiveness)与更广泛的结果(broader consequence)。大部分关注简单有效性的研究把目光集中于内在的、直接的以及积极的制度结果,但是需要注意到制度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因果代理者的作用。实际上,制度结果已经超越了自身领域的问题解决式的方式。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国际制度有效性与全球治理日益密切。有学者指出,国际制度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核心方面。当前,制度的影响已经越过专门问题的限制,对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便形成了在无政府、非中心社会环境下,专门问题领域对治理的需求。[27](P89—90)实际上,国际制度的发展已经影响甚至修正了国际社会的一些构成性规则。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治理的需求在稳步增加,国际制度构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支变革力量,扮演了国际社会治理供应者的角色。尽管不能把解决专门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作为适应国际治理需求的万应药,但它却构成了可预见未来的最佳选择。国际制度作为全球治理的来源,构成了治理的结构框架。因而,从国际制度作为权力治理的供应者的角度对有效性研究所做出的精辟论述,无疑对国际制度研究、全球治理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发展指出了一条研究途径。
当然,有效性研究还需不断的深入。关注国际制度的广泛结果,需要不断加强有关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数据库(the International Regimes Database,IRD)建设,使得相关研究团体的成员可以方便使用⑥。鉴于建构主义对有效性研究的挑战,需要更系统性地把制度的集体行动视角和社会实践视角结合起来,尤其需要关注建构主义所提倡的三个进程:合法化、角色定位及反思主义的评估方式。[24](P26)同时,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加关注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决定制度有效性方面发挥的作用。此外,通过借鉴法的有效性包括社会学、伦理学及法律教义学的维度来论述制度有效性,也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收稿日期]2010-08-30
注释:
① 广义上的制度效果(the effects of regime)可以分为制度的分配效果(the distributive effects),认知效果(the cognitive effects),进程效果(the process effects)及侧面效果(the side effects)。具体介绍参见:Oran R.Young,Inferences and Indices: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 Regime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1,No.1,February 2001,pp.113-114.
② Olav Schram Stokke,The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Putting Effectiveness Theory to Work,FNI Report 14,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Oslo,2001,pp.5—23.转引自孔凡伟:《制度互动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新领域》,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③ 有关有效性的标准问题可参见:Oran R.Young,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④ 有关奥斯陆—波茨坦方案的总体介绍参见:Detlef F.Sprinz and Carsten Helm,The Effec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Regimes:A Measurement Concept,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0,No.5,1999,pp.359-369; Carsten Helm and Detlef F.Sprinz,Mea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egim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5,No.5,2000,pp.630-632.有关奥斯陆—波茨坦方案的最新发展参见;Detlef F.Sprinz,Jon Hovi and Arild Underdal,Separating and Aggregating Regime Effects,Paper presented at the 45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Le Centre Sheraton,Montreal,Quebec,17-20 March,2004; Detlef F.Sprinz,Regime Effectiveness—The Next Wave of Research,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th Annual Convention,Hilton Chicago,CHICAGO,IL,USA,Feb.28,2007,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181165_index,html.
⑤ 有关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有效性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参见王明国:《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机制有效性的一种新的分析视角》,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6期;王明国:《权力、合法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有效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
⑥ 从案例研究到运用国际制度数据库的有关情况,请参见:Helmut Breitmeier,Oran R.Young and Michael Zürn,Analyzing 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 Regimes:From Case Study to Database,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该书认为,应该关注数据库的质量控制(quality control)、兼容性(compatibility)以及许可(a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