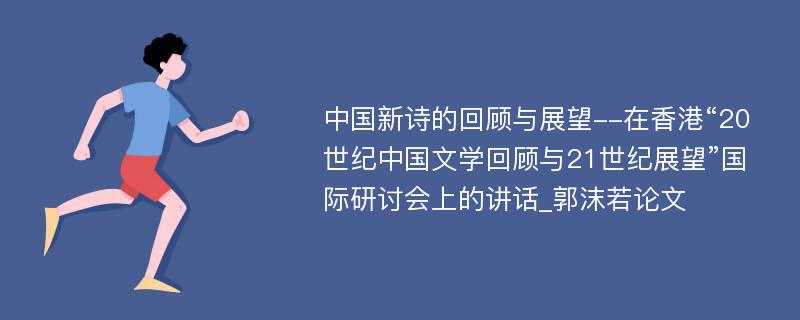
中国新诗的回顾与展望——在香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新诗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345(2007)05-0028-04
从1916年胡适和郭沫若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开始写新诗至今,中国新诗刚好有了90年的历史。
陆放翁有“尝试成功自古无”的诗句。胡适却充满信心地反过来说:“自古成功在尝试”。他一方面写文章鼓吹“诗体的大解放”,一方面自己动手写白话诗,并“愿大家都来尝试”。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期发表胡适《白话诗八首》。在胡适带动下,沈尹默、刘半农、康白清、刘大白、傅斯年、宗白华、俞平伯、罗家伦、田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陈衡哲、黄仲苏、周太玄等等纷纷开始尝试写作和发表新诗。郭沫若也把他在日本写的新诗于1919年夏秋寄回国内发表。1920年有三部诗集出版:《分类白话诗选》(选入68位作者的148首新诗)、《新诗集》(选诗103首)和胡适的《尝试集》。《尝试集》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个人诗歌专集,当时产生很大反响。1921年中国新诗的奠基工作——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同年还出版了康白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出版了汪静之的《蕙的风》、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田汉的《江户之春》和潘莫华、应修人、冯雪峰、汪静之的诗合集《湖畔》。紧接着,刘大白的《归梦》、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闻一多的《红烛》、陆自韦的《渡河》、王统照的《童心》、朱自清的《踪迹》、朱湘的《夏天》、梁宗岱的《晚祷》、俞平伯的《西还》、《忆》、刘半农的《扬鞭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冯至的《昨日之歌》等等,便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
90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短暂的一瞬,在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诗歌史上也只能算很短的一小段,但在伟大时代的感召下应运而生的中国新诗,在这短短的九十年间却取得了不应低估的重大成就。
回顾9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我想是否可以把它分为三个30年来研究。第一个30年是1916—1646;第二个30年是1947—1976;第三个30年是1977—2006。
第一个30年(1916—1946),新诗从草创、奠基到不断发展、普及深化,伴随着时代的风云、革命的深入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高涨与胜利,出现了诗人辈出、流派纷呈、各种诗体争奇斗艳、各种思潮交错递进的繁荣局面,逐步形成了新诗既学习西方的各种形式手法,又吸取祖国几千年古典诗歌精华,既有现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种创作方法、各种流派风格多元互补,努力创造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新诗的优良传统。早在草创、奠基的头十年(1916—1926),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指导下,新诗的创作就进入了十分广阔的艺术天地,出现了你追我赶、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兴旺景象。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清为代表的写实诗派,以郭沫若、邓均言、田汉、成仿吾为代表的浪漫诗派,以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派,以冯雪峰、潘莫华、应修人、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派,以徐志摩、朱湘、陈梦家为代表的新月派,各自以不同的特色和姿态登上诗坛。后来的二十年,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诗,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又很快形成流派。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诗人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斗争,上前线到延安,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后方的诗人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了抗战的怒吼,诗歌融入血与火的战斗,枪杆诗,街头诗,郎诵诗,大量出现。以臧克家、艾青、田间为代表的“密云期”诗人,以蒲风、王亚平、林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派诗人,以胡风、鲁黎、曾卓、绿原、牛汉、罗洛为代表的胡派诗人以及延安、晋察冀的诗人肖三、柯仲平、方冰、刘御、陈辉、蔡其矫、魏巍、严辰和在重庆、昆明、桂林的郭沫若、徐迟等诗人,都以火焰般的激情、高昂豪迈的调子,刚劲明朗的语言,唱出了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爱国主义的最强音,掀起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新高潮。以穆旦、袁可嘉、郑敏、杜运燮、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湜、唐祈为代表的九州派诗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歌唱时代风雷、倾吐民族心声,把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不断推向新的境界。
第二个30年(1947—1976),包括了三年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和10年文化大革命。新诗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坎坷曲折和狂风暴雨,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海峡两岸的新诗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各走各的路。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好诗不多,值得注意、影响较大的只有在国统区大量发表、揭露鞭挞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黑暗的袁水拍的讽刺诗《马凡陀山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中国大陆开始进入了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幸福的新时代。各少数民族的诗人、歌手们同汉族的诗人们一起用不同的语言和声音,由衷的唱出了激情的欢乐颂歌。虽然由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七月派”的诗人们被打成反革命,1957年又把艾青、公木、苏金伞、穆旦、吕剑、唐湜、唐祈、公刘、白桦、邵燕祥、高平、流沙河、孙静轩、胡昭、梁南、昌耀、林希、赵恺、高深等一大批新志诗人打成“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歌唱的权利,没有打入另册的诗人们也只能按统一的规范和要求创作,诗歌的天地越来越小,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文革”时期,华夏大地变成“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白茫茫一片,其中的惨痛教训应当全面总结、深刻记取,但我认为这30年中的前20年,新诗创作仍然是有成绩的,不能全盘否定。50年代初,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铁衣甫江、高深、胡昭、饶阶巴桑、汪承栋、张长等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写出了一批歌唱祖国、歌唱新生活的有民族特色的诗。来自解放区的老诗人艾青、严辰、公木、朱子奇、郭小川、贺敬之、李季、张志民、蔡其矫、魏巍、闻捷等等,同国统区的老诗人臧克家、徐迟、邹荻帆等等,与新出现的一大批青年诗人,为李瑛、邵燕祥、公刘、白桦、严阵、顾工、张永枚、雁翼、韩笑、傅仇、梁上泉、未央、高平等等,组成了歌唱祖国春天,歌唱民族新生、歌唱社会主义建设的诗歌大军,他们都曾写下了激情洋溢、真挚感人、各具风采的诗篇。其中,特别是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闻捷写新疆民族生活的抒情诗,李季写石油工人生活的叙事诗和李瑛的各种题材的不少抒情诗,既高扬时代精神,又有个人的艺术独创性,是很有代表性的有思想艺术力量的诗歌力作。
第三个30年(1977—2006),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新诗乘着思想解放的浩荡东风进入了最活跃、最繁富、最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历史新时期。被打成“右派”而沉默了二十多年的一大批诗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以及受牵连的诗人,因其诗风受西方现代派影响而受到排斥并一度从诗坛上消失的诗人,都像“出土文物”一样,重新出现,以充沛的激情,深沉的思考,新颖的构思,唱出了在他们的胸中压抑了多少年的激荡人心或引人深思的“归来的歌”。不算“归来派”但同样在“文革”中被迫沉默的各民族老中青三代诗人也以无比兴奋激动的心情欢唱祖国的“第二个春天”。知识青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诗人,为食指、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叶延浜、李小雨、周涛、杨牧、李松涛等等,更是以全新的姿态耀眼的光彩出现在中国诗坛。新诗潮,后新诗潮,新生代,后新生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各种旗号,多元多样,五花八门。西方在两三百年间先后出现过的“主义”和流派,中国诗坛在一、二十年间便全部演绎了一遍。新诗创作出现了“美丽和不美丽的混乱”。尽管作为对“文革”时期及其以前把诗变成“政治”的简单工具、变成非诗的标语口号的反动,有些青年诗人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放弃诗人的责任和使命,完全不要诗的崇高品格、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把诗当成随心所欲的儿戏,甚至鼓吹“下半身写作”,宣扬肮脏、丑恶和下流,把诗变成毫无意义、毫无美感甚至无聊无耻的另一种非诗的消费品。但总体上说,这30年毕竟使自由的缪斯全面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诗百花争艳、流派纷呈、多元互补的光荣传统,我们对中国新诗的未来应当充满信心。
台湾、香港、澳门对新诗也是在“五四”新诗传统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以纪弦、钟鼎文、覃子豪为代表的台湾老一辈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罗门、蓉子、向明、叶维廉、文晓村、非马、白荻、金築、李魁贤、管管等台湾第二代诗人,席慕容、罗青、萧萧、林焕彰、简政珍、白灵、岩上、台客、向阳、绿蒂、刘建化等等中青年诗人,和香港的犁青、蓝海文、张诗剑、晓帆、王一桃、林子、古松、澳门的傅天虹等等诗人,都按自己的方式,以不同的艺术创造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诗歌无疑是中国新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九十年来中国的新诗成绩显著,诗坛的上空群星灿烂。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包括了几代人、各民族、老中青的阵容可观的诗人队伍。在这几代诗人中,我认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大诗人:“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杰出诗人郭沫若、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的诗坛巨匠戴望舒和从30年代开始影响中国的新诗创作半个多世纪的现实主义诗坛泰斗艾青。
郭沫若(1892—1978)虽然为他自己所说“郭老不服老,诗多好的少”,晚年的创作与他作为大诗人的地位和水平很不相称,但在“五四”时期却正是他以“昂首天外”的雄大气魄和前无古人的创新智慧树起了新诗创作的第一块光芒四射的丰碑,为中国新诗的奠基、开拓与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诗集《女神》,以火山爆发般的滚烫激情,黄钟大吕般的洪亮声音,气吞宇宙的广阔胸怀和大胆奇丽的天才想象,“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歌颂时代的新潮,呼唤民族的觉醒和“凤凰”的再生。《女神》最充分、最强烈、最浪漫、最全面、最撼人心魄地体现了“五四”时期要冲决一切障碍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真正实现了时代所要求于新诗的“诗体大解放”和思想与感情的大解放,它以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艺术的相结合的高度成就,登上了“五四”时期中国新诗创作的最高峰。郭沫若不愧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伟大代表。
戴望舒(1905—1950),崛起于自由诗派领潮人郭沫若、格律诗派领潮人闻一多、象征诗派领潮人李金发之后,从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搁笔,他只出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四本薄薄的诗集,共存诗90余首,数量很少,却质量很高,有不少传世精品,为《雨巷》、《我底记忆》、《元旦祝福》等等。他的诗歌创作,总体上经历了从逃避现实到回归现实、从消极对待人生到积极参与人生、从个性的柔弱到人格的坚强、从诗风的萎糜到诗风的雄劲健朗的变化过程,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正直真诚的诗人对时代生活的真切感应,是时代风云在诗人心灵上的投影。在创作方法上,他以现代主义为主导,又广泛吸纳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技巧,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在艺术风格上,他是在新诗创作中最早自觉地追求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结合而卓有成就的诗人,与那些欧化倾向很明显突出的诗人相比,他的诗颇有民族风味、极富传统神韵;与那些单纯强调我国古典诗歌传统和民族民间通俗诗风的诗人相比,他的诗又更多现代派的风貌。他后期那些抒发自己炽热的爱国激情和深刻的时代感悟的诗篇,并没有出现一般常见的“思想进步带来艺术滑坡”的现象,而是仍然保持着他构思独特、语言精美、手法多样、不断创新的艺术追求,大都达到了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在那往往以愤怒狂暴的呼号代替精心制作的艺术的动荡年代,戴望舒的诗是为此瑰丽多彩、永不凋谢的奇葩。我认为,称他为中国20世纪现代主义新诗的巨匠是并不为过的。
艾青(1910—1996)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是创作时间最长、艺术成就最大、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我们时代伟大而独特的诗人”。他早年赴法国学画,回国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在狱中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抗战爆发以后,他“满怀热情从中国东部到中部,从中部到北部,从北部到南部,从南部到西北部——延安”,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目睹了祖国人民的苦难和抗争,写下了《我爱这土地》、《吹号者》、《太阳的对话》、《向太阳》、《火把》、《黎明的通知》等一系列深刻感人的不朽诗篇,树起了他自己的也是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座现实主义高峰。50年代上半叶,他还写了《礁石》、《写在彩色纸条上的诗》等诗歌精品。蒙冤22年复出之后,他又在古稀之年,奇迹般的焕发青春写出了《鱼化石》、《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充满青春活力、令人心灵震撼、独放异彩、光芒四射的杰出诗篇,登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又一座艺术高峰。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在“五四”时期,戴望舒的杰出创造也只限于第一个30年,他45岁就过早地去世了。只有艾青不懈追求、不断创新、光彩照人的艺术青春跨越了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三个30年。他86岁的生活道路和60多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监狱、战争和22年右派的严峻考验,对土地、人民、祖国、时代和宇宙人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深刻体验、独到感悟和独特思考,才通过自己出众的艺术才华和卓越的诗歌创作,为此充分强烈、为此深沉有力、为此富于个性而又精彩绝妙地表达出时代的感情和人民的心声。在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上,他吸纳各种创作方法,融合多种艺术流派,既继承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广泛吸收外国诗歌的手法技巧,既坚持“五四”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新诗的审美规范,不断探索前进、开拓创新。他在诗歌创作又和诗歌美学理论建设方面出类拔萃的巨大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港澳的几代诗人,在中国诗坛上有口皆碑,而且在国际诗歌界也具有广泛影响。早在1954年,艾青才44岁的时候,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聶鲁达就把艾青称为“中国诗坛泰斗”。美国文学评论家罗伯特·C·费兰德,把艾青、希克梅特、聶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日本学者在认真研究了艾青的诗和诗论之后说:艾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外国大诗人和评论家们的评价应当说是公允的。
回顾过去九十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包括对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这三位大诗人的简要概括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有这样三条带规律性的重要经验:
第一,新诗是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必须、必然要这样那样、或曲或直、或强或弱地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表达出人民的情绪呼声。诗人是他的时代、他的祖国和人民的敏感的神经、动听的琴弦和多情的歌手。只有与时代共脉搏、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心连心的真正诗人,才可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就。
第二,无论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也无论是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或别的什么流派,都不是彼此隔绝、互不联系的,而是多元互补、彼此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诗人必须善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既扎根本土,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努力学习外国一切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既坚持走自己的路,运用自己得心应手的创作方法,又认真学习别的“主义”和流派的手法技巧,镕铸古今、中西结合、提高自己、为我所用。
第三,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要不断开拓创新。创新是诗的生命。模仿别人,保守僵化、雷同重复绝不是诗。但创新是为了不断地满足时代和人民日益增长、发展变化的多方面审美需要,是为了诗歌艺术的真正繁荣,而不是使诗失去读者、失去人民的喜爱、失去艺术生命力。无论怎么革新创造、变化发展,诗必须是诗。诗人要有自由心态、开拓精神、探索勇气和创新智慧,要在题材领域,思想境界上不断地开拓、在艺术手法、语言运用、风格技巧等等方面也要不断地出新、出奇、出美,但不能把种种肆无忌惮、随意涂鸦、信口胡说当成“诗”。诗是使人心生敬畏、让人变得聪明、美好、圣洁和崇高的艺术品,是最精彩、最精粹、最精美的文学,是文学中的文学,它从内容到形式都自己的规律和审美标准,毫无诗意、毫无韵味、毫无美感可言的文学垃圾绝不是诗。“五四”以来经过时间考验,为读者喜爱和传颂的好诗,无一例外地都是真、善、美的结晶。
温故是为了知新,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经过九十年风风雨雨中的开拓前进、不断探索、大胆创造,中国新诗已走出了一条与时代风云、祖国命运、人民愿望血肉相连的广阔的发展道路。新诗的形式风格、语言艺术、诗体建设方面,两岸三地各民族的几代诗人都作了许多有益的试验和成功的创造,取得了多方面的丰富经验,为中国现代诗建设在新世纪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开拓创新,中国新诗在新世纪走向更大的繁荣是大有希望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诗界革命”时是“西学东渐”,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要“西化”。新诗的产生,“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
现在不同了。1988年1月发表的《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宣言》这样宣告:“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2004年12月23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东学西渐与“东化”》的文章,强调我们“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
中国新诗作为东方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继续不断地向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学习的同时,努力“吸收孔子的智慧”,以自己独特的创造参与到“东学西渐”和“东化”的文化交流中去,我想一定可以在未来世界诗歌的大花园里大放光彩、创造辉煌!
标签:郭沫若论文; 诗歌论文; 艾青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女神论文; 戴望舒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