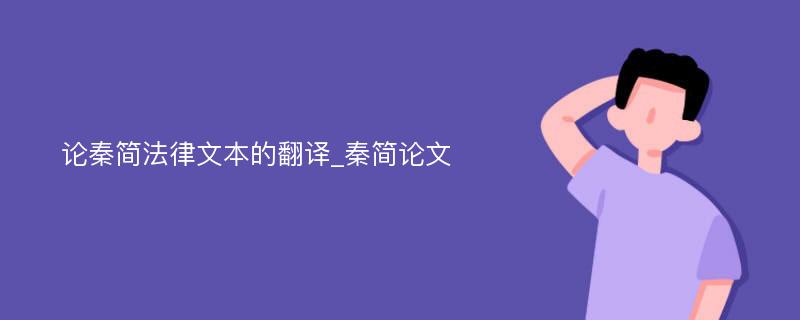
秦简《秦律杂抄》译文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律论文,译文论文,秦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下文凡引均只注页码)出土后,整理小组的注释方便了读者。笔者谨就《秦律杂抄》的一些译文提出商榷,以就教于方家。
一
简文有: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游士律。(第80页)
竹简整理小组注释:
游士,专门从事游说的人。《商君书·农战》:“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算地》:“故事诗书游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都主张对游士加以严厉限制。在,居留。
关于“游土”概念,目前学界意见未尽一致。不过笔者倾向于竹简整理小组的理解(有关“游士”概念的辨析,笔者将另撰文专论)。《汉纪》荀悦之说,或可为此处的注释作补充,其曰: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页)。
竹简整理小组注释:
责,诛责,一种惩罚。
将“责”理解成“诛责”、“一种惩罚”不确。“诛”为“诛杀”、“诛除”之意,惩罚程度最为深重;“责”有“责罚”、“追究”之义,并非指某一种具体的惩罚,其惩罚程度低于诛杀可知。两者并列对举,则明为对惩罚的泛指。如《尉缭子·原官第十》:
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
文中“赏”和“赉”并列对举,意为奖赏;“诛”和“责”并列对举,意为惩罚。《后汉书·钟离意传》:
朝廷莫不悚傈,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其中的“诛责”,也是对惩罚的一种泛指。
就“责”在睡虎地秦简中的使用来看,将本条简文中的“责”理解成“诛责”也并不是很稳当。“责”在睡虎地秦简中的使用,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为“债”的假借,如《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有责(债)于公及赀、赎者居它县,辄移居县责之。公有责(债)百姓未赏(偿),亦移其县,县赏(偿)。(第38页)
一类为“责令赔偿”、“责令补偿”之意,如《秦律十八种·厩苑律》:
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第 23页)
又如《效律》:
甲旅札赢其籍及不备者,入其赢旅衣札,而责其不备旅衣札。(第73页)
一类为“积”的假借,如《日书甲种》:
除日……利市责(积)、彻□□□除地、饮乐。(第183页)
一类为“责罚”、“追究”义,如《日书甲种》:
危日,可以责挚(执)攻撃(击)。(第183页)
很显然,第四类“责”的含义适合本简文义。竹简整理小组在上引《日书甲种》中将“责”解释成“处罚”,意近。竹简整理小组注释:
故秦人,即《商君书·徕民》的“故秦民”,指秦国本有的居民,与原属六国的“新民”对称。出,出境。
《商君书·境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削籍即自簿籍上除名,使该人脱离秦政府的控制。
从条文中“故秦人”的法律用语,我们可以推断该条“游士律”应当制定颁布于秦国完成统一前。理解这一点将有利于我们对整条简文的解读。
竹简整理小组认为,“削籍即自簿籍上除名,使该人脱离秦政府的控制”,似可商榷。因为就削籍来说,《商君书》“生者著,死者削”之语指的乃是最为普通的情况,而在其他情境中,削籍则并非一定是使某人摆脱秦政府的控制,它也可以是让某人从一类簿籍中除名而转到另一类簿籍中。因为就秦汉文献以及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秦不但有普通的民户籍,还有高爵者籍和刑徒籍(有关秦的户籍分类,可参考张金光先生《秦制研究》第十二章第四节的相关内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如《法律答问》有:
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第129页)
此明确规定高爵者大夫和普通的士伍不可同户籍。《秦律十八种·仓律》有:
隶臣欲以人丁粼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妾欲以丁粼者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敃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第35页)
此明确规定隶臣妾被赎,其原为边县的,户籍必须迁返边县。这说明,刑徒在服刑期间,有专门的刑徒籍对刑徒进行登记。因此,就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条简文来说,在未掺入其他的因素之前,则可能有两种解释。即:要么从户籍上除名,以脱离秦政府的控制;要么从一种户籍上除名,而转到另一种户籍上,但照样在秦政府的控制之下。
对整条简文应该如何解释?竹简整理小组这样翻译:
游士居留而无凭证,所在的县罚一甲;居留满一年者,应加诛责。有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罚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这就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所在的县罚一甲”是罚县还是罚游士?上述解释给人的感觉是罚县。但罚县并没有理由,因为游士有无符传,靠的是县的检查和勾稽,而不大可能是县的上级机构。倘若游士刚一入境即被县发现,则罚县更是让人无法接受。另外,简文强调“居县”,固然可以理解成是对施罚对象的强调,但亦可能是对施罚主体的强调。因为游士无符,如果由其户籍所在县来实施惩罚,就会大大增加秦政府的行政运作成本。由此,我认为,“居县赀一甲”或可解释为“所在的县罚游士一甲”。循此路径,则其后之“卒岁,责之”也是县对游士实施的惩罚。
第二,“削籍”是和“故秦人出”构成并列关系,还是承接关系?竹简整理小组认为是并列关系,其理由建立在将“有为”解释成“有帮助”的基础上。实际上,“有为”的“有”放在句首,也可以表示一种存在,即有某种情况出现。从逻辑上就一般情况来说,游士凭借自己的势力和能量“帮助秦人出境”和“帮助除去名籍”都有可能,但如此一来,本条简文不应该归入“游士律”不说,最大的问题在于简文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思维脉络不合。因为“故秦人出”也有合法与非法之别,而合法的出入根本就不需要游士的帮助。由此我认为,此处的“有为故秦人出”,乃是承接前文“游士在,无符”而来,针对的乃是无符的游士。其后之“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乃是对这种原为秦人的无符游士出境的惩罚。出境,在此不必一定理解成是出秦国现在的国境,因为本条简文颁布时正处于秦统一过程中,因此“出”也可以理解为出原秦国的国境。有学者在引述本条简文时认为削籍是管理者所为,如张金光先生,并进而认为这种削籍的行为是非法的,造成了户口脱漏于国版,是严重犯罪,故论处甚严重,则是忽视了简文本身所处的语境。
综上,整条简文可以试译如下:
游士居留而无凭证,所在的县对其罚之一甲;对居留满一年者,应加责罚。游士原为秦人(而无符)出境的,要从原户籍中除名,上造以上罚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二
简文有:
不当禀军中而禀者,皆赀二甲,法(废);非吏殹(也),戍二岁;徒食、敦(屯)长、仆射弗告,赀戍一岁;令、尉、士吏弗得,赀一甲。·军人买(卖)禀禀所及过县,赀戍二岁;同车食、敦(屯)长、仆射弗告,戍一岁;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赀一甲;邦司空一盾。(第82页)
又有:
徒卒不上宿,署君子、敦(屯)长、仆射不告,赀各一盾。宿者已上守除,擅下,人赀二甲。(第83页)
竹简整理小组注释:
徒,意为众,徒食指一起领食军粮的军人。屯长,队长,《史记·陈涉世家》:“发闾左謫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汉书·陈胜传》注:“人所聚曰屯,为其长帅也。”仆射,一种军官,据简文次序,其地位在屯长之下。《孙子·作战》曹操注:“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可参考。
同车食,指同属一车一起领食军粮的军人。古时每辆战车除车上战士外,还有附属的徒兵。
竹简整理小组认为军中“仆射”地位在“屯长”之下,或可商榷。理由有二:
第一,据简文仆射和屯长的排位,则仆射地位恰在屯长之上,而非其下。上引两条简文,共有三处出现屯长和仆射,分别为:徒食、敦(屯)长、仆射;同车食、敦 (屯)长、仆射;署君子、敦(屯)长、仆射。徒食、同车食和署君子地位最低,相信无疑义。简牍和文献有关古人职位的排列,均遵循着从低到高或从高到低的顺序,而不会出现高—低高或低—高—低的情况。如此则此三处的排列均是由低到高,仆射地位应在屯长之上。
第二,《商君书·境内》曰:
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严万里校《商君书》,诸子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4页)。
“五人一屯长”,类似“五家为伍”,则屯长是军队中最下级的军吏。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屯”字,将屯长解释为最下级的军吏也较合理:
芚即屯也。《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一,地也。尾曲。”此屯之本义也。自后通用为盈满蕃聚之义,而本义转微,故更造从草之“芚”字当之,犹出之本义,象草木益滋上出达。及后习用以为入之反,而草木滋上之义晦,乃更造从草之茁字当之。茁即出也(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7页)。
“屯”“象草木之初生”,则将屯长解释为军队中最初级的官吏,其地位最低,亦合情理。秦末陈胜、吴广所任屯长亦当与秦简中所看到的屯长具有相同的性质。因为陈胜、吴广两人皆为屯长,而假如其时九百人为一屯的话,则理应只有一个屯长才合理。
三
简文有:
战死事不出,论其后。有(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第88页)
竹简整理小组注释:
出当读为屈。除,《考工记·玉人》:“以除慝。”注:“除慝,诛恶逆也。”据此,除有惩办的意义。
整条简文翻译:
在战争中死事不屈,应将爵授予其子。如后来察觉该人未死,应褫夺其子的爵位,并惩治其同伍的人;那个未死的人回来,作为隶臣。
将“出”解释成“屈”,稍显牵强。我认为,“出”用的是其最普遍的意义,释为“出现”为佳。后文“有(又)后察不死”,说的正是与“不出”相反的情况。
将“除”理解为“惩办”也值得商榷,理由有二:
第一,《考工记》注“除”,是“诛除”之意,竹简整理小组将之引申为“惩办”,似有放大其义之嫌。古籍多见“诛”、“除”连用者,亦可说明“除”往往为“诛”之义。
第二,战争中死事之人,即使未死,也不一定会回到他原籍所在地,而有可能潜逃,故此而惩办其家乡毫不知情的同伍之人,似不合理。本条简文后半部分就谈到“不死者归”如何处理的问题,正可以说明不死者存在不归的可能。所以“除伍人”不应理解为“惩办”之意,而应理解为“免为伍人”,是针对不死者后人而言的。“除”之有“免”的含义,见之于《墨子》:
敌人卒而至,严令吏命,无敢讙嚣。三最并行,相视。坐泣流涕,若视。举手相探、相指、相呼、相麾、相踵、相投、相击、相靡,以身及衣,讼驳言语。及非令也,而视敌动移者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伍人逾城归敌,伍人不得,斩。与伯归敌,队吏斩。与吏归敌,队将斩。归敌者,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先觉之除。当术,需敌,离地,斩。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50至351页)。
睡虎地秦简中多见“除”释为“免”者,如《效律》
同官而各有主殹(也),各坐其所主。官啬夫免,县令令人效其官,官啬夫坐效以赀,大啬夫及丞除。县令免,新啬夫自效殴(也),故啬夫及丞皆不得除。(第72页)
器职(识)耳不当籍者,大者赀官啬夫一盾,小者除。 (第74页)
两处“除”,竹简整理小组均释成“免罪”,则“除”有“免”义可知。
我们注意到,简文实际上是分成两个步骤来讨论对不死者的惩罚的。首先是对其已受爵后人的惩罚,然后才是对不死者的惩罚,中间似不应掺杂其他人在内。另外,通读睡虎地秦简,我们发现,简文凡是谈到惩办违法之人,其惩办措施均较具体,而不会以“惩办”之意笼统言之。故而,“除伍人”之“除”释为“免”为佳。
综上,整条简文可以试译如下:
在战争中战死而未归者,应将其当受之爵授予其后人。如后来察觉该人未死,应褫夺其后人的爵位,免为士伍;那个未死的人回来,作为隶臣。
收稿日期 2005-09-15
标签:秦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