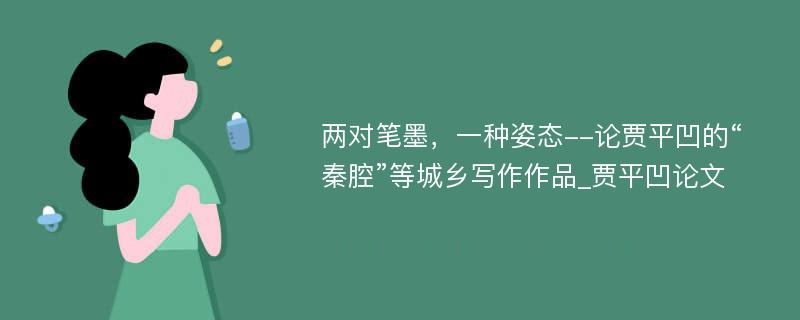
两副笔墨,一种姿态——论贾平凹城乡书写中的《秦腔》及其他作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腔论文,笔墨论文,城乡论文,姿态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贾平凹三易其稿的新作《秦腔》终于问世了,在单行本出版以前,《秦腔》已经在《收获》杂志2005年的1、2期上连载。这部耗尽作者一年零九个月时间的长篇小说,曾被传为贾平凹的封笔之作,而作家自己也声称《秦腔》之后长时间内可能不会再写长篇,因为费尽心血的《秦腔》已经让他心力交瘁。《秦腔》以秦地陕西的地方戏曲名为题,呈现的是秦地之乡村图景,发出的是秦人之声音。这部乡土题材的创作在贾平凹的城市乡村的两种书写中到底占有什么位置,具有什么价值,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一、“为了忘却的纪念”:给乡村立传树碑
如果说关注当下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是作家保持长久的旺盛创作力的一个秘诀的话,那么贾平凹无疑是一个典型。多年来,贾平凹始终面对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的种种变化,从1980年代的“商州系列”、《浮躁》到90年代的《高老庄》,直到新近的长篇《秦腔》,无一不是解读时代变动中乡土中国的生动读本。也就是在他熟悉的不离不弃的乡村生活的书写中,贾平凹一次又一次地贯注自己的思索与忧患,从而也始终保持了与当下现实相连的持久关注与耐心表达。
《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① 清风街上的男女老少、婚丧嫁娶、邻里纠纷等都如流水般穿织在作者细密的文字里。它展现的是当下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农村问题,以清风街上的大家族夏家为主,从最细微的角落开始,演绎了一部有关乡村的现实流年史。作者没有刻意去设计一个故事的野心,他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流水账式地清风街人细枝末节的生活,那些鸡毛蒜皮的人和事显得杂乱无章,阅读者很容易在某个地方就中断了阅读。但在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② 氛围中,如果放下架子耐心地慢读,顺着流畅的文字摸下去,并放弃那种寻找史诗与寓言的企图,你渐渐地就会被牵引进这个村镇里,与作者共同感受它亲切的起伏与呼吸。
夏家在清风街上是望族,天字辈的仁、义、礼、智四兄弟个个是能人。夏天仁已逝,儿子夏君亭是现任的村干部,雄心勃勃要繁荣清风街;夏天义曾是在清风街呼风唤雨的老主任,一生比珍惜自己生命还要珍惜土地,虽退下来了但说的话仍然掷地有声,威信不减当年;夏天礼在另外的乡做过财务,退休了一直偷偷地做贩银元的生意;夏天智是退休的小学老校长,头脑清晰明事理,痴迷秦腔,热衷于在马勺上画秦腔脸谱,他的儿子夏风读书上完大学,现在是省城的知名作家,一家因此风光。夏家的人事联系着清风街诸多的人事关系与利害冲突,最显在的矛盾来自新旧村干部对于清风街发展的不同策略。君亭一心想改变清风街多年来靠土地吃土地的局面,地少人多的贫困导致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这些人在城市里做着最辛苦最低廉的事情,因工伤而亡的人不在少数,而往往就是那一点用性命换来的微薄的抚恤金竟让农村的家人矛盾重重,争得脸红脖子粗。君亭计划在清风街的国道旁建农贸市场,希望能拉动清风街的经济,而建市场就涉及到占地。夏天义坚持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不仅不会让本来地就少的清风街再失去有限的耕地,而且自己还执意另外去淤地。君亭阴险告密击退了站在夏天义一边与自己意见相左的村干部秦安,又充分利用清风街的恶人三踅控制住建市场过程中的人心波动。一方面是夏天义本着一个老农民对土地的最朴素的珍爱与尊重,视土地为性命(他的下台也就是因为他心疼被糟蹋的土地而组织农民阻挠修建国道),一方面是夏君亭借着大政策的支持,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效益。很显然,作者在夏天义的身上投注了很多感情,他那种孤胆英雄式的淤地壮举无疑首先是打动了作者的,那种愚公移山式的顽固也是作者欲罢不能的、无法言明的。清风街的农民们对于办市场刚开始时认为“与其让一部分人富,不如要穷都穷”,而市场办起来后又纷纷抢摊位争收入。清风街人的意识里已经穷怕了,对于致富,他们有着热情的向往与艳羡,但是又掺杂着心有余悸的恐怕与谨慎,狭隘和狡猾使得他们缺乏长远眼界的同时又丝毫不错过日常的任何现实算计。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儿媳之间总在为赡养父母的问题纠葛不清,谁都认为自己吃了亏;梅花为给自己增加收入,给乘客卖票时不撕票,结果丈夫雷庆被运输公司整治。在这里,以伦理维系感情的宗法制传统社会形态已经松动,人际关系也不再只是讲信义、重礼节、追求亲密和谐,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仅仅只是长期以来对于乡村的某种想象。
就清风街而言,它正处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当下的农村,土地流失或者被城市化的规划所蚕食,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农民没有热情耕种庄稼,精神文化生活的空白被聚众赌博、或者是对于城市文化生活的粗制滥造的模仿等所占据,摊在农民头上的各种税费使农民无法承受,农民围攻政府集体抗税并借机闹事、发泄过剩精力的事件已经司空见惯。而城市化进程带来另外一个世界的新鲜,也带来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化过程中的现代观念、意识、现象都流进了清风街,影响着清风街的方方面面。传统的乡村农业文化已经解体,相应的思想意识观念也随之改变,渐趋衰落的传统文化就像秦腔的衰落一样,无法挽回。小说中人物对待秦腔的观念正反映了新旧观念的冲突。夏天智对于秦腔相当痴迷,没事总爱听一段,而清风街上几乎人人都会吼上几句秦腔。夏天智的儿媳妇白雪是县剧团的秦腔演员,美丽贤惠,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身在省城的夏风对于妻子的表现不屑一顾,他深知秦腔在现代社会生存的困难,极力鼓动白雪放弃秦腔表演,随他去省城另外谋职。现实情况也的确不乐观,吸引清风街上年轻人的更多是流行歌曲,而秦腔表演越来越受到冷遇。夏中星在任剧团团长时立志振兴秦腔,仅是为自己的政绩多加一块筹码而已,他高升后剧团更加不景气,演员纷纷另谋出路。和秦腔的衰败一样,清风街也在衰落,在颓败。就像作家张生戏称的在《废都》以后就盼望《废乡》的出现,而《秦腔》就是一部“废乡”。
把琐碎的日子写得有滋有味,是贾平凹的通常手法,也是他的过人之处。就是清风街上这些拉拉杂杂的人与事,他硬是把它讲述得生机有趣,场面写来也是从容沉稳。他声称要为故乡立传树碑,用以纪念那正在日日变样的故乡,于是他以清风街为自己故乡的影子,讲述了清风街细碎的生活流程也就折射了故乡的现实褶皱。然而,在这种带有告别意味的纪念式“树碑”中,作者其实已经很清醒地知道,这个清风街已经面目全非,他再也回不去了。用文字来做纪念,其实只能在心灵上给予自己一种慰藉,其实就是在做一种告别。如果说《高老庄》里子路返乡又离乡的情节也意味着对故乡的告别的话,但是他爱的两个女人都在高老庄,西夏对高老庄祖先的巨大兴趣使得她竟然坚持留在高老庄,如果把这看成并非作者一时兴起的情节设计(实际上西夏作为子路的妻子,在文中一直热衷于对高老庄人种退化问题的探究,高老庄神秘的白云湫、血性的蔡老黑、个性迥异的菊娃和苏红都是吸引她的原因),那么这依然暗示着子路终将回来。而《秦腔》里,可以看作作者化身的夏风,对于清风街的一切并没有留恋,并且极力想摆脱与清风街的联系,包括亲缘。如果说子路对高老庄还留有一丝牵扯的话,那么夏风对清风街的心理则是彻底的决裂。子路对已经离婚的菊娃仍然割舍不下,他回来给父亲办三周年的祭祀,他收集高老庄的土语俗语等等,都印证着子路与高老庄在血肉层面的联系。而夏风,在《秦腔》里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了,清风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没有他在场也能办得轰轰烈烈,不象子路在高老庄,几乎任何事情人们都要找子路讨主意,子路是大家心里承认得见过世面而又代表高老庄的人物。然而夏风不是,他在清风街的实际生活中几乎被清风街忘记了,大家只是把他当作清风街走出去的一个招牌,可是究竟他会在清风街起多大作用,清风街人是不指望的。事实上,夏风也不准备对清风街有多大发言权,他正一点一点地试图脱离清风街,对于清风街,他的心是冷的。清风街在走向颓败和荒凉,作为作者化身的夏风,他的心也在远离,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作者贾平凹心也凉了呢?就像夏风一样,贾平凹是不是也对这片他曾经如此灵魂萦绕的村庄抱定了失望与悲凉呢?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他已经放弃了或者说是丧失了任何做结论的企图,他只想做一个告别,一个告别时的总结,于是便才有了这给故乡立传树碑的《秦腔》,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二、从《废都》到《秦腔》:从“城的颓败”到“乡的颓败”
在《秦腔》里,故乡的一切都正在走向颓败,无论是当地的世风人情,还是传统文化和人的精神状态。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给乡村带来了生机,但是也扰乱了乡村固有的秩序,特别是固有的传统道德在当下乡村的衰微与沦丧,不能不让贾平凹这个在传统文化中浸淫成长的农村娃子生出无限的心酸与迷惘。乡村在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大都是灵魂的精神家园所在,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萧红笔下的呼兰河。贾平凹在踏上文坛之初也就是以他对乡村人情美、人性美的书写引起关注,而他笔下那些发自内心创作出来的美丽、温婉、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几乎都由衷地给了乡村的女性。对于后者,贾平凹一直都是坚持始终的,这或许与他的女性观有密切联系,但是前者,在他的作品中则有着明显的变化。80年代的商州系列等小说,乡村的美好是作者极力突出并着力渲染的,但慢慢地,这种美好不再是单纯的美好了,它开始带上杂质,或者说是带上某种变化以及作者对这种变化的思考,于是在乡村中开始出现道德的滑坡、传统文化的崩解、精神追求的丧失等现象。比如90年AI写作乡村的《高老庄》,写城中村的《土门》。当然不能说,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以及它对农村的经济影响是使乡村在精神层面变得衰退的缘由,只是为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发展经济,一方面又有精神的颓败与失落,这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乡村农民受传统的思想意识影响较城市人更深,那么当制度、器物、体例等层面发生改变时,乡村的文明、文化、精神层面的变化却迟步了,于是出现一种错位。当这种错位发生了,必然会给现实带来诸多矛盾与困扰,那么后一层面试图向前一层面极力靠拢则是大势所趋。但是,问题也就出在此,在靠拢的过程中,往往不是去接受一些新的观念,而是用旧的思想观念中那些貌似可以适应前一层面实则背道而驰的东西,比如专制思想,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性或者智性决策,而是传统思想中的独裁,是陈腐的皇权意识的变种;或者是用旧的思想观念去诱发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丑恶种子,比如说享乐、腐败,难道不也是传统封建社会中专制与皇权的派生物吗?用沉积在受到几千年封建思想影响的人意识中的那些负面因素去解释当下精神的颓败,难道不是更加合适吗?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是精神道德衰退的因由,倒是应该从精神道德本来的根源去找缘由似乎更加合理。因为“如果老的精神状态继续存在,现代市场就仍然是一个没有内容的形式,一个空壳,一种假象,一种导致另一类型虚假现代性或者也许是伪现代性的新现代化策略。”③
乡村衰败的涵义首先是指它在传统仁义道德层面的衰败,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颓败是必然的,而面对这种颓败的悲凉也是情理之中的。贾平凹声称《秦腔》的写作过程是“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④ 当故乡传统的文化形态开始消失,曾经熟悉和习惯的乡村开始变得陌生与复杂,面对已经面目全非的故乡,贾平凹明白这不再是记忆中的那一方精神家园,迷惘、心酸、心惊一齐涌上来,倒化成了一股对于灵魂如何安妥时的“惘惘的威胁”。当这些情绪平静下来,要把已经颓败乡村形诸笔端时,贾平凹感到了言说的困难,他唯恐无法把握,也唯恐化成文字了也就成为一种告别了。
说到写颓败,在贾平凹的创作生涯中,《废都》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当它在1993年问世时,是那样一针见血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普遍精神状态。那是人们感受到了却还没有想到一个确切的词语表达出来、或者是还只有隐约的感受而无法言明的一种精神状态。《废都》写了一个西部城市,面对城市,出生农村的贾平凹或许不是最权威的发言者,但是有着二十多年的居住时间的他,以曾经的乡村生活经验做底色,来写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感受和体验,却是最令人期待的。应该说贾平凹并没有让阅读者失望,有人从《废都》里面读出了名士风流和文人的颓唐,有人从中感受到了世纪末废墟式的悲凉,有人还体验到了作者的中年心境与中年写作,⑤ 而有人从那些大量的性描写中得到了感观的满足。而作者自己呢,在对庄之蝶沉迷欲望的显露描绘中,西京城始终弥漫着一股颓废、无聊与空虚的气息,或许这就是小说名字“废都”之“废”吧。然而,在贾平凹对这座废都的书写中,在庄之蝶与几位女性的性爱周旋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他掩藏不住的男性中心意识与旧式士人颓荡、陈腐的价值观念:《废都》以庄之蝶与昔日恋人的一场文字官司贯穿始终,其间呈现的文化界是一片乌烟瘴气,西京城里的四大名人沉浸在追名逐利的欲望场中,庄之蝶更是如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借与不同女性的性爱来排遣内心的空虚与无聊,而这些女性,无论是知书达理的妻子牛月清,精明的保姆柳月,还是风情万种的唐婉儿,无一例外纷纷都无条件地臣服于他并为他作出超常的牺牲。整个西京城陷落在一片精神的废墟中,活在其中的人们挣扎在欲望的沉沦中。西京城(其实就是西安)的“废”或许应该这样来看,一方面它来自这座曾经是十二个王朝之都的历史名城和文化古都在当代的败落而带来的“废都文化心态”,那就是“自卑性的自尊”、“无奈性的放达”和“尴尬性的焦虑”⑥;另一方面,它还应该是90年代整个社会心态的缩影,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以下事实,90年代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一体化思想局面的打破带来价值的多元,而整个社会突出对经济利益追逐的同时,精神诉求的消隐又带来社会心理的失衡与混乱,处于一个世纪末的人的心态大抵就象《废都》中所写的一样。因而,“废都”之“废”是属于贾平凹笔下的西安城的,也应该是世纪末中国的写照。
综上,《废都》的确是贾平凹对于社会、时代与一个城市对话的敏锐感受,但是,就人与城的关系而言,从《废都》中无法看到时代大变动中人与一个城市相遇时碰撞出来的火花以及人在这种相遇中的大悲欢。也就是说,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与废都,很大程度上只是作者以个人私我经验从事的城市书写,贾平凹或许试图以文人庄之蝶那种颓唐去表现“废都”之“废”,但实际上他却沉溺于其中并在沾沾自喜的欣赏与玩味中顾影自怜。看看他倾注在庄之蝶身上的那些符号,西京城四大名人之一、名作家、受政界领导赏识、有女人无怨无悔为他献身、走到哪里都受无限尊重……无一不是个人式的生存与精神喟叹,在庄之蝶那里,时代不过是为个人的伤口和伤口的舔拭提供了背景音乐,而庄之蝶所居住的城市也只不过为他营造了一个欲望沉迷时更公开的社交场合。贾平凹这个出生于乡村、在城市接受教育并留在城市的作家最终无法超越城市之“废”,无法认识到“废”也是城市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方面,无法上升到对“废”的哲学美学观照层面。贾平凹的城市书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双重人格纠葛中的男性面对城市欲望时的心理误置。之所以这么说,是在于他仅仅表述出了个人与城市欲望相遇时的颓唐式沉溺以及沉溺后的空虚,没有对欲望的社会历史价值以及其广阔的城市舞台背景的透析。他误置了人与城的关系,用城对人的感性俘获取代了人对城的理性穿透。他想写出对城市的整体把握,但却陷入了城市欲望的陷阱无力自拔,因为他开掘的是城市给予人生命内涵中情欲的外化式催生,却无力把握城市场内化为人之生命形式时人与城市的命运互动。小说结局处庄之蝶的逃离只能说明人对城市的失语,这种失语正是作家无法以社会历史眼光深入城市“文明之渊、罪恶之薮”的本质而来的心理大溃败。在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对城市是隔膜的,至少是不亲近的。那么贾平凹的城市想象与书写,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城市依赖却拒斥、不熟悉但想亲近的矛盾心理感受。
相比较而言,写城市底层小人物的《白夜》在城市日常生活层面显得更为亲近与平实,夜郎是城市闲散人物的典型,他成天无所事事,游荡、空虚、无聊,却又不知道如何改变这一切,城市是他最坏的但又是最好的庇护,他诅咒城市又不愿离开城市,他与城市之间互相耗损、互相折磨,他代表着城市中一股顽固的力量,低徊在城市空间但支撑着城市的精髓。
如果说在《废都》中,城市是精神废墟的话,那么在《白夜》中,城市指向生存的苦闷与尴尬;在《土门》中,城市在蚕食乡村的同时自身却混乱无序。这些城市都是颓败的,就像《废都》中周敏在城墙上吹出的埙声一样,它就是废都的基调,悲凉之极。
城市是颓败的城市,乡村如今也是颓败的乡村,从城市的颓败写到乡村的颓败,作者的精神阵地一点点地失守。在现代化进程鱼龙混杂的大潮中,这种失守防不胜防,也无处可防。从《废都》到《秦腔》,作者终于唱出了精神废墟上的苍凉悲曲,尽管带着几许不甘或者质疑,尽管残酷,但终究是现实的真实表达。
三、“在”而“不属于”:游走于城乡两极间的灵魂
行文至此,如果可以的话,我试图透过贾平凹写的关于城市与乡村的长篇小说,这样来探究他的心理。从乡村进入城市是他一直的奋斗历程,城市给了他事业的名利与声誉(就像《浮躁》中的金狗,《高老庄》里的子路,《废都》里的庄之蝶)或者是谋生的处所(就像《白夜》中的夜郎),但是他的传统文化根基始终与城市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依然以农民自居,他把孤独灵魂的安妥给予了生育他的乡村。城是颓败的城,欲望沉迷、名利追逐、空虚无聊、精神颓废……那么乡就通常是心灵的后花园、灵魂的安居处了。但是当贾平凹离乡又返乡后才发现,乡村呈现着一片萧索的荒凉,土地大量被征、劳动力流失、精神饥荒、道德沦丧——在真实的感受层面,乡也是颓败的,这便是《秦腔》里的清风街(其实早在《土门》里的仁厚村不仁厚的书写和《高老庄》里子路家乡人种退化的呈现中已见端倪)。《秦腔》的后记里,贾平凹以这样的一句话结尾:“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⑦ 在为故乡立传树碑的告别仪式里,贾平凹以乡的颓败暗示精神家园的丧失,在“身”的几十年离乡以后,“心”的离乡又成为无可挽回的命运。故乡的“气”散了,对灵魂的凝聚力也就消隐了,即使他想回去,但是来自城市的现代文明召唤也已经使他不再适应、或者说是不愿适应乡村的旧有生存习惯和方式了。从城的颓败到乡的颓败,灵魂的百转千回,个中滋味恐怕只有贾平凹自己才能体会了。那么可以说,无论城还是乡,面对这生存的二元空间,贾平凹都是游离的。他居住在城市,但是不属于城市;他曾经属于乡村,但是那个乡村已经消失了,只在记忆里给我们留下一个背影。面对城,还有乡,“在”而“不属于”或许就是贾平凹最恰如其分的心灵注解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大都是从乡村走向城市,面对城与乡,他们有太多的复杂感情。郁达夫那些真率的泛发着生命欲望与激情的文字,不能不说渗透着城市带给他的个性迸发与现代文明理念的印痕,他的情感审美方式与行进方式都是城市的,但是当贫困阻挠他的情欲在城市正常舒展时,他终究不忘将情感的归宿引向乡村,尽管只是一时的心灵抚慰。就像他的《还乡记》那样,带着对城市的抱怨甚至憎恶还乡,幻想田园的宁静与浪漫,他的《南迁》也是叙述一个在城市感情受挫而且疾病染身的男子到乡下修养身心,而他的后期作品《迟桂花》,浸淫在城市文明之久的“我”,在乡野女子的健康、质朴的美的洗礼下,灵魂竟然得到净化。再看沈从文,依赖城市谋生谋职以生存的他,精心经营着湘西世界,建筑着他内心那供奉着优美人性的希腊小庙,始终以乡野健康、优美的人性反衬都市萎缩的生命和虚伪的道德,以“乡下人”的姿态从事着生命自然形态的书写。在极尽都市人生的庸俗和生命的退化以后,乡村便是他期望中灵魂的净土,即使避免不了象《长河》中那些现代质素的侵入,《边城》式的湘西在他城乡对立互参的写作中始终是动情所在。而就萧红而言,她短暂的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穿梭无数的城市。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身在异乡写作《呼兰河传》,无限深情地叙说故乡的人与事。然而故乡不止是有她爱的祖父,以及记载她童年欢乐的花园,还有那永远混沌的人们,那生便生了,死便死了,惰性一天天耗损着生命的呼兰河人,面对故乡,萧红颠沛流离的灵魂依然得不到安妥。而鲁迅,站在知识者启蒙的高度,一次次对于中国古老乡村的愚昧和麻木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书写,《故乡》中他返乡又离乡,终于理性地超越故乡的依恋情怀,高蹈于无论是城还是乡的“在”而“不属于”的绝望与苍凉。
与这些作家不同的有一点,贾平凹似乎更关注于事实层面而非情绪层面的城乡表达,也就是说,他在写城市、乡村带给他的失望时,往往执着于那些具体的盘根错节的细节中的人与生活。他把生活写得如此之实,不是想象,不是虚构,不是写意,不是情绪的象征,也不是宏大叙事。但是他有着与这些作家一样的苦痛挣扎,他游走在城乡两极寻找归所,永远在路上。
这种游离对于贾平凹而言,有这样一个因素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他对于城和乡的双重隔膜。对城市的隔膜几乎来自他先天的不熟悉,由乡入城时产生的与城市精神的距离感已经悄然沉积在他的生命体验里了;而对乡的隔膜则首先是基于熟稔,熟稔以后就会对它的细微改变如此敏感,当它的改变超越了贾平凹所能承载的故乡记忆时,隔膜也就随之而来了。于是,从《废都》走到《秦腔》,贾平凹在达不到对城市进行理性穿透的同时,也丧失了、放弃了对乡村的发言。他只有以一种不介入的姿态,舞动城乡书写的两副笔墨仅仅只去呈现城与乡的现实褶皱,在那些细碎密实的字里行间体味书写的乐趣了。那么,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就是,在城乡二元生存空间里徘徊的贾平凹,写尽了城的颓废和乡的衰败并感受到双重的失望之后,他还能用什么继续他的写作呢?他继续写作的资源又在哪里呢?一切都在期待中。
注释:
① 《〈秦腔〉后记》,《收获》2005年第2期,第208页。
② 同上。
③ 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5页。
④ 同①。
⑤ 张新颖《重读〈废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文章声称“重读《废都》,最深的感受是,这是一部中年人写的书,写的是中年的心境和经验。”
⑥ 《〈废都〉创作问答》,《文学报》1993年8月5日第2版。
⑦ 同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