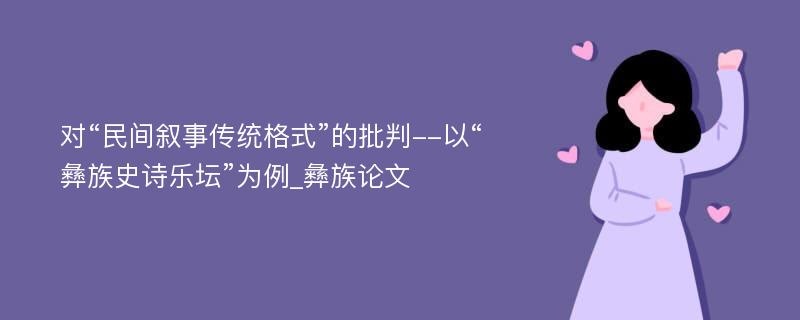
“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中)——以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文本迻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彝族论文,为例论文,史诗论文,文本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568(2004)01-0018-09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三、史诗《勒俄特依》及其“文本迻录”过程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文革”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阶段,也就是50年代后期,在“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民间文学工作方针指导下,各地民间文学机构相继成立,在民间文艺采风工作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仅“民间史诗、叙事诗就有上百部”之多,云南、四川的彝族史诗搜集、整理正是在这样的“运动”中孕育的。从1957到1960的两、三年之间,除了撒尼彝族的叙事长诗《阿诗玛》之外,从调查、搜集、翻译、整理到出版,后来被称为彝族“四大创世史诗”的作品均已面世,其中就包括诺苏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由巴胡母木(冯元蔚)、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共同整理的翻译本,收入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于196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文革”后的80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停滞已久的民间文艺事业开始迈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时,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中两部作品还在继续完善之中,《查姆》经郭思九、陶学良进一步整理、修订后,于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勒俄特依》的彝文本与汉文本也由冯元蔚进一步整理、翻译,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的确是凉山彝族文学的一件盛事。从彝文到汉文的翻译工作,既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也是一件意蕴深远的大事。至此,译本改写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彝学界一直仅将“勒俄”作为阐述彝族历史、社会等级、奴隶制度的“旁证”材料,并将作品的文学特质及其诗歌属性引入了民间文艺学的探讨,进而被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纳入到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之列(注:朱宜初、李子贤:《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第14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彝族文学史上给予了诺苏彝族这一古老的文学传承以应有的地位,同时也让广大的汉文读者了解到:在20世纪50年代惟一存在的“奴隶社会活化石”——大小凉山,除了“触目惊心的阶级压迫和暗无天日的奴隶主统治”之外,彝族人民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勒俄特依》汉译本面世的积极意义所在,也是本文在此要特地强调的一点。
今天对这段文本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学术史给以客观评价是必要的。但正如钟敬文教授所指出的,“评价必需符合事实的真正性质和保持恰当程度,否则就容易丢掉科学性……评论一种历史上的学术、文化活动,既要弄清楚它本身的性质、特点、产生与演变过程及社会功能等,又要究明它产生、存在的历史、社会背景,究明当时社会运动的根本要求和它对这种要求的对应性及其程度。要达到这点,评论者必须占有尽可能多的资料,必须进行过艰苦的分析、综合、推断、论证等过程,至于那种只凭用惯了的一套现成公式,或一时爱恶、感想去进行判断的作法,结果恐怕是要跟历史的真实相去遥远的。”(注:钟敬文:《六十年的回顾》,原文系1987年钟老为纪念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60周年而撰,收入季羡林主编、董晓萍编的“世纪学人文丛”之一《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486~48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我离先生的这一要求还很远,因而以下回顾或许只能算是一种感想,尤其是作为一名彝族学人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的感想,而非判断,更非抨击。因为史诗本身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着一个比较特殊、也比较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比较全面地结合史诗文本《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的历史实际与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会看到:还原诺苏彝族史诗传统多相性的文本形态,对建设一种“立足过去、面对未来”的民间文艺学史批评,抑或是对今后制订口头史诗记录文本的制作规程,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也有实践意义。
(一)《勒俄特依》的制作流程: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
为完成学术史的梳理,我于2003年2月先后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和成都两地对当年参加史诗搜集、整理、翻译的两位彝族学者曲比石美和冯元蔚进行了专题访谈。这里我们不妨按两种汉文译本出版的先后次序,重新回顾一下“文革”前后相继面世的《勒俄特依》汉译本,从搜集、整理、翻译到出版,到底走过了哪些重要的文本转换流程,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明确界定这些史诗文本类型的批评尺度。
2003年2月19日,冯元蔚先生在笔者的访谈中详细地回忆了他本人两度参与史诗搜集、整理、翻译工作的来龙去脉,他的夫人赵洪泽先生还提供了不同版本的《勒俄特依》(彝文本)。在此,我们引述其中的一些访谈片段:
冯: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勒俄》。到了解放后,1958年全国文艺采风啊,省委宣传部把我调起去当采风组组长,负责凉山这一片。采风嘛主要是民间文艺采风,所以省上去了一些人,凉山州也调了一些人参加,一共有十几个人。其他的同志都去民间搜集去了。我呢,因为有这个基础,对《勒俄》有偏爱,我就别的不大管。
曲布嫫:您就专心致志做《勒俄》了。
冯:当时分别搜集了8个版本。然后又找了8、9个德古(ndepggup头人),德古完全用口背,我记录。然后回来以后,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8个版本和口述的记录弄成卡片,进行整理。因为这8个版本中的任何一个次序都是混乱的,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
曲布嫫:民间口传就这个特点,异文多。当时您把这些版本都记录下来了,也就是把每个德古的口述都写了一遍?
冯:哦。记下来以后,我又把它们弄成卡片,一组一组、一段一段地对应,再编出个次序来。
……
曲布嫫:做卡片,比如说到了“武哲惹册涅”(vonresse cinyix雪子十二支),就用卡片把8个版本都对应出来。做卡片的目的就是对照?
冯:对,对照。对照基础上又搞个系统,从哪儿到哪儿,上下看起来有个顺序,不至于颠颠倒倒。
曲布嫫:然后再重新排列?
冯:嗯。
曲布嫫:这个就是58年做的工作。当初您这8个版本是在哪几个县收的呢?
冯:主要是在昭觉、西昌、美姑、布拖,重点是这四个县,然后我在昭觉又找到其他几个县的版本,比如雷波的啊,金阳的啊,冕宁的啊。
曲布嫫:喜德和越西这边有没得,当时?
冯:没有。哦,喜德有,越西没有,我当时也没去。
……
曲布嫫:阿普(注:冯元蔚先生与本文作者有亲戚关系,按彝族辈分,我称他为“阿普”(appu),即爷爷。),我打断一下,回到刚才的话题。您说你找过8到9个德古。这些德古的名字您现在还记得到不?
冯:都记不到了。
曲布嫫:嗯。当时那些田野笔记也都找不到了?
冯:找不到了。我也是遭抄过家的。大头是给阿鲁斯基拿走了,剩下的是几次抄家啦,搬家啦,搞得纸片片都找不到了。光是我的笔记本,这么厚的都是十几本。
曲布嫫:抄家都抄走了?简直是。这个就是最痛心的事情,心痛死了?
冯:是啊。
曲布嫫:还有就是《勒俄》的彝文本与后头的汉文本,两个本子能不能对应?
冯:基本对应。这个主要是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呀……
曲布嫫:很难对译,就是。
冯:哦。所以说,从汉文版本的角度来呢,主要是考虑汉族读者。所以,你太对应很了呢,就别别扭扭,读不通的样子。
曲布嫫:所以就是说,彝文版基本按原来的,汉文版考虑了汉语表述。
以上访谈说明第一个《勒俄特依》汉译本(注:巴胡母木(冯元蔚)、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整理、翻译:《勒俄特依》,收入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的《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的搜集、整理过程,大致是将各地的八、九种异文与八、九位德古头人的口头记述有选择性地汇编为一体,并通过“卡片”式的索引与排列,按照整理者对“次序”也就是叙事的逻辑性进行了全新的组合,其间还采取了增删、加工、次序调整等后期编辑手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文本制作过程的“二度创作”问题:第一,文本内容的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书写出来的抄本,一是口头记录下来的口述本,也就是说将文传与口传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史诗传承要素统合到了一体;第二,忽略了各地异文之间的差异,也忽略了各位口头唱述者之间的差异;第三,学者的观念和认识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对史诗叙事顺序的前后进行了“合乎”时间或历史逻辑的调整;第四,正式出版的汉译本中,没有提供详细的异文情况,也没有提供口头唱述者的基本信息(注:“若想使一篇民间文学作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除掉记录准确之外,还必须附有不可缺少的证明材料。对广大读者和研究者说来,这些材料并不比原文次要多少。当你站在博物馆中一个没有任何说明的艺术陈列品面前,你要作何感想呢?不附有必要的说明材料的作品正和博物馆中没有标签的古物一样,只能归作可疑的,最低限度是不确切的材料一类,降低了它的科学价值。这些材料包括:何时、何地、从谁那里记录来的,讲述者(或演唱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讲述者在何时、何地、从谁那里听来的等等。任何一个故事、歌曲都不能缺少这些最起码的材料。如果我们从一个讲述者那里记了许多材料,就应该进一步地了解他的个人经历,可能的话,最好对他讲述或演唱的技巧作些总的评述。一个人选择某个故事或某个民歌除掉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于他的心理状态、他所处的生活环境,而且在转述这些作品时,常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自己听到的、看到的、经受过的)东西。搜集者记录讲述者的个人经历,就是提供材料,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作品。只要搜集者认真严肃地做这一工作,不把它看成是简单的填表格,那么他的材料无疑的会给读者及研究者以莫大帮助的。”引自刘魁立:《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原载于《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见《刘魁立民俗学论集》,第16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在这几个重要环节上所出现的“二度创作”,几乎完全改变了史诗文本的传统属性。按照有些学者的理解,这个译本大概属于当时在文艺部门(非学术部门)领导下的“民间文艺采风工作”所产出的“文学读物”。那么我们是不是也不应该将之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来加以评判了呢?
第二个汉泽本则是出于学术的目的了。曲比石美和冯元蔚两位彝族学者当时作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的彝文资料整理者,一同参与到了《勒俄特依》的搜集、整理与翻译工作中。对此,冯元蔚先生回忆到:
冯:……然后就是到了1977、78、79这三年。这个时候,社科院不是发起要写一本《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吗?
曲布嫫:对,我知道那本书。
冯:然后呢,我又是写作组的副组长,我就负责彝族文化这部分。
曲布嫫:后头,你们出了一本书的吧?
冯:哦,就是为了给这本书提供资料,写的人单独有,我呢主要是提供资料。
曲布嫫:就是说为了提供历史、社会这方面的资料嘎?
冯:对的。嗯,这样呢,我就把我这个《勒俄》的底子(注:指《勒俄特依》第二个汉译本。即曲比石美、卢学良、冯元蔚、沈文光搜集、翻译,冯元蔚、曲比石美整理、校订:《勒俄特依》,辑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编《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内部参考资料。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1978年7月承印。)拿到西南民族学院印出来。
曲布嫫:这个本子我这回在下面看到过,是1978年印的吧?
冯:是1978年。
2003年2月12日上午,曲比石美先生在与笔者面对面的访谈中,更为详细地回顾了第二次的史诗搜集、整理、翻译与出版的工作,他认真、审慎的态度,使我们进一步获得了当时集体参与史诗文本汇编的工作过程,对我一周后从冯元蔚先生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也构成一种更细微的补充:
曲比:那是1977年的年初,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
曲布嫫:中国社科院的啊?历史所还是民族所?
曲比:两个所都参加了。还有云南、四川、贵州,一共五个单位,那么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就叫“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
……
曲比:嗯,冯元蔚书记和我是搞搜集、整理与凉山彝族有关的资料。
曲布嫫:搜集、整理?
曲比:搜集、整理、翻译。
曲布嫫:您们就负责这方面的事情。
曲比:哦。冯书记负责,我合作。其中就有一个《勒俄特依》。当时呢,是搜集民间所贮存的一些版面。
曲布嫫:就是版本嘎,不同的版本。
曲比:版本。不同的版本残缺不全。有些比较全面一点,有些文字资料很差。有是有,但是版本呢,很短。
曲布嫫:我现在看到的本子中,有的也很短。
曲比:很短,很不齐。当时我们搜集了可能十几本吧,大多数都很短。
……
曲布嫫:曲比叔叔刚才您说到你们当时搜到十几个本子,……在您的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本子是哪里搜到的?或者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本子的?您还有印象不?
曲比:这个(在)昭觉,当时州委的背后是城西乡,搜到了一本。我觉得呢,比较之下,那一本好一些。
曲布嫫:好一点?但是当时是从城西乡哪一家搜到的呢?还记得到不?
曲比:搞忘了。
……
曲布嫫:当时你们搜集、整理《勒俄特依》,是以你们当时搜到的十几个本子进行综合?还是说你们也到民间去听过人们唱《勒俄》啊,说《勒俄》啊?有没得当时的现场录音?
曲比:没得,没得。没有听过。
曲布嫫:也许是当时没有这个条件?
曲比:《勒俄特依》吗?我原来还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知道吗?主要是来自三个方面。一个吗?主要是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大毕摩(bimo,彝族祭司)。他的资料是很齐全的,当时,我也看到过一些。第二个方面,我自己也是……
曲布嫫:您自己也是毕摩,哈哈。
曲比:我学过毕摩。学过毕摩呢,还是不外乎是这些,内容呢多多少少也掺杂各个方面,也了解一些。再一个呢,是民间的“克斯”(kesyp,口头论辩的一种论说方式)呀,“阿斯纽纽”(axsytnyow,婚礼上转唱)呀,也听到过一些。所以过去多多少少了解一些情况吧……
曲布嫫:嗯。
曲比:再加上口头采访,口头采访有关头人。大头人些,凉山彝族的,知道《勒俄》的。
曲布嫫:哦,就是。
曲比:比如说,阿侯鲁木子呀、果基木果呀,瓦渣色体呀,恩扎伟几呀,这种是德古。
曲布嫫:对的,这次我去美姑也跟恩扎伟几谈了一上午。
曲比:恩扎伟几,这个,还有吉克扬日这些,阿之营长、吴奇果果,这些人你都熟悉。
曲布嫫:吴奇果果我熟悉。
曲比:这些人中间有些既是德古,又是毕摩。吉克扬日就是毕摩,还有恩扎伟几呀,专门唱阿斯纽纽的。
曲布嫫:哦,他这方面很厉害。
曲比:喔唷,他厉害得很,他一夜唱到天亮都唱不完的他。
曲布嫫:就是,这次下去,我也问了他的。
曲比:(当时)采访过这些人。
曲布嫫:你采访他们的时候,也是当时做调查的时候下去采访他们的吗?
曲比:调查,是调查的时候。还有搜集版本,各种各样的版本。所以,来自这么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过去了解一些情况,第二个呢采访头人,第三个呢搜集版本。然后综合拢来。当时呢,角度不同。当时我们搜集、整理、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本书服务,给他们提供资料。最后有了这些资料,他们就分别写,写了以后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这本书的总撰呢,原来准备叫周志强总撰……
我们就是为提供凉山彝族奴隶社会资料服务的。
曲布嫫:所以,它这个目的不是文学的。
曲比:不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原始性比较强一点,真实性好一些,有研究价值。
从上所述,我们大致了解到第二个《勒俄特依》的汉文译本,就是以1977~78年间为完成《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而搜集、整理、翻译出来的内部资料为蓝本的。那么,前后出版的两个汉文译本之间也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写作组(以下简称“写作组”)在1978年内部出版的资料本上登载的《凉山彝文资料选译说明》就明确指出:“本书(《勒俄特依》)曾于一九六○年由冯元蔚、沈伍己二同志整理翻译、由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审订出版。这次又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编:《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内部参考资料,第1页。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1978年7月承印。辑入曲比石美、卢学良、冯元蔚、沈文光搜集、翻译,冯元蔚、曲比石美整理、校订:《勒俄特依》。)那么这一文本制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与第一个汉文译本大体相似,即汇编性强。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前一个译本基本上是出于文学目的的民间采风;后一个译本则是服从于当时的政治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术目的,即为了提供说明“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资料,以期反映“奴隶制度下的等级、阶级和旧的民族关系等状况”,针对性相当强。因而,它也不是一个符合民间文艺学的科学资料本。第二,作为彝族学者、也作为曾经是毕摩的曲比石美先生参与到了整个工作中之外,还有两位彝族学者卢学良先生和沈文光先生也做过大量的工作(注:这两位学者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父辈,在彝族文献与文学研究方面颇有专功,但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去世了,因而不能提供他们两人对这一段工作的回顾。),这些彝族学者皆精通彝汉文,尤其是曲比石美先生出身于毕摩世家,在1956年的民主改革之前他一直还在从事毕摩这一宗教职业,因而他们的共同协作,至少对史诗的翻译、校定工作十分有益。
“写作组”还进一步强调了当时的工作原则:“在补充收集的基础上,对上述彝文原件进行整理、校正和翻译时,本着保留原貌和忠于原文的原则进行。但由于它们在四川彝族地区又流传范围广,时间长,版本各异,说法不同,又由于我们水平不高,且受时间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加上各地方言不同,对其中的某些字、词,音义难辨。因此,整理中不免有些差误,翻译不准、甚至错译之处更是难免,如《玛木特衣》最末的几小段,从对彝文的读音到翻译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它地方的个别译文也有类似情况。我们只好参照一些说法,按字分析进行翻译,必有不当之处。”(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编:《凉山彝文资料选译》第一集,内部参考资料,第1页。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印刷厂1978年7月承印。)至于其中提到的“彝文原件”当是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讲述人的史诗异文,因而“本着保留原貌和忠于原文的原则”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了。
为什么我们要深究《勒俄特依》汉译本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呢?因为迄今为止,以上两个译本一直是中国学界研究凉山彝族的重要文本。仅就史诗研究而言,学者的资料引证和分析大都以它们为范本,而文本分析也一向是中国史诗学界的侧重点,尤其是对《勒俄》的研究,长期以来依赖于汉文译本的阐释,鲜有学者超越书面文本的局限去探索它背后的史诗演唱传统,而由这种活形态的演唱传统所规定的文本形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几近湮没在死寂的书面文本分析之中。而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正是本论文的学术追求所在。
(二)关于《勒俄特依》文本的几点质疑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勒俄特依》(汉译单行本)本作一简单的介绍。全诗译本共2270余行,由〈天地演变史)、〈开天辟地〉、〈阿俄署布〉、〈雪子十二支〉、〈呼日唤月〉、〈支格阿龙〉、〈射日射月〉、〈喊独日独月出)、〈石尔俄特〉、〈洪水漫天地〉、〈兹的住地〉、〈合侯赛变〉、〈古侯主系〉和〈曲涅主系〉等十四章组成。该译本的“出版说明”是这样表述其出版宗旨的:
彝族古典长诗《勒俄特依》,流传于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它以其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和丰富的想象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万物的生长、人类的起源、彝族的迁徙等等,其中也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情景。1982年我社出版的彝文版《勒俄特依》,是由冯元蔚同志搜集整理的,它深受广大彝族读者的欢迎。根据广大读者想阅读汉文本的要求,冯元蔚同志将它译成汉文,现予出版,以飨读者(注:详见冯元蔚译:《勒俄特依》(出版说明)。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但是,在出版的环节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个汉译单行本在封面上将史诗明确定义为“古典长诗”,与1960年将之纳入“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的作法是一个矛盾;二是1999年《勒俄特依》的彝文本又发行了新的版本,与老版本同样,彝文本与汉文本之间有一殊异之处,也就是彝文本为15个章节,比汉文本的14个章节多了名为《阿略举日谱》的一章。因此,在彝汉文两种文本之间出现了“异文”。关于这两个问题,在访谈中冯元蔚先生作了如下解释:
曲布嫫:那么,阿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注意到你用的这个词呢是“彝族古典长诗”。那么现在汉族学界呢,研究彝族史诗基本上把你这个《勒俄特依》作为一个范本来研究,老是说彝族有“四大创世史诗”,包括《勒俄》、《梅葛》、《查姆》和《阿细的先基》。就是说,阿普,你当时把它命名为“古典长诗”的时候呢,您有啥子考虑呢?
冯:这个呢我都没有咋个深究。
……
曲布嫫:我看了一下,阿普,这本(彝文版)好像跟汉文版不一样。汉文版是册尔节(celyjjie 14章),彝文版是15章。比较之后,我发现彝文版多了《阿略举日茨》(atnyujjussecyt阿略举日谱)那一章。
冯:《阿略举日》啊?《阿略举日》原来是有,后来我到美姑去调查,补充了一下,有人认为它有点牵强附会。所以我又把它删了,觉得“阿略举日”的故事等于是离开了传统,民间倒是有一些传说。
曲布嫫:我这次到美姑调查,《勒俄》里面有《阿略举日》,肯定有一章。
冯:有啊,它是《阿略举日茨》(atnyujjussecyt阿略举日谱),没得“阿略举日”的故事。
曲布嫫:“布德”(bbudde故事)?“阿普布德”(appubbudde神话、传说、故事的彝语总称)是没得。
冯:哦。对的,原本是没得,后头有一节我把它弄进去了,有人就说有点牵强附会嗦,我就删了。
曲布嫫:“阿普布德”(appubbudde)一般是散文体的,散体形式。那么就是说包括像支格阿鲁射日射月,一般的《勒俄》里面都有射日射月,有的版本还讲到他怎样跟木兹(muzyr雷神)打仗。我觉得不能说有就不对,没得就对。这个不能这么简单来说,因为每一个版本都不一样。比如我下去搜集到的版本,有沙马土司的版本,有阿都土司的版本,还有宜地土司的版本。所以版本系统不一样,内容也会不太一样。
关于“古典长诗”与“民间长诗”之间的矛盾,我们应当将之纳入整个中国史诗学发展进程中来看,正如前文提及“史诗”概念的重新界定,是我国史诗学术史上比较晚近的成果之一。因此,不必在这里更多地予以讨论。但是,关于彝汉文版之间出现的章节差异,牵连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既然《阿略举日谱》在彝文原本中存在,整理者鉴于“异议”而在汉文本中“删除”,正是出于对“牵强附会”的矫枉过正。因为彝文原本中一般按史诗的传统叙事,只讲到“神人”阿略举日的系谱,并没有后来一些学者望文生义地联想出来的“猴子变成人”的“故事”。但是,汉文本为避免这种“附会”就将整个一章删去的作法,正好说明这章的原始译文采纳了“猴子变成人”的“故事”。据我搜集到的几种抄本,并且结合史诗演述人和地方德古头人的讲述来看,“阿略举日谱”原为史诗《勒俄阿补》(公本)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阿略举日谱》这个环节上出现的有无之变,正好引出另一个文本问题,那就是当初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忽略了史诗文本的传统形态,混淆了“公本”与”母本”之间的差异。
据我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在《勒俄特依》第二个汉文译本的正式出版之前,学界已经在讨论史诗的文本问题了。实际上,岭光电先生是第一位对史诗《勒俄》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做出过历史性贡献的学者(注:岭光电(1913-1989),彝名牛牛慕理。1913年出生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田坝区胜利乡斯补村,是斯补兹莫(土司)——煖带田坝土千户后裔。1936年毕业于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后回乡兴办“私立斯补边民小学”,在凉山彝族现代教育史上写下重要的开篇之章,岭光电先生因此被誉为“民族教育的革新者”。1939年任西康省政府中校参议;1942年到西康省宁属屯垦委员会(驻西昌)任边民训练所教育长;1944年任夷田特别政治指导区(直属西康省)区长,西康省彝族文化促进会理事长;1947年任西康省政府边务专员;1948年被选为国民立法委员;1950年加入“国民革命同志会”并任国民革命军第27军少将副军长。岭光电先生在从军从政之时,对彝族文化进行了一些研究和介绍:1936年和彝族同仁一起编纂《新彝族》一书;1942年发表《彝族倮倮经典选译》(《西康青年》),后来陆续发表《圣母的故事》、《倮倮的怅恨歌》等译著和论文;1943年整理12篇彝族历史、文化、故事编辑成《倮情述论》,引起朱光潜、马长寿、马学良等学者的重视,后来他们彼此在学术上常有交往。1950年4月10日岭先生率领人马回到西昌,接受解放军整编,受到政府欢迎。1957年,参加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4工作队,从事彝语调查、研究工作。同年底,调四川省民族出版社。1962年调四川省民族委员会参事室。“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揪回家乡,受到不公正待遇。1978年至1988年,党和政府为岭先生落实了各项政策,实事求是地否定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1978年调四川省民委彝文组工作,专心致志地从事彝族文化的整理、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1981年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编目整理,并受聘至中央民族学院彝文专修班任教,编写、整理了大量的古彝文经典书籍,如《雪族》、《古侯传》、《玛木特依》(《教育经》)和《凉山彝族习俗点滴》、《彝族尔比尔吉》等著作,还撰文阐释许多彝族古语及彝汉文化关系等。1985年着手整理《忆往昔》,经多次修改后于1988年出版。岭光电先生落实政策后被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凉山州政协常委、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顾问等职。1989年2月15日因病在西昌逝世(摘编自《甘洛县志》)。)。早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期,岭先生就搜集到了流传在凉山西北部的史诗文本,并开始整理和翻译《勒俄》(注:据冯元蔚先生回忆,他1948年在四川边疆师范学校上学时,还读到过岭先生翻译的汉文油印本《勒俄》,当时从译本的长度看,大概只是一个简本。摘自《冯元蔚先生访谈录》。)。80年代初期,岭先生被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与马学良先生一道从事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那时我也正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此后,岭老在《勒俄》的翻译、整理工作方面继续辛勤耕耘,先后译出了《史传》、《古侯》(《古侯公史传》)、《武哲》(《雪族》,又称为《子史传》)。这些不同的版本,先后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印室编印出来,作为当时的彝文古籍文献整理班的教材使用。岭老的长子岭福祥先生指出,其中《母史传》的底本就是他父亲在40年代末期整理、翻译过的《勒俄》,为今所见较早的彝文抄本,原本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注:见中央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编译室编《彝文文献选读》,第302页。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从岭先生的文本注释、翻译情况来看,80年代初期学界对《勒俄》版本的分类情况已经形成一种基本共识,那就是普遍认识到这部长诗的文本形态比较复杂,其中“阿补”(apbu公本)与“阿嫫”(apmop母本)之分,成为至为关键的一点。也就是说,《勒俄》尽管有许多异文及异文变体,但最基本的文本类型是按照彝族传统的“万物雌雄观”来加以界定的。对彝族文学研究有素的萧崇素先生早在1982年9月就撰文指出:史诗有4种不同的“版本”,《勒俄阿嫫》(母史传)、《勒俄阿补》(公史传)、《武哲》(子史传)和《古侯略夫》(公史续篇)等四种(注:“彝族著名史诗《勒俄特依》现有两种译本,皆以《勒俄阿姆》为正本。史诗内容丰富,文词华丽,易为人所接受。但据了解,彝族的《勒俄特依》并不只这一种。计有以下四种:(一)《勒俄阿姆》(彝史母本)。这是成书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五言叙史长诗。一般毕摩和群众中都流行这本书。传世的《勒俄特依》,现在整理、出版的,都是《勒俄阿姆》。(二)《勒俄阿补》(彝史父本)。内容比较扼要,着重阐述彝族谱系及迁徙地域,对远祖树居,古代部落绝灭,古侯、曲涅两部落如何由三大渡口进入凉山等,都有细致地描写。(三)《武哲史》(雪源子史编)。大部分与《古侯阿补》相同,但增加了部分重要的内容。对‘三贤时代’的兹(领袖、酋长、部落长)、莫(官员、军事首领)、毕(部落文字和祭祀的主持人,毕摩、大巫师)、卓(百姓等)的人物、职权以至管理结构,对与‘俄竹人’(西番、普米)等民族关系史,皆有较详细的描写。《武哲史》是《勒俄特依》的续本,也是研究彝族古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史料。(四)《古侯略夫》。据说这本彝书是部头较大、内容较全面的手写本,是《勒俄特依》的续本,内容异常博大丰富,一般人不易见到,也不易读懂。金阳一带曾流传有古彝文本,但在‘四人帮’毁灭文化的时代,当地曾强迫烧书达四次以上。据说还有少量的这类手写本还保存在民间,但须用细致的说服方法才能得到。以上四种《勒俄特依》,绝大部分是用七音句或五音句写成的。本身既是神话、传说,又是史诗,既有文学价值,也有史料价值,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应该迅速抢救,搜集各种不同版本和口头记录,加以集中整理、翻译、出版。”引自《彝文古籍概说》,载于《萧崇素民族民间文学论集》,第288~291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并对四种文本的异同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除去他将当时已经面世的两种史诗译本“大胆地”归为《勒俄阿嫫》(母本)之外,可见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史诗文本形态的多样性,而且强调不能忽视各种文本之间的区别。我们不禁要问:萧老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勒俄特依》第二个汉译本之前,为什么没有引起整理者的重视呢?仅就“公本”与“母本”之间的差异,冯元蔚先生在访谈中是这样回答的笔者的:
曲布嫫:还有一个问题,阿普,就是说,这个《勒俄》呢,下面分“阿补”(apbu公本)、“阿嫫”(apmop母本),分“阿诺”(axnuo黑本)、“阿曲”(aqu白本)。“阿曲”呢基本上是“阿嫫”这部分;“阿诺”呢基本上是“阿补”。您当时做“勒俄”是将“阿嫫”、“阿补”综合在一起呢?还是以“阿嫫”为主,或以“阿补”为主的呢?有没有这方面版本的区别?
冯:我也问过这个。所谓“勒俄阿嫫”(hnewo apmop即母勒俄)、“勒俄阿补”(hnewo apbu,即公勒俄),在内容上毫无冲突的,“阿补”、“阿嫫”的分法,很多人包括我访问过的那些德古都这么说的,内容上没有冲突。所谓“阿补”呢,有点简单化、提纲化,“阿嫫”呢是繁本。
曲布嫫:只是说版本的长短?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冯:是的。只是详略之分。
曲布嫫:那您当时听到过“阿诺”、“阿曲”这种分法没有?
冯:听到的呀。听到的就是没有啥子多大差别。
曲布嫫:但是我下去调查时,美姑那边说他们分得很清楚。为啥子呢?比如说,西西里几(xyxie hnijyt婚嫁)的时候就只能唱“阿曲”或“阿嫫”;“措斯”(cosy丧葬)的时候只能唱“阿诺”;“措毕”(cobi送灵)的时候呢,“阿诺”、“阿曲”都可以说。为啥子说结婚的时候不能唱“阿诺”那部分,像“石尔俄特”就属于“阿诺”那部分,因为“惹约帕阿莫”(sseyur patapmo生子不见父)……
冯:不吉利。
曲布嫫:对,不吉利,所以结婚的时候就不能唱这一段。所以我现在是根据它在哪种场合下使用“阿诺”,或是在哪种场合下使用“阿曲”,这样子来分。
显然,将“公本”与“母本”整合到一体,是现行汉译本最大的结症所在。当时整理翻译者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自到民间的史诗演述场合进行实地观察所致。而长期以来“公本”与“母本”之间的异同及其传统规定性,尚未得到高度重视,也没有形成进一步的讨论。本文认为,这或多或少与汉译本的出版有关,因为译本没有对文本的流布情况、文本的搜集整理过程作任何说明。如果读者或学者缺乏对彝族史诗传统的了解,或许就会认为,这种汉文整理翻译本就足以反映彝族史诗《勒俄》的原生面貌了;而对于了解本民族史诗传统的彝族学者来说,则缺乏一种客观的学术批评尺度,缺乏一种正确的史诗观照态度,这与整个中国史诗研究界长期以来的学术导向有关,也与过去我国史诗学的理论建设滞后于作品的普查、搜集、整理和研究有关。这就是我们这里对史诗《勒俄》的文本作一学术史清理的出发点。因而,仅仅在各种异文之间进行“取舍”和“编辑”的作法,无疑忽视了史诗传统的特质及其文化规定性,在这一重要的彝族史诗文本制作过程中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历史遗憾。这是我们今后在史诗文本化制作工作中必须汲取的教训之一。
我在田野过程中与史诗演述人曲莫伊诺谈起他自己的两个《勒俄》写本时,无意间听到了他对《勒俄特依》彝文整理本(这位演述人不懂汉语,也不识汉文)的“评价”:
曲布嫫:(拿出《勒俄特依》的彝文新版,马拉嘎叔叔借我的)伊诺,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你原来,就是你18岁写这个本子的时候或者之前,看到过这一类的出版物没有?
伊诺:(翻开书来看了一会儿)这种没有。我知都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书,也不知道坝区那些比较接近街上的地方上有没有卖的?我是没有看到过。啊波——,tepyy cyzzit guma sinip mgema jjyhxuo dasuw(这本书把包谷籽和荞麦籽混在一起咯),我分不出来。
曲布嫫:啥子呢,啥子“包谷”、“荞子”哦?
伊诺:你看嘛,哪些是“阿补”(apbu公本)的,哪些是“阿嫫”(apmop母本)的?他们写在一起了,现在不好分(辨)了。
曲布嫫:你倒是会用比喻嘎,很形象。等我记下来。还是你用彝文直接写要准确一点,把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写在这儿算了(把笔记本和笔递给他)。
伊诺:(接过本子和笔)你说的是哪句话?
曲布嫫:“包谷”、“荞子”那句。我爸爸老说你语言丰富,这个比喻就非常深刻,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注:摘自2002年11月12日的田野访谈。)
按史诗演述人的话来讲,彝文整理本也同样存在“把包谷籽和荞麦籽混在一起”的情况,换言之,就是将“公本”与“母本”整合到了一起,现在单凭文本再做区分是很困难的。因为曲莫伊诺细读之后认为,被整合的部分大到段落,小到具体的诗行。这种情况大概也是受了汉文译本及其工作思路的影响所致。
在我们对史诗汉译本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之后,就会见出后来各地陆续搜集、整理的史诗译本,也几乎在走同样的路子:始终没有任何关于史诗演述人的确切信息,始终没有史诗文本来源的信息。史诗文本的汇编过程更是一个迷障,遮断了人们正确读解史诗传统及其文化语境的目光。遗憾的是,彝族学者大都生于斯、长于斯,有的自幼就在“勒俄”传统中熏染传习,但似乎没人对已经出版的《勒俄》文本提出质疑,或是关注这些出版物背后的史诗传统,从过去到现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目前处于一种怎样的传承与传播状态。“勒俄”本身当是一种史诗传统,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书面文本,乃至扩大些说,一个语言艺术文本。然而“勒俄”后面一旦加上了“特依”(teyy经书、书籍)二字,仿佛也就变成了一堆沉寂无声的纸页,从这些印刷出来的文本中我们听不到史诗演唱的任何音声,更看不到史诗传人的身影,民间传统文化语境更随之而丧失殆尽。许多学者的探讨,尤其是本民族学者的研究,大都面对这个写定的译本而止步不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