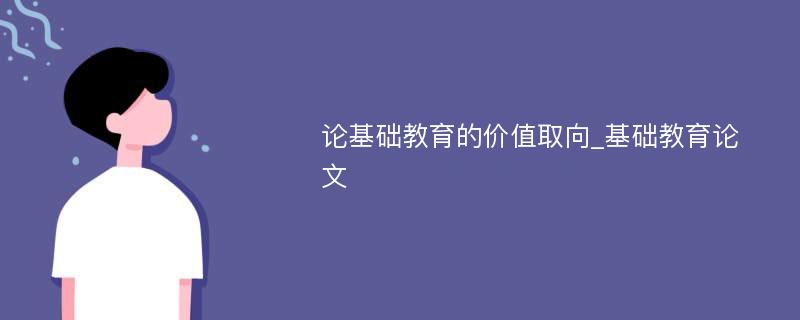
试论基础教育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价值观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础教育是指与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和特殊教育相区别的一种教育,它的对象是儿童,少年和一部分青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建设一个能够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及经济建设需要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制度,已越来越成为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重点。在世纪之末当我们反思传统的基础教育,把一个怎样的基础教育带到二十一世纪,使我们的教育更好地面向二十一世纪,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时,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实行“应试教育”的传统基础教育的弊端。尤其是在对基础教育的价值进行科学界定的问题上,仍存在不少误区。为此,笔者拟就基础教育的价值观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基础教育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的奠基工程
对价值这一概念,马克思曾经指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6页。)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326页。)可见,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客体的某些属性对人、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是客体的某些属性能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成为主体所追求的目的。而人是主体,又是客体,具有主客二重性。在实践活动中,他是主体,在现实存在中,他又是客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价值是作为价值客体的人对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或社会的价值。它可以区分为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人的社会价值即他对社会的价值,这取决于他的行为客观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人的自我价值,则取决于他的行为客观效果满足自我需要的程度。人的社会价值的实质就是主体的人的创造活动,是他的创造活动对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积极意义,是他的创造活动对他人满足的程度。实践是主体的人的创造活动的载体,是实现人的社会价值的力量源泉。同时,在实践中,人还要去实现自身的生存、享受和发展,也就是人的能力、个性、尊严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的价值实现,取决于人的知识积累的多少、取决于人的聪明才智发展的水平。但是,最终还必须取决于人的创造意识,取决于人的道德品质,人的进取心,人的胆识和自强不息等人格素质,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可见,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即人最终实现自身完善化的发展应当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
教育价值首先取决于它本身固有的属性。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三层含义:(1)它可以促使人的先天素质得到发展,使生理、心理的素质得以呈现出来,也可以使人的固有、内在本性外化出来;(2)使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人类的本质转移于新生的个体中,也可以说使人类固有的本质内化于个体中。如语言的掌握,文学工具的运用等;(3)按照一定社会要求造就出一定样式的合格的社会成员,这是将外在的特定的社会本质对象化于主体的过程,即个体社会化。这三层含义的集中点就是教育具有发展人的素质和改变人的状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客观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价值的终极目标的实现是和人的价值实现相统一的,即教育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有效载体和手段。关键是我们要确立科学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教育系统工程,使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传授知识,局限于传授思想、技能,而应致力于提高与扩展人的价值,增长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在兼顾德、智、体、美、劳等多方面素质教育的过程中,最终实现人的自身完善化的发展。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人实现价值过程中的起点和蓄势阶段,为此,基础教育应当也可以成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的奠基工程。
二 从我国教育价值观的历史演变看教育价值观的科学回归
教育本身职能的多样性,人们评判教育的角度的科学性,决定了教育具有多种类型的价值,如道德价值、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这些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国度,在同一国度的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其独特的观念。教育价值观问题,实际上就是人们在宏观上对教育价值的追求问题。翻开我国教育价值观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轨迹。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孔子为鼻祖的一代又一代教育家,他们追求的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还说:“君子务道不务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注:《论语·里仁》。)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汉书·董仲舒传》。)朱熹、王守仁都把“存天理,灭人欲”当作教育应当追求的理想价值。这些教育价值观在封建社会基本上被代代相传。究其实质,他们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追求所谓的重义轻利,以道制欲,是盲目地致力于人格的完善,贬低物质利益的价值观。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和发展,以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改革派人士,他们开始在教育上追求“经世致用”的价值,洋务派提出了“自强”和“求富”的口号,以开办“洋务学堂”为先锋,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种教育价值观中已明显地体现出对“用”这一目标的追求,也就是对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力和科学技术人才的追求。当然,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这种追求仍是“犹抱瑟琶半遮面”的,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从此,实际上敲响了新中国教育价值观的“定音鼓”,即必须强调教育满足社会政治、经济需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膨胀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教育的唯一社会功能,从而使教育完全沦为一种使“四人帮”等人实现阴谋和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才重新开始重视教育与生产力,特别是与现代社会、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生产力之间的密切关系,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毅然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教育开始迎来春天。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是体现教育价值的本质属性,把对人的素质教育的地位提高到第一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教育价值观的一次科学回归。
纵观我国教育价值观的回归轨迹,教育价值观存在着两个十分明确而又对立的出发点,即两种不同的教育价值观。一是从人的完善化来评论教育价值的“人”的教育价值观:一是从社会需要来评论教育价值的“人力”的教育价值观。前者的追求在于唤发人的天性,培养人的智慧,发扬仁性,成为仁人;后者的目的在于创造公民、国民,或商人、工人、士兵等。前者认为后者是反人道、非人道,压抑了个性发展,使人非人化;后者认为前者是将教育抽象化、理性化了,而人的价值在于他是物质价值、社会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的承担者和创造者。“人”的教育被誉为“理想的价值”,“人力”教育被贬为“工具的价值”。事实上,笔者认为这种誉贬是无意义的,在这两种教育价值观现象的背后,凝聚着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为提高人的素质而进行的教育和为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教育,其终极目标是同一的——实现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推动人的自身完善化的发展。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对人的需求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一致的。一方面,人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归根到底应取决于他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实际贡献,取决于他的创造。而要发挥人的创造才能,人又不得不按照社会需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人就不能不成为手段,成为工具了,人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条件,得到所谓的绝对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又不能不考虑其享用的价值和自身得以全面发展的目标的实现,不能不考虑他应有的人格、权利、尊严等得到维护。这也是社会高度发展的标志。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下,现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巨大的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同等地,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3页。)这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仅应保证人民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且生产享受和发展资料,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一切有损社会主义公民权利、自由、人格,必要的生活资料及发展资料的行为,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观的。这样理解,就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统一起来了。换言之,教育的价值就是为社会培养大批自身素质得到高度发展的人,正是这些人
创造出更多的能满足人的生活、享受、发展所需的社会财富,再反过来推动人的自身完善化的发展,如此循环不断推动人类的前进。
三 提高民族素质,是基础教育价值观的核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力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则是更明确地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这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础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础教育基本目标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它的对象和着眼点是全体人民,而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人;第二,基础教育的功能是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奠定基础,它强调的是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而不是专业或某些专门人才的培养。由此可见,提高民族素质是基础教育价值观的核心,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育教学观念与思想,教学方法以及评估指标体系等,都必须服从这样一个核心内容。
我们知道,整个民族素质是由每个公民的素质构成的。讲人的素质不仅包含有人的生理上的与生俱有的特点,而且包括人的体质,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即一个人在德、智、体、美、劳诸多方面的质量。那么,如何提高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教育教学质量呢?在身体方面,应包括身体发育的正常,体质强壮,无后天的残疾等。在文化素质方面,应包括掌握文化工具(包括会说普通话等),一定的文化教养(文化修养、理论修养、艺术借鉴与实践),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良好的心理特征(智力、兴趣、情感等)。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应包括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责任感、义务感)、道德观等。民族素质不仅取决于每个国民的素质,它还应当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特性,如中国人民的勤劳、刚健等。这些素质作为民族意识通过民族文化世代传递下来,形成自己的特色,整个民族素质既有赖于个人的素质,而又构成个人素质发展的条件。所以,作为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核心的基础教育,不可忽视对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发展。
鉴于以上认识,在基础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强调这样两点:一是不断发展学生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素质;二是要充分发展人的潜在的各种才能,焕发出人的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提高主体意识,让学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的意义、激发自信和奋发向上的精神,为人最终自如驾驭自己的创造活动提供准备。
要实现这样的基础教育过程,我们就应当打破侧重于“外铄”、“规范”,视学生为可塑物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框架,防止片面强调教师的主导与绝对权威。而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强调学生的主体发展,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侧重于“引发”、“生长”,视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发展自我素质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价值,萌生创造的欲望。今天,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股热潮,滚滚涌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价值观的定势在作崇,使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本身,仍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为适应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素质,而未能将人的自身完善发展提到突出位置。同时,由于社会财富未获得极大的增加以及教育事业本身发展的有限性,决定了以高考为代表的升学竞争仍如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左右着我们的基础教育,使“应试教育”对基础教育的价值发生着负向作用,从而使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受到亵渎。教育对人的价值的发展本身就存在两种作用:一种是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可以激发学生向上,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对自身价值认识的正向作用;另一种是通过传道、授业、解惑,可以压抑学生灵性,闭塞学生耳目,贬低学生自身生存的意义的负向作用,前者使学生越学主体意识越强,越自信,越充满创造的欲望,后者使学生越学越感到自己不如人,越自卑,越对人生感到漠然,以高考为目标的“应试教育”,所产生的正是后者那样的负向作用,由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相当一部分学生难免最终失望,如此艰巨残酷的任务,决定了学生在步入幼儿园——这个基础教育的基础的大门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就必须在高考所规定的课程体系中跋涉前进。而最终的落榜,又必须使学生得出“我不行”的结论,从而使其自身自信、创造等素质受到扼杀。可见,当前,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核心的基础教育,首先应当定位在以提高主体意识“我行”的焦点上。具体地讲要着力做好如下工作。
(1)在整个教育事业的规划上,要把加强基础教育作为最主要的环节,以改变基础教育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发展缓慢的状况。改变只重视高等专业教育而忽视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思想,有条件的大城市、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应逐步普及高中教育,提高基础教育的平均受教育的年限。
(2)认真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针,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课程标准和教材,比如在继续提高语文、数学、外语等基础学科的教学水平的同时,应增加自然、历史、地理、体育、美术、音乐等科目的教学时数,以及提高这些科目的教学水平,真正解决基础教育中重教育的外在实用功利价值,而轻教育对个体内在的人格陶冶价值;重教育的科学价值取向,而轻教育的人文价值取向这样两种价值观的偏差。
(3)在教育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教育民主,培养学生做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人以至做未来社会的主人,打破传统教育“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师生共同参与教学和管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为宗旨,既体现教育的科学性,又体现教育的艺术性、民主性,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教育价值,实现人的整体发展,使学生德育的心理过程、知识的思维过程、能力的培养过程、艺术的感染过程、体魄的发展过程、潜能的开发过程协调一致同步进行。
(4)要强调基础教育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说,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内部,具有它独立的、不依附于其他类型和层次教育的价值。这是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观念基础,不能只以能否为高一级学校提供生源的多少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应该明确,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但并非是基础教育唯一的任务和目标。在全社会,也必须折断唯一用升学率来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标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基础教育去实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个性发展。
(5)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很难设想一群本身素质不全,进取心不强的教师,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学生,能激发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早在1922年,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就提出:“必须把全国第一流的人才绝对集中于培养教师的大学里,这件事应作为当宰相的第一要义”。这一思想在日本教育中从法律规定到理论、到实践足有体现,这也是日本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从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重视师范教育,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真正使教师成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充实教师队伍,才能引发教师的自豪和责任,才能优化教师队伍的层次结构和教师个体的素质结构。
综上所述,只有当我们在全社会的战略决策上、教育制度上、教育操作上规范整个基础教育过程,才能真正使基础教育履行素质教育的职责,才能使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基础教育价值观的核心的实现成为可能。
总之,基础教育价值观的科学定位,有着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首先它可以促使人们去反思传统价值观的弊端,为现代教育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其次,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又会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审视目前的教育教学,为素质教育的全面展开进行理论准备;最后,基础教育价值观的科学界定,也会从另一个层面上推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确立科学的人才观,更好、更快地发展基础教育,提高民族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培养出数以亿计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