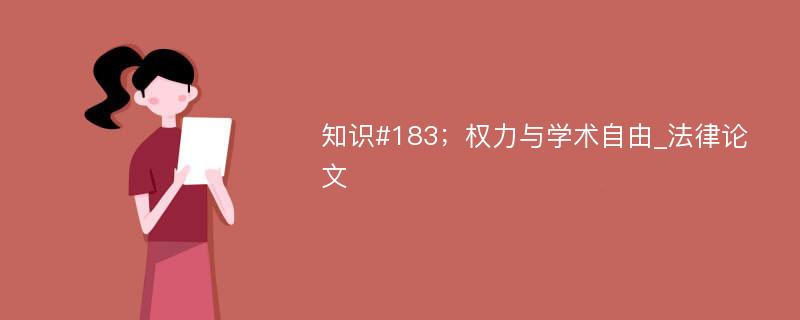
知识#183;权力和学术自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学术论文,自由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2)01-0022-03
孔子说过一句值得反复玩味的话: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细细咀嚼一下,觉得好象不对劲。从孔子的生平事迹来看,他设坛讲学,开私学之风,招收弟子,主张有教无类,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显然肩负的是教化天下、开启民众智慧的重任。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巨人,应该是最先晓得知识的力量的,一旦下层民众掌握了知识武器,那么,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写历史。知识是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唯一的阶梯,知识和自由乃一母同胞。孔子对此视而不见,断然割裂了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他害怕民众造反,说到底他还是有阶级立场的。
然而,孔子这句话无疑已经暴露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向社会的权威中心发出警告,知识乃自由的必由之路,知识的启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颠覆国家政权。那么对知识分子呢,包括孔子本人,这些人类中的一小撮应算作掌握知识的合法者,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孔夫子并没有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西周末年,盗贼纷起,天下分崩离析,学术下移,而政权的束缚松弛下来,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相对较大,学术自由在当时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严肃的问题。以孔子的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来看,他似乎不愿意给人留下话柄,他的学术观点本身就是一套权力话语,学术自由的纵容极可能将他苦心营造的政治理想主义摧毁。孔子的沉默,已经表达了他的观点:作为知识分子,他渴望学术自由;作为权力话语的制造者和现存政权的代言人,他又惧怕学术自由的放任。这样一种难堪和矛盾在学术领域,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绵延至今。
而有个问题是确定无疑的,在东西方的古代社会,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是不存在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个明证,他以蛊惑青年和不信神的罪名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因为他奉理性为最高的神祗,这明显违背了当时的宗教精神。而且最为要命的是,苏格拉底公然反对当时雅典的民主制度。有意思的是,在临刑前,苏格拉底的朋友已经做好了帮他逃跑的一切准备,不料却被他一口拒绝了。他认为,重要的不是活着,而是正义地活着。他决心遵守国家的法律,以死捍卫法律的尊严。苏格拉底之死绝不仅仅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它最早标示了学者的自由权利与政治、宗教等外部力量的紧张关系。而苏氏从容就戮、遵纪守法的行动则是用其生命表达了同时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国家公民在遭遇两者身份冲突时的人格立场。苏氏和孔子其实站在同一角度审视学术自由问题,即在国家权力框架的约束之下,展开学术研究,当学术观点与前者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保留自己的异见,而服从既定的政治安排。打个比方,学者们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站在当代史的角度,如果给学术自由下个定义的话,那么不妨表述如下:学术自由即是学术界人士在其胜任的学科领域内,在教学和研究中享有的调查、言论、出版、交流等自由权力,而不受任何政治、宗教等外在权威的干涉和威胁,学者对学术事务的处理完全依据学术标准进行。我之所以要强调从当代史的角度来下定义,因为这一狭义的或者说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是直到现代社会才被总结概括出来,其间经历了数千年的血的教训,也只有到现代社会,在资本主义法权体系建立之后,为现代法律制度所定性、保护的学术自由权利才真正开始生效。
这个意义上的学术自由是在19世纪初的德国首先得以确立的。其思想奠基者是三位哲学家洪堡、施莱尔·马赫和后来担任了柏林大学首任校长的费希特,他们使学术自由作为一项学校生活的基本准则被确定下来。学术自由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被重新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强调绝非学者们的随心所欲。在此之前发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与大学无缘的,起重要作用的是当时的一些官方和民间科学社团。大学则置身事外,因为那时候的自然科学不登大雅之堂。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一直处于被抑制状态,这直接造成学术自由紧迫感的缺失。大学的传统职能还是以传授既成知识为主。既然大学错过了第一次科学革命,那么,针对即将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大学必须将研究提升到仅次于知识传授的重要地位。开展学术研究,需要破旧立新,确立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正好顺理成章。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大学自身的行为。大学可以规定学校的师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自由,但不能防止大学外部力量对这种自由权利的随时剥夺。学术自由应该是大学和国家签定的共同契约。唯有国家颁布法律予以认可,这样的学术自由才具备上述的严格意义。
这一进程一直拖到20世纪初才陆续完成,许多国家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明确保障学术自由。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规定:“艺术、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1976年的《高等学校总法》将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定义为三大自由。世界诸国纷纷予以承诺。[1]至此,学术自由才获得比较完满的形态,防止了苏格拉底悲剧不再重演。但有个容易被遗忘的历史细节需要提示一下,现代学术自由制度的确立还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确立有必然联系。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必然打破宗教的疆界,使政教分离成为可能,为学术自由清除了宗教的蛮横势力。虽然有些大学到现在也无法割断与宗教的联系,但至少划定了二者之间的有效边界,减少了宗教干涉的随意性。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还确立了国家的权力主体地位,使现代法律的制定、实施成为可能,这样才谈得上学术自由的法律保障。
学术自由在20世纪以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普遍原则。其对于高等教育、对于学术事业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于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的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而紧接着又规定: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学术自由是一项国家赋予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的特殊权利。它不同于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普通公民也享有出版、言论、结社的自由,学术自由也纳入了这些自由权力作为其基本内容,然而,国家在赋予学者这些自由权利时显得谨小慎微。因为学者的身份有别于一般公民,学者的话语具有“暴力性”的特征。大学向来都是个集保守和激进、传统与现代、因循与裂变的敏感之地。造成这一切陆离百怪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是知识。知识是大学实施其功能的基本要素,也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其形式可能有科学与人文、真理与谬误之分。归结到一点,知识在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日常现实、与权力关系纽结在一起。从来就没有一种与人类无关纯粹的知识。把大学称作象牙塔纯属无稽之谈,大学自诞生之日起至今,就渗透进各种政治、宗教势力,通过知识的阐发,对日常生活予以凌空驾驭。人类历史上历次重大社会变迁,具体现在学者话语的暴力革命上。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家才既给了大学学者以自由,又特别加以约束。学者们好比戴着枷锁做自由地旅行。
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约束一直处于一种紧张关系,时有松懈,但从未解除过。可能许多学者在大学何以享有学术自由这一问题上的认知是趋于一致的,即大学是发现并传播真理的场所,而对真理的发现和传播,必须挣脱现实的束缚而保持远距离的观照,这要以自由为先决条件,无论这种自由是柏拉图似的精神自由,还是法律规定的实质自由。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专制体制下,只标榜一种绝对真理而剥夺了其他知识的存在价值,大学只能因循,不能创造,其结果是学者自由权利和学术生命力的全部丧失。因此绝对真理是和学术专制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承认真理只是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对真理的追求则从无止境,每位学者都有权利致力于这场永无终点的赛跑。
然而,这是一种以真理来标识学术自由合法性的主流观点,似乎并不能解决学术自由及其束缚的紧张问题。假如学者们是在追求真理,那么,他们自觉确立的内部学术规范就足以约束他们的学术生活,而不必又从外部社会权威的角度施以强行限制。而古往今来,对学术自由的侵害,恰恰是来自于大学之外的权威,而非学者们自己达成的学术自律。因此,学术自由合法性的基础并不像布鲁贝克等学者说的那样,是单纯“对真理的追求”。苏格拉底就从未认为自己拥有了关于事物(如真理、公正和善)的绝对的确然的知识。他曾有个疑问到死也未明白:“为什么热爱真理的人会不时招惹麻烦呢?”[2]
我对这个问题试图做出的回答是:知识不仅具有“真理性”,还具有“权力性”。福柯通过对历史文本的阅读,从中发现了知识的权力谱系并断言,“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3]这种知识特性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广泛存在着,甚至惯以标榜寻求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也不例外。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经历了宗教的血火洗礼,而体现出悲壮的殉道精神。而在当代,科学无疑已凭籍数百年来的辉煌成就,成为当今最大的“元话语”,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被等同于真理,被赋予绝对的价值,而一切人都被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一个国家政权也会以科学的名义,来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在承认知识的权力特性的前提下,来讨论学术自由及其约束的关系,就不会再死守类似绝对真理的绝对学术自由观念。那不过是空中楼阁。要知道,学术自由并不仅仅是为真理和大学而单独存在的,它最终指向人类社会,为其提供有用的知识,这种知识可能是正确的科学知识,也可能是解释更为有效的人文知识。学术自由和学术约束互为条件,享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承担学术责任和职业道德,一个学科自发形成的学术规范是对学者的内部约束,一个国家的法律则是对学者的外部约束。学者的研究成果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并通过有效的方法取证,否则,越出本学科范围,散布毫无根据的言论,怂恿视听,便超出了学术自由的界限。
现代国家在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中界定学术自由时,无不将自由权利的行使和遵纪守法相提并论。因为学者作为知识的掌握者,其言论和著作对学生和普通大众的影响力是潜移默化的,甚至具有瞬间的“爆炸性”。学术自由通常被定义为学者在本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和研究自由。[4]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严格或者说是狭义的理解。学者作为社会公民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这是知识的权力特性的域外扩张,法律不能予以剥夺。因此,讨论学术自由问题,还有必要区分出一种广义的学术自由含义。
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将这种范围广延的学术自由称作“学者的政治自由”。[5]他具体论证道,学者的政治自由意味着学者们在教学中坚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主张,这些主张有利于澄清在大学课堂上、在书籍文章中没有被彻底解决的学科难题。并且学者们必须明确指出他的政治或道德观念与他对事实的分析判然有别。总而言之,学者们不应该将自己的政治信念或道德准则带进课堂。如果他迫不得已这样做,那么,他应该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区分开来。希尔斯本人是一位保守主义思想家,他重传统价值,强调社会系统的稳定,认为学者不能假借学术自由的名义公然反抗公认的道德规范,造成社会失范。因为一个社会的首要功能是维护其现存秩序,它要防止一些学者的乱说乱动。
希尔斯对学术自由的区分,为探讨学术自由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学术自由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为真理而存在,它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问题交织在一块。尤其与政治的关系更为敏感,这是在研究学术自由时所无法回避的。希尔斯对此也一笔带过,很少论及其中厉害关系。现代国家,政府、教会、学术团体极少再对纯粹学术问题指手划脚,但常常通过大学管理者,对学术事务的处理施加影响。这就牵扯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的另外一对矛盾关系:大学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
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中世纪大学享有类似行会的高度自治权,而学者个体却鲜有学术自由。[6]而大学如受到政府或教会的绝对控制,没有一点自主权,外界力量会直接越过大学行政当局,置学者于严密监控之下。因此学术自由又必需以大学自治为前提。在当代社会,大学不得不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完全的行会式自治已不可能。而学术自由已成为普遍接受的法则,国家权力机构通过立法形式确认大学和政府的权利义务关系,保证不干预学术事务,确保大学行政管理和学术自治的独立性。
但由于大学这种知识生产部门的特殊性,即使在西方自由、民主、多元化的社会,政府也试图介入到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复制过程中去。[7]这种介入通过人事任命的方式,决定大学的行政管理者,再通过他们施加对学术事务的影响。在大学的权力架构中,行政权力可能被放大,危及到学者的学术自治。中国高校就存在这种权力失衡现象: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过小。法律对学术自由的界定一般都是界限模糊的,学者实际享有的学术自由具体体现在大学的实施层面。如果行政权力大到可以经常性干涉学术事务,那么学术自由的法律条款就成了一纸空文。因为学术自由最终离不开学术权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