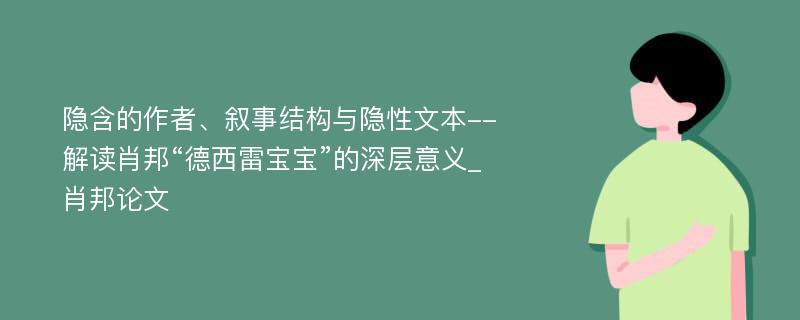
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肖邦论文,婴孩论文,文本论文,意义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隐含作者”( implied author) 是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来的概念。所谓“隐含作者”就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西方传统批评强调作者的写作动机,学者们往往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史料考证,以发掘和把握作者意图。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视作品为独立自足的文字艺术品,不考虑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历史语境。布思所属的芝加哥学派与新批评发展同步,关系密切。两者都以文本为中心,但也存在重大分歧。芝加哥学派属于“新亚里士多德派”,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摹仿学说中对作者的重视。布思的《小说修辞学》旨在系统研究作者影响控制读者的种种技巧和手段。该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正值研究作者生平、社会语境等因素的“外在批评”衰落,关注文本自身的“内在批评”盛极之时。(注:当时新批评已经衰退,结构主义和形式文体学等其他“内在批评”则正在勃兴之中。)在这样的氛围中,若对文本外的作者加以强调,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于是,“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就应运而生了。(注:在2003年10月于美国哥伦布举行的“当代叙事理论”研讨会上,布思说明了当初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的四种原因:(1)对当时普遍追求小说中的所谓“客观性”(作者隐退)感到不满;(2)对学生将叙述者和作者相混淆感到忧虑;(3)为批评家忽略修辞和伦理效果而苦恼;(4)人们在写作或说话时,常常以不同面貌出现。布思没有提到此处所说的“社会历史原因”,有避重就轻之嫌。布思讲完后,笔者马上发问,提出了这一原因,布思当众表示完全认可。就布思自己提及的四个原因而言,前三个原因都无法说明为何要提出“隐含作者”这一概念,因为谈“真实作者”就可以解决问题。只有布思提到的第四个原因和这一“社会历史原因”才能真正说明为何要提出“隐含作者”来区别于“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完全以作品为依据,故符合内在批评的要求,同时,它又使批评家得以探讨作品如何表达了作者的预期效果。这一概念提出后,在西方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笔者认为,应同时关注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不可偏废。西方学界传统上只重视真实作者,后又矫枉过正,一味关注隐含作者,忽略作者的生平和社会语境对作品的影响。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政治批评的发展,真实作者和创作语境重新受到重视,“隐含作者”的概念则受到强烈冲击。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1],与真实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真实作者的了解往往有助于对隐含作者的把握,对两者之关联的认识对于深入研究作品也大有裨益。值得强调的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往往会隐含作者的不同立场。但是,西方和国内学界均易对某一作者的立场形成某种固定的看法,从而影响了对作品之间差异性的认识,而这种差异性往往是具体作品的潜藏文本(隐藏于表层意义之下的深层意义)的重要载体。若要解读作品的潜藏文本,就需要摆脱阐释定见的束缚,全面深入地考察作品的叙事结构与主题意义的关联。此外,还需要将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相结合,探讨作品隐含的立场与真实作者的关联。
二、肖邦作品中的不同隐含作者
凯特·肖邦( Kate Chopin,1851~1904) 是美国南方重要女作家,擅长描写地方色彩,也十分关注女性经验。她18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觉醒》,大胆描写女主人公对传统的反叛,对自我发展和性爱幸福的追求,具有较强的早期女性主义意识,遭到当时保守的批评界的攻击和出版界的抵制。为此肖邦的创作和出版均受到影响,她本人也长时间被忽视和遗忘。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妇女运动的兴起,肖邦才重新得到批评界的重视,被尊为早期女性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若仔细考察肖邦的不同作品,会发现其中隐含着大相径庭的意识形态立场。就性别问题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1.以《觉醒》和《智胜神明》(1889)为代表,提倡妇女的自我发展,反对男权压迫。即便描写传统女性,也只是作为一种衬托。2.以《懊悔》(1894)为代表,提倡传统妇道,倡导回归家庭。3.以《一双丝袜》(1896)为代表,对无私忘我的母亲角色既同情又反讽。4.以《一小时的故事》(1894)为代表,表面上看具有较强的女性主义意识,实际上对追求自由的女主人公不乏反讽,立场相当保守。5.以《黛西蕾的婴孩》(1892)为代表,是性别问题与种族问题相交织的作品。表面上是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而实质上褒白贬黑,在潜藏文本中为白人奴隶制辩护。
在这五类作品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可谓直接对立。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智胜神明》( Wiser than a God) 和《懊悔》( Regret) 。前者的女主人公出身贫寒,却拒绝了富家子弟的求婚,凭藉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成为著名钢琴家。在此,肖邦以赞赏的态度描述了女主人公对家庭桎梏的抗拒,对个人成长的追求。与此相对照,在《懊悔》中,肖邦却对摆脱了家庭束缚的女主人公大加反讽。这位女主人公行为穿戴都十分男性化,年至五十依然独身,只是以一只狗、一把枪、“一些家禽、几头母牛、一对骡子”为“她的伴侣”。然而,在受邻居所托,和邻居家四个年幼的孩子相处了两周之后,她开始产生出浓厚的母爱,孩子被接走时,她对独身懊悔不已,“她的啜泣好像在撕扯着她真正的灵魂”。这一懊悔的结局与“懊悔”这一题目相呼应,明确表达出肖邦对母子亲情、家庭生活的肯定和重视。《懊悔》从题目到故事都与《智胜神明》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为何会产生这种差异,可从肖邦的生活经历中找到部分答案。(注:除了另有说明,本文中有关肖邦经历的信息,均来自Per Seyersted,Kate Chopin:A Critical Biography和Helen Taylor,Gender,Race,and Region。诚然,作者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信息和想像创作出与自己的生活无关的作品,但作者的创作也往往与其经历不无关联。)肖邦在父亲和曾祖母的影响下,性格独立,还受到同时代的各种早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故具有较为鲜明的女性自我意识。但她毕竟生长于19世纪后叶保守的美国南方,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她早育多子,深深的母爱导致《懊悔》这种颂扬母子亲情的作品的诞生。然而,作为六个孩子的母亲,肖邦也深知繁重家务对女性事业发展的阻碍,因此会写出《智胜神明》这样的作品。肖邦31岁时,由于丈夫突然去世,不得不独当一面,获得了自我成长的机会,可对丈夫的眷念有时又使她宁可放弃自己“真正的成长”,只要能换得夫君回。[3] (P183)了解了肖邦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肖邦有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早期女性主义意识,有的却不涉及性别政治,有的甚至与女性主义背道而驰。总之,我们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去看一个作者的不同作品,而应当关注每部作品的“隐含作者”。
当代批评界对肖邦的内在矛盾性和其作品之间立场的差异性缺乏认识,普遍视肖邦为进步作家,忽略上面区分的第二和第三类作品,聚焦于第一、第四和第五类作品,将这几类一概视为进步作品。然而,若全面深入地考察,也许会发现第四和第五类作品中存在表面文本和潜藏文本、浅层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对立,表面进步,实质则正好相反。阐释定见及其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两类作品的深层意义。笔者曾撰文对第四类作品中的代表作进行了探讨(注:参看申丹《叙事文本与意识形态——对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的重新评价》,《外国文学评论》,2004(1)。),揭示了作品隐含的多重反讽和深层内涵,本文将聚焦于第五类作品中的代表作《黛西蕾的婴孩》。在这一类作品的表面文本中,性别政治与种族政治相交织,但在潜藏文本中,呈相反走向的种族政治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置换了性别政治。
三、《黛西蕾的婴孩》之潜藏文本
《黛西蕾的婴孩》是肖邦最有名的作品之一。黛西蕾看上去是典型的白人,但属于身份不明的弃婴。她在白人养父母家长大,嫁给了家族显赫的农场主阿尔芒·奥比尼,可她所生的儿子很快显现出黑白混血的特征,母子因此遭到阿尔芒的无情抛弃,痛苦至极的黛西蕾抱着儿子绝望自杀。阿尔芒准备焚烧黛西蕾母子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自己的母亲写给丈夫的一封信,得知其实自己才是黑人母亲的后代。这一作品得到了西方学界的较多关注,以往的评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1.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反男权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进步作品[4],黛西蕾代表了这双重压迫之受害者的形象[5] (P160),作品莫泊桑式的出人意料的结局强有力地说明种族主义是如何不合情理[6] (P25—26),就反种族主义这一主题而言,这一作品跟《汤姆叔叔的小屋》同属一类[7] (P145)。2.有的学者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作品反种族主义和男权压迫的立场仅限于表意层次,社会颠覆性不够强[8],作品具有较强的意义不确定性[9]。(注:后结构主义学者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黛西蕾究竟是白人还是混血?但他们都承认受莫泊桑影响很深的肖邦笔下的故事结局是莫泊桑式的(其特点为突然转折,颠覆先前的假定)。作品的戏剧性主要在于:黛西蕾生下混血儿后,阿尔芒断定她有黑人血统,然而结局却揭示出其实阿尔芒才有黑人血统。这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个问题:黛西蕾究竟是自杀身亡还是走上了独立生活之路?被阿尔芒抛弃后,极度绝望的黛西蕾连拖鞋和睡衣都没换,抱着婴儿消失在“水很深的”河边“那茂密的芦苇和柳树丛里”,“再也没有回来”。在此之前,极其柔弱的黛西蕾给养母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会死去。我非死不可。这样痛苦,我实在没法活下去。”在解构主义出现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人将作品中的这些因素视为不确定。19世纪末的肖邦毕竟是为尚未受到解构主义怀疑论熏陶的读者写作。)3.有的学者抛开种族问题,仅仅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切入,探讨阿尔芒代表的男权力量对黛西蕾代表的女性的压迫,以及后者摆脱压迫的努力[10]。4.有的学者从结构形式上切入作品。如埃里克森就聚焦于作品中的童话成分与“表象与现实之间的对立”这一主题的关联,探讨这一反奴隶制的作品如何借鉴和偏离了(读者阐释期待中的)童话故事的结构框架[11]。5.有的学者从心理角度切入《黛西蕾的婴孩》,认为作品“超越了社会含义,探索的是人格中的阴暗面”[12] (P222),阿尔芒代表了“人类共有的”内心罪恶的潜能[13] (P133)。6.有的论著涉及了《黛西蕾的婴孩》中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在阐释中均出现了偏误。对于这一类,笔者将在第四部分中详细探讨。
若全面仔细地考察《黛西蕾的婴孩》之叙事结构,则会发现在文本的深层,种族政治呈现出一种相反的走向。作品中存在真白人与真黑人之间的两种根本对立。第一种对立涉及种族歧视。黛西蕾被误认为是混血儿后,给养母瓦尔蒙德夫人写了封绝望的信,白人养母毫不歧视,对她发出了深情的呼唤:“我的亲女儿黛西蕾:回家吧,回到瓦尔蒙德府来;回到爱你的母亲身边来。带着你的孩子。”(注:本文中《黛西蕾的婴孩》的译文均引自凯特·肖邦《觉醒》,杨瑛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157页,笔者对有些文字进行了改动。英文原文则取自Kate Chopin,A Pair of Silk Stockings and Other Stories,New York:Dover,1996,pp.1—5。)瓦尔蒙德府的主人是黛西蕾的养父,养母的呼唤显然暗含着白人养父的欢迎。阿尔芒的父亲老奥比尼身为门第显赫的白人奴隶主,却娶了黑人为妻,也不歧视混血的儿子,与残酷抛弃“混血”妻儿的黑人(注:当时的种族主义系统奉行“一滴血”原则,只要遗传了一滴黑人的血,就是黑人(见参考文献中Ellen Peel," Semiotic Subversion in' Desiree' s Baby' ," p.227)。)阿尔芒形成直接对比。孩子的有色保姆最早发现孩子的混血特征,虽然她自己是有色人种,却歧视自己的同类,也是种族主义者。黛西蕾的养母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前来看望时,“窗前坐着一个黑白混血的黄皮肤保姆,正自顾自地扇扇子”。黛西蕾向保姆问话时,“那女人庄重地( majestically) 低了低她戴头巾的脑袋,‘是的,夫人’。”副词" majestically" 含有“高贵”之意,一般不会用于描述奴仆的行为,作品似乎在借之反讽有色保姆在自己“同类”面前表现出来的傲慢。也就是说,在这一故事里,白人没有种族歧视,有黑人血统的人才有种族歧视。
第二种对立涉及人种的本质:白人品质优良,而黑人则品质低劣。这种对立由三对镜像人物来体现:1.白人老农场主与混血新农场主之间的性格对立;2.白人妻子与混血丈夫之间的性格对立;3.白人少妇与黑人婆婆(以及白人养母与黑人婆婆)之间的性格对立。第一对镜像人物之间的对立由叙述评论来直接表达:“年轻的主人阿尔芒·奥比尼的统治……是严酷的,他手下的黑人早已忘记了快乐,而在老主人随和( easy-going) 宽容( indulgent) 的统治下,快乐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形容词" indulgent" 常用于描述家长对孩子的溺爱,似乎在暗示老主人对黑奴家长般的关爱,新老主人间的对照则在暗示真正的白人奴隶主是善待黑人的,只有像阿尔芒这样的假白人才虐待黑人。尽管阿尔芒是黑白混血,但文本却一再暗示他的低劣品质来自于黑人血统。不仅他的皮肤“黝黑”( dark) ,而且他的性格缺陷与他的白人父亲和其他白人都形成了直接对比。(注:阿尔芒只继承了白人父辈的一个特点:对未来的妻子一见钟情,在其他方面都与父亲形成了鲜明对照。就一见钟情这点而言,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也为老主人娶黑人为妻作了铺垫,同时也可能是一种障眼法——“奥比尼家所有的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坠入情网的”,仿佛阿尔芒跟纯白人血统的父辈是一回事。)至于阿尔芒与白人妻子的性格对立,文中有这么一段叙述议论:“结婚,以及后来儿子的出生,大大软化了阿尔芒·奥比尼那专横霸道、苛求严厉的禀性( nature) 。这就是温柔的黛西蕾之所以感到快乐的原因……自阿尔芒看上她那一天起,他那张英俊黝黑的脸就很少由于皱眉而显得丑陋了。”白人血统的黛西蕾是“美丽温柔、慈爱真诚”的天使,对黑奴充满爱心,与阿尔芒的白人父亲性格相似。而有黑人血统的阿尔芒则是恶魔般的人物,在黛西蕾的影响下才暂时变得善良。当黛西蕾被误认为“混血”后,阿尔芒疏远了她和儿子,与此同时,“在对待黑奴的态度上,仿佛魔王撒旦的精神突然控制了他”。不少学者仅从“爱情”这一角度来看阿尔芒的变化:爱情使他变好,而失去爱则使他重新变坏。[8] (P236)然而,在潜藏文本中,隐含作者很可能在暗示优越的白色人种的感化力:与温柔慈爱的白人女子接近就能变好,与之疏远则反之。这种暗示似乎也见于阿尔芒与白人父亲的关系,他在父亲去世后才接管农场,文中没有描述他在此之前如何对待黑奴,他也很可能是在失去父亲的感化之后才表现出专横冷酷的天性。作品刻意突出了误认为黛西蕾为混血之后的阿尔芒如何不通人性:“‘阿尔芒’,黛西蕾喊他,那声音简直会像一把利刃直插他心窝,假如他还是个人。但他不予理睬……”。作品还进一步将阿尔芒对妻子的残忍描述为魔王撒旦与上帝的对抗:“可当他这样狠狠刺伤妻子的心灵时,他又觉得,他好歹也同样狠狠地回敬了上帝[对他的不公]。”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天使般的白人黛西蕾与上帝同为一方(注:正如很多西方学者注意到了的,肖邦将自杀途中的黛西蕾暗喻为头上有光环的殉难圣徒:“她没有包头,让头发披散着,太阳光照在那褐色的丝缕上,反射出一圈灿烂的金光。”),与撒旦般的黑人阿尔芒构成对立的双方。(注:作品多处暗示黑白位置或种族秩序是上帝的安排,任何想要颠覆这一秩序的企图都只能是徒劳的,任何对主的安排的挑战——就像阿尔芒觉得自己仿佛狠狠地回敬了上帝对他的不公——都只会遭到命运的报复和嘲弄。)2.阿尔芒对上帝的敌意很容易加重西方的基督教读者对这位黑人的不满。
黛西蕾与她的黑人婆婆构成了另一对性格对照的镜像人物,这一镜像关系又通过她的白人养母与黑人婆婆之间的对照得到加强。黛西蕾一切以丈夫为重,“她爱他爱得那么痴迷。他一皱眉,她就发抖,可仍然爱他。他一微笑,她就认为上帝赐给了她最大的福祉”。前文提到了肖邦在立场上的矛盾性,一方面倡导妇女独立,一方面颂扬传统妇道。黛西蕾如此缺乏自我意识固然令人感到遗憾,但她对丈夫忘我的爱也体现了一种传统美德。她无私忘我地爱丈夫,而丈夫却残忍地将她抛弃。与黛西蕾相比,她的黑人婆婆也显得不负责任:
瓦尔蒙德夫人有四星期没见到黛西蕾和她的婴孩了。她到达拉布里府时,一眼瞥见那宅子,就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每次来这里,她都有这种感觉。那地方看起来真够凄凉的。许多年来,它得不到一位女主人的温婉( gentle) 照料(注:肖邦没有用" gentle" 一词来直接修饰“女主人”,这很可能与她对这位黑人女主人的看法有关。)。老奥比尼是在巴黎娶的妻,又是在巴黎埋葬了妻子。那位夫人太爱自己的故土( loved her own land too well) ,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里。
“不负责任”是当时白人眼中黑人的一个典型特征[16],也是肖邦在刻画黑人时通常加以强调的一个特征。[2] (P80)黛西蕾的黑人婆婆未能到丈夫的府上尽妻子之责。诚然,从情节安排来说,当地人物必须对阿尔芒母亲的血统不知情,这样才会有结局的出乎意料。此外,作品描写的美国南方尚处于奴隶制时期,也无法容纳这种白人和黑人明媒正娶的婚姻。但作者完全可以给出另一种借口,譬如阿尔芒的母亲在巴黎患病,无法到先生的府上来尽责。即便给出同样的借口,叙述语气也可以较为同情或较为中性,而文中实际出现的文字却带有指责的意味,(注:副词" too" (“太”、“过于”)带有明显的贬义。试比较:“非常”爱自己的故土。)使读者对这位缺席的女主人产生一定的反感。作品没有直接描述黛西蕾的白人养母瓦尔蒙德夫人如何尽妻责,但通过描述她对拉布里府之凄凉的反应(不寒而栗),作品显然在暗示她的性格与黑人亲家正好相反。“不负责任”这种白人眼中黑人的性格缺陷是黑人阿尔芒母子共有的。黛西蕾的白人养父在阿尔芒向养女求婚时,希望阿尔芒“认真考虑”黛西蕾来历不明的问题,而阿尔芒却“毫不在乎”。这似乎也从侧面说明白人负责,黑人不负责。我们还可以透过文本的表象,进一步看到阿尔芒与黑人母亲的相似之处:阿尔芒在误认为黛西蕾为混血之前,是深爱妻子和儿子的(这很可能是受到充满慈爱的白人妻子感化的结果),但一旦认为妻儿是混血,就残忍地将之抛弃,这是典型的不负责任。阿尔芒的母亲也深爱丈夫和儿子(这也很可能是受到充满慈爱的白人丈夫感化的结果),而既然文本暗暗责备她未尽女主人之责,那么也就可以推断,倘若她处于跟儿子类似的情形中,也很可能会像儿子那样不负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的引语将拉布里府的凄凉完全归罪于阿尔芒的黑人母亲,根本未考虑拉布里府这两年的白人女主人黛西蕾。这里可以看到作者不顾事实,让景物描写为自己的立场服务。紧接上面的引语出现了下面这段文字:
这房子,陡峭的屋顶,黑压压,僧帽似地覆盖着环绕黄色灰泥房屋的宽大回廊。阴森森的巨大橡树,围绕在房子四周,挨得很近,那伸得长长的枝条、密密层层的叶子,棺材罩般地罩在屋上。年轻的主人阿尔芒·奥比尼的统治也是严酷的( Was a strict one,too) ,他手下的黑人早已忘记了快乐,而在老主人随和宽容的统治下,快乐是他们习以为常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通过增加一个副词" too" ,前面再加上一个加重语气的逗号,作品不仅制造而且强调了黑人阿尔芒的严酷统治与阴森景物之间的关联。此外,作品将阿尔芒的冷酷无情与老主人的温暖慈爱相对比,又从逻辑上消解了白人老主人与这一象征性景物之间的关联。棺材罩布的意象仅跟阿尔芒相关,显然指向阿尔芒造成白人妻子和其子死亡的结局。这一凄凉阴森的景物描写也加强了阿尔芒与黑人母亲的关联,后者被指责为造成这种凄凉状态的唯一原因,前者则被描写为与这种阴森景象性格相通的唯一人物。作者通过采用“隐去不提”和“直接对照”的手法,解脱了处于同样位置的两位白人与这一凄凉阴森景物的关联,从而加强了阿尔芒的低劣品质来自于黑人母亲的暗示。
看到隐含作者精心制造的这种种“黑白对立”之后,不难意识到《黛西蕾的婴孩》是为白人奴隶制辩护的作品。在这一虚构的奴隶制社会里,白人温良慈爱,黑人残酷无情;白人尽职尽责,黑人不负责任。这是在赞美白人的种族优势,抨击黑人的种族劣根性。奴隶制的主要特征为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在肖邦的笔下,出现了黑白分明的两种奴隶制天地。在以白人为主人的天地中,既无种族歧视,也无种族压迫,(真假)黑人不是成为白人的妻子,白人的“亲”女儿,就是受到白人家长般的关爱。与此相对照,在以(真)黑人为主人的天地中,(真假)黑人则受到(真)黑人主人严酷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失去快乐,遭到抛弃,乃至丧失生命。作品很可能在暗示:黑人的种族劣根性才会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地狱,而白人的种族优势则使奴隶制成为黑人的天堂。
为了进一步看清作品的潜藏文本,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作品的最后一段文字:
几星期后,拉布里府上演了古怪的一幕。在打扫得光光的后院中央,燃起了一大堆篝火。阿尔芒·奥比尼坐在俯瞰这幕景观的宽大过厅里,就是他在指挥五六名黑人往篝火上扔燃烧材料。篝火上原已堆满了大批极其贵重的婴儿衣物,又扔上一只精致优雅的柳条摇篮,连同它的全套精美的附加物。接着扔上去的是丝绸女衫,还有丝绒的和软缎的,还有花边、绣品、女帽和手套。那批结婚礼物都是质地十分精良的。最后要扔到火堆上的是一小捆信,那是黛西蕾在他俩订婚期间写给他的天真无邪的小小手札。在存放这些信的抽屉的最里面,还留有一封信。但那不是黛西蕾写的,而是他母亲写给他父亲的信的一部分。他读了这封信。信中,他母亲感谢上帝赐给了她丈夫的爱:——“我日夜最最感谢上帝的是,”她写道,“他如此妥善地安排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亲爱的阿尔芒永远不会知道,我这个深爱他的母亲,原来是遭受奴隶烙印之灾难( cursed with the brand of slavery) 的种族的一员。”
英文" cursed" 不仅有“遭到诅咒”、“遭受不幸”之意,而且还有“应该遭咒”( deserving a curse) 之意。[15] (P56)诚然,阿尔芒的黑人母亲在写下" cursed with" 时,不会暗示让黑人沦为奴隶是应该的,而只会表达“不幸”之意,但作者如此措辞,则有可能是利用那一词义来暗暗为南方奴隶制辩护。阿尔芒的母亲身为黑人,是她命运的不幸,但上帝解救了她,赐给她白人丈夫的爱(请注意作品再次把白人和上帝描述为同一方),白人丈夫也爱混血的儿子(“我们亲爱的阿尔芒”)。在这一虚构世界里,白人给予有色人种无私的爱,而有色人种却不予回报。阿尔芒的母亲因为“太”爱自己的故土而未到先生的府上尽责,阿尔芒的父亲则抛家在异国陪伴妻子终身。下一代更是如此,黛西蕾给了阿尔芒忘我的痴爱,得到的却是丈夫的无情抛弃和绝情焚烧遗物。在上引片段中,出现了倒叙的手法,阿尔芒是在拿黛西蕾的信时读到他母亲的信的。也就是说,他先发现了自己的黑人血统,然后才坐在过厅里,指挥黑人焚烧收集来的遗物,但叙述次序则正好相反。不少学者忽略了这一倒叙,误认为阿尔芒在焚烧遗物时依然以为自己是白人,他的这一行为是为了净化自己的白人血统[7] (P140),因此这一场景构成对白人种族歧视之极端行为的抨击。其实,情况正好相反。这里描述的是以黑人血统为标志的阿尔芒对白人弱女子黛西蕾进一步的绝情和迫害。作品中用了较多笔墨来刻画黛西蕾的衣物和其象征的柔弱,譬如,黛西蕾抱着婴儿往河边自杀的路上走去时,“没有换下她身上单薄的白色衣衫和脚上的拖鞋……她穿过一片荒弃的田地,地上的残梗,戳伤了她非常纤巧的鞋子里柔嫩的双脚,把她薄薄的衣裳撕成碎条”。衣物的纤弱和人物的纤弱紧密相联,难以分离。“把她薄薄的衣裳撕成碎条”的描写强化了黛西蕾被残害的悲剧。从这一角度,不难理解作品为何会渲染对黛西蕾母子衣物的焚烧:“又扔上一只精致优雅的柳条摇篮,连同它的全套精美的附加物。接着扔上去的是丝绸女衫,还有丝绒的和软缎的,还有花边、绣品、女帽和手套。”在这样的细节描写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黑人阿尔芒对黛西蕾母子本身的摧残。这种摧残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也是情感上的:“最后要扔到火堆上的是一小捆信,那是黛西蕾在他俩订婚期间写给他的天真无邪的小小手札。”从这一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采用的强调句式" it was he who dealt out to a half dozen Negroes the material which kept this fire ablaze" (就是他在指挥五六名黑人往篝火上扔燃烧材料)——“黑色”主子和黑人奴隶在联手实施对白人血统的身心迫害。叙述者采用了“古怪”( curious) 一词来形容这一场景,似乎在暗示只有黑人才会如此不近情理。(注:这一场景也可理解为已经知道自己有黑人血统的阿尔芒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当众焚烧妻儿的遗物,从而制造自己作为“白人”丈夫与“混血”妻儿进一步决裂的假象。但若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必要通过细节描写暗暗建立“衣物的纤弱=人物的纤弱”、“焚烧母子衣物=对母子的进一步摧残”这样的关联。)
在阅读《黛西蕾的婴孩》时,读者一般都对黛西蕾倍感同情,对阿尔芒十分反感。以往的批评都从以下三个方面找原因:1.天使般的黛西蕾与魔鬼般的阿尔芒在性格上的不同;2.男权对妇女的压迫;3.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但倘若能打破阐释定见的束缚,穿过作品的障眼法,就能看到潜藏文本中一个更为根本的对立:白人受害者和黑人迫害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表层的种种对立。在潜藏文本中,黛西蕾和阿尔芒的性格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白人的种族优势和黑人的种族劣势之间的差异;男权对妇女的压迫也在很大程度上为(真正的)黑人血统对(真正的)白人血统的压迫所置换;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则被颠覆成了(真正的)黑人血统对黑人血统的歧视和(真正的)黑人血统对(真正的)白人血统的迫害。
四、真实作者、叙事结构、阐释定见
隐含作者是从作品中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深入考察《黛西蕾的婴孩》的叙事结构,我们发现其隐含作者在种族问题上是非常保守的。若要更好地了解作品的立场,还需要进一步考察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关联。肖邦1851年出生于美国南方的一个富商家庭,10岁时,南北战争爆发,她的家庭和闺中好友的家庭都站在南方奴隶制一边。他们居住的圣路易斯城当时处于北方联邦的铁腕统治之下。与肖邦感情甚笃的同父异母兄弟冲破高压,参加了捍卫奴隶制的南部联盟的部队,后被捕入狱,死在出狱返家的途中,他的死给了肖邦很大的打击。肖邦自己则冒着坐牢的危险,将北方人系在她家门口的联邦旗帜扯了下来,还和女伴一起去监狱给南方俘虏送花。肖邦的娘家有很多黑奴,公公是残酷无情的农场奴隶主,丈夫是种族主义“白人同盟”活动的积极分子,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丈夫死后,肖邦自己也当过一段时间农场主。肖邦的成长背景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 迥然相异。斯托在美国东北部长大,年少时曾受到父亲学校里反奴隶制情绪的感染,在访问肯塔基州时观察到黑奴的生活状况。1850年搬到美国东北角的缅因州之后,进一步受到反奴隶制讨论的影响,开始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是站在北方的立场上,为了提高民众的反奴隶制意识而创作,而肖邦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不难看出,《黛西蕾的婴孩》中多种褒白贬黑的“黑白对立”与肖邦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肖邦创作时,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已经废除,种族主义遭到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公然为其呐喊,而只能暗暗加以辩护。种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为人种优劣论。美国南方奴隶制时期不少哲学家、法学家和伪科学家都纷纷著书立说,宣传白人血统优于黑人血统[14] (P79—80),以此维护白人对黑人的统治。肖邦则在《黛西蕾的婴孩》中,虚构了种种“黑白对立”,为人种优劣论提供支持。这一作品也为白人主子善待黑人奴隶的神话提供了支撑。在现实生活中,肖邦的白人奴隶主公公对待黑奴十分严酷,但在肖邦的笔下,黛西蕾的白人奴隶主公公却成了慈爱的化身,黛西蕾本人也对黑奴慈爱有加。
挪威学者Per Seyersted和英国学者海伦·泰勒对肖邦的生平和创作语境进行过专门研究,但他们均未对《黛西蕾的婴孩》的叙事结构加以全面深入的考察。Seyersted用颇为中性的眼光来看这一作品,认为尽管肖邦对“混血人”黛西蕾遭受的厄运愤愤不平,但由于文中很强的戏剧性,这一短篇更像是莫泊桑笔下的作品。[2] (P94)Seyersted显然对肖邦的种族主义立场感到不安,一方面轻描淡写地分析肖邦有的作品中的种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不时为肖邦辩护,甚至凭空得出了“她显然不赞成奴隶制”这样的结论[2] (P93)。泰勒对这一无根据的结论提出了批评,指出肖邦持有完全正统的南方种族观,“种族主义是她写作中的一个中心因素,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简单为其开脱”[16] (P155—156)。遗憾的是,泰勒也未对《黛西蕾的婴孩》的叙事结构进行全面考察,未看出文中多种“黑白对立”,因此也出现了偏误。她将情节简要介绍为“因生了个黑色婴儿而遭受耻辱的妻子自杀了(后来她的丈夫才发现孩子的黑色血统源于他自己的混血)”[16] (P166)。泰勒认为肖邦之所以让女主人公自杀,是出于以下两种原因:“一方面或许是出于种族主义的原因,避免人们怀疑在路易斯安那的白人社区里有混血的人存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不可能从为社会所弃的人转化为幸福的新娘”,因为女主人公“无法应付社会驱逐和[作为女性]无可避免的社会边缘位置”。[16] (P50)笔者对此难以苟同。倘若第一种原因成立,那么肖邦就应该让阿尔芒这个真正的混血儿去死,而不是让黛西蕾这个真正的白人去自杀。第二种原因是存在的,但聚焦于妇女的边缘位置很容易掩盖文中更为根本、更为中心的种族政治。
凯瑟琳·伦迪也十分了解肖邦的生平,但她同样未对《黛西蕾的婴孩》的叙事结构加以全面深入的考察,仅仅从黑人妇女如何受到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这一角度切入,(注:伦迪解释道:尽管读者最后发现黛西蕾很可能不是黑人,但由于情节围绕着大家都以为她是黑人这点展开,因此她的探讨也以此为基础。)因此没有看出作品的潜藏文本,评论中也出现了前后矛盾。伦迪指出肖邦在这一作品中同情的并非黑人妇女,而是白人妇女,这个天使般的白人妇女被一个品质恶劣的黑人男人错误判断和宣告有罪。[17] (P134)但伦迪的总体评价却是:“读者和批评家均认为作品表达的是种族主义和奴隶制造成的悲剧,其实作品表达的是更为具体的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悲剧。身为黑人和女性所遭受的损害大大超过身为黑人和男性所遭受的损害。”[17] (P131)类似的前后矛盾也见于埃米莉·托特的阐释。托特一方面强调作为农场主的阿尔芒是黑人,另一方面又说阿尔芒是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体现了白人奴隶主“无可避免”的性格特点。[18] (P205—206)这完全忽略了(黑人)阿尔芒与白人父亲的性格对立。像这样的前后矛盾很可能源于“肖邦是进步作家”的阐释定见与文本事实的冲突。阐释定见的力量不可低估。美国学者鲍尔十分关注《黛西蕾的婴孩》的历史语境,对肖邦所在的路易斯安娜州南北战争前的法律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受当代阐释框架的影响,鲍尔认定肖邦是反种族歧视的进步作者。[19] 她首先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阿尔芒从少儿时起就知道自己是混血儿。(注:鲍尔认为阿尔芒早在结婚前就读到了母亲的那封信。且抛开莫泊桑式的结局不谈,作品叙述阿尔芒读信时采用的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一般过去时,说明他是在拿黛西蕾的那一小捆信时第一次读到母亲的那封信。)然后她凭空断言肖邦是在为两类迥然相异的读者写作:一类是肖邦同时代的“心胸狭窄的”读者,他们会将阿尔芒魔鬼般的性格与他的黑人血统相联,另一类是心胸宽广的读者,他们会认为阿尔芒的残忍源于害怕自己的黑人血统被发现,从而被剥夺继承权,甚至根据当时的法律而沦为奴隶。[19] (P174)从这一角度,鲍尔将阿尔芒描写成被社会环境扭曲了性格的受害者(注:其实,肖邦采用了" nature" (秉性)一词来暗示阿尔芒的低劣性格是与生俱有的。),乃至美化成“尚未到来的新的南方的文化英雄”[9] (P81),这一作品也就成了揭示“奴隶制所造成的后果”的进步作品。[19] (P174)这显然是将当代的阐释定见通过一种凭空设定的读者而强加给了肖邦。
不仅学界的共识构成阐释定见的枷锁,而且学者自己对某位作家形成的大一统的看法也构成一种阐释障碍,影响对该作家不同作品之差异性(不同隐含作者)的把握。泰勒认为肖邦以及处于同样历史环境中的另两位白人女作家均同时表现出性别问题上的进步性和种族问题上的保守性。[16] 然而,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很可能隐含大相径庭的立场。如前所述,肖邦在性别问题上并非立场一致,而是有时进步,有时保守。(注:学界一般认为在性别问题上,肖邦的后期作品比前期作品进步。其实情况没那么简单,这一点从本文涉及的几篇作品就可见出:《智胜神明》(1889);《懊悔》(1894);《觉醒》(1899),这三篇作品呈现出“进步—保守—更为进步”的曲折走向。)在种族问题上,肖邦的不同作品也同样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肖邦的《贝尼图家的奴隶》(1892)和《超越贝游河》(1891)。前者的主人公是一位黑人大叔,50年前曾是贝尼图家的奴隶,后几经转手,现已获得自由。但他一心想回到贝尼图家做奴仆。贝尼图家的人为了“这个老黑人自己的安全和幸福”而收下他当仆人;“这个老黑人”则从中获得“自我满足”,并逢人便告“我属于贝尼图家”。这无疑是怀恋南方奴隶制的作品。另一短篇的主人公是一位黑人大妈,小时候精神受了刺激。作品聚焦于这位黑人大妈与农场主的小儿子亲如母子的深厚感情,重点描述了这位黑人大妈如何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毅力把负伤的男孩安全送到了家,(注:作品没有提到男孩和其父的种族,但明确提到男孩的" black curls" (黑色卷发),有可能涉及的是黑人之间的关系。在奴隶制时期,肖邦所处的路易斯安娜州也有不少自由的有色人当农场主,但种族之间的通婚是法律禁止的( Virginia R.Dominguez,White by Definition,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26) 。)在这一过程中,她克服了自己多年来不敢走过贝游河的心理障碍,获得了新生。这是一篇正面描述黑人妇女的作品,很可能与肖邦自己的黑人保姆有关,肖邦作为母亲与这位黑人妇女也可能有某种心理上的认同。两篇故事的题目也很说明问题:“贝尼图家的奴隶”聚焦于奴隶身份和从属关系,主人公是扁平的黑奴代表;“超越贝游河”则指涉主人公克服自己心理障碍的过程,人物有血有肉,有令人赞叹的优良品质,而主人公身为黑人的种族属性又使作品带上了某种进步性。(注:美国南方白人作家创作的怀恋奴隶制的作品中,常常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黑人保姆,这一形象对将奴隶制神话化起了一定作用。但其他作者笔下的黑人保姆往往是以善良宽厚的母爱为唯一特征的扁平型象征人物,笔者认为肖邦笔下的这一黑人保姆在本质上与众不同。)
五、结语
文学作品的解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通常会遇到很多阐释陷阱,关于作者的阐释定见往往构成一个最大的陷阱。若要避免陷入其中,我们不妨首先尽量抛开成见,对作品的叙事结构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判断这一作品本身隐含的立场,然后再阅读先前的评论、有关作者生平和创作语境的资料以及该作者的其他作品。不少西方学者拘泥于阐释定见和表面文本,将《黛西蕾的婴孩》这一本质上为奴隶制辩护的作品解读为反奴隶制或揭露人类阴暗心理的作品,尊其为肖邦“最成功的”[7] (P139)、“最好的短篇”[13] (P133)作品,甚至称之为“世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20] (P73),不能不说是一种批评的遗憾。这一作品之所以会得到西方历代批评家和选集主编的广泛赞赏,恐怕其表层文本和潜藏文本都起了作用。表层文本的戏剧性(尤其是莫泊桑式出人意料的结局)和悲剧性(父权和种族双重压迫导致的一个弱女子及其婴孩的死亡)对读者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此外,潜藏文本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立场也迎合了白人读者集体无意识中的种族优越感。然而,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当代西方读者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倘若发现了《黛西蕾的婴孩》的潜藏文本,应当会改变对这一作品意识形态立场的评价。总而言之,只有打破阐释定见的束缚,全面深入地考察作品的叙事结构,关注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关联以及该作品的隐含作者与其他作品的隐含作者之间的关联(不同的隐含作者又往往跟作者生活经历的不同方面有所关联),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批评的遗憾”。
吴冰教授、刘建华教授和笔者文学方向的博、硕研究生拨冗阅读了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谨在此深表谢意。
